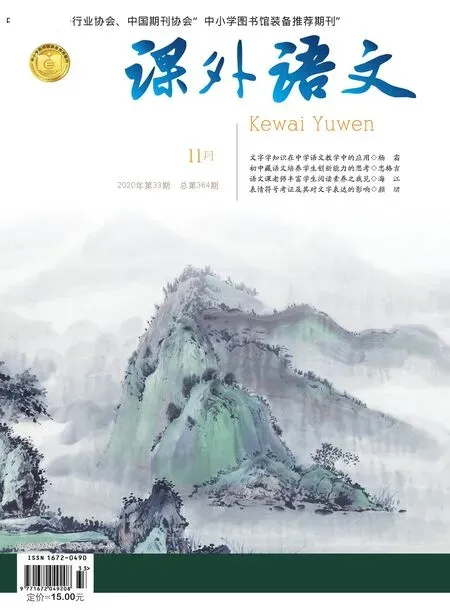散文解读的独特性探究
——以汪曾祺《昆明的雨》为例
郭 敏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学府中学,广东 深圳 518000)
新文学运动以来,文学界的旗手们皆以打破数千年的“道统”为务,小说、诗歌等以借鉴西方文学样式而呈现新的面貌,以达到与前人划清界限的目的。唯有散文,无西方文学形式可以借鉴。现代散文理论的开创者周作人破清代正统的“桐城派”,以晚明“公安派”为宗师,强调散文的“审美”特性,以呈现美的生活、抒发美的情感为宗旨。从此,中国现代散文就走上了以“美文”为主的发展道路。汪曾祺世称“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作品是沿袭了“五四”以来散文发展的主流的,《昆明的雨》即是其中的典型。
美文如何科学地品鉴其“美”?现代文学批评经历了作家中心论、作品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几个阶段。各学派有其科学性,也有其局限性。对于一部作品的解读,作家的特殊性、作品的唯一性、散文的文体特点、读者的参与等都是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的。
一、“真情实感”的特殊性
从创作论上讲,散文写作要有“真情实感”。但是“真情实感”不等于生活的实录。具体到每一篇作品中应作具体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读作品的内涵。《昆明的雨》写的是作者三四十年代在昆明就读西南联大时期的生活。文中“美”的事物很多,如倒挂的仙人掌、各种各样的菌子、火红的杨梅等等。为什么汪老先生笔下只写了这些事物而没有写其他事物?这就与他当年的细节记忆有关。在他的眼中,昆明雨季里的这些事物是美的,是能传达他心中对“美”的认知的。但是,这些“美”的事物并不等于生活中真实的存在。例如文中写到的牛肝菌,作者写到它的颜色、味道以及做法。这一切与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是分不开的。换作另一个作家,是不会这样表述的。因此,汪老先生笔下的景,是以汪老的眼光看世界的“景”,即对象的主体化。从这个角度说,只有走进作家的主体世界,走进作家的创作,才能真正感悟作家笔下所叙之事、所状之物的美。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汪老先生在文中使用了许多表现色彩的词汇,例如“浅绿”“深褐”“黑红黑红”等。因为汪老先生除了是一位散文大家,同时也是一位画家。从小师承其父的汪曾祺对绘画颇有天赋,其国画作品深得中国绘画之精髓。画家对于色彩比一般人敏感,因此,作品中出现许多表现色彩的词汇也就不奇怪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本文画面跳转很快,有点类似于电影。以第8段为例,一盘鲜香可口的牛肝菌、一个乘客下火车去捡鸡枞,牛粪般的干巴菌、类似鸡油的鸡油菌……一个一个画面接连不断地向我们眼前扑来。这种画面感极强的表现方式,也与作家本人的绘画才能相关。
前人有批评汪老先生笔下的昆明生活快乐、闲适,然而当时正处于全民族抗战期间,这样的笔调颇不相宜。诚然,《昆明的雨》展示的是一个景美、人美的和谐美好的社会,是汪老先生眼中的一片圣土。但如果把他笔下的社会等同于当时的昆明社会,就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指向。文学不是生活的实录,而是作家借文字以表达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其根本指向是审美,而不是记录。抗战爆发之初,汪曾祺从香港转至大后方的昆明,求学于西南联大。他天性乐观活泼,不以生活为苦。虽时常以粥度日,跑防空洞以躲避日寇的飞机,但这一切苦难并未改变他那颗始终乐观向上的心。其后的人生历程中虽遭遇各种挫折屈辱,汪先生一样坚强地活了下来。在一个积极乐观的人眼中,这个世界总是美好的事物更多一些。因此我们在阅读《昆明的雨》时,陶醉于他笔下那馨香的缅桂花,那个略带羞涩的卖花姑娘,那个送花给房客的女房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一切的美好看作汪先生对美好生活的讴歌与赞美。苦难中的美,更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汪老师回忆西南联大生活的其他作品,如《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上课》等,莫不如是。
从叙述视角这个角度考查,我们发现,《昆明的雨》有两个“作者”,那学生时代的“我”和写作时的“我”。本文写作时间是八十年代,是作者离开昆明之后四十余年的回忆之作。在这四十年中,作者曾被划为右派,劳动改造、被他人诬陷等,生活对于一介文人不再充满诗情画意。然而作者却一直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对于美的热爱和向往是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因此,当朋友邀请画一幅画时,作者想到了仙人掌、牛肝菌、青头菌;写杨梅,与自己后来在全国各地吃过的杨梅进行对比;写午后的雨,以至于四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不同的叙述视角让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更深刻地把握作者的所思所想。
因此,阅读一部作品,如果不靠近创作者的心灵,是无法获得真正的审美感受的。
二、含蓄的表达情致
《昆明的雨》是一篇叙事写景的散文名篇。散文作为独立于诗歌、小说的文学样式,是有其自身的独特规范的。相比于诗歌,散文更聚焦于具体的人事物景,表达也多含蓄蕴藉。相比于小说,散文更能表现真实的生活,更精准地表达作家一时一刻的主观感受。
以《昆明的雨》第10段为例。这段文字首先写到“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并引用李商隐著名的《夜雨寄北》。作者有没有乡愁呢?没有明说。但读者是能体会得到的。离家千里求学,家乡在战火中煎熬,哪个游子没有思念之情?作品继而写到与朋友去莲花池的经历。见到陈圆圆的石像,酒店里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的鸡,以及一大架木香花。这个因雨而停留在小酒店的经历,作者终身难忘,以至多年后写作本文时仍描绘得生动细致。“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这个“情味”是什么呢?或许想到自己与陈圆圆一样流落异乡,有家难回,或许因这个宁静的下午摆脱了俗世的诸多烦恼,或许什么都不是,只是沉浸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遥想每天为艰辛的生活所折磨,这个下午,这个充满诗意的下午是多么难得?散文即是如此,在表情达意方面表现得更加委婉。这就需要读者参与进来,进行有意义的解读。在接受美学大师姚斯看来,作品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要在读者阅读中实现,而实现过程即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读者在此过程中是主动的,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受作品的性质制约,也受读者制约。对于《昆明的雨》第10段的解读,不同的读者依据文本信息,可以解读出丰富的内涵。而汪先生的这部作品也因在不同读者心中留下不同的审美印象而获得永恒的价值。对于这篇散文解读的过程本身即是作品美学建构的过程,也是读者获得审美享受的过程。这,就是散文的魅力所在。
由此可见,散文的阅读如果离开读者的主体参与是无法想象的。读者只有深入作者的心灵世界,深入文字之中,才能解读出有价值的内涵。北宋苏轼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语言的短处正在于无法表达无比丰富、深刻的情意,在此情况下,作家选择了通过意象的塑造、意境的营造创设一种情境,作者与读者心灵相通,共同感受这个情境,这就是真正的审美。一部作品至此才算最终完成。
综上所述,散文阅读与散文的文体特点密切相关,也与作家的个性、创作情境、读者的解读与建构分不开。对于作品的解读,唯有进行具体科学的分析,才能获得作品的美学价值。也唯有如此,才能领会作家在文字背后传达的意义,即海明威所说的“冰山下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