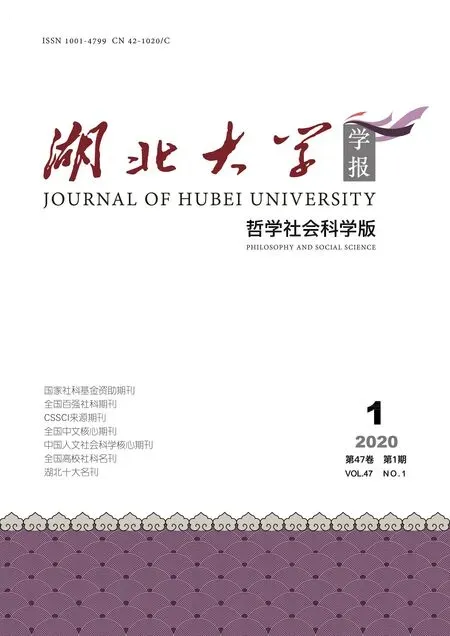现代中国“文学话”批评的生成及其体式特征
——以对话体“文学话”为例
黄念然, 杨瑞峰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文学话”是传统话体文学批评应对现代文学批评语境新变的产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进行思想改造、话语注新、结构重设、逻辑鼎革等多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综话“文学”的一种话体文学批评,“文学话”产生的先决条件是晚清以来新式“文学”范畴的确立,因而相较其他话体文学批评而言,它具有更高的综合性和特定的时代性。故此,对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的这一文学批评体式进行生成学意义上的理论溯源与风格探略,不仅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考察传统文章学的最后总结形态及其向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转型,进而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学科提供更为多元的基础文献,而且也将带动话体文学批评研究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一、古典文论的“话”性与话体文学批评
“任何理论作为对在实践中出现的某些规律性现象的整体把握,往往标志着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因此,其内部也总是存在着一个从分散到集中,从朦胧到相对清晰的过程”(1)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8页。。因此,把握“文学话”批评的生成,对其母体形态迁衍流变的历史漫溯是首要条件。要对作为“文学话”批评母体形态的传统诗话、词话等话体文学批评之历史发展有较深入的了解,更合理的方法并不是学界惯常所做的那样,对其创体时间进行历史考古,或对其文本文献进行全面搜寻与考订,而是应该首先厘清话体文学批评得以成为一种独特体式的内在动因及其演变轨迹。
事实上,早期话体文学批评的创制初衷正是通过讲述一些与“文学”相关的“故事”“以资闲谈”的。诗话是确立最早的话体文学批评,关于其创体,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滥觞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六一诗话》开篇即言:“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4)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4页。祝尚书先生认为,欧阳修这句短序,向我们揭示了关乎诗话的两个基本信息:一是据其自称“居士”可以断定该著的诞生时间为熙宁四年六月至次年卒前这段时间内;二是“这种新的诗学著作不再用死法教人如何作诗,而是将表达形式定位为‘闲谈’,即用随笔式、漫谈式的诗歌批评和叙事方法,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得到直观的、甚至是情绪化的感受”(5)祝尚书:《论宋诗话》,《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祝先生这里所谓“随笔式、漫谈式的诗歌批评和叙事方法”的总结可谓极其精准,一方面,点明了话体文学批评流贯始终的语体特性;另一方面,所谓“叙事”与体式命名意义上“话”的故事性内涵互为应答,确证了从“话”性维度考察话体文学批评生成、流变的合理性。
词话继诗话而起,早期诗话偏重记录“诗人逸事”、“诗作本事”的“话”性特质也在词话中得到了延续。最早以“词话”命名的是杨湜的《古今词话》。关于《古今词话》以“录事”为基本表征的“话”性品格,赵万里先生在为《古今词话》撰写的“题记”中指出:“其书采辑五季以下词林逸事,乃唐宋说部体裁”,“案杨湜此书,乃隶事之作,大都出于传闻。且侧重冶艳故实,与《丽情集》、《云斋广录》相类似”(6)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17页。。除此以外,在宋代,凡以“词话”命名者,均与《古今词话》的内容保持一致。对此,孙克强曾有描述:“从现存宋代的词学专书来看,如果不是记逸事、录本事者,则不以词话名之。”(7)孙克强:《词话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同样,“文话”创生伊始,也具有明确的“话”性特质,慈波在《文话研究引论》一文中就指出“记录本事丛谈”是“文话”的主要内容之一(8)慈波:《文话研究引论》,《江淮论坛》2006年第3期。。即使到了民国,文话创作中对“录事”的热衷依然肆响不绝,甚至在某些作品中,由于对“故事”的过分热衷,导致其理论本色反遭压抑,而其本身作为话体文学批评理论著作的身份也颇为可疑了。这其中的典型代表首推郑振铎的《民族文话》。《民族文话》实际上是郑振铎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记录历代文学作品中有关民族大义的英雄故事的一部著作,其创作并非在今人所熟知的传统话体文学批评的理论之维上展开,而是借用“文话”之名,延续“文话”最原始的“话”性内涵,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关于其创作动机,郑振铎曾直言:“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把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们的抗战故事,特别是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里的,以浅易之辞复述出来,当不会是没有作用的。”(9)郑振铎:《民族文话》,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自序”,第3页。由此可见,在话体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以“故事性”为基本表征的“话”性始终居于重要位置。
除却“体兼说部”意义上的“故事性”之外,“话”性的第二重内涵即指前文提及的“随笔”、“漫谈”特征。与“故事性”不同,前者仅仅局限于话体文学批评范围之内,后者则具有更为久远的理论渊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先在性的理论预设情势。“随笔”、“漫谈”实际上更多地指向一种语言风格,其为话体文学批评所吸纳,一方面由早期话体文学批评讲述“故事”的内在需求所决定,因为既然要讲述故事,就不可能如纯粹的学理文那样,作“正襟危坐”、“高屋建瓴”式的逻辑演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先秦以降的散体文学叙述风格对后起文类的影响。就此而言,“话”性喻指随笔、漫谈的内涵在中国古典文论的发展过程中波及更广。
正如王明强所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自先秦时期就具有明显的‘话’性:随机性和零散性。这种‘话’性正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最初形态,是后来各种‘话’体得以最终形成的基础因子”(10)王明强:《文话:古代散文批评的重要样式》,《长江学术》2007年第1期。。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特性同中国古人重感悟、重直观的思维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具体体现为中国原初的文学批评大多并不是以专论形式面世,而是多以碎金散玉的方式出现,与西方文论的体系化、浑整性判然有别。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体际互渗”的角度来理解“话”性的“漫谈”指向。“谈”在这里既是一种话语风格,又是一种文论体式。前者以先秦以来的“对话体散文”为代表,后者则可取《论语》为轨则。陈桐生曾对先秦对话体散文的历史源流进行梳理和辨析,认为其发轫于《尚书·商书》,在《国语》中大体定型,成为了一种以“主客问答”为基本方略的稳定结构形式,并颇有见地地指出其“以记叙的形式说理,体现了中国早期说理散文的文体特色”(11)陈桐生:《先秦对话体散文源流》,《学术研究》2017年第8期。。而《论语》之中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见地也正是通过这种类似“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的。
由此可知,首先,古典文论的零散性决定了很多文学理论思想的阐发都寄生于非理论性的经、史、子、集之中,而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以体系完备的专门性文学理论著作为基本载体;其次,在很大程度上,话体文学批评之“漫谈”风格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借鉴了“以记叙的形式说理”的古代文学创作传统。因此,“漫谈”性由散文等非纯理论性的文体中抽绎而出,继而影响到理论性的话体文学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创作与理论之间“体际影响”的结果。
二、现代“文学话”批评界说及辨体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体式,话体文学批评尽管在起始阶段以“纪事”为本职,但很快就纠正了这种理论认知方面的自觉性缺失,从而自动提纯为以讨论诗、词、文等不同文学种类的理论、批评问题为主职的理论形态。就诗话而言,尽管最初的《六一诗话》主要记述了一些与诗相关的故事,“以资闲谈”,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括其主要特征为“体兼说部”,但随着其后诗话创作的勃兴,其内容与形式也陡然丰富起来,往往兼及诗法、诗论乃至考证、辨讹之类。至北宋末年,以叶梦得的《石林诗话》为代表,总体而言已经更为侧重诗歌理论的阐发了。到了南宋,诗话以理论探讨为主又兼及其他职能的特点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当时的《彦周诗话》曾讲:“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12)许顗:《彦周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8页。诸如张戎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的理论化色彩更为浓厚。其后,诗话在自身发展与后学辑录的过程中虽有“乱体”现象产生(13)降及清代,受重视考据、崇尚严谨的学术风气影响,诗话、诗论、诗法等不同文体的相继勃兴加之有些著作本身就诸体兼备,以至于学界常常将举凡成编的所有诗话、诗法、诗论及考证类的诗学著作统统称之为“诗话”,如清代何文焕编的《历代诗话》,就将钟嵘的《诗品》、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与记事闲谈的《六一诗话》、《温公续诗话》、《中山诗话》等混为一谈。及至其后丁福保编定《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尽管有重视理论轻视故事的取向,但大致仍沿用了《历代诗话》的基本体例。,但总体上,对其作为一种“诗学理论”的认识也时有强化。到了晚近时期,“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14)郭绍虞:《清诗话前言》,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辑:《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便构成了一种集体性的认知倾向。词话由故事性的词学著作滑向词学理论的历史路径大体上与诗话一致。早期南宋杨湜的《古今词话》主要以记录本事为职,但元明以来,诸如明代俞彦的《爰园词话》以及清代毛奇龄的《西河词话》、郭麐的《灵芬馆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等,虽沿用词话之名,在内涵上却已非以记录词事为宗,而是理论性的论词专著。
话体文学批评中,发端较早且于“叙事”到“论理”的内容转变路径上与诗话、词话保持一致者,当推“文话”。“诗话、词话和文话,均起源于宋代”(15)王水照:《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然而文话却一直处于自居边缘的尴尬境地,并未得到学界重视。从思想内容的角度来看,“历代文话的内容思想,大多集宗经、法古的大成”(16)王更生:《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新局——从整理“文话”谈起》,《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从体式自觉的意义上来看,“文话”虽渊源久远,但由于其发端依赖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因而其批评对象主要是“古文”、“骈文”、“辞赋”等。文话发展到现代,一方面,其传统体性得以保存,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在
三项检查,花去上千块钱。检查结果,不是红斑狼疮。不是红斑狼疮,是一件幸运的事。就是这一刻,妻子头脑清醒开来。妻子说,这是一个骗局。大姐问,怎么是骗局?妻子说,医生怀疑我得红斑狼疮,就是想多开化验单,就是想多拿回扣。医生开出来的药,妻子一样不拿。妻子说,不是想拿回扣吗?我一粒药都不拿。大姐说,你不拿药,皮肤病怎么好?妻子说,不是红斑狼疮,我就不会死!妻子气哼哼地丢下大姐,想直接坐车回家。大姐说,就算你回去,也要去我家吃过晌午饭吧。
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言说方式及文体形式的影响下,其本身又裂变出一种全新的批评体式——“文学话”。
现代以来产生了大量的“文学话”,就其发行载体而言,既有以专著形式面世的,如朱光潜的《谈文学》、赵景深的《文学讲话》、胡风的《文艺笔谈》、黄道明的《文学丛话》、李广田的《文学枝叶》、何典的《文艺漫谈》等;又有以新生的文学报刊为发行媒介的大量单篇“文学话”,如王引才1918年发表于《南洋》杂志的《文学谈》、丁致中1928年发表于《暨南周刊》的《谈文学》、白眉1931年发表于《民立学生》杂志的《文学漫笔》、槐青1932年发表于《平潮》杂志的《文学谈屑》、华林1947年发表于《自由谈》的《谈文艺》等,数量庞大,一时难以辑尽,但通过上述例举便可得知,无论就文本而言,还是就“作者”而言,在当前的文学批评界,均属“陌生面孔”。
“文学话”的新生特质加之其与长期居于边缘地位的“文话”之间因体式裂变关系而缔结的历史姻缘,造成了学界长期以来对“文学话”批评的盲视:首先,对于民国“文学话”批评及其相关资料的整理研究成果目前基本阙如;其次,由于其母体批评疆界的不确定性和其本身对传统话体批评空间的拓展,造成了“文学话”与“文话”之间边界不清,乱体频仍的现象亟待廓清。“文学话”的诞生,逻辑起点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17)近年来,对“文学”概念古今转变的研究热潮不断兴起,诸说纷纭。在所有论述中,笔者较为赞同的看法是漫长的古代文化发展史中,中国有“文”学而无“文学”。在“文”学与“文学”的分野意义上来考察现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与范畴转换,不仅理路清晰,而且很容易看出中西“文学”乃至文化思想的不同。具体落实到话体文学批评领域,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文话”与民国时期新生的“文学话”之间的差异,进而有效避免乱体现象的产生及随之产生的不必要的辨体麻烦。关于“文”学与“文学”之差异的论述,参见赵辉:《建构中国“文”学及其理论话语体系的必然途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向现代意义上由西方传入的“文学”观念的让渡。关于古今“文学”观念的历史转换,余来明指出:“时至清末,随着西方新文学形态和文学观念输入中国,‘文学’概念经历古今转换与中西涵化,逐步演为表述近代分科体系中独立学科门类的新名,并被用来指称以语言文字为表达方式的艺术。”(18)余来明:《“文学”概念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这里透露的是一种“文学”术语古今转换的复杂情势,其中包含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中国现今通行的“文学”概念与古代中国的“文学”用义判然有别;二是现今中国作为一个学科分类体系中被一致认同并可由当今学人随意支取的“文学”概念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文学形态传入中国后形成的。这就为我们从批评对象的角度理解民国“文学话”提供了便利。可见,“文学话”是一种专“话”新式“文学”范畴及其观念体系中诸问题的话体文学批评,与专“话”“文”(古代诗文并置意义上的“文章”)的“文话”并不相同。
尽管中国新式“文学”范畴的确立有赖于西方文学观念的化孕,但“欧风美雨”的灌注带给晚清以来中国文坛的,绝非单一的“文学”范畴,随之而来的还有价值论意义上更为重要的西方全新的文学知识与思维方式。就“文学”本身言之,“‘文学’这一词语的含义与‘文章’相比,不仅价值高下立见,甚至显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利话语,而且具有相当广域的容量”(19)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5页。。反映到“文学话”领域,其本体建构始自对传统话体文学批评体式规定性的钻研,却又将其嫁接到了凝聚有大量西学因子的现代文论的脉络中,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的改造。于“文学话”而言,即使是延续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地固守本事,而是通过在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削传统之“足”以适现代之“履”的方式达成的。比如,传统话体文学批评中,记录文学本事、文坛逸事是初创期的重要内容,但在“文学话”领域,则发生了微妙的改动:以赵景深于1927—1930年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253则《现代文坛杂话》来看,“文坛逸事”变身为“文坛消息”,既有对世界文坛新变的捕捉,又有对作家作品的简介,其视野之宽广已远非传统话体批评只在中国本土文坛范围内部转圈可相比拟。
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影响或作用于“文学话”领域,促使“文学话”将批评触角深入世界视野,在世界文坛的大框架中建构自身知识体系固然为“文学”与话体文学批评寻求本体发展提供了便捷,但也为我们理解“文学话”之“话”性特质设置了另一重障碍。要逾越这一隔障,除了在“文话”与“文学话”之间进行有效辨别之外,还需在“文学话”与同为新生理论形态的文学理论著作之间进行辨体。因其所“话”对象的综合性,与诗话、词话、文话、小说话、剧话等相比,“文学话”最容易与“论体”相混淆。通过前文对话体批评生成及其特性的梳理可以看出,所谓“话体”,其主要特征是随笔散体,故而应当是由一系列不相连贯的短文组成,其常用体式往往如《人间词话》那般,分则论述,各则体制一般较为短小,虽全书(全篇)围绕一个总的话题展开,但具体到各则,则任由作者心之所至,随机赋得,并不按照严格的逻辑顺序和话题关联度组织行文,有思绪跳荡的随想录特质。而“论体”则一般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论体”著述往往论题明确,理论指向性极强,与“话体”著作理论指向上的松散性大不相同;其次,“论体”著作在行文谋篇方面具有极强的逻辑性。这里的“逻辑性”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指在论证过程中具有横向整合特点的严密逻辑性,其二则指纵向意义上倾向于历史梳辨的历史概括性。“论体”之作的基本特性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且在当下西方文论强势话语的主导之下日益突出,并不难理解,因此,要对“文学话”与“文学理论”进行深层辨别,关键还在于对“文学话”本身体式特征的核定。
三、从对话体看“文学话”批评的“散”体特征
“文学话”作为话体文学批评之一种,其体式特征同样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规定性得以确立,但是,仅就内容方面而论,经典的文学理论著作与“文学话”同样致力于文学基本原理的阐发,其研思理路也基本一致,因而很难实现有效甄别,所以,“文学话”之体式标出性的确立,主要还是一个形式或风格意义上的探索问题。关于现代话体文学批评的体式特征,黄霖先生将其归结为总体上“给人一种‘散’的感觉”(20)黄霖:《应当重视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这里的“散”具体到“文学话”,堪称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微观视之,作为话体文学批评的现代变种,“文学话”之“散”体特征的生成既有对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语言改制”(白话文兴起)与“语体变异”(“谈话风”、随笔文学、清谈文学等的时兴)的及时应答,又有对其母体形态体式稳健性与强大生命力的积极捍卫。宏观来看,作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文学话”之“散”源自一种在对本土文论传统的回味和对异域新知的认同过程中通过有效促成二者在民国文学批评场域中“珠胎暗结”之关联而实现的巨大风格张力。具体而言,“文学话”之“散”通过“守恒”与“察变”两种致思路径的双重变奏得以显现。
就“守恒”的角度而言,“文学话”延续了传统话体文学批评的基本意绪,语言上以“漫谈”、“散议”为基调,形式上大多分则论述,各则短小精悍,不做深入解析,思维上重视直观感知,保有随机赋得的印象式批评遗风,这些特质在传统的诗话、词话、文话之中皆有体现,无需赘言。更能说明“文学话”体式特征的在于“察变”的一面,即体现“文学话”对传统话体文学批评形式进行有效改造的一面。质言之,这种改造具体落实为其对一种可以“对话体”名之的论述风格的创构。“文学话”之“对话体”,又可大致分为“书信对话体”、“问答对话体”与“商榷对话体”三种。
“书信对话体”由朱光潜创制,并在其《谈美》之中得到了具体表现。“书信对话体”的特点是往往在理论阐发的过程中,通过事先预设一个“对话人”,以期达到一种关乎文学原理的交流效果,而实际上,作者预设的“对话人”未必真实存在,所以,交流的目的也未必真正实现。比如,朱光潜在《谈美》一书的“开场话”中就明确将该著的写作定位为给自己的“朋友”写信,并希望得到回音。他说:
从写十二封信给你之后,我已经歇三年没有和你通消息了……在写这封信之前,我曾经费过一年的光阴写了一部《文艺心理学》。这里所说的话大半在那里已经说过,我何必又多此一举呢?在那部书里我向专门研究美学的人说话,免不了引经据典,带有几分掉书囊的气味;在这里我只是向一位亲密的朋友随便谈谈,竭力求明白晓畅。……一切事物都有几种看法,我所说的只是一种看法,你不妨有你自己的看法。我希望你把你自己所想到的写一封回信给我。(2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但实际上,《谈美》并非一封普通的书信,而是一部关乎美学、文学、艺术学基本原理的理论著作。所以,这种“对话体”的设置,只不过奠定了其“明白晓畅”的论述风格,与《文艺心理学》等“引经据典”、“带有几分掉书囊的气味”的纯理论著作拉开距离,进而为其划归话体文学批评创造了条件。
与“书信对话体”不同,“问答对话体”的对话双方是客观存在的,无需主观预设,因此也达到了实际交流的效果,但由于在“文学话”批评中出现,所以其所讨论的文学理论问题一般只是“点到为止”,并不深入,且论题切换频繁,并不就某一个特定话题作抽丝剥茧式的深入剖析。该体以1933—1934年《珊瑚》杂志上连续发表的《文学谈座》系列问答短文为代表。《文学谈座》设有“十问十答”(22)原文分别以“第一问”、“第二问”等标题,后有作答,共标明了“九问九答”,但实际上当为总计“十问十答”,因为“第九问”之后又设“第七问”(前文排序正常,且无缺序现象),盖为排版错误,非有意为之。另外,原文并未署名。详见《文学谈座》,《珊瑚》1933年第3卷第11期。,其论述内容涉及文学语言论(“第一问”讨论“音韵”)、文学体裁论(“第二问”讨论“尺牍文”、“第五问”讨论时下流行的“小品文”、“第九问”讨论经典“日记”文学问题)、文学典故论(“第三问”从文学考古的角度讨论“夏禹治水”)、文学文本论(“第四问”讨论岱雨的《快雪堂诗草》)、文学创作论(“第六问”)(23)“第六问”下属“三小问三小答”,理论性的问题只有第二小问,属较为浅显的创作论问题。参见《文学谈座》,《珊瑚》1933年第3卷第7期。、文学作家论(“第七问”、“第八问”讨论王国维、况周颐的作品),涉猎广泛,体现了提问者的机敏和对答者文学知识之丰富,但论谈并不深入,只是提出问题,简要作答,具有极其鲜明的话体特征。例如,“第六问”第二小问,问曰:“……如读国文百日通,可得作文门径否?”答曰:“国文百日通尚可看,多看短篇小说及报纸副刊的小品文,都能助益。”(24)《文学谈座》,《珊瑚》1933年第3卷第7期。
所谓“商榷对话体”,整体来看,也存在一个鲜明的“呼应结构”,指的是不同文学理论家(包括普通文学爱好者,不专指文学精英)围绕某一具体的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并以“组稿”的形式同时发表其讨论成果。相比“书信对话体”,其讨论双方(或多方)是真实存在的,因而与“问答对话体”更为接近,但从论述的具体性和独立性角度来看,它又与“问答对话体”不尽相同,因为“商榷对话体”的商榷双方虽围绕一个共同的题旨,因意见相左(或相近但侧重点不同)而进行商榷,但在话题的衔接度上则相对松弛,不必陷于“问—答”的困境循环而使自我表述得到限制,因而篇幅也相对较长。该体主要见于民国时期一些文学报刊举办的特定话体文学批评专栏中,典型例证是1944年《中国文学》(重庆)杂志发表的“艺文丛话”系列文章。“艺文丛话”栏目自1944—1945年陆续发表了共约三十余篇“文学话”,由于这些“文学话”发表于不同刊期,所以其内容也较为丰富,主题不一,但同一期发表的系列文章基本都有一个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比如,第1卷第4期上发表的“艺文丛话”第四辑,围绕“文学语言”问题,共刊发了7篇短文,除第一篇《语言与文学》为张世禄所作,其余六篇《汉字拉丁化问题》、《语言的阶级性》、《文言与白话的分野》、《语言的欧化问题》、《方言文学与国语文学》、《简字与学习》均为编者辑录,属典型的“文学话”。
如前所述,中国古典文论的“话”性特质具有双重指标,其中重要的一端便是随笔式、漫谈式的话语表述风格,这种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文学批评由“话”性向话体的跃升奠定了基础。这里所谓的随笔、漫谈的风格不仅存在于以《论语》为代表的古典文论名作之中,而且还寄生在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对话体散文”之中。但其与“文学话”之“对话体”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异。《论语》虽采用了“对话体”,但由于其本身为后人辑录,故而缺乏理论生成的现场感,造成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委以“对话”之名,但其实质还在于通过孔子对其“对话者”意见的点评,阐发孔子本人的文学论见。由此观之,《论语》所显现的价值倾向与其他诸如《文心雕龙》等传统文论作品别无二致,都以强势话语一方对弱势一方的主动灌输为表征,“对话”双方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交流和互相启发。而古代的“对话体”散文属于文学作品范畴,其“散”更多地指向一种文体命名意义上的语言风格,“对话”因而也成了一种单纯的形式,并不担负传递某种理论见识的使命。
与之相比,“文学话”之“对话体”意味更为深长。诚如朱光潜先生在《谈对话体》一文中所言,“文学话”领域的“对话”“专指不是戏剧、小说或历史,而是自成一种特殊体裁叫做‘对话’(dialogue)的那一类,像柏拉图的许多著作”(2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459页。。由此可见,这里的“对话”不寄生于任何文学体裁,其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体裁,这就使其与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种的“对话体散文”拉开了距离。然而,所谓柏拉图式的对话体毕竟与孔子式的对话体相似,究其极,还是一种个人观念的“对话”式抒发,因而不能不令人对朱光潜先生所谓“对话体”之“对话”到底是形式上的还是实质性的这一问题产生疑窦。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朱光潜先生对其之所以提倡说理文最宜采用“对话体”作了进一步说明:
对话体特别宜于论事说理。在不用对话体的论事说理的文章中,作者独抒己见,单刀直入,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算“自圆其说”;至于旁人的种种不同的看法,可以一概置之不问,至多也只是约略转述,作为己说的佐证或是作为辩驳的对象。但是同一事理往往有许多方面,观点不同,所得的印象或结论也就不同;而且各人的资禀修养很可以影响他的见地,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理的看法没有完全是客观的。……
事理虽有多面的看法,却不一定每面看法都是对的。有时须综合各面才见全体真相,有时某一面特真,而真也要待证明其它各面错误后才明显。对话虽是各面平铺并陈,却仍有宾有主,着重点当然仍在主,正如一出戏里许多人物中必有一个主角。宾可以托主,也可以变主,改变他的思路或纠正他的片面观的偏蔽,所以宾的用处仍然很大。(2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459-460页。
不难看出,朱光潜先生所谓的“对话”,并非形式主义的“对话”,而是“主”与“宾”可以有效互动甚至势位逆转的现实意义上的“对话”。“文学话”对这种“对话体”的采用,就实际效果而言,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中流贯不息的由处于文化高势位一端的知识精英向处于文化低势位甚至边缘地带的普通人单向灌输文论知识的历史积习,加之为了达到对话的有效性以期实现观念共鸣与思维交锋,“文学话”自觉吸纳白话文、口头俚语入文,这样一来,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开始由部分普通大众分享,使得“文学话”批评形式之“散”超越了在传统话体文学批评中定位于“随笔式”、“漫谈式”的笼统界说,进而落实为语言的浅易与形式的改制。于是,一种脱胎于旧传统而又超越了其母体的全新理论言说方式得以生成,知识精英的理论见地介入到大众表达的话语机制中,既为“文学话”本身的普及创造了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理论知识的大众化传播扫除了障碍。
四、结语
现代“文学话”批评的产生,体现了传统文论适应历史语境、应对文学流变而积极作出自我调整的不懈努力。话语表述方面,“文学话”尚求自然流露,自觉吸纳白话文、口头语入文,避免了传统文论因语言表达的精英化诉求所造成的理论普及方面的“等级”隔膜,具有“大众参与”的先天优势;谋篇布局方面,“文学话”远取孔夫子对谈说理的形式传统,又对其进行改造,使传统的形式主义“对话体”升级为一种通过实质性“对话”及对话机制中“主”“宾”双方的增益互补甚至势位逆转达到思想交流的全新文论形式,别开生面;行文逻辑方面,“文学话”既不同于传统文论近乎“玄”化的古奥精深,又有别于当下文论西方话语主导之下的自我迷失;文体形态方面,“文学话”挣脱了传统文论“正襟危坐”、条分缕析的框架,谈之论之而无禁区。作为文学批评史发展链条中“古”与“今”之间“居间”的文论形态,受限又得益于现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文学话”一方面点染着中国古典文论幽思绮想的风神,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浸入了现代新知的流彩。
“文学话”的提出与建构,不是单纯的概念演绎问题,它关乎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历史本相的还原与整体看法,也关乎我们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细节性理解。“文学话”批评实践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也不单纯是对特定历史时段批评经验的补充或者完善,与此相反,它更近乎一次颠覆性尝试,或者说一种重构性的试验,它将引导我们仔细勘察历史现场,重新解释和说明现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批评以何种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就精神实质而言,“文学话”所传达的批评精神,乃是以逻辑性、科学性构筑起来的相对封闭的文学批评述学规范中,“自由主义”的批评姿态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所彰显的那种批评的“文学性”诉求也有其活动的空间。故此,对“文学话”这一“有实无名”的批评文体学范畴的解码,不仅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考察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晚近以来所发生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重大变革,进而为我们重构中国文学批评的完整版图提供一条全新的思路,还有助于引导我们去思考在当前的文学批评语境中,现代文学批评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建设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