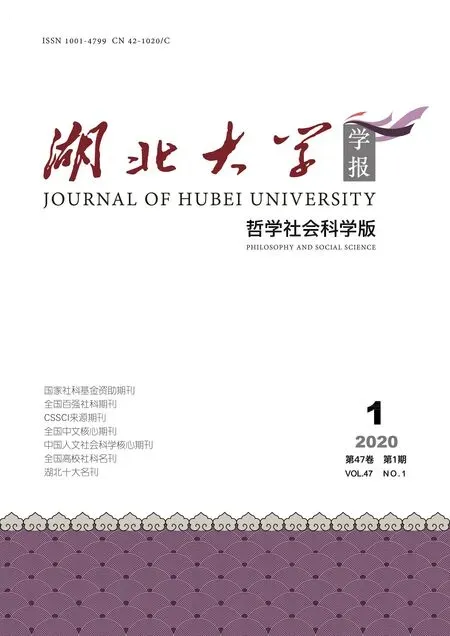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研究的由来与旨归
林文勋
(云南大学 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1)
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研究是我和我的学术团队近二十年来重点研究的一项课题。唐宋以来,中国社会中兴起了一个新的“富民”阶层,这是唐宋时期发生并对后世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深刻社会变革。历史上,“富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一经崛起,就迅速发展成为社会的中间层、稳定层和动力层,使得唐宋及其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了与以往显著不同的历史特征,形成了一个新的“富民社会”。
“富民社会”这项研究,既是我们在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研究中发掘的一个新问题和新领域,同时也是我们聚焦于这一新问题、立足于这一新领域,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提出的一种新阐释,是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演进变化,特别是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再认识与再研究而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
一
关于中国古代“富民”阶层和“富民社会”的研究,最早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在围绕“唐宋社会变革”这一重大学术问题,探寻唐宋社会的重大变迁时,我发现财富力量的崛起成为影响唐宋社会变革的一股重要力量。最典型的就是唐人李冗的《独异志》中有一条“至富敌至贵”的记载: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上,问左右,曰:“不见。”令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左右贵人启曰:“何臣等不见,元宝独见之也?”帝曰:“我闻至富敌至贵。朕天下之主,而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1)李冗:《独异志》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47页。
这段史料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其中的“富”无疑代表了当时社会中的经济力量,尤其是指货币力量;“贵”则指政治力量。换句话说,所谓“至富敌至贵”,就是经济力量崛起,成为与政治力量同等重要的一股社会力量。而且史料中这话出自于帝王之口,可以想见当时政治上层对这种现象的切身感受,或至少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社会观感。这在古代社会,应该说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因此,“至富敌至贵”的出现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进一步看,中唐以后两税法的实施,其税制原则“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2)《旧唐书》卷118《列传第六十八·杨炎》,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21页。,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当时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从此以后,以财产税为主的赋税制度取代了以人头税为主的赋税制度,成为唐朝中期以后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基本准则,这无疑是财富力量的崛起使然。
那么,财富力量何以会崛起?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我们发现,中唐以来财富力量崛起这一历史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而这一社会阶层就是“富民”阶层。
“富民”,在史料中又被称作“富室”、“富家”、“富户”、“富人”、“富姓”、“多赀之家”等,某些情况下还可称为“大姓”、“右族”、“望族”、“豪族”、“兼并之家”等。“富民”作为一个特定社会人群和群体的称谓,古已有之。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现存历史资料中,唐宋时期有关“富民”的材料大量出现于史籍。这逐渐引起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在对唐宋时期的“富民”史料进行进一步梳理和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并非仅仅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而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
对于“富民”群体是否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看法,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过质疑和建议(3)参见李振宏:《国际视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路径选择》,《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王曾瑜:《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张邦炜:《宋代富民问题断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这些观点和意见无疑都给予了我们重要的启发。但是,把“富民”这一群体放在整个社会变迁的大视野下看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富民”就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第一,“富民”是社会分层的结果。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显著加快,“贫富无定势”(4)袁采:《袁氏世范》卷3《治家·富室置产当存仁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页。,贫富关系处于经常性变化之中;户等制从九等户制转向五等户制;新的社会群体和名称不断见诸当时史籍。凡此均说明,唐宋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分层的时代。置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看,作为拥有大量财富和良好文化教育而又没有政治特权的一个群体——“富民”无疑是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结果,而它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着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离开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历史情境,就没有“富民”的崛起,也没有“富民”阶层的成长壮大。
第二,“富民”迅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有的学者在与笔者交流时指出,“富民”虽然是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但它到底在社会中有多大的比例?如果占比不大,那“富民”阶层对社会的影响应该也不大。事实上,考虑一个社会阶层对社会的影响,不应该单纯地看它的规模和占比的大小,而应该看它在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中的实质地位。经济学中有一个“帕累托定律”,又被叫做“二八定律”或“关键少数法则”。这一定律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发现,指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往往只占较少的部分(20%),而不重要的因子却往往占多数部分(80%),因此,只要能控制好这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就可以控制全局。
宋代以来,“富民”阶层人数虽然并不一定占多数,但确实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北宋苏辙曾指出,当时社会现实中富家大姓“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5)苏辙:《栾城集》(下)卷8《杂说九首·诗病五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5页。。南宋叶适也曾论述到:“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6)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57页。因此,朱熹就告诫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计(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先)借谷米,及至秋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戒,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26页。这些都反映出“富民”已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础,离开“富民”,社会就将失去赖以维系的根基。所以,宋人吕大均说:“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而邦本自固。”(8)吕大均:《民议》,吕祖谦编:《宋文鉴》卷106,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77-1478页。这里讲的“主户”,相当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富民”。由此可见,在唐宋社会中,“富民”确实成为了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对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基层控制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成为整个社会稳定的中间层和发展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
第三,“富民”在唐宋以来的中国社会中,一直显现出强劲的成长性。这种强劲的成长性,集中体现在国家对其的依赖越来越大,甚至成为国家进行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要依靠。如宋代的衙前、里正等役,主要就是由“富民”担任。《宋史·食货志》载:“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定差。”(9)《宋史》卷177《食货上五·役法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95页。宋代,衙前、里正之职役通常为第一等户承担;耆长之职役一般由第二等户承担;弓手、壮丁、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职役则通常由第四、五等户承担(10)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510-513页。。“富民”成为差役特别是重要差役的主要承担者。
到了元代,虽然经过了朝代更替,但“富民”的成长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替而受到影响。由于元朝是以马上得天下,不谙中原制度,政令不齐,反而为“富民”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使得“富民”阶层继续承袭唐宋以来的发展之势,得以赓续和壮大。明人于慎行就说:“元平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简,其民止输地税,他无征发;以故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其来非一朝夕也。”(11)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2《赋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9页。到了明代,设立粮长制度,以“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赋税”(12)《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九月丁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第1279页。,又设立里甲制度,“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之长”,“管涉一里之事”(13)《明太祖实录》卷135,洪武十四年正月丙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第2143页。。正是以“富民”阶层为依靠对象,明代在江南地区建立起了由粮长、里甲构成的“以良民治良民”的基层控制体系。正是因为“富民”阶层在社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国家对“富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依赖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代。清人黄中坚根据他的观察,直接指出:“今之承事于官者,率富民也。”(14)黄中坚:《蓄斋集》卷1《限田论》,《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可以说,历宋、元、明、清,“富民”一直是国家赖以依靠进行基层控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这既集中体现了“富民”的成长性,又充分说明“富民”确实代表了新的社会发展方向。
二
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对中唐以来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全面的和深刻的:
第一,全面性。中唐以来,“富民”阶层对社会的影响具有全面性。具体而言,在唐宋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例如乡村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乡村社会的内在发展动力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兴盛、宋代衙前里正和明代粮长制的出现、宋代“地方精英”阶层和明清“士绅社会”的形成乃至宗族势力的发展,甚至诸如明代苏松地区重赋这些特殊的经济现象,实际上都与“富民”阶层有关。南宋叶适详细论述了富人在社会中的影响:“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而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15)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第657页。这表明“富民”是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阶级关系的核心。张守说宋代“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读书应举,或入学校”(16)张守:《毗陵集》卷3《论措置民兵利害札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6页。,表明作为中上户的“富民”是推动乡村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依靠。宋代以“富民”充当衙前、里正,明代以“富民”充当粮长,表明“富民”是国家控制乡村的重要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富民”是国家对乡村实施统治的重要依靠,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正是因为“富民”对社会的这种全面性的影响,只有系统地对“富民”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事实和深层逻辑。
第二,深刻性。“富民”阶层的崛起,引起了中唐以来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推动了唐宋以来契约租佃关系主导地位的确立,同时引起了国家乡村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的重大调整。契约租佃关系自秦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土地以后就已经出现,但一直没有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富民”的兴起,为契约租佃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因为“富民”与“贫民”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之间不能抑良为贱,只能结成平等的契约租佃经济关系。这是一种最佳的关于土地生产经营的制度安排与现实选择。杨万里《与虞彬甫右相书》记载了一个典型案例:“某之里中有富人焉,其田之以顷计者万焉,其货之以舟计者千焉。其所以富者不以己为之,而以人为之也。他日或说之曰:‘子知所以居其富矣,未知所以运其富也。子之田万顷,而田之入者岁五千,子之货千舟,而舟之入者岁五百,则子之利不全于主而分于客也。’富人者于是尽取其田与舟而自耕且自商焉,不三年而贫。何昔之分而富,今之全而贫哉?其入者昔广而今隘,其出者昔省而今费也。”(17)杨万里:《与虞彬甫右相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37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5-286页。这位富者没有选择租佃制经营,也就没有选择最有效的制度安排,结果导致经营的失败。可以说,契约租佃制是“富民”阶层最佳的制度选择。
而从基层治理来看,明代初期建立的粮长、里甲制度,根本上说就是一种依靠粮长、里长等乡村“富民”阶层实行“以良民治良民”的基层控制模式。官府选用“富民”阶层充当粮长、里长,实施对乡村基层的控制,既可以发挥他们在乡村中固有的权威,更好地实施乡村控制和赋税征收;又可以通过粮长、里甲制度,将“富民”阶层纳入到官府主导的组织框架之中,以加强对“富民”阶层的制约和控制。因此,粮长、里长等“富民”阶层可以视为政府在基层社会的“包税人”或“代理人”(18)高寿仙认为,明朝的乡村控制策略可以理解为一种“经纪体制”,粮长、里长类似于政府的“包税人”和“承包人”(参见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69页)。夏维中也将乡村富户视为国家在基层“代理人”,认为地主富民是国家权力通过里甲组织实现乡村统治的阶级基础(参见范金民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812-813页)。。正是充分利用和依靠“富民”阶层,明初在江南等地建立起了以里甲制度为核心的“以良民治良民”的乡村秩序。如日本学者小山正明所言,正是由于粮长制度和里甲制度的实施,明代乡村社会形成了粮长—里长户—一般农民三种乡村等级身份序列,这一序列又是与乡村统治系统,即赋役征收机构重叠在一起的(19)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82页。。以里甲组织为基础,粮长、里甲构成了明初江南地区完整的基层组织体系。“富民”阶层对社会影响的深刻性可见一斑。
正是因为“富民”阶层在中唐以来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才断言,随着“富民”阶层的崛起,中唐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汉唐的新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富民社会”。
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构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理论体系。何谓理论体系?我们认为,大凡理论体系,都是由若干重要学术论断所构成。学术论断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观点和认识,它具有统摄性、引领性、指向性,它往往会开辟学术研究新的领域。
通过对唐宋以来“富民社会”的深入研究,我们提出了五个有关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理论体系的学术论断:①“富民”阶层是唐宋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新兴阶层;②“富民”阶层一经兴起便迅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中间层、动力层和稳定层;③“富民”与国家的关系是唐宋以来中国社会最核心的关系;④“士绅社会”是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⑤中国传统社会依次经历了上古的“部族社会”、秦汉魏晋的“豪民社会”、唐宋以来的“富民社会”,并最终向着“市民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这一社会演进即为中国古代史的新体系。
如何开展好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理论体系的研究?我们确定了这项研究的“四部曲”,即“微观—宏观—微观—宏观”的四个研究步骤。
第一步,从微观研究入手,深入研究“富民”阶层的崛起、特征和历史作用,指出“富民”阶层是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兴起的新阶层。现主要完成《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和《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等成果。第二步,从微观上升到宏观,以“富民社会”为理论基石对“唐宋社会变革”这一学术命题进行新的阐释,指出这场变革就是从汉唐的“豪民社会”走向中唐以来的“富民社会”。现已完成《唐宋社会变革论纲》等成果。第三步,再次从宏观回到微观研究,通过个案解剖和具体考证,重点研究“十至十九世纪富民与乡村社会变迁”。第四步,再从微观研究上升到宏观研究,对中国古代“富民社会”进行整体性研究。
我们将一本“学贵自成体系”旨要,突破断代史研究局限,开展跨时段研究,将中唐以来到清代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进行研究,分析其变迁过程,系统揭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特征和历史地位。
三
作为一项突破断代史研究局限的贯通性研究,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理论体系的研究,力图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再认识。
第一,力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主线进行再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对于传统社会来讲,编户齐民的演变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民”的演变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通观中国古代,“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先后经历了从先秦依存于部族到汉唐出现“豪民”、唐宋以来“富民”崛起、近代以来逐渐形成“市民”的历史进程。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中,汉唐时期,大家已经充分注意到“豪民”阶层的兴起,在近代,大家也已经注意到“市民”阶层的兴起。而对处于其间的“富民”阶层,我们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许多历史问题认识不清,就与我们对“富民”阶层缺乏足够认识有关。
第二,力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再认识。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是整个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决定着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形态。“富民社会”下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既有对抗的一面,又有依赖的一面。以往,我们往往强调其对抗的一面,而很少注意到另一方面。试以《水浒传》的记载为例。取材于北宋宋江起义的《水浒传》里记载:庄客多拥立庄主来对抗封建官府。按照我们以往的观点,庄主奴役和剥削庄客,庄客应该起来反抗庄主,为什么反而会拥立庄主为王来对抗官府呢?宋神宗时御史中丞邓绾在上奏中说:“富者所以奉公上而不匮,盖常资之于贫。贫者所以无产业而能生,盖皆资之于富。稼穑耕锄,以有易无,贸易其有余,补救其不足,朝求夕索,春贷秋偿,贫富相资,以养生送死,民之常也。”(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9,神宗熙宁八年冬十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605-6606页。这生动揭示了贫富之间相互依存的一面,也说明进一步科学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三,力图对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再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演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如何对其进行阶段划分?有的基于历史发展法则进行划分,有的基于历史事实进行划分。我们主张基于历史事实进行划分。基于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上古的“部族社会”、汉唐的“豪民社会”、宋元明清的“富民社会”,并最终向近代“市民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这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阶段,也是中国古代史的新体系。
为实现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再认识的目的,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着力推动历史研究从平面式、静止式的研究转向一种立体式、动态式的研究,在研究中力求体现“三性”:
一是历史的变化性。
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化性。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中国古代“富民社会”这项研究,同样必须揭示历史的变化性。从“富民”阶层的发展变化来看,唐宋时期,经营农业致富的“富民”无疑占大多数。而到明清时期,经营工商业起家的“富民”则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以致有不少学者认为明清出现了“市民”阶层。其实,大家所引述的那些所谓“市民”,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富民”。从“富民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看,随着“富民”阶层对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获取,逐渐形成了一个“士绅”阶层。所谓“士绅”,主要就是依靠其取得的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的“富民”群体。从根本上说,“士绅”的来源和基础就是“富民”。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的士绅只能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来理解,因为他们是同拥有地产和官职的情况相联系的。……他们构成以地产为基础的家族阶层。”(2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7页。“士绅家族之所以能不断主宰农民,不仅靠其拥有土地,而且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士绅中间主要产生出将来可以被选拔为官吏的士大夫阶级”(22)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30页。。随着“士绅”阶层的出现,有学者指出,明清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23)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页。。我们认为,“士绅社会”是“富民社会”的最高阶段,同时也是其最后阶段。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揭示其变化。
二是历史的复杂性。
不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就很难真正地理解历史。中国古代“富民社会”这项研究,其复杂性尤其要引起注意。比如从“富民”阶层的社会角色来看,由于它是社会的中间层,这个阶层上通官府,下联百姓,有时可代表官府,有时又代表百姓,这个阶层与国家的关系,既有矛盾,又有依赖,始终处于博弈过程之中。唐宋以来的历次改革,主要着力点就是调整国家与“富民”阶层的关系。又比如,从“富民”阶层的社会形象来看,既有“长者”型,又有“豪横”型,如何评价其社会作用,就需要以历史眼光加以客观认识。所以,只有揭示历史的复杂性,我们才能够还原真实的历史。
三是历史的鲜活性。
历史是鲜活的,因为历史永远与现实相通。唐宋以来“富民”阶层的崛起和“富民社会”的形成,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其所引起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甚至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划分阶级,主要划分为五等。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了宋代的五等户制。当时,乡村主户也按照土地资财被分为五等。上户通常指一、二等户,有时也包含三等户,称为“上三等户”,属于地主和富农。三等户在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中户;四、五等户则称为下户,属于一般农户及少地而需佃种部分土地的农户(24)参见王曾瑜:《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梁太济:《两宋的户等划分》,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49页。。这与近代划分阶级时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序列颇为类似。由此,我们可以说,“富民”阶层的兴起,实为解构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把关键性钥匙,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富民社会”研究的重大理论意义。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行历史阶段划分与社会形态划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二者之间具有某种联系。我们今天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之所以存在重大分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分清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其混在一起,就很难讲得清楚。
个人以为,对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可各展其说,进行多元化实证研究。但对社会形态进行划分,则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原典,准确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把握好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提高学术站位,去科学准确揭示历史发展的中国道路。这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