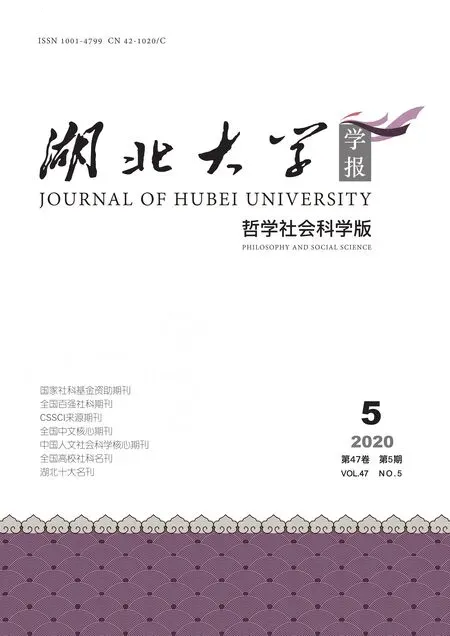在自我与他人之间
——论舍勒与萨特对“羞感何以发生”的还原
汤波兰
(长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一、被忘却的“羞”
对于“羞”,我们绝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与“羞”打交道。每个人都必定有过“羞”的经历,也经常会看到他人“羞”的表现。“羞”的现象在生活中是如此普遍,如吃饭穿衣一般与人形影相随,以至于通常都不为人所察。事实上,人们不关注“羞”,甚至有意忽略“羞”、遗忘“羞”——因为人们“怕羞”。“羞”似乎是生活需要之外多出来的一种情绪,它总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且不受控制:一个人不是想羞就能羞、想不羞就能停止羞的。“羞”从来不会由强迫而产生或终止。一个人的意识或意志再坚强,也决定不了“羞”的发生,借用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因为它“不是意识或意志的样式”注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6页。。“羞”有它自身的逻辑,这是一种“无中生有”的逻辑。一个人在“羞”的瞬间,往往忽然就面红耳赤、心跳加速、浑身振颤,焦虑、畏惧、懊恼、悔悟等一起涌上心头,脑海里开始萦绕一些避之不得的问题: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会这样?总之,在此刻觉得“羞死了”。显而易见,“羞”与人的生存状态有着密切关系,它让人感到生存际遇的困境。而“羞”当然也与人的道德生存状态有着密切关系——它是决定一个人道德感的重要因素。微观来看,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知羞”,是社会对一个人道德与否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而宏观来看,毋庸赘言,现代社会的道德滑坡与现代人司空见惯的“不知羞”表现之间,不会是偶然的巧合。我们常常感叹世道浇漓,人心不古。所谓人心不古,照舍勒看来,就是人失却了“羞”的“气质”,已难在现代人身上觅见“羞”的踪迹。当然,现代人的“无羞”,指陈的是现代社会的总体状貌,并不是说现代人作为个体完全没有了“羞”的体验。人,作为一种“有羞之在”,无论想羞与否,都难以从“羞”中彻底逃离——生命的完整历程必定会在“羞”的伴随中展开。就此而言,我们有充分理由去正视“羞”的现象,弄清楚“羞”的本质以及“羞”的体验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羞”的体验,可称为“羞感”,这是舍勒发明的一个概念。在“羞感”的名目之下,有一个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性”问题。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意指同一范畴之下的单个成员不必具有该范畴的所有属性,而是与其他成员在一定程度上相似,借着这种“家族相似性”,它们可归属于同一范畴[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不说“羞感”,而更习惯于谈论“害羞”、“羞涩”、“羞怯”、“羞耻”、“羞愧”、“羞辱”等等[注]日常语言中存在大量与“羞”有关的词汇,由此也可知“羞”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以及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些与“羞”有关的概念,即构成了一种家族相似性,我们仅仅通过字面意思很难把它们清楚区分开来[注]因为难以区分,所以在很多辞书中,干脆就用它们来相互界定。不过,也有学者从行为关系(主动或被动)、行为性质(失败、过错或受害)、行为相关者(包括现场者、期待者、竞争者、亲近者、受害者、敌对者等)与行为反应(包括逃避、适应、改进、改过、自强、报复等)等方面初步辨析了这些不同类型羞感之间的差异。参见陈少明:《关于羞耻的现象学分析》,《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它们表征的情感现象,相互之间没有一个是完全相同的,却都与“羞”有关,指示着与“羞”相关的感受与反应。但是,难以区分并不意味着这些概念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任何的不同,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把这些词语视为同义词。假如我们结合特定的场景,对切身的情感体验进行细致地分析,还是能够体察到这些概念彼此之间的细微差异。指出“羞感的家族相似性”,有利于我们把握特定的羞感现象,而不同类型的羞感具有相似表现,这意味着,至少有一种体验构成了“羞感”的最重要表征,这就是“害羞”。“害羞”代表着一种不能向外人宣示、无以名状、朦胧而私密的情态,它是最单纯的“羞感”,是“羞感”最本真、自然的表达。“羞耻”、“羞愧”、“羞辱”等其他更复杂的羞感,之所以归属于“羞感”,是因为它们在身体变化或外在表现上与单纯羞感相似,都会表现出“害羞”的姿态,如脸红、低头、视线转移、目光回避等,但是它们作为情感活动,在精神层面上展开的反思、自责活动则是单纯羞感所缺少的。另外,同样作为“羞感”,它们与外界的关系也不太一样:有的伴随着一些指向自我的负性评价以及某种行为上的抑制,要求有隐秘或隐私的特权;有的用于指称要求诉诸良知、自我谴责的事件,而这种要求是公开的。必须指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对于“羞愧”、“羞耻”、“羞辱”等复杂羞感似乎已有较多认知,但这仅仅是表象。因为在对“害羞”这种单纯羞感的认识上,我们恰恰是模糊的。这种模糊,并不是说我们不清楚“害羞”的外在表现以及由“害羞”表征的羞感得以产生的生理机制,而是由于羞感自身内容的复杂性和理解角度的多样性,在羞感的本质、羞感与道德、生存的关系等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依旧付诸阙如。我们依然可以发问:“羞”从何起?
这一困境的出现,当然有学理探讨不足的原因。如前所述,羞感是一种属人的、普遍的情感现象。然而,自古以来,伦理学家们却很少探讨“羞”的问题,去追问“羞”对于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羞感”在伦理思想史中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论题。在舍勒之前,仅有亚里士多德对羞感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作过专门但难称系统的论述。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对“羞耻”(羞感的一种形态)进行考察的哲学家,相关论述集中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四卷第九节(1128b10-1128b36)与《修辞术》第二卷第六节(1183b11-1185a16)。然而,亚里士多德主要围绕羞耻与德性之关系的论述,是经验论、自然主义意义上的,这种带有实证性的认识方法,其最大特点是将羞感作为外在对象予以考察,而其原则性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羞感本身与羞感的表达或表现形式[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林克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亚里士多德将羞耻(羞感)直接认定为一种道德情感,但羞耻与善恶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清楚说明。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对于羞耻是否为一种德性的回答,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他一方面说羞耻不是一种德性而是一种感情[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4页。,另一方面又说羞耻是一种“出于对某种高尚[高贵](即荣誉)的欲求和为着躲避某种受人谴责的耻辱的”[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83页。德性。更关键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对羞感的经验论处理,并没有(或者说难以)对羞感的产生机理(精神意义而非生理意义上的)给出根本性解释。
要超越对羞感的经验论、自然主义理解,克服其缺陷,只有遵循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才能做到。所谓“现象学的”,是指对“羞感”的理解,不应是反思性的、对象化的,而应是返身性的,亦即生存论意义上的,即直接从生存体验的直观描述中获得答案。现象学的“面向事实本身”要求回溯到羞感发生时的源初状态,使羞感“事化”、“情化”、“境化”,以便从中看到纯粹的“羞感现象”,这是界定羞感本质及其源起的必经之路。就此而言,舍勒的探索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舍勒对羞感作了最为出色的考察,有专文《论害羞与羞感》问世。关于舍勒《论害羞与羞感》一文的价值,弗林斯评价说:“人们一定会称赞舍勒的论文。在有关害羞现象的哲学文献中,这篇论文无疑是最优秀的。在其中,舍勒对现代社会中害羞如何变成一种罕见的人之为人的表现形式做出了很好的反思。”[注]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心灵》,张志平、张任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37页。舍勒的这篇论文(虽然并未完成)详述了羞感的本质、发生机制及其表现形式,并从中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在文中,“羞感何以发生”问题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说明。对此,舍勒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羞感具有“居间”发生的本性,羞感内嵌着一个“自我-他人”的发生结构,在所有羞感体验中,有一个“转回自我”的事件发生,在此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自我”(及自我价值)。有趣的是,萨特同样在“自我-他人”的结构中对羞感发生进行还原,虽然他的方法和进路与舍勒一样,都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但他却作了与舍勒几乎相反的思考,从而与舍勒构成了一组醒目的对比。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用了相当篇幅分析“羞耻”这种现象[注]萨特对舍勒《论害羞与羞感》一文似乎并不熟悉,因为这篇现象学的经典论文虽然早就发表了,但萨特在论及羞感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未有引用。参见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82-376页。。萨特虽然认同羞感的产生如舍勒所说,是对“自我感觉”的确证,说“羞耻实现了我与我的一种内在关系”[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282页。,但他更强调“他人在场”、“他人的注视”是羞感产生的前提。在萨特看来,在羞感体验中,除事关“自我”存在的明证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发现“他人”毋庸置疑的“存在”。以下试对舍勒与萨特就“羞感何以发生”的解答作一梳理评析。
二、羞感:转回自我
舍勒认为,人具有生命与精神的双重本质,但是,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是“精神”[注]舍勒:《哲学人类学》,罗悌伦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舍勒的“精神”概念具有独特的含义,从现象学角度来看,“精神”即各种意向性行为,它在外延上不仅包容了传统西方哲学中的“理性”概念,还含有情感、意志之意,是理性、意志与情感行为的复合体。“精神”这种“自我意识之光”使人拥有了感觉自身的能力,也正是“精神”造就了人的“自我意识”。精神的这种作用,最鲜明地反映在人的羞感体验(“羞感”也属于精神范畴)中。在人的双重本质结构的敞开中,羞感伴随着对“自我”的感觉而出现,羞感“是对我们自己的感觉的一种形式,因此属于自我感觉的范围”[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4页。。换言之,在羞感体验中,人感觉到“自我”,并由此产生出自我意识。那么,人是如何在羞感体验中感觉到“自我”并产生自我意识的?舍勒指出,在任何羞感体验中,都有一个被他称为“转回自我”的事件发生,而“转回自我”既是“引起羞感的原动力”[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6页。,也是对“自我感觉”的一种确证。
舍勒描绘了许多事例来解释“转自回我”。例如,在一场突发的火灾中,一位被惊醒的母亲,为了从大火中救出自己的孩子,她并不会先好穿衣服,而是急忙抱起孩子往外冲,等到脱离了危险,她忽然注意到自己只穿着内衣或光着身子,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羞感。再例如,一个沉浸于爱情之中、本来很怕羞的女子,在与钟爱之人相会时,她的感觉和目光完全被对方吸引过去了,以至于在爱人面前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衣衫不整,直到爱意稍稍褪去,沉醉稍稍松懈,她忽然萌发出对自己和自己身体的意识,羞感也将随之而产生[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4-185页。。在这两则事例中呈现的就是典型的“转回自我”。而从这些事例来看,所谓“转回自我”的机理是:一种指向外部的强烈兴趣(专注于某个人或某件事)吸引着一个人,使他/她的自我意识暂时消失,排除了他/她对自我的感知与察觉,甚至忘记了自我的存在,而当他/她的注意力从对兴趣的专注中“苏醒”过来、“转回”到自我时,他/她就会产生羞感。
首先,“转回自我”现象说明,“羞感”与“自我”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羞感以人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力为前提。这一点可以在心理学研究中获得一定的认同。心理学研究认为,儿童在早期阶段没有自我意识,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因而是没有羞感的,他们在生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害羞”,并不是真正的害羞,而是由陌生人引起的“恐惧”[注]参见威廉·麦独孤:《社会心理学导论》,俞国良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3页。。然而,羞感的产生与自我意识的萌发并没有孰先孰后的顺序,与其说羞感产生于“自我感觉”,毋宁说羞感就是一种自我感觉行为,这应该更符合舍勒的本义。作为自我感觉行为,羞感具有意向性特征。通常人们会认为,羞感的意向相关项是“自我”,羞感是以“自我”为对象的体验。舍勒却认为,羞感“与我们的个体的‘我’之状态毫无关系”[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9页。,也就是说,羞感的意向相关项不是“自我”——既不是“自我性质”,也不是“自我状态”。一个人并不会因为感觉到“自我”就产生羞感体验。羞感只与某个事实相关,“这个事实自发地‘要求’害羞”[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9页。。在舍勒那里,这是与“价值”相关的一个事实,是不同等级价值之间相冲突的事实[注]舍勒构建了一个“质料价值系统”,其中包含四种价值样式,按照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感性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舍勒认为,羞感是一种意向性情感,它始终以价值为意向相关项。羞感发生时,必定伴随着对价值的感受,而且对价值的感受越强烈,羞感也就越强烈,同时,对羞感的遮蔽冲动也越强烈。羞感反映了不同等级价值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羞感产生于不同等级价值意识的碰撞和冲突,其中较低等级的价值威胁着较高等级的价值,较高等级的价值抵抗着较低等级价值的威胁。参见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5-171页。。所以,在根本上,羞感的意向相关项是“价值”。羞感的感受对象是自我价值,自我感受原本也与价值相关,是对自我价值的感受(严格地说,是人在转回自我后的自身价值感受)。这种自身感受和自身价值感受是原本的,并非来源于他人的印象。
其次,“转回自我”通常是转回作为“个体”的“自我”,进而形成一种关于“自我”的“个体感”:“自我意识是直接的‘对自己作为个体的意识’”[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284页。。可见,羞感与自我的个体性有关。在舍勒看来,羞感“这种感觉与生命单位的个体化程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72页。,“个体化”指明了与羞感产生有关的先决条件。“个体”与“个别”不同,生命可以在作为“个别化”存在的同时缺少“个体性”。例如,植物是个别化的存在,但植物之间不存在个体性差异,因为植物没有个体性;动物具有一定的个体性,但动物缺乏自我意识,故产生不了羞感,不会“难为情”。人则不然,人是既有个体性又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存在。个体化的意义在于:“生命个体化程度越高,生命个体的价值差异就越明显,与此相应的价值差异意识就越强”[注]张志平:《情感的本质与意义——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而一切羞感的产生都是以生命个体的价值差异意识为前提的,只要有价值差异意识出现(这种差异意识最终落实在自我身上,而非他人身上)的地方,就会发生“转回自我”并产生“羞感”。这涉及到“普遍化”与“个体化”的矛盾。对此,舍勒也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比如,一位裸身的女子,分别以“模特”、“病人”、“女主人”的身份出现在画家、医生、仆人面前时,都不会感到害羞,因为此时的她,是作为一个“普遍的”、“一般的”对象、一个类的成员出现,而不是作为“个体的”、“特殊的”对象被关照,她消隐于这种类成员的身份之中,没有要为之害羞的东西。但假如她感受到自己的类成员身份“消失”了,被画家、医生、仆人以“这个女人”(而非“模特”、“病人”、“女主人”)的眼光打量,“转回自我”便会发生,她就会产生强烈的羞感。当然,舍勒认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即由一开始的作为“个体的”对象出现,转变到作为“普遍的”对象出现(设想一位与情人幽会的女子,她感到对方不再以独一无二的“恋人”眼光看待她,而是在打量“一位美丽的女性”),也会发生“转回自我”,并产生羞感体验。这意味着,“转回自我”与羞感不会出现在一个人无论是作为“普遍的”或“个体化”的对象被给予之时,而只会在“普遍的”看法与“个体的”看法发生冲突——“自己的意向和所体验到的对方的意向不相同,而是相反”[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6页。的时候出现。一言以蔽之,羞感发生于“普遍化”与“个体化”的矛盾、冲突之间。
如前所述,从意向对象来看,羞感是对自我价值的感受。不过,羞感意向的并非自我的所有价值,“真正的羞始终建立在对肯定的自我价值的感受之上”[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215页。,而与否定的价值无关。通过“转回自我”,羞感将阻止那种与自己预期意向相冲突的意向转移(无论是从“普遍”转向“个体”,还是从“个体”转向“普遍”),以保护自我以及自我的肯定价值(只有肯定价值才值得保护)。换言之,羞感与“个体性”的维护有关,是个体在面对普遍性时对自我及自我价值的保护。这种保护,一方面是抵制较低层次价值的侵犯或诱惑,使人意识到不应该置自我于当下的状况和情势中,从而避免陷入自我价值沉沦的处境,即堕落于较低层次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呵护更高层次的自我价值,使之免遭侵袭或亵渎,此时,羞感就像是一道“不可伤害的屏障,像界限一样围绕着人的身体”[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96页。,它“首先是高贵的生命针对卑贱的生命的一种自我保护”[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256页。。在此意义上,舍勒将羞感比喻为保护自我的“天然的灵魂罩衣”[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96页。。
舍勒反复强调,羞感是出于自我的体验,是人对自我及自我价值的一种意向形式。虽然在羞感体验中常常会有一个面对他人的问题,有他人的在场甚至他人的注视,但是羞感的本质界定中并不包含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羞感可以与他人无关,因为他人在场、他人的注视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羞感产生的必要条件和直接动因。就像在前述事例中,一个怕羞的裸身女人,被画家、医生、仆人注视着,甚至她也知道被他们注视着,却可以没有羞感体验。舍勒认为,羞感由被注视引起,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是一种错觉,事实是“知道被人注视本身还不一定引起羞感”[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5页。。“注视”虽能带来直接性的感受,但并非所有的“注视”都能令被注视者产生羞感。羞感的产生不取决于“注视”本身,也不取决于被注视者是否知道“被注视”,而取决于注视者与被注视者的价值意向是否一致,取决于羞感的原动力——“转回自我”是否被引发。只有被注视者预期的价值意向与注视者的价值意向发生了冲突(如发生了“普遍化”的“模特”、“病人”、“女主人”与“个体化”的“这个女人”的冲突),或者说由于双方的价值意向错位,被注视者转回自我,才会萌生羞感。可见,相比于“知道被他人注视”,“转回自我”才是羞感产生的关键一环。即使由他人注视引发了羞感,羞感所牵涉的仍是关于自我价值的一个事实:无论是面对自我,还是面对他人,在羞感中体验到的都是一种自我价值之意向冲突(发生在普遍化的价值与个体化的价值之间)。甚至,在舍勒看来,还可以有纯粹的面对自我而羞,比如,一个怕羞的姑娘仅仅在镜子面前打量或触摸自己的身体,就会萌生羞意,足见羞感的产生与他人是否在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舍勒认为:“就像在他人面前的害羞一样,在害羞一词的每个方面都存在同样本源的‘面对自己的羞涩’和‘面对自己感到害羞’”[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3-184页。。归根结底,羞感与他人无关,而只与自我相关,是自我面对自我而羞。
值得注意的是,舍勒并没有在羞感体验中完全排斥“他人”承担一定角色的可能,因为他很清楚地谈到:羞感虽然是一种自我感觉,“但这绝不是说,它因此始终只与害羞者的个体的自我相关”[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8页。。言下之意,羞感可以与他人相关,具有内向性特征的“羞感”也可以出现在主体间的交往过程中,从而具有一定的外向性。舍勒明确指出,在源初地“面对自己而羞”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源初地“面对他人而羞”,甚至,我们还可以同样源初地“替他人害羞”。可见,在舍勒这里,羞感的发生分为他人不在场与他人在场两种情况:他人不在场时,“我”可以“面对自己而羞”;他人在场时,又包含两种情况——“我”可以“面对他人而羞”,或者可以“替他人害羞”。对于后者,舍勒也举出了一个“可以常常观察到”的事例来说明:听人讲不正经的故事,如果在场的都是男人,“我”不会感到害羞;但是有一位姑娘在场,即使这位姑娘并不害羞,“我”也会体验到强烈的羞感,为之脸红[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8页。。那么,“替他人害羞”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羞感体验?又是如何产生的?可以肯定的是,“替他人害羞”虽然涉及他人,但产生“羞感”的依然是“我”,是“我”在羞,不是他人(讲述者)在羞,羞感的主体没有脱离与他人相对的“自我”,只不过,此时,“我”的“羞感”由他人引起,“我”为之感到害羞的事实,不是“我”的行为,而是他人对第三者或“我”的行为(在一位姑娘面前讲述不正经的故事):“就像一个套语所明确表达的那样:‘我从你自己的灵魂深处感到羞愧’”[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8页。。在“替他人害羞”中,“我”体验到的依然是一种价值意向之冲突,一种“对个体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是针对一种总之已被给定的自我,无论在我身上或是在他人身上”[注]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第188页。。“被给定”意味着,他人的行为成了“我”的自我(意识)的内在构成,由于其价值层次与“我”的自我价值标准不一致(低于“我”的自我价值层次),“我”因此体验到羞感。可见,“我”不是单纯的个体形式,而可以扩展到“他人”(通常“他人”都不是陌生人,而是“我”热切关心的人),此时“他人”被赋予了自我的价值形象。一个人能在多大范围内替他人害羞,可以体现出这个人的自我圈的大小。所以,“替他人害羞”并不是真正替代他人去感受“羞”,真正的“羞感体验”是无法替代的。“替他人害羞”虽由他人而起,实际是以“我”的“善羞之心”替“他人自我”而害羞。另外,“替他人害羞”不同于“羞他人”。严格来说,“羞他人”不是一种羞感体验,而是“我”对他人在某种情境中的行为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否定态度:他人之行为违背了应然之则,假如是“我”,“我”会对此害羞,而他人却没有为此感到害羞(例如,在上述情境下,讲述者没有为在一位姑娘面前讲不正经的故事而“害羞”),这时,“我”通过“羞他人”来督促、刺激他人产生羞之体验。从根本来说,“羞他人”指向的是“他人”,应羞的是他人而不是“我”。可见,“替他人害羞”与“羞他人”的主体与对象都不同:“替他人害羞”中的主体是“自我”,对象是“自我价值”,“他人”及其行为只是作为中介出现,而在“羞他人”中,“他人”及其行为构成了对象,羞之主体却悬而未定,只有当“我”的“羞他人”行为唤醒了他人的“羞心”,羞感才会出现,真正的“羞”之主体才落实为“他人”。“羞他人”实际是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一个基于“我”的立场对他人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当然,“替他人害羞”与“羞他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二者的前提和基础都是一个有尊严的“我”以及“我”的价值观念,这个有尊严的“我”能够自觉按应然之则行事:“替他人害羞”当然是对自我高等级价值的肯定,“羞他人”则通过对他人行为所作的否定评价,反映了“我”对应然之则的领悟、贯彻以及对可羞行为的疏离,从而体现出对自我价值的维护。
总之,对于“羞感何以发生”,舍勒强调关键的一环在于“转回自我”,并且,通过羞感,我们感受到的是“自我”(及自我价值)。无论他人是否在场,无论是否有他人注视,羞感都有可能被体验到。羞感的发生,不必有“他人”的“参与”,通过羞感,我们不能像确证感受自我一样确证感受他人(因为“他人”是缺席的)。当然,在“替他人害羞”问题上,反映出了舍勒对羞感“他人之维”的模棱两可态度。一方面,舍勒认为他人的存在并不能在羞感体验(即使是替他人害羞)中得到确定;另一方面,舍勒似乎又认为羞感的发生结构可以是人际互动的,在羞感中,自我和他人可以是处于联系中的双方。在那个“可以常常观察到”的事例中,舍勒并没有讲清楚“替他人害羞”与第三者(姑娘)的关系:“我”“替他人害羞”,仅仅是因为有一位姑娘在场(无论该姑娘是否害羞),还是因为这位姑娘感到了害羞,而在“我”身上产生了同感,又或者在“我”身上产生了情感迁移,以至于“我”要“替他人害羞”?归根结底,我们还是需要证明他人是否存在,需要澄清“我”能否把握他人,需要解释“他人如何在一个人自己的自我之内被给予和被经验”[注]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心灵》,第78页。。因此,回答“羞感何以产生”,存在从“他人之维”切入的可能性,而这正是萨特所做的工作。
三、羞感:他人之镜
如前所述,舍勒与萨特都是在现象学意义(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是现象学的一个变种)上讨论羞感。舍勒认为,羞感是一种与价值事实相关的意向性情感,萨特则认为,羞感是一种与行为相关的意向性情绪,是意识的一种样式。萨特所说的行为,和舍勒所说的事实一样,是直接的、源初的、非反思的,因此“尽管羞耻的某些复杂和派生的形式能在被反思的水平上显现,羞耻一开始却不是反思的现象”[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282页。。萨特认为,情绪“是对于新的关系和新的要求的把握”[注]萨特:《萨特哲学论文集》,潘培庆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9页。。情绪出现在意识走向世界的通道被中断之时:当领悟到无法改变世界,把握某一对象变得不可能,由意识所引导的身体就通过非反思行为——情绪,在改变自身的同时改变世界的实际性质和结构,“即意识通过改变自己来达到改变对象的目的”[注]萨特:《萨特哲学论文集》,第89页。。羞感就是这样一种情绪。问题在于:是谁,以何种方式,切断了意识走向世界的通道,以至于使“我”产生了“羞感”这种情绪?对此,萨特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其一,“我”以自为的方式做了一个粗俗的或笨拙的动作,抬起头,突然发现有人在看着“我”,“我”一下子为自己的动作感到羞耻[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283页。;其二,“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或透过锁孔向门里偷窥(即使是无意的),忽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有人注视我,“我”感到自己是一个羞耻的存在[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26页。。萨特试图通过这两个例子说明:是“他人”通过其“注视”切断了“我”的意识通向世界的通道,让“我”感觉到“我”,并对我的行为(亦即对“我”)感到羞耻。
显然,在萨特这里,羞感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即“我”、“我的现实行为”与“他人的在场”(以“注视”为表征),三者缺一不可。羞感是对这三者的统一“领会”:羞感既不在“我”的意识之中(“我”的庸俗的动作不是“我”有意识地做出来的),也不在“我”的身体之中(当“我”侧耳倾听时,“我”并没有“脸红”),同时也不在他人之中(是他人的注视使“我”感到羞耻,不是他人感到羞耻),而是存在于这三者构成的某种结构之中——萨特的描述是:“羞耻按其原始结构是在某人面前的羞耻”[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282页。。这个羞感发生结构的核心,并不是作为被注视对象的“我”与“我的现实行为”所构成的具体处境,而是在他人的注视之下,作为行为主体的“我”产生了自我意识,并开始将“自我”作为审视和反思的对象,为这个“我”之所是的具体处境感到汗颜。所以,萨特认为,“羞耻假设了一个对别人而言的对象——我,但是同时也假设了一个感到羞耻的自我性”[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62页。。羞感的本质在于“我在他人面前对我感到羞耻”[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62页。。如果没有他人的注视,自我意识就难以被激活,也就产生不出羞感。
因此,在萨特看来,他人的注视才是羞感产生的关键一环。具体而言,他人的注视将“我”对象化了,在对象化过程中,“我”获得了自己的规定性,实现了对自己的认识。他人的注视使“我”意识到“我”自己:“我看见自己是因为有人看见我”[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27页。。所以,羞感可以认为是由他人的注视在“我”身上产生的返身作用造成的。“我”在被他人注视时,他人的目光相当于一面“镜子”。“我”自己并不能直接“看”到自己的面貌,只有借助“他人之镜”,并通过这面镜子投射过来的“自我镜像”,才能间接地“看”到自己,这镜像对“我”产生羞感有直接的激发作用:“我”通过镜像来衡量自己,比照镜像来审视自己,形成对自我的认识,“我”没有把握“我”能够经得起镜像的衡量,因此对自己“所是的存在”感到羞耻。原则上,这面“他人之镜”不必是物理意义上的场镜,而可以是心理意义上的心镜,亦即不必真的有他人在注视“我”,只要“我”想象甚至错误地认为被人注视着,羞感就可能产生出来。
萨特对“注视”的看法别具一格。在萨特这里,注视不是通常所谓的“知觉”。两者的区别在于:知觉是对知觉对象的“看”,它可以与知觉对象无关,而注视不是一种单方面的、具体的“看”,不是两个眼球的聚焦,它可以表现为“树枝的沙沙声”、“寂静中忽然响起的脚步声”、“窗帘的一次轻微晃动”等等,以至于“我”会感到注视无所不在(虽然往往是虚惊一场)。所以,注视与被注视者的意识相关,“是意识到被注视”[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26页。。这也决定了眼睛在知觉和注视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不同。对于知觉来说,眼睛是不可或缺的、单纯的视觉器官;对于注视来说,眼睛则不是突出的参与因素,而是构成了注视的物质基础和被注视的背景:“我”在被注视时,如果“我”体会到注视,“我”就不再知觉到注视“我”的眼睛,也感觉不到“我”与注视“我”的眼睛的距离——萨特这样描述到,“他人的注视掩盖了他的眼睛,它似乎是走在眼睛前面的。这种幻觉的产生,是因为眼睛作为我的知觉对象,保持着在我和它们之间展开的一段确定的距离”[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25页。。此一距离是如何形成的呢?归根结底,形成于他人的注视对“我”的分隔,亦即由注视所引发的“我与我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由注视所建立的不仅仅是一种“我”与“我”(以及“我”与他人)的认知关系,而且也包含一种“我”与“他人”的存在关系。
总之,是他人的注视引发了“我”的羞感。在羞感中,“我”究竟是为什么而羞呢?萨特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羞之所羞者是自我的存在,是“我对我所是的东西感到羞耻”[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282页。。羞的对象被萨特指定为“我”,而“我”之所以能成为羞的对象,是因为在他人的注视中,“我”的自由和超越性脱离了自身,“我”成了他人注视、判断、给定的那个对象。在被注视之前,“我”是“自为的存在”,是“我”的处境的主人,是主动的行为者,行为(如前例中的“偷窥”)本身并不会给“我”带来羞感,而在发现他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之后,“处境”脱离了“我”,“我”之所以感到羞耻,是由于他人的注视揭示了“我”的存在状态——“我”现在这个样子,并且这种存在状态是向他人显现,因为“通过他人的显现本身,我才能像对一个对象做判断那样对我本身作判断”[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283页。,判断“我”就是他人所看见的那个样子。与此同时,“我”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我”被他人的注视固定住了,丧失了(表面上的)自由,成为被他人构组、打量和评价的客体——某种对象化的东西,它规定着“我”,使“我”从“自为的存在”一下子退化成了“为他的存在”,而“这个存在不是我的可能,它并不总在我的自由内部的问题中;相反,它是我的自由的限制”[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29页。,而“使我认为他人是使我变成对象性的主体的态度——这就是羞耻”[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63页。。“我”为这个向他人显示出来的“我”的具体存在感到羞耻。逃避这种羞耻性存在的梦想,也成为了“我”的内在超越冲动:羞耻证明了“我”的这种存在,而“我”想要否定它。总之,“正是羞耻和骄傲向我揭示了他人的注视和这注视终端的我本身,使我有了生命”[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28页。。在此意义上,羞耻是一种对自我存在状态的确认:“我”通过羞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在确认“自我”的存在之外,萨特认为,在羞感体验中,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发现“他人”无可置疑的存在。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一直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如何才能证明“他人的存在”?在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中,“自我”与“他人”构成了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由这种认识关系必然牵引出的疑问是:“他”是谁?“他”“在”吗?从“我在”能否通达“他在”?知觉无法证明他人的存在,因为“他人”不仅有一个物质性的身体,“他人”还有心灵、意识,“我”能够感知他人的身体,却无法知觉他人的心灵,否则的话,“我”便与他人合为一体了。然而,他人又是一个可见的实体,他人恰恰存在着,由此便出现了一个难题:怎样以非知觉的方式来证明他人的存在?萨特认为,对于“我”来说,他人只能以“主体”和“对象”两种形式出现,其他任何形式或者这两种形式的任何综合都是不可设想的。然而,一方面,如果“我”明白地感受到作为主体的他人,“我”就不能认识他,不仅对他无法形成任何概念或知识,也无法作用于他,与他发生任何交往上的关系——因为作为主体的他人根本不可能被认识,在主体性中他人什么也不是;另一方面,假如“我”能够认识作为对象的他人,“我就只达到他的对象存在和他的没于世界的或然实存”[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76页。,因为作为认识对象的他人只不过是他的一系列表现与活动。所以,无论如何,他人是无法被我知觉到的。在某些场合下,他人甚至不是指具体的个人,而是未被分化的、模糊不清的、复数的,在此情况下,“我”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有”他人呢?萨特认为,“我”与他人的关系应该“归结到我的意识与他人的意识的最初关系上。在这种关系中他人应该作为主体直接给予我”[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20页。。他举例说,“我”在做一次公开演讲,“我”被听众注视,被对象化了;当“我”的注意力放在演讲上时,听众(他人)的在场是未分化的。如果“我”的注意力转到听众,比如想弄清楚听众是否正确理解了“我”的演讲,因此反过来注视听众,这时,听众就对象化了,作为一个模糊的整体也解体了、复数化了(变成一个个的听众),而听众的注视也消失了。通过这一事例,萨特试图说明他人的非认知性,同时也指明了确证他人的方式——“看到我们被注视”[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53页。:只要“我”真切地体验到他人的注视,“我”还有理由怀疑他人的存在吗?“注视”切断了“我”与世界的关联,在他人被直接给予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人就是注视着“我”的人。所以,他人的注视,不仅引发了“我”的羞感体验,让“我”发现了“自我”,也让“我”“看见”、“发现”了他人。
他人的注视使“我”成其为“我”。在他人的注视中,“我”不仅体验到了羞感,也同时体验到了他人,注视的无所不在也揭示了他人的无所不在。萨特在羞感中开出了一个自我与他人的二维空间。羞感是在“我”与“他人”的关系当中被体验到的,羞感映射了“我”与他人的关系:一方面,他人是“我”和“我本身”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事实上,他人不仅是我看见的人,而且也是看见我的人”[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290页。。“我”是通过他人来完成对自我的认识的,在此意义上,他人的存在是确定“我”存在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我”是被他人注视的对象,是一种“被注视的存在”,无论他人是真实在场还是由自我虚拟出来的在场,“我怎样向别人显现,我就是怎样”[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00页。,“我”都有“为他”存在的一面。这就是“我与他人的互为规定性”:他人从“我”这里确认其存在,“我”也从他人那里确证自己的存在。萨特说:“注视使我们跟随我们的为他的存在,并且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对他而言才存在的那个他人的无可怀疑的存在。”[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53页。然而,羞感既向“我”显示了“他人”无可质疑的存在,也暗示了互为对象的“我”与“他人”之间具有一种“敌对关系”。由于意识到了自己,“我”就有可能起来反抗,夺回“我”的自由,“我”也可能把“他人”凝固在“我”的存在中,由此,在“我”和“他人”之间就出现了一场“注视”的决斗,一场没有最后的胜利者的竞争:“我们不停地由注视的存在向被注视的存在摇摆,并由于交替的变革而从这二者中的一个落入另一个”[注]萨特:《存在与虚无》,第499页。。萨特想强调的是,“我”与“他人”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肩并肩的共在关系,“他人”不是“我”可依赖的伙伴,而是充满敌意的、异己的,“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填满的虚无,相互冲突、相互否定。众所周知,最终,萨特就这种关系做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形容:“地狱即他人”[注]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
结语
由以上可见,在解答“羞感何以产生”时,舍勒与萨特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舍勒来说,通过羞感,“自我”体验到的是意向价值的冲突,羞感唯一确证的是“自我”,单纯立足于“自我”本身,羞感也是可以理解的,亦即,无论他人是否在场,无论是否有他人注视,羞感都有可能被体验到,羞感的发生不必有“他人”的“参与”,在羞感中,不能像确证感受自我一样确证感受他人(因为“他人”是缺席的);但是对于萨特而言,羞感所表明的是水平层面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它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为条件,体现着“个体对他者如何看待自我的意识”[注]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羞感所确证的是注视“我”的他人,如果没有他人在场,哪怕是想象的他人,羞感将是不可理解的。舍勒从羞感出发过渡到自我,其关键的环节是“转回”,而萨特则从羞感出发过渡到他人,其关键的环节是“注视”。不过,这一显著差异并不妨碍舍勒与萨特可以在更根本的问题上取得共识。他们都认同羞感体验内嵌着一个“自我-他人”的发生结构,他们借回答“羞感何以发生”,来探究“自我”、“他人”以及二者的关系,利用羞感这种情感(情绪)体验来彰显“自我”与“他人”的主体间性,同时也拓展了对主体间关系的理解:主体间的关系并不只是一种认识关系,还是一种存在关系。在方法上,他们都是“现象学的”,这个定语是他们思考羞感的特征,也是他们整个伦理学思考方式的特征:用现象学的方法来把握意向性感受活动与意向感受相关项之间的关系,试图在对情感现象的实证描述与超验的形而上学建构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从理论意义来看,他们对羞感发生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是从生存体验的直观描述获得答案(有意识地这样做),超越了以前对羞感现象的自然主义认识,证明了现象学方法可以运用于以往被视为纯粹经验的领域,从而开辟出一条从情感理解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