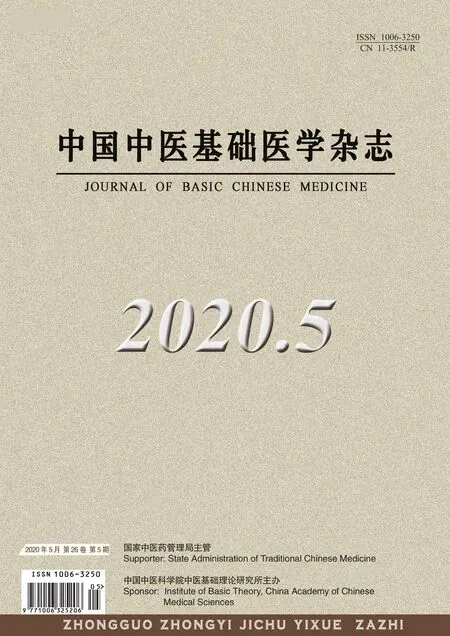术语“药对”源流考❋
臧文华,卞 华,白红霞,蔡永敏,3Δ
(1.南阳理工学院张仲景国医国药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4;2.河南省张仲景方药与免疫调节重点实验室,河南 南阳 473004;3.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郑州 450046)
药对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经实践证明有效的2味药物的配对使用。在现代中医药学名词术语规范确立以前,“药对”“对药”“姊妹药”“对子药”等各种不同的名称散见于古今医籍著作中,少有文献对其系统梳理与归纳。本文通过查阅考证古今医药学著作,考释“药对”术语的源流与沿革,分析前人对这一术语认识的发展脉络,对“药对”及相关名称进行辨析,为其规范定名和相关术语的正确应用提供参考。
1 “药对”配伍的理论基础
关于药对配伍的内容最早可追溯到先秦的文史资料,如《吕氏春秋·别类》即有合药而服,能愈人病,能益人寿的记载,即“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1]。《吕氏春秋·本味》亦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1],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之复杂性,单味药或难取效,故出现了2味或2味以上药物配伍治疗疾病的临床实践。
药对的配伍内容还见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我国最早的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其中“疽病”篇曰:“冶白蔹、黄耆、芍药、桂、薑、椒、茱萸,凡七物。骨疽倍白蔹,肉疽倍黄耆,肾疽倍芍药,其余各一”[2]。方中通过不同药物的配伍,分别用于治疗骨疽、肉疽、肾疽。该书中虽无药对配伍理论,但已初步体现了药对配伍的雏形。而同时期经典著作《灵枢·邪客》即有半夏与秫米配伍治疗“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暝”[3],《素问·腹中论篇》亦有“以四乌鲗骨一藘茹,二物并合之”治疗“血枯”[4]等药对雏形的记载。《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4],从药物的性味合和角度阐述药物的配伍运用。该书不仅论述了药对配伍原则,而且还为后世留下了药对配伍的典范。
在《神农本草经》中,虽未直接提出“药对”之名,但已有药物相互作用的“七情”理论记载。如《神农本草经》卷一载:“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5]”又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5],这些论述就是药物配伍运用的最早准则。《黄帝内经》之性味配伍,《神农本草经》之七情合和,从不同角度阐释药物配伍,为药对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 “药对”配伍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张仲景全面总结了汉代以前丰富的临床经验,提供了辨证论治及方药配伍的重要原则,从临床角度对“七情”配伍用药理论进行了全面印证[6],应用药对不下百余种。《伤寒杂病论》中不仅有相须、相使药对,还有相畏、相杀药对,更不乏相恶、相反合用的例证。张仲景颇得药对使用心得,在《伤寒杂病论》中有许多应用药对治病的经验,以2味药组方达40余首,成为后人研究药对的基础。如由半夏、生姜组成的小半夏汤主治“诸呕吐,谷不得下”[7]。《伤寒杂病论》中的经典药对已为后世医家所沿用,如和解少阳药对柴胡、黄芩,调和营卫药对桂枝、白芍,缓急止痛药对芍药、甘草,疏肝柔肝药对柴胡、白芍等。
历代医家不断丰富和发展药对的内容,并有著述传世,以“药对”命名的文献,见于成书公元2世纪初的《雷公药对》。此书是一部托名雷公的药物学著作,作者不详。陶弘景认为本书在药物主治及品种方面较《神农本草经》有所补充。此书还收载了一些新的药物,并论及药物的佐使相须。此外,北齐徐之才撰《药对》二卷,后世医家认为此书是在《雷公药对》的基础上加以修订而成,《嘉祐本草》称其“以众药名品,君臣佐使,性毒相反及所主疾病,分类而记之……其言治病、用药最详”[8]。但《雷公药对》与《药对》皆已亡佚,仅能从现存的其他著作中见到部分内容。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一“序录”载:“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华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9]”《新修本草》卷二“药对岁物药品”条下载:“右此五条出《药对》中,义旨渊深,非俗所究,虽莫可遵用,而是主统之本,故亦载之。[10]”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第二卷“药对岁物药品”条下载:“此亦《素问》岁物之意,出上古雷公《药对》中,而义不传尔”[11]。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小品方》《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医籍大量收录了临床常用药对及其组成的方剂,如《小品方》以杜仲、牡蛎配伍治虚汗[12],《备急千金要方》以葱白、生姜配伍治疗妊娠伤寒[13],《外台秘要》以葱白、淡豆豉配伍治伤寒初起等[14],都可谓药对应用之典范,但此时期的医籍著作中常是有方无论,对药物的协同作用、药对的配伍规律及配伍理论述及较少,医家遣方用药更多是经验的积累,未能将临床用药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宋金元时期至明代,学术争鸣气氛活跃,众医家著书立说,创制新方,阐释方义,有关两药配伍的论述更是屡见不鲜,药对配伍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宋·宋令祺撰《崇文总目辑释》卷三载有《新广药对》三卷[15]。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开方论之先河,其卷四专论方药,将药之寒温,证之虚实,方之大小、奇偶等加以分析,强调药物配伍制使的关系,书中不乏关于药对配伍的经典论述[16]。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将《素问》中62个病证逐条分析,制定处方,其中诸多药对配伍体现了其偏重寒凉、降火益阴的学术思想[17]。《丹溪心法》所载左金丸(又名回令丸)[18]、《景岳全书》所载洁古枳术丸[19],既是经典药对又为常用方剂,药对配伍也由经验上升为理论,对指导临床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明代医家不仅继承了前人有关药对配伍的方法,且在临床实践方面又有创新。如《韩氏医通》专列“药性裁成”一章,认为通过炮制、配伍,可使药物发挥多种作用,更加适应病情,即“药有成性,以材相制,味相洽而后达”[20],书中对补益药对的配伍应用,尤具心得,如论述当归“主血分之病……血虚以人参、石脂为佐;血热以生地黄、姜黄、条芩,不绝生化之源;血积配以大黄”[20]。并以苏子、莱菔子、白芥子配伍,创制名方“三子养亲汤”[20],为后世常用方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总结了前人药物配伍的经验,还对前人的药对作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如对徐之才10剂药对的补充纠正,对易水学派关于药对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等[21],丰富了药对配伍的内容。
3 “药对”配伍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清代大量方论专著的出现,使得药对配伍理论的发展日渐成熟。医家在药对配伍理论上进行了全面探讨与实践。如罗美所著《古今名医方论》中集多位医家对名方的评述选方严谨,论方精审,其中不乏大量关于药物配伍的精彩论述[22]。《得配本草》是清代论述药物配伍的专著,重点阐述了药物间的配伍作用,可以说是自唐宋以来论述药对最多且最详的著作。书中以得、配、佐、使、和、合、同、君等类别论述药物配伍后的功效和主治,对指导临床配伍用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得配本草》卷二载:“知母,得人参,治子烦。得地黄,润肾燥。得莱菔子、杏仁,治久嗽气急。配麦冬,清肺火”[23]。分别列举了知母、人参药对,知母、地黄药对,知母、杏仁等药对的作用。此外,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24]、吴仪洛《成方切用》[25]等蓍作集各家之言,详述组方理论,尤重于配伍原理的阐释,对于配伍用药的分析也较为详细,扩充了药对配伍理论的内容。徐灵胎《医学源流论》设专篇论方药配伍,卷上“方药离合论”及“古方加减论”阐发古人制方及药物配伍之微旨妙义,可谓融会贯通,剖析入微,对药对配伍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贡献[26]。
近代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重视药物配伍研究,拟方遣药注重实效,书中所载诸多药对的配伍应用巧妙精当,有寒药与热药同用,补药与攻药俱行,润药与燥药兼施,通药与涩药并存等多种配伍形式,开拓了药对配伍应用和研究的思路[27]。现代中医药学著作如《中药配伍运用》阐发了药对配伍应用之精义[28],《药对论》将药对按功效分为13类400余对[29],《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收编药对24类277对[30],《中医临床常用对药配伍》收编药对11类509对[31],《中药药对大全》系统论述了药对组成、作用及应用,并列举600对药对的功效特点、临床效用等[32]。《名医效验药对》辑录了名中医应用药对之经验,按不同的病证分类列举了效验药对的主治应用[33],这些专论药对配伍的著作不仅收编了大量中医古籍中的经典药对,还总结了近现代名中医应用药对的临床体会,更创制了许多现代药对,大大促进了药对理论的完善。
4 “药对”及相关名称辨析
“药对”之名始见于成书公元2世纪初的《雷公药对》,后世的本草著作均沿用该名称。明代医家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又将这种常用配伍的药对称为“对药”,其卷六“瓜蒂散方”条下曰:“瓜蒂苦寒,能吐顽痰而快膈,小豆酸平,善涌风涎而逐水,香豉能起信而潮汐,故佐二物而主治……此所以为吐虚风虚寒之对药也。[34]”
现代中医药学著作均以“药对”作为规范名,如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中医药学名词》载:“两味药成对相配,多有协同增效或减毒作用。[35]”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药专业统编《中药学》教材也对“药对”作了明确阐述,指出“把两药合用能起到协同作用,增强药效;或消除毒副作用,抑其所短,专取所长;或产生与原药各不相同的新作用等经验配伍,统称为药对或对药”[36-37]。有些著作还称之为“姊妹药”“对子药”“兄弟药”“姐妹药”等[31,38]。
关于药对的组成,《临床中药学》载:“药对……即两味药成对(个别由三味药组成),是临床上常用的相对固定的配伍形式,是中药配伍应用中的最小单位。[38]”该著作将个别由3味药组成的常用配伍也称之为药对,但有学者提出采用3味中药配伍使用,具有“三足鼎立”“互成犄角”之势,谓之“角药”[39-41]。《中医中药角药研究·名医名方验方组药配伍技巧》亦指出,3味中药的有机结合即为“角药”,并系统阐述了角药的概念、意义和历代医家对角药的认识及当代医家临床应用角药的经验等[42]。从功效作用、组方意义角度讲,角药比药对更为复杂、广泛和深厚,其配伍已超出“七情合和”的范围,因此两药配伍为药对,三药配伍为角药,二者不宜混淆。
5 结语
药对绝不是2味药物的随意堆砌和排列组合,它是前人治疗经验的总结,是七情配伍用药的发展,是经实践证明有效的2味药物的配对使用。药对作为从单味药发展到复方的关键节点,其基础研究已成为方剂配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对发展中药药性理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其规范定名和相关术语的正确应用意义重大。鉴于此,本文通过考释“药对”术语的源流与沿革,厘清其发展脉络,为其规范定名和相关术语的正确应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