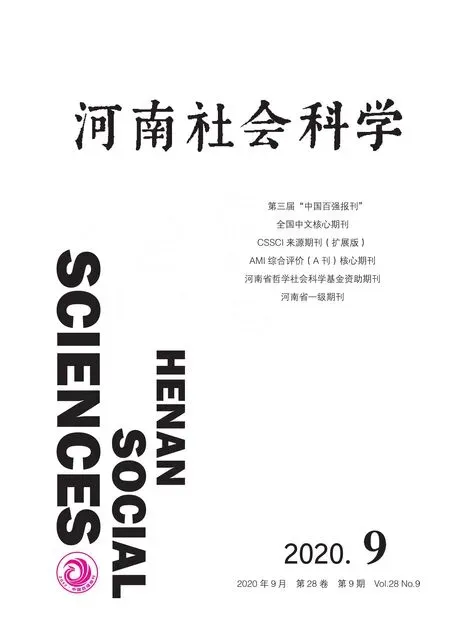关于我国公序良俗原则司法适用的法理思考
郭剑平
(广西师范大学 法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其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原则,指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和行为的目的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①。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一般道德,克服了成文法的局限性并对私法自治起到限制作用,不仅能够保持法律的稳定性,而且推动了实质正义的实现。目前,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在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适用范围与各项认定标准等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研究这一原则如何正确地应用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公序良俗原则司法适用的现状
为了了解公序良俗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现状,笔者以“公序良俗”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对2013 年至2018 年的司法裁判文书进行搜索与采样分析,共搜索到判决书571份。其中,以公序良俗原则为主要判断依据对案件作出判决,或者当事人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并以《民法通则》第七条作为裁判依据的判决书共有169份。通过对裁判文书进行实证性研究,我们发现:法官越来越多地在裁判文书中应用公序良俗原则作为裁判的依据和理由;公序良俗原则调整民事纠纷的范围比较广泛,类型也较为多样,涉及民法的各个领域。
(一)运用公序良俗判断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这方面的案件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由于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或者在婚姻存续期间保持长期同居关系引起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包括对第三者的赠与合同、补偿费、承诺以及民间借贷等。在这些案件中,法官基本认定建立婚外男女朋友关系违反《婚姻法》关于夫妻忠诚义务的规定,是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从而认定赠与合同及承诺书等无效。对于公序良俗在婚外同居关系中的应用在“泸州遗赠案”中较早地得以体现,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案件作出判决后出现了反对判决结果的声音。这些反对者认为,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婚姻道德再也不是能够压死人的大帽子,案件的最终判决是对当事人处分个人财产的限制。在该案争议的背后,存在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即“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道德和个人对财产处分的自由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在本文的样本裁判中,法院都是以承诺或赠与违反公序良俗作为裁判结果的。第二类是当事人“托人情”“找关系”而形成的委托合同。在这类判决中,法院认定借助人脉关系、通过请客送礼等方式来达到目的,是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行为。基于此,由于托人情疏通关系而形成的劳务合同无效是运用公序良俗对劳务合同效力的判断。第三类是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合意而形成借贷合同,且该款项目的系用于赌博、赌场放高利贷等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活动,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当属无效。
(二)运用公序良俗判断侵权行为的非法性
公序良俗原则被应用在判断侵权行为非法性的案件中居多,如强行铲平他人祖坟、将房屋建在他人坟墓上、在他人祖坟上修路,以及在诉讼中请求开棺验尸等②,法院往往认定此类案件有悖于我国的公序良俗,判决侵权行为人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例如“原告黄某兰诉被告刘某江、徐某斌恢复原状纠纷”③一案中,被告刘某江、徐某斌的养鸡场内有原告黄某兰家的祖坟,被告强行铲平了该祖坟。法院在认定该案的过程中认为,尽管祖坟位于被告的养鸡场内,但不能因此限制并剥夺原告祭祀祖先的权利。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祖坟使用的土地尚未有明确规定,但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和我国历来的民间风俗习惯,尽管原告对祖坟并不享有所有权,但其应该享有对其祖坟的管理权,这种管理权实际上包含了对他人破坏坟墓的限制,也就是说,任何人未经死者的近亲属同意,不得随意破坏死者的坟墓。基于此,破坏他人坟墓,既是对权利人财产权的损害,也是一种损害死者近亲属精神权益的行为。
公序良俗原则比较广泛地应用在判断侵权行为违法性的案件中,在此类案件的判决书中,公序良俗原则往往被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
(三)运用公序良俗原则解决侵犯人格权、名誉权纠纷
该类纠纷大多数涉及死者骨灰、祖坟等,法院以人格权作为案由进行裁判。其中一起案件中,法院判定被告拒绝交出骨灰的行为有违社会公序良俗,侵犯了多数亲属对已故亲人表示追思和敬仰的权利④。第二起为被告将原告的伯父伯母和兄弟的坟墓用推土机推平,其行为违反了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公序良俗原则的法律规定⑤。在“郑某雄等诉余某英等婚姻家庭纠纷”一案中⑥,原审法院认为,骨灰属于《物权法》中特别规制的物,对于骨灰的处分应该建立在符合公序良俗原则的基础上,不能以交易、使用和收益为目的。多个近亲属同时存在时,应该通过协商来确定对死者骨灰保管权利的归属;确定保管权利后,仍然应该保证其他近亲属的祭奠权。无法通过协商或者协商结果不一致时,可以根据善良风俗或者当地的道德习惯进行判断,依照与死者生前关系的远近进行区分。法官在解决此类侵犯人格权、名誉权纠纷时,往往通过运用公序良俗原则予以裁判。
(四)运用公序良俗解决继承、赡养、物权纠纷
在运用公序良俗原则解决继承和赡养纠纷问题的裁判中,有案件是因为家庭矛盾所引发的,如亲兄弟为家财分配多次大打出手,反复动用大量警力和其他人力,法院认定其行为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背道而驰⑦。还有一些案件中,法院判定成年子女应该对老人尽到赡养义务,即当子女长大成人、经济独立之时,反哺父母的养育之恩理所当然,符合公序良俗原则。
运用公序良俗原则解决物权纠纷的案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分家析产问题。分家行为是自然人对自己合法财产作出的处分行为,是我国民俗习惯的体现,但是分家之后的子女应该对父母尽到赡养义务⑧。第二类案件为相邻关系纠纷。法院认定当事人一方擅自改变房屋原有结构,将原作为厨房的房屋的一部分改建为卫生间的行为有悖于公序良俗⑨。第三类案件为法院认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与他人同居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此时一方立下遗嘱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由于遗嘱的目的和内容均无效,由此取得的财产应该予以返还⑩。
二、我国公序良俗原则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对所查阅的样本裁判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公序良俗原则在司法适用中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概念界定不明确,仅被法院作为增强裁判说服力的工具
法官使用公序良俗原则仅仅是将其作为增强裁判说服力的工具。在样本裁判中,一些判决书在裁判依据的部分写道:“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判决如下……”此类裁判文书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可以直接依照具体的法律条文,但为了增强裁判的说服力,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裁判理由加以引用。此时,公序良俗原则并没有发挥其作为基本法律原则的功能和价值,而是沦为增强裁判说服力的工具。从本质上说,此时即使裁判文书上没有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仍然会得出相同的裁判结果。这种问题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官对于具体法律规则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清楚、深刻,同时,也不难看出法官对裁判结果心存疑虑,想要通过公序良俗原则增强裁判的说服力。此时的公序良俗原则并不是裁判依据和评价依据,其存在本身并没有实际意义。如在“闫某田与闫某林等继承纠纷案”中,在纠纷事实清楚、判决适用依据明确的情况下,法官仍然将《民法通则》第七条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之一。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但本文认为公序良俗原则的概念界定不清,对其含义认识不够透彻是法官将其作为增强裁判说服力工具的重要原因。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将公序良俗原则和其他相关概念混用的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混用。我国《民法总则》颁布之前,司法实践中经常将违反公序良俗原则表达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法官在寻找案件适用的大前提时往往会造成混淆。有些裁判文书以“违反公序良俗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为依据,认定行为具有违法性而无效。这些概念的混用造成法官判断时的混淆,表明法院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外延、适用范围等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
(二)不探求适用条件,借助公序良俗原则向一般条款逃逸
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一些法官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时存在一定的任意性。裁判的案件有明文对应的具体条款时,有的法官置明文规范于不顾,而把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司法裁判中的主要依据,用公序良俗原则取代具体法律规范,借助公序良俗原则向一般条款逃逸。例如在样本裁判中,当事人双方存在婚外情关系,原告认为双方争议的标的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借款,而被告则认为该标的属于原告补偿给被告不正当两性关系的分手费。针对这一争议,法官依照《民法通则》第七条认定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值得思考的是,《婚姻法》第三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以及《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为本案裁判提供了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但法官却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案件裁判的主要依据,这是以公序良俗原则取代具体法律规定,从而造成了借助公序良俗原则向一般条款逃逸的现象。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兜底性条款,其适用具有兜底性,只有在符合以下几种条件时才能适用:首先,对于裁判的案件事实没有相对应的具体法律规范;其次,有两种以上的法律条文可以适用,但法律条文之间存在矛盾关系。如果有具体法律规范相对应却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则会陷入向一般条款逃逸的误区。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裁判者并没有重视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条件。法官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一方面先要判断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另一方面需要查明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相对应的公序良俗。
(三)不同主体对于公序良俗的认知不同,导致判断标准不统一
我国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适用存在判断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公序良俗原则本身具有的模糊性为法官的裁判过程提供了自由裁量的依据,法官可以根据自身对公序良俗的认知来进行裁判,使得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进行裁判的标准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法官是确保公序良俗原则在司法适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重要主体。客观上说,法官对于公序良俗判断标准不统一的原因在于不同地域关于公序良俗的认知不同。古语有云“五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地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于善良风俗的看法,不同地域所沿袭的传统风俗也存在不同。就善良风俗来说,内容相同的善良风俗在不同地域的理解不同,不同的社会认同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法官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员,其认知范围和角度都来自其本身对生活的认识,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的理解。这种理解和认知在法官裁判案件、形成和论证判断标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决策。由于不同的裁判者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对于案件的理解也存在不同,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也就会出现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情况。
(四)类型化研究不透彻,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
笔者通过对不同法院之间的相似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判决结果不尽相同,甚至相似案件会出现相反的判决结果。比如对于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案件中通过“托关系”“找熟人”而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裁判,法院一般认定请托行为本身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但从裁判结果的角度上看,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有的法院认为通过请托行为实现就业目的的行为违反平等用人的就业选拔制度,违反公序良俗,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故认定双方委托法律关系无效,已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进行赔偿。有些法院认定此类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认为涉及权钱交易等违背公序良俗,裁定驳回起诉。
司法适用过程中正确运用公序良俗原则并真正发挥其司法功能离不开理论研究的支持。对于推动公序良俗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类型化研究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公序良俗进行裁判的案例数量还相对较少。2001 年发生的“四川泸州遗赠案”被称为我国公序良俗第一案。除此之外,具有典型性意义的案例则少之又少。认识来源于实践,理论研究是以司法实践为基础的,而司法实践无法为学者提供更多的案例,这就造成我国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的类型化研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由于公序良俗原则本身具有模糊性,为了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适用该原则,法国和德国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对判例予以类型化;而日本也是在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将我妻荣教授的类型化研究结果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史尚宽先生和王泽鉴先生都对公序良俗原则的类型化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以期明确判断标准、避免同案不同判问题的产生,从而更好地发挥公序良俗原则的价值和功能。
三、我国公序良俗原则司法适用的对策与出路
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多元化与复杂化,公序良俗原则在民法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如何正确适用该项原则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运用好公序良俗原则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并树立司法权威,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正确界定公序良俗原则
我国于2017 年3 月15 日通过的《民法总则》首次以立法形式对公序良俗原则予以确定,这是我国立法机构在总结过去民事司法实践经验以及国际上民法立法、司法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再整合。虽然公序良俗原则的概念与地位被《民法总则》以成文法的形式予以规定,但是基于公序良俗原则本身带有的不确定特性,该原则在事实上还是较难以被精准界定的,存在司法滥用风险。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谨慎且合理地运用公序良俗原则来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是值得肯定的。法官肩负着维护司法公正的使命,因此在运用公序良俗原则这一法律工具时,应当时刻保证其中立裁决者的角色定位,在对案件作出裁判时需要有明确且充分的理由。法官在运用公序良俗原则时,应当表述清楚该原则的内涵,以及如何根据该原则的内涵形成裁判结果,避免用模糊的概念表达作出错误的司法判断。
法官在深入理解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并对公序良俗原则进行界定时,需要密切关注几个主要问题:(1)应当避免公序良俗原则与强行性规定同时使用。公序良俗原则在民法中并不属于强行性规定,该项原则具有一般性、授权性的特质,用来弥补强行性规定的不足。(2)需要明确公序良俗原则中善良风俗的善良属性。该原则的善良风俗不是平常的习惯与风俗,必须是以善良为前提的风俗。法官在运用善良风俗习惯进行裁判时应当仔细斟酌,唯有真正的善良风俗才能被采用。
(二)规范公序良俗原则适用的基本条件
1.在法律强制性规定模棱两可或法律未作规定的情形下适用
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曾世雄先生指出:“作为或不作为脱序,而强行法又苦无强制或禁止之规定可用时,公序良俗之规定,方使发生补充之功能。”我国现有法律中关于公序良俗原则要件的一些规定属于一般性条款,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某种法律行为,假若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特殊规定时才能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这样才可以防止发生利用公序良俗原则向一般条款逃逸的现象。
原则与具体规则相比具有兜底功能,只有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者没有具体规定时才考虑适用原则。以当事双方恶意串通的法律行为为例,各国现行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在德国民法中,并没有特别针对这一行为的具体法律规定,故德国一般通过适用善良风俗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即违反善良风俗并造成第三者损失,特别是造成债权人损失,如果合同双方旨在对第三者造成损害,或者这个损害至少可以由合同双方当事人事先预见并加以考虑,或者对此损失由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则该合同可以是违反善良风俗的。我国现行法律对此特殊情况有特别的规定,要求法官在处理此问题时适用法律的特别规定。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类似的有失公平的案件应当优先考虑适用特殊规定,当成文法没有特殊规定时方可适用公序良俗原则。
2.应当适用本国现行的公序良俗
善良风俗是一个可变的概念,“视时地之不同而迥异,它包括了一系列在一定环境与一定时刻为诚实、正派、善意的人们所接受的伦理规则”。总而言之,公序良俗原则会因为时间、地点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昔日为违反公序者,今则未必然。又甲地有背公序良俗者,乙地亦不一定以为然。因之,公序良俗之涵义常随各国之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念之不同而异。”所以法官在以公序良俗原则进行裁判的时候应当采用的是本地区综合经济、社会、人文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所形成的公序良俗。
此外,采用哪一个时间段内的公序良俗,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公序良俗原则是由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但是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历史发展会经历很多时间段,不同时间段内的公序良俗也会有所差别。法官在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时应当采用当下的公序良俗。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具有不间断发展的显著特征,英格兰的法官对于法律价值观的变迁有一种清晰的观念:“所谓违背政策与法律的确定标准必须因时而异。上一代人确定的所谓违背政策与法律的规则,在我们当代的法院里已经发生了变化。规则虽然还保持着,但是其适用却根据对待公众意见的导向发生了转变。”法官在运用公序良俗原则进行裁判时,必然采用当地、当时的公序良俗原则。
(三)加强对公序良俗原则司法适用的类型化规制
类型化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案例归纳在一起,以不同类型案例集群为基础,对每一类型案件的构成要件、判断标准进行归纳,要求法官在裁判相同或类似案件时行使有限度的自由裁量权。由于公序良俗原则内涵的不确定性,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难以正确运用其进行案件裁判,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功能,应该将该原则予以类型化。公序良俗原则的类型化有利于增强司法裁判中对公序良俗原则适用的确定性,由此应在公序良俗原则类型化的基础上,重视对现有案例的归纳和比较,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具有指导性的案例,并对目前具有明显违反公序良俗特征的行为进行类型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公序良俗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功能。
我国著名学者梁慧星教授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类型化的划分极具代表性,他根据我国国情将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分为以下十类:(1)危害国家公序行为类型;(2)危害家庭关系行为类型;(3)违反性道德行为类型;(4)射幸行为类型;(5)违反人权和人格尊严行为类型;(6)限制经济自由的行为类型;(7)违反公共竞争行为类型;(8)违反消费者保护的行为类型;(9)违反劳动者保护的行为类型;(10)暴利行为类型。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梁慧星教授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类型化的划分有利于法官运用公序良俗原则裁判案件,增强裁判的确定性,避免裁判标准不统一和同案不同判问题的产生。司法实践中在公序良俗原则的类型化问题上应该遵守以下几个原则:第一,要遵守时代性原则。要认识到公序良俗原则类型化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要着眼于当前的社会发展情况,符合当前社会的价值标准,动态的发展是公序良俗原则的生命力所在。第二,要遵循本土化原则。应该将公序良俗原则的类型化立足于本土,在司法适用中遵循本土化原则。不同地域对公序良俗的认识不尽相同,不同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也可能会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的认知。第三,应坚持明确性原则。在对公序良俗进行类型化规制时应坚持明确性原则。类型化划分的目的是指导法官对相同或类似案件进行归纳,从而更好地运用公序良俗原则进行案件裁判,如果将公序良俗的类型化设置得过于抽象,那么就丧失了类型化的目的,可能会造成司法适用中法官判断的混淆。
(四)明确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
案件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主体是法院,判断的对象应该是民事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不是当事人在生活中的其他行为。在规范公序良俗原则司法适用的过程中,应该明确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
1.明确判断公序良俗的时间基准
在判断公序良俗的时间基准这一问题上,学界普遍认为应当以行为发生时的公序良俗为准。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体现时代性是公序良俗原则发展的要求。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往往会认定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违反金融秩序,从而依据公序良俗原则认定该借贷行为无效。直到2015 年8 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法人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也就不能依据公序良俗原则判定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无效。除此之外,我国的传统道德长期谴责婚前同居行为,然而现代社会对于婚前同居行为有了较高的接受度。由此可见,社会道德观念是不断发展的,社会道德的判断标准也不能一成不变。基于此,判断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应以行为发生时的公序良俗为准,应根据当时的社会评价标准来判断。
2.明确判断公序良俗的空间标准
对于善良风俗内容的判断,梅仲协先生认为,“判断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应该根据的是整个民族的意志,而非在某一特定情形中局限”。德国立法中也将善良风俗内容的判断限定为整个民族的意志。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不同民族之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在日益趋同,但是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或多或少依然存在,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历史传统也不同程度地被加以保留。如果忽视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而以某一民族的公序良俗标准取代其他民族的标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基于此,在某一民族聚集的地区可以采取该民族的标准。在如我国这样的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在公序良俗的认定中适用民族标准时不能“一刀切”,而应当依据双方当事人的民族标准进行判断。
3.明确判断公序良俗原则的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
国家标准指的是判断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时以全国占主流的大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地方标准指在特定地区内以占主流的大部分人的意见来判断。这两种判断标准各有利弊。对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优劣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在判断公序良俗时是该适用国家标准还是该适用地方标准。就国家标准而言,针对全国的整体立法有助于实现规范的统一性,从而实现保护全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的价值目标。但这种标准本身在关注整体性的同时可能会忽视局部某些地区的情况,以至于可能会牺牲部分群体的利益。相反,地方标准的优点在于能够满足特定地区群体的需要,具有因地制宜和针对性强的优势,但可能会过于关注地方利益从而忽视了整体利益。由此,妥善处理好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适用大多涉及的是婚姻家庭或是祖坟等一些私人的伦理道德问题,而这方面的观念往往在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在判断公序良俗原则时可以适用地方标准和民族标准。由于我国是单一的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不同地域之间存在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差异,而采取国家标准无法照顾到不同的民族和地域,由此在判断公序良俗原则时更应该采取地方标准。与此同时,为了避免采取地方标准带来的不利后果,还应该将国家标准作为制定地方标准的依据,从而起到总体把控的作用。
注释:
①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②参见(2017)黔05民终第397号民事判决书。
③参见(2015)郯民初字第2287号民事判决书。
④参见(2013)钟民初字第1882号民事判决书。
⑤参见(2013)土左民初字第684号民事判决书。
⑥参见(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121 号民事判决书。
⑦参见(2014)穗花法东民初字第186 号民事判决书。
⑧参见(2013)鄂江汉民一初字第00243 号、(2015)金永芝民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⑨参见(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3474 号民事判决书。
⑩参见(2016)豫0782民初819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