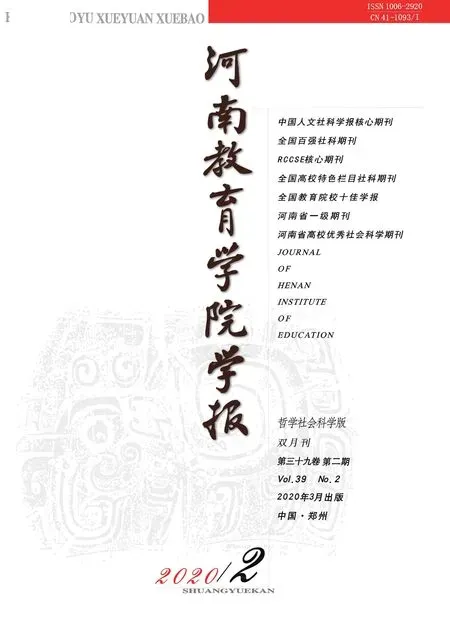自“多样的统一”至“尽善尽美”:论岑家梧的民族思想
庄振富
岑家梧生于1912年7月27日,广东澄迈县(今属海南)人。父母早逝,自小家贫。早年受摩尔根影响,遂学习人类学,并立志到边地去作社会调查。大学时,他得到一位堂兄资助,去日本留学,专攻史前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回国后,曾在西南民族地区作社会调查,致力于“西南学”研究。岑家梧一生既致力于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又热爱诗歌、艺术,其人类学研究多跟艺术相关,并有诗集传世。《民族研究文集》是岑家梧研究西南民族的论文集。此文集收录的论文时间跨度,几乎涵盖作者一生。由此文集,我们略可以知道作者一生的治学视域和学术成长轨迹,知道其观点之变化与思想之成熟轨迹。兹就其学术地位、民族思想及其思想的价值取向三方面作一评述。
一、“综合-创新”:岑家梧的学术地位
人类学发展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老派人类学家仍坚持主张人类学是只研究人本身及人种的学问,但其概念已有所延伸,不再局限于只研究人类躯体和人种区分的“体质人类学”。在英美国家,人类学实已包含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后者被称为民族学。德法的人类学传统,将民族学剔除在人类学之外,把对本国以外的落后民族及殖民地的民族的研究称为“民族学”,把对本国民间知识的研究称为“民俗学”。至于中国的人类学家,有留学于英美者,有留学于德法者,均以各自的知识背景服务于本国民族文化和乡村社区的研究,因此既可以称他们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也可以称他们为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已故人类学、民族学家江应樑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类学的种子,带动了不少人到国外攻读人类学。到三四十年代,我国人类学就已果实累累。当时的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代表人物……南方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杨成志、黄文山、陈序经、伍锐麟、罗香林、江应樑、岑家梧、王兴瑞、罗致平、梁钊韬等。”[1]
相比杨成志、陈序经等老一辈学人,岑家梧作为后起之秀,主要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岑家梧在日本留学期间,即撰写了《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和《图腾艺术史》三部著作(1936~1937年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史前史是人类学关注的重点,如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中就提出:人类学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2]11谈到为何撰写《史前史概论》,岑家梧在自序中说:“余于年前归国,间尝旅行北平、南京、上海各地,见国人对于史前之研究,颇乏兴味。除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刊行二三专门报告外,关系本题之译著,殊不易见,遂发著作本书之志。”[3]他的《图腾艺术史》一书,发前人所未发,以翔实的资料、鲜明的观点系统地论述了图腾与艺术之间的渊源关系,奠定了岑家梧在图腾艺术领域的地位。陈钟凡和陈序经两位前辈在序中充分肯定了岑家梧的研究。1983年该书再版时,著名人类学家卫惠林先生为之写序,重申此书的重要性:“在30年代对于西方学者学说研究能有此成熟的介绍和评述,确已难能可敬,厥功甚伟。”人类学家杨堃先生在《岑家梧〈中国原始社会史稿〉序》中总结了岑家梧三部著作的学术地位,更对《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一书赞赏有加。[4]岑家梧在人类学和民族学等领域的成就,当时有“南岑北费”(“北费”指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之定评。[5]
除了早年撰写的《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史前史概论》三部书,岑家梧于西南民族的研究,用力最勤,而且极力倡导人类学本土化建构。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的人类学者就不断探索人类学本土化的可能,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移植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而是提出建立中国民族学主张,如蔡元培在《说民族学》中提出发展中国民族学的设想,并且派遣学者赴各地调查,试图建立中国民族学体系。[6]295后来有孙本文、黄文山、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如费孝通撰写《江村经济》,林耀华撰写《金翼》。费孝通提出“礼治”“无讼”“差序格局”等阐释中国社会的术语,已经初具中国特色。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在人类学中国化方面主要采取“模仿-创新”模式。所谓“模仿-创新”模式是指“先掌握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进而熟悉国外人类学的发展现状,了解他们的优势与不足,然后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7]53。费孝通就学于马林诺夫斯基门下,谙熟功能论。他通过对功能论的模仿,以之为研究中国的视角,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术语。与“模仿-创新”模式不同的是“综合-创新”模式:“和西方多数人类学理论是从研究简单社会得出的理论不同,人类学理论运用到中国这样的复杂社会,或者人类学家对中国进行研究时,一定离不开综合的方法,既包括综合西方各人类学理论之长,又包括综合中国各学科。”[7]53岑家梧主张“综合-创新”。要做到“综合-创新”,首先必须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包括考古学、汉族历史和少数民族的地方县志等,并以整体意识观察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往来关系,考察二者在历史上的渊源影响;其次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搬国外人类学理论。
岑家梧的综合之路与费孝通的模仿之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目的都是寻求人类学本土化,而不是一味照搬西方理论,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其不同之处在于,岑家梧始终坚持历史研究与现状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这也是南派人类学的特点。关于岑家梧的治学主张和特点,南明森在其硕士论文中有所论述。他认为,岑家梧在田野调查时必观照历史文献是其治学的最大特点。而究其缘由,恐怕跟岑家梧早年在日本留学,受日本人类学影响不无关系。[7]54在岑家梧看来,历史文献的记载相当于过去所做的田野调查,以此观照现状,对理解该现象的变迁状况的有极大助益。而费孝通先生早年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不重视历史文献研究,至晚年才提倡“补课”。[7]54-55费先生曾说:“马林诺夫斯基提倡田野调查的实证主义,批评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现代的问题,虽然马老师也声明历史还是有它的价值,但强调说不能用它来推论、预测社会的变化,不能用它来作为研究现代问题的根据。到我这一代人的时候,这个圈子更出现社会学研究不要混在历史里的提法。我受了这种提法的影响,有一段时期跟了潮流走,也不很重视历史了。但是很快我觉得从‘今天’是可以推测‘昨天’的,因为历史并没有‘走’,它还包含在‘现在’里。”[8]76-77“深入挖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8]81总而言之,研究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即使是研究西南民族地区,也需要多学科的融合、多视角的转换。
岑家梧一生虽短暂,却著述丰赡。诚如徐杰舜等所言,岑家梧先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9]
二、以图腾、艺术和民俗为核心的西南民族研究
《民族研究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一书不是岑家梧的专著,而是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至“晚年”所写论文的合集。《文集》时间跨度很长,展示了岑家梧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学术成长的历程。岑家梧在20世纪40年代已迎来学术的巅峰期,大多数有影响力的文章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如在徐杰舜等的阶段分类中,岑家梧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两个阶段分别为:1938年至1945年的田野调查阶段,1946年至1949年的总结阶段。[9]
《文集》中收录20世纪30年代的文章有两篇:一为1936年发表于《现代史学》3卷1期的《东夷南蛮的图腾习俗》,与岑家梧《图腾艺术史》一书出版的时间几乎同时,可见岑家梧这一时期关注的重点在图腾艺术领域。若说《图腾艺术史》所搜集的材料更多来自国外,那么《东夷南蛮的图腾习俗》就是岑家梧将眼光转向中国少数民族的开始。但他当时还没有从事田野调查工作,只是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另一篇为1939年写成的《嵩明花苗调查》。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中山大学外迁,几经辗转,于1939年迁至云南澄江。岑家梧接受中英庚款资助,前往云南民族地区做调研。这篇文章正是在云南嵩明县从事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并于1940年发表在《云南边疆》第8期。首先,岑家梧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爬疏,考察了嵩明县花苗的历史迁居情况和地理分布状况,并在年龄、姓氏及花苗与汉人的交流诸方面,做了详细记录。其次,花苗的经济生活也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如花苗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业为辅,又有少数狩猎生产者。花苗的家庭手工业,以织布与刺绣为最普遍。但其所织的布为麻布,极为粗糙。由于花苗不产棉花,棉纱须购自汉人,价格极其昂贵,所以花苗纺织棉布者较少。岑家梧认为,刺绣与蜡染是花苗最具特色的工艺品,花苗刺绣上的几何花纹,具有文字记录的功能。最后,他还考察了花苗与教会的关系和花苗的一般习俗。一方面,西方传教士曾深入梁王山布教,极大地影响了花苗的社会生活。“现在的花苗,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差不多全是教徒,三十岁以上的也有半数属教徒。”[10]14在教会的影响下,花苗的语言、教育、婚姻、社会组织和丧葬风俗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花苗的一般习俗如衣饰风格、饮食习惯、住所特点等,经岑家梧的分析,亦详细可见。
1940年7月,岑家梧发表了一篇理论综述性文章,即《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该文所据材料之翔实,眼光之独到,见解之深刻,非大师手笔不能为之。西南民族是当时人类学研究的重镇,几乎所有的民族学家都汇聚到西南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岑家梧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的。首先,西南自汉代开拓以来,一直有文献记载,如司马迁之《史记·西南夷列传》,晋常璩之《华阳国志》,南朝宋范晔之《后汉书·西南夷传》,北魏郦道元之《水经注》,唐樊绰之《蛮书》、刘恂之《岭表录异》,宋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和周去非之《岭外代答》。至于元、明、清三代关于西南民族的著作就更多了,例如,元张道宗的《记古滇说》,明萧其实的《夷俗记》,清李调元的《南越笔记》等。这是中国的文献。还有外国的文献,即早年来华的传教士的记载,如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仕于元,记有《马可·波罗游记》;晚清时布拉克斯屯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著有《扬子江五月考察记》等。其次,岑家梧认为,历史上关于西南民族的著作,虽不下百数十种,但多为传闻,谬误重重,缺乏人类学的知识,都不能算是科学的著作。以人类学知识为背景对西南民族进行系统研究,始于杨成志教授。他于1928年深入云南罗罗(彝族)聚居地,一共待了一年八个月,写成《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此前有日本人鸟居龙藏氏于1902年遍历湘、黔、康、川、滇各省,著有《苗族调查报告》和《从人类学上所见的西南中国》二书,影响较大。此后,研究云南苗族的人类学家有凌纯声、陶云逵、芮逸夫,研究广西瑶族(盘古瑶、蓝靛瑶、花蓝瑶)的人类学家有严复礼、商承祖、庞新民、费孝通、王同惠,研究浙江畲民的人类学家有沈有乾、何联奎,研究海南岛黎人的人类学家有刘咸、王兴瑞,研究广东沿江的水上疍民的人类学家有陈序经、伍锐麟、何格恩等。上述学者对西南民族的研究,均取得很大成就,为人类学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最后,岑家梧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我们今后的研究目的应有三点:其一,进行各族体质的测量,确定各族体质特征,因为“这不但可据以决定各族的系统分类,同时更可阐明各族过去在体质上互相混血而构成今日中华民族的事实”[10]31。其二,对各族文化区进行调查,划定各族文化区域,认识各族的文化特质,进而研究各族文化的互相传播、同化的现象,说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10]31其三,对各族历史深入研究,包括史前史。如从考古学上发现,我国北部的旧石器,有许多带有南方文化的特征;殷周的铜器、玉器,其中有些原材料出自西南各地,这都充分说明了自远古时代开始,西南各族和中原汉族已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几千年来,各族共同生活在同一的环境中,利益趋于一致,形成了利益共同的集体。[10]32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国人类学的民族研究是以建立民族独立自由统一的新中国为目的的。我们从这篇文章中,亦可看出岑家梧毕生研究的志趣和理想即是“西南学”的构建。
《文集》一书收录岑家梧在40年代写成并已发表的论文有20篇,是该年代论文的主体部分。其中,1940年所写的文章,关注点在于民族的起源、图腾和身体装饰;1941年至1943年所写的文章,则关注民族之艺术;1943年至1945年即转向民俗文化研究了。这些论文是岑家梧在田野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下面分别论述之。
(一)民族起源、图腾和身体装饰研究
除了《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岑家梧在1940年撰写了三篇重要文章,一为《海南岛黎人来源考略》,刊于1940年2月《边事研究》10卷8期;一为《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刊于1941年《责善》2卷4期;一为《西南民族的身体装饰》,1941年发表在《文史杂志》1卷9期。
首先,论述海南岛黎人的起源。考察一民族的来源问题,盖有两种方法:一是从体质上找类似,一是从地形上寻相近。当时研究黎人的学者不在少数,如林惠祥、罗香林、史图博(H.Stubel)、刘咸等。学者所持的观点有二:一为南来说,一为北源说。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说:“黎人之来路有北方大陆及南洋两条。南洋远而大陆近。古代之黎人,似以由大陆一路为是。由大陆则汉以前广东系南越族所居地,或即南越族所移居。且黎人有文身之俗,古越掸亦有文身之俗,此亦一同点,若谓掸族有文身之俗,黎族亦有之,似即掸族。然台湾之番族亦有文身之俗,其文身之纹样与黎人甚相类,然而台湾番族乃马来族而非掸族。黎族种属及起源问题与古越族极有关系应合而研究之。”[11]128可见林惠祥是主张北源说的。罗香林在《海南岛黎人源出越族考》一文中同样主张黎人北源说。持南来说者有史图博和刘咸。史图博著有《海南岛之黎族》一书,认为黎人的风俗习惯,多与波利尼西亚人有关。刘咸于1934年间深入五指山考察,发现海南岛黎人的口琴,与太平洋群岛土人的口琴类似,所以断定黎人属于海洋蒙古系。[10]34以上二说,岑家梧较赞同后者。从体质上观察,黎人体质与海洋岛人相似。从地形上看,在石器时代,当时海南岛与南洋群岛、印度、印度支那半岛以及雷州半岛互相连络,地形与今日大有差异。这一点我们从石器时代出土的遗物中均可找到证据。其地形既连络,其文化亦自构成一系统。“海南岛黎人,确属南方系统之民族,其迁来岛上,不由亚洲北部大陆,而由亚洲南部诸岛屿,此史前时代之情形也。进入历史时代,安南、雷州、广州附近之黎人曰俚,政府屡次遣兵讨伐,黎人又反而逐渐南迁,乃形成今日之状况。”[10]37
其次,论述南蛮祖先槃瓠传说和瑶畲的图腾制度。槃瓠传说,大概自汉代起就已流传,见诸文字记载的有干宝的《搜神记》、范晔的《后汉书》、王通明的《广异记》等。三书所讲的槃瓠故事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槃瓠与公主婚配而生蛮族。岑家梧相信槃瓠传说是含有图腾意义的神话,因为它满足图腾制度的首要特征:“原始民族的社会集团,采取某种动植物为名称,又相信其为集团的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12]1既然槃瓠是“南蛮”的祖先,那么“南蛮”在今日具体指何族?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岑家梧认为,槃瓠之后的“蛮夷”,计有苗、瑶、畲、僚、壮以至仡佬。“僚、壮、仡佬等族是否亦有槃瓠传说,还有待于他日调查。黔滇一带的苗族,据我们的调查,他们的起源传说,是伏羲女娲兄妹型,而非槃瓠公主型。至于现在尚保存着狗人配偶而生其俗的槃瓠型传说的,只有瑶、畲二族了。”[10]58
再次,论述西南民族的身体装饰。身体装饰包括衣服、头颈饰、鼻耳饰、手足饰、齿饰和黥纹六类。第一,据岑家梧调查,云南一般彝族的服装,多以皮革制成,而苗、瑶族早已发明麻制衣服,较为进步。由于妇女的衣饰较男子的繁缛,故从妇女的装饰入手研究,最为妥当。岑家梧认为,妇女的装饰之所以比男子的更考究、华丽,其原因大概是:一者易于婚配,服装之繁缛易引起男子的注目。二者表示富有,如苗民每逢集会,便盛装出席,以夸其富有。三者重视事主,如在集会时,苗民不穿新衣或花衣,不足以表示敬意。因此,西南民族妇女的衣服,无论从形制、挂饰还是颜色上看,都具有独特的艺术感。第二,西南民族的头发、颈饰均有其特点和美感。例如苗、瑶族相信祖先为槃瓠,故其髻发如椎角,以类狗耳。瑶族妇女的头饰爱用象征狗的两耳的布帽。畲族妇女头上则多戴布冠竹筒,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的串珠,工艺精巧。岑家梧认为:“这也是畲族尊崇图腾的记号。瑶、畲同属槃瓠图腾的崇拜。故刻意于头幅的装饰,再演变而为种种形式。”[10]43西南民族的颈饰多用贝壳及绿玉之类。第三,鼻耳饰亦是人类装饰自身的一种,但岑家梧认为,我国西南民族中不存在鼻饰习惯,而耳饰则颇可注意。黎族、傣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开钦族等族均有佩带耳饰的习惯,耳环饰物或金箔,或银铜,或珠玉。耳饰艺术或许出于人类审美的观念,但也具有实用的功能,如瑶族男子亦戴耳环,其目的却不在装饰,而是作为娶妻的标志。广东北江瑶族,一般娶妻后即戴上一对耳环,娶妾后则戴两对耳环。第四,手足饰以手饰最为普遍,有手镯、手圈、手环、戒指,材质多为金属,亦有玉制的。在西南民族中,足饰则少见,而多以衣布包裹。第五,齿饰在过去颇为盛行,如樊绰《蛮书》载有“黑齿蛮”“金齿蛮”及“银齿蛮”等。但齿饰的风俗今日已经很少见了。齿饰或为染齿,或为毁齿。傣族仍有染齿的习惯,毁齿则几不可见。第六,以黥纹饰体者,在我国境内各民族中,极为常见。据岑家梧考察,饰黥纹的民族有越人、哀牢夷、濮、黎、伢人、怒子等族,分布于东南至西南各省。但今日西南民族中盛行黥纹装饰的,只有黎人和摆人(傣族)。[10]49傣族的黥纹只限于男子,黎族的黥纹则只限于女子。或黥面,或黥手足,或黥体部。岑家梧从黥纹的图案和方法上分析了傣黎之间的异同,阐述了黥纹习俗。
(二)民族艺术研究
实际上,《西南民族的身体装饰》一文,已涉及民族艺术研究。1941年至1943年间,岑家梧又陆续发表了三篇专论艺术的文章:《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之意义》(1941年发表于《责善》2卷3期),《西南民族之舞乐》(1943年发表于《文讯》4卷1期),《西南民族之工艺》(1943年发表于《文讯》4卷4、5期合刊)。在此期间,岑家梧原要出版《西南民族艺术导论》一书,却因抗战吃紧而告终。他对艺术素有特殊的兴趣,曾在《中国艺术论集》的自序中说:“余性嗜艺术,幼曾习画,以家贫莫能继。长治社会学,而于艺术考古,志趣未衰。”[13]5所以岑家梧在从事史前史研究时,尤其注意旧石器时代的洞壁艺术,撰写《史前艺术史》和《图腾艺术史》探讨原始艺术起源问题。他另著有《中国艺术论集》,辑成《艺术考古实录》和《唐代艺术图录》两册,为其研究中国艺术之实绩。此外,他还写了不少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的衣饰工艺和民间艺术品的论文,收在1949年出版的《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中。岑家梧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艺术,成绩卓著。中国后起的艺术人类学将岑家梧目为学科的奠基者,他当之无愧。
首先,阐述西南民族艺术研究的意义。岑家梧指出,由于西南民族在物质、精神文化水平方面,都较内地为低,所以“他们的艺术,还只表现在古朴的工艺品及身体装饰上面,而他们的音乐跳舞,也还保持着原始的状态”[10]74。但无论是西南民族的身体装饰,还是苗瑶的刺绣、染色,罗罗(彝族)的打毡,都远远胜过非洲、大洋洲、北美洲等处土人的初民艺术。他主张研究者应深入大西南,对西南各族艺术作深切的研究。其益有三:其一,有助于解决艺术起源问题。他认为,正如英国人可以到大洋洲、南洋群岛去研究,美国人可以到北美洲印第安人中去研究,法国人可以到非洲土人中去研究一样,我们可以深入西南边疆去研究,充分挖掘那里的艺术资源,以解决艺术起源问题。因此,研究西南边疆艺术具有世界意义。其二,有助于推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西南民族艺术与内地汉族艺术并非扞格不通,风马牛不相及,而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西南民族艺术尚保持着汉族艺术的“原始状态”。例如,蜡染是唐代著名的工艺,汉人早已失存,却流行于花苗社会中。欲要研究唐代这一工艺,就得深入到苗族地区去。以此类推,研究中国古代音乐舞蹈,最好是到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调查访问。[10]76其三,有助于建设新中国的艺术。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学者意见不一,或提倡复古,或主张西化,或建议折中。岑家梧则提出“综合”的方法,一反前论。所谓综合,即既要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又要吸收他族文化的精华,灌注新的血液,使中国文化达到更高的水平。换言之,中国新艺术的出路,在于“发扬我们固有艺术的优良传统,吸收西南民族艺术的精华,使内地和边疆各族艺术作有机的综合,如此中华民族艺术创造的全貌便可窥见”[10]77。
其次,研究西南民族之舞乐。舞乐包括跳舞、音乐和唱歌,三者紧密结合,形式丰富。跳舞时,必有音乐和诗歌互相伴奏。第一,跳舞活动一般只在特定的时节举行,如择偶集会或丧葬仪式。岑家梧指出,西南各族的舞蹈,以苗人的舞蹈较为纯熟可观,可分为绕舞、对舞、跳舞、滚舞四类。苗瑶族的群舞都是有节奏的体操式跳舞,拍子极为重要。与体操舞不同的是模仿舞,动作较复杂。模仿舞的形式即模仿动物的动作,或表演人类日常生活的动作。开钦人最擅长模仿舞。岑家梧总结道,体操舞只有单纯的动作,多用于群众娱乐或男女社交;模仿舞则表现一民族一切复杂的文化生活。舞者随着一种狂热的情绪而动作,便形成前者;后者则必须加以种种练习,才能使其逼肖于所模仿的对象,达到固定的目的,所以模仿舞便成为原始戏剧的雏形。[10]82第二,西南部族的音乐,最常见的乐器有芦笙、口琴和鼓,以芦笙最为特殊。芦笙为男子吹奏乐器,口琴则为女子之必备。苗民在跳场、跳月、跳花等集会时期,芦笙不特为至要之乐器,且为男女双方寄情之媒介。芦笙的音调缓和悦耳,沉郁低回,如蚊蚋声,由吹奏者呼吸的强弱而生简单的音程;芦笙的曲调则有开场曲、行路曲、迎神曲、祭曲等,多以口传见存。第三,西南民族的唱歌之风是很盛行的。歌唱的形式多样,除了节会时载歌载舞外,还不时举行唱歌竞赛,歌唱至佳者,往往博得全社会的荣誉,所以人人醉心于唱歌。据岑家梧的分类,歌唱的内容有两大种类:一为情歌及一般歌谣,都是触景生情的写实主义作品;一为叙述人类起源及历史传说的祭歌,采用象征性的描写。二者同时流行于各族民间,各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10]92
再次,关注西南民族的工艺。岑家梧将之分为纺织、刺绣、染色、建筑和铜鼓五类。(1)纺织。西南民族的纺织品多自织,自给自足,很少向市场购买,亦不假手于人;且其工艺之精良,做工之细致,非工业产品所能媲美。刘锡蕃这样描述广西壮族的布匹纺织:“其工细者,数月而成匹,曰娘子布。其质为苎麻,染青色。九洗九染,布敝而色犹新。侬人(即壮族)尤所优为,故有‘侬人青’之名见称于社会。此等布匹,非其情爱素熟者不易得之。欲购者虽重价不卖也。”[14]131(2)刺绣。此项工艺广泛存在于苗瑶社会中,技术之精湛,远胜内地妇女。王兴瑞曾记录道:“我们在瑶山时,常见瑶族妇女于工作之暇,或牧牛无事,常手不离针线,殷勤刺绣,这已成为她们的天性了。”[10]96-97苗瑶妇女能有精湛的刺绣技术,是长期练习的结果。苗人刺绣所用麻线材料及其表现的几何纹样,自有其特点。(3)染色工艺。岑家梧指出,西南民族中,爱美观念最强者莫过于苗人,他们极喜花布衣裳,所以极注意染色。如花苗即是因其衣服染色斑斓而得名的,蓝靛瑶亦由其蓝靛染布而得名。花苗的染色法需以蜡作辅助,所以也称“蜡染”,包括两道工序:一即用蜡绘花于布;二即染色,去蜡则花见。这只是言其概要,具体则有微异。(4)建筑。人类最初的住所形式,不外穴居与巢居,穴居发展至地上居住,巢居则发展为楼居。苗族的屋宇多作楼居,人居楼上,下蓄牲畜。岑家梧认为,各民族的建筑形式之不同,是因为各民族审美观念不同,但西南各族的住所很少具有艺术性,倒是藏人的建筑颇为华丽美观。如藏人的喇嘛寺建筑,因崇信佛教,外观之恢宏壮丽,至可惊叹;其内部装饰亦极讲究,如厅堂柱子以美丽的藏绒包裹,墙上饰以壁画,色调谐和,光彩富丽。所以,“在西南民族中,若果论到建筑艺术,当推藏人一系为最著”[10]102。(5)铜鼓。经岑家梧考证,至今使用铜鼓的民族可确定为仲家(布依族)、摆人(傣族)和黎人三族,均属于掸语系。铜鼓形如腰鼓,表面施以精致的纹样,或附饰蟾蜍数只,或只有简省的几何纹样,如太阳纹、酉字纹、卷花纹、旌旗纹等。这便是铜鼓的工艺所在。
此外,岑家梧还撰有《中国民俗艺术概说》和《中国边疆艺术之探究》两篇论文,均为民族艺术研究之力作。
(三)民族风俗研究
1943年至1945年间,岑家梧的研究目光主要放在水族仲家(即布依族),关注点集中于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上。其研究水族的文章有三篇:《水书与水家来源》(1948年发表于《社会科学论丛》新1卷)、《水族仲家风俗志》《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1944年发表于《风物志》月刊1期),其中《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被称为宗教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岑家梧对民俗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族仲家风俗志》一文。现就其研究水族仲家的三篇论文做一分析。
首先,对水家水书的研究。水书是水家鬼师所用的占卜文字,除鬼师外,普通水家人多不认识,但水书对于水家生活影响极广。岑家梧从水书的种类与用途、内容与结构、来源传说诸方面做了详细介绍,并从水书推测水家的来源。一般人认为水家即住在水上的民族,岑家梧认为,水家似为古代殷人之一支,原住中原一带,其后逐渐南迁中桂,因与闽南语族系杂处,而语言风俗上,受闽南语族系之影响,即成今日之状态。[10]123其理由有三:其一,水家四周为汉人、苗人、瑶人及仲家,而水书除水家外,其他各族未曾获有。可知水书为水家固有之文化,非自外传入。其二,水书字体与甲骨文、金文颇多类似,而水家独能保存此种古文字,不可不疑其祖先与殷人有关。其三,关于水书水家的来源有种种传说,从传说中可知水家在历史上的迁徙路径为:由西北南下,至江西而入黔。所以水家是原住中原一带的殷人后裔之说,较为可信。
其次,水族风俗的研究。岑家梧将水族的风俗分为衣饰、饮食、住所、生育、婚姻、丧葬、节令、征兆与禁忌、神话传说等九类,涵盖水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1)衣饰。水族男子的服饰与汉人无异,妇女的衣裳则绣以花边;男女服饰均喜用青蓝色,头巾则由青黑色布织成。(2)饮食。水族的主食为红米饭,蔬菜则以青菜、白萝卜为主,肉食以鸡、鸭、猪为常见。水族最爱食火锅,又最能吃辣。烟酒亦普遍。(3)住所。水族多楼居,楼下养牲畜,楼上住人。其房中置有神位,上挂鸡毛鸭毛及纸条,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所在。(4)生育。凡妇女受孕后,要遵守许多禁忌,如在吃食方面忌吃母猪肉和公鸡肉。产妇未满月时,不得到他人家中,否则会给人家带来不吉利;也不能与人同席吃饭,不能挑水,不能进厨房,以免使龙王及灶神受浊。岑家梧认为这完全是一套汉人的禁忌了。(5)婚姻。婚前男女双方须请媒人议婚,实由家长做主。订婚时要请鬼师按照水书择定日子,然后男家的父兄及村中的男子数人与媒人,带聘礼至女家订婚,聘礼有布匹、首饰、糖、米花、猪等。订婚当晚,女家将猪宰杀,以猪头供神,猪肉分给村人,同时设宴款待男家客人。席间,双方家长与邻人须各饮酒一碗,以为盟誓,日后若有毁约,则有邻人见证。翌日,女家以鞋袜文具等送至男家,订婚礼即告成。结婚时讲究亦多,如新娘出门时,要持一把伞辟邪,且一路不得回顾娘家。入男家门时,男家的男女大小须躲避,尤忌孕妇看见,待新娘入房后,家人才来招待她。三五天后,新郎须伴新娘回娘家,是谓回门。(6)丧葬。水族每逢亲人去世,常厝棺家中一月至数年不等,非请鬼师择日出殡不葬。出殡前一日开吊,事前讣告亲友,并在村内设歌堂,晚间请以歌唱为业的人来唱孝歌,内容均属歌唱死者及各种神话传说,直至天明。出殡时,燃爆竹,放火炮,吹喇叭,击铜鼓。葬后三天,丧家杀猪、鸡、鸭等款待全寨的人,谓之复山。[10]172-173(7)节令。水族的节令有三月的清明节、九月的年节等,以九月的年节最隆重,在此节日举行的仪式有招魂、悬铜鼓、拜祖和再拜祖等。(8)征兆与禁忌。水族的征兆与禁忌种种,夹杂着不少汉人的习俗。(9)神话传说。水族的神话传说主要有三类:一为空心竹的故事,即伏羲女娲兄妹故事。伏羲与女娲为兄妹,幸存于洪水泛滥后,为繁衍人类计,伏羲提议兄妹二人结婚,妹妹不允,急忙逃去,哥哥紧追不舍,至一处,妹妹问竹子,竹子曰:“可避东方。”妹妹避到东方,仍为哥哥追及,不得已而成婚,遂有今日之人类。婚后,妹妹常怨恨竹子没良心,所以至今竹子还是空心的。[10]175二为虹蜺的故事,虹蜺是一种有两个头的动物,似龙,有足,有须,云游天际。三为雷爷传说。
再次,对仲家作桥的研究。仲家的“作桥”意即还愿,为一种特殊法事,仪式隆重,多于每年旧历冬季举行,日期由鬼师择定。“作桥”的目的有四:一为度厄;二为求子或祈佑人丁康乐;三为求财;四为求神引渡,死后灵魂直往天界。其中以第二项为最重要。“作桥”的道场由鬼师布置,中置神坛,挂神像七幅。香案上置供物,有白米、鸡蛋、小猪、母鸡、公鸡、鸭、鹅、小狗、水牛、鱼等。
最后,对仲家风俗的研究。仲家的风俗有作醅、赶表、不落家等。“作醅”是就饮食而言的,即用生糯米及盐、糖、醋等及生猪肉和水少量,置于瓮中,密封约一月后,便可食。仲家最喜糯米饭伴糖,手抓而食。亦极嗜酒,不醉不欢。“赶表”即春季的男女集会,男女未婚者,若一见钟情,即约定赶表的时间和地点,作浪漫的幽会。“不落家”是指女子婚后住夫家三日即返娘家,以后只有农忙或年节到夫家一二日,直至数年或十余年怀孕后,始回夫家落家。不落家的时间愈长,女性愈受人尊重。仲家的婚姻仪式多已汉化。丧葬仪式则较为特殊,由女婿执行坎牛的仪式。仲家和水家均在新坟上插伞一把,因伞有辟邪的功用。
三、岑家梧民族思想的价值取向
《民族研究文集》一书为我们展现了岑家梧先生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丰富的思想还有待后来者来挖掘和继承。岑家梧民族思想的价值取向,概有两方面。
其一,对进化论思想的服膺。进化论是人类学界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其发展经过古典进化论和新进化论两个阶段。古典阶段的进化论,代表人物有斯宾塞、泰勒、摩尔根,其最早的思想根源还可以追溯到实证主义的孔德、辩证哲学的黑格尔、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古典进化论认为人类文化是一元线性发展的,即人类文化的起源只有一个,把源头寻到,便可知道其以后的发展;世界各族文化都遵循同一路线,只是发展程度不一,有些民族进化得快,有些民族进化得慢,但他们总会逐渐往前进化,所以各民族处在同一路线的不同阶段上。此外,古典进化论学派也考虑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即文化传播所带来的交流碰撞,会使一个民族文化发生怎样的质变,从而破坏自然发展的演进系统,但他们认为外来因素只是不规则的侵入者,须把它们剔除,才能知晓进化的真相。进化论最明显的观点即阶段说,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将人类文化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大阶段。岑家梧早年受摩尔根影响最大,他曾说:“我很醉心摩尔根的工作。”[10]430古典进化论曾遭到来自传播学派、历史批判学派以及英国功能学派的尖锐批评,经过20世纪初期的衰落后,于1930年代又复兴了起来,形成以美国人类学家怀特为代表的新进化论。怀特和摩尔根一样,都同意人类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是从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全世界各种文化都必定经历几个相同的阶段。所不同者,一是怀特不像摩尔根那样以食物和生产工具作为进化的标志,而是用能源的获取来作标志;二是怀特特别强调文化发展的独立性或超有机体性。属于新进化论学派的还有斯图尔德,他主张多线进化论、文化生态学以及文化涵化等。[15]
岑家梧是忠实的进化论者,但他不同于古典进化论学派,也和以怀特为代表的新进化论有别。他同意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段说,但他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多线发展的,每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并非循序渐进,偶尔也会呈跳跃性发展。[16]93他也同意进化论主张的遗俗说,认为民俗学的任务就是设法从现代遗俗中还原它的原意。英国功能派曾批判遗俗论,认为一切文化都具有现实的功能,不存在所谓遗俗。但岑家梧反对说,正如生物个体上遗留许多不必要的器官一样,如鲸鱼的后肢,蛇的前足,马的上蹄,人类的尾骨、盲肠、耳朵的运动筋,胎儿的体毛等,“文化现象也有如体质那样的逐渐演化发展过程。在演化中,旧的逐渐消失,新的逐渐生长,在新旧文化作有机的转化时,旧的文化,往往也有许多像生物的体质一样,作痕迹的遗留”[10]289。以实例观之,南美巴西、太平洋群岛、南洋群岛以至中国南部的越族、僚族所具有的产翁制,若干民族的近亲姻亲合一制的亲属称谓,如岳丈、岳母与舅父、姑母同一称呼,表兄弟与大小舅及姊妹夫同一称呼等,均属遗俗论。所以,“进化论者借遗俗以还原前代制度,当然不能目之为狂妄、虚构”[10]291。然而,岑家梧并不完全认同进化论者所谓的文化遗留法或遗俗说。“若果采取两种毫无关系的民族文化,硬套入同一阶段来互相说明,像以澳洲土人艺术说明欧洲驯鹿期的艺术那样,当然会有问题。”[10]285他主张:“像我国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自古已经接触,文化上也发生过传播的关系,彼此的艺术,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采用边疆艺术来说明古代中国艺术,是无可非议的。”[10]285
其二,对“中华民族”的体识。身处抗战年代,寻求民族的复兴、国家的统一几乎是那一代学人心系天下的匹夫之责,五四时期就有李大钊、孙中山、王光祈、梁启超、梁漱溟等知识分子的积极呼吁,如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的演说,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光是汉族的复兴。但那时对中华民族的概念的理解还比较狭隘,孙中山所理解的中华民族只包含汉、满、蒙、回、藏五族。至1939年,顾颉刚基于战争和政治的原因,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认为中国各民族是一家,不应存华夷之别;没有汉人的文化,也没有蛮夷的文化,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17]这种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惟费孝通撰文予以商榷,认为“不能把国家与文化、语言、体质团体画等号,即国家和民族不是一回事, 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即不同民族的存在)。谋求政治的统一, 不一定要消除‘各种种族’(即费氏所谓的民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 而是在于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18]。
在此背景下,岑家梧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东有夷,北有匈奴,西有氐羌,南有越人及苗、瑶等,再根据近代学者提出中国民族新的分类有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蒙古系、突厥系、氐羌系、苗、瑶、罗罗、黎人等,现在都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了。”[10]238“我国边疆民族,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原因,文化较中原落后,但他们并不是劣种人,他们的体质和我们一样,并无优劣之分,都是我们的手足兄弟。我们有帮助他们发展和共同进步的义务,没有压迫和统治的权利。我们也反对传播派认为低文化总是为高文化所消灭、所征服的理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丛体,新文化来了,便代替旧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辐合交替性。中华民族文化,虽有区域性,但是我们可以由文化的辐合交替的原则上指出中华民族将来发展的趋势,必须汇合各区文化的精华,使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更加充实和壮大。所谓多样的统一,就是将来中华民族文化的尽善尽美的所在。如何使中华民族文化达到这种境地,这是中国民族学所应从事研究的课题,也就是建立中国民族学的最高目的了。”[10]240-241
四、结语
如上所述,岑家梧的民族思想,其核心自“多样的统一”至“尽善尽美”,对内汇合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使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更加充实和壮大;对外弘扬自己固有的文化,同时吸收他族文化的优长,注入新的血液,使二者有机综合,把中国文化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他将此悬为中国民族学之最高鹄的,皓首穷经,兢兢业业,在民族学领域耕耘近四十载,取得骄人的成绩。他对西南民族文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既有对民族的神话起源、图腾信仰和身体装饰的研究,也有对舞蹈、音乐和工艺等民族艺术的研究,更有对民族习俗的研究。岑家梧的民族研究,纵必追溯历史,力图连接起人类的史前时代和有史时代;横必比较文化,旨在说明中原汉族文化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求其二者多样的统一而至尽善尽美。这是岑家梧先生的贡献之所在。
历史、辩证地看,岑家梧的著述,当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费孝通曾说:“一个学者的理论总是反应(映)他所处时代的实际。时代在变动,一个学者的理论也总是跟着在变动。”[19]207岑家梧的学术著作多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那时到今天,我国考古学界、民族学界和历史学界发现了很多新资料,提出了很多新理论,这就使得以前的论著存在过时的地方。但我们不必过分苛责,因为任何研究都“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长河,每个具体研究者所做的贡献都是有限的”[4],只有一代一代持续地研究下去,我们才可能更深刻地把握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