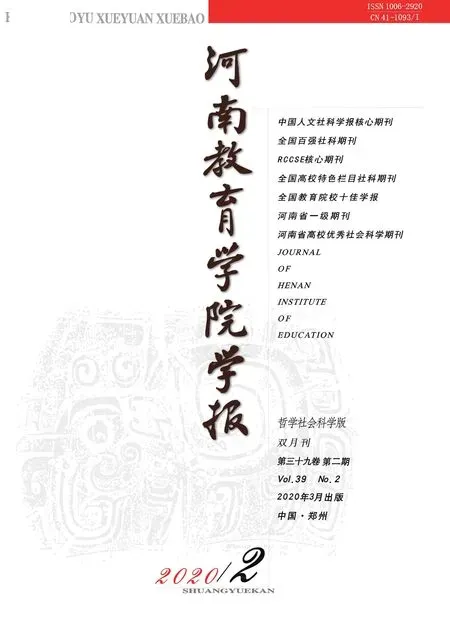文化空间的概念及其学术视野
杨 晖
一、引言
从发生学上看,空间与文化不仅仅是载体与实体的关系,更意味着二者背后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没有脱离一定空间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空间,文化和空间耦合是人的基本存在形式。文化空间,既是文化得以创造并展开表征的地点与场所,又是人作为主体以文化为线索和内涵,展开一系列权力博弈的空间和场域。文化空间,源于哲学层面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索,继而到地理学的人文转向,再到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实践论批评,以及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学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得到了多学科、多角度的关注与研究。
二、文化空间及研究综述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本身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客观容器。康德认为时间与空间都是一个先验的存在形式。黑格尔的空间哲学属于一种抽象的超验论。[1]20世纪上半叶,地理学家索尔将人类学、社会学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文化景观阐释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化景观蕴含着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与族群互构而成的一种文化整体性。马克思对时间的研究甚于对空间的研究。他关于空间的生产实践论的“点到为止”,却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起到了方向指引的作用。一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空间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客观的物理环境。1974年,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出版,提出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概念,将空间认知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特别提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三重概念来阐释空间生产,从而开创了对空间认知与阐释的社会、文化批评研究范式。[2]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提出“文化表现”和“文化场所”两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文化场所”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3]。乌丙安认为:“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4]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文化空间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彭兆荣等认为福建南音富含文化空间的表述因子,进而提出一个跨区域的“南音文化圈”。[5]类似地,乌丙安认为孟姜女口头遗产在中国已形成一个很大的民间传说圈,故事、传说物、遗址等分布最集中、表现最充分的地区构成文化空间,对其保护必须先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6]向云驹以人类学视野,全面梳理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文化空间的理论渊源、概念与特征,尤其提到文化空间是人的身体化的空间,同时分析了国内文化空间的资源、保护原则等应用方面的原则与路径。[7-8]苑利等主要从申报保护实操目的出发,阐释了文化空间内涵、普查申报与保护开发的思路。[9]黄龙光以少数民族歌场为例,分析其物理属性、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三合一的整体的文化空间性,提出少数民族歌场整体保护的思路。[10]刘朝晖以中俄比较的视角,总结了文化空间的空间区域、文化表现与主体价值认定三层含义及其保护启示。[11]邵媛媛在研究巍山彝族“打歌”保护与开发中,将“文化空间”等同于文化情境,以激发文化主体性从而实现“打歌”活态性、原真性保护与开发。[12]苗伟认为,文化空间是“人及其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场所,是文化的空间性和空间的文化性的统一”。文化空间是物化的、人化的意义世界,具有动态性、意识形态性等特征。[13]季中扬分析了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中文化认同困境及其破解思路。[14]朱刚以大理白族石宝山歌会为个案,形成了将歌会作为文化空间进行认知与阐释的时空二维分析框架。[15]孟令法以浙南畲族史诗《高皇歌》的演述场域为例,讨论了文化空间的流动性,认为文化空间的边界不是固定的,它应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对文化实践的时空建构来决定。[16]覃琮梳理了当前国内对文化空间作为遗产类型与研究视角的两条路径,指出未来文化空间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适用性与拓展性。[17]综上,国内文化空间研究大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作为研究视角,主要出于普查、申报、保护与传承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其中,文化空间概念的使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与文化生态之间模棱两可。据此,如果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人文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目前即使在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研究中,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多重主体的空间化及其社会文化批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阐释文化空间的属性,深入解析文化空间的学术视野,以充分释放文化空间既作为相关领域研究对象,又作为一种跨学科学术视野的学术张力。
三、文化空间的属性
第一,地域属性。任何事物都必须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人类文化也不能例外。文化是人类在不断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中,逐步创造和积累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的产品。文化空间建基于一定的区域场所和空间范围之上。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类型,文化空间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文化空间首先是一个空间,它绝不能凭空产生,必须有其相应的物质基础。土地、河流、砂岩、林草、空气、星辰和微生物等相关自然要素,庙宇建筑、广场街区乃至各种舞台等人工建造物,都是构造文化空间时必备的物理成分。如果离开了人的创造活动,任何空间便只能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场所,不能成为人的世界的空间维度。只有与人的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空间,才是可触可感的文化空间,才是具有地方感的地域空间。所谓普适性文化,事实上是我们称之为“文法”的普遍的内在文化逻辑。真实的文化都与一定的地方息息相关,不论这个地方是大是小,地方之上则是创造文化空间的民族、国家、社会等人类集合体。正是因为地方之上聚族而居的人类,文化空间才富有了烟火味与人情味等富有文化情怀的特征。这样,文化空间对于人来说也才真正发生意义。作为一种地方性存在,文化空间是实实在在的经验实体,文化空间虽不能够在范围或体量上具体划定,但总体上还是应该具有一定的边界范围。“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文化空间’应该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地域界定。”[8]生态博物馆、民俗文化村、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等文化空间一般比较容易划定其范围。对于诸如歌场、庙会、转山等边界范围相对模糊的文化空间而言,就只能以文化主体操弄相关文化表征的实践及其影响来圈定边界范围。如西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寨神林文化空间,其地域范围主要以寨神树为中心,以寨门、风水树以及村落林地等界标按资源权属划分并确认,是文化、空间与权属交织叠加的一个地域性复合体。
第二,文化属性。文化空间,是由根植于一个文化传统的标志性核心文化统领的综合性文化丛,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文化空间的文化属性是自然空间经过人化的结果,是人积极应对自然、适应并改造自然的一系列观念、技术与精神的相关智慧产出。“只有空间化的文化才是具体的文化,没有地点和场所的文化,是一种很抽象的文化。这种空间具体性和人的归属有直接的关系。人在其生活中形成自我统一性。这种自我统一性必须具有空间性。文化与空间的关联导致文化和人的一定生存方式的一致性,形成了文化认同,文化身份的认同。”[18]人与动物可以共享一定的自然空间,但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独特的创造能力,可以根据人的自我需要,按照人的标准空间化地创造并传承各种文化,其中有直接促进生产力的生产性技能,有规约自我社会的文化习俗和制度,有通过塑造精神、熏陶情操、寄托情感应对心理问题的哲学、宗教与艺术。正是由于这些文化的创造和传承,生活在文化空间里的人才有了文化身份归属,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化空间的文化及其表现,无论是以城市发展积淀为符号的历史街区文化空间,还是以生产技艺及消费累积为核心的技艺文化空间,或是以宗教信仰诉求为中心的庙会文化空间,都有旗帜鲜明的标志性民俗符号。这些民俗符号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式占据着显耀位置,而人以这些符号为中心进行一系列空间化的文化实践,实现社会化的空间实践。因此,不是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是文化空间,否则极有可能陷入“泛文化空间论”的陷阱。文化空间里的文化,应该是拥有一定文化史的文化沉积带,且对与该文化空间有直接关系的人们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文化空间即使不是一座文化富矿,也是一个文化富集地。
第三,社会属性。文化空间是人的承载物,是人的身体化的容器,是群居社会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及其结果,文化空间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它是一种人化空间,是社会组织、社会演化、社会转型、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类有目的的劳动应用。”[19]405人是一种群居性高等动物,人自古至今靠集体的力量求得生存和发展,仅靠个人的力量单打独斗无法生存,更别说发展了。无论在原始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无论是传统谋生方式还是现代生产方式,都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集体协作。空间无论大小,对人而言皆具有社会性,人一旦降生,即使还没有实现社会化,也必须开始与其他人一起共享空间,因此,文化空间是一个集体的而非个体的空间。文化现象是人与禽兽相异的独有特征。人类必须历经很长的时间并占据相应的空间,才能形成文化空间。人只有以集体为单位组织一系列文化表现来激活与贮存文化记忆,才能实现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人类社会才能因此获得生存和发展。文化空间周期性的文化表现,是对社会及其成员的一个核心文化招引。无论是祈吉禳灾的信仰诉求,娱神娱人的文艺展演,还是商贸往来的获利诉求,文化空间都充满社会互动的蓬勃生机与活力。同时,在文化空间的相关文化展演活动中,所有组织机构、神职人员、文艺分子以及广大观众都各有分工并各司其职,以保证精彩纷呈的公共性文化展演等社会活动如期顺利举行。文化空间有助于淡化个体观念,增强集体观念,促进构建社会共同体的意识。例如,滇中南彝族民间咪嘎哈(1)咪嘎哈,彝语,当地每年农历二月首轮丑日举村进行的大型祭祀,为彝族史诗英雄支格阿龙的仪式叙事遗存,旨在求子祈丰,祈求吉祥平安。咪嘎哈神林是一个典型的民间信仰类文化空间。节祭仪式,具有凝聚各方、团结村社、整合社群的社会生态意义。[20]
四、文化空间的学术视野
第一,整体视野。文化空间是一个具有人类学渊源的概念,研究文化空间首先要具有一种整体视野。文化空间的整体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空间的自然环境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表现,构成一个整体的文化生态;二是文化空间里呈现与表征的文化并非单一项目,而是综合性文化集群。文化空间是人类在人本主义驱动下空间生产的过程及其结果。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理念,在空间与人之间,人创造一系列的文化成果在“人-地”之间进行一种“无缝衔接”,使环境与人之间原生的生态共同体关系得以保持和维系。如果我们回到人类之初的创世叙事,神话中无不叙述天地万物与人类祖先皆为一母同胞,无论这个母亲是创世神祇还是英雄始祖。后经过原始宗教信仰的“万物有灵”观及其实践,才有了人与动植物互化的变形母题叙事。这些综合起来演绎出“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哲学。对文化空间的整体研究,从某种角度来说,主要就是为了揭示、反思和批评人与空间整体分裂的现实,并为修复“人-地”生态关系提供智识思索。文化空间里的文化集群,不仅有相同的历史记忆渊源,而且从文化类型上看是一种立体多元的综合呈现。滇中彝族传统“开新街”(2)开新街,滇中晋宁、峨山等地彝族每年春节后第一个赶街日,须举行隆重的开街仪式,届时各民间灯会依次巡街展演拜年。开街后,商铺才可开门营业,农民才能下地耕种。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空间。开新街仪式当日,毕摩主持开街仪式,民间灯会巡街竞演,人们穿着节日盛装赶街,对歌打跳,走亲会友,场面隆重。开新街仪式集彝族民间祭祀、依歌择偶、花鼓舞巡拜、赛装、地方特色饮食炊爨于一体。当日,各种歌舞同台展演,异彩纷呈。不论人类学的文化生态观照,还是民俗学的歌舞聚焦,还是社会学的社会互动,都只能代表开新街文化空间整体之一部分,如此各取所需给予重点关注,只是各学科之间的一种学术分工,研究展开后相关调查、分析、阐释和批评,都离不开整体视野,因为开新街这个文化空间在客观上就是一个空间化的社会文化体。
第二,动态视野。文化空间是一个历时与共时结合的文化综合体,研究文化空间应该具有一种动态视野。文化空间不是静止不动的,在历史的视线里它总是处于动态之中。文化空间的动态所指,一是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带来的变迁,反映在时间上主要表现为空间文化化的时代性;二是空间文化的周期性表征,表明文化空间不仅是文化存续的形式,更是具有蓬勃生命力的空间形式。文化空间生产意味着,空间在占地容积、形状格局甚至空间存废等方面所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以及这样的空间变化对文化及其主体带来的影响。文化空间格局的动态变化,是作为空间主体的人操弄的结果。人进行这样那样的空间生产总是出于历史与现实诸多原因。因此,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导致的空间格局改变与再改变,以及空间文化表征及其主体生活改变等,都是文化空间研究动态视野所应包含的内容。同时,文化空间的周期性文化表征,以历时的视角观之,精彩纷呈的年度性文化表征基本遵循一定的传统与规律。但如果以共时的视角观之,各个时期的文化表征又有着适时的创新与个性,因为文化就是在不断的继承创新中才获得持续发展的。另外,文化空间里的文化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它虽然也可能包含某些地方性历史遗址、文物民俗等,但空间主体对文化的周期性生活化展演,才是串起这些地方性遗址、文物等文化核的内在精神脐带。所以,文化空间的文化表征不是一种静态的展示,而是一种活态的展演,与人紧密相连,并直接服务于人的日常生产生活而获得动态展演与表征。云南镇沅易地扶贫搬迁拉祜族苦聪复兴新村,属于少数民族文化空间生产与文化移植表征。复兴新村就地新建的拉祜族苦聪人历史文化博物馆,是一个新兴的文化记忆之场。这座博物馆与苦聪人复兴新村融为一体,把苦聪人的日常生产生活纳入其中。这样,以整个复兴新村为文化空间容纳的苦聪传统文化就活了起来。复兴新村动态地展示并表征了拉祜族苦聪人的传统与文化。
第三,关系视野。文化空间是一个社会场域,它是文化化的空间,更是社会化的空间,文化化与社会化交织的一系列操作过程与结果,都是多重复杂社会关系不断冲突、协调、共谋的过程及结果,研究文化空间还应该具有关系视野。“文化空间生产是指运用文化的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建构空间文化表征意义的过程。”[21]文化空间是以人的标准建构对人产生意义的世界。人是社会性聚居的高等智能群体。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展现出的是一个社会关系图谱,其中涉及政治权力、经济资本以及文化象征多重力量的反复较量,其中必定充满了利益相关各方为了利益均衡而进行协商、妥协、让步、结盟等一系列往复运作。文化空间生产及其文化表征,其关系有从“人-人”“社群-社群”“社会-国家”“国家-国际”“人-地(自然)”等多重关系。这些关系由小到大,从内到外逐渐扩展,体现出一种周期性交往的公共性,其中不断生发团结与分离、冲突与协调、离散与聚合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空间意义的生成依赖围绕“生成-解体-再生”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规律。同时,作为文化空间系统化表象的文化表征,是各种形式的文化展演与呈现。文化表征必须遵循基于“结构-功能”的逻辑才能平稳运行。每一个文化子系统都是整个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子系统都代表着背后的社会组织的利益。文化表征是多个文化主体协商并达成社会交往并利益互惠的结果,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深入挖掘文化空间生产及其文化表征背后相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力量,以及多重力量之间冲突与协作的关系交织与博弈过程,揭示文化空间基于结构-功能平稳运行的深层逻辑,总结阐释文化空间生产及其文化表征的规律,是文化空间关系视野可能遵循的学术路径。
五、结语
自20世纪7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之后,空间再也不是哲学思辨上的先验存在,也不是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纯粹物理空间,而是以人的标准并经人化即空间生产与再生产后的意义世界。源于人类学概念的文化空间,是空间文化化与文化空间化的时空结合体,如果将其放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则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而存在。文化空间是多元立体的文化集群及其表征。纵观目前有关文化空间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将文化空间视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实操讨论和个案阐释阶段,鲜有针对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也缺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文化空间及其多重主体空间化的社会文化批评。文化空间具有地域性、文化性与社会性等属性,文化空间背后的各方主体以不断协商的方式实现文化建构及其表征,文化表征有机润滑并黏合了文化空间中的地域维度与社会维度,使文化空间在历史视线中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研究文化空间,应该具有整体视野、动态视野与关系视野。这三重视野下对文化空间的研究,可能需要注意包括地理边界扩大与缩小等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文化表征的活态性、集群性与系统性,文化生产及其文化表征背后所涉权力、资本等各方社会关系及其交织渗透与协商共谋等内涵与细节。同时,对文化空间文化表征的关注,即使出于一种学科分工而权宜截取某种文化形式,也要将其放置在表演理论视阈下的情境、过程与动态研究中,将其与自然环境、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观照,否则所追寻的文化符号展演可能只是一种流动的幻象,难以深度揭示并总结文化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与文化表征的真正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