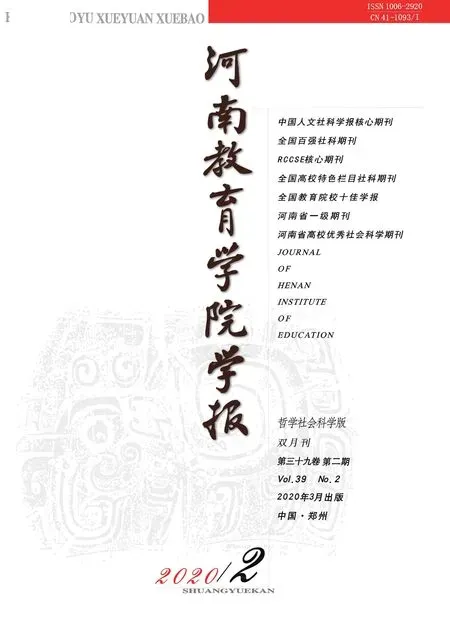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的典范之作
——评《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
柳 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思潮与建构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日益高涨的推动下,学界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进行了深入细致探讨,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然而,学界对以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20世纪头十年间的中国文学史著述,相关研究大多冠以“草创期”以至于存在诸多缺陷的评价,认为此时期国人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往往缺乏严谨的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编纂过程过于随意,乃至与“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编纂旨趣相左,较少予以公允的评价。有鉴于此,客观还原20世纪头十年间中国文学史编纂的缘起、意图及其所面临的时代难题、历史意义,将有助于客观评价该时期中国文学史编纂在中国文学史学上的重要意义。温庆新博士所撰《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一书[1],结合20世纪初期的时势背景与文教思想,探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学术资源、目的意图与历史维度,“以古还古”,并借此分析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与彼时学术变迁、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所言或可裨补学界之缺憾。
一、探讨近代时势背景、学术资源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
该书以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等20世纪初期编纂的中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细致考察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如何借用由西方传入的“文学史”框架、以“教材”形式寻求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与传统学术、西学知识的有效衔接,借此探讨中国文学史编纂如何通过改良传统学术以维系彼时的“人伦道德”。该书详细分析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与近代学制改革、学术变迁大势、古典目录学传统及西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乃至彼时编纂者的知识结构与心态转变所带来的诸多个性编纂旨趣。由此,该书设置五章,分别是:第一章“近代学术之变迁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第二章“古典目录学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第三章“‘外来经验’、古典目录学的杂糅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第四章“‘中国’想象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及第五章“个性旨趣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前四章主要从近代学术变迁、彼时学者的学术“自律行为”、学制变革,乃至传统学术与“西学”知识相杂糅等角度探讨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所产生的共性影响,以便深入分析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建构历代文学衍变史迹的方式、特征及缘由。第五章则讨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在无大量可供借鉴的同类著述的情况下,如何依据自身的个人经历、学养诉求及学术旨趣而展开中国文学史编纂的个性选择,以便详细比对20世纪初期不同文学史的个性编纂旨趣及其意义。此举使得该书的相关研究能够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演进实情。
(一)从特殊时代背景考察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话题创新与书写内容
该书指出,近代学制变革深刻影响彼时新式学堂的教育改造,尤其是《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等的颁布对近代学术变迁影响深远。而“中国文学史”编纂作为近代学术变迁的重要一环,不可避免受此影响。由此,该书发现晚清教育改革虽然规定了“中国文学门”的具体内容与教学方法,但因教育目的及授课模式异于先前,大学堂教员们必须重新编纂各科教案。故而,中国文学史教案的编纂不仅要根据钦定、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更应满足沟通传统学术与西学思想的时代需求。但学界仅仅注意到大学堂编纂的教科书是据各“章程”而撰(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未曾注意到约略同时兴办的教会学校有关中国门类课程的教科书编纂与各“章程”之间的关系(如黄人《中国文学史》)。因此,近代学制变革如何影响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内容设置、框架体例、编纂意图等,急需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经学大义”被置于近代大学各科目之首,由此导致近代大学的“中国文学门”将“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群经文体”“各种纪事本末”列为必修课,成为编纂中国文学史的方向标。近代学制变革深刻影响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内容设置及框架体例,从而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产生了本质影响。正如温庆新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之关系发微》等前期研究成果中所指出的:该时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在“致用”意图的指导下,为突出“小学”治学的传统,强调以音韵为根、重视方言研究,主张承继“小学”传统的同时应与“今之各国文字等”相通以顺应时代需要,以便进行自我改造。[2]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该书认为诸如此类的编纂选择表明:近代学制变革、学术变迁与“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文学史视域下的“小学”书写乃至对“小学”传统的严格恪守。这些是探讨近代学制变革、学术变迁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时不可回避的话题。从该时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者的人生经历与思想价值看,上述所言深刻影响着编纂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及方法论,促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关注文学的地域性差别。这就导致该时期的编纂者强调文学史视域下的经学史重构、“小学”书写与传统学术的近代改良,进而主导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内容。该书上述话题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置于彼时特殊时代背景下考察,往往发人之所未发,有助于充分发现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产生缘由及其历史意义。
(二)从编纂者的学术资源探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策略
该书对20世纪初期特殊的时代背景进行考察后,又从彼时编纂者所能接触的学术资源及其学术训练等角度,进一步探讨编纂者进行中国文学史编纂的书写策略及其必然性。
众所周知,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欲有效把握文学发展的流脉,最直接、最有效的选择是借助古典目录学。[3]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与近代学制变革及所要求的科目、课程设置有很大关系;而近代学制变革所制定的各“章程”有关各科类的课程设置,均要求从《四库全书总目》取经。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必然会转向传统目录学视域。正如该书所言,虽有学者注意到上述现象,但对《四库全书总目》如何影响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两者之间如何双向互动等探讨,几无涉及。有鉴于此,该书详细探讨了《四库全书总目》批评理念、批评方法,乃至对某一具体问题的有关论断,如何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把握古代学术、文学变迁的参考。同时,该书分析了《四库全书总目》有关文学家的生平、时代背景、创作环境,乃至社会发展状况、内部规律的探讨如何影响彼时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书写与批评方式;继而分析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如何根据彼时时势所需,从精神层次、价值层面乃至批判方法等方面对《四库全书总目》等传统学术进行诸多扬弃。此类探讨有助于客观还原彼时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借助《四库全书总目》寻求中国文学史编纂模式的努力过程。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在承继以古典目录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同时,还要不可避免地受彼时中西交流的背景影响。“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舶来品,决定其在编纂过程中必然存在西方的“外来经验”。这种“外来经验”不仅促使编纂者征引外来的同类著述,如黄人《中国文学史》大量参考了日本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自言曾借鉴过笹川种郎的《历朝文学史》、远藤隆吉的《中国哲学史》等;而且对编纂者探讨中国文学演进的论断厘定、评判标准乃至框架设计,亦有着深远影响。20世纪初期的文学史编纂大多隐含着某种程度的比较视野,这对彼时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探讨“外来经验”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进化论、几何主义、力学主义等“外来经验”与传统学术如何消融,乃至此类消融对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颇为迫切。该书的此类分析,有助于客观认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过程中如何进行中西学术的艰难选择。
二、分析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意图、编纂旨趣及其学术史价值
应该说,从近代特殊时势背景、学术资源探讨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书写内容与编纂策略,皆为了深入揭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意图及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因此,还原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意图,进而深入分析相关文学史著述的个性编纂旨趣及其探索过程、经验教训,就显得十分必要且迫切。
(一)指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政教化倾向及其“中国”形象建构
诚如该书所指出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难局面,彼时有志之士通过“致实业”、办教育、重构学术史等举动,试图实现开民智、进行人伦教化的启迪目的。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史编纂是近代教育改革与学术改良的重要一环,黄人、林传甲等编纂者对传统学术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主张恢复传统的“人伦道德”。由此,该书指出黄人、林传甲等人在编纂中国文学史时,试图践行“依自不依他”的文化传统,通过“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寻求历代文学变迁过程中的文治教化、人伦道德等传统以“经世致用”,启迪学生、开化民智,最终实现振兴民族与国家的意图。比如,黄人认为编纂《中国文学史》的目的是“谋世界文明之进步”[4]1。林传甲更是因“悲民智之日浊”而意图通过编纂《中国文学史》实现“关系民族兴衰,可为万世炯鉴”的目的。[5]152-155来裕恂则主张编纂《中国文学史》应“日新其德”[6]2。可见,“人伦道德”“依自不依他”[7]392-395的传统,不仅成为治文学史者的学术自律行为,更是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存在明显的政教化倾向,并使这种倾向贯穿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讲授的全部过程。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这种政教化书写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者采用“文学史”的形式对此前的文学进行总结,培养适合彼时国家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以满足彼时社会发展、政治改良的时势需求,最终寻求传统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体系的有效勾连点。因此,此时期的中国文学史往往强调“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国家之关系”应当成为“文学要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在中国文学史中重构“文学利于国家”的政治理念。这种现实需求促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往往强调历代文学进步之一面,从而塑造历代文学试图通过改革、改良冲破重重倒退阻隔且积极向上的“中国”形象,否定“有妨世运人心”等历代文学作品的消极意义。有鉴于此,该书得出如下结论: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试图透过想象与建构的方式,将“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历代文学作品的书写史迹为切入口,采用“作为进步的历史”与“作为历史的记忆”等方式,以“中国”形象的国家化建构替代对历代文学作品的政教化评判,以便时人从中感知出一种具有强烈集体认同感的文化记忆,最终获得包含历史真实与塑造真实两重面孔的“中国”自立自强的历史图景。[1]136-147此举是通过有特殊针对性的选择,来建构彼时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所需的历史凭借。故而,将民族富强、国家兴盛及教育启智的时代呼吁与文明进化视域下的“中国”想象相结合,成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建构“中国”形象的“范式性例证”。此类论断富有真知灼见,颇能洞见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时代意义。因此,该书相关讨论得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予以客观的学术定位与意义评判。
(二)从个性旨趣分析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探索过程及其意义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无大量可供借鉴的同类著述,缺乏可供参考的范式与模型。编纂者虽然可借助于传统学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把握中国文学发展之大势,但如何有效切入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书写,同时寻求可供参考的评价体系与方法,则随编纂者的个性旨趣而各显神通,精彩纷呈。因此,该书详细分析了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如何促使文学史兼具“传记体”色彩的“文学家代表”,兼具目录学意义的作品考辨及资料汇编,以及兼具选本学意义的“作品选”等旨趣选择。同时,该书分析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如何采用“专题形式”将“诸科关系文学者”与文学史之间有效融合起来,通过“附以鄙意”与“文典”式以身传教来授课,从而形成自身的个性旨趣。再如,探讨来裕恂的《中国文学史稿》因个人承继“风”“雅”诗教传统而大量摘抄汉魏诗歌,在编纂过程中大量摘录其所撰写的另一著作《汉文典》,同时以文字学、文章学作为编纂的两大思想,此类编纂旨趣有别于黄人、林传甲的选择。可见,因编纂者的授学情形、学术素养﹑编纂策略的差异,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呈现出了诸多个性旨趣。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呈现出一种“草创”的艰难探索过程。对此进行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此时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共性选择,为后世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总之,该书坚持还原的研究思路,综合采用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文本细读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历史社会学与文学政治学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紧紧围绕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方式、过程、缘由及其时代意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深入把握近代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亦有助于还原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诸多实情,以见彼时有志之士编纂中国文学史的艰难抉择。同时,此举不仅能细致还原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在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中最终导向传统学术的现代改良之一面,以适应彼时形势之所需等过程;亦可探讨外来的“中国文学史”如何与传统学术进行接轨,如何成为编纂者践行其目的意图的工具,编纂者又在哪些方面对西方的文学史理论进行了取舍。此类话题创新及问题研究,不仅客观还原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时势背景、目的意图及编纂者的艰难探索过程,而且,可据此合理评判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历史意义,丰富中国文学史学史的研究,为建构中国文学史学科提供经验,对如何深入讲授中国文学作品提供一定的参考。可以说,该书研究方法科学,问题意识突出,研究结论新颖,可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