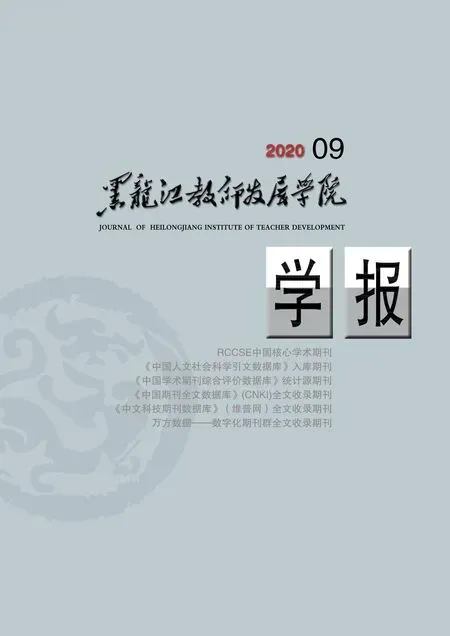拟古基础上的主旨与思想创新
——探析陶渊明《拟古九首》
卢 潇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陶渊明博览群书,对于前人的诗歌创作有着很好的继承,但这种继承并非只是简单地借用、模拟诗句或是诗歌主旨,而是将前人诗歌化为己用,融合自己的人生感悟、创作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主旨、语言文字等的创新,《拟古九首》就是其中一例。
一、辨析《拟古九首》诗歌创作之主旨
众多学者认为《拟古九首》是陶渊明于晋宋易代之后,有感于当时政治、时代的黑暗所作,如刘履在《选诗補注》中说道:“反靖节退休后所作之诗,类多悼国伤时托讽之词,然不欲显斥,故以拟古、杂诗等目名其题云。”[1]312黄文焕在《陶诗析义》中也说道:“陶诗自题甲子者十余首,其余何年所作,诗中或自及之,其在禅宋以后,不尽可考。独此诗九首专感革运,最为明显,于他诗隐语不同。”[1]312等等。从陶渊明在诗歌中大量采用比兴艺术手法来看,《拟古九首》确实是有所寄托,且寓意丰富,但如果把陶渊明的《拟古九首》都局限于悼国伤时之作,则未免有以偏概全之感。
如《拟古·荣荣窗下兰》首联:“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1]309,用了“兰”和“柳”的意象,“兰”表示高洁,“柳”表示惜别,诗人用这两个意象来比喻作者和友人当年友情的美好,同时又流露出与友人分别的依依不舍之意,但因友人“中道逢嘉友”以至“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1]309,让诗人不免有些怅然若失之感,而且结尾四句直接表达出作者对友情之易变、难以长久的慨叹:“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1]309是遗憾如今朋友之间交往的不深厚,不能做到性命相交,而且这首诗在主旨上与《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有相似之处:“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2]11—12,即都是感叹交情不终的,这也与“拟古”之题相呼应。因此,黄文焕在《陶诗析义》中的说法:“初首曰‘遂另此言负’,扶运之怀,无可伸于人世也”[1]313。还有刘履把这首诗歌中的模糊性称谓“君”实指为晋君,都认为这一首诗歌是为政治而作,不免有牵强附会之感。再如《拟古·仲春遘时雨》一首讲述的是燕子在第二年的春天又飞回到诗人的屋檐底下,并提问诗人:“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1]317前人多认为这首诗有政治寓意,如马璞在《陶诗本义》中认为“此首似讥仕宋室者不如燕也”[1]319,似乎不太可信,因为诗人想要借助燕子来表达自己虽然穷苦,即“门庭日荒芜”[1]317,但依旧心如匪石,不会改变自己的内心。再加上这首诗模仿的是汉乐府的《相和歌辞·瑟调曲》中的《翩翩堂前燕》:“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这首乐府用了燕子第二年的飞回对比反衬兄弟们流落他乡无法回家的悲惨遭遇,所以陶渊明在这首诗中应该也是欲借助燕子的飞回来比较衬托自己坚定的心志。袁行霈先生认为“此诗只是借燕归旧巢,抒发恋旧之情以及隐逸之坚。若曰通篇皆比喻刘裕讨伐恒玄事,句句凿实,如破谜语,则嫌牵强,且了无趣味”[1]319,是很有见地的。
由以上的分析来看,把《拟古九首》都认为是为政治而作则不太可信,应是陶渊明在拟古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人生感悟而作。而且就陶渊明在九首诗中所表达主旨之丰富,如感叹朋友情谊之不忠厚、荣华富贵之短暂、盛衰之无常、知音之难求,追求声名之不朽、安贫固穷之人格理想等等,每一首诗歌都有自己的主旨,亦有陶渊明自己的见解,所以不能局限于是为政治而作。
二、拟古基础上的主旨创新
因众多学者偏重于认为《拟古九首》是写当时朝代更替之感,有政治寓托之意,或是偏重于研究这九首诗模拟的是哪些古代诗歌,而忽略了陶渊明在这九首诗中对于人生的、历史的思考。因此,在这一部分,笔者主要分析陶渊明在拟古的基础上是如何对前人诗歌的主旨进行创新的。
陶渊明的《拟古九首》虽题为拟古之作,但不局限于模拟《古诗十九首》,如第一首《荣荣窗下兰》是模拟《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明月皎夜光》,第二首《辞家夙严驾》是模拟曹植《杂诗》中的《仆夫早严驾》,第三首《仲春遘时雨》模拟的是汉乐府《相和歌辞·瑟调曲》中的《翩翩堂前燕》,第四首《迢迢百尺楼》模拟《古诗十九首》中的《驱车上东门》《去者日已疏》,又类似阮籍《咏史》中的《开轩临四野》,第五首《东方有一士》“全诗声吻格调绝似《古诗十九首》”[1]313,第七首中的“皎皎云间曰,灼灼叶中华”模仿的是卓文君《白头吟》中的“皎若云间月”,第九首《种桑长江边》是模拟郦炎的《见志诗》和繁钦的《咏蕙诗》。《拟古九首》虽是拟古之作,但陶渊明并非像是西晋诗人的拟古诗那样,只是稍加改变语言风格、用词绮丽典雅,使其更加文人化,而是依旧保留古诗中质朴的语言风格,并在诗歌的整体意境和主旨上都有所开拓和创新。正如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说:“靖节《拟古九首》,略微隐喻,而实写己怀,绝无模拟之迹,非识见超越,才力有余,不克致此……”[3]
如第一首《拟古·荣荣窗下兰》是在《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感叹世态炎凉、交情不终的基础上发出对于真正友谊的思考,即“多谢诸少年,相知不中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1]309真正的友谊不会因地域、时间上的离隔而有所改变,并且能够做到尚意气轻生命,能为知己者死,这才是忠厚的表现,也是诗人对朋友、知己的认知,显然其诗歌内涵已经超出了《明月皎夜光》里对朋友不相援引的埋怨和愤恨:“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2]11而是上升为对事态常理的理性认知。
再如第二首《拟古·辞家夙严驾》模拟的是曹植的《杂诗·仆夫早严驾》:“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无志,甘心赴国忧。”[4]曹植在这里追求的是一种功名之志,是现世之事业,但这种思想却是陶渊明在这首诗里所否定的,其通过借助田子泰其人虽去世但声名永垂的事迹来表述自己对于声名的思考,即“声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1]314,由此看出陶渊明追求的是不朽之声名,但不是通过建立当世之功名即建功立业而得来的。因为对建功立业的追求虽然能得名,但这个名只局限在现世之中,不能长久,陶渊明所要追求的是高于现世之名,即对于节义的追求,显然陶渊明在曹植的基础上对于声名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再如第四首《拟古·迢迢百尺楼》模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驱车上东门》和《去者日已疏》。陶渊明在这首诗中虽然也表达的是人生短暂,但他是从自古人们汲汲于追求功名利禄作为切入点:“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想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1]320人在世时汲汲于争夺荣华富贵,但生命却是有限的,无论生前建立多少功业、享受多少荣华富贵,死后还是一场空,但每个朝代的人总是不罢休,乐此不疲,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耳,因此诗人发出慨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1]320虽然《驱车上东门》和《去者日已疏》也都提到了墓葬之地,如“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墓。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但只是通过描写墓葬之地来表达人生短暂之意,如“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2]22“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2]24陶渊明则在此基础上加深了这类诗的思想主旨,批评人们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不是停留于感叹人生短暂。而且陶渊明能够突破时间的限制,思考古往今来人们都只能够享受短暂的荣华富贵,最终还是一切都归于无,否定并可怜那些在世时汲汲追求功业利禄的人们,可以看出诗人在这首诗中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超越了功名利禄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此外,《驱车上东门》和《去者日已疏》还有很多消极之语,如“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2]22,陶渊明则在其诗歌创作中去掉了这些消极的因素,以客观的角度,超越时空的界限,以宇宙观来思考人们对功名利禄追求的结果。
最后是第九首《拟古·种桑长江边》,因诗人以桑树因江水上涨而被摧毁起兴,因此众多学者认为这是政治讽喻之作,并将此诗句句指实,与当时的政治事变一一对应,当代学者田晓菲却指出:“其文学样范乃是郦炎的《见志诗》和繁钦的《咏蕙诗》”[5],这两首诗都是借助比兴植物“灵芝”“蕙草”来表达醒世之主旨以及自己的政治失意之感的,如“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值泰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6]183“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植根阴崖侧,夙夜惧危颓。寒泉浸我根,凄风常徘徊……百卉皆含荣,己独失时姿。比我英芳发,鶗鴂鸣已衰。”[6]385但陶渊明并未局限于醒世主旨、失意之感,而是有所深入,继而描写自己不幸的经历和思考自己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境况:“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1]330,即表达出自己生不逢时,又不善于处世,直至落得如此窘迫地步之叹,但是与前两首诗歌主旨不同的是,诗人并不后悔自己沦落到如此境况,因为这是诗人忠于内心的选择。
从《拟古九首》多处化用前人的诗句、借鉴前人诗歌的主旨以及表达内容的丰富性来看,这九首诗并非是陶渊明仅仅针对当时政治所作出的讽喻之作。而且诗人在这九首诗中有意营造“拟古”的氛围,以“拟古”为题,有时空相隔之感,再加上语言风格和意象使用都有意识地贴近于古代诗歌作品,可以看出诗人是有意淡化个人具体身世,是就人生的普遍境况来思考,对汉魏古诗的“古意”进行再创造,因此在主旨上有很多创新之处。
三、陶渊明在《拟古九首》中的思辨意识
众多学者认为《拟古九首》创作于晋宋易代之际,即宋武帝永初元年或二年(公元420—421)左右。陶渊明此时的思想应是处于发展中的后期阶段,即由个人际遇矛盾感受发展到对人生、事态常理能够有着超越的认知,从小我走向大我。
大约从29岁任江州祭酒起到41岁正式告别官场以及之后几年的田园生活里,陶渊明此时期的诗歌,主要思考的是出与处的矛盾,如《归园田居·其一》:“少无世俗愿,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虚室有馀闲”[1]74,表明了自己对官场的厌倦和对田园的喜爱。但是此时陶渊明的思想还是有很多矛盾之处,一个是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让他不得不出仕,如在《归去来兮辞》中就直白地说到自己出仕的原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1]451—452另一个则是建功立业的理想也让他想出仕,如《杂诗》其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1]336陶渊明前期的思想不仅充满着矛盾和痛苦,其对人生的思考还带些消极的思想,如《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1]84即否定人们在世间的种种努力,因为生命短暂,一切终当会归于空无;再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吁嗟深厚名,于我若浮烟。”[1]106不仅否定了在世时的声名,连身后的声名都否定了,认为声名对自己来说毫无意义。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在前期的诗歌里充满对个人思想矛盾的思考,处处有“我”的色彩,对人生的思考认识也偏于消极。
《拟古九首》应该可以代表陶渊明思想发展的后期阶段,陶渊明在这九首诗中开始以超越时空的眼光和更加客观的态度来思考人生,对生命、声名、儒家思想的认识也更具思辨性。如对生命的认识,虽然此时的陶渊明也感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但能以超越时空的眼光和更加客观的态度来思考人生,即纵观每个朝代的权力更迭,人们对功名利禄的争夺,对荣华富贵的享受,最终都会随着生命的消失而归于空无:“……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1]320否定当时人们对外在功利的追求,并从历史的角度做出解释,这些都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消逝。其对声名的认识也与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不同:“声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1]320陶渊明并不否定人们和其本人对声名的追求,但他把声名分为两种,一种是现世之声名,通过建功立业就可以得到,但这种声名是带有功利性、利己色彩的,同时也很短暂,也是陶渊明所否定的;另一种则是流传于后世的不朽之声名,是通过自己对道德上的追求所得到的,陶渊明通过举例田子泰、伯牙、叔齐、荆轲这些人的声名之所以能够永传后世,是因为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了“节义”的特点,这正是陶渊明所要追求的,而且这种声名具有利他性,受后人尊崇,陶渊明鼓励自己和他人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利他性的声名,以实现自身道德上的超越。
再如其在第八首《拟古·少时壮且厉》中所表达出的济世安民的儒家思想,陶渊明的这种思想真正代表着儒家精神。钱志熙先生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中分析了陶渊明所服膺的这种思想:“儒在后世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真正的儒家精神,以济世弘道为原则,贞纲弘毅为人格;一种是统治者所说的儒术,即指礼教制度,所谓礼俗之士所执守的就是这种儒。前一种儒家精神,纯粹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之中,魏晋时代的一些优秀人物,都追求这种精神,即他们所说的大儒、通儒、君子之儒。陶渊明所追求的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一种理想的境界,这种理想境界他称之为‘道’。”[7]在这首诗歌中,诗人写到自己想要和别人讨论自己的困惑:“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1]324,但诗人又担心:“……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之。”[1]324即诗人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国家太平百姓安心,但诗人的这一努力,不同于稷下士人所谈论的:“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1]325即不管当时的统治者是不是明主都要为当时的执政者服务。陶渊明虽然也有济世之志,以国泰民安为目的,希望能遇到明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并非是明主,陶渊明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也正是他怕被欺骗和感到孤独的原因。
此外,沈约在《宋书·隐逸传》的序中对隐者的分类和在《陶潜传》中对陶渊明生平事迹的介绍,也可以看出陶渊明对内心任性自然和外在出仕的追求是并不矛盾的,“他们身上既剔除了一般隐士仅重藏身以求高名的虚伪一面,也抛开了多数士人为了高官厚禄一己之私而混迹官场的心态,从而达到顺从内心的‘道隐’和利国利民的从仕。”[8]陶渊明所要追求的不是一般隐士所要追求的“激贪厉俗,秉自异之姿”或是借助声誉来求得仕途的通达,而是“哲人”的境界,即:
亦有哲人,独执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耻从污禄,靡惑守饵。心安藜藿,口绝炮胾。取足落毛,宁怀组织。如金在沙,显然自异; 犹玉在泥,涅而不缁。身标远迹,名重前记。有美高尚,处知若无。劣哉群品,事静心驱。苟能立志,争此匹夫。进忘陨获,退守恬愉。曰仁与义,其径不迂。为之则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9]。
陶渊明一方面隐居于田园是为了保持志向的高洁,虽然日子清苦,但不会为了“五斗米”而去做违背内心的事情(出仕);另一方面,如果遇到明主,能够出仕以兼天下,出去做官不仅不用违背内心还能够秉持着仁义,能够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陶渊明还是很愿意出仕的。因此,陶渊明所要追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归隐和出仕。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在这个阶段已经超越了对个人荣辱得失的认知,而是上升到儒家的大同至德境界。
与前期的思想相比,陶渊明对人生意义的认识更具思辨性,其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生命之短暂、人们对声名的追求,而是鼓励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基础上追求更具有价值意义的东西,能够真正具有儒家的大同至德境界,不要局限于当世之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可以发现《拟古九首》虽言拟古,但就其创作主旨的丰富性和思考的深厚性,不能将其简单地概括为是借“拟古”来抒发异朝换代之感。而且《拟古九首》所蕴含的丰富哲理,与前期的诗歌思想相比,逐渐淡化了个人意识,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对人生的认知也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