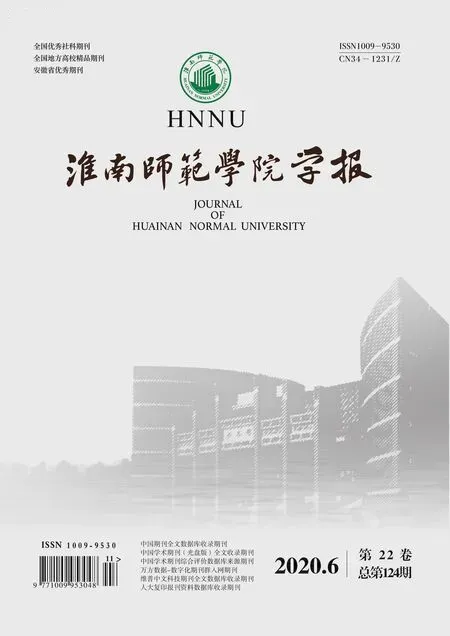王弼对老子孝道观念的发展探微
张 磊
(景德镇陶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403)
王弼作为中国历史上利用既有之传统文化资源,创造、建构、阐发自身思想理论的典范,影响之巨,旷世罕见。综览王弼生平,其本人未曾着意建立一套范畴全新的学说系统,而是倾重于借助原有之简册典籍,以对文中哲学概念迥新诠释的手法,不断开示新的义理视野,从而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理论系统。单就注老而言,王弼在抉发诠解过程之中,毫无扞格地实现了儒道、古今之汇通。碍于文章篇幅所限,今专就王弼对老子孝道观念的发展加以论析,以管窥其中关键。
一、抑末——息末:道德观念上的认识转变
《老子》一书中曾两次言及“孝”,分别为“六亲不和,有孝慈”①(《老子·十八章》)与“绝仁弃义,民复孝慈”②(《老子·十九章》)。六亲者,父子兄弟夫妇之谓也。和为相应也[1](P26),如《易·中孚》:“鸣鹤在阴,其子和之”[2](P285)。细审其中含义,尚有两层意蕴值得玩味:首先是“和”之本身所具有的和谐之义,“和”所代表的必然是多个行为个体之间所展现出来的和谐状态。如《老子·二章》中所提及的“音声相和”,陈鼓应解作“乐器的音响和人的声音互相调和”[3](P81),便在着力凸显此义,大可借资以为佐证;其次便是对“和”这种状态内在性的思考,《老子·七十九章》云:“和大怨,必有馀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按照其书的内在逻辑,这应是老子对世人行为的直接否定。世人通常认为“和”当来源于后天的道德规范③,但并未意识到此种仍有馀怨之和,却非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更甚者,基于道德规范基础上的“和”往往还会造成“强哭者,虽悲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4](P1032)的现象:为了与人交好,故作和气,勉强作为。其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外在的齐同甚至人性的伪诈,反而消解了“和”的本初含义——对不同事物本质的内在肯定与认同。“和”的本义我们还大可从文字训诂学中找到端倪,“和”④乃形声兼会意字,或言“甲骨文从侖(口吹排箫),禾声”[5](P645),或为“乃从‘’象形,象形者象编管之形也”[6](P93-102),排箫外在之形状,断非截然同一,而古人仍以其形象“和”之义,乃撷取其本质齐一而已矣。如此看来,后天之“和”与本然之“和”实走向了截然不容的对立两面。然而按照老子思想的内在理路,这种结果的产生只能归结为后天道德的形成,而后天道德形成的归因则是“大道废”,即“失道而后德”(《老子·三十八章》)。可见在老子的理论中,后天之德与后天之“和”的关系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二者在互为因果中愈渐失调。
综上可见,老子言“不和”并非是针对后天之“和”而言,而意在指向先天本然之“和”的崩坏,几与“大道废”同义。老子所特重的是“和”的情质,而非失去忠信内涵的貌饰之“和”。故而所谓“六亲不和,有孝慈”即指只有当亲友之间的交往失去情质之时,后天的道德才会被构建出来,转而继续加深这一悲剧。至此可知,老子此处所言之孝慈乃是后天道德伦理范畴下的孝慈,对其持贬抑态度。
那么老子其人是否如后世学者所言,“根本不承认孝在哲学或伦理上的地位,不承认它对社会的作用”[7](P216)呢?老子在十九章中已着重予以揭示。至于“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一句的疑惑,自郭店楚竹简出土以来得到学界空前重视,在研究中,关于字形和意义的探讨都得到了充分展开。亦有大量证据表明“绝仁弃义”当作“绝弃”,这几成学界普遍之共识,上文已叙,不待深辩。即便如此,然涉及此章尚有几处重点,须加数语予以明确。首先这里所讲到的“‘智辩’‘巧利’‘’不是社会行为而是这些行为所造成的社会状态”[8](P4),这是下文论证的基础性前提。其次我们便可依据文义梳理出此章的逻辑:由摒弃“智辩”“巧利”“”而上升至“民利百倍”“盗贼无(亡)有”“民复孝慈”。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孝慈”与其它二者在关系上所存在的疏离,作为社会状态而言,“民利百倍”与“盗贼无(亡)有”是世俗普遍认同与哲学思考认同的统一;而“孝慈”却不然,尽管他姑且可以称作是普遍认同,但却绝非是老子哲思式的认同,因为上文中老子已然将其否认。故而,要想达到文章整体理路的通畅,还需对“绝弃,民复孝慈”这一对关系加以深入分析。谛观竹简“”“”二字,我们不难发现,此二字不能简单等同于“伪诈”:“伪诈”作为一种“欺诈行为”[9](P38),其义域相对狭小,仅仅指向欺诈这一特定的行径。而“”则不然,心旁加“作”“為”的造字结构旨在说明有心去作为,即抱有某种主观目的性与功利性去作为,其指向的是人的一种普遍性行为,这与老子所奉行的“无为”是背反的。我们从而似乎也为“孝慈”的哲思认同找到了合理的解答,即老子这里所提及的孝慈并非等同于前面所论及的孝慈,而更像是在对后天道德伦理范畴下的孝慈作过减法之后,以发自本性真心的“孝”作为首要前提而展现出来的本然状态。在五千言中,老子对孝道的核心认识是一以贯之的,他提及“赤子”“婴儿”以及上文的“六亲不和,有孝慈”都旨在说明他所主张的孝慈当是以人的淳朴本性、真情流露为核心,而非强调外在的行为与规范,至于他仍以“孝慈”称之,或因言筌所致。
至此我们便可得出结论:老子所倡导的孝道乃是源于先天、发乎本然的真孝,反对由后天道德规范训练出来的“孝”⑤。那么他是否主张抛弃一切道德包括道德行为呢?根据后世研究之结果答案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意愿里包括老子)深知抛开一切外在形式的思维跃动,最终只会流为空谈,此种言说也只能是老子的无奈之举,他属意要批驳当时矫饰虚假的伪孝行为,只能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滋生虚假孝道的道德礼仪。为周全故,他也只能在文本之间委婉地表达自身的真实意图,而“绝仁弃义”这样与儒家直接激烈的对冲,只是后世的羼入。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老子的表达太过隐晦,不经几番周折与思考很难领会其中奥义。尽管他的初衷是一方面想要以理论挽救日渐下坠的世道,另一方面又想防止陷入纯粹精神境界提升式的深渊,但就总体看来,其思想仍表现为一种抑制末流的态势,其整体的哲学理路仍是在不断地做减法、反对“欲仁”,老子一味地提倡“反”“复”“损”等莫不是出于此种考虑。老子言说的凝练与隐晦,往往让后世产生误解,“绝仁弃义”的攒入便是明证,这虽有悖于老子的初衷,但也暴露了老子思想的一种欠缺。王弼已然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为其补益,在保留其“抑末”——批判虚假孝道礼仪的基础上,又着力提升、开解、明确老子思想中重视孝行的一面,悄然将“抑末”转变为“息末”。“‘息’在这一言中可以有全然相反的两种含义:一为止息、停息;一为滋息、生长”[10]。“止息”尚在老子的理趣之内,而“滋息”却不再为老子思想所涵摄,尽管上文言道老子并不反对有为。正因如此也成全了王弼非儒非道而又即儒即道的玄理思想。地
王弼在对老子的孝道思想进行发挥时已深刻展现了这一点。王弼曾言“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慈孝忠臣不知其所在矣”[11](P43),“自”字表明,他同老子所侧重的如出一辙,都是旨在抑制虚假的慈孝,而宣扬发自生命自然之真切的慈爱。他在《论语释疑·学而注》中亦表达过这样的思想:“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12]。但是仔细品味这段注解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暗藏的玄机,“自和”与“自治”既可以代表着结果,又可以指代着行为过程。当强调结果时,“自和”与“自治”所反映的只是一种浑然淳朴的现象,诚如老子所倡导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但是,当我们把“自和”与“自治”当作一种行为过程去理解时,那么“自和”与“自治”便演变成了“依照本来的样子去和”“依照本有的样子去治”。这样的论断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仍能从此篇章中找到端倪,如王弼接下来讲到“鱼相忘于江湖之道,则相濡之德生也”[11](P43),强调的便是鱼只要按照本该有的生活方式去过活,则世俗生活中所渴求的最大德行便会被呈现。如此看来,他与老子的思想便有大相径庭之感,这种差别更加直接地体现在了王弼对《老子·十九章》的理解上:
圣智,才之善也;仁义,行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绝,文甚不足,不另之有所属,无以见其指。故曰此三者(言)以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属,属之于素朴寡欲。
王弼认为“三言”当指“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而“直云绝”是因其“文而未足”,即“三言”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间必有凿枘,但老子书中却又多次提及“不尚贤”“去甚”“去奢”“去泰”的积极意义,可见此为王弼借老子之口以抒发己意之言。此“三言”诚然非老子之本意,老子本意之“三言”当为“简略的语言”之义,“三言”是那个时代的通行语,譬如“臣请三言而已矣”[13](P475)“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14](P1367)等,莫不如是。“‘三言以为’就是‘以三言为’”⑥,这在《老子》一书中亦能找到例证,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老子·三十八章》)。可见老子欲要表达的当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等情形,简而言之便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与老子所倡导的“多言数穷”“希言自然”契合无间,足可见老子思想之本来面目尚是以“抑末”为紧要的,而王弼则不然,“我们认为‘著’比‘注’或许更能体现王弼的哲学思想”[15](P236),《老子指略》中言:“父子兄弟,怀情失直,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盖显名行之所招也”[11](P199)。由此可见王弼关注的诚是德行中的质实,这与老子之思想齐同,但他却又不似老子那样反对后天道德规范,反而有意地拔高道德伦理的重要性。置言之,王弼是在有意地推动有真情质的后天道德伦理,王弼对老子在孝道观念主张上的发展由此便完全展露出来,即借老子对事象道德的“无为”之语一转而为“真为”。
探讨孝道观念仅仅涉及“孝”这一概念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尚需从相关概念以及其上位概念中检讨此观念的内涵。“孝”的上位概念便是仁德,“绝仁弃义”虽非老子之本意,但是老子对仁义仍抱有审慎态度。王弼也曾直接阐明他对待“仁义”的态度:“夫恶强非欲不强也,为强则失强也:绝仁非欲不仁也,为仁则伪成也。”可见,王弼不仅不反对“仁”,而且主张积极地“欲仁”,他所反对的只是“为仁”,也就是罔顾自然、造立施化的做法。这种做法所带来的是名教制度的固化、异化。由老子之“绝仁”到王弼之“欲仁”是王弼对老学思想在道德观念认识上的转变与发展,王弼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了老子的价值观。
二、德性自然——伦理自然:形上观念上的局度衍展
王弼要想彻底完成这一观念的具体转化,仅仅只在“孝”这一概念上下功夫尚且不足。诚使整个思想翻陈出新,亟需进一步对该理论的某些基本概念进行重新诠释。
老子崇本,其哲学基础是“道物论”[16](P159)。老子有意将世界区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本体和现象的两部分。有待的、有限的现象世界必须依赖于无限的、绝对的、独立的本体世界才能得以产生、存在和运行。老子对孝道观念的阐发是基于“道”这个根本性的核心概念而提出[17](P142),“道”之首要、根本性的意义是形而上的本原意义,“道”“似万物之宗”“可以为天地母”。形上意义上的“道”是世界的本原和一切规律的终极原因。“道”尽管不可被言说,却可以被指认,同时“道”也并不是远离着这个世界、从远处指导着这个世界,而是通过这个世界发生作用。这就意味着“道”一方面是老子孝道观念的内在依据,一方面又是他评价孝道观念合法与否的判断依据。如《老子·十八章》提及:“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⑦。即“大道废”“智慧出”“六亲不和”“国家昏乱”导致“有仁义”“有大伪”“有孝慈”“有忠臣”,“大道废”“智慧出”“六亲不和”“国家昏乱”虽未必探讨的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⑧,但其讨论核心的一致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借用王强先生言便是:“‘大伪’‘孝慈’‘忠臣’与‘仁义’一样是对‘大道’的遮蔽”[18](P108)。由此可见此处之“孝慈”并不符合“道”,也就不能称之为老子话语体系中“行于中而人不知”[19]的真孝慈。然而“道”却又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面对这样无形无象的“道”我们又该作何理解,并以之为孝慈真假与否的判断标准呢?
要想真正地理解老子之“道”,我们必须从“道生之”和“德畜之”两个序列去加以分析,老子的“道”不但有“生”的功能,还有“成”的功效。所谓“成”即是关注万物在出生之后如何存继并充分实现自我的问题。这揭示出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将无形无相、不可捉摸的“道”与有形之万事万物联系起来,同时亦赋予“道”的内容与内在规定性。老子言“道法自然”便是对“道”在本体论和内容双重意义上的终极揭示,至于《老子》文本中的“自然”之本义为何,学人目前仍有争论⑨,但“自然”之“自”具有“由……始”⑩与反身代词两种含义用以表达“原初状态”“自己如此”两重蕴意,却已是学界公论[20](P40-41)。“原初状态”是对“道”根本性的揭示,而“自己如此”则是“道”成物的具体原则。池田知久认为“(自然)是形容‘万物’‘百姓’的现有状态(存在样式和运动形态)的用语,并不是意味着客观的对象nature的名词”[21](P43)。“‘自然’作为一个名词,指代的是一种行为者自身主导的状态或过程,‘道’所法的这个状态或过程正是‘道’自身带来的”[20](P79),简言之便是道法自身,以自身与生俱来的特性作为自己发展的准绳。而老子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因之,万物自身的特性便是最接近“道”的特性,万物自身便成为了万物成为自身并赖以发展的根本与依据。王中江把老子的“道”理解为一种“弱作用力”的“道”[22],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老子惜墨如金,却在短短的五千言中反复提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十章》)及其与之相类似的话,便可验证此种说法。作为这种逻辑的延伸,“孝”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也应是自然的,即发乎人内在情质的,不矫饰、不做作的,不需要外部规范强制约束的。这对人张扬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培育人的自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自然”的内容为何时,我们又会陷入理论表达的困境。“自然”是“本来如此”与“自然而然”的统一,我们无法准确且详细地描绘出万事万物应然的状态,按此逻辑我们亦无法准确勾勒出“孝”该具备何种特质。任何对“道”或“孝”的刻画都只是对“道”或“孝”的无限接近,或直言是蒙蔽,而不是“道”与“孝”之本身。所以他言“希言,自然”,反对一切后来人为对孝德伦理道德的规范与界定,这是老子对德性自然的一种肯定。也因之老子只能借助“无”“不”“废”这样具有否定意义的词来勾勒出非道、假孝的部分,而剩下留白的部分才是对“道”与“孝”最有价值的表述。这是老子对于以儒家为代表的“泛道德论”倾向以及世俗生活中道德异化的限制与消解[23](P10),正因这样的“留白”,为王弼后来的发挥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王弼与老子虽然身处境况类似,但时代、人文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王弼要想解决新问题、提出新主张,势必不能再蹈循老子之故义,必须别开生面。老子将“道”视作无形无状之根本,亦常将“道”“无”并称,却从未将“无”等同于“道”,在老子眼中“无”仅仅“只是对道的接近”,是“道”所具备的某种属性。然而在王弼的疏解过程中,他却有意识地将“道”与“无”的概念进行了置换,从而改变了“自然”一词的内在哲理意蕴,促成了自身孝道观念的显扬。王弼首先做的便是置“道”为“无”。王弼特重于语言分析的功能,他认为世间之现有概念似有两种:名号与称谓。“名出乎彼,从客观;称出乎我,从主观”[24](P138)。“但是一旦需要表述名号和称谓的根据和原因时,他们就会体现出自己的局限性来”[25](P72),即“语言不能表达语言作为其部分的某个整体,即语言还没产生出来的那种状态”,因此在王弼看来,老子将万物之所由、众妙之所出的大道强为之名,显然是不妥当的。其实老子也意识到这一点,“道可道,非常道”便是力证。于是王弼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与“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的文本基础上,将万物之本源概括为“凡有皆始于无,则未形未名之时,则为万物始”[11](P1)。王弼的这一番理论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从认识过程来说,本来是天地万物→有→无,把他颠倒了,就成谓无→有→天地万物”,而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弼对老子哲学思想的申发。但是王弼其目的似乎并不止于此种颠倒,他又进一步对“无”做了重新解读与定义。王弼言:
谷神,谷中央无者也。无形无影,……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此至物也。(《老子·六章》注)
欲言“无”耶,而物由以成,欲言“有”耶,而不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象之象”也。(《老子·十四章》注)
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老子·十六章》注)
可见,王弼虽以“无”称“道”,但并不认为“道”不存在,而是足可以之成物,并经由万物开显,王弼言:“事有宗,而物有主,途虽殊而同归也,虑虽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执古之道,可以御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11](P126),便是在强调其中道理。由此可见,王弼以“无”称“道”的目的是:一方面在有意消弭“道”的实有性,以补老子言说之短,另一方面则是在赋予“无”以“理”的内容。劳思光、刘荣贤曾分别以“普遍规律”[26](P31)“物理”[27]释王弼思想中的“道”,大抵是可信的。由此王弼之“道”便成了既有既无、超越有无的绝对存在,亦无怪乎牟宗三先生曾赞王弼此举曰:“有而不有,则不滞于有,故不失浑圆之妙;无而不无,则不沦于无,故不失终物之徼”[28](P134)。即便如此,我们仍需注意的是,王弼为学的主要精力并不在于对宇宙规律的深度探索,亦不在于纠老子言说之偏与匡宇宙生成之正,他最根本目的乃在于对人事的注重——王弼借“道”为“无”之势进而将法自身之“自然”转捩为法“理”之“自然”,从而构建起属于自己的道德伦理体系。
钱穆先生曾指出“虽道家思想盛言自然,其事确立于王弼,亦不为过甚矣”[29](P363)。可见王弼亦重视“自然”这一概念,丁虎亦言“其(王弼)学的基本精神应为‘自然’而非‘无’”[30](P312)。在王弼的哲学里,“无”与“自然”是紧密连接的逻辑体系,王弼曾解释“自然”说:“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11](P40)。也就是说,“自然”没有具体的表现特征以供感觉器官进行感知,它仅仅只是“无”在物上的表现形式与物自身的存在方式而已,亦可称其为物的本然。同时,“无”作为物的本然属性,就意味着“‘无’是成就该物而非他物的前提条件”[31](P238),但是上文我们也已经提及王弼之“无”并非绝对的空无⑪,而是有其具体内容。至此稍加思考,我们便不难发现,王弼虽然一再强调“无”,但他仍不否认万物各有其先天规定之内容,即“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32](P2)。至此可见王弼将老子那“无法准确且详细地描绘出万事万物应然的状态,……(以及)我们亦无法准确勾勒出(的)‘孝’……(的)特质”给“固定”了下来。尽管王弼仍注重万物在由“道”创生之后“自相治理”,但是时空与物、物与物之间保持的这种和谐关系仍是依赖于无形无象但切实存在的“道”(“理”)来维系。
综上所述,王弼真正实现了“哲学并不仅仅是对存在及其本质的抽象思辨,而是始终与人自身实现或敞开存在本质(达到‘存在之存在’)的过程相联系”[33](P4)。他相信有一种绝对的“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上,并规定约束着世界万物,同时他又注意到在万物之中,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人既有同于他物的个体生理自然,又有异于他物的个体精神自然,而后者更为重要。他曾分析过人类的精神自然,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一)于己之自然,即将荣辱之身或社会之身回归自然之身;(二)于人自然,即非“强使”对待他人;(三)伦理自然,即强调“人们在日用伦常中所遵循的伦理道德常被看作如人的生理机体一样,皆属人之本然所有,并非后天主观的努力获得”[31](P240)。故王弼称“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11](P40),从而在逻辑上肯定了伦理道德的先天合理性,实现了伦理自然的理论建构,至于人所要做的仅仅只是“任其贞事,用其诚”[11](P95)。所以“孝”作为后天伦理道德的一种,王弼并不如老子那样审慎或反对其存在,而是认为只有其存在才符合“道”,他所戒惧与憎恶的仅仅只是“孝”在实现过程中产生的“伪”⑫。
汤用彤先生亦认为王辅嗣虽然以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为基础著书立说,不过他并没有废毁儒家的礼乐,只是主张所谓的仁义礼敬都必须出自本然、不造作。为政者治天下如能使世间事物臻于这样的境界,才能称得上是“王道至大者”。可见王弼实将老子之思想在生成论基础上便予以转深,经过这一番以道释儒的解释,儒家的礼乐制度就成了合乎“自然”的礼乐制度,亦即“名教”出于“自然”。
三、自化——教化:政治观念上的理论突破
老子思想的最终目的乃在于救弊,王弼亦是如此。孝道观念作为维系中国社会的重要纽带,自然会在其各自的政治主张中得以伸张。与其言此,毋宁说是二者都为了达到其政治主张而构建出互为迥异的孝道观念。因此,要想彻底地明了王弼对老子孝道思想的发展,我们还要对二人的政治观念加以深入解读。
老子曾明确提出过自己的政治思想,即“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的“小国寡民”制度。“对于‘小国寡民’,通常的解释是:国家小,人民少,这是老子对其理想社会的描述。但从下文多次使用的‘使……’‘使民……’的句式来看,(老子)显然并不是在进行描述,而是在进行设计”[34](P234)。但需要指出的是,“小国寡民”式社会形态未必是人君治下的政治模式,而是一种以原始淳朴民风为基础、以精神境界修养为路径的自治自化形式。
当然这样的解读并不意味着老子的这种理论就是复古与落后,也并不表明它仅仅是一种理想式的精神境界,相反,他是在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建立社会秩序的方式。孙思昉言:“老子之政治思想以无为为源,以农村为归”[35](P73)。李若晖也认为:“老子所设想的‘国’和‘民’,是在一片固定土地上永久居住的血亲氏族。单纯血缘和地缘成为他们永不失落的自然本性”[36]。可见老子所构建的社会图景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因此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就显得格外重要。老子云“使民重死而不远徙”⑬,虽然此句中“重死”和“不远徙”之间存在的关系一直令人费解⑭,但此时的“民”贪生重死和不轻易迁徙(或只是近距离迁徙)却是不争的事实。如若不然,老子也不会言说“虽有舟舆,无所用之”(《老子·八十章》)。老子又言“乐其俗”,即乐于其俗,这就意味着在圣人辅万物以自然的状态下,这种符合于百姓自然生活需求的风俗就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制度章程,而“孝”作为人类本能的外显⑮,是很难不被包含于风俗之内的。综合上述几点可知,老子要想凭借这样纯粹的、由地缘与血缘构筑起来的社会单元为基本单位形成一个宽松自由而又和谐统一的社会组织,是没办法也没有理由不重视“孝”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老子所设想的这种政治制度既是其孝道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其孝道观念的落实处。
但是作为守藏室史的老子遍阅古今,也深深意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而此道理又无论在任何方面皆可适用,譬如本可以使人愉悦的“五音”“五色”,在达到极致乃至过度时,就会出现“令人耳聋”“令人目盲”的境况。由此类推⑯广延至社会政治领域,便可以清楚认识到:“社会上政治上诸制度,往往皆足以生与其原来目的相反之结果”[37](P199)。而能够典型体现这一论断的则有《老子·五十七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溢彰,盗贼多有。”故而他又要以戒惧和审慎的心态防止这样事态的发生,所以他一再告诫圣人及君主要效法“道”“天”“地”,要以无为来顺应和达成万物生民的“自然”。孝道作为老子所设想之理想社会的必要“制度”,自然集中表现老子政治设计的这一特点。虽然他没有对“孝”在政治中的作用及运用做出明确描述,但老子却提出了“大道废,有仁义”的思想,在老子看来仁义乃是起于大道废弛,世俗社会中这种标榜名号上的仁义其实正是一种“私”,改变了“天地不仁”的本来样貌,扰乱了事物自身固有的本性,而以人为的方式去刻意改变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的本性,以仁义来晓谕天下,只会导致天下纷争不已[38](P91)。仁义是乱人之性,而非人之本性,而“孝”则应该发自人之本性,而不应该成为扰乱人之本性的原因。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我无为而民自化’,成为了老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39]。同理,道德无有而孝自行就成了老子对待“孝”以及使孝道成为维系人民淳朴自然生活的重要原则,于是老子便有意地通过精神境界的培养来实现理想社会。
细审老子之政治主张,其深层原因大抵有二:一是“老子的自然之道以人为最终极的关怀,在对待自然万物时以及社会治理时要求人的自觉和自省”[40](P202);二是老子政治主张之理论是以原始氏族社会为模板来进行塑造的,而后者又是前者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但随着客观世界的不断变化,政治的影响力不断被人为地强化,伦理道德开始与政治制度相结合,乃至依附于政治规范,这就使得王弼所处时期的“孝”尽管还承担着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但却与老子政治理想中承担维系社会存在核心作用的“孝”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随着“孝”地位的下降,王弼意识到,首先就当世而言,“孝”已经不能承担老子所赋予其的政治理想,再者如若再单纯地提倡自觉、纯粹之“孝”也恐难为当时朝局所见容,故而他在老子“自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教化”的观点。
王弼云:“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盲、聋、爽、狂也”[11](P28)。可见,王弼认为人固然有自然之性,固然自然之性已有定理,但在后天的发展过程中尚有“顺”与“不以顺”之区别,因之要想万物全部“顺其性”“性其情”就必须“皆各得其一”。作为本体论的解释,这固然是以寡与众、一与多来确立本体之“无”的绝对性和必要性,但也正是有了本体之“无”这一至寡之“一”的作用,万物才会“繁而不乱,众而不惑”[32](P2)。如归于事象人生,则意味着百姓不能再像老子所设想的那样自己治理自己,只能是由至寡之人治理万民,而至寡之人即为君主。于百姓言之,亦需要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来治理万事、统御至众之万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才不至于混乱,人民才会有序。王弼在注解《周易》时亦表达了此种观点:“屯体不宁,故利建侯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时也,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草昧’也。处造始之时,所宜之善,莫善建侯也”[2](P40),王弼通过以寡治众、持一统多,确立了君主的合理性与正确性。虽然王弼极力强调诸侯息乱来保证君王持守清净,并以此契合道家“无为”的旨趣;但他又同时强调了安民的关键在于德行之正,并主张以谦德来“弘正”。王弼注曰:“神则无形者也。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2](P115)。从注文角度来看,圣人之所以“神道设教”,乃是因为此“教”是天之大德的体现,由此设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尽管王弼在注解中对此进行了一定补充:天道之“神”在于其无形、“不使”,但我们也很难将其理解为一种老子思想意义中的“无为”,而更像是一种“无为之为”之教。
由此,王弼彻底论证了“教化”的正当性,那么谁又能够体察天道肩负起教化万民的责任呢?王弼认为是圣人,因为“圣人与天地合其德”[11](P14),圣人能够体悟到“道之自然”,圣人能够“全则天之道也”[41](P709),他们能够根据“朴散”的自然规律所出现的等级名分来“定尊卑”制定秩序系统,从而使“朴散”的万物移风易俗,复归于道,即“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11](P74)。由此可知,在王弼看来尽管“自然”为“本”,“名教”为“末”,但是名教的产生完全符合“以无为用”的一般规律,名教是圣人顺任自然之道而为,名教所规定的一切是“道”所赋予万物的自然规律的呈现。因此老子所摒弃的、认为足以扰乱人性的后天伦理道德被王弼赋予了先天的合理性,近而获得了存在于世象人间的合法性,作为伦理道德组成部分的孝道观念自然也成为了教化人民的一种存在手段。
四、结语
王弼对老子孝道思想发展的意义在于,王弼既看到了老子对世象社会精神虚伪和文化沉沦的警惕,又看到了老子理论本身所暴露出的欠缺。从一个新的视角、用一套不同于老子的理论重新定义并诠释了“孝”的内涵,一方面它批判了后天社会伦理关系的虚伪性,强调其情质,另一方面他又积极与政治名教相结合,以图适应当时的社会背景,并从形而上层面赋予其合理性,形成了一套兼会儒道的哲学思想。尽管其理论仍存在某些不到之处,但这种思想的提出一方面丰富了道家孝道思想的内涵,为我们正确认识孝道、重构当今社会之道德伦理规范提供了好的建议与想法,另一方面,王弼的“以传解经”的解释学方法也为我们重新诠释经典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注释:
①参阅楼宇烈的《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16版)。下文凡引《老子》不做特殊标记者,皆依据此版本,只标注章节,不另作注脚。
②郭店《老子》简1、2两组,有相当于《老子》今本十九章的文字,与今本“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内容不同的是,简本作“绝□弃□,民复孝慈”。对于“绝□弃□”,裘锡圭先生最先释读为“绝伪弃诈”,但此说亦招致学界不少批驳,如庞朴、季旭昇等人认为“□”所代指之字应是有“谁提倡过维护过的”或“很多儒家或一般认为重要的价值”,但又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字对应其释读。故本文暂以隶定之字替代之,写作“绝弃”。另,学界亦有学者认为“民复孝慈”该释读为“民复季子”,如季旭昇在《读郭店楚墓竹简札记:卞、绝伪弃作、民复季子》中便坚持此说,刘传宾亦称引之,然惜未能成为学界主流,故此仍遵循“民复孝慈”,不做申论。
③如《荀子·礼论》云:“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取也。”便是认为后天的道德规范是成就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虽然儒家思想中也强调了遵礼的自发性、内在性,但是不可置否的是后天道德规范的树立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滋生了一系列虚假道德的出现,这是老子之着眼点,也是老子之“和”思想的真正意义所在。
④说文“和”“龢”异字。“和”在“口”部,“龢”在“龠”部。许慎以唱和为“和”,以调和为“龢”。然古经传中二者实通用无别,今则“龢”废而“和”行,疑“和”“龢”本古今字,许特强为之别耳。卜辞中有“龢”字,文曰:“叀(惠)龢用”骨文合集三〇六九三篇),金文如克鼎之“锡女史小臣作之作 ,鲁 钟之作,虢叔钟之作 ,君妇壶之作 。
⑤冯友兰先生亦言“至于由学习、训练得来的仁义,那就有模拟的成分,同自然而有的真仁义比较起来它就差一点次一级了”。
⑥“三言以为”正确语序当为“以三言为”,属宾语前置中的介宾倒装或言介宾提前句,在古代汉语中这种句式十分普遍,如“自以为是”的调整语序当为“以自为是”,略可为证。
⑦“大道废,有仁义”句下,帛书及通行本均衍“智慧出,有大伪”句,郭店简本无此句,当据删。
⑧老子在第二十五章将“道”分为自然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人之道,自然之道似总领其它,是天、地、人之道的本源,是永恒不变的法则。但这里老子又提到“大道废”,并联系“智慧”“六亲”“国家”等词,乃知此处之“道”乃指“人道”言。任继愈又认为所谓仁义、智慧、孝慈、忠臣乃是老子认为的病态社会中所出现的反常现象,在“道”的社会里不会出现此种问题。置言之便是“大道废”方出现此类种种,由之可见此处之“大道”统摄“智慧”“六亲”“国家”等概念。参阅黄炳辉、陈永栽的《老子章句解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版)和任继愈《老子今译》(古籍出版社1956版)。
⑨常见的有以下几种观点:(一)自然而然,相对于物来说没有外力干涉下自我存有的状态,而对人而言则是顺物性而为的动作;(二)事物内在的本性。即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也是事物保持自我存在的特性;(三)事物的应然状态。最近较为新的提法是刘笑敢将“自然”理解为“人文的自然”,即万物存在的一种和谐状态。这种说法似乎更强调从与人的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待。
⑩自,作鼻形,今俗以作始生子为鼻子,故自表“由……始”义。参阅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版)。
⑪即同前文所叙之王弼强调“无”,乃消解道乃一实有,而非要否认道德存在。
⑫王弼倡导真情,而反对伪善。王弼似乎预设了理想的人性是可以完全按照本来状态发展的,而不顺性命只能造成损性。虽然王弼似乎对性与情的区分并没有持一种十分积极的态度,但据已有的文献,仍有几处涉及此关系:静专动直,不失大和,岂非性命之情者邪?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宗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比性情也。“性命之情”这个概念显然是庄子最先使用的,王弼注释《老子》多处使用了庄子哲学中的观念,这个观念显然体现了性情一体,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分性与情。有学者指出,王弼的“性命之情”是指“天的自然本性”,天之情不失天之性,才是天之真情。
⑬帛书甲乙本均作“使民重死而远徙”,可知“远徙”之“远”字,非做远近解的副词,而是作“疏”“离”解的动词。如《广雅·释诂》:“远,疏也。”《国语·周语》“将有远志”,《晋语》“诸侯远己”,《论语·学而》“远耻辱也”,在此“远”皆训“离”。
⑭一般有两种认识:一为并列关系,如河上公曰:“君能为民兴利除害,各得其所,则民重死而贪生也。……政令不烦则民安其业,故不远迁徙离其常处也”;再为因果关系,如王弼言“使民不用,惟身是宝,不贪货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远徙也。”
⑮在本源情境下,“孝”是作为人性自然情感的显现,是自己如此的,诚如阳明先生所言:“见父自然知孝。”诸如自然社会中仍会在无意识的条件下产生“反哺”“跪乳”的行为,这种无意识一旦随着人的理性自觉的不断张扬,渐渐地开始由无意识转而进入为有意识的活动,就意味着孝道思想已经被完整地树立起来。尽管两者在分析时表现出的特征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后者这种理性自觉是建立在前者自然冲动基础之上的。
⑯崔清田提出“推类是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此观点提出之后,引发学界广泛讨论,具体观点分列如下:(一)“推类”是类比推理;(二)“推类”是中国式类比推理;(三)“推类”即推理;(四)折中策略,即它的内容或形式,既有‘推类’的特殊意义,亦有作为‘推理’的逻辑基础的一般意义”。本人认为“推类”是类比推理,并且这种类比推理是中国式类比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