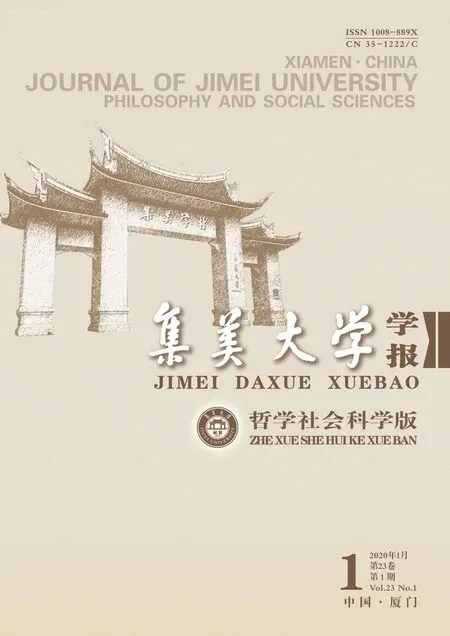虚幻的使命,幻灭的理想
——从不可靠叙述看《上海孤儿》中命运的幻灭感
盛春来
(1.武汉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三峡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一、引 言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凭借其多年来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创作斩获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追述往事,展现主人公在经历重大历史事件后个人失落的情感,他善于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烘托一种悲伤的情绪并在读者身上产生共鸣,从而使人深深同情并认同主人公的命运。布鲁斯·金(Bruce King)在评价石黑一雄的作品时说:“他通常围绕虚假的或者误导的记忆进行写作,表明人们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怎样移植情感并且改变历史。”[1]165石黑一雄研究专家谢弗(Shaffer)也说:“石黑一雄的小说是主人公带有问题的或者带有妥协的过去的心理神秘之旅,他的所有叙述者都在生活中遭遇了深深的心理断裂,总是通过一个长期斗争来把过去和不合时宜的现在联系起来。”[2]26发表于2000年的小说《上海孤儿》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通过不可靠叙事的写作手法揭示了记忆的不可靠,也从本体上展现了个人理想破灭后的幻灭感。
不可靠叙事是石黑一雄作品的典型特征,戴维·洛奇(David Lodge)以石黑一雄的代表作《长日留痕》为例,论述了不可靠叙事“揭示表象和真相之间的鸿沟,展现人们如何歪曲或掩盖事实”。[3]155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 )从人道主义角度论述了《上海孤儿》中因为战争导致了租界生存的危机。[4]241在石黑一雄获得诺奖以后,国内对他的研究也渐入高潮,对《上海孤儿》的研究集中在身份建构、家园政治、创伤记忆和中国形象等主题分析(1)身份分析主题见:方宸.石黑一雄《上海孤儿》中身份的建构与解构[J].外国语文,2012(2):27-30.王飞.《上海孤儿》主人公班克斯的身份困境[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9(2):56-60.家园政治主题见:王卫新.石黑一雄《上海孤儿》中的家园政治[J].外国文学研究,2017(5):35-43.创伤主题见:石春媚,石吉文.迷失与重生——《上海孤儿》中创伤书写的空间维度研究[J].外语教育研究,2018(4):52-56.张晗,刘积源.《上海孤儿》的创伤悲剧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5(4):60-66.中国形象主题见:丁萌.石黑一雄对中国形象的客观建构——以《上海孤儿》为例[J].沈阳大学学报,2018(4):518-523.,但鲜有人从不可靠叙事的写作手法论述该作中的幻灭主题,因此弥补这些遗憾正是本研究的要义所在,这也会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该作品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展现了主人公的幻灭感既源于个人长大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也源于主人公对父母过于理想化的想象,应该看到,这种幻灭感也是当今人类所不可回避的生存状态的真实描摹,带有很强的普世性。贯穿《上海孤儿》的不可靠叙述手法不仅见证了班克斯作为叙事者和人物时而重合、时而分离的双重身份,还使得读者产生模糊、不信任、不确定的心理效果,进而也建构了小说的主题——对人类如孤儿般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
二、不可靠叙述之主观叙事
幻灭感来自于个人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冲突,当理想在现实中破灭的时候,个人难免会产生失落和惆怅,但人生就是由充满美好的理想走向理想破灭的过程。石黑一雄曾说“要想让孩子长大没有创伤就得让他们受欺骗”。[5]82在他看来孩子总是生活在对未来怀有美好期望的肥皂泡之中,当他们长大后肥皂泡终究要破灭,为了避免理想破灭后的失落,就得让他们生活在善意的欺骗之中。所以在成长小说《上海孤儿》中,石黑一雄运用不可靠叙述从形式上、本体上展示了人生幻灭的生存状态。
《上海孤儿》依靠碎片化的不可靠回忆来编织故事,正如该小说的英文题目WhenWeWereWOrphans(当我们是孤儿时)显示那样,孤儿隐喻了人类要脱离母体、单独生活的生存状况。小说充满了主人公班克斯的第一人称回忆,作品的不可靠叙述首先就体现在叙述方式上是第一人称主观叙事,因而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有评论指出:“班克斯在第一人称的复杂回忆中,随着他试着理解他的世界、他自己和他的过去,他把信仰、不确定和不可靠结合在一起。”[6]79读者跟随班克斯的记忆一步一步走进他的心灵,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叙述者不停地在记忆和现实中穿行,亦真亦幻地展现了个人的成长历程。从全文的布局来看,该小说由七个部分构成,每个部分都被作者以清晰的时间和地点分割开来,时间上大都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地点的变化也主要在伦敦和上海之间,这样的文体结构在有的批评家看来像是“笔记式的侦探小说”。[7]17在作者石黑一雄看来:“从根本上而言,他之所以喜欢采用回忆的手法是因为它就像一个过滤器,人们可以透过它审视自己的生活。因为回忆往往模糊不清,自我欺骗的成分便始终存在。”[8]292作者毫不掩饰地承认由于回忆模糊不清,因此存在欺骗的成分,所以小说人物命运的真实性也相当可疑。正如作者所言,回忆就像一个过滤器,班克斯的回忆也是选择性地回忆儿时的往事,他的回忆过滤掉和父母无关的东西,甚至在他的记忆里只有关于父母的美好回忆。撇开一个少年对父母的爱而言,回忆里只有美好的成分本身就表明了该回忆的不可靠性,更重要的是他的记忆都是从他自己的视角出发,回忆的都是他自认为对自己影响重大的事情,所叙述的都是采用第一人称主观视角,因此这也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在第一人称回顾往事的叙述中,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个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情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和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9]187一个人的眼光不仅涉及他(她)对事物的认知程度,还涉及他(她)对事物的感情态度、立场观点等。作为一部明显带有成长小说特征的作品而言,主人公班克斯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跨越了十几年,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早已物是人非,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通过检视前后不同的叙事眼光就能体察到主人公不同的心境的变化,从而能深入揭示作品的主题。当班克斯意气风发,成了伦敦的大侦探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邂逅了在他童年起决定性作用、抚慰幼小的班克斯,并把他从遥远的上海带回英国的恩人张伯伦上校。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班克斯请已经落魄的上校吃饭。
“现在回想起来,我选择去多尔切斯特法式餐馆吃饭实在是有欠考虑,毕竟当时我已经猜测到上校手头拮据,由此也该想到如果他连账单上属于他的那一半都付不了,这对他的自尊心会有多大的伤害。但在那时,这种事情我根本不会去考虑。我一门心思关注的只是怎样最充分地让这位长辈好好看看分手这些年来我的巨大变化。”[8]22
在此选段里,叙述者和人物的叙事眼光悄无声息地实现了转换,从“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看,当时的我实在考虑不周,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上校的手头拮据,但从“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看,我一门心思只是想给他展示我取得的巨大变化。虽然叙述者和人物是同一人,但叙述者“我”分别处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并且认识观和感情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毫无疑问,叙述者“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我已经成熟,能够自己实现从伦敦到遥远的上海去寻找失踪多年的父母的夙愿,两种叙事眼光的对比恰好反映了叙述者之前和现在在认知和情感等方面的差异,可见,在揭示命运的反复无常和记忆的不可靠性上,隐含作者和叙述者“我”是一致的。
在小说叙述中,叙述者“我”也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提醒读者注意他的叙事是在回忆中。“就拿我刚才提到的有关妈妈和卫生检察官的插曲来说,我一直肯定自己对所有要点记得一清二楚,但是,在头脑里再过上一遍,我就发现其中一些细节不是那么肯定了”。[8]63作者这些前后模糊不清的记忆使得读者很难相信作者的叙述,这尽管会增加读者在阅读中接受信息的戒备心理,但也印证了记忆的不可靠,为后文出人意料的结尾打下了伏笔。当班克斯父母为了鸦片贸易而争吵的时候,作者也耐人寻味的写道:“也许就在这时妈妈关上门,带我离开了书房。其他事我就记不清了。当然,我对那天父亲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尚且无法确定,具体说了什么话就更记不清了。以上只是根据回忆形成的大致情形,其中无疑不乏事后想象的成分。”[8]81在这里,作者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叙述自我的记忆是模糊的、不可信的,含有事后想象的成分,他对事件的记忆明显的带有自己的阐释和想象,所以在真实性上也值得怀疑。弗洛伊德说:“记忆是叙述者在当下生活的各种困难的驱使下,由充满期待的幻想构建而成的,就像梦一样,通过隐喻和双关将来自不同源头的因素浓缩起来。这不仅意味着明显的记忆是欺骗性的,本质上就像是做梦样,而且还意味着记忆的形成可能是对于当下各种困难的回应”。[10]1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叙述者第一人称的不可靠的记忆叙事就是使自己并不存在的、寻找失踪多年的双亲的“使命”意义化。
三、不可靠叙事之修辞维度
发端于韦恩·布思(Wayne Booth)的不可靠叙述的概念在当今学界引起了“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之争。[11]22倡导修辞学方法的韦恩·布思认为:“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这样的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反之就是不可靠的。”[12]158布思判断叙事是否可靠的标准是思想规范(norms),即作品中事件、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11]74也就是说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思想规范是否一致决定了叙事是否可靠。一般而言,读者在初次阅读中很难一下子就能分辨出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是什么,大多时候也是在通读文章之后,才能体会出隐含作者所传递的思想规范和主题等。在初读《上海孤儿》的时候,特别是在文章的前半部分,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叙事在记忆与现实之间不停地切换,稍不留神就难以分辨哪是现实,哪是回忆。从小说的第一部分前面开始,班克斯就邂逅了年轻的女子莎拉,莎拉不断地引起他的注意,班克斯的叙述也是围绕她不停地闪回,叙述者“我”总是在和莎拉的交往以及成为侦探的叙述之间一次又一次地展开对往事的追忆。初读作品,隐含读者的意图很费解,直到最后读者才明白,这样如梦如幻的叙述正是为了揭示莎拉对班克斯若即若离,使得他总是徘徊在记忆和现实之间,处于想实现远大抱负和对年轻女性的爱慕而辗转的两难状态。
“布思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另一种涉及价值判断,读者在阅读时需要进行双重解码(double-decoding):其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判断事情的本来面目。”[12]这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都在小说中有很多的反映。
首先来说,班克斯长大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多年前在上海失踪的父母的踪迹,在他的记忆里,“幼时的我一直以为妈妈是反鸦片运动的领导人物”[8]59,所以长大后,他在大英博物馆里想找到有关妈妈的报道的资料,当他最终真的在大英博物馆里找寻妈妈的记录时,“因此,难免对只字未见她的名字感到有些失望。要说名字被反复引用、赞美、诋毁的也不乏其人,但在我查找整理的所有资料中,就是一次也没有看到妈妈的名字”。[8]59这段话确凿无疑地显示叙述自我确实在陈述往事,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在班克斯眼里就是真实存在的,但这样的事实在读者看来是不可靠的叙事,其效果就是使读者哑然失笑,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叙述者班克斯也就成了被嘲讽的对象,原来母亲并非如记忆般美好、高大。在叙述者眼里,言之凿凿的事实,却在读者眼里产生了荒谬可笑的效果,这也在不经意中暴露了叙述者本人不可靠的记忆、狭小的视域和自欺欺人的性格特征。这在布思看来就是“作者和读者会在叙述者背后进行秘密交流,达成共谋,商定标准,据此发现叙述者话语中的缺陷,而读者的发现会带来阅读快感”。[12]22作者和读者此时绕开叙述者班克斯完成了文字背后的秘密交流,作者通过叙述者荒谬的陈述给读者带来了荒谬可笑的审美效果。显然,作者并不只是有意显露主人公班克斯的可笑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班克斯的滑稽可笑的特征旨在展示后现代语境中人的生存状态——对一切模糊不清,处于纷扰和不确定的状态。
其次,叙述者班克斯经常叙述模糊不清的往事,并且还不忘附上自己的价值判断,在故事的开头,当他回忆参加友人的聚会时,“相信正是这种焦虑不安的心情,使我如今回想起那个晚宴时,许多事情都显得颇为夸张,虚假不实……如我所言,我肯定这些印象无一确切,可记忆中的那个晚宴就是如此”。[8]122班克斯这种模糊不清的叙述恰好反映了叙述者本人犹豫不决、处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措置状态。历史上,由于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上海等地出现了大量的国中之国——租界,在那里殖民者践踏所在国的主权,复制宗主国的生活模式,对当地输出殖民文化,这虽然满足了殖民统治的要求,但也使生活其中的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产生了深深的文化认同的困惑,以致从小生活在租界里的班克斯和他的好友哲一直把租界当做自己的家,对班克斯来说,“我在英国住了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真正觉得它是我的家。只有外国租界,它才是我永远的家”。[8]233哲也不想回到父母的祖国——日本,哲被家人视为不够“日本化”,班克斯也被认为不够“英国化”。班克斯和哲都陷入了深深的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父母的故国难以适应,另一方面自己长期生活,承载他们记忆的地方——租界也只是帝国主义孤悬海外的殖民前哨,虽然对他们有归属感,但也是空中楼阁,缺少根基。在租界里洋人和华人并存,瓜皮帽和西装随处可见,所在国的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生活在其中的人,特别是小孩子难免会陷入身份缺失和文化断层的无归属感,因此班克斯、哲连同承载他们记忆的租界也就带有了深深的文化孤儿的烙印。“人类对自身的存在和身份的感知是以记忆的延续为前提的。一旦丧失了记忆,或中断了记忆的连续性,身份就无法得到确认,自我就没了灵魂,存在就成了虚无。”[13]139叙述者模糊不清的记忆和不可靠的叙述都凸显了对自己无以为家的身份归属的焦虑感。
四、不可靠叙事之认知(建构)维度
布思的修辞法以作者为中心来判断叙事是否可靠,塔马·雅克比反其道而行之,他强调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看叙事是否可靠。“读者和叙述者的世界观的差异,而不是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不一致,能使得读者确定叙述者是不可靠的”,[14]22以隐含作者为中心的修辞维度的不可靠叙述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认知建构维度的不可靠叙述可以互相补充,两者的结合可以更好地解读文本的内涵。从认知维度而言,读者的阐释框架非常重要,“当文本或语境信号向读者显示叙述者有可能是不可靠叙述时,读者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或价值观念、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动记忆掌握的文学规约等参照框架对叙事者的话语进行解码,通过叙述话语的隐含含义来推断事情的真相”[15]22,破解叙事者的含糊和自欺欺人的叙事目的,实现深入理解文本背后的含义。《上海孤儿》里,虽然父母失踪已经有十几年,但班克斯还是把记忆定格在十几年前父母失踪的时刻,在读者看来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主人公看来却是坚信不疑的事实。好友哲和班克斯都相信班克斯的父亲是由于绑匪勒索钱财而被绑架的。“爸爸房间的窗户视野开阔,面对江河;睡的床是绑匪从汇中饭店偷来的,非常舒适”。[8]102在孩童的班克斯看来,即使是父亲被绑架,父亲的生活场所也还是很温馨的,丝毫没有被虐待,也不存在危险,似乎父亲只是被别人接去度假一样。长大后的他按图索骥,依照童年的记忆寻找双亲,即使在解救的细节上都和儿时的想象一样。班克斯已经长大,但他的回忆却自欺欺人的停留在小时候,难道班克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虚幻的吗?且不说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记忆的不可靠性,单是岁月流逝,沧海桑田,稍有点常识的读者就能根据社会经验和文学规约理解这种不可靠叙述的意图。班克斯在追述往事的时候曾意识到自己的记忆有含混不清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不必要真的认为他就是那样幼稚地相信时隔多年,双亲还关在上海的某个地方,毫无疑问,叙事者正是通过这种不可靠叙述来展现理想与现实的破裂,而由这种断裂引起的理想的幻灭感,正是作者所要传递的真实意图所在。由此可见,作者正是通过这种不可靠叙述的手法来展现个人成长的失落感。
叙述的不可靠还体现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些不太令人信服的情节,读者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或价值观念、文学规约等参照框架判断出对叙述者的可信度。认知建构叙事学代表A.纽宁( Unning)也说:“不可靠性与其说是叙述者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读者的阐释策略。”[16]95《上海孤儿》的高潮几乎都安排在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首先,在战争的隆隆炮火之中,班克斯居然跑到前线去寻求中方军人的帮助,替他找寻自己臆想的被关在靠近前线房屋里、失踪了十几年的父母。大战在即,个人的家事应该是次要的,但把战争和家事两件事并置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令人质疑他失踪的父母是否真的能在前线找到,如果真的找到了,那将是极大的巧合,事实是没有找到,但也动摇了叙述者叙事的可靠性。离奇的是,班克斯竟然在战场上与费尽心力要找的儿时朋友哲不期而遇,相逢的地方居然就是臆想中关押班克斯父母房子的附近。班克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关押父母的房子时,出人意料的是从房子里走出的竟是失去亲人、成为孤儿的中国小姑娘。就在读者瞪大眼睛想要核实班克斯究竟能否在房子里找到他父母的时候,作者故意引而不发,叙述的焦点转换到房屋被炸乱的样子,他和好友哲也一起被日本士兵带走,聪明的读者还是一眼就明白,班克斯的父母并未找到,叙述者心心念念的理想破灭了。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菲利普叔叔向班克斯揭露他父母失踪的真相的时候,菲利普居然说自己加入了共产党。班克斯的妈妈,一个有着典型的维多利亚风格的美女,连做鸦片生意的英国父亲都感觉配不上的白人女性,居然会在丈夫出走以后,下嫁一个和土匪差不多的中国军阀顾汪,以换取军阀对班克斯的资助,该军阀当着客人的面鞭打她,调教“白人娘们”、蹂躏班克斯的母亲。一个漂亮而又有正义感的白人母亲沦落成别人的玩物,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这些情节都使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能明察其中的不可靠之处。难怪作者石黑一雄坦白地说:“在写作之前,我对中国的了解都是来自书本,只是借助几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和父亲的叙述,我才把故事的场景选择在我不太熟悉的中国”,[17]406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读者能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或文学规约判断这些叙述都是不可靠的。
这种不可靠叙述产生了无限的张力和强烈的反讽效果,作者并非意在展示主人公痴迷的傻劲,读者也无意讥笑班克斯的执着,也许正如石黑一雄在接受访谈时所说那样:“当然,你长大了怀着失望的心情——也许是深深的失望——世界并非如你以前想象般美好。”[2]166在小说的结尾,班克斯也不无感慨的总结说:“也许世上有人能够不被此类忧虑纷扰,心无牵挂、无忧无虑地终其一生。可对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就注定要孤身一人面对这个世界,岁岁年年地追寻逝去双亲的影子。我们只有不断努力,竭尽全力完成使命,否则将不得安宁。”[8]281班克斯终其一生苦苦追寻的只是逝去的双亲的影子,也就注定了他找寻的结果必然是令人失望的。如果说他在伦敦的成长是值得称道的奋斗历程,那么重隔十几年回到上海的班克斯,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具备寻找到亲人的可能,难怪班克斯见到在精神病院的母亲后说:“奋斗是没错,问题是最后并未改变什么。总之,一切都过去了。目前我生活的主要目标是控制身上的风湿病。”[8]282此时的班克斯已经看穿世事,尽管他毕生要实现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实现,但不幸的是他已是疾病缠身,班克斯奋斗了一生什么也未改变,除了疾病和回忆,什么也没有得到。难怪歌德说:“人越努力就越迷茫。”班克斯何尝不是越奋斗越失落呢?至此,小说展现命运的幻灭感、奋斗的失落感一目了然。如果我们非要找到主人公全部悲剧的根源,E.M.福斯特(Forster)曾说过的话也许能使我们窥见端倪,“一个孩子的全部生活取决于它对父母理想化的想象”,[4]245班克斯的全部生活和失落感就来自于他对父母理想化、自我拔高的英雄式的想象,叙述者“我”想象地把父母的形象拔高到他们不曾达到的高度,生活在父母“高大形象”投射的影子里,这也就注定了班克斯的命运的悲剧色彩。随着班克斯的长大,美好的童年在日渐远离,残酷的现实渐次褪掉神秘的面纱,原来世界不再是想象般的美好,依靠这种不可靠的记忆编织的梦想终究有破灭的时候。
凡此不可靠叙述,其目的还是为了展现人物失落的命运,石黑一雄在谈论孤儿的隐喻的时候说:“在我们生命的时刻,当我们走出童年呵护的肥皂泡的时候发现世界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温馨,即使当我们长大,我想这些失望还是存在。”[2]166班克斯成长的历程就是走出被肥皂泡包裹的美好记忆,进入人类如孤儿般幻灭的生存状态。叙述者和叙述人物的班克斯在此也完全融合,在作者看来,长大的过程就是理想破灭的过程,失望是难以避免和普遍存在的。应当指出,无论是班克斯、莎拉还是养女詹妮弗,乃至不知名的战场上的小女孩,这些孤儿都笼罩在理想破灭的失望之中,所以孤儿的形象带有普遍的隐喻含义,暗指了人生理想破灭的生活状况。
五、结 语
《上海孤儿》中叙述者通过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事使一个不存在的使命意义化,依托不存在的使命实现的梦想必然是破灭的,同时也揭示了后现代语境中个人对无以家为的身份归属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也随着梦想的破灭而产生幻灭感。小说前面关于记忆的部分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最后几章的描写又回归到现实主义层面,这完全吻合了前面部分是回忆、追述往事的不可靠性,后面章节写实,凸显了在现实面前理想必然破灭的失落感。不管是叙述者通过回忆找寻双亲的故事,还是其他孤儿的故事,无论是虚幻的使命,还是幻灭的理想,或是孤儿的隐喻,通篇文章渗透着幻灭的情绪,这种幻灭的情绪既是小说人物的悲剧,也是作者本人对当今人类难以回避的生存状态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