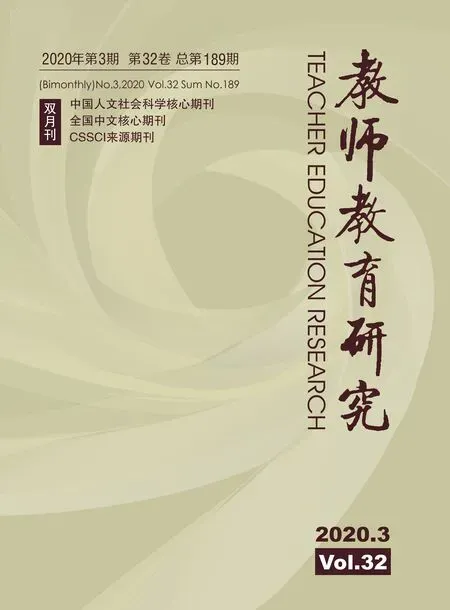民国乡村教师负面情绪的心态史考察
吉 标,庞美琪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山东济南 250014)
一、问题提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在乡村,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的改造,而乡村的改造又首在推广新式教育,推动乡村教育的重建。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事业的主要承担者,对20世纪上半叶我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所提的民国乡村教师,主要是指民国时期任教于县级以下区、乡、镇和村落学校,以乡村儿童为教育对象的教学人员。民国时期,乡村存在多种类型的教育机构,如公办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以及家族私塾等。笼统地说,任职于上述各类学校的教师都属于乡村教师。但由于公立(体制内)或私立(体制外)的乡村新式学校是乡村学校的主体,教会学校较少,而私塾又受政府的严格限制,所以民国乡村教师主要也是以乡村新式学校的教师群体为主。[1]从来源上看,乡村教师群体成分较为复杂,初期以失意的科场士子、改良后的塾师为主,后期以初中和师范毕业生为主。
限于资料查阅与搜集的困难以及研究队伍的不足,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学界对民国乡村教师这一群体的关注和研究并不充分。新世纪以来,随着一批民国教育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中国近代史文献资料数据库也纷纷建成,加之受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影响,民国乡村教育逐渐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借助历史文献和原始资料,从社会史、生活史视角对民国乡村教师的经济收入、生存状况、职业发展、社会角色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考察了以往宏大理论叙事模式下所忽视的乡村教师的真实生活境域,取得了颇多学术成果。事实上,民国乡村教师的形象并非像主流教育史学描述的那般模样。就笔者所搜集和占有的资料来看,民国乡村教师群体生存状态比较低迷,存在严重的心态失衡,对职业充满了抱怨、牢骚和焦虑等负面情绪,“随波逐流,与俗浮沉,对于事业不肯努力,甚至消极颓废,悲观自放”[2]现象比较普遍。目前,虽已有研究者开始关注民国乡村教师的负面情绪,但整体来看,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全面的考察和系统的研究。
二、民国乡村教师研究的心态史视野
心态史学是历史学知识体系与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为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提供了新的认识论视角,它重视历史上各类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研究各种社会群体的精神风貌、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关注其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1932年,法国历史学者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出版了《1789年的大恐慌》一书。该书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心理进行了细微考察,指出集体心理往往是社会重大危机的根源,是影响事件之间真正发生因果关系的关键。应该说,勒费弗尔仅仅是从心态史的视角来看待、分析历史事件,而严格意义上的心态史研究方法则开始于法国年鉴派的创设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1938年,费弗尔发表了《心理学》一文,系统阐述了他对集体心理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提出要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关注一定时代大众心理状况和群体意识,强调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来研究个人的心理成长。与传统史学只关注物质生产和社会结构不同,心态史重视民众个体日常的观点、看法、行为、态度,注重揭示这些微观要素对历史发展的实际影响,这有助于弥补传统史学研究的视角偏狭,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野。20世纪80年代后期,心态史开始引入我国史学领域,并逐渐影响到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目前也已引起教育学领域一些研究者的关注。[4]
从心态史的视角切入来研究民国乡村教师,首先要考察其日常生活史。“日常生活史是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史。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特点和本质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领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细节,恰能细致入微地反映出时代的氛围”。[5]虽然我们无从回到民国乡村教师的日常生活现场,但可以借助他们留下的大量文字,来还原他们的日常生活,透视和分析他们真实的情绪体验。从1901年我国自编的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问世至1949年,由当时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团体、出版机构或个人创办的教育期刊累计达千种以上。这些期刊介绍西方教育理论与方法,传播国内外最新的教育实验成果,也刊登了当时很多乡村教员的教学日记。
其中,《民众周刊》《民众生活》《教育短波》《教师之友》《教学生活》《小学教师》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由乡村教师撰写的生活回忆文章,详细记录了乡村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形象地展示了乡村教师职业的酸甜苦辣,真实反映了他们在困顿环境下的心理感受。笔者重点查阅了1929年至1939年间发表在以上期刊上的自传体文章,来透视民国乡村教师的生活史,剖析民国乡村教师的负面情绪,揭示乡村教师精神生活的另一面相,拓展民国乡村教育的研究视阈。
三、民国乡村教师负面情绪的表征
通过阅读和分析大量乡村教师的自传性文献,可以看出,民国乡村教师的负面情绪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对微薄薪酬的抱怨
民国初期,新旧政治体制出于交替、变革过程中,全国教育经费投入体系尚未建立,初等教育经费主要是由地方自筹,中央政府对教师的薪俸没有统一规定。而且,由于军阀混战,经济衰败,教育经费频繁被挪用,乡村教师收入缺乏稳定保障。直到1917年,教育部才公布《小学教员俸给规程》,对小学教师的薪资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共分三等十四级,“正教员每月最低8元,最高60元;专科正教员及专科教员最低6元,最高40元;助教员最低4元,最高22元”。[6]该《规程》还明确,教员薪水可依据工作表现酌量升级,但中央政府的这一规定在地方上却难以落实,各省通常仅作参考,而另订新规。如河北省新城县(今河北高碑店市)规定,“教员月薪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10元、乙等8元、丙等6元”。[7]而且,当时小学教员的薪资标准遵循“县立学校高于乡(村立)学校、高等小学高于国民(后改为初级)小学”的原则,乡村小学教师所领取的薪金通常位于教师群体队伍的最低层。
1933年,为了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颁布了《小学规程》,对小学校长、教职员的聘任等作了具体要求,规定小学教员的月薪应根据教师的学历和经验分等级评定,但最低不得少于所在地个人基本生活费的两倍。[8]事实上,乡村教师实际能领取到的报酬常常很难达到应有的标准。如在江苏江宁县(现为南京市江宁区),政府认定的基本生活费为每月18元,而江宁县小学校长的最高工资才36-40元,一般教师的工资为20-24元,乡村教师甚者低至12-16元,尚达不到民众基本生活费的标准。可见,大多数乡村教师的薪资几乎难以维持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计,难怪会有一些教师常常为自己低微的工作报酬而滋生抱怨:
“你看看大学教授,一月几千元的薪水,吃东西,穿大衣,多么舒服!小学呢?像本县小学教员,月薪不过十元,又还不能按月发给,常常积至三四个月,总发给一次,那么,枵腹从公,怎能不长吁短叹呢?……说到了薪金,是令人塞心的呀!每月合计起来四五元柴米面共用,一切的杂费—油盐菜—都由四五元之内开销,拉磨一天,不过所得粗饭一饱!残忍哪!”[9]
“枵腹而从公”,饿着肚子教书,完全无私和忘我的境界非一般乡村教师所能为也。尤其是在“父母啼饥子女号寒的时候”,乡村教师很难做到在学校中倾力投入,一心向学,尽其教养之责任。
(二)对高负荷工作的牢骚
民国中后期,虽然师范教育获得迅速发展,但所培养的乡村教师仍难以满足当时的需要,况且真正的乡村师范生大多不愿回乡村执教,师资培养与基层教育所需人才不匹配的矛盾尤为突出,乡村学校师资匮乏现象比较普遍。很多学校通常只有1名教师,面对几十个年龄不等的学生,开展复式教学,“上课时,教会了这班,再掉头去教那班。其余的要教他们写,教他们算,总不好给他们空坐在那里。下了课还要去当心他们啊!”[10]繁重的教学工作让很多教师面临较大的教学压力,并且乡村小学教师往往身兼多职,既要教书,又要充当校役,各种杂事零碎、繁多,“一会儿摇铃,一会儿扫地,抹黑板,倒痰盂,冲茶,看门,买物”。[11]乡村教师的工作不限于学校内,他们还是乡民的依靠,要经常担任“评判者”的角色,协调处理邻里矛盾,“待下了课拿起书回到教舍,想要认真治学或是备课之时,常有邻里为鸡毛蒜皮之事找到教员们面前,请求为自己做个公正的‘审判’”。[12]另外,乡村生活中的许多社会和文化事务,如农业、公共卫生、法律、自卫,以至村民婚丧嫁娶中的礼俗事务等,都成了他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一个教员就如同一个万全的杂货店,从黎明即开门头照应顾客,直到下午十点方才闭门。店内的记账也是他的,买卖货物也是他的……就算他有行者孙的本领,也总是忙得不了。”[13]因而,有小学教员如此自嘲,“乡村小学教师至少可以在他的名片上印上‘村公所秘书’‘村主张公道团文书’‘村十年建设计划书编订委员会委员’等头衔。”[14]当然,这些头衔都是义务性质的,“兼职不兼薪”,给乡村教师增加了额外的工作负担。
(三)对单调生活的倦乏
乡村小学处于新式教育体系的底端,政府无力投入,学校建筑一般都比较简陋,常借用地方庙宇和其他公产为校舍,教室大多破败不堪,室内光线昏暗,教学设施也难以满足正常的教学需要。乡村教师通常“从早到晚地上课,下课”,而且常常孤单一人住在校内,“自炊自食”,因而“终日所见所闻,真像嚼蜡样的无味!”山东省小学教员冯汉臣如此描述自己第一天去邻村执教的遭遇:自己背着行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即将任教的那个村庄,找到校长家里,而校长连他是否饥渴这类礼貌问题都没问,就把他领到“充作学校和教师住所的破败的关帝庙里”,“幸我来时,慈母为我包上了几个馍头,几个咸鸭蛋,由包内取出,各地捡了几片纸字,折了些树枝来,用几块砖头支起铁瓢来点火煮水,柴又不十分干的,只是冒烟,伏地去吹,熏得满眼流泪”。[15]这就是当时乡村小学教师困顿生活的真实写照。假如有多个同事在学校一起从教,可以互相支持和协助,闲暇时也可以互相慰藉,但由于乡村中大部分学校是“单级独教”(1)民国时期,学生人数少、交通不便的乡村学校一般采取“单级独教”的方式来授课:即一个教室里容纳四个年级以上的学生,由一名教师来实施教学。,缺乏交流的对象,也没有其他休闲娱乐方式,因而寂寞、单调的生活对乡村教师来说是一种常态。而每到星期假日,往往更显无聊。“独自住着一所庞大的农村校舍,一眼望去,只见课桌、墙壁、讲台、卷子、榻位等东西,找不到一个知己的朋友可以聊天……虽然有时可以到农家去走走谈谈,以解寂寞,可是白天里,农民全忙在田里。一到晚上,他们那疲乏的身体,全是很早睡了。假如向外面跑去,既无公共的娱乐场所,又无社会教育的设施。张望去,只有一片田野而已。除了关门看书,方步郊原,根本没有良好的去所。那生活是多么的单调乏味啊!”[16]
事实上,乡村教师精神的苦闷、烦躁现象确实比较严重,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感,只不过这种情绪在单级独教的乡村教师身上表现得更明显,感受也更深刻而已。应该说,造成乡村教师心理状态低迷、消沉的原因很复杂,但从很多小学教员的自我叙述来看,待遇过低、物质生活困苦以及学校生活的封闭是影响其精神状态的最直接原因。
(四)对豪绅专权的憎恨
历史上很长时间里,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领导权一直掌握在地方乡绅手中。乡绅是地方公益事业的主要承办者,他们通过资助地方教育,赢得一定名望,进而巩固家族在当地的权势。民国成立后,我国虽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政治体制,但由于政权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能力有限,乡村社会基本保持着前现代社会的自治状态,乡村豪绅仍然是乡村社会的实际领袖,他们在乡村中的权力基础仍然牢固。乡村各项公共事业的开展还必须借助于乡绅的力量才能完成,在办学方面同样如此。学校校长、学董或管理员之类几乎都由当地的“头面人物”担任或经他们首肯,学校教师的聘任、学校经费的筹集、教学设施的采购、教员薪水的发放等关键事务都要他们经手。既然乡绅在当地有如此大的社会能量,新式教育的推动和乡村学校的运行就绕不开地方乡绅,因而,有许多乡村教师想尽办法与他们联络,“作为与民众接近的线索,希望收到速效”。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与这些“办公事”的乡绅保持友好的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才能保障学校各项事务的顺利开展;只有把这些地方士绅“伺候好了”,才能在乡村立足,“保管自己的位置稳如泰山”。
民国以来,在国家权力逐渐下沉的大背景下,由乡绅主导的旧的乡村秩序逐渐解体,乡绅越来越成为一个落后保守的阶层,他们变得自私而狭隘,拒绝外来的变革。因而,有人评价民国乡绅群体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天然仇敌”。[17]一些乡村豪绅对于新式教育并无多少了解,但并不妨碍他们插手办学,控制学校,并借此来揽权、敛财,谋取个人私利。“乡村中的富户或是安分守己的人,常是对于公家的事务推诿不办,抱着‘不惹闲事’的主张,所以一些穷极的无耻汉,乘机把个什么长什么员的头衔戴在自己的头上,满心里以为管管公家事,最低限度也是弄些酒菜吃吃,省下回家啃窝窝。”[18]
由于乡绅掌控乡村学校办学的大权,教师的聘任由他们定夺,所以取悦乡绅、曲意逢迎甚至行贿就成为一些乡村教师谋求生存的第一要务。“每一学期开始,我们奔走的路线:第一步先要向村长接洽,卑躬厚待以求尤诺;其次再哀求视学——劝学所所长——发给委任。两方面能办理安当,那么你就是识别字的流氓,或卖卜相爷的消费者,也都可以坐镇一个小学。你若是奔走不力,那么你就是师范生也要被赶出场外。所以每逢一学期终了,各教员们便自恨爷娘何不给我生下四条腿和两个嘴!奔到了教员位置的人,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在村长前献殷勤乞哀怜,以求自己的地位稳固。”[19]
在一些地方,更有豪绅土劣利用自身的权力作为要挟,盛气凌人,四处招摇,通过各种方式对乡村教师进行赤裸裸的欺诈和盘剥。由于乡村教师一般都非本地人,人际关系不熟络,在当地缺乏根基,一旦遇到地方土劣为难时,他们常常用“请酒”“送礼”的方式拉近关系,久而久之,一些土劣就习惯性地敲诈,向他们“打秋风”竟成为一种乡村“流弊”。对于乡村土劣的恶行,有教员撰文进行了严厉控诉,“他们的操行和成绩,都坏到无以复加,真叫你无所措手足,再次就是我们乡村小学董事会,处处捣乱,只是添了村中土劣争权的工具,安插地痞流氓的机会,他们是乡村教育的最大阻碍”。[20]由于乡绅对乡村教师有“生杀大权”,“即使你学问渊博教法优良而对这般人应付不好,不但对你的薪金,故意长期拖欠,并且会节外生枝地加以非难”,而如果得罪了他们,“你的名片上得剥下上面的尊衔来”。[14]乡村生活的这一潜规则也使得一些不擅长阿谀奉承、不熟谙人情世故的乡村教师生存艰难,无以施展抱负,以致对教师职业心灰意冷。
(五)对自身专业发展的焦虑
生活是指人类生存过程中各项活动的总和,是对人生的一种诠释。人置身于社会中,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人除了肉身生活之外有灵魂,还有内在的精神生活。乡村教师群体内也不乏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精神性需求特别强烈,在艰苦困顿的环境中依然会压抑不住地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对他们而言,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满足自身专业发展的需求,以便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素养。曾有一位刚毕业的师范生如此描述他刚到乡村任教时的雄心壮志:“去年的夏天,朋友介绍我到乡村去当小学教员,当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啊!这正是我所向往做的事。早就讨厌五花八门的都市,愿意到乡村去,脚踏实地的观察农村破产的情形。同时我还这样的想:乡村里是静寂的,没有什么应酬和物质的诱惑!每天除教书外,其余的宝贵时间,用来研究个人所最得意的东西,有了心得,再去指导这些中国未来的小主人。”[21]还有一位乡村教师就曾详细规划专业发展的计划,准备开展校内教师的研讨活动,“关于团体方面的进修,我也时常有这种企图,什么三民主义教育研究会,我都有一番提倡计划的功夫,上年我也曾协助本村小学教师召集教员联合会,研究的结果,规定各个人出资订购书报一份或二份,互相传阅,共同研讨。”[15]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乡村教师自我提高的基本需求很难得到满足,“乡僻地方,交通不便,报纸杂志,不容易定阅;同行的研究罢,学识多数都相仿佛,切磋也不大见进益;约定日期相会,合购书籍参阅罢,离校既感不变——乡村小学的教师,每星期日离校出谈,多为办学者不许。财力也有不及——现在乡村教师的薪金,一学期不过五六十元,生活费尚不容易办理,那里来的余钱买书。”[22]
总之,尽管一些乡村教师对于专业进修和学习有较高的期待,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在交通不便的乡村,“报纸都见不到,其他的更不必谈了”,要想在职学习、进修异常困难,专业发展的渴望也难以实现。
(六)对所担社会角色的惶恐
作为乡村里稀有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民国乡村教师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依靠,他们的责任不止于担负学校教育的使命,“并不是单单教好几个小朋友,办好一个学校就算完了的”。[23]新文化运动以后,教育思潮不断革新,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对乡村教师有更高的期待,希冀他们能取代旧塾师的地位,成为乡村中的“文化导师”,“乡村教师既是乡村学校的灵魂,又是乡村社会的指导者;教育上一切的新方法,新编制,新理想,都有赖于教师去应用,去实验;乡村社会中的一切公共的活动,好事业,好制度,也都赖教师去指导,去推行……”[24]除了学校教育的责任之外,乡村教师还被赋予三种使命,“一为指导乡村方面的使命。乡村教师对于乡村本地,应行改进的事业,应肩负指导的责任,如乡村的交通、卫生、农业等等。二为乡村社会改造方面的使命。我国有些乡村的风俗制度,非从根本改造不可。如病疾祈卜鬼神、定以吉凶等迷信事件,一般无知的乡民,以为很是灵验,故不能改造,遗传成一种永久的习惯,但是乡村教师的知识较高,能力又大,当然要负这种改造的责任。三为国家方面的使命。我国现几年正在危机的时候,一个乡村教师,固然不能到战线上冲锋,但也应该努力宣传,使农民得有国家观念,为国牺牲,以谋国家强盛。”[24]
从一些乡村教师的实际描述来看,由于他们自身知识结构存在先天缺陷,平时与农村生产生活联系较少,社会实践能力不足,所以在开展社会教育时常感觉到能力胜任与角色适应的困难。比如,当民众提出“为什么蔬菜闷闷就烂了”“为什么花有香气”这一类问题时,他们常哑口无言,十分尴尬。“有的乡下人非常难弄,他们时常要来‘点’你的斤两(即试你的程度),要问你奇奇怪怪的字,要教你记账,择好日;在菩萨面前求得了诗,也得你替他们讲解(教师就在菩萨的面前);假如你不去回答他们,他们就要到东邻西村去给你宣传,说你不好。”[25]
可以看出,很多乡村教师对自身的知识与能力并无自信,他们在乡村中的实际地位与乡民的较高期待形成较大的反差,在社会参与中频频碰壁,颇感尴尬和不适,甚至滋生妄自菲薄之感。受制于自身的学识、能力和视野,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实难完成社会和时代赋予的重任,难以担当民众“文化导师”这一艰巨的使命。对他们来说,理想常遥不可及,生存是非常现实的考量,乡村教师角色不过是一份清贫、低微、不得已而为之的职业。
四、结语
民国时期全国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民风开化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各地方乡村教师的主观感受也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这一社会群体的负面情绪是普遍存在的,也必然会投射到日常教学活动和教学管理过程中,对乡村教育整体生态产生持久的影响。需要指出,虽然民国乡村教师整体生存状态并不理想,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不高,精神状态也比较低迷,但事实上他们仍可凭借自身的知识与文化资本,在乡村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奉献乡里、教化民众、维持乡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了乡村教师应有的社会价值。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从心态史视角关注民国乡村教师,剖析其内心存在的负面情绪,并非无视学界对乡村教师群体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而是旨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讨论维度,揭示以往同类研究中所忽略的乡村教师的另一面向,以期能对乡村教师群体的社会形象有更客观、全面的把握,为新时代乡村教师研究和乡村教师发展提供历史的镜鉴。[26]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乡村振兴计划,建设新农村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和迫切要求。乡村的复兴离不开乡村教育的重塑。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乡村进步的重要推动者。一支自愿扎根乡村、热爱乡村和服务乡村的教师队伍,是发展乡村教育、提升乡村文化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为了让更多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就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学校协同努力,多管齐下,尽力保障其物质生活条件,同时给予积极的人文关怀,激发其内在的成就感,增进愉悦的情绪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