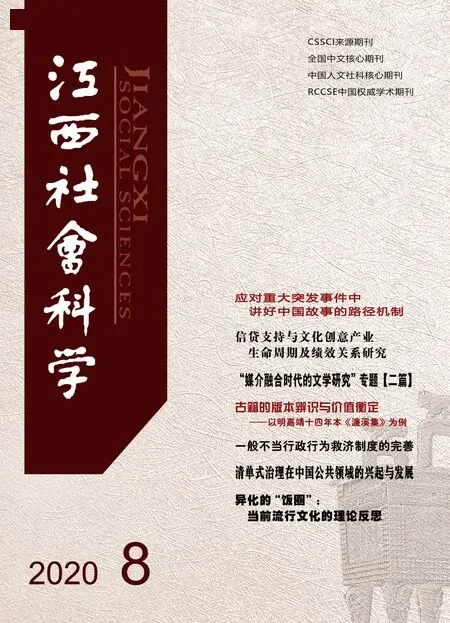媒介融合时代作家的自我呈现
■韩传喜 黄 慧
传播媒介的更迭进化,不仅会作用于具体的传播过程,而且会对行为主体的认知、行为、心理等产生影响。自我呈现作为个体形塑自我角色形象、界定自我社会地位的主动性表征行为,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因传播技术、介质等的变化而迥异于传统媒体时代。作家在媒介融合时代的自我呈现行为,从呈现介质、表征方式到呈现内容、呈现效果再到呈现动机等,都因传播环境中各要素的变迁而重塑。同时,亦存在因呈现行为的变化而生发的新问题:呈现内容的强控制性使作家的形象建构行为有陷入“完美主义自我”困境的趋势;身份焦虑、信息焦虑、利益诱惑等使作家的呈现行为显现出功利性取向。作为肩负引导大众阅读、维护文学生态等角色责任的作家,其自我呈现行为的倾向和取向与其角色作用的实现之间具有直接相关性。
自我呈现的概念,源自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戈夫曼以舞台表演为隐喻,将面对面人际交往中的互动双方类比为舞台表演中的表演者和观众,认为互动双方具有主动进行自我表露的需求和动机,“表演者想以不同方式给观众造成某种理想化印象”[1](P29),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表征手段,通过正向信息的主动传达和负向信息的有意隐藏的前后台控制,建构符合其理想标准的个人形象。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个体,社交活动是其完成社会化、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而自我呈现行为与之相伴而生,且交往主体间个人信息的主动表露和无意识流露在互动伊始便已存在,个体通过此维系与他人的互动关系,在与接收者的积极互动和获取其正向反馈间获得自尊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等。
由此看来,作家的自我呈现即是“从事文学创作有成就的人”[2](P602),在社交活动中应用多种形象建构策略,以塑造符合其认知中理想化角色形象的自主性表征行为,作家就与其个人形象、作品等相关信息予以外在展示,在个人和他者的双主体呈现中建构包括其性格特质、角色地位等在内的形象特征。作家的自我呈现行为是其参与社会交往、建构稳定互动关系的必然,在趋向于其理想化标准的形象建构中,显现自我个性、标注所属群体、界定自我社会角色地位,实现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和群体归属感的追寻。作家形象建构行为中个人和他者的双主体呈现,强调因作家社会角色的独特性而显现的个性特征,即除了作家个人之外,与其社会角色具有密切相关性的他者呈现亦是其形象塑造的重要面向。“在存在主义里,‘他者’ 的概念源于我以及与我的关系。”[3](P234)作家身份的区隔和凸显,同与其相互关联的编辑、读者、杂志社等具有直接相关性,而作家这一角色只有处于同编辑等他者的关系网络中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他者呈现成为作家形象建构行为中的外在补充和延展。作家形象建构中的他者呈现所指涉的主体是除了作家本人之外与其具有相互关系的机构或个人,前者包括杂志社、出版社、运营商、书店等,后者包括与作家相关的编辑、评论家、读者等。
从本质上说,个体的自我呈现是社交活动中互动双方就其个人形象进行的信息传播行为,传播环境因之与自我呈现行为相互作用。当传播环境因技术的革新发生变化时,个体的自我呈现行为从介质、表征到内容、动机等,俱因传播环境中各要素的变迁而重塑。戈夫曼对个体自我呈现的研究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是对处于以报纸等传统媒介占据主流的时代中面对面互动行为的探究。随着传播技术更新迭代,人类传播进入由新旧媒介相融共生的媒介融合时代,信息传播和接收的渠道、内容形式等随传播技术的革新发生转变。环境的变化作用于行为,个体的自我呈现行为在变动不居的传播环境中亦随之转变。媒介融合时代,作家的自我呈现因传播环境等的变化,显现出迥异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形象建构图景,形塑出一个繁复多样的场域。
一、面对面社交时代作家的自我呈现
传统媒体时代,因传播资源匮乏、传播渠道单一、信息表征方式受限等特点,作家的自我呈现主要在“去介质化”的社交场域中进行,即以面对面互动中的形象建构为主,借助言语、动作、表情等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表征方式,主动呈现与其个人正面形象相关的信息,包括与作家的品行、特质等相关信息的主动流露,或是与其名望、地位等社会资本关联的诸如作品的质量、个人成就等内容的呈现。比如,作家通过开展新书发布会、举办研讨会、分享会、开展签名售书活动等,在与读者的面对面、近距离交流中对其作品进行正面宣传,增加自身的社会资本。在以他者为主体的呈现中,根据主体性质的不同,既有借助报纸、杂志等媒介渠道进行的传播,又有在面对面交流中的“去介质化”呈现。前者如出版机构或编辑等个体通过报纸、杂志等刊登作家的作品信息、人物介绍等以此呈现作家的形象;后者如与作家关系密切的编辑、读者等在其社交圈中与他人面对面交往时通过语言和非语言方式呈现作家的个人形象、作品等信息。
此外,传统媒体时代,作家自我呈现的内容比重及呈现效果因呈现主体、介质等的不同而有所偏重。就呈现的内容而言,作家形象建构中的个人和他者呈现因主体社会角色的不同而存在差别。在个人呈现中,鉴于面对面社交中有关个人形象信息的强传播性,作家所呈现的更多的是与其个人形象相关的信息,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成为其个人形象的正面补充。比如作家携其新作出席读书分享会,作家个人的形象特征以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观众,作品成为作家个人形象的补充,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们,多会选择携带获奖作品出席读书分享会,畅谈自己的创作感受。而在他者呈现中,鉴于编辑、杂志社等他者的主体特性,多以作家的作品呈现为主,与作家个人形象等相关的信息附着于作品之上,比如编辑等在其社交圈中分享与作家相关的信息,作品信息是呈现的主要方面。甚至有为数不少的编辑,会将自己责编的作品,请作家签名后赠送给朋友,对作家作品进行推介。
在不同主体呈现的效果方面,作家的个人呈现是在与其个人形象和社会成就等相关信息的主动表露和有意隐藏的能动性选择间,建构趋向于其认知中理想化的角色形象,正如戈夫曼所认为的,“表演者想以不同方式给观众造成某种理想化印象”[1](P29)。但是,鉴于观众是具有独特的认知模式、个性特征和价值观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观众在接收表演者主动呈现的信息时,拥有对表演者无意识流露出的信息的观察能力和对呈现信息的认知与评判能力,再加之面对面交往的即时性,作家对其前台的控制度相对较弱,自我呈现中的不确定性较强,其角色形象建构的效果不定。比如,在作家与读者的面对面交流中,作家所倾向于呈现的个人形象与读者对作家形成的印象之间可能存在出入。并且,传统媒体时代,传播资源由专业的媒体机构所掌控,个人所拥有的传播权有限且范围较小,在作家的个人呈现中,作家所拥有的传播资源相对匮乏,其自我呈现行为多在无介质的社交场域中进行,因无介质呈现的受限性和面对面社交的亲密性、频繁性等,其呈现内容的传播范围较小,但就其影响深度和持久性而言,作家的个人呈现优于他者呈现。而在他者呈现中,编辑、杂志社等因角色分工不同而掌握更多的传播资源,可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介就与作家相关的作品和形象信息公开传播,比如在报纸或杂志上刊登作家照片、人物信息和作品信息等。同时,编辑等个体化的他者还可借助无介质的面对面社交呈现作家的形象信息,且因编辑、杂志社等他者本身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影响力,所呈现信息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更强,其对作家的个人形象和作品成就等呈现的传播和影响范围更广。但是,鉴于他者所处与作家的关系圈层的位置的不确定性,即费孝通先生所言差序格局中处于内圈和外圈的不同成员,在呈现时因关系的密切度等的差异而存在不同取向,他者对作家的形象建构所达到的积极或消极效果的不确定性较高。
二、介质化社交时代作家的自我呈现
随着人类传播因技术更新迭代进入新旧媒介融合的时代,作家的自我呈现行为因传播环境的变化而具备与之相关的新特征。融合区别于替代,媒介融合强调在传播技术冲击下,旧媒介与新媒介相融合以求共存和发展的现状,信息传播和接收的方式、表征手段等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发生转变。“融合改变了现有的技术、产业、市场、内容风格以及受众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4](P47)传播介质多样化、信息数量冗余化、表征方式多元化和个性化、传播主体去中心化和双向化等成为媒介融合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特征和趋向,且个体因技术赋权而打破传统媒体时代被动的信息接收状态,迈入享有信息传播权和选择权的阶段。从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延伸人体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时代,技术的更新促进传播媒介的发展,媒介是人的延伸,技术亦成为人的延伸,通过传播介质、表征方式等方面的作用,实现了人体感官和神经系统全方位的延伸。新旧媒介的融合为作家搭建出一幅信息传播介质丰裕、表达方式多样的自我表征图景。作家在媒介融合时代的自我呈现,借助技术革新作用于传播环境所带来的便利,通过新旧媒介等多种传播介质,以兼具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表征方式,在内外双重动力的驱使下建构符合其认知中理想化的角色形象,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实现了对其自我形象立体化、多层次且生动直观的延伸。
第一,伴随传播技术的革新、应用和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旧媒介的融合,作家自我呈现的介质由单一走向多元。传统媒体时代“去介质化”的自我呈现在传播环境的变革中逐渐从主流退居其次,媒介融合时代介质化的呈现行为成为社交活动中的主流,即“表演者-观众”模式的面对面人际交流,被“表演者-新媒介/旧媒介/融合媒介-观众”模式的线上社交所取代,后者逐渐成为行为主体用以呈现自我的主要方式。并且,作家在媒介融合时代因技术赋权而享有信息传播权和表达权,可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和方式呈现与自身相关的信息以建构自我角色形象,同时,作家的信息接收方式亦因传播环境的变迁而发生转变。凡此种种,推动作家用以自我呈现的场域和呈现介质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发生变化。
媒介融合时代,在作家的个人呈现中,除了面对面的“去介质化”社交,还可通过微信朋友圈的动态更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作品推介或语音分享、微博上的公开评论、抖音平台中的短视频呈现等介质化的线上社交平台,呈现与其个人形象和作品相关的信息。具体而言,作家可通过微信朋友圈呈现与其自我个性和作品成就相关的信息。微信朋友圈在当前俨然已成个体现实社交活动的网络化延伸,鉴于其强关系、交互性、及时性等特点,个体在其间进行的呈现行为具有延伸、强化、拓展其现实社会角色和社交关系的作用,作家通过微信朋友圈分享作品链接、发表个人感悟、传播最新的创作等进行自我呈现,这不仅会因微信朋友圈的裂变式传播等特征而扩大作家呈现内容的影响范围,而且鉴于介质化传播的强可控性等特点而使作家形象建构的倾向在朋友圈中更易达成,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难以实现的。作家个人或作家群体也可联合创设、运营相关的微信公众号,传播作家的作品、人物采访、线下或线上活动、作家创作谈等信息,于作家而言是扩大其个人和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亦是其自我呈现行为在网络空间中的另类延伸。作家还可通过微博平台传播个人就某事的公开评论或分享作品的链接等,用以呈现与自我个性、作品信息相关的内容,以此完善、丰富自我的角色形象。此外,短视频在当前已成为个体传播与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不仅成为大众获取娱乐信息的渠道,而且成为政府、高校、杂志社等主体用以宣传、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亦成为作家、编辑、教师等主体用以建构自我形象的场域之一。作家作为以作品传播为目的并肩负特有角色责任的主体,需重视并顺应传播趋势和大众“网络集聚地”的迁移规律,借助短视频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以形塑自身角色形象,并且,鉴于短视频传播所具有的直观性、生动性、亲切性等特点,不仅有助于作家作品和思想的传播,而且有助于在泛娱乐化的社会环境中注入严肃文化的元素,扩大文学等严肃性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唤起大众对严肃性文化的需求,发挥其引导大众阅读、形塑文学氛围、弘扬优秀文化等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传播与个人和作品相关的信息的作家数量并不多。或许是因为对新兴信息传播方式的陌生感、投入成本、个人对新媒介的态度和评价、价值观等方面的原因,大部分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通过新媒介方式进行自我呈现存在不少障碍。
在他者呈现中,鉴于信息传播介质的增多,编辑、杂志社等传播与作家有关的信息的渠道亦随之扩大。编辑、读者等个体可通过同作家个人呈现时相似的传播介质,呈现与作家作品和个人形象等相关的信息,诸如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抖音等平台。杂志社、出版社等机构除了报纸、杂志等传统的纸质传播介质外,在媒介融合时代还可通过开设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抖音账号等入驻新媒介传播渠道,通过新的传播介质将作家的作品、作家的创作思想加以呈现。杂志社、出版社等他者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或节选推送作家的作品、创作谈等,或者推送评论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等内容,比如《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节选、评论文章《吴平安:浏漓顿挫,豪荡感激——莫言七古〈鲸海红叶歌〉赏析》、创作谈《邓刚:我的脑海里经常波涛起伏》等,《小说月报》微信公众号推送的《2019年精品赏读:房伟〈小陶然〉》、创作谈《南翔:在历史与现实坐标中的“曹铁匠”》、创作谈《吴君:世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等;还可通过微博平台以评论、节选内容等方式传播与作家个人形象、作品等相关的信息,比如人民出版社的微博账号中发布的系列“荐书”文章、对作家的评价性文章等。此外,还可借助短视频平台发布作家本人对作品的推荐视频或他人推荐作家作品的视频,或通过视频直播由作家本人或他者推荐作品,或举行作家创作谈、读书心得等线上直播活动,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抖音账号直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洱携其作品《应物兄》谈“如何读书”、发布王志推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怎么办?》的短视频等,readwriter抖音账号发起的“作家悦享会”系列活动,作家周晓枫向用户推荐其散文代表作《巨鲸歌唱》、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王春林向用户分享作家阎连科的长篇散文《她们》等。
第二,作家自我呈现的表征方式,亦从传统媒体时代以语言和非语言手段为主的单一化表征,演变成借用多种辅助性表达方式,如表情包、图片、短视频、语音、网页链接等多样化表征方式。在作家的个人呈现中,可在介质化的社交中应用的多种表征方式,成为其形象建构的有益补充,作家在此期间所呈现出的是更全面、更具说服力且控制性更强的个人形象。比如作家在微信朋友圈中分享其已出版作品的链接或推荐文章,作家老藤就多次转发了《战国红》《刀兵过》等自己小说的链接和相关评论文章,作家乔叶亦多次转发了小说《藏珠记》《她》等的链接和相关评论;作家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介与他者开展社交活动时借助表情包、图片等方式丰富自我呈现的维度;作家本人通过短视频平台介绍个人作品或通过杂志社、出版社等短视频平台推荐个人作品、发表创作谈、读书经验等。作家在媒介融合时代自我呈现的表征方式更加丰富多元,所建构的角色形象的传播和影响范围更广。在他者呈现中,除文字、语言等传统的表征方式外,编辑、杂志社等可通过在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介渠道上发布作家的采访视频、刊登作家的照片、作家作品的网页链接、作家阅读作品的语音等新型表征方式,建构更为生动立体、具有亲切感和人情味的作家形象。比如《人民文学》杂志社微信公众号的有声/朗诵栏目发布作家本人朗诵其作品的音频:作家夏笳朗读其作品《爱的二重奏》、作家王松朗读其作品《烟火》节选等;《文艺报》的微信公众号“文艺报1949”的微播报栏目,作家铁凝朗读其作品《阅读的重量》、作家莫言朗读新作《一生恋爱——献给马丁·瓦尔泽先生》并配有其朗读的视频、作家李敬泽朗读《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忆雷达先生》等。杂志社、出版社等他者在呈现作家作品、形象时多样化表征方式的应用,尤其是作家的照片、采访视频、作家朗读个人作品的视频或音频等,不仅使作家的个人形象更加具象化,而且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这些方式于读者而言是对作家及其作品产生共鸣和情感共振的重要方式。
第三,因传播环境、呈现介质和表征方式在媒介融合时代的转变和发展,作家自我呈现的内容可控性和效果亦随之变化。媒介融合时代,作家的个人呈现因介质化社交互动成为主流且所拥有的传播权和表达权的扩大等,而对所呈现内容的控制性增强,倾向于作家认知中理想化的形象建构成为可能。作家在媒介融合时代用以自我呈现的渠道主要以多元的线上社交即介质化的个人呈现为主,而介质化的特点之一是互动双方社交行为的不在场性和去场景化,有学者将其称为“语境坍塌”[5],因其去除了面对面交流的即时性,作家在呈现前可对相关信息反复调整、修改以使其更符合其认知中理想化形象的标准,其形象建构中的前台控制性强化,且前台所呈现的信息以积极正面为主。并且,因互动行为中在场性和即时性的去除,使得观众观察和捕捉其无意识流露的信息的可能性被剥夺,与作家的性格、特质等有关的负面信息被其严格控制在后台。前后台的强控制性和接收者因介质化社交的受限性,使作家所呈现出的自我形象更符合其认知中更为理想化的角色形象,并且某种程度上而言,接收者对作家形成的认知受其主动表露的内容的影响,以此修正、维持或颠覆作家既有的角色印象。而他者呈现中,鉴于传播环境的变化,作家的社交圈在媒介融合时代不断扩大,与其相关的编辑、读者、杂志社、出版社等个人或机构所呈现的与作家相关的内容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强,作家对他者呈现的内容性质的控制度较弱,正面和负面形象的建构因他者的身份、与作家关系的紧密度等而不固定。此外,他者呈现中对作家作品等信息的呈现,经常是同时呈现多位作家的作品或呈现一位作家作品的一篇或几篇内容,对于作家而言,他者呈现虽会因主体特性、呈现介质、表征方式的扩大和多元化而提升传播与影响范围,进而成为作家提升个人角色形象地位的有益补充,但是呈现的低频率和低专注度又增加了作家借助他者呈现的成本和壁垒,某种程度上而言降低了其呈现行为的有效性。
在呈现的效果方面,作家在媒介融合时代自我呈现的传播和影响范围扩大,但实际所获效果却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因传播环境、呈现介质、表征方式等在媒介融合时代的变革,不论是作家的个人呈现还是他者呈现,其信息传播和影响的范围进一步拓宽;但另一方面,作家自我呈现的效果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又因接收者、情境等多方因素而充满不确定性,作家倾向于建构的理想形象与实际在接收者心中形成的形象间存在产生偏差的可能性,他者呈现的效果因呈现内容的占比、频率、范围、与作家的关系密切程度等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在作家的个人呈现中,作家虽可通过频繁、多样且随时随地的线上社交,在强效的前后台控制中建构趋向理想化的角色形象,但对于互动行为中的另一参与者——观众而言,作家所呈现的有关其品质、成就等方面的信息的有效性,还受制于观众对其呈现行为的认知、评价和印象形成,以及作家现实的社会角色形象的束缚。亚里士多德所提“修辞术”的概念中强调对观众/听众的重视,认为对演讲中的信息接收者的分析是演讲取得成功的重要环节。戈夫曼在“拟剧理论”中亦强调互动行为中观众反应的重要性,认为观众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其在接收表演者有意传达的形象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捕捉表演者无意识流露的信息作为对其形象认知的补充。作家在媒介融合时代自我呈现的前台控制性、呈现信息的传播和影响范围、形象建构的直观性和立体性等方面得到强化,并不等于作家的形象建构行为在观众方会获得与之期待相一致的效果,对作家自我呈现行为的接收者而言,对作家形成的印象与作家期待的理想形象之间是否一致,不仅取决于作家“给予的表达”,还取决于作家“流露的表达”、接收者个人的价值观、个性和喜恶等。并且,接收者在与作家交往中形成的交往经验以及由此建构的认知图式,亦是影响其呈现效果的重要因素。社会认知图式理论强调既往经验和认知的重要性,图式是“某种认知结构,它体现了由某一概念或某类刺激所构成的认识,这类认识可以来自其自身的构成要素,也可以来自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6](P91)。接收者在交往经验及认知图式的影响下对作家的呈现行为予以评价后形成某种印象或修改既有的印象认知,突出作家在网络空间中的呈现行为亦受制于其现实的社会角色。“如果没有现实的人,就没有镜中的像。”[7](P165)作家在现实中的角色形象是其在网络中形象建构的基础。
在作家形象建构的他者呈现中,拥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的编辑、杂志社、出版社等个人和机构,在所呈现信息的权威性、范围和影响力等方面更具优势,因而所建构出的作家形象的说服性和可信性更强,并且从社交圈子的角度来看,借助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他者呈现具有裂变式扩大作家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作用。但是,鉴于他者呈现时的内容选择性及单个作家作品呈现的低频率,作家通过他者呈现建构角色形象的难度和成本较大,并且,在他者呈现所达到的实际效果方面,不仅受制于观众个人的因素,而且因他者的身份、与作家的关系密切度、呈现的情境、他者数量在新的传播环境中的剧增等而蕴藏不确定性。
三、作家自我呈现行为驱动力的变迁
行为的发生存在特有的机制,不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媒介融合时代,作家的自我呈现行为,表面上看是为了表达自我、建构理想化的角色形象,但究其本质,却是受制于内在心理或外在环境压力的自我实现行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而每当一种需要得以满足,另一种需要便会取而代之……这些需要或价值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需要具有一定的级进结构,在强势和优势方面有一定顺序”[8](P1-4)。马斯洛强调的是行为主体需求满足的递进性,亦是对需求实现后满足感逐渐降低的另一种阐释。以此来看,作家在不同的传播环境中的自我呈现,是其对占据不同地位的需求的满足行为。传统媒体时代,因个体对外在环境感知的有限性,作家自我呈现的动机主要在于其内在心理,建构与维持良好的社交互动关系并在社交中占据有利位置是驱使其进行自我呈现的主要动机。作家在与个人形象和作品等信息的主动表露中,展现自身的社会角色地位和所属群体,以获取他人认同、赞赏和关注,满足其对自尊感、归属感、成就感等的追求。
而媒介融合时代,作家自我呈现的动机因信息传播和接收环境的变化,演化成外在环境与内在心理双向驱动的行为。媒介融合时代,拥有传播权和表达权的个体通过网络、移动终端等开展社会交往活动成为主流,在传播介质和表征方式的更新与递增间,个体竞相通过线上社交呈现与其理想化形象相关的信息,以此顺应新的传播环境中形象建构的趋势和潮流。媒介融合时代,介质化的线上社交中的自我呈现成为个体形象建构行之有效的方式,传统的自我呈现方式已不适合当前的社会环境和社交情境,比如一些作家尤其是网络作家,通过网络、自媒体等介质进行自我呈现,以符合接收者喜好和期待的呈现介质和内容表征方式提升了个人知名度和影响力,而囿于传统的自我呈现方式的作家群体中,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却不乏被“技术红利”所埋没之人。基于现实效果和从众心理,作家身处其中受之影响,在外在环境的变动中通过线上社交进行自我呈现。另外,作家在媒介融合时代被海量信息席卷,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焦虑和身份焦虑。媒介融合时代,个体接收的信息数量以几何式剧增,其日常所能接触和了解的社会生活的范围边界无限扩大,个体用以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系在海量信息的接收中亦被扩大化,个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因之而更难达成,极易形成阿兰·德波顿所言的“身份焦虑”,而通过趋向于理想化的形象建构以提升自身社会角色地位和受欢迎度是缓解焦虑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理的双重驱使下,作家在媒介融合时代不断通过新的传播介质和表征方式进行自我呈现,建构更为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来缓解身份焦虑,实现自我满足和社会认同。
但是,事物的发展具有两面性。媒介融合时代,作家的自我呈现因传播环境的变化,在形象建构的传播和影响范围、即时性和持久性以及前台控制性等方面得以强化,作家在理想化的形象建构中缓解其身份焦虑和信息焦虑,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其自我价值的确认及对自我满足感、心理幸福感和身份认同感的追寻。但另一方面,对前台控制的强化虽能避免因表演失误带来的形象崩溃,并在理想化的角色形象建构中实现自我满足,却在逐渐强化的控制中有陷入“完美主义自我”困境的趋势。而作为对自我认知具有重要作用的他人评价,一旦因接收的内容过于“完美”甚至失真,会使其评价失效以至于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偏差。并且,媒介融合时代,作家在海量信息接收中面临的利益诱惑增多,其自我呈现的功利性倾向在身份焦虑的压力下成为亟须关注的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指在作家形象建构中的主观和客观、功利心和虔诚心之间的矛盾。前者指的是作家在自我呈现时,对所呈现内容性质的控制与衡量,所指向的是其自我呈现时所达到的前台控制度;后者强调作家自我呈现的趋利性与保持对文学的虔诚心之间的矛盾,比如,作家在媒介融合时代为了增加自我的社会资本、缓解身份焦虑,借助信息获取的便捷性进行虚假呈现甚至出现学术不端行为,便是功利心胜于虔诚心的具体体现。
四、结语
总的来说,作家在媒介融合时代的自我呈现,需要其在借助传播环境变化带来的便利扩大自我呈现范围、强化前台控制力度以缓解焦虑、满足自我需求的同时,一方面要重视“受众”分析,作家呈现的角色形象归根结底需在接收者的立场进行评估和再传播;另一方面要重视形象建构过程中主观和客观、功利性和虔诚心之间的矛盾,在繁杂的信息场中摆正心态以实现有效且积极的形象建构。尤其要注意的是,因作家社会角色的独特性,其在媒介融合时代自我呈现的内容应首要考虑其文学性和社会效应,将对文学的虔诚心而非功利心作为呈现准则。并且,鉴于作家形象建构中他者呈现的重要性,在以他者为主体的呈现中尤其要保持呈现内容和立场的客观性,特别是与作家作品相关的信息传播。作品质量是衡量呈现比重的重要标准,他者呈现中应主要以高质量作品为主,且在呈现存在不足之处的作品的同时传达对作品的客观评价,如此才能发挥其引导大众阅读、建构良好文学生态规范的作用,进而使文学的传播环境走向良性的发展轨道,促进文学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