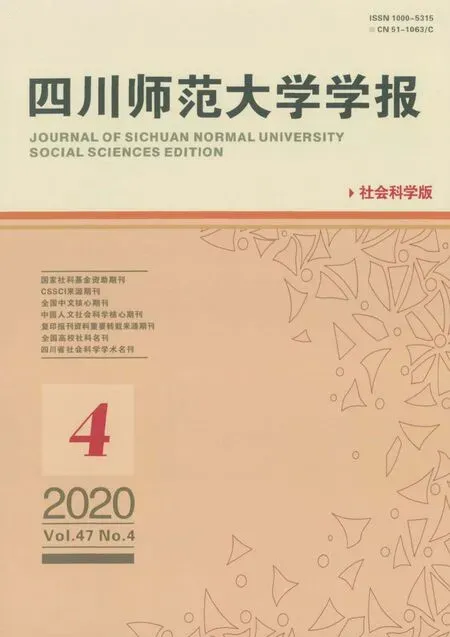论后习俗社会视域下哈贝马斯共同体思想中的相互性问题
李长成,陈志新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随着西方习俗社会向后习俗社会转型,社会合理化进程使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祛魅化”和“解神秘化”,即“能够创造意义的形而上学-宗教世界观的同一性已经土崩瓦解了”(1)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自我逐渐从以等级制为核心的传统目的论和有神论的囚禁中解放出来,成为游荡在无意义世界的居住者,不再受先定的目的论价值秩序的限制。由此,如何处理自我之间的相互性关系、构建新型共同体成为众多思想家关注的重大课题。国内学者冯周卓等结合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层结构的分析,探讨了如何重构社会共同体的合理化(2)冯周卓、王益珑《哈贝马斯对社会共同体的二维架构分析》,《河北学刊》2015年第5期,第12-18页。;严宏考察了哈贝马斯从交往共同体到法律共同体的演变过程(3)严宏《从交往共同体到法律共同体——哈贝马斯对现代西方国家的演进式重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56-62页。;在此基础上,杨礼银进一步从横向结构分析了哈贝马斯的交往共同体、语言共同体和法律共同体及其相关关系(4)杨礼银《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中共同体的三个基本层面》,《哲学研究》2019年第10期,第116-123页。。本文则立足于西方习俗社会向后习俗社会转型,着重从政治哲学视角来探讨哈贝马斯共同体内部的相互性问题。
一 公道意义上的相互性
如何看待西方后习俗社会的根本特征?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道德价值领域的合理多元性上,人们无法就好生活问题达成理性共识,即“世界观的解中心化”。上述主张,一方面,明显受到马克斯·韦伯“理性多神论”的影响,即各种竞争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得到合乎理性的解决,价值领域缺乏任何传统意义上具有共同约束力的不可置疑的至善标准。在此意义上,它们类似于罗尔斯所说现代社会的“理性多元论”,即使正直的个人具有充分的理性能力,我们也不能期待经过自由讨论后总能达成一致的判断(5)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另一方面,这与哈贝马斯提倡的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有关。在他看来,后形而上学思维足够简单,它否定了以外在于我们的语言、实践和生活形式的“上帝之眼”来看待问题的基础主义思维、绝对主义思维等。因此,哲学应主动放弃传统的“第一科学和百科全书”的抱负,放弃其掌握真理和理论的“神圣意义的特权”,不再拥有一种关于“好生活的肯定理论”,接受经验科学的“易错论式自我理解和程序合理性”(6)上述引文参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7、49、36-37页。。
在哈贝马斯看来,为了确保社会成员在世界观多元性的后习俗社会平等共存,需要伦理上保持中立的正义观,坚持道义论意义上的正义观,即正当(权利)对善的首要性和优先性。就此而言,他无疑深受康德道义论正义观的影响。这种优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直接的道德意义上看,正义是“所有社会美德中的最高美德”,其要求超过其他任何的道德利益和政治利益,无论它们多么重要和迫切。在此意义上,“道义论反对效果论”。其二,从基础的道德意义来看,正义原则是“独立推导出来的”,不依赖于任何特殊善观念的支撑。在此意义上,“道义论反对目的论”,即“不以任何终极人类意图或目的为先决前提,也不以任何决定性的人类善观念为先决前提”(7)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与康德道义论意义上的正义论不同,在哈贝马斯看来,首先,正义不能置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顾而单独处理个体的价值和尊严问题。在后习俗社会视域下,自我摆脱目的论框架获得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独立个体,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私人劳动和他人的中介合法地追求其特殊私人利益,即“以等利害交换的方式满足人们的自我利益”(8)慈继伟《正义的两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引言第2页。,但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不必然导致他人利益得到合理实现。因此,大家只有共同遵守正义规范的相互性承诺,每个个体或全体的正当利益才能得到保障。这种相互性承诺旨在确保个体或群体间的相互得利(9)李长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正义批判思想探论》,《伦理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7-23页。。就此而言,哈贝马斯无疑反对康德而认可休谟等人的观点,认为正义的必要性在于解决个体或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其次,他改变了正义规范论证的前提。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下,正义规范的论证既不能求助于传统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也无法诉诸经验主义的心理学基础,同样不能指望康德提供的独白式的普遍实践理性主体自身。在吸收语言哲学转向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认为正义规范的论证扎根于以沟通理解为目的的话语论证实践中。这一论证建立在寻找更有说服力论据的合作沟通上,没有欺骗和强制,也没有必然实现的保证,只能依靠共同的努力并通过不断试错才能实现。“论证实践当中建立起了一种合作竞争机制,共同寻求更好的论据,在此过程中,参与者追求的目标始终是沟通”(10)于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这表明哈贝马斯在吸收米德、阿佩尔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既力求脱离康德正义观的唯我论前提,又避免陷于道德情感主义和道德怀疑主义之网,他赞同科尔伯格等人倡导的道德认知主义,认为道德判断可以基于道德的理由得到理性论证,同样存在真假问题。
那么,后习俗社会视域下,正义如何化解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冲突,实现相互得利并确保共同利益的实现呢?首先,哈贝马斯明确反对图根哈特的处理方式。尽管图根哈特不反对通过采取形式普遍化的原则来处理利益冲突,认为只有对每个相关者同样有利的规范才能得到证明,但他认为规范有效性只具有意志意义,而不具有道德认知的意义,不能被视为类似于真理命题的有效性要求。论证的需要不是使道德认识成为可能,而是确保参与各方能形成公平的意志妥协。在此意义上,“论证的设计不是使公道(impartiality)的判断成为可能,而是使自由地免于影响或意志形成过程中的自主成为可能”(11)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71.。因此,论证不仅需要相关各方的参与,而且需要力量(power)的平等和平衡。哈贝马斯指出:“即使理性利己主义者之间能达成公平的利益妥协,但这种理性是策略意义上的目的合理性。”(12)Jürgen Habermas, Truth and Justification, trans and ed. Barbara Fultner(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241.理性利己主义者可能会出于功利性算计或外在强制力的目的遵守规范,但缺乏恒定的道德性动机。此种工具意义上的相互性不能被称为真正公道意义上的相互性。
其次,哈贝马斯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与善观念相分离的客观意义上的物质利益。利益离不开人们立足于“第一人称的多元视角”对其展开的诠释和评价。“现实生活中客观的共同利益往往只是体现了部分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具有得到普遍认可的有效性”(13)Jürgen Habermas, Truth and Justification:268-269.。因此,在后习俗社会的视域下,善观念冲突与利益冲突往往交织在一起,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为此,哈贝马斯主张通过商谈论争的程序来确保真正公道意义上的相互性得以实现。“真正的公道仅仅适合这种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一个人可普遍化的那些规范能得到普遍同意,其原因在于它们体现了所有相关者的共同利益。这样,判断的公道性表现在下述原则里:约束所有相关者以一种利益平衡的方式采取所有他者的视角”。为了保证判断过程中的公道性,商谈伦理学设立了可普遍化的程序规范U来检验各种利益诉求的有效性,确保共同利益的实现,即“一切期望满足每个人利益的规范,所有相关者能够接受普遍遵守它所带来的结果和附带效果”。这一原则来自于商谈伦理学中已经蕴含的话语论证D规则,即“那些满足有能力参与实践商谈的所有相关者赞同的规范才是有效的”(14)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65,66.。
在哈贝马斯看来,后习俗社会视域下的正义概念只能是公道意义上的。利益冲突问题既不能通过孤独主体的独白式运作来解决,不能将其缩减为主体间力量的妥协,也无法获得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公道意义上的相互性旨在通过可普遍化的程序使参与者在道德意义上克服自我中心视角,相互采取参与者视角和所有他者的视角。不过,哈贝马斯并不赞同亚当·斯密等人提出的“公正旁观者”或“公正观察者”的视角(即第三人称视角),因为“理想的中立观察者是作为孤立的主体来运作的,并根据其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来收集和评价其信息”。(15)Jürgen Habermas,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 on Discourse Ethics(Cambridge:the MIT Press, 2001),48-49.“公正旁观者”享受的特许地位使其以独白的方式与其他参与者孤立开,而不能以真正参与者的身份进入主体间共享的道德世界。
与之相反,公道判断的形成需要考虑所有参与者自身的观点。参与者在参与的互动过程中对称性地和相互地采取每个他者的视角(即包容性的我们视角),平等考虑所有他者的利益,而不能脱离这一过程单独采取“公正旁观者”的视角。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后习俗社会视域下利益冲突的解决唯有通过公道意义上的相互性来实现。这种相互性需要从公道程序的意义上去理解。但这种相互性能否确保共同体成员间的平等对待呢?
二 承认意义上的相互性
与休谟等人立足于正义的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是指物资资源的匮乏,主观条件是指利他主义精神的不足)来探讨利益冲突的解决方式不同,哈贝马斯不仅主张脱离主体哲学的唯我论前提,通过公道程序意义上的正义来破解利益冲突问题,而且认为正义需要强调每个个体人格的不可侵犯性,解决平等尊重每个个体的人格尊严问题,即相互承认对方平等享有的自主权利。一方面,哈贝马斯明显吸收了康德关于自主、尊严、目的王国等思想。在康德那里,这些主张通过权利优先于善的安排得以实现。以保障个体自主权利为核心的正义法则摆脱了利益的纠缠,但它不是消极意义上的禁令,而是积极意义上的自我(即理性意义上的本质自我)自由立法。理性这样做不以任何人类的终极目的或决定性的世俗善观念为前提,而是出自于理性存在者“尊严的理念”,即理性存在者超越一切相对的价值(即价格)之上,具有“无条件的、无与伦比的价值”,即内在的价值。尊严的根据则来自理性存在者意志的“自律”或“自主”。进一步来看,自由概念则是解释意志自律的“钥匙”。“这种理性必须把自己看做它的原则的创制者,独立于外来的影响,因此它作为实践理性或者作为某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必须被它自己看做是自由的”(16)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2-73、92页。。
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在拒绝康德独白式的唯我论前提以及现象自我与本质自我等一系列二分法的基础上,主要吸收了黑格尔早期关于主体间性的相互承认的思想来重新阐释康德的自主等思想。在《劳动与相互作用》一文中,哈贝马斯卓有成效地探讨了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认为黑格尔放弃了康德的自满自足的主体哲学前提,提出了“表述的辩证法、劳动的辩证法以及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的辩证法”(17)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如果说黑格尔早期关于劳动与相互作用的辩证联系的思想体现了作为主体间性的精神模式优先于作为自我反思、唯心主义独白式的模式,那么成熟时期的黑格尔则颠倒了这种优先性,绝对唯心主义的自我反思的、独白式的主体性占据了主导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对黑格尔早期相互承认思想的研究比霍耐特更早,不过,二者都“一样从黑格尔的承认概念中至少看到了相互性和和解的可能”(18)Robert R. Williams, Hegel’s Ethics of Recogni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13.。
可见,哈贝马斯围绕承认意义上的相互性展开的思考首先表明了权利优先于善的道义论追求,旨在实现平等对待、相互承认的道德共同体理想。这种追求,一方面,有利于在世界观多元化的后习俗社会视域下,确立伦理上保持中立的正义概念,从而调节主体间的平等共存。因为传统的未经反思的伦理信念无法具有约束性的力量,不再能指导人们如何去过更好的生活,故“它尽力打破和超出特殊共同体实质性伦理的界限,提供一种形式的和普遍的道德理论,这样做时,它从好生活的伦理领域推出,将自己限定在正义议题范围内,这些道德问题的解答可以建立在好的理由的基础上”(19)Jobanna Meehan ed., Feminists Read Habermas: Gendering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New York: Routledge, 1995),206.。另一方面,权利本身不是实现其他善的工具性手段,而应视为目的。正义和权利具有压倒一切的首要性、绝对优先性和不可侵犯性。利益冲突解决的公道程序后面表达了实质性的道德信念:每个人都应平等尊重彼此的人格尊严。由于个体化只有通过社会化来完成,这种平等对待的道德理想同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关系网络相互交织。“个体的平等权利和对个体人格尊严的平等尊重依赖于个体间的关系网络和相互承认的系统”(20)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202-203.。这种关系在话语论证中已经作为规范性前提被预设。
但这并不意味着正义完全排除善的问题。正义当中的善不是伦理意义上的,而是道德意义上的。“正义当中的善提醒我们,道德意识受制于道德个体的自我理解:道德个体知道自己属于道德共同体”(21)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第31页。。这个普遍主义共同体完全摆脱了排他性共同体的伦理限制,是不断将陌生的他者当作我们中间一员的包容性共同体。它既强调个体间相互承认对方作为人格的平等价值,又重视个体间绝对差异的相互承认。“对差异十分敏感的普遍主义要求每个人相互之间都平等尊重,这种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容,而且是对他者的他性的包容,在包容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22)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第43页。。在此意义上,相互承认的社会结构包括三个方面:特殊性、个体性与普遍性。独立个体间普遍主义的平等承认关系将个体间的差异囊括在内,体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统一。不过,在霍耐特、吉利根等人看来,这种所谓的他者仍旧是一种脱离了伦理语境的一般化的他者,而不是真正具体的他者。因此,这种相互承认只体现了对称性的相互性。
其次,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这种正义论思考是实质意义上的,但与罗尔斯《正义论》中的看法存在根本区分。平等待人、相互承认的规范理想并非是从哈贝马斯提出的公道程序中推出的,而是话语论证得以顺利进行的规范前提预设或理想化话语论证的前提条件预设。一方面,从话语论证本身来看,这种前提不能仅仅理解为纯逻辑以及纯程序意义上的,它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以对称性的相互承认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的存在。“因此,逻辑运用的条件以社会伦理的条件为前提”(23)龚群《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4页。,否则,论证会陷于施为性矛盾而无法进行。就此而言,罗尔斯认为哈贝马斯关于合理商谈先决条件的哲学分析在“宽泛的黑格尔意义上乃是逻辑的一种”的说法无疑是有问题的。(24)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405页。另一方面,这种前提是近代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道德普遍主义是历史的结果。由于卢梭和康德的推动,它产生于有着相应特征的特定社会中。经过漫长的可以看得见的斗争,两三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见证这一社会基本权利实现的直接趋势”(25)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208.。
哈贝马斯充分肯定了西方启蒙文化的划时代贡献,即高扬理性,通过保障个体权利,实现个体间的平等。这一现代性的政治理想不应在后现代理论等批判抽象普遍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浪潮中遭到废弃,它追求的是实现人格平等和尊严的理想。其立论的主体中心前提需要变革并不代表理想本身不可取。从主体间性出发,相互承认彼此的自主权利和人格尊严,相互包容对方,不断扩大我们的视域,并将这一追求与特定的文化传统相脱钩,是哈贝马斯共同体思想所体现出来的实质内容。
从正义原则本身来看,罗尔斯从保证判断公道的“无知之幕”出发,最终却推导出实质性的两条正义原则,力图在不危及自由的前提下解决社会生活中实质不平等的问题。从正义论的前提来看,尽管罗尔斯强调了两条正义原则的安排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但他同康德一样设定了关于本质自我这一形而上学前提,无法有效回应后习俗社会视域下多元世界观的挑战,也缺乏主体间性的维度,无法解决现实中主体间正义共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从对权利的理解来看,哈贝马斯认为罗尔斯将权利等同于用来分配的善,且当作事物一样来加以占有。这种权利主要指的是自由主义主体私有权利,而不是政治参与和政治交往的积极自由权利。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被人为割裂开。
最后,从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逻辑来看,哈贝马斯在吸收科尔伯格、塞尔曼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不管是公道意义上的相互性,还是承认意义上的相互性都是道德判断能力发展到后习俗水平阶段的产物。科尔伯格从道德认知主义角度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六阶段。其中,水平A(前传统水平)包括第一阶段即“惩罚与服从阶段”,采取的是“自我中心主义视角”;第二阶段即“个体的工具性目的和交换阶段”,采取的是“具体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的视角”;水平B(习俗水平)包括第三阶段即“相互个人间的期望、关系和一致阶段”,此阶段采取的是“同他人相联系的个人视角”;第四阶段即“社会制度和良心维持阶段”采取的是“从主体间的协议或动机区分社会的视角”;水平C(后传统和原则化水平)包括第五阶段即“权利优先和社会契约或功利阶段”,此阶段采取的是“优先于社会视角”;第六阶段即“普遍伦理原则阶段”,核心是普遍正义原则,具体体现为“人类权利的平等和尊重人类个体的尊严”,也就是彼此视对方为目的而不是手段,采取的是“道德视角”(26)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123-125,128-129.。
但由于科尔伯格局限于经验分析,他强调更多的是主体内部能动的学习过程,而缺乏相应社会条件的分析。塞尔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阶段论:水平1,采取“分化的和主体的视角”(5-9岁);水平2,采取“自我反思/第二人称和相互(reciprocal)视角”(7-12岁),在这种相互视角中,自我与他人仍只是作为单独性个体发生关系;水平3,采取“第三人称或一般化他者和相互(mutual)视角”,在这种相互视角中,行为者除了采取参与者视野外,还采取旁观者视野以客观中立性态度审视发生的事情,双方认识到要相互协调各自的视野(27)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142-144.。这一视野的出现才是科尔伯格道德判断能力发展中从习俗水平发展到后习俗水平的关键。
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认为前传统阶段的相互性(reciprocity)包括“权威主导的互补性(非对称性)和利益主导的对称性”。这两种相互性只是代表了“正义的自然胚胎形式”(28)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163、165.。此阶段体现了在行动过程中作为参与者与他人发生关系。习俗阶段中社会世界仍然深嵌确定性的生活世界中,道德与伦理没有截然分开,自主的道德无法形成。正义议题在已经得到回答的好生活的问题框架中被提出。这个框架或得到更大的救世神学或宇宙论整体的支撑。从视角类型来看,这个阶段观察者视角与以往阶段的参与视角相结合。后习俗社会阶段,随着世界观的解中心化,社会世界开始成为问题,为化解利益冲突和解决平等对待问题,此阶段出现了公道意义上的相互性和承认意义上的相互性。从这些理想化形式的根本相互性中可以去探明此阶段的正义设想。
不管是公道意义上的相互性,还是承认意义上的相互性,仅仅依赖行动者的理性认知能力来破解利益冲突和平等尊重的问题是否能确保哈贝马斯的共同体设想取得成功呢?
三 关心意义上的相互性
在后习俗社会视域下,“主体越是个体化,他越是置身于一个密集交织的相互承认网络中。也就是说,他们相互暴露,亦相互具有脆弱性。除非主体通过语言外化自己,参与主体间的关系中,否则将无法形成其个体身份的内核”,比物质利益的分配更重要的是,承认“人是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并在道德上需要关切”这一基本事实。(29)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199.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远远重于人的利益需要,优先于对生命的粗鲁威胁。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别人视为潜在的利益争夺者,更重要的是视他人为脆弱易受伤害,因而需要相互关心的社会化个体。可见,确保共同体实现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公道的程序和平等的对待,而是社会化个体间的关心或同情。“这种关心有两方面作用:维护个体的完整性;保护相互承认的生命纽带之网。通过这一纽带,个体可以相互稳定其脆弱的身份”(30)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200.。使共同体成为必要的不再是利益问题和承认问题,而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身份认同的脆弱性。为此,“他一再提及‘同情(sympathy)和恻隐(compassion)的道德哲学’”(31)慈继伟《正义的两面》,第87页。。
在哈贝马斯看来,共同体除了解决利益冲突和相互承认任务外,还需要解决社会团结问题。“既然道德适合于解决社会化个体身份的脆弱性,它们总是必须同时解决两个任务。它们必须通过设定平等尊重每个个体的尊严而强调个体的不可侵犯性,但是它们必须同时保护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关系之网,从而使社会成员能作为共同体成员生存下来”(32)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200.。与前一个任务相对应的是“正义原则”,它提倡的是平等对待;与后一个任务相对应的是“团结原则”(即相互关心或同情原则),它倡导的是对邻舍福利的关心或同情。正义同时意味着团结,两者作为共同体的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正义则包括程序意义上的公道原则和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原则。确保这两种原则实现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把其他人当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33)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第31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关心意义上的相互性是公道意义上和承认意义上的相互性得以实现的前提。
公道意义上的相互性和承认意义上的相互性是否与关心或同情不存在任何关系?一方面,哈贝马斯强调社会成员间相互理解的认知维度和交往主体的认知能力,“话语的交往前提没有包括对关心的考虑”(34)Axel Honneth, Disrespect: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123.。因为这些非对称性的同情和关心态度会影响对称性的公道和承认意义上的相互性,它们需要从实践话语程序中被排除。另一方面,就公道意义上的相互性而言,他认为关心或同情是实践话语的道德前提之一或认知运作的情感前提条件之一。“通过话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个体不可剥夺的说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利,二是克服自我中心视角”(35)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202.。只有每个人对他人都富有关心或同情的敏感,才能在道德意义上克服自我中心视角,并取得重要的认识行动,就利益问题达成道德性共识而非策略性妥协。在此种情况下,人只有在主观上努力去关心或同情他者的合理利益,克服自己的自爱倾向,才能在客观上达到公道要求。就承认意义上的相互性而言,它同样离不开同情等道德化情感的驱动。
由此看出,相互关心或同情原则并不是哈贝马斯正义原则的外在补充,而是植根于其共同体思想的整体结构中。不管何种意义上的相互性,都离不开关心或同情等道德情感的推动。不过,尽管哈贝马斯在公道意义和承认意义的相互性中强调了关心或同情的重要性,但他没有考虑在道德的发展过程中,同情的视角是如何出现的。“关心或同情只是表现为某种动机的补充,而不是主体间关系的构成部分”(36)Johanna Meehan ed., Feminists Read Habermas: Gendering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220.,这导致他将关心或同情排除在道德发展的结构之外。
如何理解哈贝马斯的相互关心或同情原则?尽管他和吉利根在展开关心或同情的道德思考时,都强调了社会化个体身份认同的脆弱性,但这个原则不同于吉利根的关心原则,原因在于它“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相互间没有任何优先性或不对称性,排除了伦理意义上的特殊主义因素”(37)Axel Honneth, Disrespect: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123.。吉利根的关心原则强调的是非对称性的关心,并将其置于道德的中心而不是边缘。不过,哈贝马斯认为在后传统社会视域下,吉利根并没有将伦理与道德、价值与规范、证明与应用等很好地区分开,将伦理意义上非对称性的关心带入普遍主义道德中。这无疑会导致其道德思想无法有效应对世界观解中心化的挑战。因此,二者观点分歧的关键在于:后习俗社会视域下非对称性的关心或同情是否可能,如何处理它与普遍主义正义原则的关系?一种非形式的、对语境敏感的、后习俗社会视域下的伦理共同体生活是否可能?
在霍耐特看来:“后传统哲学观念和政治理论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无法不触及社会统一的价值信念的地位,在这个关节点上,传统伦理的渐渐贬值就开始了。”(38)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伦理无法再预先规定哪种引导个人生活的方式是可取的,个人自我实现的不同价值形式处于多元共存的状态。因此,后习俗伦理只具有形式意义。就此而言,哈贝马斯与霍耐特的看法并没有根本分歧,但霍耐特明显不赞同哈贝马斯对于团结的看法,认为团结只能从集体共同的目标中才能产生。在此以共同目标为基础的共同体内,个体因其特殊能力和特性而获得承认。这种承认经验实际上是个体体验到的“群体自豪感或集体荣誉感”,其对群体的价值获得其他成员的一致认可。“在这些群体的内在关系中,互动形式正式获得了团结关系的性质,因为每个成员都认识到自己得到了其他成员同等程度的重视。”(39)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第133页。每个人不仅被动地宽容他者的特性和能力,而是积极主动地关心他者的具体特性,群体的共同目标才能获得实现。
这种意义上的“对等”关心或同情并不等同于哈贝马斯所指的“对称”关心或同情。“对等”关心或同情并不是同等程度上的相互重视,指的是特定群体内成员的团结关系;“对称”关心或同情则是同等地相互关心,指的是超越了伦理差异、包括了所有人的普遍共同体内的团结关系。可以看出,在相互性问题上,哈贝马斯与霍耐特的思想仅仅在承认意义的相互性上具有一致性。霍耐特回避了物质利益分配问题,也不赞同哈贝马斯道德意义上对称性的相互关心或同情,认为其忽视了他者的具体差异性和自我实现。
哈贝马斯之所以强调对称性的相互关心和同情,主要原因在于天然的同情和恻隐之心太弱,不足以导致个体的他向关注。正如道德情感主义的主要代表休谟指出的:“在我们原始的心理结构中,我们最强烈的注意是专限于我们自己的;次强烈的注意才扩展到我们的亲戚和相识;对于陌生人和不相关的人们,则只有最弱的注意达到他们身上。”一方面,休谟认为,“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遵守这一法则的原初动机只能是私利;另一方面,他认为“对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天然的同情心难以承担这一重任,为解决同情的偏私问题,休谟引入了一种“稳固的、一般的观点”即普遍化的视角。(40)上述引文参见: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9、569、540、624页。这一视角是正义法则得到良好运行以及政治家们公开教导、父母的家庭教育等社会化措施的产物。不过,它仍然难以弥合正义与理性利己主义者的鸿沟。
在哈贝马斯看来,共同体不是理性利己主义者追求其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或手段,也不是桑德尔所说的“构成性共同体”,而是社会成员相互得利、相互承认和相互关心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是包容差异的普遍主义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预设对实质性共同善的伦理承诺,只是强调个体之间的平等,但又不否定绝对差异。在后习俗社会的条件下,哈贝马斯认为这种伦理只能是形式上的。实现这种共同体的条件不仅仅是公道的程序和平等待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社会成员间必须彼此相互怀有足够强烈的关心或同情。同罗尔斯等人相比,哈贝马斯共同体实现的主观条件无疑要求更高,但在后习俗社会道德存在“动机不足”的问题,依赖何种动机资源完成这一任务就成了问题。(41)慈继伟《正义的两面》,第90页。
哈贝马斯在继承和发展康德道义论道德哲学和黑格尔的社会伦理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道德认知主义、道德情感主义的合理因素,通过整合道义论道德理论与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推进了共同体思想的相互性思考,但其思想中留下了普遍与特殊、理性与情感、道德与伦理、正当与善等一系列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反映了哈贝马斯共同体思想所面临的思想困境,而且反映了世界观解中心化后,西方后习俗社会在处理自我相互关系、构建新型共同体过程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