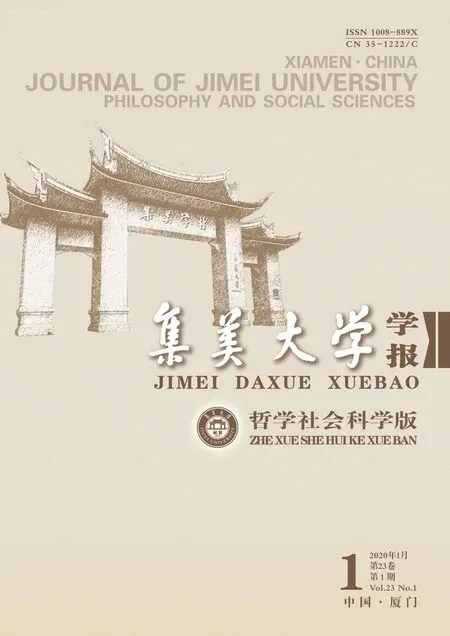孔老论人际沟通中的“怨”
陈巧玲,谢清果
(1.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怨”是人际关系中极为特别的一种情绪。聪明的中国人还创造了个词“埋怨”,借以表达“怨”的重要特征是埋藏在心灵深处,旁人不易察觉。成语“怨天尤人”,点出了怨恨的对象,既可以是“人”,还可以是“天”。“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孔子本意传达的是正能量,就是乐天知命,学以忘忧,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一种体现。其反面正是既怨天,又尤人,而这种负能量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可能导致自身彻底的失败,不可不慎。“怨恨是一种有明确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这种‘强抑’的隐忍力通过系统的训练而养成……这种自我毒害的后果产生出某些持久的情态,形成确定形式的价值错觉和与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2]。可见,怨恨的产生与表现方式有其个性因素、心理因素与文化因素。中西在怨恨的理解与处置上各有特点。

作为孔子的老师,老子对“怨”也其自己的看法。他分别在《道德经》(王弼本)第63章和第79章中提到“怨”,并对如何处理“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论语》中有9篇20处提到“怨”。本文就以老子《道德经》和孔子《论语》文本为核心,管窥中国人“怨”的心理与文化表述。
一、对“怨”产生根源的剖析
“怨”是人际关系中常见的情绪,因此对于修身养性有深刻思考的孔老于其作品中多处对“怨”进行了探讨。而葆有慈心济世情怀的孔老,其理论诉求自然是以消怨和顺为目标。
(一)放利多怨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孔子明白以“利”作为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即作为评介标准,会产生许多“怨”。毛子水、杨伯竣都解读为行为的主体会招致他人的怨恨。这种理解不全面,因为也可能是行为的利益相关者对行为者的怨恨。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就很容易处处时时伤害到他人利益,也就成为别人怨恨的对象了。这也是为什么孔子在同篇中一直倡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之所在,亦即理之所在,具有公道人心,也就不易滋生怨恨,即便有怨恨也易于消解。
《道德经》第72章提出了“夫唯不厌,是以不厌”[4]的主张,统治者只有不厌弃(压迫)百姓,百姓也就不会厌弃统治者。这里的“厌”与“怨”性质类似。显然,老子是希望统治者能够爱民亲民,“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4]。老子告诫统治者不要去排挤人民安宁的居处,不要厌弃人民生存所依靠的一切。就社会治理而言,统治者的行为是“怨”产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统治者无怨于民,民亦无怨于君上。因此,老子为作为统治者的圣人指明了安邦除怨之道:“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4]统治者要有自知之明,不四处自我表现,不扰乱百姓生活。要有自爱之尊,不到处显摆。诚然,也是要消解自我中心主义对君民关系的干扰,从而从根源上消除了“怨”产生的心理土壤。
(二)劳而生怨
《论语·里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显然,孔子心里也明白,在三番五次去劝谏父母无果之下,容易产生“怨”的情绪。只不过,孔子提出“劳而不怨”是为了树立一个孝子的形象,作孝子,就应当无论多么劳烦,都不生埋怨,而是极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角度确立起子女对待父母应有的伦理规范。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可见,孝子作为常人可能在“劳”的情况常生“怨”,但是每每在要生“怨”,或者初生“怨”的时候要能够“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能够以“贤”来规范自己,因为贤者自然是遵礼行礼的。 并以违礼的不贤来自鉴,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复归作为人子应有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父母也应当知道子女的苦心,不要做无谓的固执。爱子女就应当给子女自己选择的权力,担当的责任。也应当从爱的角度出发,对子女多给予理解与关爱。不要轻易地以父母之身份来压制子女。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4],如果把这句话用于理解父母与子女关系,也是很贴切的。父母生育了子女而不占有,培养了子女而不自恃自己的能力,成就了子女而不去居功。父母如果有这样的心胸,一方面自己怎么可能产生“怨”,另一方面,子女也不可能产生对地父母的“怨”。“怨”所以产生,皆是因为利益,因为以自我为中心来考虑问题,一旦达不到自己的愿望或目的,就会产生“怨”。老子则直接以“为而不争”的品格,从根本上消解了“怨”产生的心理根源。
(三)念恶生怨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在孔子心目中,伯夷、叔齐两位贤人之所以少为人所怨,是因为“不念旧恶”。在日常生活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与人相处不会轻易产生“怨”,乃在于圣贤也不与人计较,尤其不会念念不忘别人的过失,不会睚眦必报。
同样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4]。行为的主体如果能够“无常心”,即心中没有先入为主之见,而是以他者的心意为心意,这样对待善者与不善者都能够善待,因为不求回报,只是做自己所当为之事。对信者与不信者都能够以诚信之心待他,因为不存交易之念,而是有成就他人之心,以“歙歙”的自然心境,行自己所当行,心底无私天下宽,葆有一颗慈母之心。
(四)远之则怨
人际关系当有合适的距离,距离产生美,超越了距离可能会产生彼此伤害。孔子以女子、小人与主子的关系为例谈了自己的看法,老子则以“冲气以为和”为原则,强调个体应主动在“为人”和“与人”的奉献中构建普遍性的和谐人际关系。两人都认为应当坚持斗而不破的原则,以求和平共处。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孔子对人性有深入的探究。“性相近,习相远”的论述就表明孔子深知教育化人的重要性。当然,他也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此处所言的“女子”与“小人”,并不是女性和品德低下的人,而是“专指婢妾仆隶等”。[5]孔子以自己与同时代士人的生活阅历告诉我们,一些当时的下人与贵族之间是有矛盾的,那些地位低的婢女或小妾,以及做家务的下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他们有时也企图攀龙附凤,不安分守己。主人对他们好点了,他们有时就不知道自己是下人,甚至做出有失身份(无礼)的事情来。相反,如果主人疏远他们了,他们就难免心生怨恨。孔子对此洞若观火。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些生活情境下,与下人相处,是要把握分寸,注意远近的尺度,避免产生“怨”。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4]虽然老子并不就女子与小人问题来谈论,但是,道理却是共通的。正确转化为奇邪的,良善的转化为妖恶的,是因为人的迷惑很久了。如果用于分析孔子上文的问题,同样是适用的。这里的“人”可以指下人,也可以指主人。也就是说,主人如果没有把握分寸,可能会产生许多幺蛾子。下人如果没有注重自己的身份也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老子于是建议要像圣人那样有原则,但不过分;有威严,但不伤害;正直,但不放肆;发光,却不耀眼,从而能够自养己身,又可以保下人之身。诚为最善。
二、对“怨”的态度
孔子与老子对怨的成因有了深刻的理解,那他们俩又是如何看待“怨”这一问题的呢?亦即对“怨”的态度如何?
(一)“匿怨”为耻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那种心中有怨而表面上却装出同他人友好的人是可耻的。这种人正是巧言、令色、足恭,这种人言不为心声,表情虚假,装出和善的样子,表现出十足的恭敬,而内心却是另一种想法。没有真性情,是伪善,是德有亏的表现。孔子喜欢率真,而反对虚伪。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也肯定人生中处处都可能生怨,但有怨不可怕,可怕的是将怨埋在心里,蓄积起来,会使人扭曲人格,对社会产生更为恶劣的影响。因此,有怨应当面锣、对面鼓地解决。
《道德经》第54章明确提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4]可见,老子强调一位真正有德性的人,一定是将所学习和信仰的思想观念亲身付诸实践的人。因此,一旦面对“怨”的情况出现,一定也会认真地对待,绝不会当鸵鸟。理由老子早在第79章中就明确指出:“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4]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百姓之间,还是官民之间,都有可能产生“怨”。而这个“怨”的特点在于开始的委屈,个体得不到最舒服或者自身最满意的生活状态,且认为自身的生活受到他人或社会的干扰而导致的,即将自己不理想的生活状况归咎于他人或社会,于是在心中产生了“愤恨”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没有得到疏导,或者没有马上威胁到其生存,因此情绪没有马上爆发出来,于是就蓄积了起来。但是,日积月累,量变会产生质变,即由小怨演变为难以调和的“大怨”。而一旦“大怨”产生了,再去“和”,去解释,去劝服,去补偿,都无法完全平息其内心深处的“怨”。老子作为史官,历记祸福成败得失古今之道,可以说是见得多,识得广,历史的教训告诉他一个善为道的人,绝不是等到“大怨”产生了才用自己的真心真情去感化,那时已经产生了伤害。对于“怨”这种有杀伤力的情绪,应当要培养“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4]的先见之明。防范于未然,方是上策。
(二)行“怨”为耻
匿“怨”固然可耻,行“怨”就更可耻了。《论语·宪问》载原宪与孔子论“耻”的对话: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请教孔子关于“耻”的问题。孔子则旗帜鲜明地以为有道的邦国服务为荣,而以为无道的邦国服务为耻。进而原宪提出,如果做到了“不行”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种心理,算不算为“仁”?孔子肯定了克服以上四种反常的心理状态是难能可贵的。但,能不能称得上“仁”,则没有明确表态。虽然孔子没有直接肯定不行“怨”可为“仁”的表现,但是孔子至少肯定了不行“怨”是正人君子的基本要求,因此,虽然不算达到“仁”的境界,但至少是臻至“仁”的基本阶梯。自然,以行“怨”为耻是儒家情绪管理的应有之义。
(三)“可以怨”
“怨”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论语·阳货》载有孔子教导门人当学《诗经》的言论: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是因为先秦时期,《诗经》成为士人社会生活中表情达意的一种媒介,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常常引《诗》以讽刺时政。当时的知识贵族们习惯于对《诗经》文本用一种断章取义式的引用来说明当下的时事和时政,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所载:“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6]而君主们也习惯于通过《诗经》文本所蕴含的典故来深入理解臣子们断章取义后所要表达的全新含义。用一种来自于舆论的话语体系来处理政事,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古老而令人赞叹的政治智慧。因此,孔子才教育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掌握这一套《诗经》的话语体系,是没有办法在先秦时的统治阶级言谈交流中获得话语权的。如此看来,先秦时期表达“怨”,有其合理合法的途径。其实这种方式本身就是管控“怨”的有效手段,“怨”有地方抒发,自然就易于消解。
三、化“怨”之法
“怨”既然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危害性,就不可不慎,就应当努力去化解,消解为上。孔子二人对此也有其成熟的化解之法。
(一)报怨以德
既然“怨”是如此不好的情绪,那么就应当有所防范。而防范的关键是从认识与情感两方面处手。老子在第63章中明确提出了解决之道:“大小多少,报怨以德。”[4]从理性角度而言,要充分认识到“怨”的巨大危害性。“怨”不仅于内心深处燃烧着愤怒的火焰,这种火焰可能会伤害到自身的身心健康,而且威胁到他人的身心健康。因为当心中有“怨”时,就可能自残,可能发泄在他人身上,从而害人害己。因此,老子提出“大小多少”的四字真言。“怨”刚开始的可能只是火苗,只是不开心,不愉快,只是一句抱怨,然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当谨小慎微,一定要抱着大其小、多其少的态度来看待“怨”,即便是鸡皮蒜毛的小事,也不可大意。都把它当成大事来看待,力争妥善处置。等到有一天,对方唱起那句名歌词“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那离报复的时刻就不远了,遭殃的可能就突然大增。其实也不突然,所谓突然只是你自己没有感觉而已。而对长期受压抑有怨气的人而言,一点也不奇怪。老子的“大小多少”之教,意在告诉世人,“怨”不容忽视,要“知常曰明”,对人的脾气性格要有了解,对人要区别对待,善于换位思考,还要“见小曰明”,特别注意事物细小的变化,尽可能在事物还处于萌芽的时候,及时解疑释惑,多做暖人心的工作,化解“怨恨”于无形。
再者,要真正化解“怨恨”,还得有境界,这就是老子提出的“报怨以德”。人要有格局,尤其是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更当如此。因为任何事业都需要众人协助,而赢得人心,人心归附,依据的正是“德”。一个有好口碑的人,就能得道多助,自然就易于成功。而“德”的内涵是对正义、真理的信奉,走正道,做正事,说真话,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关系和谐。这个德还体现在面对别人的“怨”,尤其是无理取闹的“怨”、怨错对象的“怨”、视小怨为大怨等一切突如其来的不和谐因素,该如何面对,是勇敢地怼回去,还是坚强地承受下来。就是老子所说的“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4]。垢、不祥正是怨的表现形态,圣人正是能够承受住方方面面的“怨”,才能成为天下的共主。从这个意义上讲,“报怨以德”,是一种胸怀,一种格局,一种气魄。也可以理解成德是怨的反面。德与怨如同水与火。德可以报怨,克怨,化怨,如同水可以灭火。
孔子的弟子问起“以德报怨,何如?”时,孔子回答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回答偷换了概念。弟子问的是“以德报怨”,即如何面对“报怨”的问题,而孔子回答的侧重点却在于“报德”的问题,把弟子的“以德报怨”置换成“报德”。这或许正是孔子的高明之处,因为他后面的回答既回答了弟子问题,又超出弟子的问题的范围。他说用正直来报怨,这是处理“报怨”的问题。用现在的话说,你有怨,我理解,我就耐心地给你解释,我就以正当的理由,正确的方向直面对方的问题,给予合情合理的处理,从而化解了怨。孔子还说用善行来报答善行,就是“其德交归”的意思,德与德相互交往,如同思想交流,使思想更丰富一样,德性相交往,让德性更丰厚。此外,《礼记·表记》还深入表达了孔子的德怨观:“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7]就此而言,孔子赞赏“以德报德”和“以德报怨”,同时也不反对“以怨报怨”,因为怨而招来怨,是“怨”主体自己应当知道可能会遭的还报,因此是自己应当承受的。当然对怨的对象而言,则具有以怨报怨的权力,同时也可展现以德报怨的高姿态,高境界。但孔子极力批判“以怨报德”,认为这样做是该受到刑罚的。
不过,显然孔子的“以直报怨”与老子的“以德报怨”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有据理力争的豪气,我可以帮助您,我可以理解您,但我必须教化您,您的是与非,我的是与非,我们要论一论,以理报人。当然,这个直,有正直、耿直、爽直等含义,也自然体现出一种高尚的德性,不是走歪门邪道。而老子的“以德报怨”显然更有“慈爱”的德性,你的怨,无论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包藏祸心,我不跟你计较。我尽我所能帮助你,既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又可以舍己为人。圣人的特征就是:“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4]圣人既没有积累财富的爱好,也没有与人争先的习惯。圣人的这种损有余补不足的行为方式,是化解怨恨的利器。因为老子说过,“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4]大怨也就是大患,根本上源于“有身”,即有私。而一旦我“无身”了,忘我了,我对别人的埋怨也好,怨恨也罢,都能够向父母对待犯错误的小孩一样,宽容,理解,以最大的耐心、勇气与智慧来帮助孩子成长。
(二)以“仁”化“怨”
《论语·述而》有言:
(子贡)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据毛子水研究,这一对话发生的历史语境中,孔子一行人当时居卫国,而卫国又发生了蒯聩与辄两父子争当皇位的事件,弟子想先了解孔子的倾向。于是子贡才以伯夷、叔齐的故事来曲折地了解老师的意见。而孔子评价伯夷、叔齐是贤人,且为逃避皇位而出走他国,是求仁得仁的做法,不会产生“怨”。因此,蒯聩与辄争皇位而大起干戈是不仁,自然会遭到孔子的反对。[5]107如此看来,孔子认为可以用仁心仁行来化解“怨”。
《论语·颜渊》亦载有以“怨”释“仁”的段落。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求教孔子关于“仁”的问题,孔子指出,出门在外,要有像对待贵宾那样恭敬待人,役使民力时,要有如同承办大型祭祀那样严谨细致,小心谨慎。总之,要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以感同身受的方式,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自己不欲做的事,就不要强加给他人。这样做,在国家社会层面上不会产生“怨”,在家庭层面上也不会产生“怨”。如此看来,孔子正是以“无怨”来呈现“仁”的应有之义,可谓言简意赅。
老子对“仁”也是很欣赏的,虽然他认为仁的境界并不等于“道”“德”的境界,甚至还提出“绝仁弃义”的观点,但是,老子的本义是要去掉“仁”之名,而求“仁”之实。老子批判的是当时礼崩乐坏的时候,徒有“仁”之名而失“仁”之实的现象比比皆是,故而有感而发。他在《道德经》第8章中提出“与善仁”,其含义是人与人的相交,要本着一颗仁爱的心,以仁爱的心来彼此相待,自然可以长长久久,不会生“怨”,有“怨”也能及时化解。
(三)劳而不怨
虽然上文已引用《论语·里仁》中的“劳而不怨”,不过,《论语·尧曰》中所提到的“劳而不怨”是将其当成一种从政的重要品格与素养来看待,两者的语义是有差别的。足见孔子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这正是其爱民思想的自然流露。《论语·尧曰》有:
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此处孔子把“劳而不怨”看成是一种从政必须具有的能力与品德,即施政者能够管理百姓,而百姓心甘情愿。其内在的道理是,施政者有爱民之心,“择可劳而劳之”,能够根据百姓的实际情况加以引导,让百姓得利多,而付出少,因此百姓能够不辞辛劳。
其实《论语·宪问》还有一处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这句话显然是称赞管仲深谙为官之道,以至于他剥夺了伯氏骈邑三百户的采地,让伯氏吃粗饭食,到老都没有怨恨的话。可见管仲做到了“威而不猛”,当然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劳而不怨”,伯氏还能够有基本生活保障,并没有使其陷于绝境,因此,管仲施政还是留有余地的。进而孔子赞叹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人在贫困之境易于滋生怨恨,到此贫穷境地能不生怨,是很难的。换句话说,这对施政者与被管治者都是不容易的。施政者行政的分寸,被管治者能反躬自省,而不生怨恨,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如此看来,“劳而不怨”诚然是孔子极为推崇的治理原则与能力。
还有《论语·微子》也在政治情境中探讨如何远怨的问题。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
在注重血亲政治的古代,取得自己姻亲家族的支持,是政权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周公就告诫儿子伯禽要善待亲族之人。“施”,杨伯竣解读为“怠慢”,而毛子水释读为“驰”,为“弃忘”之意。意思虽然不同,但是都表达了要善待的意思。因此,下文才接着说不要让大臣因为不被重用而产生“怨”。君臣不和,国之大忌。于是,周公提出了一个原则:如果老臣没有大的过错,就不要弃而不用,不要对他们求全责备。这是一种远怨的政治智慧。
(四)躬自厚以远怨
当然,孔子与老子在面对“怨”的时候,都有一个相同的取向。那就是更多地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来找原因,而不是把事情推给对方,怨恨对方。如果这样,那事情就会恶化,会产生剧烈的冲突,导致两败俱伤。“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强调多问己非,而不苛责于他人。而上文已言,老子把给予他人、成就他人当成自己的使命,又怎么会跟人去计较短长高下呢。自然也就远离了怨恨。
其实,解决“怨”的问题,还是从“怨”产生的土壤着手。“怨”既然生于“心”,自然就要从心地做文章。《礼记·礼运》有言:“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圣王修治心田的努力,是达到天下大同的根本法宝。而《道德经》中,老子则提出了“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4]的制度性安排。圣人手中有债权人的凭证,但不依此苛责于债务人,而是给对方以充分的时空去完成自己的承诺。或者我们可以说,要实现“天下大同”既要有人的素质提升,又要有制度性建设,以保证“怨”有疏导的渠道,有化解的机制,从而使社会和谐。
(五)不怨天,不尤人
《论语·宪问》有载孔子的感叹: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作为圣贤,也有类似老子在第七十章中的感叹:“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4]孔子感叹时下不了解他,没能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唯独“天”是他的知音,这是因为他以天为使命。老子感叹世人追求享受,而对他尊道贵德的保身存身之教充耳不闻,对于他以历史的深刻教训来启迪世人,世人却无法理解,老子视世人的态度为“无知”。孔子何以有“不怨天,不尤人”,大概他知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天(道)永远在那里,等待人们去感悟,去实践。《论语·阳货》有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因此,不要去埋怨天。那为何不要责备人?因为对他自己而言,《论语·述而》有言:“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就是说,孔子自己坚持学习,而且把学习所得教授给他人,他是不知疲倦的,且不苛责于人,而是努力启发他们。
如此看来,孔子与老子对自己的思想学说难为世人所理解和推行有自知之明,他们都不固执,都坚持走自己的路,相信他们所信仰的正道终究会为世人所理解和推行的,一切只是时间问题,这是他们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