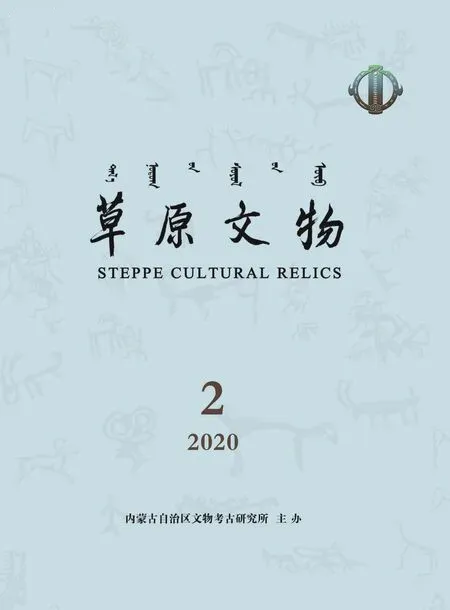杆头饰的起源、分布区域及功能※
李水城
(北京大学)
所谓杆头饰是一种动物圆雕为主的小件铜器,铸造,胎体较薄,空腔,一般高10~20 厘米,因其装置在木柄顶端,故名。其造型大致分两类:一类上部为简单的空心球或球形铃铛,有些表面带镂孔,内置石粒或铜珠,摇之可发出声响。另一类为鸟兽类圆雕,如牛、鹿、羊、虎、鹰、鸟或格里芬神兽等,有些鸟兽的身体也被制成空腔的铃铛,内置石粒或铜珠,可发出声响。杆头饰下部为纳柲的銎,圆柱、方柱或扁方柱状,上有用于加固的销钉孔。也有很多在銎部一侧加铸小的圆环,以便悬挂铃铛、璎珞或流苏一类装饰。
杆头饰是用于礼仪活动的仪仗用具,有时也被视为权杖。由于其本身就是球形铃铛或设有悬挂铃铛的装置,使用时会随人或车子的移动叮当作响,其上悬挂璎珞或流苏则随风飘扬,清脆的铃声和鲜艳的色彩无疑会强化仪式的神圣感,活跃现场气氛,令参加仪式活动的人大脑迅速兴奋并产生愉悦感。
一、中国境内考古所见杆头饰
20 世纪末至30 年代初,瑞典学者安特生(Andersson,J.G.)连续撰文介绍了一批早年从中国古董市场流出的小件铜器,主要有兵器、工具、仪式用具或装饰品等,大多出自北方长城沿线①。1932 年,他在《动物风格的狩猎幻术》一文中首次将一类鸟兽圆雕的小件铜器称作杆头饰(Pole-top)②。后来,由于此类遗物中鹿的形象比较多,也有西方学者称其为鹿形杖首(stag-shaped finial)。
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杆头饰集中出现在春秋时期,最晚延至西汉。流行的区域主要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宁夏南部、陕西北部、河北北部,最东可至赤峰及周边地区。其次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和新疆西部也有发现。此外,在西南的四川盐源、云南的滇西北、滇西、滇池和洱海周边也有分布。但北方和南方的杆头饰在造型、内容和造型风格上区别明显。即便在北方,长城沿线与西北地区也有较大的差异。
1. 鄂尔多斯地区
1933 年,安特生撰文介绍了一批国外博物馆收藏的杆头饰。文中他特别提到,敏斯(Ellis H Minns)教授建议,将这些出自内蒙古的青铜器统一命名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③。

图一 内蒙古博物院及鄂尔多斯博物馆藏杆头饰
目前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杆头饰可分为如下几类:一类为空心圆球状,下接柱状銎(图一,1)。此类发现较多,造型也近似权杖头,部分器表镂空,内置铜(石子)珠。有个别还在圆球上加铸一立兽。比较特殊的是在圆球下接圆柱高銎,其上有2-3排对称突起,一侧封口,一侧开方形口(图一,8)。第二类为禽鸟头部圆雕,颈部为銎。常见鹤(图一,3)、鹳(图一,4)、鹰(图一,5)等。第三类为圆雕动物。所见有绵羊(图一,2)、虎(图一,6)、驴(图一,7)、马(图一,9)、北山羊(图一,10)、卧马(图一,11)、羚羊(图一,12)、刺猬(图一,13)、熊及怪兽等。个别在兽头顶部加铸圆管,可插放饰物(图一,14)。
2. 宁夏、陕北、冀北及内蒙古赤峰地区
宁夏南部的西吉县杨郎墓地出土一批杆头饰,个体都不大。多为空心球状,下接圆柱銎(IM7:24),高6~8 厘米(图二,1)。其他还有鹰首、鸟首、犬首、鹿首等。有两件为绵羊头圆雕(IIIM4:1),大角弯曲,颈为銎。高6.7、銎径3.6 厘米(图二,2)④。固原博物馆还藏有出自杨郎乡的鹰首杆头饰,下接方柱状銎。高6.1、銎径边长 3.1 厘米(图二,3)。这批遗物均为战国时期。
陕西北部与鄂尔多斯毗邻,这里的杆头饰主要出自榆林地区。在神木县的纳林高兔遗址出有2 件圆雕刺猬,造型惟妙惟肖。高9.8 厘米(图二,4)⑤。
河北的杆头饰集中于北部张家口地区。所见有并排站立的北山羊一对,立于长方柱状銎上。高7.8、宽6.5 厘米(图二,5)。在赤城县出有立于方匣状底座上的马,下接扁片器柄。高13.9 厘米(图二,6)。早年在康保县出有鸠鸟杆头饰(C 1832),双眼镂空,腹两侧有竖条镂孔,中空,内置铜(石)球,足部为喇叭状圆銎。高13.6 厘米(图二,7)⑥。
内蒙古东部宁城县小黑石沟墓地出土的杆头饰造型特殊。其中,2 件为龙首(M8501:77),眉、眼、口、鼻俱全,头上长有一对突角,弯颈为銎。高约12、銎径约5.5 厘米(图二,8)。一件为男性生殖器(M8501:73)。高约12、銎径约4 厘米(图二,9)。一件为人头圆雕(M8501:74),瓜子脸,浮雕五官,颈部为圆柱銎。高约10、銎径约3 厘米(图二,10)⑦。
3. 西北地区

图二 北方长城沿线出土的杆头饰
(1)青海
1983 年,在湟源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出土4 件杆头饰。其中2 件(M87:1)为鸠鸟、牛与狼造型。下部为鸠鸟首,圆眼,鸟喙长直,呈圆柱状,颈部为銎。鸠鸟头顶有一头母牛,四足间有一牛犊正吮吸母乳。鸟喙前端站立一头狼,翘尾张口狂吠,与母牛对峙。器高12 厘米(图三,1)。另有2 件鸠鸟杆头饰,均残损⑧。
1982~1983年,在湟源县采集1件杆头饰,整体呈“L”形。底部前端伏卧一男子头像圆雕,面朝前,颈部圆柱状,中空,有槽孔。后部为一男童,昂首前视,身体两侧有浮雕男子头面像。器高7、长7.7 厘米(图三,2)⑨。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有球形铃首杆头饰(M801),器表有竖条镂孔,中空,内置石珠,下接圆柱銎(图三,3)⑩。

图三 西北地区出土的杆头饰
1985 年,大通黄家寨墓地出有雄鸡杆头饰(M16:5)。头顶带冠,环眼,尖喙,长颈,腹部球形,有横向梭形镂孔,中空,内置橄榄状石粒,短尾。长10.8、高7.8 厘米(图三,4)⑪。类似杆头饰在湟源县栏隆口乡上寺村也有出土。头顶带冠,勾喙,长颈,卵圆腹有竖列梭形镂孔,中空,短尾(图三,5)⑫。在湟源县巴燕峡征集一件鸠鸟杆头饰,粗颈,背部铸羽翼纹,腹中空,有竖列梭形镂孔,内置卵石,短尾上翘。器高11、宽5.6、壁厚0.2 厘米(图三,6)⑬。
青海所出杆头饰均属卡约文化,年代为公元前1千年前后或稍晚。
(2)甘肃
1980 年,在甘肃省永登县榆树沟发掘一座战国晚期古墓,墓内殉牲(马、牛、羊头骨)大量,出土铜杆头饰10 件。其中4 件为鹰首,圆眼,勾喙粗壮,头顶及脑后铸羽纹,颈部为銎(图三,7)。奔鹿6 件,分两式。一式为奔跑的小鹿,下接方柱短銎。长5.2、高6.5 厘米(图三,8)。二式为立鹿,下接片状台座。长5、高5 厘米。发掘者将此墓定为沙井文化⑭,但其所在位置已超出沙井文化的范围,墓内大量殉牲,随葬杆头饰与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所出相似,应为匈奴墓⑮。
1994 年,在甘肃永昌乱墩子滩遗址采集2 件枭面浮雕杆头饰,大眼,勾曲喙,颈部为粗短銎。高4.5、直径3.8 厘米(图三,9),年代不明⑯。
(3)新疆
1961 年,新疆伊犁自治州特克斯县在修建农田水利设施时出土一批小件红铜器。一件为牛头圆雕,中空,头顶犄角上扬,牛眼突鼓,双耳朝后,颈部为筒状銎,牛额及颈部一侧有销钉孔。器长8.8、銎深6.8 厘米(图三,10)。一件为“牛角杖首”,角尖稍残,剖面菱形,呈环形弯月状,下接圆柱銎。銎中部有球形突起,似象牛头。双角间距8、銎孔残深1.5 厘米(图三,11)。另有三件“弯月镰形杖首”,造型相同,下部为銎(皆残)。其中,一件体扁平,器表有三道突棱,环径7.5、厚0.5、宽1~2、銎孔残深0.9 厘米(图三,12)。一件銎部有球状突起,环径7.2、銎孔残深1 厘米。一件体扁平,有凹槽,环径6.5、厚0.3、宽1~1.5、銎孔残深1.5 厘米。据介绍,在这批遗物出土地点附近分布有两汉时期的土墩墓,推测为姑师或塞人遗留,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不明⑰。考虑到这批遗物均系红铜铸造,年代不会太晚,属青铜时代的可能性很大。
4. 西南地区
(1)四川
20 世纪80 年代,四川盐源一带盗墓猖獗,大量文物流落民间,当地文物部门征集到一批墓中随葬的杆头饰。后在盗掘地点做过数次抢救发掘,但再没有新的发现。

图四 四川盐源出土的杆头饰
这批征集品种类较杂,其中最完整的杆头饰杖顶站立一只雄鸡(C:9)。高冠,翘尾,立于圆盘上,圆盘周缘有四枚穿钮,套小环,环上挂圆形铜片,摇动可发声响。杖柄由九节铜管组成,每节长35~39厘米,阴刻密集的鱼纹,末节底端为圆锥形鐏。杖长134.8、圆盘直径5、柄1.4 厘米(图四,1)。
一件为“三女背水”圆雕(C:643)。杖顶铸有三女子立像,品字形相向立于倒锥形台坐上。她们穿着相同,头戴螺蛳状尖帽,着紧身上衣和刺绣花纹的筒裙。背上驮的水罐用背带勒于前额。圆柱柄,上饰密集螺旋纹。器高16.2、杖首残长9.3、宽5.7、銎残长6.9厘米(图四,2)。
第三类数量最多,样式也最复杂,均为片状,造型结构颇似汉代流行的摇钱树。中心为主杆部分,下有銎或实心圆柱。整体布局均为对称的圆环枝杈。主杆顶部有人形,双腿岔立枝杈上,两侧为圆环枝杈、对马、人骑马、双环、对鸟等。以编号C:27 为例,顶端为长尾鸟,两侧为圆环枝杈,上下共四组。主杆下为銎,上细下粗,有菱形銎孔。长12.1、宽10 厘米(图四,3)。编号C:29 顶端一人形,头顶花蕾,两侧接对称圆环枝杈、人骑马。主杆下接菱形实心插柱。长20.3、宽11.2、杆长7.7、厚0.4 厘米(图四,4)。C:654 顶端为一人形,右臂上扬,左臂置腹前,两侧为圆环枝杈、对马。主杆下接椭圆实心插柱。长15.6、宽9.8、杆长3.5、厚0.3 厘米(图四,5)。C:28 为两组圆环枝杈,上面一对大圆环,饰同心圆和连珠纹,下接一对小圆环。主杆下接实体六棱插柱。长13.9、首长8.6、宽9.2、銎长5.3、銎径0.9~2 厘米(图四,6)⑱。
盐源所出的杆头饰以汉代为主,个别稍早可至战国晚期。
(2)云南
云南的杆头饰主要见于滇西北、滇西、洱海和滇池周围。特点是在顶部铸有人物或飞禽、鸟首,区域特点较鲜明。
1977 年,在滇西北的德钦县石底发掘一批石棺葬,出有少量杆头饰。一件为鹿首圆雕,鹿角分五枝,角端悬挂菱形叶片,摇动可发声响,颈部为銎。器高9.8、銎径4.3~4.6 厘米(图五,1)。一件为飞鹰圆雕,勾喙,大眼,展翅翱翔状,足部为銎。器高4.2、长4.8、翼展7.2 厘米(图五,2)⑲。德钦纳古石棺葬出有一件,为马头圆雕,颈部为銎(图五,3)⑳。这批杆头饰格调粗犷,立体感强,与北方地区风格接近。

图五 云南出土的杆头饰
洱海周边的大理、祥云、弥渡、宾川出土杆头饰较多,造型以禽鸟为主,少量动物。特点是禽鸟或单或双,也有的多只聚在一起,器高10 厘米左右㉑。在祥云县红土坡14 号墓出土一批。所见有鸳鸯(M14:110-2),高14.2、宽5.6 厘米(图五,4)。长尾鸟(M14:109-2),高13、宽10.8 厘米(图五,5)。凤凰(M14:106-6),高12、宽4.5 厘米(图五,6)。还有雄鸡、白鹭、鸬鹚等㉒。在祥云大波那古墓铜棺内随葬一件,断为三截,杖头为两只圆雕的花豹,相互缠斗状。杖长125、銎径1.3 厘米(图五,7)㉓。
滇西保山出土的杆头饰有圆雕的鹰鸟,勾喙,长尾,栖于竹节銎柱上(图五,8)。圆雕公牛,立于“Y”形器柄顶部(图五,9)。圆雕立鹿,站在梯形台座上(图五,10)。这批遗物可能属于古哀牢国㉔。
在昆明滇池周边的古墓常出杆头饰。江川李家山出有雄鸡(M69:209),卧在鼓形坐上,器表镀锡。残高8.5、銎径1.5 厘米(图五,11)。有栖于铜鼓上的雄鹰,通体鎏金(M69:160)。雄鹰昂首勾喙,口衔一蛇,缠绕在鹰的头颈部。高7.3、銎径1.9 厘米(图五,13)。还有跽坐于铜鼓的滇妇(M59:159),束发,梳银锭髻,佩耳环,着对襟长衫,双手垂膝,跣足,通体鎏金。器高6、銎径1.9 厘米(图五,14)㉕。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杆头饰有孔雀(图五,12)、兔(图五,15)、雄鸡、公牛、鱼等㉖。昆明羊甫头墓地出有滇妇、孔雀、鱼等造型。除铜器外,还有木雕,器表髹漆,所见有立于叠置蘑菇状杖柄的鼠鼬(M113:61),小眼,咧嘴,有髭,长尾下垂。高23.2 厘米(图五,16)㉗。云南的杆头饰主要为西汉时期,个别可早至战国晚期。其中,羊甫头墓地的年代下限晚至西汉末至东汉初。
在广西平乐县的银山岭墓地也出有少量杆头饰,所见多为立禽或立兽,器高5~6 厘米,造型和艺术风格与云南接近,年代也大致相同㉘。
中国境内早年出土的杆头饰均系旧藏,年代不清楚。以往学界对杆头饰出现时间有西周以后说㉙、战国说等㉚。上世纪70 年代以来,在宁夏南部的西吉县、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呼鲁斯泰㉛、西沟畔㉜等地相继发掘一批东周至西汉的古墓,不仅获得了杆头饰的绝对年代,也了解到这类器物的使用者为活跃于北方长城沿线的戎狄或匈奴。甘肃河西走廊的此类遗存也与羌或匈奴有关,青海境内的杆头饰属卡约文化,族属应为居住在河湟地区的羌人。
二、国外考古所见杆头饰
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杆头饰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山以西的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蒙古等地非常流行,其造型和艺术风格与中国北方地区比较接近。
1. 乌拉尔山以东至蒙古高原
从乌拉尔山向东至西伯利亚、蒙古高原都有杆头饰分布。这个地区的西部以费利波夫卡(Filippovka)遗址为代表。该址位于俄罗斯南乌拉尔奥伦堡市以西的乌拉尔河与伊列克河(R.Ilek)交汇处。上世纪50年代在此发现一处包括25 个土丘的冢群。1986~1990年,俄罗斯考古学家发掘了其中的17 座,除部分被盗,大多保存完好。在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中以鹿的造型最多,也有一些格里芬神兽、北山羊、狼和骆驼等动物。该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5~前4 世纪,属斯基泰文化晚期至萨马尔泰文化。
该遗址1 号冢出土3 件杆头饰,片状,顶部浮雕骆驼头,圆眼、小耳,张口露齿,下部身体饰卷云纹,象征毛发,底部为长方片状插座,上下均有销钉孔。高23~24.5 厘米(图六,1)。在乌发(Ufa)博物馆藏有一件出自1 号冢的立鹿杆头饰,硕大的鹿角呈弯曲的横“8”字状,立于长方台坐上(图六,2)㉝。

图六 乌拉尔山以东至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杆头饰
在西伯利亚的阔尔苏科夫斯基(Корсуковский)窖藏出有球形铃首杆头饰,器表镂空,内置卵石或铜球,下接圆柱状銎(图六,3)。在伊利姆斯卡(Илимска)出有奔跑的野山羊杆头饰,大角,长耳,短尾,腹部椭圆形,有铃形镂孔,中空,内置卵石或铜球,立于“凹”形銎座上(图六,4)㉞。在托姆河(р. Томь)的乌斯齐(Устье)遗址出有北山羊杆头饰,大角弯呈环形,尖耳,短须,立于圆柱高銎上(图六,5)㉟。在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有公元前7~前8 世纪的杆头饰。一件为麋鹿,体型瘦高,环眼,鼻孔透穿,长颈,长腿。高14.9 厘米(图六,6)㊱。在南西伯利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采集有驼鹿杆头饰,大头,环眼,短颈,体型肥硕,立于方形箍座上。高6.6 厘米(图六,7)㊲。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有出自阿尔泰的圆雕大角鹿杆头饰,时代为公元前7世纪。鹿角硕大,从头顶延伸至臀部,四肢浮雕在方銎上。高11.7 厘米(图六,8)。在鄂毕河上游的什达卜克村(с. Штабка)出有驼鹿杆头饰,头顶的大角呈花辫状,立于圆柱銎上(图六,9)㊳。
在图瓦的阿尔然(Аржан)1 号王陵出有一组北山羊圆雕杆头饰,造型雷同。其中出自26 号墓室的一件昂首,环眼,大角回旋弯曲成环状,身体壮硕,站立在方銎或圆銎上。高11.4 厘米(图六,10)㊴。在蒙古国的马诺舍夫斯卡(ст. Маношевская)遗址出有麋鹿圆雕杆头饰,立于扁柱台座上(图六,11)。造型与西伯利亚古布斯卡(ст. Губская)遗址所出非常相似㊵。
2. 北高加索、东欧草原和东南欧地区
北高加索一带的杆头饰流行于公元前7~前3 世纪,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写实动物圆雕或铃首,造型风格与乌拉尔以西地区类似。在库班地区的克列尔灭斯(Келермеc)2 号冢出有球形铃首杆头饰,高17厘米(图七,1)㊶。也有的为桃形铃首(图七,4)。动物类有圆雕马头(图七,2)、鹦鹉头(图七,5)和野山羊头(图七,6)等,年代为公元前7~前6 世纪的前半叶。
在克里米亚(Крым)出有鹰首造型(图七,3)的杆头饰,属斯基泰文化晚期㊷。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有出自库班(Koban)文化晚期的大角鹿杆头饰,前半个身体圆雕,作站立状,鹿角硕大,分为6 杈,两侧附有半圆环,环内悬铜铃。颈部亦附铜环,悬铜铃。后部躯体为銎,年代为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图七,7)㊸。

图七 北高加索斯基泰文化的杆头饰
第二类杆头饰见于北高加索和东欧草原,时代也在公元前7~前3 世纪,造型比较独特,所见分为三种。一种为片状牌饰的浮雕,造型多为格里芬神兽,个别为人物造型,下接“T”形座架銎箍,两侧常附有小铜环。一件为狮身格里芬神兽,前爪搭在幼鹿的颈部,张口撕咬鹿头(图八,1)。一件为虎形格里芬神兽,双翼翻卷,一只前爪抬起,方框下部的两侧悬铜铃(图八,2)。在克拉斯诺库茨基(Краснокутский)冢墓出有恶龙有翼神兽,颈上排列齿突,长尾翻卷上扬,前爪抓着小鹿的颈部,撕咬鹿头(图八,9)。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一件公元前375~前325 年的雄鹿杆头饰(GE DN 1898 1/328),大角,短尾,口衔物,一前肢蜷曲跪地。高15.3 厘米(图八,10)。在亚历山大鲍里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опольский)冢墓出有女神造型的杆头饰,她头戴圆帽,面如满月,双手掐腰,身着长裙,站立在“T”形銎架上(图八,3)。
第二种仅一件。片状,“山”字形,三个锥尖顶部各自栖息一鹞鹰,两侧鹞鹰口衔铜铃,下接圆柱短銎(图八,4)。
第三种数量最多,其造型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顶部为兽头或鸟首圆雕,个别为浮雕动物牌饰。中部为鸟兽的躯体,均设计成造型各异的镂空铃铛,内置卵石或铜珠,摇之可发声响。下部为圆柱銎或棍状实心柄。如德聂伯河上游的波波夫卡(Поповка)遗址5 号冢出有鸭形杆头饰,躯体为卵圆铃铛(图八,5)。在乌里斯基-阿乌尔(Ульский аул)遗址2 号冢出有雄鸡杆头饰,头顶有冠,小圆眼,张口鸣叫,腹部为三角形铃铛(图八,8)。该遗址1 号冢出有公牛杆头饰,长角,短耳,躯体为三角形铃铛(图八,17)。还有一座随葬品丰富的墓出有格里芬浮雕牌饰,下接梨形铃铛,器表为镂空螺旋纹(图八,11)。还有的顶部为栖息或飞翔的鹰鸟,下为长椭圆状铃铛(图八,12、13)。在克列尔灭斯3 号冢出有鹰首格里芬,勾喙,桂叶状立耳,躯体为梨形铃铛。高35、直径11.5 厘米(图八,15)㊹。其他还有勾喙巨大的鹰首或犬首杆头饰,前者躯体为三角形铜铃(图八,14)。后者立耳,张口吐舌,下接梨形铃铛(图八,16)。
在北高加索的孤布斯卡雅(ст. Губская)遗址出有卧鹿杆头饰,大角,昂首,卧在球形铃铛上(图八,6)。在库班地区马霍什夫斯卡娅村附近的冢墓出有立鹿杆头饰,站在球形铃铛上。高24、铜铃直径10.6 厘米(图八,7)㊺。这个地区曾发现杆头饰的木柄,长达1.75 米㊻。

图八 北高加索和东欧草原出土的杆头饰
据俄罗斯学者研究,当时居住在这一区域的有斯基泰人,也有非斯基泰人。
北高加索出土年代稍早的杆头饰为公牛造型。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特里(Tli)墓地出有2件,青铜,铸造,空腔,牛头和前肢圆雕,后部躯体为銎,上有销钉孔。造型写实。一件牛头正面平视,牛角朝前再向上弯曲。牛角间距10、高9 厘米(图九,1)。另一件牛头高高昂起,面朝右,牛角弯曲向后。牛角间距9、高7.5 厘米(图九,2)。特里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2 千纪后半叶,属青铜时代晚期的库班(Kuban)文化㊼。
北高加索最早的杆头饰可追溯到红铜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造型为抽象的牛头,上部为弧曲的大牛角,下接上下贯通的圆柱管銎,以纳柄。在库班河和捷列克河(р. Терек)流域发现一批。其中在新斯瓦波德内伊一号冢(курган 1 у ст-цы новосвободной)出土3 件。一件牛角向两侧斜伸,再90 度上扬,角尖后弯。高7.8、宽8 厘米(图一〇,1)。一件牛角向两侧水平延伸,再90 度上扬后折下弯,銎箍饰几何纹。高约7.8 厘米(图一〇,4)。一件牛角向两侧水平延伸,再向上折曲,角尖向前内收。高8.5、宽13.5 厘米(图一〇,6)。同一地点的31 号冢(курган 31)出土2 件。一件牛角向两侧弧曲上扬,合拢近椭圆形,銎柱螺旋状。高10.5、宽10 厘米(图一〇,2)。一件牛角向两侧上扬弧曲近椭圆,角尖后弯,銎柱表面铸凹凸纹。高8.2、宽9.8厘米(图一〇,3)。在巴穆特村冢墓(курган у с.Бамут)出土1 件。牛角向两侧弧曲上扬、角尖前弯。高7、宽10 厘米(图一〇,5)㊽。在普谢鲍伊斯克伊冢墓(курган у ст-цы псебойской)出土1 件。牛角向两侧弧曲上扬,角尖内收弯向下。高约9、宽12 厘米(图一〇,7)。此类杆头饰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 年前后,属迈科普(Maikop)文化㊾。

图九 北高加索特里遗址出土的杆头饰

图一〇 迈科普文化和颜那亚文化的牛角杖首

图一一 东南欧地区出土的杆头饰
同样的器物在伏尔加河至乌拉尔之间的颜那亚(Ямная)文化㊿也有发现。牛角向两侧弧曲再上扬,下接圆柱高銎(图一〇,8)年代与迈科普文化大致相同。
东南欧发现有与特里(Tli)墓地相似的杆头饰。在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皮洛斯(Pylos)狮鹫勇士墓出土一件(SN24-151),为青铜铸造的公牛头,中空,颈部为銎(图一一,5)。发掘者认为,此器应为墓主生前使用的权杖,也是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此墓的年代为公元前1500 年
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库库廷--特利波里(Cucuteni-Tripoli)文化发现有陶塑牛头杆头饰,牛角大多破损,颈部为纳柲的銎(图一一,1、2),有些还在器表绘黑彩几何纹(图一一,3、4)库库廷-特利波里文化的年代为距今6000年前后,属于铜石并用时代。
3.安纳托利亚

图一二 安纳托利亚出土的杆头饰
在西亚,安纳托利亚的杆头饰出现较早。在土耳其中部偏北的阿拉卡·休于克(Alaca Höyük)遗址出土一批。造型分三类:一类为青铜圆盘状,也称“太阳圆盘”此类器结构较复杂,主体为圆形或方形,底部有“H”形短支架。圆形近“Ω”状。有的将圆盘内部隔出若干小方框,方框再用“X”栅格分割,栅格上套有活动的环,移动可发声响。圆盘底部两侧向外伸出一对弯曲向上的圆棍,形若牛角。圆盘外周顶部铸有花蕾和人形(图一二,1)。有的将圆盘扭成螺旋麻花状,底部两侧向外延伸出一对牛角。圆环内并排站立3 只圆雕动物,面向一致。中间为高大的雄鹿,头上的大角分为五杈,高出圆环顶部。两侧站立稍小的公牛(图一二,2)。有的圆盘粗犷厚重,圆盘内站立3只圆雕动物,中间为高大的雄鹿,面朝前,头上硕大的鹿角分出多个枝杈。两侧动物个头稍小,面朝后,背影像是狮子。圆盘底部向外延伸为两个环,圆盘顶部铸有人或动物(图一二,3)此类圆盘杆头饰的高度和直径为20~35 厘米。
第二类为方框状,下有圆柱把手,形若拍子。方框内隔为栅格状,套有活动的竖铜条,滑动可发出声响。方框外周左右两侧铸有雄狮追逐野山羊的圆雕,顶部铸有雄鹿和雌鹿的圆雕(图一二,4)
第三类为单纯的动物圆雕。有单独的公牛站在“T”形台座上,大角弯曲朝前,身体表面镶嵌银带、银钉和同心圆纹,牛颈、鞍座和牛角镀银(图一二,5)。有的为圆雕驯鹿,站在分成四杈的底座上,身体表面镶嵌银丝同心圆、十字、折线纹。器高54厘米,被认为是狩猎之神(图一二,7)。阿拉卡·休于克墓葬的年代为公元前2400~前2200 年。
1955 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入藏一件杆头饰,此器出自安纳托利亚中部,年代为公元前2400~前2000 年,属青铜时代早期。此器用砷铜铸造两头并列的公牛,头上长有大角,立于平面微鼓的“T”形台座上。器高15.9、牛角宽14.6 厘米(图一二,6)
4. 伊朗
公元前8~前7 世纪,在伊朗西部的卢利斯坦(Luristan)省也流行青铜杆头饰。一类为片状,外周有圆框或方框,框内浮雕人物和动物,造型和结构与安纳托利亚的“太阳圆盘”相似,二者或许有亲缘关系。
到日本展出的一件为圆形,框内中间为浮雕人物,两侧为对称的马,圆框下部接管銎,两侧有圆环。高11.3 厘米(图一三,1)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1943.1162),方框形,外框表面铸“《”纹,框内空间隔成上下两栏,上栏约占2/3,浮雕3 位手拉手并列站立的人和对牛,人物面相雷同,环眼,高鼻,卷云耳,小嘴。中间一人身材略高,双脚并拢站立于团花之上。旁边二人站立于牛背上。下栏中间浮雕一立人,两侧为公牛,屈肢,耸臀,牛尾卷至背上,牛头抵在人的头部。人手搭在牛膝部。方框下部为圆柱銎,两侧有圆环。器高13.6 厘米(图一三,2)。
第二类为圆雕动物,下接管銎。巴迪巴尔(Bard-i Bal)遗址出有单体动物和对兽造型的杆头饰。一件顶部为上半身侧身相向的对称山羊,下半身合体构成圆柱銎。羊背部和管銎附有3 对螺旋圆环,管銎下部有锥刺。器高约15 厘米(图一三,3)。另一件为单体的羚羊,仅塑造头颈部,下接圆柱銎。高约13 厘米(图一三,4)

图一三 伊朗公元前8~前7 世纪的杆头饰
第三类数量较多,系神人动物组合造型,下接圆銎,结构复杂,富于变化,几乎一器一样,无雷同者。在塔图尔班(Tattulban)遗址出土一件上部为神人,身体呈拉长的圆柱状,铸有两具浮雕兽面。此人头戴梯形圆帽,环眼、环耳、高鼻,双手抓住怪兽的颈部,怪兽与人体相交处两侧有变形的鸟首,鸟喙朝下。人体圆柱下端展宽为臀和下肢,双脚站在三角插座上(图一三,5)。另一件上部为身体被拉长的神人,头戴柱状圆帽,双手被怪兽撕咬。圆柱肢体下部展宽为臀,下肢岔开,站在圆柱銎上。高16.5 厘米(图一三,6)在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一件(5.2012),结构复杂,上部神人头戴梯形圆帽,环眼,双耳为两个张嘴的怪兽头,拉长的圆柱肢体叠置了3 具浮雕兽面,双手抓着怪兽颈部。怪兽与人体相交处有一对下垂的鹰头。下肢臀部为对称的牛头怪兽,前肢抓着张嘴怪兽的颈部,双腿岔开,站在圆柱銎上。高22.3 厘米(图一三,7)。
三、杆头饰的起源及功能分析
以往学术界对杆头饰的来源众说纷纭,大多数学者认为此类器物与斯基泰人关系密切。上世纪90 年代,有日本学者认为,杆头饰可能源于中国商代的杆头铃考虑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出土兵器确有附加铃首、兽首、或在容器底部附以铜铃的现象,但杆头饰源于商代的说法还缺乏证据。
公元前一千纪前半叶,杆头饰在东起西伯利亚、中亚到北高加索、东欧草原的广阔区域内开始流行,在西亚、伊朗高原和中国北方长城沿线也出现了此类器物,此时恰恰是斯基泰文化形成并快速扩张期,这绝非巧合,二者之间应有内在的联系。公元前3 世纪前后,随着斯基泰文化的衰落,杆头饰也最终衰亡,但在继起的萨尔玛特文化中还有部分孑遗。
在黑海周边,杆头饰的出现可追溯到前斯基泰时期。北高加索库班文化的牛首杆头饰出现在公元前两千纪后半叶,属青铜时代晚期。在土耳其哈图沙附近的阿拉卡·休于克墓地出有牛或鹿造型的杆头饰,年代为公元前2400 年,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北高加索迈科普文化的牛角杖首早到公元前3000 年前后,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库库廷-特里波利文化的陶塑杆头饰为公元前4000 年前后,属铜石并用时代。可见,杆头饰最早出现的地区就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北高加索和东南欧一带。
库库廷-特里波利文化的彩陶牛首杆头饰已显现出作为权力象征或仪式用具的雏形。公元前3000 年前后,在迈科普文化的大型冢墓内随葬有纯金和白银打造的圆雕公牛杆头饰,极为奢华,其功能亦不言自明。公元前1500 年,希腊狮鹫勇士墓出土的牛头杆头饰被认为是墓主生前使用的权杖。在蒙古高原图瓦1 号王陵内不仅随葬有一件权杖,同时还随葬有一组五件大角羊青铜杆头饰(图一四)同样也具有昭示墓主身份和权利的意图。

图一四 图瓦1 号王陵出土的杆头饰和权杖
在土耳其阿拉卡·休于克墓地发掘的14 座高等级大墓中,多数随葬杆头饰,有的墓内还随葬金柄权杖这些杆头饰普遍采用工艺复杂的失蜡法铸造,造型各异,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准,而且每墓仅有一件,无论男女,显然也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国外有学者对这批杆头饰的用途做了推测性复原,再现了阿拉卡·休于克一位君王下葬的场景。人们将先前葬有王后的墓穴打开,准备将刚去世的国王并穴与之合葬。墓穴上方搭有大帐,帐顶横置的木架上安有多个“太阳圆盘”杆头饰。国王棺床四角的木柱上安置有牝鹿杆头饰(图一五)。
以上画面仅为推测,杆头饰是否如此使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此复原图确有与考古发现不相符之处。在阿拉卡·休于克发掘的14 座高等级大墓中,仅有3 座未随葬杆头饰,其余11 座墓各随葬一件但在此复原图中,一座墓便使用了多个杆头饰。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安置在帐顶和棺床四角的杆头饰仅供仪式过程临时使用,并非全都随死者葬入墓中。
根据考古发现,杆头饰在其出现之初已彰显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功能,甚至扮演与权杖类似的角色,这在前斯基泰时期的北高加索地区表现得尤为充分,如在某些社会高层人物的墓中随葬金质或银质的杆头饰。进入公元前一千纪以后,斯基泰文化迅速崛起,杆头饰开始成为这个驰骋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标志,并在重要的仪式活动中作为仪仗用具。大量杆头饰的禽兽动物躯体被设计成铃铛,或设置有佩挂铃铛、璎珞或流苏的圆环,目的就是在使用时可发出声响,以声色强化仪式感,使参与者兴奋的神经被迅速调动起来。根据北高加索等地的考古发现,早期杆头饰的杖柄长约1 米左右,晚期加长到1.75 米
中国境内的杆头饰集中出现在春秋时期,最晚延续至汉,与斯基泰文化基本共始终,且主要流行于北方长城沿线,显然与斯基泰文化的东传关系密切。而北方长城沿线的杆头饰出现时间又明显早于四川和云南,后者应是草原文化沿青藏高原东麓逐步南下影响的产物。

图一五 阿拉卡·休于克(Alaca Höyük)杆头饰推测复原图
另一方面,考虑到在殷墟等地发现一种牛角造型的铜器,其造型和结构与杆头饰类似,在新疆西部的特克斯县曾出有牛头和牛角造型的铜器,在空间上将殷墟与北高加索的类似遗物串联起来,暗示这种牛角造型的铜器在前斯基泰时期就已经东传,并在商代晚期的王畿之地出现了类似仿制品。但此类器似乎延续时间很短,影响范围有限。到了西周早期,出现了一种鸭头(或鹅、大雁)造型的杆头饰,并用于一些身份地位较高的人物墓中,明显具有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功能但此类器与典型的斯基泰式杆头饰造型迥异,本土因素更为强烈。
随着斯基泰文化的扩张,杆头饰从黑海沿岸和北高加索传入中亚、西伯利亚以及中国的西部和北方长城沿线,继而沿青藏高原东麓影响到中国西南地区。杆头饰的造型共性很强,地域色彩也非常鲜明。在黑海沿岸和北高加索,早期多见牛、鹿一类食草动物的造型,或为写实的牛头,或为抽象的牛角。晚期动物种类增加,并出现格里芬有翼神兽或神人的造型。在中亚草原和西伯利亚地区,杆头饰以驯鹿或驼鹿的形象最为常见,再就是长有大角的北山羊一类。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鹿和羊仍较多见,还有牛、马、驴等家畜及少量的熊、虎、刺猬等野生动物以及鹤与鹰等。在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盐源不见野生动物,云南则流行禽鸟,如鹰、凤、孔雀及鹤、雁等涉禽,也有少量的野生动物,如鹿、豹、兔和鼬等。不难看出,杆头饰的动物种类往往与所在区域的野生动物分布趋于一致,显示出此类器在东传过程中不断融入地方元素并本土化的大趋势。
注 释
① Andersson, J. G. 1929,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en,BMFEA,No.1, Stolkholm.
②Andersson, J. G. 1932.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BMFEA, No.4, p.221, Stolkholm.
③Andersson, J. G. 1933, Selected Ordos Bronzes, BMFEA,Bulletin No.5, P.143, Stockholm.
④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 1993 年1 期。
⑤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编:《萌芽成长融和——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臻萃》,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2 年。
⑥郑绍宗:《略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青铜牌饰》,《文物春秋》1991 年4 期。
⑦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编著:《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⑧青海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 年4 期。
⑨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湟源县博物馆:《青海湟源县境内的卡约文化遗迹》,《考古》1986 年10 期。
⑩卢耀光、李国文:《大通上孙家寨史前时期墓地》,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再现文明-青海省基本建设重要发现》,201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