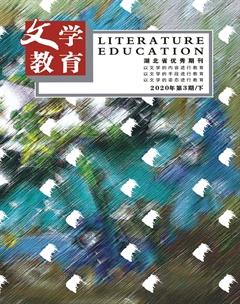论戴小雨《农历才是历》中的家园意识
黄鑫明 雷霖
内容摘要:《农历才是历》又名《又见满田黄》,是戴小雨以农历廿四节令作为叙事轴进行创作的一部中篇乡土小说。小说描写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物质上的乡村,而是一个精神栖息的家园。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和故事整体呈现给我们的正是当代农村的各种小人物在乡村凋敝的现实环境中的坚持与守望、迷茫与失落、挣扎和无奈,从多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当代农村的生态现实和环境挤压和异化下的普遍的人类性。
关键词:《农历才是历》 诗化现实主义 叙事时间 家园再构 家园意识
戴小雨是湖南沅陵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具有浓厚的乡土情怀,近年来由于小说集《农历才是历》受到学术界关注。但目前对他小说的评论并不多,既有的评论多集中于对其小说中家园意识的解读,而对《农历才是历》中独特的叙事艺术及其价值研究甚少,故笔者试图从非典型城乡二元对立、诗化现实主义、时空叙事三个角度对其叙事艺术特色及价值进行研究。
一.非典型城乡二元对立下的家园再构
《农历才是历》这部中篇小说原来的题目叫《又见满田黄》,家园意识的表达是小说的核心所在,但该小说的家园意识不同于传统乡土小说的家园意识,小说中弱化了城市这一背景,消弭了城乡界限,冲破传统乡土小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性,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叙事框架,更多的体现为城乡界限消弭中的家园意识。乡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与城市对立的现实乡村这一概念,不再只是拘束于逐渐破败土地,更是被无限延展的一个理想中的精神家园。其笔下既书写了现代文明对地域化文化的冲击,城市化背景下逐渐凋敝的乡村。展示了破败的现实环境中农人的迷茫与失落、挣扎和无奈,从多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当代农村的生态现实和环境挤压和异化下的普遍的人类性。但更强调少数人对土地的精神层面的一种特别的坚守和眷恋。土地不仅仅是生存家园更是千百年来人们的情感家园。《农历才是历》真实地记录了一群老农地精神诉求——当家园开始荒芜所有人都在逃离,依然有一群人在坚守。因为对他们来说或许生存在何处都可以得到满足,但灵魂只有土地才能安放。这么一种由现实到理想精神层面的拓展,使乡村不再局限于现实乡土而是扩大为无限延展的精神家园,土地所代表的不再只是物质生命还是一个理想化的灵魂栖息地,呈现出对传统家园概念的再构。
二.诗化现实主义下的家园再构
“诗化现实主义”是一种基于社会转型时期物质文明高度且急速发展之下艺术创作的新尝试,要求人们立足且关注当下,不断思考自身处境及命运,改变自我生存处境。[1]p72-73
小说采用诗化现实手法,创作基于乡村但不临摹乡村,强调在基于现实原貌的基础上结合儿时记忆,以温暖的笔触生动的细节描写,赋予“乡村叙事”以现场感,将他所感知联系环境并赋予那些自然与物事相应的感知。 基于这一手法使原本看似平常的乡村景象因诗性的叙述而具有了美的气质与韵味,以温暖的笔触再现了记忆中美丽的乡村,突破了传统之下在破败中悲痛,开辟出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在美好中惋惜。这种描摹既是对作品环境的刻画亦是对作品主题的有力支撑,这一点与俄罗斯诗人叶赛宁诗歌化的故乡不谋而合。
(一)“化荒为美”现实的诗意转化。环境,是作者为小说人物性格塑造和情节遵循生活逻辑发展而创设的场景和背景,但也是创作者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对戴小雨而言《农历才是历》与其说是创作,倒不如说是借田生老汉的嘴诉说着他眼中逐渐逝去的故乡——沅水截留,打工潮兴起,家园逐渐破落。社会革新是必然趋势,但旧的在不断被抛弃,新的又无法生根,故乡不见了,城市又无法扎根,到哪里都是游子,到哪里都无法安家。所以在他的《农历才是历》中充斥着因这样的矛盾而让人生出窒息的痛楚。但作者并没有采用直接冲突的方式去刻画逝去的家园,他不想再给本就破败的家园增添更多的伤痕,于是他用诗意的语言塑造了不同以往的乡村,“那满田遍坎恣意疯长的野艾蒿与狗尾草在瑟瑟秋风中轻舞飞扬。屋前的草浪一阵又一阵。”[2]p92-93乡村在他诗意的语言中得到了清晰而真实的还原。但他也没有过度美化荒废的家园,戴小雨说过:我是把语言当小说内容来写的。他笔下的一切美都是真实乡村的样貌,只是美的过于凄凉,”“冬天漫长而沉静,整个南木村好像没有生灵活动的迹象,只能从傍晚时分那几束斜斜的炊烟判定这个村落里还有人迹。一切都是那么悄无声息,就像生活在深水下的鱼类,任凭水面海浪滔天,船来船往。田生老汉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什么……日子,单调而落寞”。这些极具真实性的描写使得小说读起来质朴亲切,一样的环境,一样地离开和坚守,让那些有过农村生活体验的人都仿佛置身其中。田生,春,皮草鞋,刘安福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只是他们的故事被讲述出来了而已。
(二)“以梦为实”记忆的溫暖再现
戴小雨小说《农历才是历》中的乡村不同于往常乡土小说中的喧嚣破败,依然是安静和美丽的。那份美丽来自天然,也来自作者记忆深处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作者更通过独特的温暖化笔触交织着记忆和现实。小说写在当下,但却是建构在记忆中的美好,这是创作中的不自觉也是不可避免地。那不断上涨的潮水,肆意飞扬的野花,荡漾在心间的满田黄都是只存在记忆中不可追回的存在,但农民出身的他不忍直面现实破败,依然用温暖的笔触来包裹现实的残酷,以至于有时候作者也分不清笔下的乡村到底是儿时的家园还是现在的土地。但就像他说的那样“生命再难也要有温暖,乡村的衰败不可避免,但我的乡村,我的邮票我生命的温暖永远停留在那里,这是不管社会怎么变迁都不会改变的“也许现实的家园在破败,但我们依然需要为自己构建一个美好的精神栖息地。
三.时空叙事下的家园再构
时空叙事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小说以农历廿四节令作为叙事轴进行叙述,不同于以往的乡土小说对土地家园凋敝的直接描绘,这部小说中时节作为故事启承传合的内驱力,巧妙地将光阴流失,生命盛衰,寓于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中,通过节气的轮回反映乡村当前真实的生存状态,并通过塑造田生老汉和春等乡村留守老人的人物形象,以一群年迈之人重新种活葫芦丘为目标,诠释了一个热爱土地的老农民丰富浓烈的心灵空间。展现出他对土地那份热爱与坚守,同时也表达出对于故乡破败,家园不可寻的惋惜。
(一)灵与肉的冲突
春耕秋收是乡村亘古不变的模式,一部农历不仅指导者农民耕种更是其精神的依托。但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深刻改变了传统乡村,改变了农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现代技术将耕种从季节中剥离出来,时间变得似乎不再重要。土地不再承载生命而乡村也不再使人眷念。灵魂与肉体就此被割裂开了。但只有田生知道这二者是分不开的,他出生在这片土地,他的一切都扎根在这片土地。就像中文写的那样“春的世界就像洗衣潭的那潭水,起风或用手去拨它才会动,更多的时候都是静静地躺在那儿。浑了,不知道水有多深;清了,可以照得见人。[3]p82-83这四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田生老汉就是在这潭水面前激励与欣赏自己。”面对着“进城潮”两个老人执拗的像战败的士兵,即使看不到希望也要固执的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也许年迈的肉体可以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苍老的灵魂却无法离开,或许生存在何处都可以得到满足,但灵魂只有土地才能安放。《农历才是历》其标题本身就是对土地带来的原始生存方式的一种坚持。时令与季节的交替轮回,不仅仅是作用着农业生产更暗示着光阴流失,生命盛衰。田生老汉和春是这片土地最后的坚守者,他们执着的不仅仅是生养他们的水葫芦田更是早已扎根不可离去的灵魂。
(二)守与弃的抉择
自我挣扎的心理斗争是小说的一大特色。立春时突如其来的再耕种一次的想法,雨水时极力劝说好友的渴望,大暑时因米米意外离世的绝望,立冬却迟迟不见雪的颓废和在下一个冬天的再次起航。小说以时节为线索基于环节描写描绘了田生复杂的心里斗争。心理描写离不开环境塑造,戴小雨笔下的乡村不同于以往的热闹的乡村,戴小雨塑造的是一个宁静祥和的乡村。喧闹热烈会勾起人们的向往,而安静到近乎孤寂的乡村勾起的则是无限的感慨和追忆。曾经鸡鸣狗吠,蝉鸣蛙叫的乡村如今人烟稀少,没落被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了面前,这对依然坚守的人来说是一种渗入骨髓的悲哀和茫然。在这么一种深入骨髓的寂静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坚持不住开始逃离,越来越多的场景开始模糊,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向城市靠拢,甚至就连曾经一起在水葫芦田战斗过的皮草也要离开,“仙优六号”已经被更先进的种子取代。工业化浪潮改变着乡村人民的生活状态的同时也改变了乡村的命运。一千多年来南木村人口从来没有低于500口,但就在几十年之间人口一下子骤减至六十来口。曾经最肥沃的水葫芦田也被荒废,哪怕犁了四五遍也还是像沙一样《农历才是历》中田生老汉与春执拗的坚持与守望,皮草鞋的挣扎与无奈都真实的展现了当代乡村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乡村在城市的挤压下的无路可逃。刘安福家的悲剧,米米的离开更是给无可奈何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老友们纷纷离去就好像当初青年人离开一样,他们无可奈何但又别无选择。
田生的挽留与抵抗在社会变革面前显得那么无力,不断寻找的同时也在不断失去,不管再做多少挣扎所有的楠木村迟早都会衰落以至于最后消亡。但田生用再一次的满田黄做了一场悲壮的告别,孤独的将军站在城墙上挥舞着大旗,也许下一波敌人的进攻他就会倒下,但他依然坚守着最后的家园。看着眼前他所熟悉的乡村一步步的凋谢,在他眼里陌生的钢筋和水泥构筑和的城市又如此荒诞,也许终有一天田生老汉也会坚持不注,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有多少“敌人”,那些敌人究竟又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也许某一天当他站在仅存的家园上回望过去,家园已成一片废墟。也许在社会变革中,乡村家园的失落是一种无可避免,但当构成特定的地域文化的各种因素平衡丢失,模糊,破碎甚至趋于消亡之际,总有一些人因漂泊而找不到灵魂的归宿。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去建设这个世界,回过头却发现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找不到自己的家,偌大的世界哪里才是家园?在历史的演进中独行者往往更能体现出悲哀,因为被人遗忘的代表的是无人记忆,而不被人遗忘却又不可追回的才是最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家园已经坍塌,再多的回首也只能望见一片废墟。
结语:在田生老汉看来,只有土地才是家园。当乡村逐渐破败,所有人都在逃离,田生却对荒弃的田地念念不忘,这是根植于血脉中的眷恋,他固执地选择留下来,他走不出季节更换带给他的生命悸动与愉悦。
对农民来说追随农历进行耕种是生命的自然舒展,对作家而言农历背后所代表的是乡土与家园这一创作母题,撰写乡土是他们对当下浮躁社会家园逝去的惋惜,而对于向像戴小雨这样本就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人,乡土文学的创作便是其坚韧生命的最好绽放。戴小雨认为自己就是一株冬小麦,大雪是他的被子。“有时候也会觉得孤独寒冷,可想起母亲那句话,雪落得越大,麦子就越青绿,心里就会温暖开来,在雪后的坡地慢慢生长。”是的,戴小雨出生在一场扑天盖的大雪之中,用他的话来说那场雪盖住了乡村的麦田,但怎么都盖不住他那嘹亮的啼哭,他的哭声嘹亮而具有穿透力,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横冲直撞,穿越麦田厚厚的积雪,栖落在瘦弱的麦芽上。他不自认为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自己没那么伟大,他只是一株脆弱而坚韧的冬小麦,在合适的季节被播种在这篇大地上,慢慢发芽,抽穗,扬花,饱满,再以沉甸甸的果实反馈这篇生养他的土地,他用乡村的诗意构筑“生命最原始的母语空间”,用一株冬小麦的眼光留下最后的家园,仅此而已。
讲故事的人往往是故事本身,戴小雨作为乡土作家正如他笔下的人物一般始终执着于乡村。哪怕乡村逐渐荒凉,那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故乡。戴小雨忘情叙写着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笔端流淌着悲凉。笔下的所有一切人物都寄托了作者对故乡土地远去的悲凉感。
参考文献
[1][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2][3]戴小雨.農历才是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作者介绍:黄鑫明,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本文为作者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校级项目“沅陵籍作家群的乡土叙事研究”的结题成果;雷霖,文学博士,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地方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