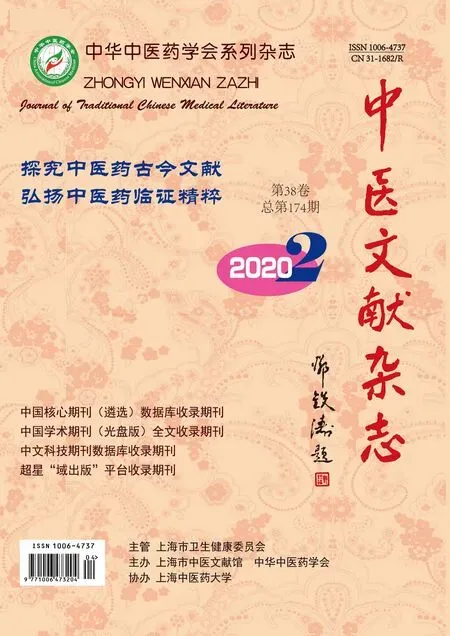北京地方志医学资料挖掘浅析*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医治病强调因地制宜,医学从而具有了地域性。研究地方医学,对于推动医学发展具有实际意义。北京作为六朝古都,亦是全国医疗水平的代表,研究北京医学的历史文化,探讨影响北京医学发展的各种因素,可从根本上推动北京医学的发展,亦可为全国各地医学研究提供借鉴。
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其所含医学资料是研究地方医学最贴切的材料。目前,北京现存地方志多为明清及民国时期所修。本文选取记事涵盖时间较长、收录资料较多的13种北京地方志,包括《康熙大兴县志》《康熙宛平县志》《康熙怀柔县新志》《光绪昌平州志》《光绪昌平外志》《光绪延庆州志》《光绪顺天府志》《民国密云县志》《民国顺义县志》《民国通县志要》《民国房山县志》《民国良乡县志》《民国平谷县志》,对其中的医学资料进行挖掘,发现涉及太医院、官办医药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医家、流行病、土产药物、药王庙等内容,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太医院
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自周代已有,唐代为太医署,宋代为太医局,金代始称太医院[1]。因为统治者对医药的重视,太医院的地位曾在元代达到顶峰,后随着清朝统治的衰微而没落。
北京地方志中关于太医院的记载,涉及机构位置、官设、职能、制药、医学教育、医药祭祀等。《光绪顺天府志》卷七“京师志七衙署”载:“太医院使一,左右院判各一,掌医之政令,率其属以共医事;掌九科之法以治疾;掌灸制之法以治药。教习二,简能者任之。”[2]由于清政府强化对太医院的控制,太医院的职掌受到削弱,其对地方医药机构、御药库等并无管辖权力。其次,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太医院所设科目由十一科缩减为九科,包括针灸科的废除[3]。《康熙大兴县志》卷一“舆地篇古迹考”载:“古铜人,太医院内,相传海中潮涌出者,虚中注水,关窍毕通,用以考验针灸,古色苍碧,其光莹然射目。”[4]《光绪顺天府志》卷七“京师志七衙署”载:“药王庙神像前铜人像,始作于宋天圣时,元至元间修之,明英宗时又修之,三皇庙内有针灸经石刻,明时重摹上石者。”[2]此针灸铜人即为仿天圣铜人所制成的正统铜人,因八国联军战乱,现流于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正统铜人是《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文本的权威解释,对于针灸史和针灸教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5]。此外,还有关于太医院制药的记载,《康熙宛平县志》卷一“地理篇古迹”载:“端午日,太医院捕虾蟆海中,刺其眉棱,取蟾酥例也。”[6]
太医院作为全国医疗水平的代表,目前关于其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主要引用实录、会典、史稿、档案、《太医院志》等材料[3],地方志可作为补充及参校资料,充实完善太医院的研究。
官办医药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
明清时期,地方医药机构荒废。政府为加强统治,下令在地方修建福利机构,如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等,有些机构兼以提供医疗服务。北京地方志中关于社会福利机构的记载,详至机构位置、修建、规模、运营等。《光绪顺天府志》卷十二“京师志十二厂局”载:“京师广宁门外,有普济堂……其有疾者,药之养之,分医以治而稽其事。病各有坊,疕者,疡者,遘四时疠疾者,彼此异区不相乱。死则蔽以棺……圣祖仁皇帝赐之碑额……”[2]政府虽下令修建社会福利机构,但少有财政支持,更多的是靠地方官绅捐建,且没有过多地参与管理[3]。明清政府在地方医政上的作为仅限于疫病赈灾,并通过社会福利机构来实现,而对于百姓的日常医疗需求并不理会。社会福利机构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但毕竟非专业医药机构,在解决基层医疗问题上,可谓杯水车薪。
医 家
北京地方志中关于医家的记叙,可分为太医院医官及民间医者,涉及从医经过、医疗事迹、医学著作等,且注重对医德的记载。《康熙宛平县志》卷之五“下人物貤封”载:“国朝,章时震,号龙门,宛平人,生而孝友淳笃,读书尚论千古,不屑为儒生章句。少多病,遇塾师治之,良已,因请其术,遂旁通岐黄家言。虽历官太医院,非其志也,惟济世活人差慊于心。”[6]太医院医官因其服务对象为皇族的近侍衙门属性,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医技高超,另一方面,他们又承受着患者主导、制度繁复、地位不高、待遇较差等各种压力,可以说远高于今天从医者所面对的压力。研究医官的从医经历及医疗事迹,对于今天从医者的医术及医德的培养亦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志中的民间医者虽多为正史所未记载,但对地方确有重要的医学贡献。《民国通县志要》卷八“人物志孝义”载:“滕致祥,致祥字瑞轩,清孝廉,性纯笃,以孝友称。母病,祷天愿以身代,果愈……精医学,著有《奇症医案》、《妇科准绳》二书,卒年六十四。”[12]地方志中的医学著作可补充现有医学著作,如郭霭春编写的《中国分省医籍考》。
太医院医官的来源主要是医官子弟保送或者征召地方良医[3],是宫廷医学与民间医学融合的体现。宫廷医官与民间医者的结合研究,对于燕京医学的源流考究具有重要意义。
流行病
明清时期疫病多发,北京地方志中以时间为轴线记载了疫病的发生。《光绪延庆州志》卷十二“杂稽志祥异”载:“神宗万历……十年春,大疫”“庄烈帝崇正……十七年春,大疫”“嘉庆……七年,大疫”“道光……十三年春,饥瘟疫流行”“同治二年六月,大疫。”[11]
北京地方志关于疫病的记载显示,疫病的发生多与虫害、水涝、饥饿和干旱等因素相关,且发生时间多为春夏之季。关于疫病的记载列于灾异、祥异等类目下,反映了此时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仍带有迷信色彩。《光绪顺天府志》卷六十九“故事志五祥异”篇记载,崇祯十六年“昌平大疫,十月巩华城群鬼夜号,月余乃止。”[2]
疫病泛滥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以及“父子相食”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北京地方志中记载了政府对于疫病采取的相关措施,包括瘗葬死者,施药赈济等。《光绪顺天府志》卷六十六“故事志二时政下”载:“同治元年……七月庚寅京师疫,发给广储司实银二千五百两,分交五城祗领。选择良方,修和药剂,于五城内外坊地面分段设局施放。”明清疫病的多发为温病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结合自然环境及社会因素,研究地方流行病的发生原因,借鉴当时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医学的相应发展,对于当今流行病的防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土产药物
1.涉及内容丰富
北京地方志中关于药物的记载一般列于物产类目下,内容涉及药名(详至来源)、别名、植物、生长、鉴别、入药部位、炮制、性味、质量、产量、主治、禁忌等。如《民国房山县志》卷二“地理篇物产植物药类”载:“天南星,一名虎掌,因叶形似,非根也。南星,因根圆白如老人星故名。九月采,根苦温有大毒。李时珍曰:味辛而麻,故能治风、散血气;温而燥,故能胜湿、除涎;性紧而毒,故能攻积、拔肿而治口涡舌烂。”[13]
对比不同时期所修北京地方志,可发现其中药物记载的变化。从体例上来说,康熙时期所修地方志对药物的记载一般较为简略,仅有药名,光绪后所修方志内容较为详细。其次,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地方志所修内容详略亦有不同,从中亦可体现出地方官员对其重视程度的不同。从药物来源范围来说:早期地方志中药物来源范围较为狭窄,对于蔬属、果属、虫属、禽属等类属中可入药的物种收入较少;后期方志的药物来源明显增多。此外,对比同一地方不同时期的地方志对于药物的记载可见,同一药物的药名发生变化,药物的种类亦有增减。如《雍正密云县志》卷一“物产篇药类”中有“麝香、熊胆、鹿茸”[14],《民国密云县志》中已无相关记载。对此可结合地方环境变化、疾病、医生的用药情况等对北京土产药物发展史进行研究。
2.引用材料详实
北京地方志中关于药物的记述不乏各种材料的引用,包括:辞书,如《尔雅》《说文解字》等及其注疏;医学著作,如《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虞搏医学正传》等。利用材料对药物进行考证,如《光绪昌平外志》卷五“新志校勘记物产志校勘”载:“瓯李,案《诗经·豳风》孔颕达疏:薁即薁李。字典:薁亦音奥。陆玑《草木虫鱼疏》:唐棣,奥李也。《论语朱注》:唐棣,郁李也,非瓯李。”[15]是清代考据学在中医药方面应用的体现。对于考证无果的情况,如《民国房山县志》卷二“地理篇物产”载:“瘦骨草,旧志载之,未知其义,或即透骨草之误,或另有所据,姑存待考。以上四十九种皆载旧志者,今略加解释以明其用,挂漏舛误待正后贤。”[13]体现出修志者的严谨。地方志中所引用的材料可作为相应著作的校对材料,对于旧志文本破损的情况,还可利用其它时期的地方志进行补充,地方用药习惯可补充同一时期本草著作的不足,医者论述的引用,如李时珍、陶弘景、陈藏器等,亦可为研究医者学术思想提供材料。
此外,土贡类目下有关于进贡药材的记载。《光绪延庆州志》卷三“赋役志物产”载:“每岁甘草一百五十觔,黄芩一百五十觔,苍术一百觔,芍药一百觔,每岁杨木长柴八十觔,后改折色,按土贡旧志所载。”[11]进贡药材一般质量上乘,这些内容可为道地药材的考究以及宫廷药物来源的研究提供材料。
药王庙
药王庙源于三皇庙。元代皇帝曾下令全国通祀三皇。到了明洪武初期,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下令天下郡县不得亵祀三皇。嘉靖年间于太医院内建成三皇庙(即清代先医庙)。而民间祭祀三皇的习惯形成已久,遂将地方三皇庙改名为药王庙[16]。药王庙的修建在明清达到鼎盛,民国时期逐渐衰落,文革时期遭到破坏,且随着科学思想的传入,其所形成的药王庙文化亦逐渐不为人知。北京地方志中关于药王庙的记载涉及分布、供奉人物、庙会等。
1.分布
据地方志所载,北京药王庙的分布,市内主要有北药王庙(旧鼓楼大街北)、南药王庙(崇文门外东晓市街)、西药王庙(西皇城根24号)、东药王庙(东直门内16号)[17];市郊区中,房山区2个、良乡区4个、顺义区2个、密云区3个、平谷区3个、通州区8个,且多为明清时所修。有学者调查显示,北京药王庙现今境遇惨淡,平谷药王庙、丰台药王庙、密云古北口药王庙尚存,南药王庙还存在主体建筑,而北药王庙、西药王庙、门头沟药王庙皆无建筑。而有的药王庙在当今仍然发挥着社会救济的作用,如平谷药王庙[17]。
2.供奉人物
药王庙中所奉人物随时间和地区而有所不同,以孙思邈和韦慈藏居多[16]。《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京师志六祠祀中”记载先医庙中供奉人物为“正中奉太昊伏羲氏,左炎帝神农氏,右黄帝轩辕氏……”[2],其余为历代名医。《光绪顺天府志》卷二十三“地理志五祠祀上”记载通州药王庙为:“供二神,曰药王,曰药圣,传是唐人韦公慈藏、孙公思邈。”[2]密云药王庙“供奉有十二位神仙,主供药王孙思邈”[17]。孙思邈为隋唐医家,而明清药王庙中多将其奉为药王的原因,与其传奇的生平经历及医学贡献有关,加上后世对其成就的不断烘托,使其“药王”形象深入民心[18]。
3.庙会
《光绪顺天府志》卷三十一“地理志十三风俗”载:“二十七八日,城内外四处药王庙,有庙场香会(《通州高志》),男女上庙进香,络绎于道。”[2]药王庙会多在每年的四月二十八日,一般认为是药王的诞辰。庙会时长1到7天不等,庙会期间的活动包括病家祈愿、药材买卖、医家义诊,还有戏曲娱乐活动等,形成了丰富的药王庙文化。另外,药王庙会促进了药材贸易,推动了药材经济的发展,如安国、樟树、亳州、禹州四大著名药都的形成和药行的出现。《光绪顺天府志》卷十四“京师志十四坊巷下”载:“兴隆街,井一有准提庵药行会馆”[2],《民国房山县志》卷五“实业篇商业”载:“药行,本城六,石窝三,长沟二,石梯二,灰厂一,周口店一”“药行,恒隆泰,南永和,北永和,广和兴,裕生泰”[13],可为中医药老字号的源流考究提供材料。药王庙会推动了地方药材经济的发展,亦促使药商对药王庙进行了大量的修建和庙会的维持。另外,地方官员对药王庙会的重视亦能体现在地方志中关于药物的修撰。
明清药王庙的大量修建是明清医疗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医疗文化现象,与疫病多发、地方医药资源贫乏、庸医泛滥等因素有关,是百姓在求医无源的状况下,转求于信仰以解脱的医疗心理体现。
小 结
除上述资料外,北京地方志中的医学资料还涉及地方医俗。《光绪顺天府志》卷十八“京师志十八风俗”载:“五月五日,渍酒以菖蒲,插门以艾,涂耳鼻以雄黄,曰避毒虫。家各悬五雷符。簪佩各小纸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项各彩系,垂金锡,若钱若锁者,曰端午索。”[2]医药遗迹,《康熙宛平县志》卷一“地理篇古迹”载:“仰山……传有药王、药圣、童子炼药山中,药碾、药池犹存。”[6]地方志非专业医学著作,且其所含医学资料分布零散,故常为医学文献研究所忽略。而地方志中的医学材料为正史所少有,其涉及范围广,内容丰富,具有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的特点,是研究地方医学的重要材料。通过对北京地方志中的医学资料进行挖掘,可为北京医学研究提供史料,进一步推动北京医学的研究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