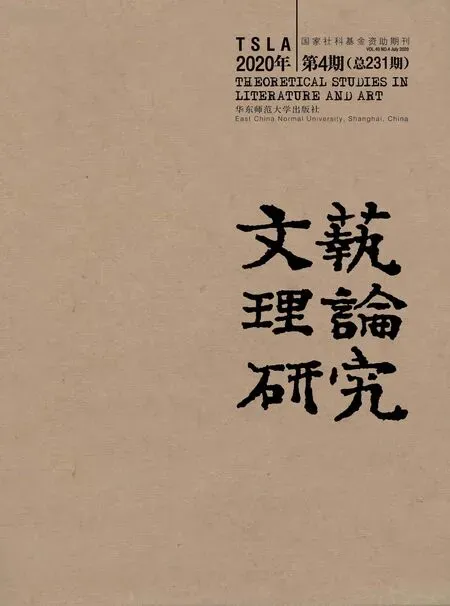从文本到世界: 一种方法论的探索
——贝尔唐·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 真实、虚构、空间》评介
高 方 路斯琪
引 言
在全球化进程日渐显著的影响下,当今世界的再现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如何重新理解与阐释变动不居的人类生存空间成为学科交汇的研究热点。面对新变化,立足于后现代语境的地理批评在对文学与世界、人类与生存空间关系的探索中应势而生。受“地理哲学”“空间转向”等理论思潮的影响,法国利摩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贝尔唐·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于1999年首次提出地理批评概念。次年,由韦斯特法尔主编的《地理批评使用方法》论文集问世。收录于该书的《走向文本的地理批评研究》被视为韦氏有关文学空间理论的奠基之作和地理批评的诞生宣言。2007年,他的力作《地理批评: 真实、虚构、空间》由法国子夜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学界对以地理为导向的空间批评研究趋势的关注和思考。这部旁征博引的论著不仅进一步完善了作者对地理批评的理论设想,系统阐述了地理批评的三大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对空间的建构作用,让世界因具有文本的可读性而得以被更好地理解。作为一种比较研究方法,地理批评以场所为切入点,“通过文本、图像以及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互动来深入研究模仿艺术所布置的人类空间”(Westphal,LaGéocritique17),多维考察不同再现形式对指涉对象产生的影响,勾勒出由点及面、从场所到地球、自文本空间向世界空间辐散的互文场域。这种研究路径既有助于丰富和保留地方文化记忆,还对探索多中心而非单一等级秩序的世界文学构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为更好厘定地理批评的概念来源、研究路径和方法,本文拟对《地理批评: 真实、虚构、空间》进行评析,以比较和拓展的眼光来审视该理论所具有的创新性、探索性与启发性。
一、 地理批评: 起源、发展与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改造能力与日俱增,世界面貌不断革新,空间格局瞬息万变。身处流动性、异质性和分裂性愈发凸显的后现代空间,人们一边应对因真实感模糊而带来的感知困惑,一边重新思考理解世界的方式。近二十年来,面对世界再现的深刻变化和由其引发的感知差异,众多学科都在自身领域展开了对地球空间的新阐释。“地理学家研究地球,社会学家亦然,人类学家、法学家等也不例外。那文学工作者呢?他们的世界是怎样的?”(Westphal and Moura 171)在对问题答案的探索中,韦斯特法尔开启了有关地理批评的最初理论构想。自20世纪90年代起,韦氏开始着手环地中海地区场所再现的考察。由于缺乏相应理论支撑,他选择采用对比方法,将每处场所置于互为对立的方位关系和时间关系中,从不同学科和媒介的视角得出有关场所再现的多元观点,并发现每一部涉及研究场所的独立作品都会呈现出该场所在某方面所具有的特性。问题由此而来:“如果把与同一场所相关的不同虚构观点联系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结果?”(Westphal and Moura 173)有别于以往围绕作家创作展开的“自我中心”(égocentré)研究路径和将场所作为空间背景的文学地理研究方法,韦斯特法尔以“地理中心”(géocentré)为指引,将被置于多重视阈交汇中的场所再现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探究“不同虚构再现对指涉对象和‘现实素’(réalème)所产生的影响”(Westphal and Moura 173),辩证地思考后现代语境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及文本之于世界的意义,逐步生成地理批评的理论思路。此外,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有关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生产方式的论述以及德勒兹(Gilles Deleuze)、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围绕空间运动发展的地理哲学概念对韦氏所关注的再现与指涉及空间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理论借鉴意义。韦斯特法尔在赴美交流期间对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发起的“空间转向”理论产生浓厚兴趣,走上后现代空间研究道路,并开始《地理批评: 真实、虚构、空间》的写作。此间,他广泛涉猎包含书籍、绘画、电影等在内的文艺领域,完善知识储备与体系构建,使其理论向更广阔的世界视野展开,历经十余年累积,最终完成了这部承载着作者有关地理批评系统性思考的理论著作。

由此可见,后现代语境中的空间与文学并非指涉与再现的单向参照,还维系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模式。首先,文学文本本身可以被视为一个集指示性、象征性和图像性于一体的符号空间,基于符号的可阐释性,文学空间总会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中或在文本以外的空间作用下,超越作家表达意图,形成新的符号空间,使外表看似稳定的文本空间内部不断发生演变;其次,受到二战后时空关系转变的影响和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后现代空间的形态与其表达的象征、隐喻意义同以往相较更加多变、复杂。加之文学再现在文本空间内对真实空间进行重塑,使后者潜在的虚拟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激活,被激发出的虚拟性通过想象和阐释活动进一步创造并丰富了空间再现的形式与内涵,形成文学对空间的反作用。因此,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实际是由文本空间与世界空间两种空间衍生出来的多重空间织就的关系网络,从本质上说,地理批评就是一种有关空间间性的研究,该理论视阈下的文学空间与真实空间的间性问题可被理解为文本与世界、我与他人共享的主体间领域的能动状态。地理批评借人对空间的感知发掘人与世界的关系,并关注上述关系在文学、绘画、电影、建筑等艺术创造行为中的表现。在语料丰富的文学领域,文本的虚构空间不仅使我们获得对真实空间的新理解与新知识,它还参与了世界的建设,让世界化为文本再现的一部分,使其成为具有可读性且积淀了文化记忆的大写之书,并由此构成与文本的互文运动。
二、 空间互动的理论基础
作为当代空间批评的前沿理论成果,地理批评之“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明确地理的导向地位,指出它既是空间研究的新动力与出发点,又是文本改造的对象和落脚点。第二,转变空间研究范式,使其由单一的再现研究走向再现与指涉的互动关系研究。为论证这一空间互动的可行性,韦斯特法尔在《地理批评: 真实、虚构、空间》中首先阐述后现代空间的三大特征: 空时性、越界性与指涉性,通过对二战以后新时空关系的分析,得出空间间性框架下真实与虚构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的结论,并进一步归纳出文本与世界所呈现的互动关系类型及其理论成因。
(一) 空时性(spatio-temporalité): 空间的反击
西方社会经历两次工业革命,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升,时间成为进步的象征,空间沦为可被时间操控的对象。地球经纬线划分和时区的确立宣告整个地球都可以在时间的把控下被精心切分,掌握时间即意味着占有空间,此时的空间从属于时间。两次世界大战打破原有时空格局,殖民空间、种族空间的出现以及空间环境恶化击垮了时间等同进步的信条。在思考如何重新理解历史和解读空间的过程中,人类的时间经验发生了质的转变: 从前代表进步、发展的线性时间逐渐被承载着瞬间体验的时间点代替。这些时间点分散在空间中,“抓住这些点-瞬间,并消除所有的等级化的排序,以致线性消失、分解,摆脱意义和单位的束缚”(Westphal,LaGéocritique31),线的消弭和点的扩张增强了时空相融的感知体验,衍生出新的时间概念,如“微时间”(tempuscule),它被理解为“时间的间隙(特定的Δt),它与指涉的理论背景相比‘相当地短暂’”(Dalla Chiara Scabia 99)。新的时空感知还激发出庞大的时间空间化的隐喻体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分叉”和“熵”,例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小径分叉的花园》让人们意识到空间化可以解构时间的线性,而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以《熵》命名的小说则使熵定律在文学创作中获得广泛应用。此外“通过作品页面的空间符号化来破除叙事直线的文本比比皆是”(Westphal,LaGéocritique40),文本空间中的时间顺序被打破,作品被赋予新的内涵。在时间空间化的过程中,历史也被纳入整体空间范畴进行考察,因为历史本身也是一段空间作用于人的历史。德勒兹高呼生成是地理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断言“20世纪是空间的时代”(Foucault 46),空间从时间中被解放,获得自身的本体论与价值论意义。
自20世纪起,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影响下产生了大规模人口流动。群体性迁移不仅让不同空间语境的交流与对话成为可能,还使从前以文化认同为划分标准的地球空间转变成了杂糅、异质的复数空间。此外,城市化进程加剧创造出以往从未有过的空间景观,如内陆城市的海洋世界、滨海城市的沙漠景观以及梦幻的迪士尼乐园等,以致现代空间被不断分割成虚实相交的更小空间,“空间增多,分裂成块,变得多样化。今天的空间有着适应各种用途和功能的一切尺寸与类型。活着,就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并尽力避免撞到自己”(Perec 14)。空间地位提升及其本体性、异质性和多样性增强,使它在文学、地理、建筑、城市规划等学科中的表现尤为活跃。“如果说探索人类空间的可能性是地理学的特性,那么文学也具有同样的特性,因为任何文本都在空间里,文本展开的主题也在空间中进行”(Westphal,LaGéocritique60),具有历史性、文化性以及多样景观的城市空间孕育着丰富的文学主题,历经了空间形态与地理面貌的变化,它“不仅仅是我们圈画在地图上的抽象框架,还是一个文学得以在时间中去探索的思想和情感框架”(Westphal,LaGéocritique60),承载着文化记忆的城市空间成为沟通文本与世界的重要纽带,因此,地理批评将空时性显著的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场所,为探究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地理交错影响下的人类涉足空间与文本空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奠定基础。
(二) 越界性(transgressivité): 从文本到世界的可能
韦斯特法尔认为,后现代时空具有内在的越界性。在法语中,越界一词“最初就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动作”(Westphal,LaGéocritique72),它以界限的存在为前提,动作本身可以是像跨越门槛一样的进入,也可能是一种强行的暴力干扰,还有可能是对规则的抗拒。随着语言的演变,该词又被赋予新的内涵,它不仅体现空间位置的变化,“更多是指违背精神层面的界限,而非物质界限”(Westphal,LaGéocritique73)。如此一来,越界就从形象、易感知的真实空间被延伸到抽象、难以感知的精神空间或想象空间,而这一过渡本身也构成了一次越界。“作为空间任何动态再现(与之相反的是静态再现)的固有属性,越界性原则是大部分专注于宏观层面的空间或空间化思考的文学、符号学和/或哲学理论的核心。[……]如果说时间线性的解构是后现代审美标准的一个元素,对于空间异质性、越界性的感知则是另一个元素。”(Westphal,LaGéocritique79)界限因异而生,并对不同状态进行分隔。因此,在以异质性为标志的后现代复数空间内,越界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不同空间的互动关系亦越发紧密。
空间因越界而流动,呈现出不稳定状态,它的不稳定性又引发新的流动与越界。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越界性既是同质平滑空间与异质条纹空间之间的不断转换,又是解域和结域的空间运动常态,还是促使伊塔马·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形成的动力。该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多层化的整体,在这个整体内,中心与外围是通过一系列对立建立起来的”(Even-Zohar 11)。对立产生界限并引发越界,使中心与外围在互相干扰下生成恒定的越界状态,系统便在此种状态下由单一的同质性走向多元的异质性。尤里·洛特曼(Youri Lotman)尝试从符号域的角度对由越界性引发的空间互动作出解释。他指出“真实空间是符号域的符号再现,一门让非空间意义得以表达的语言,符号域反过来将我们生存空间的真实世界转变为其自身形象的再现”(Lotman 124),该观点设想出“真实与非真实间的交流,甚至是一次真正的互动”(Westphal,LaGéocritique86),这种互动或越界行为发生在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空间。爱德华·索亚曾描述道:“一切都在第三空间相遇: 主观性和客观性、抽象与具象、真实和虚构、可被认知的和难以想象的、重复和差异、结构和布局、精神和身体、意识和无意识、循规蹈矩和越纪逾矩、日复一日的生活和永无止境的历史。”(Soja 56—57)第三空间涵盖了一切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使对立矛盾的事物共存,成为一个在空间上异质、文化上杂糅、与二元对立彻底决裂的新地带,虚构空间与真实空间便在越界性搭建起的第三空间相遇并产生干扰。由此推论,地理批评所探讨的文本空间和世界空间也必然会在越界性的作用下互相进入对方领域。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究竟是文本再现了世界还是世界呈现了文本。正如韦斯特法尔所言,“在后现代的广阔天地下,人们不会再说水泥、混凝土、钢筋搭建的世界比纸和墨水营造的世界更‘真实’”(Westphal,LaGéocritique13),因为越界性关照下的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早已模糊,并在交界地带形成新的空间场所,为文本与世界的互动不断创造可能性条件。
(三) 指涉性(référemtialité): 空间互动的类型
虚构空间既非真实空间的直观反映,也不是对真实空间的简单复制,作为越界的主体之一,它表达真实空间的涵义,参与真实空间的构建。二者不仅维系着互相再现的关系,还可以互为指涉。所谓指涉,即实际的参照。文学中,巴黎、伦敦等文本城市空间指涉了现实世界里法国与英国的首都。真实城市成为文学空间的指涉对象,文本空间则再现了真实城市的某些或全部特征。然而,文学亦会走在真实的前面。尽管古希腊神话中航海英雄们所标识的途经之地都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但是“话语建立了空间”,“词语创造了场所”(Westphal,LaGéocritique134—35),这些纸上的地标形成日后真实世界的地理目录。除此以外,科幻文学与电影对未来世界的某些构想已经变为现实。文学空间转变为真实空间的虚构指涉,而真实空间则将虚构的文学空间再现为事实。从“虚构由真实想象转化而来”到“真实力求再现虚构”(Westphal,LaGéocritique148),这一趋势在后现代城市空间中愈发凸显。游乐园、电影院、度假村成为以真实空间营造虚幻感知的人造场所,真实想象着虚构,虚构亦在改造真实。从空间的越界性看,真实与虚构在第三空间相遇;以真实与虚构的位置关系为尺度,二者则处于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临界界面;若追问包含或反映二者关联的世界的性质,那么,以共同可能性为前提的“可能”(Possible World)世界便成为真实与虚构共存的理想空间模型。
韦斯特法尔指出,可能世界涵盖了真实与虚构、指涉与再现之间可能存在的若干种联系,他将这些联系概括为三种主要关系类型: 同托邦、异托邦以及乌托邦。同托邦以逼真性(vérisimilitude)为标准,是指涉与再现、真实与虚构达成的一致。这种一致性意味着“一系列的现实素被安置在指涉对象的再现中”(Westphal,LaGéocritique170),它们或拥有共同的指示符(地名),或占据实际相同的地理位置。再现的空间应在最大限度上与指涉的空间建立联系,“通过叙事表达的虚拟属性将被添加到指涉对象逐渐现实化的属性中”(Westphal,LaGéocritique170),如现实中的巴黎、都柏林、纽约和雨果再现的巴黎、乔伊斯再现的都柏林以及卡夫卡再现的纽约之间都以共同可能性为原则,建立了使虚拟性不与实际或现实属性相对立的联系。异托邦以指涉和再现的彻底混乱为标志,对空间感知造成干扰,如: 莎士比亚在《维罗纳的二绅士》中将维罗纳设定为一座位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同名城市,扰乱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可能性关联。麦克黑尔(Brian McHale)曾把这种干扰归纳为“并列、嵌入、印叠和错配四种策略”(McHale 45)。通过并列联结不协调的空间,比如: 人们若打算从北京到上海,就必须要途经欧洲,在此,欧洲便成为被串联起来的不协调空间。采用嵌入,将虚构添入真实或反之,并在熟悉的场所中创造出另一个场所。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可以将一座并不存在的城市安置在一个存在现实指涉的空间当中,以激发读者对于虚拟性和现实性的想象。印叠可以融合不同场所的特点,例如当埃菲尔铁塔和故宫出现在同一座城市,这座城市便成为“第三种被剥夺了真正指涉对象的空间”(Westphal,LaGéocritique175)。错配赋予一个熟知场所不可能的品质,如把著名的沿海城市描述为一片不毛之地或将一座位于内陆的城市打造为海滨浴场。最后,乌托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有之地,与“真实的指涉对象之间不再有稳定的关系,因此它可以在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中表达再现,这个可能世界在原则上构成一切道德的典范”(Westphal,LaGéocritique180),换句话说,虚构场所的指涉对象要么不在现实中,要么只存在于未来,这种指涉关系也许会在某时转化为上述两种类型。基于上述理论铺垫,地理批评构想出文本与世界可能产生的关联,并由此证实后现代语境中二者相互影响的增强以及文本在理解与改造世界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作者一再重申:“虚构不是再现真实,而是实现了迄今尚未被表达的新的潜在性,继而依据界面超文本的逻辑与真实互动。”(Westphal,LaGéocritique171)
三、 地理批评的世界维度
在空时性、越界性和指涉性的共同作用下,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不断模糊。二者置身于后现代空间特定的文化系统中,展现出不同的空间经验与认知价值。它们不仅拉近了文本与世界的距离,使文本空间向更广阔的世界空间开放,还带领地理批评走向以多元性为原则的比较视野,多维度解读文本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根据韦斯特法尔的观点,地理批评的多元性集中体现在四个理论核心点上: 多聚焦、多感观性、时空分层和互文性。首先,多聚焦以丰富的语料为依托,旨在从整体上把握空间或场所的特征。正如“我们不可能只通过一门地理学就了解一个国家”(Giono 205),我们也不可能仅通过一部文学作品就从整体上把握所研究场所的特征。地理批评既是对空间间性的研究,也是对不同主体感知的研究。以巴黎为例,土生土长的巴黎人、到访巴黎的外地人或外国人、长期居住在巴黎的外地人或外国人对这座名为巴黎的城市均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因此,尽可能地搜集反映这座城市不同特点的文学或艺术作品,将作品集合视为一个涵盖本土、异域和异族视角的语料库,并对其加以整合分析,方能较为全面地比较出现实中的巴黎与文学、绘画、影视作品所呈现的巴黎之间存在的异同,进而合理判断空间互动的类型及影响。其次,地理批评强调空间感知,感知的多样性源自空间内在文化的差异性。空间特有的文化属性使其成为相互区别的场所,故而理解场所便是理解文化。文化不仅是视觉的感受,还体现在听觉、触觉和嗅觉上。由于每处场所均有属于自己的味道、声音和肌理,因此面对不同文化空间,我们应打破视觉占据的绝对优势,更有侧重地选择能够全面展现场所特质的感观方式,以更加多元的感观体验理解空间而非仅从视觉上对其进行简单的描述。再次,空间的生成是一个时间累积的过程,场所只有在时空关系中才能被感知。然而,空间的展开不具备时间上的同时性,所以韦斯特法尔认为,将单一的时间性强加于人类是一种霸权,而时空分层产生的多时性(polychronie)概念则可以将“不同的时间性分配给每一处文化空间”(Westphal,LaGéocritique230)。因此,在进行场所研究时,既要注重所搜集语料在共时性上具有的广度,还要把握空间文化记忆中的非共时性特征。最后,文本与空间在相互影响中构成互文关系。文本诞生于空间又赋予空间生命;空间可以诠释文本,也可以通过文本来理解空间;文本是空间的浓缩,空间则因成为大写的文本而具有可读性。至此,文本与空间的关系便被上升为图书馆与世界的隐喻。
地理批评的四个核心点向不同视角下的文本与空间关系发问,尝试以对话的方式来理解文学的世界性和世界的可读性。该理论向科学与艺术等诸多学科展开,多元化的阐释模式、跨学科的研究路径不仅进一步论证了后现代空间的杂糅性,还将有关场所与世界的地理性思考延伸至对“自我”与“他者”文化关系的探讨上。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韦斯特法尔逐渐意识到“非‘西方’理论知识的扩充对其空间研究视角的多样性或更好地界定其理论思考所产生的助益”(Westphal and Moura 173),他曾谈道:“我有意拓展面向世界的理论视野,目的是在于打开尽可能多的文化参照,用来反抗某种理论上的‘种族中心’主义。”(骆燕灵 6)地理批评的方法路径正因有助于我们走出文化禁锢,远离对“他者”的肆意杜撰,而被赋予一重对抗西方传统二元对立、驳斥主观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诗学属性。文学作品因在民族空间与世界空间中的形态、价值及影响不同而产生等级划分。但是,一旦文学被创造、空间被想象,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土地和世界空间的一部分。地理批评借地球土地的平等性和空间的普遍性来消弭文学的等级性,尝试把有等级的世界文学转变为无等级的地球文学。这既是对传统等级论、中心论和极性论的解构,也是对文本与世界关系的重塑,还为保留地域文化乃至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方法上的启示和借鉴。
从实践层面看,地理批评的“地理中心”论以场所为切入点,不论作家的国籍、种族和身份,将以该场所为指涉对象的文学创作凝聚起来,勾勒出一幅由场所(地域)向世界扩展的文学图景。汇集起来的作品所构成的重叠空间类似于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描绘的“中介空间”(in-between space),它使“去中心化的主体在‘当下’中赢得了某种身份”(Bhabha 216);从方法层面看,地理批评实现了比较方式的创新,让我们意识到在异质性凸显的后现代空间中,比较不仅仅局限于平行的比对,还可能是一种处于交叉点上的状态,因此,“把不可压缩的平行距离融入碎片的整体话语中”(Westphal,Parallèles241),将绘图学思路引入被置于不同再现交叉下的空间研究,可以更加开放的眼光来审视这种对比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从研究角度层面看,地理批评集中展现的复数观点有助于那些在地缘、语言或种族体量上被相对边缘化的文学作品以空间间性的方式融入世界文学的宏观空间,让文学在地球空间范围内自由地流动和越界。韦斯特法尔指出,世界文学是“地理批评的一个维度”(骆燕灵 6),地理批评对空间间性的研究有利于打破文学的等级体系,为世界文学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平等”“交流”“互动”等问题开辟一条地理空间路径;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空间也在其自身不断充实的过程中为地理批评带来更加多元的文化视角和更为丰富的文本语料,两者势必会在未来的发展中成为相互构建的坚实力量。
结 语
理论的生成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地理批评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其有待完善之处。哈利德·齐克里(Khalid Zekri)认为,韦斯特法尔在第四章中有关指涉性的论说并不令人信服。按照韦氏的观点,“采用地理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要认识到文学再现被包含在世界中,包含在一个被拓展的真实中”(Westphal,LaGéocritique191),然而,这样论断实际是把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转化为“虚构作为一种再现形式在社会世界中流通”的问题,那么,真实与虚构“两者之于对方存在真正的自主性吗”?在地理批评的视角下,“文学创作是否会再次制造出和经验世界里一样的空间指涉对象”(Zekri 171)?除了这些问题悬而未决,韦斯特法尔的论述主要基于庞杂的欧美语料,对东方作家及其作品少有提及。所以,他的研究难免会沦为一种笼统的概括。由此可见,地理批评所具有的广阔世界维度使翻译成为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文本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翻译被理解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多维过程,改变了传统地理语言类型的边界”(D’hulst 340)。虽然韦斯特法尔曾多次谈及翻译之于地理批评的重要性,却并未对此形成系统的理论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翻译在理论构建中发挥的作用。再者,“地理中心”的批评策略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主观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但是它研究的场所仅限于文学艺术作品指涉较多的大城市,因此该方法论指向的研究对象会显示出一定的等级划分。最后,地理批评面临实践之难。批评者不但应具有较为完善的知识储备,还需投入大量时间进行语料搜集。那么,如何界定语料搜集的“度”?怎样判定语料搜集的全面性?正如罗伯特·塔利(Robert Tally)所说:“这种以地理为中心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对此韦斯特法尔在书中也默认了: 你怎么知道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文本可以开始分析了呢?他说有一个可描述的临界点,材料收集到一定数量使你觉得该是对这个地方有个完整认识的时候了。然而,材料浩如烟海,没完没了,而且每天都有新的概念添加进那个文本库。你在哪里收手呢?”(袁源 塔利4)
尽管地理批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遭受了些许质疑,但仍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法国著名书评杂志《批判》(Critique)曾在2008年刊载一篇有关《地理批评: 真实、虚构、空间》的评介性文章。作者克洛艾·科南(Chloé Conant)在文中指出,“多学科的要求使韦斯特法尔偏移了自己的参照场: 文学与地理学、建筑学以及硬科学等并驾齐驱。此时的比较方法便从跨艺术转向跨科学”;该书在内容方面涉及的“文学语料十分丰富,[……]参考文本涉足哲学、宗教、政治领域,且不局限于在法国已普遍流行的后现代文论”;就写作风格而言,“文章紧密的安排使渊博的知识条理分明。准确又不失活泼的文字令阅读变得愉悦,十分‘清晰的脉络’让主题发散开来”;此外,这部作品的实践价值在于“它向‘应用文学’敞开了大门[……]而绝非是证明专业性的条条框框”(Conant 831—32)。法国勒阿弗尔大学在2011—2012年举办了两场有关勒阿弗尔文学再现的专题研讨会,旨在发掘和研究围绕这座城市展开的文学作品,是对地理批评方法的应用与理论的实践。位于法国北部沿海的勒阿弗尔不仅是印象派和野兽派绘画诞生的摇篮,还与一众法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密切相关: 它在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笔下反复出现,是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的旅居之地,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生长于斯,阿尔芒·萨拉克鲁(Armand Salacrou)长眠于此,孕育出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主义萌芽“偶然性”,成为帕斯卡尔·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写作灵感的来源。以学术研讨会为形式、地理批评为方法,把有关勒阿弗尔的作家和作品凝聚在一起,让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身份各异的研究者(有些研究者居住在此地,有些研究者因参加会议造访过此地,有些研究者仅在书中读到过这座城市)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和思考有关这座城市的空间再现和文化记忆,既可以深化对于作家和作品的认识,还能触及所研究空间的身份本质——“任何文化身份都不过是永不停息的创造和再创造的结果”(Westphal,LaGéocritique188)。由索尼娅·安东(Sonia Anton)主编的《勒阿弗尔: 写作的领地》系列丛书已出版了两部论文集,汇集了两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所收录文章涵盖与勒阿弗尔相关的文学、绘画、雕塑、摄影及电影作品研究,搭建出有关该城市空间再现的语料库模型。基于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和研究的可持续性,有关该地的广义语料库还将继续得到扩充,思考的问题也将得到深化,例如: 当下作品中勒阿弗尔的再现与印象派或野兽派时期的空间再现有何不同?勒阿弗尔的空间研究经验是否适用于其他城市?
从概念的提出到理论的形成,地理批评历经十余年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被不断拓展,它的跨学科视角对其他相关研究亦有所启发: 空间共生的理念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维度,引发了对世界进行文学勾勒的绘图学思考,以及对空间与权利关系的哲学思辨。只要人类对空间探索的脚步不停歇,那么虚构与真实、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将始终居于研究者的视野中心。随着空间研究“地理转向”趋势的增强,地理批评定然会凭借自身所具有的跨学科优势和比较方法的可塑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大有作为。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habha, Homi K.TheLocationof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Collot, Michel. “Pour une géographie littéraire.”Fabula-LhTn°8, 《Le Partage des disciplines》, mai 2011.
Conant, Chloé. “Pour une saisie plurielle des espaces littéraires.”Critique737 (2008): 830—32.
Dahan-Gaida, Laurence. “La géocritique au confluent du savoir et de l’imaginaire.”Epistémocritiquenuméro spécial géocritique vol.9. Automne 2011.
Dalla Chiara Scabia, Maria Luisa. “Istanti e individui nelle logiche temporali.”RivistadiFilosofia64 (1973): 95—122.
Di Pasquale, Fabrizio. “Territoire, espace, lieu: éléments pour une réflexion géocritique.”CahiersErta13 (2018): 9—21.
D’hulst, Lieven. “Literature and Globalism: A Tribute to Theo D’haen after Globalism?”CanadianReviewofComparativeLiterature43.3 (2016): 337—41.
Even-Zohar, Itamar.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Today11 (1990): 9—26.
Foucault, Michel. “Des espaces autres.”Architecture,Mouvement,Continuité 5 (1984): 46—49.
Giono, Jean.L’Eauvive. Paris: Gallimard, 1972.
Lahaie, Christiane. “Éléments de réflexion pour une géocritique des genres.”Epistémocritique, numéro spécial géocritique vol.9-automne 2011.
Lotman, Youri.LaSémiosphère. Limog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moges, 1999.
骆燕灵翻译整理:“关于‘地理批评’——朱立元与波特兰·韦斯特法尔的对话”,《江淮论坛》3(2017): 5—12。
[Luo, Yanling, ed and trans. “Conversation on Géocritique between Zhu Liyuan and Bertrand Westphal.”JianghuaiTribune3 (2017): 5—12.]
McHale, Brian.PostmodernistFi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7.
Perec, Georges.Espècesd’espaces. Paris: Galiliée, 1985.
Soja, Edward.Thirdspace:JourneystoLosAngelesandOtherReal-and-ImaginedPlace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6.
Westphal, Bertrand.LaGéocritique:réel,fiction,espac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7.
- - -.“Parallèles, mondes parallèles, archipels.”RevuedeLittératurecomparée2 (2001): 235—41.
- - -.“Pour une approche géocritique des textes.”Lagéocritiquemoded’emploi. Limog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moges, 2000. 9—40.
Westphal, Berrand, and Jean-Marc Moura. “Entretien.”RevuecritiquedeFixxionfrançaisecontemporaine16.6 (2018): 171—78.
袁源 罗伯特·塔利:“文学空间研究与教学: 罗伯特·塔利访谈录(英文)”,《外国文学研究》3(2019): 1—15。
[Yuan, Yuan, and Robert T. Tally, Jr. “Doing and Teaching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T. Tally, Jr.”ForeignLiteratureStudies3 (2019): 1—15.]
Zekri, Khalid. “Bertrand Westphal,LaGéocritique.Réel,fiction,espace.”Itinéraires3 (2012): 16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