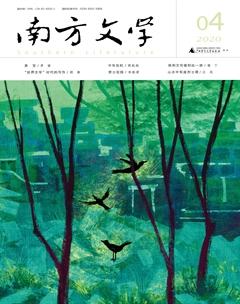马尔康:从梭磨河到脚木足河
阿贝尔
十八年后,我对横断山中的马尔康的印象已成空白;这次去,竟有初见之感,梭磨河南流的错觉得以纠正——实际上,她南流至梭磨乡王家寨便转向西流,甚至一度偏北,直到在木尔基河坝汇入脚木足河。
这次,我走九寨沟,翻弓杠岭到川主寺,过黄胜关上尕尼台,离开213国道,沿瓦(切)松(潘)草原风光路南下。看过了甘南草原、青海草原和呼伦贝尔草原,我对眼前的草原有些倦怠,同车的人停车拍照,我只留意到路坎不知名的小花。十八年前路过瓦切,我写了《瓦切的晚霞》,这次到瓦切正值午后,依然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只不再是晚霞,而是蓝天和多层次大朵飞流的白云,还有地面如同别墅的小楼群。
瓦切的海拔超过3500米,相较于内地天地间缩短了距离,气流变换迅速,白云奔流的速度远超我们的车速。六月,草地上很多野花都开了,蒲公英和毛茛最惹眼,还有一种木本串生的紫红花——像野海棠。草原上的水也是极好看的,河无高岸,水满满的,缓流,无声,反射着云天和太阳光。车上草丘,视线可以抵达草地全貌的时候,河流呈现出曲折婀娜的面貌,常见柔美的“S”形,如同女身,河流的灵气也流溢出来。白河月亮湾一段最为显著,地图上看全是弯弯绕,发端于查真梁子北坡,在唐克汇入黄河。
查真梁子是黄河与长江的一个分水岭。查真是藏语“柳树”的意思。自然不是内地常见的柳树,而是高山红柳。像对瓦切野生鱼的印象一样,我对查真梁子的印象也止于白林等阿坝友人所发图片,多是冰天雪地、寒气袭人。
我们到达查真梁子时,一场暴雨已酝酿成熟,头上砸下冰冷的雨点,四下乌云翻腾,东南一侧的雪山云雾笼罩。我停车疾步走上观景台,避开立石做的地标,先是眼睛对着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继而是镜头对着。上到查真梁子之前我便透过车玻璃看见了这列雪山,问同车的泽让闼雪山的名字,他回答不了。其实,我已猜到是黑水境内达古冰川一线。我对川西地理比较熟悉,想象力能够挣脱地表悬于高空,像航拍器一样追踪到自盆缘山区到雪山草地的主要大景。
因为足够的海拔高度,查真梁子看起来并不险峻,近周的山峰也都不高,形势类似青海境内祁连山腹地的大松树垭口,海拔也颇接近,都是草原与山地的分界线。
下查真梁子,就算进入了梭磨河谷,也即是进入长江水系。河谷宽绰,有草场和少许耕地,省道两旁的山脉给出了一个具体、清晰的空间,我意识到我们的草原之旅结束了,有种重返“世界”的感觉——是喜悦也是失望。
喜悦也来自突然从不同方向呈现在眼里的雪山。梭磨河不是发端于查真梁子,而是发端于比查真梁子更远更高,介于黑水、红原和松潘之间的羊拱山,山的另一侧是流经黑水和茂县的金马河的源头。梭磨河不同于白河,她从源头开始就是一条山谷的河流,而非草原河,只是源头的山谷有一些高山草甸的面貌。这样的河源面貌我在弓杠岭南侧的岷江源和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夺补河源头看见过。
这是一条河流的幼年与童年,清澈涓细,但已经能觉出她潜力无穷的基因,甚至在雨后浑浊的河水中可以嗅到生殖的气息。这样的气息弥散在湿润的空气中,包含了每一径流携带的植被的味道。
梭磨河谷开始打动我是在过了壤口之后,特别是康玛尔寺到刷经寺一段。这段河谷下切得厉害,落差极大,梭磨河在接纳了壤口河等众多雪溪后水量也充沛起来;这时,河谷的位置还很高,加之雨过天晴,顺流而下可以看得极远、极清晰。六月,近山远山全是新绿,点缀着常绿的松柏的葱郁,南方遥远的雪山一直在视线之内,整个河谷都被框在圣洁而自然的氛围之中。河谷有村寨有寺院,有青稞有蔬菜,渐渐有了烟火气,但这烟火气又不同于内地的庸常污浊,而是一种异域的干干净净的古老气息。我几次试图停车拍照,都因一念之差放弃了。那种雨后晴朗的天气,是可以拍出新翠、高清的梭磨河谷的,无论是大景还是细部都会格外真实、生动。
刷经寺一带河谷出现较多耕地,村寨明显增多,那些曾经是山林却已开垦耕种了几百年的河谷、山坡有一种异域农耕的美学。这样的美学或许是内地人传播给世居民族的,但又脱离了内地人庸常的趣味,以青稞、荞麦的观赏性展示出土地与世居民族的特殊关系。我记得几个村寨的名字:色隆、亚休、老康猫、喀尔郎、白帐房、马塘……
在我的印象中,紅原是草原,翻过查真梁子就该是马尔康的地界了。然而我错了,梭磨河上游的壤口乡和刷经寺镇都是红原县管辖的,过了刷经路口才算进入马尔康的地界。
进入马尔康地界,梭磨河谷有了不同于上游的面貌。尽管落差也大,河水奔腾,水声轰鸣,但河谷下切得非常厉害,河床和公路都显得平缓了许多。这时的梭磨河谷才是我理解的符合“峡谷”定义的河谷,也是我想象中的梭磨河峡谷。我放慢车速,打开车窗,让河谷湿润的风吹进车来,让下午的阳光照进车里,让峡谷的空气接触到我的身体。随着海拔的下降,视野是缩小了,但视线所及却变得具体、清晰。如果把梭磨河峡谷比作一个身体,那我算是贴近、进入了这个身体。我不知道车里的人在这个美丽温润的身体中是什么感觉,我是感觉到了她的呼吸、血流、心跳和整个肌肤弥散出的有着古老丰富的植被的气息。从水边到山坡到山顶,是大片新绿,间杂小片或孤立的松柏,在雨后显得格外洁净。虽是新绿,却也不觉幼稚,新枝新叶都完全舒展开来,一些花正开,一些花刚开过,空气里散发着雌性的气味。梭磨河涨过水,从草原流下来,携带着草根树叶的味道和花香,我的嗅觉亦能分辨出生殖的气息。
车过马塘,我也只是听同车的白林说是马塘——阿来出生的村子,并没多看几眼或停车观看、拍照,后来在马塘的停留则是在福格斯所著的《布鲁斯在阿坝》一书里:
翻过垭口下行2500英尺,行走约4英里后,我们到达马塘。马塘是一个衰落的小型贸易站点,商队托运的茶叶都存放在这里。马塘也是来自康猫河上游以及阿坝的部分藏人经商的地方。他们带上羊毛、兽皮以及牛羊马匹换取内地的商品。马塘的居民大多是穆斯林。这里海拔太高,就连蔬菜也难出产,他们唯一的行当就是与周边的当地人做贸易。
布鲁斯是从杂谷脑(理县)翻鹧鸪山到马塘的。“塘”是明清时设的关卡,为驻防及传递军情,通常与之前所设的铺合并。显然,马塘就是梭磨河峡谷的一个关卡与铺子,控制着由北边草原、松潘、黑水和鹧鸪山过来的藏人和羌人,和平时期关卡的意义被淡化,成了一个贸易站点和货物中转站。阿来父亲的祖上便是从松潘过来经商的穆斯林,他出生在马塘仿佛是一个必然。现在想来,我该在马塘稍作停留,过河去看一眼台地上阿来的出生地,没准还能寻一点旧迹。
马塘以下到砍竹村,有一段无人烟的峡谷或者叫原生峡谷,估计有十多公里,特别打动我。想必倘若没有修这条公路,和一百年前便没有两样。行经在这段峡谷,我感觉是一种奢侈,这奢侈不只包括了原始生态的高山峡谷,也包括了雨后晴朗的下午时光——与布鲁斯过境甚至更早的时光有一种直觉的衔接,就像南方遥远的雪山与梭磨河谷的衔接,甚至包括了内地的山水无法提供给我们的独特的审美——洁净、原始、温润、静谧,以及与我们熟悉的事物之间足够的距离感。我几次停车拍照,去到河边和桥上,用目光摩挲视线内的青山、水域和花木,耳膜承受着轰鸣的水声,内心承受着莫名的兴奋与突生的爱。承受也是享受,我在,却又是一种退避的在,像是融化后与梭磨河峡谷合一。我特别注意到梭磨河两岸的岩壁、岩壁上孤立的大叶杜鹃、杜鹃裸露的根以及生长在河湾的茂盛的次森林,同它们偶遇,突生一种说不清的感情——幸遇和爱,这爱却是为梭磨河峡谷而生,由梭磨河峡谷分派到我视线所及的每一个个体。
我不想描述这一峡谷,我只想感受,或者说享受。一百多年前,布鲁斯一行所走的小道在河谷右岸,今天的公路也在右岸。说布鲁斯一行没有我们幸运也对——我们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便走完了他们两天的行程,但我真实的感受是我们不及他们幸运,他们有整整两天的时间与梭磨河峡谷相伴,几次穿过密林,零距离地欣赏河谷的美景。他们的幸运还多了年代的馈赠,比如与黑水勇士和黑水头人的巧遇。
《布鲁斯在阿坝》一书中的老照片印证了我的感觉——今日的梭磨河峡谷与百年前的面貌几无变化。巧合的是,我拍下的一张河谷照片与书中老照片的角度完全相同,对照看,不仅河床没有变化,就是水量和岸边灌丛都没有多少变化,唯一有变的是而今两岸山上的原始乔木少了。我的照片拍摄于2019年6月11日下午,布鲁斯的照片拍摄于1908年6月9日,中间相隔了111年。
我感觉有一种东西震撼到我,那便是我与布鲁斯共同置身其中的如同梭磨河峡谷一般的时间。我们在共同时间的内部,却又分置不同的部位,布鲁斯早已不在,但我感觉他仍在,永不停息的梭磨河保留了他的气息。梭磨河尚有一种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特质,那便是汹涌、温润,富有生殖力,她的汹涌彰显出的不是雄性而是雌性,澎湃不是志向或者抒情,而是一种柔韧的美学。这样的美学在进入梭磨乡所辖的色尔米村和木尔溪村表现得尤其充分,河流的落差减小,河面增宽,略显浑浊的河水蓄积得更为丰满,颇似一位正值生育期的少妇。
车过王家寨,我被梭磨河这样的美学所吸引,再次泊车去到河岸和铁桥,感受她丰沛的活力。也恰是在这里,梭磨河由南流改向西流,直到汇入脚木足河,在白湾乡接纳了观音河才又改向南流。
英国女探险家伊莎贝拉比布鲁斯早十二年来到这段峡谷,她到达梭磨土司官寨没再前行就返回了。在我看来并无太多遗憾,她毕竟走过了梭磨河峡谷最美的一段。峡谷及峡谷世居民族的美,都被她特有的女性的直觉所捕捉并诉诸文字。她对六十三年后诞生文学家阿来的马塘的描述比布鲁斯详细而诗意。
贸易淡季的马塘无论是风雪天还是晴天都是一个苍白凄凉的村寨。石头房子低矮,屋顶由粗糙的木头和石板压在上面构成……到了七八月,这里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马塘成了一个多民族的贸易市场,客栈挤满人马,周围草地上到处是藏人的牦牛和帐篷……
伊莎贝拉特别描写到马塘的藏族女性——“马塘的戎人妇女有着惊人的美貌”,长得像圣母玛利亚,她们爱笑、好玩又害羞,像野兔一样机敏。或许这些“有着惊人的美貌”的戎妇中就有阿来的外祖母或曾外祖母。面对需要调焦的镜头,这些美丽的“野兔”一刻也待不住,以至于伊莎贝拉无法将她们的美颜定格在胶片上。
车过卓克基土司官寨,我放慢车速远远地望了一眼。官寨建在纳足沟与梭磨河交汇口的山岗上,没有碉楼。这是初接触,我的目光尚有一点游弋与羞涩。在我的眼里和感觉中,卓克基土司官寨不是一个历史遗存,而是一个阿来创造的文學符号,官寨居住的不是始封于元代的卓克基世代土司,而是并不存在的麦其土司以及他酒后与汉族女人生下的有着超时代预感和举止的傻儿。官寨绿树成荫,花团锦簇。
两天后,我造访了卓克基,走进了有着汉式回廊的四层官楼。我在乎的不是它的历史传说,而是它的建筑艺术和清晨之后明晰的光影。置身这样的光影是对已逝时间的一种抵达,也是一种泛神的发现。每层木楼,每个房间,每一件当年存留或后来添摆的物件,包括每扇窗户、每块木板,如此纯粹物质的东西一旦投下光影,精神的东西或者说神就显现了。
在卓克基,我还造访了西索民居。民居建在与土司官寨一溪之隔的台地和山坡上,旧时被称作“卓克基赶枪巴”,即卓克基街,完全是嘉绒先民“垒石为室”的建筑风格。碉房至今居住着土司时代的当差、商贾、民间工艺者的后人。我走进“赶枪巴”转悠,在接近午间的朗日里感受了空白般的时间的灼烧。“赶枪巴”及民居内部各家院前种植的绿植花卉却是温柔、美丽的,我拍到的有苹果树、大黄、高山月季、野玫瑰和岷江百合,它们不只对我是种抚慰,对脱节的历史也是一种抚慰。
在一条小巷的深处,杨素筠把一户院前遍种花草的人家指给我们,说是她在《嘉绒人的葬礼》中写到的达尔基叔叔家。碉房是一栋三层小别墅,第二层有一个盖顶的大露台,院里不见有人,只有盆栽的红彤彤的玫瑰绽放着。
下到纳足沟边,恰逢西索村人集体制作擦擦。几十近百男女聚在一起,运泥、和泥、制作,完全是一派热闹的劳动场面。我第一次看见,感觉陌生而惊异,同行的泽让闼叫出了刚刚制作出来、摆放在地上的泥塑锥形体的名字——擦擦。他告诉我,擦擦是苯教用来祈福的一种古老的物品,通常放在寺庙、墓葬、耕地牧场,为家人和部族祈福。2016年3月,在马尔康沙尔宗乡木亚足村的吉岗对面,出土了距今一千多年的“窖藏”擦擦。
马尔康市区所在的这段梭磨河谷是梭磨河流向偏北弧度最大的,也是河谷最宽、耕地最多的地带。马尔康在嘉绒语里为“火苗旺盛之地”,火苗要旺盛自然得在相对平坦、宽绰的河谷,而不是在雪山之巅,这火苗代表了嘉绒藏人的繁衍,也代表了嘉绒藏人的文明传播。对于外来部族,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王国,欲将它变成自己的世界和王国,就意味着要与梭磨河融合,把梭磨河變成自己的身体。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嘉绒藏人是成功的,他们在接纳、融合梭磨河的气息的同时,也用自己部族的灵魂与气息濡染出了璀璨而独特的文明。
我虽说在十八年前来过马尔康,但早已淡忘。一个城市有这样一条落差巨大、河水奔涌的河流穿过,我是第一次看见。在我的感觉中,梭磨河源源不断地洗涤着嘉绒藏人的灵魂深处,积淀着碳酸钙一般坚硬、水晶一般明澈的异族精神。现代文明的劲风吹进河谷差不多百年了,今天我们仍能在他们的瞳孔和眉梢看见这种精神。
卓克基到松岗一段是梭磨河最宽绰的河谷,从古到今都是嘉绒藏人部族最肥沃的农耕区。而今很多耕地被市区建房占去,所见房屋虽也画上了藏文化的符号,给人的感觉却是内地的现代风貌,在河谷坝子很难再看见石头碉房。
去脚木足河路过松岗,这次活动的主角杨素筠把松岗土司官寨指给我们看,高耸在梭磨河右岸山岗的两栋碉楼视觉冲击力极强——天空晴朗,河谷明媚,早晨的空气十分清新,车行左岸,视觉距离正好,简直就是一幅移动的图画。当时我对松岗土司官寨还一无所知,一晃而过获得的仅仅是视觉的享受,就是有什么理解也仅限于符号化的表层的意义。仅隔一天,当我读着《布鲁斯在阿坝》一书走进图画中的碉楼碉房,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
布鲁斯在松岗女土司安排的碉房住了一宿,许多当地人前来拜访,给他带来蔬菜、鸡蛋、肉和青稞饼,他给他们当中识字的人送书,给前来求医者看病送药。当他到河对岸去参观寺庙并送给女孩们小镜子的时候,寺庙的僧人阻止了他,收缴了所有的镜子并砸碎,他们不让女孩子从镜子里照见自己,仿佛看见自己长得漂亮是种罪过。他们还说外国人想用这些镜子控制她们的灵魂。拍照也被拒绝。为了驱逐布鲁斯一行带来的影响,所有的僧人都上到寺庙的顶层齐声诵经,并敲起铙钹吹响羊角号。布鲁斯一行在松岗的感受比我们今天要原始得多,当地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还是一千年前的,异域特质主要表现在人的身上;而今很多异域原生的东西已经流失,当我们在傍晚专程来到松岗,并在当年女土司的官寨遗址待到月亮升起时,我看见的、感受到的仅仅是个打造的旅游产品,空气中再没有布鲁斯嗅到的那种发自当地人身上的气息。
月亮从高的那栋碉楼的左侧升起,继而转到右侧,停在两栋碉楼之间。偶有薄云,夜空深海一般,看得清月亮上的环形山。一百年,地上的事物发生了巨变,夜空和月亮依旧。我想有一种美没变,那便是布鲁斯赏月的享受和我们赏月的享受,包括月亮赖以依托的山岗上的那两栋碉楼。
松岗到梭磨河与脚木足河的汇合处又是一段没有耕地的自然意义的峡谷,行经在这样的峡谷,很快便淡忘了刚刚获得的当地人生活的印象,甚至忘记了人类的存在。我发现岷江、涪江中有很多石头,梭磨河则没有。我刚刚将这个疑问交付给同车的当地人,转眼便看见一块屹立在咆哮的河中央的巨石。
杨素筠在车里描述河谷两岸的白玫瑰,其兴奋即使将滔滔不绝、眉飞色舞、绘声绘色三个词加一起也是不够表述的。她引用了一百多年前到达梭磨河峡谷的女探险者伊莎贝拉描写野玫瑰的原话:
透明的河水是绿的,看起来像翡翠。河边弯曲的树干上挂着蕨类、兰花以及红色和白色玫瑰长长的枝干。树干上还有一层薄薄的蕨类和美丽的南海瓶蕨,在阳光照射下仿佛是透明的。飞流直下的瀑布形成一片片水帘,溅起朵朵浪花,在一滩滩深邃碧绿的水潭里,河水停止了流动,水潭倒映出玫瑰花、铁线莲和雪山。但河水的轰鸣声一直回荡在峡谷和悬崖中。
杨素筠还列举了自己与白玫瑰的亲密接触以证明这种花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她的描述有一种异域中的异域色彩,同时还带了不老少女的罗曼蒂克。
我们从热脚过到对岸。桥头的路标指示着道路的去向——直走去金川、壤塘,右转过桥去脚木足乡、草登乡。在对岸行经约莫两公里是梭磨河汇入脚木足河的最后一段。这段河的落差仍很大,河水一路咆哮,阳光下全是泥色的波涛浪花。
车过两河交汇处,我有一点小激动,但没能停下来看看。我对两条河的交汇口总是有特别的兴趣,别说是两条陌生的、高海拔河流了。河流如人,两条河交汇变成一条河,总是有着身体意味的审美和神秘的隐义。两条河各自的流域不同、落差不同,土壤和植被有别,河水的颜色和气味也不同,而今交汇在一起变成了一条河,开始还看得出差别,甚至是泾渭分明,流淌一段后便完全交融了。在这方面,我有常人没有的洞察力,总能在汇合后的河流里看见原河。
两条长度和水量相差不大的河流汇合在一起变成一条河,就像梭磨河和脚木足河,到底该叫她梭磨河还是脚木足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因为对梭磨河的偏爱,我先入为主地将梭磨河峡谷延伸到了下一个汇合处,实际上,梭磨河在注入脚木足河的地方便结束了。为了确定她的结束,我在地图上将汇合处放大,反复地查看、感觉,直到不得不接受她作为支流的事实。
一条河有很多意义,但脚木足河于我只有一种,那就是将我引向一个古老而陌生的、与世隔绝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条70公里长、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河谷。70公里的长度,海拔仅提升了100米,可以想见河谷的平缓与宽绰,这平缓与宽绰恰恰是作为人居世界所必需的。落实到一级行政区划,这个世界就是脚木足乡和草登乡,包括我尚未抵达的大藏乡和日部乡。
脚木足河口有一段狭窄的峡谷,穿过峡谷接近脚木足乡政府驻地,河谷豁然开朗,沿河出现大片耕地,耕地从河谷一直延伸到坡度不大的山坡,带状的通村路将河谷与山坡、山坳的村寨相连,我记住名字的有沙市村、白沙村、石江咀村、帕尔巴村、蒲志村、孔龙村、大西木尔巴村……这些村都是脚木足乡下辖的,耕地之广、之肥沃超过了梭磨河谷,甚至是龙门山中低海拔河谷也是不可比的。千百年来,这些耕地都是由嘉绒藏人耕种,他们年复一年地种植青稞、蚕豆、荞麦,后来也种植土豆和玉米。他们在冲积地带和山岗建起碉楼、碉房和寺院,将虔诚的信仰与劳作作为简朴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