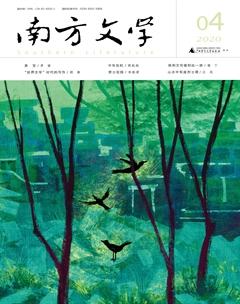“世界文学”时代的写作
“世界文学”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很庞大,尽管近些年一直在思考何谓世界文学、何谓翻译,有时候依然会迷失在思想的丛林。对我来说,在写作的时候,达姆罗什讨论的“世界文学”概念显得十分遥远。更真实的情形是,哪一本书来到了我的世界里,来到我的阅读中,最后转化成我的写作,才是切身的,所以说,世界文学是一种为我所用的东西。
在这里,我想区分两个概念,一种眼前的生活、当下的生活,另外一种是可能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构造出来的生活,写作中的生活。“世界文学”太庞大了,庞大到我无可界定,但是在这两个层面,我们可以去搜寻世界文学的位置。对我来说,写作不单纯是为了写眼前如此存在的生活,原原本本地书写它,而是为了写我想要过的那种生活,我称之为“可能的生活”。当然,可能的生活表现出来的形态也许与当下生活有着诸多相似,共享着很多东西,甚至可以说,当下生活催生了可能的生活。可能的生活是对当下生活的超越和重塑,而不是舍弃。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只要能提供我书写可能生活的手段,那么它就是我的文学。
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浙江北部的一个村子,家里很穷,从小读不到什么书,书的贫乏到了可怕的境地。而我最早接触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古文观止》 《三国演义》 《杨家将演义》《绿野仙踪》,楚辞、唐诗、宋词,等等,这些东西没有成为激发我写作的动力。后来去了一个小镇上读中学,才开始接触《百年孤独》这样的书,那时范晔的译本还没出来,我读的是黄锦炎的译本。我好像打开了一个世界,一个我感到陌生的世界,此时我才有了书写的冲动。世界文学真的给过我很多滋养,如果有世界文学这个东西存在的话。它的滋养在于,教会了我通过另一种方式来理解眼前的生活,甚至教会我通过另一种方式直接跨越过眼前的生活。江南小镇那些生活我根本不想书写,或者不想去理解,这个时候我遭遇到文学或者说外国文学。我知道我的个体经验没有普遍性,但是我想如实表达出来。在我的经历中,如果没有外国文学,其实我根本不会去读书,也不会去写作。外国文学蕴含着一种向外的、新异的力量。是外国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激发了我,所以我后来的阅读基本集中在这部分。其实那时我认真读的第一个作家是雨果。也读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鲁迅、茅盾、老舍、俞平伯、卞之琳、何其芳、张爱玲、钱锺书,等等,但是没有获得什么意外的感受。
我老家在浙江北部一个小镇的乡下。但是,对于这个江南小镇及周边的农村生活,我从小不感兴趣,只想逃离。正在此时,外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异质性的想象力、异质性的语言,尤其是异质性的书写方式,所以外国文学对我是有意义的。那么在这个问题框架里面,如果“世界文学”这个话题有意义的话,对我来说就在于,世界文学是一种可以提供异样的、陌生的生活的文学。当然,我那时候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我一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太感兴趣,认为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没有提供差异的、变形的东西,它呈现的几乎就是我已经体验到的生活,以及对这种生活的日常认知。在我阅读之初,我几乎不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书,除了一些先锋派作家,如格非、莫言、孙甘露、海男、林白等,和当代诗人,如北岛、顾城、海子、欧阳江河、王家新、臧棣、戈麦、西渡等。后来我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书就越来越少。但这几年为了教书——我们同济有创意写作硕士点,为了给学生讲解当代作家的书,补读了很多。但读完之后,刚开始我不太想与学生讨论,我觉得他们作品中那种“陌生感”不是很多。这个时候,我遇到了疑惑,我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世界文学”的概念。
卡萨诺瓦有本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里面有个说法我很感兴趣,他说世界文学是有首都的,世界文学是有中心的。如果一个作家处在中心,比如巴黎,他的书写就很容易被认知。但是假如处在边缘,就要把自己转化到中心,或者要将自己翻译成中心,要变成“首都”的一员——要把自己的书写提升到符合“首都”的标准,这样的书写才会被认可。当然卡萨诺瓦所谓的首都就是巴黎,这一点是需要探讨的。但如今的中心可能是北京吗?这个过程中,边缘是被吸纳到中心的,一个身处边缘的人的当下生活被消解、重构,最后变成中心所认可的生活。边缘的文学可以通过出版,也可以通过评论、翻译和评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最后被转化到中心。这有点像我年轻时接纳西方文学的状态,其实我想超越眼前的日常生活,于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想象中的西方人那样去写作、那样去生活。当然,边缘地区与首都之间也会产生竞争、断裂和疏离,不过当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我后来读到另外一本书——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那本书在国内翻译比较晚,2017年才译过来。里面谈到整个欧洲文学一直存在一个中心,只是这个中心在不断转移,并非凝固不变。“翻译”这个概念,在拉丁文中最早是搬运的意思。为什么是“搬运”?罗马帝国分裂后,西部变成西罗马帝国,然后又分裂成各个民族国家。文化的首都逐渐转移到了巴黎,此时就必须把整个罗马文化搬运到巴黎,于是就产生了“翻译”的概念。其实这种中心的转移,也就是把整个文明来一次中心化的过程,最终是普世帝国的转移和蔓延,翻译在其中承担了核心功能。所以,翻译这个概念内含着面向中心的运动。但是与卡萨诺瓦不同之处在于,库尔提乌斯又强调了翻译中的开放性,即一门语言,比如德语,是通过翻译实现外语化,比如法语化,从而让自己變得强大。即在对罗马的搬运——翻译中,巴黎成为新的罗马,而不是成为原原本本的旧罗马。本雅明在《译者的使命》里更是强调了翻译让文学作品的生命得以更新,让母语经历分娩的阵痛。翻译并非译作对原作的亦步亦趋的服从,而是原作和译作之间的互补。翻译,表面上看来是一个面向中心的运动,本质上却是让一门语言通过成为他者,而更加成为自身的方式。
我们读大多数外国文学作品需要通过翻译。虽然我后来做起翻译工作,然而之前基本上都在读译本,很少去读原文,后来才逐渐有了读原文的习惯,随后又有了翻译的冲动。翻译作品既不是原语言的作品,也不是母语的文学作品,它夹在中间,让母语的书写得以变形,让母语趋向一个差异性的面目。那么在撇开原文、阅读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其实是读者假想着把自己搬运到另一个“中心”的过程。其实这一切只是在自己母语内部完成的创造过程。所以,翻译这个概念如果一直包含着趋向中心的运动,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概念,让读者失掉自我,隔膜于塑造着自己的母语及其文明。所以,我曾经才会由于疯狂阅读翻译文学作品而轻视中国当代文学。事实上,翻译,应该是一个敞开、变形、转化的过程,甚至是一个消解中心的过程。翻译的内部有着试图在变形中寻求可能生活的愿望。
话说回来,为什么我当年不喜欢江南小镇那点生活?因为我觉得那个生活与我太贴近了,是让我窒息的日常生活,并不能提供我对世界别样的想象。其实,主要原因不是江南小镇和乡村生活的贫乏,而是我当时的理解力不够强大。我没有能力去理解江南小镇在当下生活之中隐藏着可能的形式。因此,就一味想着越界和逃离。
那么,写作之于我,到底是什么?写作只是如实写下自己经历了的生活,还是去重新构造自己、改变自己,用另一种方式来活在当下的生活?胡桑这个名字是我的笔名,但是,胡桑其实谐音于湖桑,后者是我老家湖州的一个桑树品种。我家的房子后面有着一大片浩瀚的桑树林。小时候我一直漫游其中。绕了一大圈,我最终还是与自己的故乡和解了。我不想用我的原名生活,我用我的笔名来生活,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写作,却又是会被误解为一种试图逃离的写作。但是这个笔名还有另一层意思在里面——我开始想要去转化当下的生活,而不是逃离。
写作,是通过他者而成为自己。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个方式是不现实的,或者不接地气的,不民族的。但是我在写作中一直反对顽固的本土、地方、民族,我一直不想把自己變成贴着地域标签或民族标签的作家。其实,我并不排斥自己身上的地域性或民族性,但前提是我需要一种开放的地域性或民族性,使其获得游走的流动性。我自己的散文集《在孟溪那边》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而且,孟溪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个小村子。现在回过头去想,世界文学给了我确认这种开放性和流动性的机会。只是当初我误以为世界文学将我引向了另一个外在的世界。现在我才幡然醒悟,这个世界其实是从当下生活中发展出来的一个世界,一个更具有可塑性的世界,它是内在,而不是外在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更确切地说是某国文学),犹如星丛,相互弥补、牵引,共同来构筑这个世界。当然,这是个乌托邦。目前的现实是,巴黎或者纽约充当着世界文学的权力中心。
取道外国文学,我又开始重新打量眼前的、当下的生活。我曾经渴望的其实不是外在的生活,而是差异的、变形的内在生活,超越日常认知束缚的生活,不断被“翻译”着的生活。我还想说,这是一种反抗民族、国家、文明中心的“翻译”,不仅反抗西方这个中心,也反抗着中国这个中心。写作,即转化、提炼当下生活,并非臣服于趋向中心的生活,而是揭示去中心的、塑形着的生活。在这样一种写作中,我又开始爱上了当下生活。
我的主要观点是:写作让我们克服(而不是舍弃)了当下现实,克服了其封闭性和束缚性,给了我们一种想象别样生活的可能性,去构造另一种生活的方式。这个时候我们求助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一直有效,因为它是异质性的,一直是在民族之间产生的,一直是在翻译之中形成的,它永远不可能超越翻译,也不再凝固于一个中心。翻译意味着各语言、民族、国家、文明之间相互的对话和交流,相互的改变和塑造。不存在一个中心可以凌驾、侵吞其余的语言、民族、国家和文明。如果缺失了永无止境的变形中的翻译,那么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就不再有效,就只剩下全球文学,或者只有一种单一的文学。那是可怕的,我们对别样生活的想象就会极大缩减。然而,世界文学是包容异质性的文学,而不是排斥异质性的文学。我们需要世界文学。可能的生活不是想要排挤当下的生活,而是更好地接近、认知、提炼当下的现实生活。我们需要可能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是世界文学,而不是外国文学?因为在这个时代,它在中国之外,在民族国家之上。如果它在一个国家之内,可能这个概念也就失去意义了。我们谈“世界文学”其实隐含了一个意思:它是所有民族、语言的文学,它是打开民族国家空间的陌生的文学。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写作就是去中心的,朝向他异的,朝向陌生的,朝向可能生活的语言行动。
这里面还需要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是首先需要回答的。如果文学可以是一切,那就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我们既然做文学批评,既然写作,那么文学要做什么,它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思考。从广义而言,文学可以是一切表达。但是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讨论的意义了。在我看来,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文学对创造性的表达有着天然的执着。什么叫创造性表达?倘若文学只能去书写一种特定的、一成不变的、无从改变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文学总是对某种生活、某种特定的书写进行纠正甚至超越。文学作为表达,可以是政治的、哲学的、审美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超越创造性的表达本身。中国不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西方,尤其是欧美,早已中产阶级化。中产阶级需要文学,但需要的是安逸的文学,不去挑战生活既定形式的文学。其实我们正处在向中产阶级社会的过渡中,却尚未到达,生活层次依然极为复杂。所以,西方的文学书写和中国的文学书写是不一样的,将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手段移植到中国的生活,会显得别扭。还有一个原因,西方文学的精神根基是两希文明,我们的精神基础却是儒释道,因为我们的汉语还没有消失,尽管我们的传统需要面临一个现代性的境况,这一点中西皆然,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明可以在现代彻底地重新开始。语言所传达的精神一经流散,就无从彻底根除。当然,汉语从魏晋以来就是一门极为开放的语言,可是虽然汉语具有强大的变形能力,却没有成为一门外语。所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首先在中产阶级社会中是合法的,假如放在中国,用来表达中国的生活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处在不同的生活和文明传统之中。但现代主义文学的表达在中国不是不成立,而是会在汉语中形成新的特征,会产生变异,这也是文学本身的力量所在。我们不能抄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达方式,不能偷窃其独特的感受力。变形和翻译要在星丛关系中完成,而不是在趋向中心的运动中懒惰地完成,不能将自己整个地交出去。这就是史书美所说的,文学话语的区域性实践。我们应该有勇气去实践,而不是回避。在实践中,可以吸纳他者的力量,但不是成为他者。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一直让文学只表达一种生活,一直用一种方式表达同一种生活,那么文学的创造性就消失了。但是,我们也不能直接搬运一种外在的生活。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包括青年作家)必须书写何种生活。外国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表达,表达同一种生活的不同方式,或者重新审视同一种生活的不同方式,同时会形成认知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这样的外国文学属于世界文学。但是,如果外国文学成为写作的模板、固定的形式,那么,它就已经背叛了世界文学。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去关注生活,或者说,要热爱生活。不管热爱何种生活,文学作为一种书写手段,必定拥有特殊的形式和方法,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形式和方法。热爱生活,首先是去感受生活,深入认识生活的面貌。外国文学所提供的方法,必须在我们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中改造、变形,必须被重新熔炼成我们看待自己生活的方法、感受我们自己生活的能力。文学,即创造性的语言表达,是认知生活的必要途径。如果生活自己就能清晰呈现,那为什么还需要写作,直接生活就行了。
第二,是媒介问题。文学对生活的表达不同于新闻、电影、广告等媒介。尤其需要追问的是,文学在这个时代还是中心媒介吗?作家讨论文学,容易形成一种幻觉——文学是我们时代中心最有效的、最博大的、最深刻的媒介。其实我们都知道,电脑和手机早就占据了我们的生活,影像早就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朋友圈早就占据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在文学中一定要探讨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还不如借助一个更好的手段,比如影像、新闻。我觉得在新闻中谈论政治问题,或者直接談论底层生活,它更有效。电影或新闻报道表达底层人的生活,比我们写一篇小说、写一首诗,产生的普及性、社会轰动性更强。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借助文学?因为文学与电影、新闻存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文学是什么?我们要追问,它提供了什么样的认知、呈现和留住生活的方式?文学的表达,是对可能的生活的探寻和追问。当然,比起权贵的生活,文学更加需要去书写底层的、卑微的生活。因为底层的、卑微的生活往往是无声的。但是书写的方式必须是文学的,倘若我们不在谈论一种广义的、毫无边界的文学。如果文学有政治性,也就在于这一点。这让文学不断挑战当下的生活,以超越性的方式。另外,我要强调,文学的能力有限。有些事情需要通过其他媒介去完成,作家也应该参与影像、新闻等媒介。一个作家,除了能够写作,也能完成生活所要求的其他职责:伦理、政治的职责。作家不应该只能够写作。文学书写不是不可表达伦理和政治,恰恰相反,文学需要承担起伦理和政治的使命。但文学书写需要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创造性的表达,不然我们就不需要文学。文学、影视、新闻、微博、朋友圈都是对这个世界的不可或缺的表达,只不过它们的表达方式是有区别的。
第三,是生活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面,生活是具体的、历史的、复杂的。这个时候我们学习西方文学,不是一定要把西方文学中的那种表达方式和生活形态搬运进来,而是将其对生活的独特表达和感受力吸纳进来。我偏爱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因为它的手段是创造性的。文学并不是只能用来表达中产阶级生活(爱情、出轨、孤独、忧郁,等等)。在当下的中国,我们不是只有这种生活——在西方也并非如此,任何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都是还原了而不是缩减了生活的复杂性,都展现出对生活本身的不可约束的想象力。我们需要面对当下生活的伦理和政治。
回到生活之中,最终是想去呈现一种中国式的生活,或者不一定是中国式的生活,而是具体的、多样的生活,又是能够有所溢出的生活。但至少,我们在通过汉语这门母语去表达生活的旁溢。这样的写作,对话语本身的构成形态有着清晰的认知。但是,我不相信在这个正在到来中的“世界文学”的时代,一定区域内的生活仅仅凭借自身就可以产生超越自己的认知。“世界文学”时代的特征在于,各区域的文学需要吸纳别的区域文学之力量,来更新对自己生活的认知。在这种更新了的认知里,我们实现了文学的创造性,也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生生不息的力量。这种生活通向自由和可能,而不是通向束缚和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