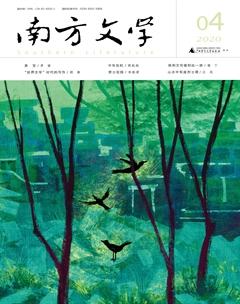电影八又二分之一
唐棣
第一部我要记下的是《威尼斯疑魂》(1973),这部电影前半段,悬念张力十足,可是越看越有错觉——这不是希区柯克的电影吗?时间碎在了各种水城景观的空镜之中。电影史上有名的“以假乱真”的情爱片段,就发生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刻——做爱场景与事后夫妇穿衣的镜头,交叉剪辑。效果是“时而交缠,时而分开,时而当下,时而未来,时而激情四溢,时而心事重重”。
电影1小时9分40秒,我看到建筑师约翰送走妻子后,也很无聊地坐在船上,这时他身边驶过一艘船,他意外看见了自己的妻子劳拉,身穿黑色葬礼服,站在那艘船的甲板上,在他呼喊妻子名字时,船匆匆驶过,很快不见踪影。随后,他企图找到妻子。
就是这个瞬间让我彻底醒了。记住了英国导演尼古拉斯·罗伊格。他比希区柯克擅长寓言。
——约翰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结束,电影结局已包含在他眼前的事物里。虽然,约翰不相信死亡预言,但他一定要找到妻子,也就是势必奔向我们都知道的结局。红衣小女孩作为他们的女儿,在电影开篇溺水而亡。在约翰从威尼斯寻找自己妻子的过程中,这个红色幽魂不断闪现。
可以说,任何电影中,威尼斯这座城市都没有这么古老而不祥,阴郁而鬼魅。电影片名Don't Look Now直译成“不要看现在”的话更好,在一部关于时间的电影之中,我们的现在包含我们的未来,未来中依稀可见过去。
这时候,谜团已解开,我可以告诉自己,最莫名其妙的“红衣小女孩”的意象,的确是昔日最美妙的象征。
第二部是我最喜欢的导演阿巴斯的《特写》(1990)。一个叫萨布齐恩的失业油漆工因为喜欢电影,冒充伊朗著名导演穆赫辛·马克马尔巴夫,取得有钱人阿汉卡赫一家的信任,骗钱拍片的故事。法官在法庭上问这个青年为什么要冒充马克马尔巴夫,萨布齐恩说了一大堆关于艺术、电影的话,大家显然对他的扮演有些无奈。
真正的答案在46分50秒处揭晓——
“因为,他们尊重我。”纪录片唯一的道德是尊重。这个尊重折射出年轻人在社会上的遭遇——“……如果我让他们把树砍了,他们就会砍,在此之前,没人会顺从我做这些事,因为我是一个穷人。”
1小时29分28秒,假冒導演的萨布齐恩在监狱门口,见到导演克里斯·马克马尔巴夫时,他哭了。
这部电影有意思的地方是真实与虚构的关系——阿巴斯的电影大部分都有这个标志。
青年萨布齐恩为自己虚构导演身份,这让他精神压力得到了缓解。而当真实的导演用摩托车载着他,去给阿汉卡赫一家道歉,他们在伊朗的街头穿梭。青年甚至买了一盆花。
电影结尾定格在青年抱着一盆花的镜头,那一刻他大概也得到了自己内心的原谅。
第三部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的《两生花》(1991),讲一个女人的两面。我迫不及待说出自己在这部电影里不大不小的发现。
首先是24分31秒处,是一个拎着两包东西的老妇人,步履蹒跚地走着。她把重物放下又拿起的动作,在镜头中,停顿足足7秒之久。当女主人公维罗尼卡推开窗,大声说“夫人,让我过去帮你”,老妇人却默然地走开了。
再到1小时 02分,老妇人的形象又出现在窗外,这次维罗尼卡用了10秒,注视着老妇人越走越远。
老妇人两次出现似乎与电影的主线无关。两个老妇人是否同一个——看上去,她们长得也很像,但通过背影能知道的是,她们都是风烛残年的象征,都是女人老去的象征。
在两个年轻女人的故事里,老妇人为什么会出现两次?
——年轻与衰老有对应关系,像《两生花》里两个身在不同国家、同名同貌的女孩一样。在时间的另一个刻度点,还有一个苍老的自己。
临老的时光,像天黑下来。天黑亮灯,而人老了,那道光在哪里?提到光,我下意识地会想起身处电影院的感觉,却没想过这和人生有什么关系。
人之“苍老”意味着时间的终结,那是一种迫近的感受,或者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临死”,对于这种感受,英国人亨利·菲尔丁说:“人生可怕的不是死,而是临死。”
第四部电影《阮玲玉》(1991)还得从录像厅时代讲起。我对录像厅的记忆就是香港电影。当年我还在上小学,总是担惊受怕地看电影,录像厅在一个公园对面,东边是图书馆,西边是民宅或公共澡堂已经记不太清了。录像厅总是站满高矮胖瘦的社会小青年,有时候他们还会喝酒。我们这些学生只能靠在角落,有几次放打架、追逐的片子,录像厅里也随之蠢蠢欲动,谁挨到谁,就开始骂、开始动手。录像厅瞬间充满了跟片子一样的江湖气氛。
我在录像厅里看到过一张脸,那张脸在这些回忆情节中闪过,我却不知道她是谁。高中肄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挤在一堆人中看到了《阮玲玉》。我心中的那张脸,就是从这部电影开始有了名字,那就是张曼玉。这部电影有意思的是,总在角色和真实人物之间摇摆,张曼玉一会儿是张曼玉,一会儿是阮玲玉。
这种恍惚的感觉,像记忆。张曼玉的脸还是那张脸,身体里却装着我完全不认识的阮玲玉的灵魂,就在我看这部电影时,似是而非地,存在于银幕上,又真真切切地,存在于记忆中。
第五部电影《银色·性·男女》(1993),改编自在国内很火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作品——不是具体某部,而是九部短篇小说和一首诗歌。导演奥特曼说过,“我把卡佛的所有作品视为一个故事”。
其实,卡佛的作品的确很像一个大故事。他有一篇小说叫《家门口就有这么多水》,写一个丈夫与人合伙杀死了一个女孩。后来,他想用同样的手法把妻子也杀了。到底女孩是不是丈夫所杀?到最后被冲淡在看似随意的对话中。最后夫妻回到了日常的睡前闲聊——“我爱你。”他说。他还说了些其他的,我边听边慢慢地点头。卡佛小说为人称道的是琐碎、日常、陌生,但这就是生活。
一对夫妻看上去很平常,你忽然发觉不太对劲,丈夫有些形迹可疑,因为一些不熟悉的细节改变了你对常规生活的看法。你现在觉得那个女孩很可能被这个丈夫杀死了。更有意思的是,你觉得丈夫还想把妻子杀掉,所以你静待一切的发生。
“雷蒙德·卡佛和我的世界观也许都有点黑暗。对于那些看似随意的事件的相似的看法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导演罗伯特·奥特曼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喜欢黑暗的卡佛,多过喜欢阳光的麦卡勒斯。
第六部《伊莎贝拉》(2006),按时间顺序,再次回到香港电影。这个故事发生在澳门,时间是1999年回归前48天。父女之间的故事从电影的中间位置才开始。
解释一下这个故事:
好色警察在若干年后遇到自称是他女儿的人,并且对他死缠烂打。而这对父女在彼此了解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各自人性中最温情的一面。
记得最深的是那种父女之间的小幽默,例如女儿和父亲在半夜一起提着大袋子搬家的姿势,或者在车祸现场看狗时候,父亲对女儿的玩笑——
她本来以为自己的狗肯定死了,可是一看却是父亲和她开的玩笑。它是女儿与父亲在上帝面前的承诺。
第七部《太平轮》(2014)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女人的心境,我称之为“爱的焦灼”——从底层女章子怡、富家女宋慧乔,到因战争而想爱不能爱的日本女孩长泽雅美。分别与她们对应的,是佟大为的患难之爱、军官黄晓明的街头之爱、金城武的悲剧之爱。导演标志性的鸽子会变成海鸥,兄弟情会变成爱情,本质上还是一样。
一个是会配合情境飞翔,一个是会让人愿意为之放弃生命。这是一部爱情片。从片中章子怡那个角色要买船票,说一定要睡遍全上海的男人中,看得出导演把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身上,请注意——是睡,而不是被睡。女人主动争取着自己的命运,掌控着自己的爱情。
《花样年华》台词说“如果我多一张票,你会不会跟我走”,這就是爱情;《太平轮》里佟大为演的那个通信兵说“我拼着命活下来,我就是想再见你一面”,这依然是爱情。
灾难面前,一艘大船如何隐喻时代?
“与其把生命交给战争,不如献给爱情”只是一种选择,一种一点不浪漫,甚至显得狭隘的选择。可是人生而为人,又总是无奈重重。
第八部要说的是比较受争议的《道士下山》(2015),我觉得它的主题比电影本身有趣:“是山,就得下;下去了,就是机会。”
——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人生设计。
“道士”不只是指具体的人物,我觉得电影还有另一种解读的空间——对电影中若干段故事,道士的意义是“看到了,就参与了”。秉承师父下山前告诉他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是一个参与者,一个参与度不够的参与者,因为对于山下这个世界,他很多时候是无法参与的。看到好功夫,就带着一张笑脸迎上去:“你教我吧?”
他没有那么多担心,万一人家不教给我怎么办?
道士这个人物是一根针,串起了一部分师徒与父子、门派的戏份,一部分战场上结识的兄弟、师徒、师兄弟的戏份,还有一部分兄弟、师徒面对妻子背叛的戏份。
小小的道士,就像人生中的一条小船,山下的世界则是一片汪洋。这是我对这部电影的理解——它的意义不在于展现一个多么正确和积极的航向,而在于随波逐流,磕磕绊绊地成长起来。
最后半部电影是我2017年筹备拍摄的一部爱情电影,一男一女一夜,以为会发生了什么,却什么也没发生。故事就是这样,人生也应如此。这年4月中旬,我大概落实了投资,就开始朝着一部电影而去。是什么想法让两人相见,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放弃欲望,平静地度过一夜?
这些问题在我5月份勘景的路上,才汇聚到一个词语上:痕迹。人和人的关系像是彼此在心中留下的痕迹。勘景回来,我就着手在剧本开头加了一段看似与主线无关的车祸戏——表哥在我筹备电影的那段时间车祸去世了。车祸是路上的突然事件,预示着一个种对原来生活的破坏,也是表明了一次重新开始。
8月10日,项目停下的那天,这部电影在我心中已经完成了一半。从最初的概念,走到人物栩栩如生,从两个人的故事,发展到两段记忆重叠,又分出两种人生轨迹——我已经很享受这个创作蜕变的过程了。
导演李沧东说过“电影不结束在灯光亮起的一刻,而是结束在观众生活中的某个瞬间”。山中一夜,两人下山,人生照常。作为导演,我最坚定的一点,就是坚持让这部爱情电影结束于明亮时——
早晨5点多,男主人公开车经过来时遇上的车祸现场,路边已经什么都不在了。车驶入隧道后,画面全黑,电话铃声响起,一块发光的手机屏幕显示出,刚在宾馆分开的女主人公的名字。他没有接电话,车冲出隧道,迎着一天里最明亮的阳光,飞驰而去。铃声一直响,在片尾字幕升起的那一刻淡去……
直到那时,“爱情”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一段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