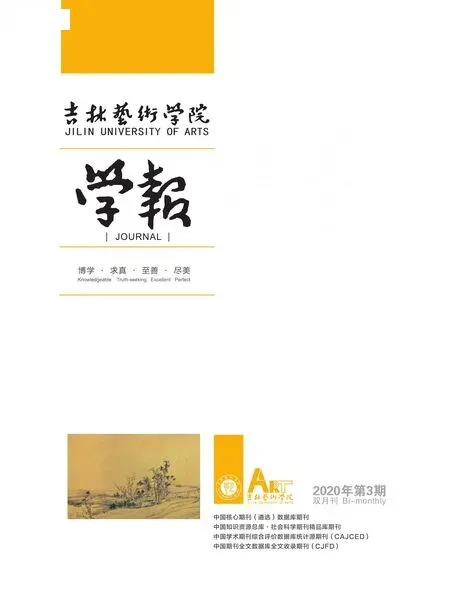承继与变异
——客家唢呐“七盏灯”仪式音声的考察与研究
罗钢芹
(嘉应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广东 梅州,514015)
一、“七盏灯”形成的人文背景
在历史长河中,无论是我国南方还是北方,吹打乐都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客家族群中,客家人习重礼仪,无论是婚庆、寿庆,还是祭祀、社火都少不了吹打乐班的煽情助兴,吹打乐已成为客家人精神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客家人都没有习惯唢呐(sorna)这个称谓。在当地,无论在文字记载还是日常生活中,客家人都习惯和中原汉人一样将唢呐称之为“笛”,而吹打乐班又称之为“笛班”,乐手称为“吹笛佬”。在客家社会千百年的唢呐吹打流传过程中,客家人以其智慧和才华将中原传统文化与客家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创造出一种独具客家特色的唢呐吹打形式——唢呐“七盏灯”。
客家唢呐七盏灯的形成与客家地区特定的族群属性、人文信仰、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它的形成也反映了客家社会基本的人文信仰和社会需求。
1. 人文信仰
客家民间自古就有尚巫崇神的传统,民间信仰活动在客家族群里是一种既古老又普遍的文化现象。客家人是南迁的中原汉人,在数次的南迁过程中,客家人将中原文化带到南方一带,如今的客家地区正是南北文化交汇融合之地。因此,客家人的神明崇拜也由此变得非常复杂,既崇拜全国性的神明,也崇拜地方性的神明;既崇拜道教神明,也崇拜佛教、巫教神明等。客家人每逢冠婚丧祭,都要举行庆典活动来敬神祈福,这些信仰活动为七盏灯民俗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文信仰基础。
2. 礼乐思想
礼乐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礼”主要是对社会中不同人的身份和地位进行划分和规范,“乐”主要是根据礼的等级不同和对象不同,运用与之对应的音乐来和谐社会关系。据《史记》记载:“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生,政之行也,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1]可以看出,在古人的丧、婚、冠等礼俗活动中,都有“乐”进行参与,礼乐思想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重要思想。
中原社会的礼乐思想在客家人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到今日,在客家的各类民俗礼仪活动中,民间音乐的参与仍然非常广泛,客家唢呐七盏灯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客家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七寸吹打拿在手,五音六律里边有,冠婚丧祭没有我,冇声冇息蛮难过”(冇,读音mao,即客家话“没有”)。虽然是一句不经意的顺口溜,但充分说明了唢呐吹打乐在当地民俗礼仪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3. 名称寓意
“七盏灯”名称中的“七”和“灯”字在客家民间有着独特的内涵。客家人常常认为“七”字代表着“吉利”,客家民间有“七上八下”“七生八死”的说法,丧事中又有“做七”的习俗等。[2]如“七盏灯闹寿堂”时,艺人喊到:“一盏灯到寿堂,椿萱并茂寿年长;二盏灯到寿堂,八一诞辰乐洋洋;三盏灯到中堂,寿星福气的确强;四盏灯到中堂,福星高照寿满堂;五盏灯寿年延,椿萱寿似彭子年;六盏灯颂寿仙,福如东海乐无边;七盏灯亮堂堂,寿比南山幸福长。”客家人对“七”的崇拜,归根结底均源自于“七”在客家社会蕴含的丰富文化寓意。
“灯”字在客家社会常常代表着“丁”和“火”,即认为“丁财两旺”。如结婚庆典时,艺人一走进主家大门便喊到:“新郎新娘,喜结鸳鸯,百年好合,地久天长。”主家接喊:“口为圣旨。”当载灯艺人慢步走向正厅时,随行的司仪喊到:“要灯不要灯?”新郎新娘齐声喊到:“要灯。”(即“要丁”)接着,载灯艺人走到正厅中央处停下,司仪在卸灯前喊四句吉利话:“七盏油灯亮闪闪,照得厅堂金辉煌,今年喜迎靓新娘,明年生得状元郎。”唢呐七盏灯的名称迎合了客家人在数字和文字中的特殊寓意,而这种特殊寓意也促成了唢呐七盏灯在客家地区的广泛流传。
二、“七盏灯”仪式的音声特征
1. 乐器与道具
七盏灯乐班由7人组成,即唢呐2人,锣、鼓各1人,小钹1人,护灯2人。乐班中使用的唢呐由乐手手工制作而成,高音唢呐音杆长约30公分,低音唢呐音杆长约37公分,用黄檀硬木制作,铜喇直径20公分。锣、鼓、小钹与常规民间乐队使用的型制一致。
道具主要由“灯”和“毛巾”组成。据七盏灯传承人彭炽宏介绍,过去使用的都是“马灯”,而现在使用“碗灯”,“碗灯”就是在碗口边缘贴上一圈齿纹状的红纸条,碗内立一根红蜡烛制作而成。道具中的“毛巾”主要用于遮住载灯艺人的脸颊,防止灯火烫伤。从七盏灯仪式中使用的“灯”来看,“马灯”明显是北方文化的产物,体现了七盏灯对北方文化的良好传承。而现在使用的“碗灯”,则是客家人结合当地文化不断改良的结果。
2. 表演特征
从表演上看,唢呐七盏灯吹打乐有“吹”“打”“念”“舞”四个表演特征。其中“吹”即指吹奏唢呐;“打”指打击乐的伴奏;“念”指仪式人员念诵的祝词;“舞”指唢呐艺人“走舞”的表演形式,这也是最为精彩的环节。在唢呐七盏灯表演的过程中,通常由低音唢呐手来进行载灯、送灯表演,司仪会将七盏油灯分别摆放在载灯艺人的头、肩膀、肘部、手腕上,此时,载灯艺人吹奏唢呐,边舞边行地完成整个送灯仪式,表演过程惊险刺激,需要载灯艺人掌握高超的载灯表演技巧和娴熟的唢呐吹奏技术。从整个唢呐七盏灯的表演来看,中原杂耍的表演成分和粗狂豪放的曲风特点尤为明显。因此,整个唢呐七盏灯表演具有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特征。
3. 程式性与新生性特征
唢呐七盏灯的表演非常讲究程式性,这主要体现在整个民俗表演的每个环节上。虽然近些年受文化环境的影响,唢呐七盏灯的表演难度在逐渐降低,但不管是哪支七盏灯表演队伍,在表演过程中,都分为“祝词”“上灯”“送灯”“接灯”这四个环节。并且每一个环节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表演时也不会出现省略某个环节的情况。
美国民俗音乐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认为:“任何表演都意味着它从来都不是第一次,表演的本质在于话语的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tation)和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station)当中,而后者尤为重要,表演总是呈现出新生性的维度(emergent dimension)。”[3]笔者认为,唢呐七盏灯的每一次表演,都受到表演者的主观因素影响,即使是表演相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表演队伍,甚至是相同的表演队伍,都会有表演风格上的一些差异。因此,唢呐七盏灯的每一次表演都呈现出新生性的维度。
4. 曲牌特征
根据表演内容的不同,唢呐七盏灯吹打分为“喜调”和“悲调”两种曲牌。在仪式表演过程中,各曲牌讲究“专曲专用”,即根据民俗活动内容的不同而选用相对应的曲牌。如在各类喜事活动中,唢呐七盏灯常使用乙字调、六字调、尺调子等喜调类曲牌;在白事活动中,唢呐七盏灯常使用悲调、双字调、反合调等悲调类曲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载灯艺人还会根据曲牌类型来改变表演方式。如演奏喜调类曲牌时,载灯艺人面带微笑,精神抖擞,此时的唢呐口微微朝上,演奏速度较快,艺人的表演动作和步伐也随之加快。演奏悲调类曲牌时,载灯艺人面部表情凝重,此时唢呐口明显朝下,艺人的演奏速度和表演动作、步伐均放慢。
5. 音调特征
在旋律音调上,唢呐七盏灯的大部分曲牌均采用羽调式和商调式为主。以羽调式婚庆曲牌为例(见谱例1),一方面旋律以La-Re为骨干音,主题音调以商音下行四度跳进到羽音(主音)作为旋律开始,特别在旋律进行中,商音的位置被多次强化,这些因素使曲调流露出一股中原曲风豪放粗狂的音乐特点。另一方面,在旋律音调中又穿插了一些婉转的小波浪旋律线条,这使得曲调又流露出婉转、细腻的客家小调风格。因此,唢呐七盏灯的音调风格具有承继性和变异性的双重文化特征。
6. 结构特征
七盏灯吹打乐在仪式中往往以单一曲牌不断循环来完成表演。从曲牌的结构来看,七盏灯吹打乐使用的曲牌大多为一段体,但唢呐艺人擅长将单一的音乐主题进行重复和变奏来形成较大的音乐规模。另外,在一些大型的礼仪活动中,唢呐艺人又会根据场合需要,将同类曲牌进行组合演奏,如在“七盏灯闹喜堂”仪式中,艺人常以《闹喜堂》+《四季春》曲牌来完成仪式,营造喜气洋洋的婚庆场景。
7. 演奏特征
两支唢呐在音色上,一明一暗;在演奏上,偶尔齐奏,大多是繁简结合,主题旋律在两支唢呐间互相承接(见谱例2);在演奏音量上,强弱交替、承接,互相陪衬,仿佛是两支唢呐间的对话,一问一答。旋律长音处常有“下滑音”奏法,这与客家人惯用的感叹语调十分相似,表现出艺人对艺术的精湛处理。打击乐的节拍固定,音量较弱,偶尔唢呐声停,单独出现一段打击乐演奏,让人感觉突然“安静”下来,产生遐想。
⑤从排沙角度,长江流域的雅砻江、金沙江、青衣江、嘉陵江、涪江、渠江、汉江的丹江口以上属于多沙区,而金沙江和雅砻江的源头、岷江、乌江、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为少沙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少沙区水库蓄水时间可以适当提前,而多沙区水库蓄水应该滞后。
七盏灯唢呐中的旋律承接、交替、繁简复合等手法,明显承继了北方唢呐的演奏特点,而旋律中频繁的“下滑音”又是对客家话语调的模仿。因此,七盏灯的演奏是一种南北文化的融合,既承继了北方唢呐的多声复合技法,又融入了客家语调的模仿成分。
三、“七盏灯”吹打乐的现状与保护思路
1. 现状分析
“当一种文化形态与传统观念相背离,传统的东西要么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得以流传,要么就被新的文化所替代。”[4]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客家唢呐七盏灯在生存和传承上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1)生存环境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客家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大量中青年农民外出打工、学习、经商,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红白喜事从简的思想在他们心中与日俱增。大部分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大张旗鼓的操办婚礼,有些甚至不举行任何仪式。在丧事方面,以前大多要做三天两夜的道场,而现在几乎只做一天,有些甚至不做。除此之外,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民间其他的庆典活动也在大量减少,如寿庆、满月酒、乔迁、庙会等。生存环境的变化使得七盏灯艺人们的收入大大减少,据老艺人彭炽宏介绍,现在他的乐班一年都接不到10场表演。
(2)铜管乐队的冲击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铜管乐在客家地区大量兴起,占据了城乡礼仪的半壁江山。特别是对于一些富裕的家庭而言,能请一支规模庞大的铜管乐队往往能给他们心里带来一种荣誉感、自豪感。如今的梅县一带就经常活跃着十多个铜管乐队,五华县也有五、六个铜管乐队。这些铜管乐队常常取代民间吹打乐班,或与民间吹打乐班共同参与到民俗礼仪活动中。
(3)同行的“优胜劣汰”
由于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普及,艺人们的活动地域大大拓宽,艺人间的优胜劣汰也更为激烈。据艺人彭炽宏介绍,以前五华县有六支七盏灯表演队伍,但现在能完整地载七盏灯表演的只有他一家。剩下几家由于表演少、疏于练习,现在只能载五盏或三盏灯表演,而且表演时还经常掉灯,已经很少能接到生意了。
2. 保护思路
(1)重建曲牌文本
据传承人彭炽宏介绍,在20世纪60年代的“破四旧”活动中,唢呐七盏灯的曲牌资料大多被烧毁,现在的表演曲牌大多靠载灯艺人的口传心授进行传承。从曲牌传承方式来看,“口传心授”传承会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干扰,影响曲牌传承的准确性。因此,对于曲牌的保护,当前应加快对七盏灯表演曲牌进行录音、录像和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文本重建。
(2)加大传承人的保护
文化学者冯骥才指出:“传承人是民间文化最濒危的现状之一。”[5]可见,民间文化的保护,关键是要保护好传承人。就目前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扶持这项民间技艺,授予传承人荣誉,定期给予传承人一定的资金补助,肯定七盏灯吹打艺术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要加大客家传统文化的宣传,鼓励年青人学习客家民间艺术,选拔一些优秀学员来传承唢呐七盏灯艺术,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3)重视客家民俗文化
七盏灯吹打和客家民俗文化之间,是“鱼”和“水”的关系,离开了客家民俗文化市场,七盏灯便无生存之地。我们应重视客家民俗文化市场的保护,引导客家民众认识客家传统民俗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同时,将客家民俗文化与客家族群的认同感相互联系,多方位、多举措地提升客家民俗文化的地位,为民间艺术的施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七盏灯”的文化人类学诠释
1. 民族性的意义
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标志和特性。西学东渐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在我国不断渗透,并取得话语权,特别在音乐界的表现更是如此,西洋乐占据我国半壁江山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客家的七盏灯民俗表演,保留了我国民族文化中最基本的符号和特征。这些民族性特征和符号,一是表现在七盏灯民俗表演的本身,二是表现在客家人的各类礼俗活动中,三是则表现在礼俗活动背后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上。七盏灯民俗表演对我们认识、传承客家礼俗文化,认识民族性和社会心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族群凝聚力的体现
七盏灯吹打乐在客家民间往往成为凝聚族群情感的重要纽带。在家族的祭祀、婚庆、寿礼、丧葬等礼俗活动中,七盏灯表演将宗亲和姻亲联结在一起,家族凝聚力在认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在民间集体性的礼俗活动中,如庙会和节日庆典活动中,七盏灯表演又将多个家族联系在一起,集体的祭祀和庆祝促成了族群的团结,凝聚力也在族群的团结中逐渐形成。
家族、族群凝聚力是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它们在长年累月的民间礼俗活动中逐渐形成,民俗音乐在这种凝聚力的产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客家社会的礼俗活动,音乐和礼俗往往联结在一起,共生共演、不可分割。七盏灯民俗表演在客家礼俗活动中,不仅是活动的背景和形式,有时更成为礼俗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五、结语
客家唢呐七盏灯是一种南北文化结合的产物,既保留了北方唢呐粗狂豪放的曲风特点和惊险刺激的杂耍场面,又融入了客家小调委婉细腻的音调成分,具有承继性和变异性的文化特征。随着文化变迁的加剧,唢呐七盏灯的生存正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我们相信,作为一种民族性的特征与符号,作为客家社会族群情感凝聚的重要纽带,唢呐七盏灯一定能在客家社会的民俗活动中继续担当重要角色。
——评陈辉《浙东锣鼓:礼俗仪式的音声表达》
——松滋礼俗——毛把烟、砂罐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