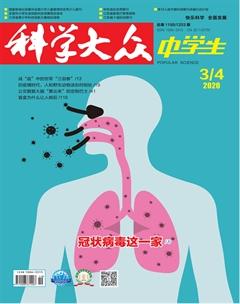后疫情时代,人和野生动物该如何相处
张燕宁



近年来,人兽共患病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尤其野生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呈上升趋势,世界范围内,在防控这类疾病上面临巨大挑战。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元凶,科学研究暂时指向中华菊头蝠这个寄主以及穿山甲这个中间宿主。这一系列研究推测逐渐在非专业的网络狂欢中“演变升华”,野生动物在一些人的眼里成为众矢之的,最终引发人们对“危险”的野生动物甚至动物的恐惧。
野生动物身上有病毒吗?当然有的。
野生动物会传播疾病吗?肯定会的。
野生动物危险吗?也会有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因为野生动物具有这些潜在的威胁性,就对它们赶尽杀绝呢?后疫情时代,我们究竞该如何同野生动物相处?
“危险”的野生动物
何为野生动物?《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将野生动物狭义地定义为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而广义地说,野生动物指的是那些“生活在野外自然环境而非经人工饲养的动物”。
这样的话就会引出几个问题:野外的老虎受伤后被救助,被送进动物园里,它还是不是野生动物?饲养场的鸡、鸭、鹅,是不是野生动物?公园里的毛毛虫、蝴蝶是野生动物,家里养的蚕宝宝是不是野生动物?家里的宠物猫、狗或兔子被遗弃后成了“流浪儿”,它们是野生动物吗?
我们按照定义去分析一下,如果老虎被救助后又被送回了大自然,它就还是野生动物;饲养场的动物属于驯l化动物,它依赖于我们的人工饲养,肯定不是野生动物;家养动物是人类长期驯化的结果,所以即使它们逃逸了或是被遗弃了,具备了部分野外生活能力,它们仍然不能被称为野生动物。
回到“危险”这个词,野生动物当然是有危险的,除了携带病毒,它们还具备与生俱来的攻击性。明天的危险会来自谁?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在这样的潜在危险下,有人提出了一个词语——“生态灭杀”。最近,由部分国内法律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建议,引发争议。其中提到,“对更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动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则可以考虑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允许科研利用和生态灭杀,但严禁食用”。言语之坚定,如同刘慈欣在《三体》里写过的那句话:毁灭你,与你何干?
暂不说“生态灭杀”这种做法对不对,就想想我们对有严重威胁的“外来物种”采取的灭杀行动何时成功过?澳大利亚的兔子?美国的亚洲鲤鱼?非洲的蝗虫?中国的克氏原鳌虾(小龙虾)?
有人曾说,“小龙虾是史上最悲哀的入侵物种,都不够我们中国人吃的,还要靠人工养殖”。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养殖小龙虾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野生的小龙虾难以大批量捕捉,并且可能携带寄生虫。事实上,野生小龙虾泛滥早已成为一个教科书式的生物入侵案例,它们遍布长江流域,造成很多本土物种区域性灭绝,并由此引发生态失衡。
刘慈欣在《三体》中还有一句话:弱小和无知从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认清你、我、它的生态位
现在,我们再来检视一下“生态灭杀”这个词。我想很多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有过“生物灭杀”这种想法一春天,南京街头的悬铃木毛絮满天飘,多少戴着口罩还打喷嚏的人想砍掉它们;夏天,蚊子四处飞,一定有人想过把蚊子灭绝了多好;还有那些蟑螂、老鼠、蝙蝠、蚯蚓,总有一款被你厌恶过。因为我们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所以动植物在人类心中还有别的分类方式——有益的和有害的、可愛的和丑陋的、能吃的和不能吃的……
然而,自然界的物种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分类,每种生物都是凭借自己的本领生存,并且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生态学一般将生态系统的生物组成划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植物是生产者,动物是消费者,细菌和真菌等是分解者,在纯自然生态系统下,我们人类本属于这条食物链上的杂食性消费者环节。但在今天,由于生物圈内几乎任何角落都有人类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人类自己的基础生态位和现实生态位几乎重合,与大部分生物都出现了生态位重叠和竞争的问题。人与动物单挑,确实很难获胜,但在群体对决中,人类赢得毫无悬念,此消彼长,如此下去,必然走向生物被赶尽杀绝或是人类与其他生物弱共存(互相伤害)的结果,然后呢……然后会有部分物种灭绝。
事实上,物种灭绝一直在发生。地球上出现过的生命形式有90%以上已经灭绝,一种生物灭绝了,会有另一种生物演化出来,取代它的位置。确实,物种存活与否,以人类的认知确实太难判断了,问题是,一个不健康的生态系统,也许会引发生态系统大范围的崩盘,甚至会引发经济、社会层面的危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所以,在生态保护中,需要拯救的从来就不是地球,而是我们人类自己。
1988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为了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为了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16年修订后,明确了它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法律框架下,我们已经开始逐渐明确自己的生态位,人类不仅仅是生态系统中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还应承担起生态系统中的调控者的角色,将原生态系统结构的被动自发协调转变为主动理性的协调。我们的调控途径,除了制度和法律,还应包括技术和文化。法律的规定和执法的力度,固然能限制人类对自然以及生态系统的伤害,但限制不代表停止,通过技术和文化手段提升公众接受度并增强人们对生态的保护认知,这才是关键。
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叶猴唯一的野外分布地区。而隐藏在大山中的一个小村庄——扶绥镇渠楠屯,在保护区管理局的批准下,已经建成了白头叶猴保护小区。村中的村民也拥有了保护区护林员的身份,成了白头叶猴的“保护神”。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白头叶猴繁衍生息的喜人场面,更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从0到∞,我们与动物的距离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守护,唯有你觉得野外的生灵美丽而有趣,才会担心它们的生存,才会真正理解为什么要保护环境。
在自然教育的领域里,最直观、最感人,也最容易引发共鸣的那一瞬间,无疑是“第一眼”。纪录片里的镜头真实再现,书本里的图片精美生动,动物园里的动物近在咫尺,可是当你在野外第一眼看到类人猿,第一眼看到世界上最大的花,第一眼看到荧光蘑菇,你才会知道,那是自由的模样。哪怕是一只普通的猕猴,你也会感觉它比动物园里的精神些。只有深入荒野,你才能看到真正的自然;只有与珍稀野生动物邂逅,你才能知道它们的生存现状;只有观察过它们的行为,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要与它们共享自然。随着这种镌骨铭心的相遇,对这种野生动物种群的保护也会逐渐展开。
那么,与这些野生动物的邂逅会有危险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没有能力判断动物的危险性。比如本文第一张图片里那只猕猴手中的面包,就是激动的游客投给它的,问题是猕猴是脾气最差的猴子,这种行为很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所以,与野生动物邂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或者跟随专业向导,以不打扰动物的自然状态为前提,保持距离,在充分了解各类动物的习性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选择。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没有条件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去邂逅它们,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看它们了?其实,很多人心目中的“看动物”,是去看伞护种、旗舰种(所谓“伞护种”,本身不一定有多高的生态學地位,但它们所需要的生存环境能覆盖很多其他物种,只要保护了它们,就能连带保护很多别的物种;而“旗舰种”甚至连生存环境这个要求都可以放宽,除了其珍稀保护价值,它的基本标准还有一条:能卖萌,能招人喜爱,能吸引眼球。大熊猫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旗舰种)。但是前文说过,每种生物都凭借自己的本领生存,并且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我们看来,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有观察价值。这里的野生动物,不应当局限于稀有的、著名的动物,无论珍稀或常见、可爱或丑陋,它们都值得我们去观察和欣赏,哪怕是一只在你家满墙乱爬的蜘蛛,都是很好的观察对象。
从0到∞,给自己挑选一个与野生动物链接的距离。我们观察它们、认识它们、了解它们,不是为了知道它们的名字、描述它们的分类,我们感受的是它们生活的环境,了解的是它们和环境的关系、它们与我们的关系,最终需要理解的是如何与它们共享自然。(作者系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守望自然科普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白玉磊责任校对:赵梦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