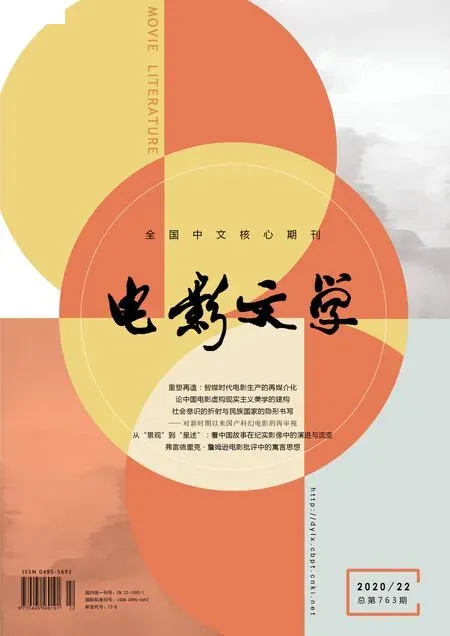论中国科幻电影的空间叙事
董迎春 覃 才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首部科幻性质的电影《六十年后上海滩》(1938)诞生以来,奇幻题材是中国科幻电影创作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的怪力乱神思想,以及古装片、武侠片的仙侠模式等奇幻增添了电影本体维度表现的奇观性。20世纪末,中国科幻电影生产普遍地植入机器人、生化武器、核武器及外星生物等科幻元素进行横向时间维度上的地理空间叙事,拓宽了中国科幻电影表现出显著的奇幻色彩。新世纪以来,顺应好莱坞题材的科幻电影的票房奇观,中国科幻电影也做了积极有效的尝试。以2019年的《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电影,借鉴西方科幻大片高投入、重视效奇观及主旋律叙事模式,将中国科幻电影的空间叙事扩展到纵向的太空空间、宇宙空间,显示了中国科幻电影在空间叙事的科技水平,以及空间表现和时代价值等方面的新探索。就中国科幻电影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而言,中国科幻电影从横向空间叙事向纵向空间叙事的转变与突进,既凸显了其从奇幻到科幻的类型转向,更缩小了中国科幻电影与欧美科幻电影的差距,具有里程碑性的价值。
一、从“奇幻”到“科幻”的空间转向
20世纪中叶以后,人文社科研究的空间转向开始影响电影领域,学术界对电影艺术的叙事认知也从原来的时间维度转向空间维度。在这一背景下,黑·卡恰德里兰在《电影中的空间与时间》一文中从二维和三维的透视视角将电影空间分为“(一)银幕表面所占据的二维视觉空间,即银幕空间;和(二)这个表面的影像(动作空间)所创造出的三维视觉空间”。戴维·鲍德怀尔从电影的结构、叙事、画面、声音等构成部分将电影空间划分为结构的空间、镜头空间、剪辑空间和声音空间及总体空间等,以此揭开了学术界对电影的空间叙事探讨。时至当下,电影的空间或其空间叙事不仅指电影制作、剪辑本身的“画格空间”,同时也意指电影艺术在“地理、历史、精神、虚拟四个维度”的空间叙事。就此,潘秀通指出:“所谓电影空间,乃是电影赖以存在的物质空间与幻象空间、银幕空间与画面空间、画内空间与画外空间……诸多范畴、诸多系列的交叉复合体。”整体而言,20世纪中叶以来的电影空间和电影空间叙事观,具有显著的技术、科技、媒体时代背景下的电影特征和接受特征,对科幻电影而言更是如此。
科幻电影作为诞生于20世纪初的电影类型(以梅里爱1902年的《月球旅行记》为标志),无论是其凸显科学技术和数字媒介手段的视效奇观(技术空间),还是其所表现的时空穿梭、太空旅行、机器人及超能力等后人类时代(近未来世界或未来世界)生存空间的题材特征,其叙事对象或者说审美参照无不是指向了一种技术和视效的奇观空间和空间叙事。就中国电影而言,虽然自早期以来“就在自己的叙事文化传统和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下形成了传奇叙事的镜头语言体系”,但表现出西方科幻电影凸显视效奇观和后人类时代空间叙事特征的作品在1938年的《六十年后上海滩》才有所体现。在此之后,虽然中国(包括香港)也诞生了《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错位》(1986)、《霹雳贝贝》(1986)、《大气层消失》(1990)、《隐身博士》(1991)、《长江7号》(2008)、《机器侠》(2009)、《未来警察》(2010)等定位为科幻题材的作品,但具有“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作品应是近年的《功夫机械侠》(2017)、《机械之血》(2017)、《机甲神七》(2018)、《疯狂的外星人》(2019)、《流浪地球》(2019)等作品。简而言之,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科幻片在中国电影产业中的比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与好莱坞科幻片生产总量相比,相差悬殊”。
就中国科幻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而言,由于受中国传统的怪力乱神小说或思想影响较大,其创作与叙事形式主要沿用中国电影主流的古装片、武侠片的仙侠奇幻模式,展现的内容主要也是修道、仙、佛之后具有的超能力和魔幻世界。与西方的科幻电影相比,中国这种“模仿和对抗传统西方科幻电影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奇幻电影,缺少的是属于科幻电影本身技术空间的视效奇观和后人类时代的空间叙事。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时代吁求之下,《功夫机械侠》《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作品展现了中国科幻电影对传统的奇幻电影的一种叙事空间、视效空间、技术空间及审美空间的超越与突围。可以说当下追求视效奇观空间创造和后人类时代空间表现的中国科幻电影发展趋势凸显了空间叙事对科幻电影发展的建构与推动意义。
显然,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电视、电影、远程通信、互联网及当下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诞生与发展,时代和社会不仅朝向“一个超地理的全球性的技术空间”方面发展,同时也越来越走向福柯所说的具有同时性、跨空间性的“空间的纪元”。因电影生产的机器发明、视效制作技术创新及探索后人类时代空间景象一直是科幻电影发展与转型的本质推动力量,科幻电影以其本体性的视效奇观(技术空间)和后人类时代空间叙事表现着时代和社会所在的空间纪元。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电影表现出的以视效奇观和后人类时代的时空穿梭、太空旅行、机器人及超能力等主题的空间叙事作品生产,整体上凸显了其对传统的奇幻色彩的反转与超越,2018年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视效制作技术、空间叙事及票房效应方面极大地拉近了中国科幻电影与西方科幻电影的距离。
二、凸显视效奇观和世界发展“主旋律”的空间叙事
在《科幻电影写作》当中,罗伯特·格兰特将科幻电影构成分为表现科学和技术主题的“硬科幻”(HARDSF)和表现政府、政治、经济、通信等主题的“软科幻”(SOFTSF)。具有国家或世界科技和政治发展主旋律特征的西方科幻大片即是“硬科幻”和“软科幻”的有效结合。在空间叙事这一维度上,科幻电影具有当下主流电影类型“使空间地域化”的介于真实与虚拟之间的未来世界地理空间创造、属于科幻电影本身的“硬科幻”即科学和特效技术创造的视效奇观空间和“软科幻”构筑的主旋律总体性叙事空间三种形态。在政治和科技的局限下,中国科幻电影的百年发展虽然“呈现出强束缚、重模仿、审查难的状态”,并在很长的时间段内具有奇幻色彩的科幻电影的发展特征,但随着中国航天、军事、人工智能及电影特效技术等科技进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幻电影生产也越来越凸显其作为科幻电影类型的视效奇观和主旋律题材并重的空间叙事探索。
首先,介于真实与虚拟之间的未来世界地理空间创造。凯瑟琳·海勒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科幻电影都是未来主义的。”在具体的叙事当中,未来世界(从未来返回过去也是以未来为参照)的时空穿梭及其生存空间创造和转换作为电影的“时空观”,既表现为电影当中横向时间维度上直接性的空间切换(从未来空间回到过去空间),同时也表现在不同空间世界当中的城市、高楼、陆地、海洋及地球等地理空间的画格创造。对科幻电影而言,这种未来世界的地理画格空间创造不仅直接地表现为具有一定现实真实基础又是特效技术虚构而出的地理空间,更是以这一空间切换的前提将科幻电影的超前、虚构性叙事赋予一种“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在中国科幻电影当中,《未来警察》(从2080年往回到2020年)、《功夫机械侠》(从未来机械时代回到清末民初)、《六十年后上海滩》(从1938年穿越到1998年)、《机器侠》(穿越到2046年机械时代)等具有横向时间维度上未来世界地理画格空间叙事的作品,在具体的世界空间当中它们往往以过去世界空间已有的中国武术或未来世界空间才有的基因技术、生化武器、机器设备等对抗黑暗势力、外星物种及机器人,以保护人类和拯救世界。
其次,“硬科幻”即科学和特效技术创造的视效奇观空间探索。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几近全部的中国科幻电影主要是以横向时间维度上的地理空间转换作为建构其科幻类型叙事的主体形式,以基因变异、生化武器、外星生物偶然掉落地球及超能力等科幻元素作为电影的题材和空间叙事构成,整体上缺少如《阿凡达》《星球大战》《变形金刚》等西方科幻大片在纵向空间维度上表现太空空间、宇宙空间及其他星球物种空间时以“数字绘景、定格动画、缩微模型、背投技术和计算机生成图像等特技”创造的视效奇观空间探索。2019年的《流浪地球》作为中国首部涉及太空空间、宇宙空间的科幻电影,它在2075年太阳老化、膨胀并即将吞没地球的前提下和人类要将地球推向4.2亿光年外的新家园过程中,以特效技术创造了地面世界(北京、上海、杭州等)的冰雪空间、领航员空间站的航天空间、地球和木星相互靠近和将要碰撞的太空空间等。这种以特效技术创造的视效奇观空间为主的空间叙事特征表现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幻电影类型本身共有的视效奇观创造和表达“不再从属于叙事的并且具有显著的侵略性、扩张性的图像‘奇观’……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叙事”的发展特征,有效弥补了中国科幻电影在纵向空间和特效技术空间上的绝对空白。
最后,“软科幻”构筑的“世界空间”叙事。西方主流的科幻电影当中,科学或者说技术的“硬科幻”往往会引出政府、政治、通信、军事等多个世界性的软科幻主题,以此创造出与西方资本主义或人类发展主潮相适合的“世界空间”。中国科幻电影发展,也是十分注重模仿和借鉴西方科幻电影的这一叙事经验。1980年《珊瑚岛上的死光》当中高效能原子电池研究、1986年《错位》当中创造的与赵书信局长一模一样的机器人、1990年《大气层消失》当中表现的地球臭氧层空洞、1991年《隐身博士》当中隐形药的发明及2019年《流浪地球》当中火种计划执行程序莫斯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政府、政治、经济、时代等在应对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生化和核武技术威胁及参与机器人学和人工智能开发竞争方面的综合影像反映。这种涵盖国家科技、政治、军事、太空及海洋等诸多战略的总体性叙事特征,构筑了中国科幻电影具有软科幻、主旋律色彩和传统的总体性叙事空间。
就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而言,虽然当下依然缺少如《变形金刚》《阿凡达》及《毒液:致命守护》等此类以成熟的纯CG技术(虚拟角色技术)创造外星物种或银河系或多维宇宙空间的视效奇观、空间奇观科幻巨作,但在时间维度上的横向空间、宇宙平行或垂直维度的纵向空间及每个时代当中国家或世界发展主旋律的总体空间叙事方面,中国科幻电影也开始以中国现有的科学技术、机器人学、环境与地球科学、生物遗传与基因技术、生化技术及数字媒介技术等研究基础和中国化的电影制作水准及软科幻的主旋律声音呈现了其对空间叙事的运用与探索。
三、“后疫情”时代中国科幻电影空间叙事的价值
作为凸显视效奇观和探寻世界或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电影类型,科幻电影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成为一种成熟、主流的电影创作类型。科幻电影能够在这个时期内成为一种成熟、主流的电影创作类型,除了制作技术的发展之外,最重大的原因是1961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代表人类首次迈入太空和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成功。这两个原来只能出现于人类的想象、幻想中的事件,如今却成为人类能够实现的事实。这就是说,科幻电影原来所表现、猜想的人类在未来才面临的时空穿梭、太空旅行、机器人、生化变异等主题,随着尤里·加加林进入太空和“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变成了闯入人们生活的现实。科幻电影所表现的这种既是未来又是当下的现实,赋予了科幻电影强大的现实震撼、电影价值及市场影响。
显然,科幻电影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迎来自身发展的黄金时期,尤里·加加林进入太空和“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贡献巨大。就人类的发展历史而言,尤里·加加林进入太空和“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标示的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人类的科幻年代。在此之后,人类再次来到的科幻年代即是当下的新冠疫情暴发、蔓延的年代,即“后疫情”的科幻时代。这个“后疫情”的科幻年代,虽然与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宇宙等空间主题不同,但也以生化危机、病毒变异的形式构成了全人类和世界的另一个现实。这就是说,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既深刻地影响、改变了人类对世界、未来的理解,也激活了科幻电影另一个维度的表现主题。应该看到,科幻电影一直以来都是一种与国家或世界科技和政治发展主旋律特征联系非常密切的艺术。在新冠疫情成为影响全人类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发展的最大现实之时,科幻电影就会介入其中。这种全人类、世界性的介入,势必将创造科幻电影新的电影创作与电影市场图景。
中国的科幻电影一直在寻求属于自身的“元”发展时代。2019年春节档的《流浪地球》以46.86亿元票房位居中国内地总票房第三,同期的科幻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票房也达22.14亿元,这种爆炸性的票房效应与市场接受度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国产科幻电影时代的来临。在这一科幻的浪潮当中,中国科幻电影通过对现有的“定格动画、运动轨迹控制系统、图像合成技术及当下顶尖的CG、3D拍摄等技术手段”的空间运用与探索,明显地表现出其对早期机械植入机器人、生化武器、核武器、外星生物等科幻元素的空间强化特征,并以此从地理画格空间、视效的奇观空间及主旋律题材空间方面构筑了中国科幻电影总体性的叙事空间。对中国科幻电影的当下和未来发展而言,地理、技术及主旋律层面的空间叙事既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叙事价值,又能创造科幻电影票房与市场的诸多可能。当然,在“后疫情”的时代,中国科幻电影还需要新的思考与转向,特别是对生化危机、病毒变异等题材的科幻创造与表达。
探讨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我们既看到当下科幻电影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也明白困扰它发展的原因。从历史的维度上看,中国早期(新世纪以前)奇幻特征显著的科幻电影,虽然它们普遍表现也以当下或未来的某项技术发明或突破,或是生化药剂和核辐射引发人的超能变异构筑电影的叙事空间,但在电影的主体叙事和镜头图像表达过程中,更多的是表现了中国武侠片、喜剧片、奇幻片的制作经验与思维。对早期定位为科幻的科幻电影作品而言,这种机械的科幻元素植入和简单的地理空间转换在电影的主体内容当中不仅比重非常小,而且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从属于具有时间特征的奇幻叙事。这让中国科幻电影整体上缺少特效技术创造的视效奇观空间。然而,新世纪以来通过借鉴西方科幻大片的制作模式,中国科幻电影慢慢地表现出以特效技术创造视效奇观空间来构筑镜头的地理画格空间和贯穿题材的主旋律叙事特征。这种凸显技术视效奇观空间、主旋律大片的总体性叙事空间的空间叙事转向是中国科幻电影摆脱早期奇幻色彩,走向科幻和构成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电影“破”与“立”的关键。
中国科幻电影近百年来的发展困境,除了有中国科技、政治环境及电影特效制作技术及资本投入等原因局限外,就电影的放映市场方面看,由于在新世纪之前中国传统的影院缺少高标准的数字电影放映厅,能够播放数字电影的3D银幕更是少之又少,这种3D放映硬件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科幻电影在画格空间、视效空间的探索,并阻碍中国科幻电影与市场传播。但随着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以“数字电影发展年”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和普及数字电影院及3D银幕以来,至2018年,据业界统计,“全国共有49条院线,全年银幕总数达到60079块”,“银幕的数字化水平达到100%,3D银幕数占比达89%”。当下,在中国居世界第一的数字电影院和3D、IMax银幕总量及近年来西方科幻电影的中国传播“酝酿”的空间冲击下,最终使《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这两部中国本土的科幻电影,满足了中国科幻电影发展、中国观众和电影市场的多重期待。
凯斯·M.约翰斯顿在《科幻电影导论》中指出:“人们对科幻的兴趣,不单单因为它在当代商业方面的强大吸引力,更因为它提供给整个社会的冲击性和变革动力。”在当今以图像视觉理解时代和人类空间的时代,以技术创造当今时代具有预言性质未来可能的科幻电影无论是其关于未来世界的地理画格空间创造,还是彰显特效技术创造的视效奇观空间探索及主旋律商业大片的总体性叙事空间构筑方面,其都以具有冲击性和变革性的奇观力量、预言力量及审美力量暗合了现代观众的图像、视觉、空间及影像期待。在全人类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后疫情”时代,网络电影、“云”观影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电影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可能是暂时的,也可以是未来的一个事实。在这一不确定的“云”趋势之下,科幻电影也需要求变和适应,以创造“后疫情”时代下属于科幻电影本身的发展时代。
结 语
2019年表现太空空间、宇宙空间及主旋律总体性空间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诞生标示着中国科幻电影对自身传统的横向空间叙事的突破与超越,并在技术空间、视效空间层面上拉近了中国科幻电影与西方科幻电影的距离。可以说当下中国科幻电影借鉴西方科幻电影高投入、重视效奇观及主旋律叙事模式的空间叙事观,表现了在凸显图像、视效奇观的时代审美趋势下观众和市场对科幻电影的认同趋势。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发展,最本质的要求即是在现在的纵向空间探索方面,走向以纯CG技术创造的虚拟外星生物和星球的空间叙事。对中国科幻电影的市场与时代发展而言,其在空间叙事维度表现出的纵深发展趋势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科幻电影的进步与兼容。“后疫情”时代是非常适合科幻电影发展的新的时代契机,中国科幻电影创作、营销需要适应“后疫情”时代的“网络化”和“云”特色,以创造自身发展的新阶段、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