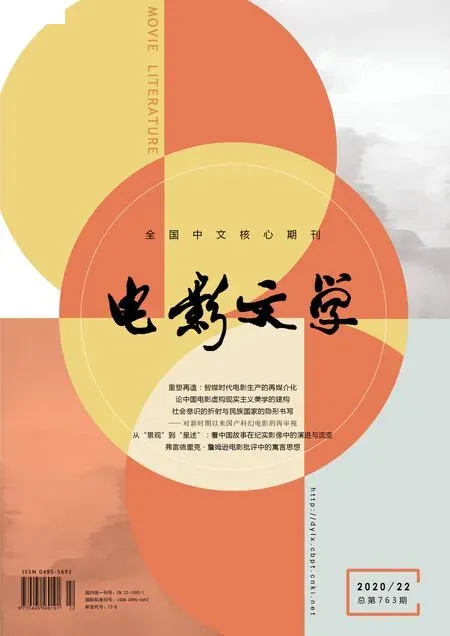叙事沉船:佩措尔德镜头下的“幽灵”们
王春香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外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75)
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把自己电影中的主角比喻成“幽灵”(Ghost),他认为,电影是关于幽灵试图找回自己的肉体性,找回自己归属感的故事。在《不死鸟》与《过境》中,主角沦为幽灵,这些幽灵重构自己身体与身份的背后,实则是在构建不同的个体创伤和关于欧洲的集体记忆。
一、《不死鸟》:身体的“再扮演”与身份的“不在场”
电影《不死鸟》讲述了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重构自己的创伤身体,并想以此找回记忆与身份的故事。面部毁容的集中营幸存者奈莉,在好友莱娜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乡柏林。容貌尚未完全恢复的她有了新的名字“埃丝特”,但不顾莱娜的提醒,她执意去找自己的丈夫乔尼。在她的记忆中,乔尼是保护者。以为奈莉已死的乔尼并没有在酒吧中认出奈莉,反而因觉得埃丝特与奈莉相似,而请求埃丝特假装自己妻子奈莉,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笔巨额财产。埃丝特选择配合他成为奈莉,知道了此事的莱娜在自杀前告诉了奈莉被捕之事的真相:是乔尼出卖了她。而奈莉选择一边探求真相,一边配合乔尼扮演妻子,一直到最后,乔尼才从她胳膊上刻下的集中营编号认出了她。
在《不死鸟》中,奈莉作为核心人物,集中体现着影片的矛盾与冲突,而她的朋友莱娜与她的丈夫乔尼更像是两个象征性的人物。前者代表了相对客观的全知视角,她熟知奈莉以及整个犹太民族遭遇的不幸,而后者则构成了一个有限的视角,如同一个冷漠却还多一层愧疚的过客。如此一来,奈莉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与选择则映射了奈莉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与身体。
在展现奈莉对自己身体与身份的迷茫之前,导演佩措尔德致力于消解她的身份,也就是将她变成一个“幽灵”,这是电影开场的一个重音符号。在一开场,奈莉的头就被包裹在血渍斑斑的绷带之下。即便如此,摄影机并没有直接展示她的头,而是选择忽视了她,将她拍成了一个阴影。接下来,导演采用了一个中景景别的固定镜头拍摄奈莉的病房,焦点聚集在坐在桌子旁边的莱娜身上,以莱娜的视角道出奈莉简单的遭遇,而奈莉始终处在焦点之外,成为一片模糊的背景。除此之外,导演还复制了许多“幽灵”来弱化奈莉的身份。在完成面容修复手术后,奈莉在一个夜晚走出了病房,来到医生的办公室寻找自己和乔尼的老照片。在医院的走廊里、病房里以及办公室里,她发现了无数个和她一样包裹着一模一样绷带的整容病人。这些和她一模一样的“幽灵”是奈莉的映射,也是奈莉的一次自我凝视,它不断提示奈莉她原有身体与身份不可逆的丧失。而另外一个符号——她和乔尼的老照片与这些“幽灵”构成了意象层面上的冲突,预示奈莉正处于悬置的处境中,将面临自我身体与身份的错位。
在顺叙的故事线中,导演设置了许多过渡的空间来呈现奈莉身体的“再扮演”与身份的“不在场”,比如战争废墟、莱娜给她的新房子或者俱乐部,而最为重要的空间则是乔尼的房间,因为当奈莉决定进入乔尼房间的那一刻,便意味着她对“回归”旧身份的渴望,意味着她需要乔尼作为辅助去重建、确认她的旧身体和旧身份。在学习表演奈莉的过程中,她以“埃丝特”的身份作为在场的表演者,而“奈莉”不在场,却是整个过程的见证者。
在重建旧身份的过程中,“埃丝特”的身体需要不断学习扮演“奈莉”的身体。重新学习成为“奈莉”的过程主要是通过系统化的符号来完成,导演把学习和扮演的过程拆解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以旧物件作为符号,另外一部分则是通过乔尼的叙述。这些客观存在的旧物件不仅成为重建奈莉形象的符号,也构建出了一种具有延迟性的创伤心理机制帮助埃丝特不断完成对记忆的回归与重建,这种“回归与重建”不仅包含个人记忆,也包含关于集中营的集体记忆。学者凯西·卡露丝在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著作《超越快乐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个体创伤、战争创伤的理论,她认为极具冲击力的创伤会在个体心理中构成具有延迟性的创伤心理机制和记忆结构。简而言之,创伤会封锁或者篡改记忆。在这样的机制之下,个体需要重复性地“入侵”“返回”创伤时刻来不断重建创伤时刻的记忆。因此,记忆会以意想不到的形式涌现出来,可能包含着自我身份的觉醒、自我欺骗与篡改,或者是对过去做出新的注解。因此,乔尼为了让埃丝特扮演奈莉所找来的旧裙子、鞋子以及信件既是“埃丝特”再扮演“奈莉”的跳板,也是让不在场的“奈莉”不断回归创伤时刻、刺激创伤心理机制并找回身份的跳板。
除了这些旧物件之外,乔尼的回忆与乔尼身份的不在场是对奈莉最大的刺激。在乔尼第一次遇见奈莉,以及在乔尼让埃丝特扮演奈莉的时候,乔尼对她否认了自己的名字,要求埃丝特称呼他“约翰尼斯”,只有在扮演的时候才可以称呼他“乔尼”。乔尼对自己名字的否定,也否定了他和奈莉的身份与记忆。在电影语言上,导演利用浅焦镜头更大程度地消融了奈莉在乔尼眼中的“不在场”,以构成对奈莉创伤记忆的冲突。在埃丝特和约翰尼斯的对话场景中,佩措尔德利用近景别的浅焦镜头,将二人位置拉近,却一直将埃丝特放在焦点之外,成为面目模糊的后景。配合着浅焦镜头的电影语言,佩措尔德强调了奈莉身份的不存在,尤其在乔尼眼中的不存在。而对身份“不存在”的强调配合着身体的“再扮演”是对创伤回忆的不断刺激,它既可以辅助完成“幽灵”的形象,又可以让身份和身体逐渐同一化。在最后的表演时刻,乔尼通过埃丝特胳膊上的集中营编号认出了眼前人的真实身份,而此刻奈莉已经完成了身份的觉醒,转身离开了乔尼。至此,电影通过“幽灵”勾勒出了个体创伤的延迟性的心理机制和记忆结构。
通过幽灵形象和创伤机制,导演描绘出的身份与身体的错位,更进一步以奈莉与乔尼、莱娜的关系作为中介表达了集体创伤的看法。《不死鸟》中,乔尼被愧疚折磨,试图遗忘犹太人被迫害的记忆,而莱娜却致力于救助犹太人,却因为在这份工作中感受到的冷漠而自杀。根据托马斯·埃尔塞瑟的观点,卡露丝的创伤机制与记忆结构有着主观同化的倾向,将集体的创伤历史变成国家策略上的叙事。托马斯将电影中的这种叙事倾向总结为:“以不在场为在场,以在场为倒置。”此外,他还批评这种做法是一种粉饰太平的策略,批评这样的电影不过呈现了受害者双重身份的遗失,并且还和这类遗失产生了和解。在《不死鸟》中,莱娜在术后对自己身体的不确定、对身份的不能认同构成了“不在场”的隐喻。同时,她对他者的扮演和重新恢复自己身份的潜意识描述了她的“在场”。最后,莱娜和埃丝特身份的错位组成了最后的错置。佩措尔德在结局通过奈莉的离开,推翻了这个叙事逻辑。也正应和了托马斯·埃尔塞瑟对国家叙事和双重遗失策略的愤怒。
二、《过境》:时空错置下的身份错置
2018年的《过境》也将镜头聚焦在了逃难的“幽灵”身上,它讲述了二战时期法国难民格奥尔在最后一刻从巴黎逃到了马赛。格奥尔原本需要带着作家魏尔登一起逃到巴黎,但在找到他的那一刻,他已经自杀身亡。他为了在马赛生存,冒名用了魏尔登的身份,并计划利用该假身份获得过境签证,逃出法国。在马赛他遇见了魏尔登的未婚妻玛丽,她一直在等待魏尔登的到来。在几经挣扎之后,他将船票让给了其他的人。
电影《过境》首先构建了错置的身份,“过境”首先意味着过境签证与逃亡,这是影片的核心人物动机。而影片中的人物之所以为“幽灵”,是因为他们为了获得过境签证,获得逃难的机会而不得不流亡,不断被驱逐,而主角格奥尔甚至盗用了魏尔登的身份。叙述产生了沉船,与一场人人自危的战争,马赛也就此沦为一座孤岛,不知名的旅店里集聚着等待着逃亡或者等待着死亡的流亡者们。于是,墨西哥大使馆与美国大使馆里排着长队,人们以苦难的语气讲述着自己的过往,也翘首以盼获得一张过境签证和船票。于是,旅店里不断有人因为无合法证件而被士兵带走,而沦落人满怀愧疚却不敢为此发声。于是穿着红裙的玛丽不断寻找魏尔登,却和拿着魏尔登身份的“幽灵”格奥尔产生新的交集。在大使馆与格奥尔偶遇的兽医以她即将离开这个地方为理由请格奥尔共进午餐,却在吃完饭的那一刻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沦为幽灵。在影片第一层的叙述中,“过境”意味着逃亡的可能性,而“幽灵”则是那些没有身份,也就没有逃生可能的流亡者,它构成了一个欧洲二战背景下的普遍语境。
而《过境》的精妙之处,是将历史放到了当代史的语境下进行了讲述,故意混淆着历史与现实,叙述令文本的世界观与空间分离,即错置时空使整部影片变为了一个虚构的隐喻。与一般历史片不同的是,导演并没有刻意装点、强调过去的背景,而将整部影片放在了现代的环境下进行拍摄。因此在关于二战逃亡者的故事里,观众却可以看见地铁、马赛的红绿灯、新潮的小酒馆以及新建起的建筑与房间。把时空错置,将二战流亡的故事放在了现代的背景下进行拍摄,无疑构成了对当代欧洲历史的隐喻。因而,《过境》不仅仅是描述了一个欧洲二战背景下的普遍语境,它还映射到了当代欧洲的语境,最显著的议题就是现代欧洲背景下的难民问题。
电影《过境》通过时空的错置和身份的错置,透露着一个预设的历史角度:关于二战流亡者的集体认同。在《过境》结局,导演设置了一个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情境,格奥尔让出了自己的船票,“幽灵”间的相处法则从生存过渡到了情愫,逃亡者成功占领马赛,而不再是仓皇逃命。导演强化着欧洲观念里一个预设的历史角度,即对二战流亡者的集体认同与同情,并将这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嫁接到了现代视角下的难民议题上。
结 语
“幽灵”作为导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镜头下的人物形象,通常指示着丧失身份的人们,而他们既渴求寻找到属于自己身体的“肉体性”,也渴望寻回精神和身份上的归属感。这种对于身体与身份同一性的追求,是电影《不死鸟》与《过境》的主要叙事动力。在《不死鸟》中,女主奈莉通过身体的再扮演与身份的不在场不断冲击着创伤心理机制和记忆结构,通过“回到”创伤时刻寻回自己遗失的身份。以奈莉为中介,《不死鸟》折射出对集中营受害者的关怀,对国家叙事策略下忽略受害者的不满。《过境》通过身份的错置和历史与现实时空的错置,使二战流亡者的故事与现代难民问题彼此折射,形成互文。而在整个叙事策略的背后,仍然捍卫着欧洲语语境下一个得到共识的历史角度:对二战流亡者的认同与关怀,以及延续到如今形成的对难民的关怀。总而言之,“幽灵”是佩措尔德政治历史表达的中介,充满着对欧洲历史与国家态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