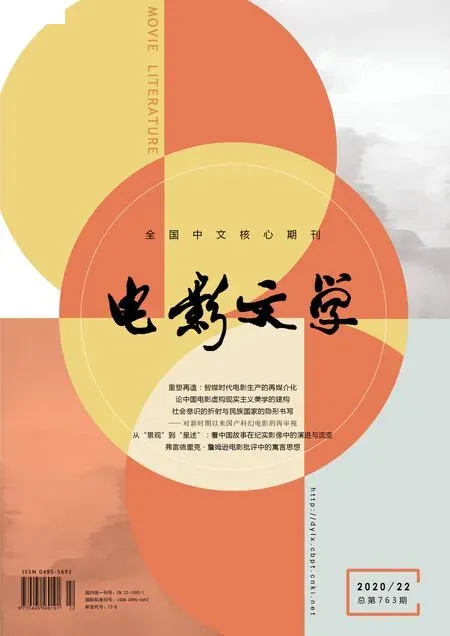从异质拼贴到文学改编
——娄烨电影研究
田 洁
(晋中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娄烨的电影长于情感流淌与诗意缠绵的氛围营造,而担任娄烨多部电影编剧的梅峰指出娄烨电影中“诗情”的特点,将诗歌的节奏带进影像叙事,时间的复沓传达人物纠结的情感,牵引人物微妙复杂的内心状态。电影镜头关注剧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捕捉人物于爱情消逝后怅然若失、无处呻吟的苍凉处境,开放式的收尾更留下绵长的悠韵难以消散,为此,勾起笔者对娄烨电影文本的窥探之念。除了电影传达的诗情氛围,娄烨多样化的电影形式,让笔者在观影过程,脑中总是浮现诸多导演的影像印记,这或许跟他成长背景过程看片量极大有关。这些观影过程的似曾相识让笔者对娄烨电影的“互文”产生兴趣,进而关注到他电影中对原文本﹙hypo text﹚的挪用,电影拼贴童话、纪录片、歌曲等异质元素,丰富电影文本的内涵。笔者意欲捕捉娄烨电影里出现原文本的细节,从娄烨电影和原文本的异质拼贴过程中,分析娄烨如何在纪实又迷离的拍摄手法中转化原文本,展示电影文本的多重意涵。娄烨电影的作品从《周末情人》至《推拿》已累积九部电影作品,明显表露娄烨电影的影像风格。近年来国内相关学位论文对娄烨电影的研究数目递增,并着重于对娄烨电影整体风格和美学的探讨,显示娄烨电影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综观目前娄烨电影的研究,已从娄烨电影文本的单一分析进入到娄烨整体风格的探究,并宏观探讨中国电影环境与娄烨电影的关系。然而,从互文角度切入娄烨电影的分析仍未见综论,并且娄烨较新电影作品《花》《推拿》的超文本﹙hyper text﹚和原文本之间的关系亦未完整研究。故笔者以娄烨电影的文本分析为研究基础,从影像叙事、电影情节、镜头语言深入娄烨电影的肌理。进而参照原文本,探讨娄烨早期电影如何挪用原文本,创造电影多重解读的空间,以及改编电影和原著小说之间如何转换,呈现娄烨电影和原文本碰撞出的意义,梳理娄烨电影从异质拼贴到文学改编的发展脉络。
一、真实与虚幻之间——娄烨早期电影与原文本的拼贴重组
娄烨早期作品依序为《危情少女》《苏州河》《紫蝴蝶》和《颐和园》,作品从电影语言的边界展开探索,揭示电影虚构的本质,明确展示不确定性的影像叙事,进而赋予电影在爱情主题的各种想象。娄烨认为第五代导演群体因电影语言的单一性造就第五代后期作品走向极端风格化、造型化的创作局限,让镜头所记录的影像失真。而电影《黄土地》的出现被定位成真实再现异域的作品,更误导第五代后期在电影语言尚未成熟时即追求电影风格样式的创作现象,阻碍了中国电影之后的良性发展。娄烨曾表示:“我认为语言限制了他们思想的传达。我完全能感受到他们思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是,受到语言表达的限制,于是思想变得单一,缺乏了他们原先开始构思时候的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第五代后期作品在电影语言贫瘠的状况下阻碍导演再现“真实”的可能性,形成“后黄土地”现象,而娄烨借鉴第五代后期的创作困境,采用模糊电影虚实的策略拓展电影语言的边界,让镜头随各种电影语言呈现作者意欲表现的真实。
《苏州河》里形式和内容的矛盾组合,实为探讨电影本身的虚构过程,而娄烨认为电影的虚构过程不仅是电影本身的虚构性,更涉及每个人对于真实的设想。当每个人看见同一件事物时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并投射自我主观的认知,而事件通过每个人的设想后的理解即含有虚构的成分。此外,《苏州河》里剧中人物对自己所阐述的故事产生迟疑,亦凸显电影内部的虚构过程。《苏州河》中人物所表现叙事的不确定性,更在电影《紫蝴蝶》有明确的展现。娄烨表示:“其实,在《苏州河》里,就有许多想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当初未必都做到了。这一次,在《紫蝴蝶》里,走的步子更大了,顺着《苏州河》的思路,往前跨了一大步,所做的就是,在摄影机面前被拍摄的东西的‘不确定性’,更明确了。”
电影《紫蝴蝶》顺着《苏州河》的思路延伸创作,更进一步地展开不确定性的影像叙事。娄烨认为:“电影作者只能是摄影机和它面前的对象之间生动、不确定的互动关系的把握者,是在剧情大致确定之下活跃的探寻者。”电影作者并非完全指导电影应该如何进行,而是在拍摄过程和剧本创作中持续捕捉不确定性的影像和故事。此外,电影《颐和园》的镜头语言延伸《紫蝴蝶》带有影像叙事不确定性的特点,娄烨曾透露《颐和园》的拍摄方式:“我鼓励即兴表演,完全不允许演员走位置,不允许定机位。我和演员工作排戏的时候,摄影组不许在场。非常极致的一种方式,我要造成的实际上是摄影机和拍摄现实的一种偶合性。”演员的即兴表演和摄影机顺着演员表演后的碰撞,让电影产生难以把捉的影像叙事。
电影《危情少女》里女主角汪籁在梦境和现实之间游走,影片频繁地使用虚实交错的手法,营造汪籁身处真实和梦境之间的境遇。电影片头片尾采用画外音和倒叙手法,重构汪籁对梦境的记忆,呼应首尾以梦境相连的剧情结构,而记忆的不确定性则反映电影里似真似幻的情境。剧中汪籁对记忆中梦境的设想,或制造影片虚实难分情境的手法,或许隐含导演娄烨意欲探讨电影本质的目的。娄烨在电影《周末情人》完成过后开拍第二部作品《危情少女》,正式进入中国电影体制内制作。影片的商业诉求无疑成为娄烨拍摄电影的考量之一,《危情少女》如何在个人特色和商业性质之间取得平衡,令娄烨在电影制作过程中感到困惑,“现在越来越难判定,是安东尼奥尼电影还是成龙的《红番区》更接近电影的本质”。而娄烨对于类型电影何者更接近电影本质的疑惑,也间接反映在《危情少女》极端的影像风格中。《危情少女》让人难以清楚区分梦境和现实的剧情,及虚实交错模糊影片真实性的手法,说明娄烨对电影虚构过程的探索早在《危情少女》中已可初见端倪。
《危情少女》创作目的为娄烨试图掌握更多样化的电影语言,娄烨曾透露:“我想碰碰那个边,电影的边,就是它能到什么程度,或者说碰碰自己的边,能达到一个什么地方。”娄烨在《危情少女》着重探讨电影语言的可能性,其跳脱首部作品《周末情人》偏重纪录片形式拍摄底层人物的琐碎生活,改以极为戏剧性的情节发展和风格化的影像实验为主。电影镜头本身作为一个记录框架,意在追求真实,然而娄烨却尝试从记录框架里拍摄极为戏剧化的情节和风格化的影像,企图拓展电影语言的宽度。娄烨透过丰富的电影语言让镜头贴近导演所欲呈现的“真实”,突破第五代后期因电影语言贫乏遮蔽导演所欲拍摄“真实”的创作困境,进而解决其在《周末情人》后所意识到得电影语言不足的问题。
《危情少女》的镜头语言一反《周末情人》的纪录片手法,影片不再追求真实的影像记录,其透过虚实交错的手法再现主角汪籁光怪陆离的经历,并磨合电影虚实的边界。影片明显表现出黑色电影﹙film noir﹚和恐怖片的风格印记,呈现娄烨对类型电影的多方探索。电影DVD封面形成电影的准文本﹙para text﹚,标注电影为“第一部空气恐怖电影大片”,凸显电影作为恐怖片的类型。而影片对光线的实验含有黑色电影的风格,影像的明暗对比极为强烈,剧中人物仅被局部打光,或人物拿着唯一光源,与周围的黑暗形成高反差﹙high contrast﹚,制造电影的悬疑惊悚氛围,并凸显人物焦虑不安的心理状态。娄烨电影的暗部处理区别了第五代曝光过度的手法,以对光线的准确掌握加以保留35mm胶卷上黑暗部分的烦琐细节。影片里藏于灰暗区域的角色面容在光线细节的保留下显得更为真实,让人得以从暗部雕琢的细微变化洞察角色的精神世界。娄烨《危情少女》为延伸自己电影语言的宽度,尝试黑色电影和恐怖片类型的多样风格,并严格处理影像光线,企图走向极端戏剧化的情节和风格化的影像,从中打破镜头本身表现真实的记录框架,隐含电影本身的虚构性。
电影《危情少女》片头显示“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方”,之后由女主角汪籁的画外音带出字卡所指的时空:“以前有段时间老是做梦,梦见好多好多我当时根本不明白的事情,后来长大了,懂了,可那些梦也全忘了。只有一个梦还记得,完整记得,后来再也没有做过像这样的梦,再也没有见到过像梦的那样的世界。”镜头拍摄人物脸部全部涂白的时空,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氛围,而梦境作为剧情的重要情节推展叙事。影片虚实交错的手法让汪籁游走在梦境和现实之间,模糊汪籁对梦境重新拼凑的记忆。此外,片头字卡“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方”出现于电影片名“危情少女”之前,或许片头字卡也影射电影本身即是另一个时空,娄烨将记录框架的镜头对准极端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和影像风格,进而从反记录的做法揭示电影本身的虚构性。
电影片头带出主角汪籁的梦境,镜头刻意拍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主角汪籁翻开此书,书中夹藏某些信息,但汪籁还来不及细看就被诡异的叫唤声给惊吓,而将书抛到脑后。之后字卡交代“汪籁醒了”,剧中醒来的汪籁又从母亲的书柜发现《仲夏夜之梦》,印证梦境里发生的事件与现实切合。《仲夏夜之梦》作为电影虚实交错手法中的重要物件,模糊汪籁处在梦境和现实之间的界域。此外,影片借《仲夏夜之梦》一书所夹的信息,带出汪籁继承家产的证明,同时却也引来父亲汪敬企图强夺汪籁家产的情节,而《仲夏夜之梦》与书中所夹信息亦暗示汪籁和刘家新互为父女的关系,《仲夏夜之梦》勾连出片中戏剧化的情节发展。电影刻意拍出《仲夏夜之梦》作为夹藏信息的媒介,模糊剧情虚实,其更作为原文本丰富电影里真假难分的梦境。电影以汪籁的梦境作为叙事主轴,《仲夏夜之梦》里的梦境情节则巧妙呼应汪籁的梦境。
电影末尾路芒为了拯救汪籁而和汪敬冲突对峙,汪籁则从后面用枕头偷袭汪敬,汪籁用枕头打击汪敬的影像,配合重击的音效产生逼真的效果,却也造成不合逻辑的情节。而影片在高张力的冲突过程里,枕头的棉絮在汪籁击打汪敬的过程中大量溅出,并持续不断地从天而降,形成一种奇异诡谲的现象。后镜头采用远景拍出大雪纷飞的样貌,并逐渐拉近至地面,原本看似雪景的影像实则为棉絮所形成的奇景,透露电影场景的虚构过程。剧中汪籁用枕头重击汪敬头部的情节,以及棉絮造成雪景的幻象,都混淆剧情的虚实,让人不断质疑镜头框架摄出的真实性。电影末尾所出现不合理的情节,借由汪籁再次惊醒的影像和画外音点破,片中大量的剧情实则为汪籁所重构的梦境,颠覆电影片头字卡“汪籁醒了”从梦境带到现实的逻辑认知,结局延续虚实交错的手法让观影者理不清何为真实、何为梦境。而电影片尾画外音所提到“美好的结局”,应指汪籁醒来过后又剪接回梦境里的影像,影片透过叠印手法转场,营造如梦似幻的效果,并带出汪籁和路茫在大雪/棉絮中拥抱的情景。电影的结局安排和《仲夏夜之梦》巧妙呼应,影片里汪籁再次从梦境醒来,回忆似真似幻的梦境,与《仲夏夜之梦》主要人物做了一场极为真实的梦境,形成似曾相识的经验对照。
二、娄烨电影《推拿》与毕飞宇小说《推拿》的互文转换
娄烨在改编电影《花》之后,接着就以《推拿》为改编对象。《推拿》是知名作家毕飞宇同名小说,毕飞宇小说细腻描绘沙宗琪推拿中心里众多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而娄烨首次以盲人题材为中心,透过影像语言呈现盲人群体的故事。电影《推拿》编剧马英力曾述及娄烨拍摄时强调电影和原著小说互为文本的密切关系:“他曾经说过,他希望把《推拿》做成一部小说和电影互为文本的作品,让看过小说的人想看电影,看过电影的人想去看小说作品。”娄烨对改编电影的期望在于透过对原著的选择、扩大和转化,紧密联结电影和小说的互文关系,产生引人对读的文本魅力。
电影《推拿》以盲人为主要题材,为了模拟盲人的感官,接近盲人的生活原貌,电影在技术层面上有着非常多需要克服的部分。镜头语言亦有所侧重,电影场景绝大多数都在室内,手持摄影机方便在狭迫的空间内穿梭,在庞杂的人物移动当中迅速地转换视角,捕捉每位角色脸部神情与细微动作,并模拟盲人“看”东西的方式,“健全人是看到一个事物的全貌,而盲人看东西时是只会看到东西的细节,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会采用手持的方式,去把这些细节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事物的全貌”。而手持镜头所造成的摇晃感亦凸显了盲人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混乱纠缠的情感状态。电影在景别的选择上,多采用特写带出盲人对于周遭认知的局限,进而让观众感受到盲人的障碍。
电影在听觉的处理上细腻地模拟盲人的感官,盲人在声音信息的接收上是大量的,他们透过声音来理解周遭。因此,声音成为这部电影传达信息的重要媒介。此外,电影尽可能在一个画面并置各种声轨,环境音、画外音、配乐与对白接连同步释出,借声音的细腻处理模拟盲人对声音觉察的敏锐度,以听觉感官作为电影的导向。电影不论在剧情发展过程或单一画面都置入大量声音信息,将电影的听觉感官极尽开展。相较于听觉,盲人的视觉则是受限的,如何让一部关于看不见的电影能被看见,娄烨为了解决这项“悖论问题”,对镜头语言做了诸多尝试。电影为了接近盲人视觉障碍的感受,鲜少采用远景拍摄,多以近景展现空间局部与地理关系,而镜头有时更逼近角色本身,透过特写捕捉他们压抑封闭的内心状态。镜头的近景与特写呈现盲人接收信息的障碍,而运镜模拟了盲人摸黑认知的过程。电影除了近景与特写的运用外,跟拍镜头﹙following shot﹚迫近角色本身移动,取景也是框限在狭小的范围进行摄影机运动,在视野有所限制的情况下,镜头语言模拟了盲人的触觉,摄影机在移动过程中仿佛变成了盲人的手,从门面逐步展开探寻,近似于娄烨所说的“抚摸”,竭力营造出盲人感知的方式。
电影《推拿》在制作上模拟了诸多盲人的感官,其尽量避免由视觉接收影像信息的方式,从片头以画外音念出剧组名单,间接道出电影在听觉上的注重,“它是制造了一个障碍环境,我们需要提醒健全人、提醒所有正常人观众,这将是一个视障环境的世界、一个声音优先的世界。毕竟这是关于‘盲人世界’的故事,所以它的听觉和视觉的比重关系不一样”。电影片头以画外音道出片名,直至剧末才打上斗大的“推拿”字样,显现视听比重的差异。而画外音不仅从片头带出,强调听觉的重要性,并且分散在各个电影段落,形成剧情上重要的过场,娄烨亦说:“画外音,可以让人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听的电影,声音优先的姿态,同时也希望能保持一些厉害的、准确的毕飞宇的语言,这是我特别希望的。”画外音保留精彩的小说文字,同时采用生冷的语气念出,电影不透过旁白渲染角色情绪或引领观众情感,而是结合毕飞宇小说里冷静客观的语言特点,保持中立视野观看盲人。此外,画外音采用疏离口吻也是为了让盲人能够阅听电影,娄烨表明:“画外音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盲人声轨,这是一个关于盲人的故事,我希望盲人也能‘看’这部电影。”画外音在电影中起了多重作用,模拟偏向听觉为主的电影,并将小说里的文字精练改编放入电影段落,辅以细腻的声音设计,使得观众更为接近盲人听觉的敏锐感知,细听文字与影像的对话。
电影剧情在小马和小蛮从洗头房失踪后,镜头环视洗头房里每个角色落寞的神态,笛声在电影院亦随着镜头做了一次环绕,最后回到吹笛子的张一光身上,辅以画外音道出:“命运实在是一件不可捉摸的事情,在命运面前,其实盲人和健全人一样都是迷信的,多多少少有一点迷信,他们相信命,因为命是看不见的,盲人也看不见,所以盲人比健全人更了解什么是命。对于盲人来讲,看得见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看不见的东西才是存在。”电影以画外音诉出盲人和健全人面对命运时同样抱持的迷信心理,环绕的运镜捕捉洗头妹们各自沉溺心事的表情,呼应电影情节在激昂过后对每位盲人表情的剪接处理。他们面对情感、面对命运的内心处境都是无异的,而命运不可预知的形式在视觉无法洞见的状况下,似乎又与盲人更为接近。镜头与声音的环绕搭配建构出命运环伺于观众周遭的氛围,意欲让观众贴近盲人听觉感受,而强调听觉环绕性的同时,漆黑的电影院更暗藏命运伺机浮动的气息,让人无法驳倒旁白里文字情境的感受。电影对于盲人感官的模拟更将想法从听觉延伸到了盲人的视觉,企图从黑暗的影像中有所突破。
电影做出了小马突然恢复“视觉”的段落,可以说是电影改编小说最大的地方。如何让盲人的感官以“看得见”的形式出现一直是电影改编的难题,娄烨曾透露:“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大困难,就是要传达一些类似于失明,或盲人对世界的感受,但这个电影又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看不见的形式。”对于“盲视觉”的诠释,可能又比盲人其他感官的细腻模拟来得无从着手,如何从盲人眼底的黑暗透显出可见的影像,电影剧组如同盲人一般,在前制与拍摄过程中不断摸索盲视觉的各种可能性。娄烨对盲视觉的模拟以“自然光”作为发想,其“自然光”应指影像以自然的光线呈现,并且消解了盲人视觉应有特定光线的概念,盲人与一般人对光线的感受无异,只有明暗的区分。电影中停电的情节,小孔在黑暗的情况下引领高唯下楼梯,同时小孔说出:“眼睛是有分工的,一部分眼睛看得见光,一部分眼睛看得见黑。”这段话也可作为以“自然光”的拍摄思想呈现盲视觉的佐证,人的眼睛只有看得见光与黑两种主要视觉,明眼人的眼睛倾向“看得见光”,盲人的眼睛倾向“看得见黑”。盲视觉并没有独立于明暗之外,没有额外的光线是属于盲人的,盲视觉即在调和光与黑两种观看模式,让人熟悉于明亮部分的眼睛更接近黑暗的视觉。
娄烨电影采取人所感知的明暗变化切入盲视觉的影像,透过多种镜头的视觉效果与实验属性的拍摄手法极尽揣摩光线的明暗组合。而电影的拍摄过程亦尽量降低对光线的修饰,多以自然的光线捕捉影像细节,让光线呈现纪实与魔幻的风格。盲人的视觉并非由“盲人的光线”去延展,而是透过人所共同感受到的自然光加以调整,并以白天与黑夜的自然光为主,电影从日夜取景进行拍摄,而光线通过镜头语言形成各种影像素材。盲视觉即在这些影像素材交叉剪接当中,拼凑出盲人经验所视的影像。
电影从日夜景的交切模拟盲人视觉可能的影像外,同时也是一种盲人内心状态的呈现,明暗闪现的背景代表盲人内心的不安与焦灼,以及他们生理时钟的混乱,盲人理不清白天与黑夜的差别,被拒斥于时间之外,小说曾提到:“健全人再怎么用功,再怎么‘夜以继日’,再怎么‘凿壁偷光’,再怎么‘焚膏继晷’,终究还有一个白天与黑夜的区别。但是,这区别盲人没有——他们在时间的外面。”盲人无法感知日夜的轮转,无法从光线掌握时间的流动,他们需要透过外部资讯来确认时间,因而电影多次插入声音的报时让盲人与时间产生联结,提醒盲人对于时间的觉察。
电影中部分影像明暗闪烁的效果可能类似于盲人对光线的模糊感知,或呈现盲人内心的波澜。盲人的视觉经验透过人所共感的光线作为发想,电影在繁复的拍摄过程中实验光影的各种组合,盲视觉即在日夜交替与镜头转换的过程被影像彰显出来,而盲视觉就像盲人与明眼人之间“心灵的大门”,让观众更为贴近盲人的感官,进入他们所存之世界。
结 语
《危情少女》《苏州河》《紫蝴蝶》和《颐和园》四部娄烨早期电影都在实验电影语言的各种可能性,开展出娄烨探索虚实界限的影像之路。《危情少女》运用虚实交错的手法对第五代后期电影的“真实”提出质疑,反对第五代后期以单一性的电影语言不断复制第五代初期影像美学的创作态度,局限镜头呈现多样化“真实”的可能。而电影更将形式内容推向极端,突破镜头本身的记录框架,以极为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开展,并挪借原文本《仲夏夜之梦》强化主角汪籁难以分清现实和梦境的处境。透过电影最后的段落,汪籁立处窗边的背景,隐约可见现代化的城市景象,和剧情设定20世纪30年代的背景产生时间错置,娄烨亦曾对电影时代背景的设定给出暧昧的答复,电影虚实交错的手法涵盖时间的不确定性,让人物在今昔虚实间游移,导引观影者进入似真似幻的梦乡,呈现导演虚构影像真实的过程。电影《推拿》为了具现小说所描写的盲人感受,在声音和影像上做了大量实验性尝试。电影模拟盲人听觉的声音设计延续娄烨在声音多重性上的特点,声音剪接无论在剧情推进过程或单格影像都混杂大量声轨,强调盲人敏锐的听觉感知,并且提醒观众影片以盲人为重心,建构出声音先行的世界,而盲人听觉的复杂性也让这部电影成为其历来剪接版本最多的作品。电影对盲人的其他感官亦多做模拟,镜头语言大量使用近景和特写,运镜多由特写移至近景,呈现盲人认知世界从局部展开探索的过程,并且辅以黑幕或失焦的影像处理,传达盲人视觉障碍的感受。导演娄烨更为了将盲人看不见的视觉感官在电影媒介具体显示出来,实验不同的镜头拍摄,重组各类影像素材,最后在拍摄过程中得出“自然光”的拍摄思想,借由光线的明暗调和趋近盲人眼中“看得见黑”的视觉。
另外,电影改编小说对“目光”的书写,电影异于小说企图借目光的描述带出社会问题的省思,而是将目光融入小马在电影复明情节后可能恢复视觉的线索之一,让观众同原著里小蛮对小马“目光”产生质疑,增添复明桥段的丰富性,为影片开展出多元的解读空间。综观电影《推拿》的改编过程,电影和小说不同媒介的转换存有许多难题,娄烨面对小说文字难以影像化的棘手问题,以繁复细腻的声音设计和影像实验跳脱原著框架,重新在镜头语言上模拟出盲人感官。透过电影“目光”的运用可以看出娄烨早期电影虚实交错手法营造真幻难分电影情境的特点,延伸至《推拿》更将模糊影像虚实的特点和盲视觉影像结合,盲视觉影像在主观镜头和客观镜头之间巧妙变换,让剧中小马的“目光”游移在见与不见之间,提供复明情节开放性的剖释。电影《推拿》成功解决小说设下的改编难题,诠释出兼备形式创意与情感内涵的影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