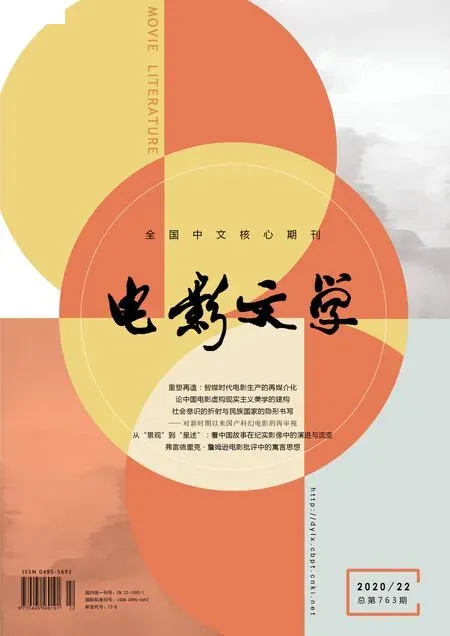基于动画史比照民族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孙韵岚
(1.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100088;2.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以动画为龙头的新兴文化产业创造了近年持续增长15%至20%的优异成绩,但这一喜人的数据仅是着眼于经济层面的考量,以至于未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常有学者围绕着三维国产动画电影映射出的美国风格或二维动画领域随处可见的日本样式等话题纷纷著文讨论,似乎在以科技发展推动艺术表现力提升的影视领域,中国动画所呈现出的视觉表象一直摆脱不了因舶来的技术操作,而造成艺术造诣层面的效仿。实质上,诸家之言的核心议题即在国产动画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民族化”。回望中国动画史,我们不难发现类似的现象在国产动画初创期也曾出现过。“《铁扇公主》虽然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但不论是其动画人物造型,还是表演形式,都较为接近西方的噱头式闹剧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代表我国参赛并获奖,却被评委误认为是苏联的作品。针对上述情况,以特伟为首的早期动画人首次提出“探民族风格之路”,在觅索前行中开创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动画学派”这一盛世。本文基于中国动画史分析动画民族化成因的历史必然性,总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照当前时代语境、探究民族化道路的建构方法,试图辅助国产动画实现艺术和文化双重层面的民族性回归。
一、动画民族化历史成因的必然性
中国动画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早期多沿用美国嬉闹喜剧型的创作模式,制作了《暂停》《大闹画室》《纸人捣乱记》等动画短片。在此期间,也曾萌芽出商业性质的广告动画片,如《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和《益利汽水》。然而,国产动画方兴的商业属性很快被抗战时期社会各界的救国热情“湮灭”,创作内容快速调整为以着重突出斗争精神来达到顺应左翼文学运动纲领的指导要求,政治教化功能主导了该时期中国动画民族化发展趋势的整体精神内涵,动画民族化伊始。
(一)民族化的精神内涵顺应国家意志的发展要求
20世纪30年代后国内时局日益动荡,尤其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加速了社会各界民族意识的觉醒。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文艺工作者迅速构建起统一的战线同盟,在左翼文化人的领导下围绕“暴露黑暗”“号召斗争”的影视创作主题,先后开展了“新兴电影”“国防电影”等多次电影运动,将左翼思潮推至顶峰。在社会大环境影响下,国产动画创作也逐步显示出对宣扬民族精神与塑造中国文化的诉求。自1931年,国产动画奠基者将视野转向现实斗争,创作了抗战宣传类短片《同胞速醒》《精诚团结》《民族痛史》,同时注重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制作了改编类影片《蝗虫与蚂蚁》《骆驼献舞》《铁扇公主》等,后者因融入了民族特色与奇幻色彩而更富娱乐趣味。但这一时期的民族化实为以驱除异己为政治目的,在民族主义的大框架下借助谙熟的题材以古喻今、教化民众,强调艺术顺应时代的政治语态,并试图淡化“软性电影”的娱乐功能,所以未能撼动左翼思潮在该时期文艺创作中“对电影意识形态宣教性‘一家独大’”的局面,奠定了我国动画民族化初期的发展方向是以民族生存为首要策略、重教化醒民的精神内涵。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党领导下的电影工作者们创作了《皇帝梦》与《瓮中捉鳖》,以讽刺的手法批判了蒋介石依附美帝国主义重蹈皇权的企图,暗示出国民党战局溃败的必然结果,反映了肃清官僚资本主义、宣扬共产主义精神与意志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新中国之初不可回避的任务。“文革”后,艺术创作从政治斗争语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超级肥皂》《新装的门铃》《邋遢大王奇遇记》等影片的问世,说明“此时‘中国动画学派’事业动画家的作品整体呈现出政治意识形态性减弱、审美自主性增强的显著特点”,满足了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期民众精神文化建设的需求。可见,动画民族化发展方向的精神内涵应时代和国家意志而变,在经历了战时的“醒民”、政治体制确立时期的“育民”,再到经济建设阶段的“乐民”三次转变后,其中政治斗争元素的减弱体现出影视艺术创作由“硬性”到“软性”的放权,但动画民族化的核心却始终留存着服务于国家意志的功能。
(二)外来艺术本土转化的有效手段
某类艺术的兴起会携带出“原产地”的文化基因,在跨地区、民族传播中凸显“他我”的迥异特征。从跨文化诠释学的视域角度分析,文化的特质性使“本我”与“他我”得以区分,是处于互动关系中相对应的认知范畴。“本我”是跨文化接受的认知基本出发点,在没有互动关系时,“他我”是独立于“本我”而存在的“物自体”;在互动关系产生后,原本的“物自体”变为“物他体”,即“他我”与“本我”发生互动关联。据此我们可以得知,基于对“本我”准确理解的前提下而产生的互动关系,是促使彼此独立的“物自体”转化为具有文化融合关系的“物他体”的必要条件。这为提升外来艺术的接受构建了理论依据,类似的方法在电影国产化进程中也可寻踪迹。1905年任庆泰将舶自西洋的电影技术与中国民族戏曲表演相结合,录制了《定军山》,这是民族文化观念影响下的必然选择。无独有偶,国产动画因机械地模仿苏联动画而出现与“本我”割裂的弊病,问题的根源在于脱离“本我”后的“他我”在“野蛮生长”过程中凸显出的迥异性,使观众因文化陌生感而产生了否定和彷徨的心理。因此,各民族经过历史沉淀而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内较稳定的共同创作理念与艺术审美追求,便成为外来艺术消解“他我”文化差异性,向“本我”转变的有效途径。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文艺创作观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艺创作观念起步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完形”过程,初期主要受到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的影响,在结合本国实践后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族化发展模式,开启了中国现代文艺创作的新纪元。
旷新年结合文学发展详细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形态下产生,被解放后的中国全盘接受”的过程:1933年初,在林琪的译文中首次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兼顾写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双重性。随即,周扬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生长于苏联独特的“社会-政治”土壤之中,不具有普遍性。在引入我国时,应该尊重我国艺术原有的创作规律,不能片面地理解艺术创作方法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依附关系,否则就会产生负面效果。可见这一时期对苏联的学习只及腠理,未至骨髓。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国国体的逐步确立、以及国内社会环境的改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萌芽提供了可能性。随着中苏建交,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很快得到了我国的认同,原因之一在于其“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的这一内容和1942年毛泽东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探讨的文艺与革命工作的相互关系较为契合。而且,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干预下形成的苏联“黄金时期”动画,注重借助动画趣味性、直观化的特征,潜移默化地对儿童起到了教育的目的,又能够与新中国儿童教育观念达成一致。正如陈培培所言,苏联动画的“黄金时期”并不是在赞誉作品艺术水准达到了某种高度,而是意在表达作品符合社会主义理念,也就是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理想蓝图”。于是,国产动画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引入,也从最初的学术探索进入到理论与躬身践行相结合的全面学习阶段。然而,由中央到地方的“一边倒”路线并没有减弱民族化的继承与传扬,动画民族化反而取代了苏联动画典型的“假定性”特征,被推向国产动画创作舞台的前端。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历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中苏理念趋同期、吸收传统民族元素的自主实践能动期、辩证思想推进民族理论创新的开拓期这三次转折后,从此民族化成为国产动画历史发展拐点下不可撼动的必然选择。20世纪50年代后,在国内外共同影响下,中国动画迅速剥离西方衣钵的裹挟,从民族艺术取材拓展其表现形式的视觉外延,达成了民族化发展中内容和形式相互统一的合弦之音——“中国动画学派”,这种雅誉甚至成为国产动画集大成时期的代名词,影响着几代动画人的创作观。
二、动画民族化发展中的困惑与徘徊
我们可以隐约地觉察出国产动画发展历程中暗指了“民族化”一词所包含的两个范畴,分别是作为名词的“民族”概念和隶属动词的“化”过程。“民族”一般泛指经过长期发展而具有稳定性、统一性、独特性的文化共同体,包含了位于核心部分的价值观层面以及外延部分的内容、形式层面,由历史、政治、语言、文化等因素构成。“化”强调了某种动态过程,即某类事物经过以同化、泛化为主的兼容过程,或异化为主的间离过程而完成的较改造前的差异性结果,最终实现民族意志的强化和输出。正如何晓兵所言,“‘民族化’不是一个人群概念,而是一种行为概念,是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人为地赋予事物以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的行为……其行为的政治目的,常常是为了民族之间的生存竞争中,强化和维系特定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相信凝聚力,和对其他民族进行区别或同化;而‘民族化’行为的艺术目的,除了部分与政治目的重合之外,主要为了保障艺术风格和内涵的独特性、可辨认性与多元性”。50年代国产动画民族化的方法以异化为主,着重突出中华民族与他国文化的差异特征,90年代之后受到美、日动画同化、泛化的兼容过程影响,造成了艺术表达、文化内涵、精神构建等多方面的“失能”“失职”现象,并表现出浅表化、断点式、单一性的特征。
(一)对“民族化”的浅表化理解
我们在讨论中国动画民族化本源时常常出现舍本逐末的现象,将研究范围直接切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创作主力的时期,而忽略了以民族精神与国家文化为依托的内涵建设,表现出对民族化理解尚停留在只关注达成民族特征的视觉形式效果这种浅表化阶段。特伟在《创造民族的美术电影》中表述了早期的美术片创作将“民族化”诠释为作品中简单添加中国传统山水画、民族服饰以及特色装饰纹样的这种较为浅显理解的反思。动画美术设计直接从民族美术取材的这种手法,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国人对动画这门新兴艺术的误读与偏化。第一,以传统绘画思维来理解动画创作过程及其相关概念,表现为最大限度上还原传统绘画造型的原貌,或注重对某类民族美术、民间艺术所使用的材质进行效仿。例如从敦煌莫高窟壁画《鹿王本生》“移植”到动画作品《九色鹿》中的角色形象,抑或由剪纸、水墨、木偶等材质构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较为突出的几类美术片片种。反映出早期来自各个艺术领域的动画工作者对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精髓的大家情怀,是艺术家将其对美术之“美”的尊崇融入动画制作的一种创举。在“美术片”冠名之下,动画作品中夸张的表现方法与假定性原则在不同程度上为遵循艺术原貌让路,退居为某类造型艺术的动态再现手段,在某种层面上成为精英文化的“衍生品”。第二,相对弱化镜头组接所扩展出的引申含义。苏联无声电影时期,库里肖夫的镜头组接实验为理解电影视听语言提供了新的视野。单个镜头素材经过不同方式的组接后会构建出新语意,观众凭借其知识储备和先觉经验进行解读,使编辑后的镜头所蕴藏的“隐性语言显性化”。而早期国产动画却很少运用特写、大特写一类的小景别,也较少依靠镜头组接来完成气氛渲染与影片叙事。以《大闹天宫》(1961、1964)为例,孙悟空与天兵天将的多次打斗片段大多以“全景”的方式呈现,角色调度尽量保持在画面内部,用人物的肢体表演来取代蒙太奇剪辑所带来的紧张感。可见,不论是以绘画思维来审视动画的外部视觉表象,或者使其内部视听组织手段逐步与电影语言“脱轨”,无疑会限制动画本体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二)“民族化”进程中出现断点式发展
苏联“黄金时期”文艺观念迅速取代美国嬉闹式的喜剧风格,成为20世纪50年代国产动画创作的主导力量。而过于直白的说教使动画一度成为政治的“传话筒”,与大众后期的娱乐需求没能达成统一,这种硬性的表达因失去了艺术创作与受众接收之间的双向交流而略显僵硬。“文革”后,“萨格勒布学派”的影响虽然为国内动画再次蓄力创造了条件,但经济体制改革的到来又搅乱了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自然转变的“生物钟”。民族化精神层面的审美满足、以及对我国动画本体的塑形非但没能得到延续和完善,反倒因为盲目模仿大量涌入的美日动画,而转为向单纯的感官刺激倾斜。民族化进程似乎总处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呈断点式发展,表现出碎片化拼合的创作特征。
(三)相对单一性的“民族化”构成
纵向来看,民族化虽然包含了对历史的继承、但又不仅仅禁锢于历史,它还汲取了符合当代文化的革新部分,历史与现实积淀出的民族统一意识形态又引导着文化的未来走向。是以,国产动画对文化的表达不应该肆意地割裂其原本具有的时空流动性,而应在实践过程中从民族历史不同时期的剖面中借力,以反复审视文化与艺术二者之间的互助关系。横向再看,民族化也应有对他者文化的吸收、融合与再改良的过程。例如作为优质IP的古典文学“西游”题材,在我国动画改编时大多保持着某种统一的制式或一贯的样貌,师徒四人的形象大多没有摆脱原著作自带的既定性概念,形成了标签化的人物形象。而日本漫画家鸟山明却大胆地借用该题材创作了《龙珠》系列作品,建构出一个与原著作完全迥异的世界观,展现其独特的创作视角。国产动画长期处于对个别传统民族元素往复挖掘的故步自封的状态,反映出“民族化”创作方法的单一性,遏制了动画发展的多元化可能。
介于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剖析、现实徘徊的解惑,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认识到民族化对我国动画发展起到了固本培元的重要意义,所以要对其修而善之、拔新领异,避免再次陷入发展误区,使其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三、当前动画民族化需要缓行的空间
全球化背景的新际遇下,国产动画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成长踟蹰。就动画本体方面而言,21世纪要求动画以跨学科、融媒体、越国界的方式发展,并非是在模糊其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原有概念,也不是肆意扩大其所能指代的内容范畴,而是需要各国加强对动画本体的构建与完善。只有明确本国动画的民族优势、掌握艺术创作的规律,才能够灵活地处理“民族”与“化”之间的变量关系,以防陷入循环往复的僵化思维模式。从文化传承的维度观察,好莱坞动画创作已经超越了民族泛化阶段,表现出对“他我”元素及形式的杂糅运用,但美国本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核心却贯穿始末,并试图通过动画作品的海外播映达成“文化融合”“文化寄居”的效果。聂欣如就曾借《冰雪奇缘》剖析美国人对暴力主体的认同,“暴力主体被美化成了处处受到别人攻击的弱女子,她的超能力也是在被迫自卫的时候才予以使用,从而为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行径进行委婉的辩护”。文化软实力犹如一把利剑重塑着我国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观,最终造成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丧失。此类现象的根源在于我国文化价值核心的动力不足。人对文化价值展现出了索取与创造的双重身份,表现为文化价值要迎合人的物质精神需求,同时又只能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现阶段动画作品所显现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对文化的承担与构建能力的减弱,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有待于加强与深化。动画民族化要做到表里如一,应探究民族传统艺术的本源,平衡文化的良性生态格局,在兼顾历史与现实的视野下审时度势地缓步前行。
(一)追溯传统艺术的本源
谈及中国传统艺术时似乎总有种不可言状的特质,如谢赫所著的《古画品录》中便将“气韵生动”题作中国绘画“六法”之最高准则,又如对某幅画作或书法品评时常用“行云流水”“形神兼备”加以赞许,这些看似无形的“中国气质”恰恰烘托出民族传统艺术本源的显著特征。
从传统艺术的视觉表象来看,与西方好用体积、光线、阴影来描绘景物的真实感不同,中国传统艺术大多具有装饰性的意象美。比如文人画作中以寥寥数笔概括出物象的特征,在剪纸作品中增添抽象的图纹线条以求佳意。这些都指涉出东方美学在艺术创作中并非以仿真为第一要务,而是更加追求因指代而产生的朦胧意蕴。如同绘画向象形文字的演变进程一样,作品的组成元素受到创作者主观的凝练概括而逐步退去对原始刻画对象外表的简单临摹,使元素因附带了一层极具表现色彩的“人工语意”而变为一种符号编码。同时,中国传统艺术还表现出对维度的特殊认知。例如,中国传统画论对散点透视以及留白技法的推崇,又如戏曲表演中巧用舞动的裙衣袖摆,将多维空间下布条甩动的轨迹转化为视觉可察的二维流动线条。对空间维度的特殊认知体现出传统美学将注意力由微观视野下物与物之间的穿插关系,转为探索宏观视角中物在场之中的聚散分布,也就是被意象化的元素符号在场域中因不均匀的布列而出现量的集聚与疏散,从而形成律动感。因而,传统艺术的视觉表象实质是抽象思维下对刻画物的主观处理、对原空间维度的打破重组,用符号化的视觉解码来解构、再定义作品的元素构成,最终实现立体向平面、写实到表意的中国审美。
从传统艺术的价值共识来看,这些与西方艺术相异的内容表述与形式展示是在特殊的观察视角与哲学思辨下孕育而生的,比如国画作品《韩熙载夜宴图》,将不同时空以断点剖面的形式陈列于方寸之间的画幅内,采用横向构图的流动视角来还原夜宴中的社会群像,展现了作者以静喻动的巧妙构思。又比如人景互融的艺术方法即便是在中国人物画中也常常可寻,其意不仅止于借助环境氛围烘托人物性格特点与气质神韵,还旨在探讨天、地、人共处的和合关系,将个人与宏观大环境相衬,意在表明基于唯心“忘我”境界下物我共存、天人合一的超然意境。民族传统艺术渗透出了较为一致的价值共通性,说明中华文化对创作者文人素养与艺术审美的影响。
再次以《大闹天宫》中孙悟空大战哪吒的这一场戏为例,二人在空中上下翻腾的激烈打斗被有意地概括为一黄、一蓝两团不断对立撞击的抽象线条。形变的处理方法上也不同于迪士尼的常用手法——注重在动画中间张中清晰地刻画两种不同形体转化时的形变过程,而是完全凭借内心感受来表现孙悟空如风一般快速应招的七十二变,整个打斗动作伴随着民族音乐的节奏起伏而产生律动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原著《西游记》中孙悟空被描写为“脆弱的和异化的英雄,尽管他具有超群的心灵悟性和生命智慧,然而,毕竟由于历史的宿命,主体既缺乏历史理性又缺乏辩证理性,呈现一种盲目的非理性冲动,最终匍匐在宗教法力和政治权利的脚下,成为两种社会势力所利用的一种武力工具”。而美术片创作时唯独截取了原著中悟空未被点悟前“闹”的性格特点,一来刻画了顽固不化的泼猴形象,二来烘托出该角色敢与苍天一搏的斗争精神。在片尾展现了孙悟空突破天界设下的重重难关凯旋的完美结局,实为作者将艺术价值共识与社会现状的看法相结合,对原著进行了有效的改编。可见中国动画想要解决民族化流于表面的问题,就应考虑如何从传统艺术的视觉表象和价值共识两大方面回归中华艺术之本源,在此基础上结合动画发展现状、艺术创作规律以及社会现实,来扩大民族化的内涵。
(二)促进良性文化生态格局的形成
移动终端、互联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广泛应用正试图改变文化的接收效果和传播力度,受众参与性从被动转为主动。这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迅速崛起的大众文化正逐步成为我国文化形态主导力量的必然结果,迫使着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在新的文化生态格局中偏离原有地位。不可否认,这种转变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从众心理会降低受众的独立判断意识;产业聚群化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现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单靠市场调节无法发挥各自的最佳功能;国家话语权缺乏有效的表达体系、有损文化身份的认同度……所以,应该从多个层面做出适度的调整,促使文化形态多口径对接的良性生态格局形成。
依据接受美学所示,作品的真正意义是在接收主体主观能动的接受活动中实现的,接受主体对作品的认同受到“期待视野”、个体的知识储备、审美倾向、思维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对电影作品的评判中,电影票房虽然能够较为直观地代表受众意愿标示出影视作品商业价值的高低,却无法完整地勾勒出作品艺术深层价值的真实水准。比如风格突出、隐喻意义深远的文艺片在国内上映屡屡遇冷的窘境便已不为稀奇,究其原因总是绕不开“小众”一词。又如国产动画大多以“儿”姓示人,影片中尽量避免过多晦涩难懂的内容和复杂的逻辑叙事以争取更为精准的市场投放,但结果却使得作品空洞贫乏,缺少民族文化作为支撑,得了小众而失了大众。可见,真正能够治标治本的“处方药”还是要落在对作品的本体构建上,并且影片的评判标准应适当地由市场商业价值向作品艺术价值放行,逐步扭转市场导向先行、制作研发缓进这类核心动力来源不对等的问题,为孕育“国粹”级动画作品提供创作环境。
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土壤自然可以为影视创作提供丰裕的养料,从民族中取材不等同于教条的延用,而是更加强调新时代背景中的民族适用性。习近平曾在讲话中多次提及重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并指明当代所指的传承绝不是简单的复古,而应该辩证地摒弃传统之糟粕,继承其精华,“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大圣归来》为例,原著中唐僧一角代表了身居高位的师者形象,对悟空越矩行为以说教或体罚的形式加以惩戒,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但是影片创新性地将唐僧“小儿化”,使师徒关系更多了几分成长中的陪伴,悟空的改变不再是外界干预的结果,而是内心自发的改变。这种对传统文学抛弃先验主义的改写才真正符合佛法普度众生的真谛,顺应了现代观众的审美转变,无疑是民族文学改编的有效尝试。所以对于影片创作者来说需要兼顾大众心理并参照他者文化的接受能力,同时结合个人艺术素养对民族传统素材进行再创作,切勿在工业化的产业机制中使个人风格趋同化。避免大众文化一家独大的局面不是蓄意否定该文化形态的现实作用,而是指明在影视作品的内涵构建方面应该将民族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作为一种参照,从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能力,有效地促进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接,为构成我国良性的文化生态格局创造了新的可能。
综上所述,中国动画民族化是国家危亡时期在精神层面迫切需求下而产生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艺术探索,在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后达到了“中国动画学派”这一创作高峰,但同时也造成了艺术观念上的分野——相对于现实题材而言,民族化常被应用于传统题材之中。自此,动画民族化对于精神与文化方面的建设便慢慢消退,而是更多地以图形符号的形式留存于创作之中,反映出国产动画实践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僵局。但是全球化进程中自然携带着异、同并存的矛盾体——个体的认知结构受国际视野的影响而改变,使人类对异国文化总是能够以“求同”的心态安然自处。可是在以“软性”对抗的新型国际博弈中,“存异”才是提升各国文化标识度的关键所在。显然我国在参与国际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因长期对民族化的狭隘理解,造成动画作品内涵建设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距离拉大,最终产生国产动画片在国内市场投石问路无果,在国际上话语权影响力低效等劣势局面。这既指出结合时代特征做出深层研究与调整的急迫性,又说明动画民族化发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应该将民族化视为切实可行的方法论,使国产动画在艺术层面完成民族艺术本源的回归,文化层面实现国家身份认同的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