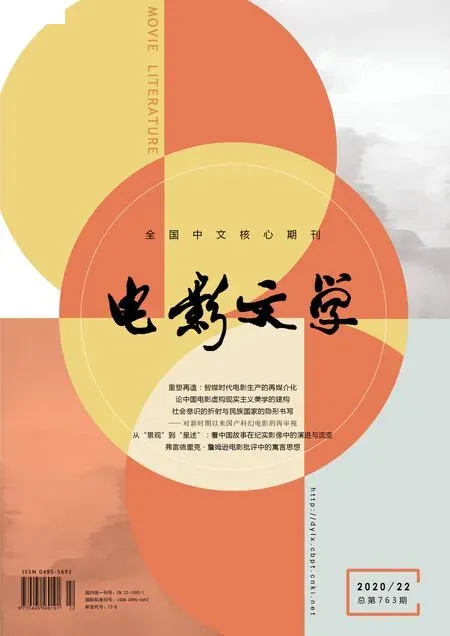批判现实的悲剧气质:《危楼愚夫》的美学风格释读
邢祥虎
(山东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受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影响,苏联/俄罗斯电影现实主义风格明显,故事性极强,艺术内涵丰富,善于挖掘人性根源,美学风格介于商业通俗与小众文艺之间,看过之后往往让人印象深刻,甚至悲剧感/沉痛感十足。2014年上映的《危楼愚夫》就是这样一部批判现实的佳作。
一、“三一律”支配下的高密度戏剧结构
“三一律”是西方戏剧理论之一种,也称“三整一律”,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经由意大利、法国等戏剧理论家的阐扬推行,逐渐成为戏剧创作的金科玉律。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尼古拉·布瓦洛把它解释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贴合古典“三一律”的中外电影作品也屡见不鲜,如《正午》《十二怒汉》《撞车》《风声》《天下无贼》《训练日》《这个男人来自地球》等,尤里·贝科夫的《危楼愚夫》也符合这一剧作理论。
影片以某俄罗斯小镇为叙事背景空间,讲述了质朴本分的水管工迪马·尼基丁维修居民楼爆裂水管时,发现楼体有两道惊人裂缝,整栋楼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出于对楼内居民生命安全的保护,他奔波忙碌了一整晚。很显然,该片主要故事情节发生在冬日夜晚,戏剧时间没有超出“三一律”规定的24小时,并且采用连贯性的线性叙事模式,剧情冲突沿一条线索延宕开去,没有插叙、倒叙、套层回环等旁枝末节的现代叙事痕迹。如此严谨紧凑、不花哨炫技的戏剧结构十分有利于引导观众,将观影注意力投射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戏剧动作、主题思想上,避免场景频繁更换、镜头快速剪辑、跳接闪回造成的精神束缚和观影压力。
作为俄罗斯新生代导演,尤里·贝科夫迄今为止已有《生活》《警界黑幕》《危楼愚夫》《太空第一步》等几部电影长片。导演似乎比较钟情于欧洲古典戏剧理论,《警界黑幕》是另一部不折不扣的“三一律”作品,讲述了一桩执法不公的交通肇事案件,故事时间同样被严格限制——从黎明到黄昏短短一天之内。归功于影片的优秀品质,2013年在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警界黑幕》一举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成就三项金爵大奖。评委会主席汤姆·霍伯给予高度评价:“通过这部电影,我们看到了现代俄罗斯的一些复杂社会现象,也看到了伟大的俄罗斯艺术以及讲故事的传统,这些都由这位才华横溢的新生代导演为我们展示。”汤姆·霍伯的评价是准确的,讲故事、讲好故事、好好讲故事永远是电影艺术的无尚追求,遵循“三一律”有助于电影导演讲好一个故事。
二、用电影烛照生活的黑暗
自黑电影常常将矛头指向国家政府、官僚政客、社会政治组织等既得利益集团或个人,揭露曝光其不为人知的阴暗面、腐败行径抑或黑金政治。表面上看是背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反体制”电影,实则充满了自我反思、自我救赎、自我批判精神,比一味的“自褒”更能彰显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国家制度自信。众所周知,韩国拍摄了许多自黑电影,比如《汉江怪物》《熔炉》《素媛》《恐怖直播》《局内人》《光辉岁月》等等,不一而足。《危楼愚夫》《警界黑幕》《利维坦》是俄罗斯电影人拍给世界的自黑电影。
《危楼愚夫》单线叙事,风格冷峻写实。一次水管爆裂引发了蝴蝶效应,揭开了市长、警察局长、消防队长、房管局长、医院院长等一干官员的受贿腐败行径及其黑吃黑的丑陋嘴脸。被奉承为“妈妈”的女市长尼娜与资本大佬勾结而谋上位,为了掩盖危楼真相枪杀房管局长和消防队长,同时焚毁危楼修建账目资料。当死亡降临于820名危楼居民时,身为“妈妈”的市长却弃绝了这些无辜子民的生命,任其自生自灭,何等辛辣的讽刺与露骨的荒诞呀!
摧毁、蛀空这座危楼的与其说是政府官员的腐败,倒不如说是居民的麻木愚昧。
影片开场以2分钟的长镜头完整地交代了一场醉汉家暴的戏,昏黄的灯光、逼仄的楼道、陈旧凌乱的居室,隔着银幕能闻到酸腐恶臭的气味,直呛观众口鼻,这样的生活毫无美感和希望可言。一群苟且偷生于废墟之上的“废墟人”,精神萎靡,行尸走肉,成年人偷窃、酗酒、赌博,青年人吸毒、嫖娼、打架。总之,他们完全不值得用任何美妙的词汇来形容。镜头扶摇直上,仰拍危楼上两道触目惊心的裂缝,从地基直通楼顶,这难道不是俄罗斯社会危机的隐喻吗,从普通民众到社会管理者都已危如累卵,无可救药。
三、心向光明的理想主义不死
幸好,社会进程中不曾缺席正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被市侩母亲讽刺为“傻子”的迪马决意以一己之力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他不顾母亲、妻子的反对,连夜去找市长汇报情况。于是第二个富有意味的长镜头出现了。冰冷的街道空无一人,稀疏的路灯闪烁着点点黄光,迪马独自走在黑黢黢的夜色里,步履坚定,没有丝毫胆怯。观众的视点被缝合进横移的长镜头,“二次同化”后,匆匆行色获得了英雄般的心理镜像。
在腐化透顶的政府面前,迪马的幻想化为泡影,他本人险遭市长杀人灭口。但是难以违背自己道德与良知的煎熬,他开始挨家挨户疏散身处险境的居民,像无畏的斗士大声疾呼:“离开这座楼,这楼要塌了,赶快出去!”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有“铁屋子”的比喻,以大嚷“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迪马充满希望的呐喊确实惊起了所有居民,然而群氓们无一清醒,将“英雄”“真的汉子”“正派的人”暴打一顿。
母亲、妻子、官僚都没有“掰弯”一根筋的迪马,受拯救者却生生制伏了他。饱受拳脚蹂躏的迪马像受难的基督一样蜷缩在冰冷的地面上,呐喊还应在他内心回荡,我们料定是蒙克般苦闷孤独的“呐喊”了,喊声中渗透着“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另一方面,迪马身上又具有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色彩,坚持守护着闪光的内核,屡败也要屡战。不知是导演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危楼愚夫》和《唐·吉诃德》里的主要人设基本吻合。唐吉诃德是禁欲主义的苦行僧,有丰富的学识,长得瘦而高,与迪马的角色形象如出一辙;而桑丘·潘沙则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派,文盲,胖而矮,与男主妈妈的角色设定并无二致。二者的互文关系,为观众敞开了深度意义解读的可能。《危楼愚夫》在第67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唐吉诃德奖特别提名奖。
柏拉图以哲人的智慧给世人描画了洞穴寓言。走出洞穴的那个囚徒就是《危楼愚夫》里的迪马,他是小镇上经历了精神启蒙而寻找光明的第一人。放开说去,迪马只是导演操纵下投射到穴壁上的光影而已,真正心向光明、戳穿洞穴假象的是尤里·贝科夫。他将现今遮掩俄罗斯社会现实的面纱不留情面地撕下来,露出化脓的伤口,刺目的淤血,电影的艺术力量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