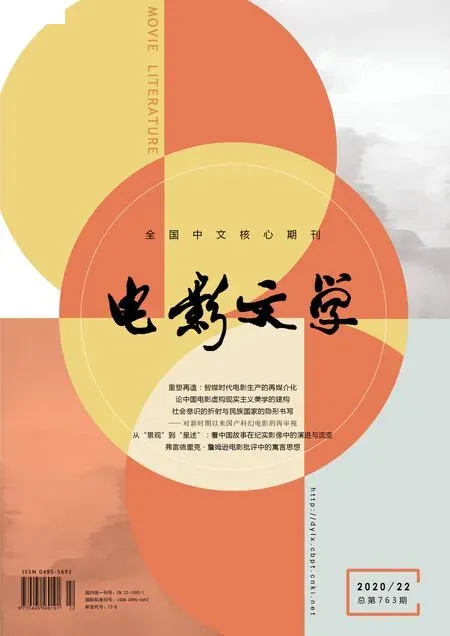微纪录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叙事特征
张青妹
(北京工业大学 文法学部,北京 100023)
什么是纪录片?按照比尔·尼科尔斯所说:纪录片的定义并非独立存在的,其定义是相对的,纪录片的含义是在与剧情片等电影的比较中产生的。通常来讲,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都可以称为纪录片。在新媒体语境下,纪录片的创作已不再局限于主流媒体和专业制作机构,越来越多的个体基于自身对社会的思考,通过随身的摄录工具记录下对现实的感悟。大众文化形态的微纪录片已成为主流纪录片以外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这些非官方纪录片在创作手法、记录形态、叙事特征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转变,但是它们和主流纪录片一道,共同承担着保存群体记忆的社会责任。《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是新冠疫情期间清华师生共同创作的抗疫微纪录片,他们和几十个普通拍客一起,用鲜活的叙事方式记录了那个特殊时期的武汉,其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语态、话语主体及其叙事偏向等叙事特征都值得研究与探讨。
一、渐进与平列相结合的叙事结构
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是它的结构关系与表达方式,包括时间畸变、空间呈现、叙述方式等各要素在一个整体结构中的配置、分解、整合与对应,常见的两种纪录片结构思维是渐进叙事和平列叙事。渐进叙事是指各个结构单位的内容之间,通过逐步推进的切入方法,时间关系、逻辑关系和程度关系上保持一种前后相继的不可逆转的结构思维方式;平列叙事是指纪录片的各个结构单位保持一种平行、并列的空间关系的结构思维方式。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将来自77位拍客的112条短视频加以剪辑,整体上采用了渐进式结构思维。该纪录片主要通过不同剪辑点的设置,在一连串镜头中建立了一种观众期待框架,使得镜头内容有了叙事性,从而实现了时空的转换,使叙事线索更加明晰、结构上更加匀称。该片以2019年12月31日为起点按时间顺序推进,从武汉洪山体育馆的跨年音乐会开始,伴随着新年倒计时和民众的欢呼声进入2020年1月1日,屏幕最左侧永远跳动着电子日历、确诊人数、重要的事件节点等,这种争分夺秒的观感提示着事件的整体进展,并通过对语言和视频材料的剪辑和安排,创造出抗疫发展的时空结构和逻辑结构——从寒冬到初春,从灰暗到希望,总体上呈现出渐进式的线性叙事特征。
在渐进叙事的总体框架下,该纪录片还穿插了平列结构思维,确切地说是采用了剖面式平列结构思维,将同一时间中不同人物的不同事件展现出来,以平行蒙太奇的叙事语言,多线叙事又相互映照,横向平列地推进着总体事件的进展,最后统一在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中。这些平列呈现的人物和行动是非连贯的,并非向着结果直接推进,虽然这些行动没有呈现因果推进的逻辑,叙事逻辑并不连续且较为松散,但观众可以清楚地综合感知到这些片段的系列性。在剪辑者的二次创作过程中,来自不同叙事主体的112条短视频被有效组接,借助平行蒙太奇丰富的叙事能力,不同的生活碎片超越了时空限制产生互文。这些平列的影像共同还原了某一刻的武汉生活,使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平列式和渐进式的叙事结构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了武汉的抗疫语境。
二、私人叙事中的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原本是文学研究中的概念,指一种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的无所不包的“完整的叙事”方式,后被历史学家借用,强调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规律性的认识与总结。新闻传播学借鉴文学与历史学理论,提出宏大叙事理论概念,被视为是对社会生活、历史、人类经验做出总结性解释的一种理论类型。长期以来,宏大叙事模式在我国纪录片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作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抗疫实践,此类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往往会采用宏大叙事来呈现其历史性,较少涉及真实的日常生活并常常淡化世俗情感的表达与诉求。但是对于观众而言,宏大叙事不够亲切、代入感略差,特别是对于每一个个体都有切肤体验的历史事件,观众更希望能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参与其中,《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微纪录片。
日本著名纪录片人小川绅介认为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并且强调应尽可能保持在现场。武汉作为全国的抗疫最前线,无数普通人拿起手机自发地记录着自己的城市,留下了一系列不可再现的历史瞬间。该片以疫情期间武汉新年为切入点,整体选取了私人叙事的视角,它虽然以碎片化叙事呈现,看似时空跳跃且结构松散,但由于个体化的碎片叙事与同一个宏大主题相结合,使得这些小片段叠加的叙事结构显得有理有序,且事件安排和剪辑过程中没有人为制造叙事动力,总体呈现出较为自然的叙事方法,一路看下来脉络清晰、整体性强。该片中这些自发的私人叙事,处处散发出“在现场”的杂糅活力,用具身的呐喊朝向同一个共同体,就像新冠疫情的蔓延所暗示的一样,在宏观上是属于全人类的经验,这些个体影像汇集在一起,共同指向了全民抗疫的宏大叙事。
纪录片常见的叙事方式是以全知视角对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在此类纪录片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众多平凡英雄却是失声的。该片把落点放在个体身上,用77位亲历者的自述和镜头,共同拾起一段抗疫的集体记忆,构建起个人悲欢与宏大主题的紧密关系。通过这些个体的微末叙事,该片并没有呈现出封城时期宏大叙事的悲怆,所展现的更多是普通民众平凡烟火气息中的乐观、勇敢和无私。在该纪录片中,私人叙事并没有对宏大叙事的意义倾向产生消解,正相反,尽管叙事视角发生转变,但家国情怀却只增不减,那些娓娓道来的个体口述让宏大的主题更加具象而有温度,武汉百姓的日常传递了灾难面前中国人的价值观与担当,把鲜活意象的宏大叙事贯穿到了每一个生活场景。事实上,当日常琐事被赋能,琐事就成为宏大叙事的载体,整部影片的叙事手法也衍变为一种亲和的宏大叙事。新冠疫情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巨大挑战,在类似重要的历史事件中,个体叙事的阐释空间十分有限,这些通过私人叙事呈现的时代图景必然会载入史册,以另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勾勒出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场景。
三、自叙与对话的双重叙事语态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中的大部分影像素材均来自普通市民、确诊病人、医护人员、志愿者等,这些叙事者以第一人称从不同视角记录了庚子新年的个体感悟,他们的自叙视角带有明显的当下视觉文化的个人中心主义特征。在基于互联网的视觉文化中,个人中心主义并不代表着只关心个人的日常生活,而是意味着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表达都以个体日常的感受为出发点。这些叙事者最初按下拍摄键的时候,没有主题策划与集体约定,他们只是有感而发地拍下了彼时的自己和他人:对空无一人的街道的伤感、对超市中播放音乐的触动、感染者对亲朋好友的愧疚、普通市民对各地支援的感恩和对政府的信任等等,都是通过自叙的方式传递的。这些叙事主要基于自身认知的主观体验,强调叙事的亲历性和不同程度的自我介入,整体来说该片系统性地采用了自叙为主导的叙事语态。
在该片中,不同叙事主体共同聚焦于疫情下的社会百态,虽然讲述的是自己的内心与生活,但是个体与社会群体并没有分离,所传递的内容也并不是自我的和封闭的,事实上这些叙述映射了疫情下广阔的社会空间,是公共空间的缩影。这种主观式的自我陈述营造了一种个人化的影像气氛,但同时也将镜头作为沟通媒介,跳出了自我中心主义的内向度的叙事,以乐于分享的方式鼓励了双向对话与沟通。在该片中,拍摄者或是以自拍的方式直面镜头与观众交流;或是用镜头代表着第一人称“我”,通过画外音和观众交流所见所感,这些叙事主体隔着线框和镜头实现了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和沟通。至此,所呈现的影像也不再仅仅是自我陈述,而是成为“我—你”之间对话的沟通渠道,这种个体表达和“我—你”对话的双重语态构成了该片重要的叙事特征。
四、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互文性叙事
纪录片并非现实的复制品,它是对生存世界的一种再现,并代表某种特定的阐释视角。微纪录片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一种历史书写方式,继承了纪录片这一基本属性。它源于草根,民间话语叙事特色鲜明,不同于官方话语的规范陈述和精英表达,民间话语是一种大众叙事,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性格和审美趣味,常以诙谐和调侃的形式来反映大众生存体验过程中的真实情感与复杂情绪。
《手机里的武汉新年》中的素材来源于民间拍客,他们可能并没有机位、角度以及景别等概念,用并不专业的设备和把持不稳的镜头、略显粗糙而富有生活质感的画面以及未经处理的同期声,聚焦于疫情下武汉最真实的模样,其叙事话语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朴素化风格,是以民间话语为主要基调的生活叙事。但是短短18分钟的纪录片中,重要事件信息的表述均出自官方话语:华南海鲜市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报道,对钟南山关于病毒人传人的采访连线,武汉决定封城的报道,除夕之夜的转播,市民出行必须做好防护的提醒,各地驰援武汉的报道,等等,这些内容在该纪录片中均以电视新闻同期声、政府基层部门的广播宣传、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等公共话语的方式呈现出来,是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对接的范例。
对于全面抗疫这一历史大事件,官方话语叙事严谨且规范,以国家的高度守卫人民的安危,以专家的视角为民众答疑解惑,客观、理性、权威、着眼大局,从宏观上报道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与此呼应的是,民间话语以其特有的叙事方式将众多的抗疫碎片加以记录,联结出一幅更加鲜活真实的社会百态:封城下武汉街道空无一人,小区里回荡着的演唱会一般的“武汉加油”的呼声,各地志愿者勇敢逆行的画面,市民或焦虑或无助或乐观或幽默的自述,简单却温暖的年夜饭场景,等等,都从不同视角阐释和解读了更加本真的状态,朴素、主观、感性,诉诸共情且直击人心,体现了民间话语的叙事力量。两种话语主体不同的叙事偏向,一“硬”一“软”,在同一个叙事文本中有效结合,并且在不同的层面相互指涉和呼应,实现了官方话语的硬叙事和民间话语的软叙事的互文。大疫面前,这种鲜活而真实的民间叙事力量与官方话语实现了有效互动,使得抗疫话语更加立体和丰富,二者共同创造和扩大了公共话语空间。
在新媒体语境下,微纪录片的产生背景和创作环境与传统纪录片有着显著区别,《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是新媒体语境下诞生的纪实影像艺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该片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语态、话语主体及其叙事偏向等方面有着不同于其他纪录片的显著特征。斯图亚特·霍尔说过:“事件在可传播之前,必须先被转换为故事。”真实生活呈现得生动形象还是平淡无奇,关键在于叙事能力和技巧的差别。该片融合了新媒体参与、对话、多元的精神,叙事策略也呈现出交叉与融合的复调特征。这些策略有效地服务于疫情故事的传播,以触动人心的画面群像式地展示了特定时期的武汉,深深感染了疫情之下的全体受众,催生出一种新的纪录片审美形态,体现了微纪录片多元叙事的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