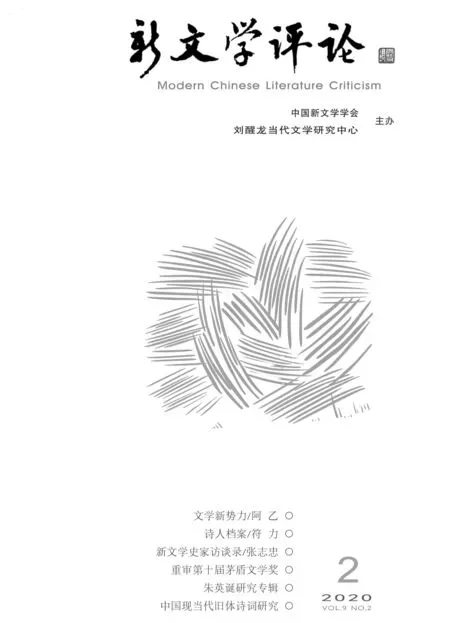阿乙小说中的色彩与图形分析
□ 王曦堇
你看,凡是在我们外界存在的,没有不同时在我们内界存在,眼睛也和外界一样有自己的颜色。颜色学的关键在于严格区分主观的和客观的,所以我正从属于眼睛的颜色开始。①
阿乙的第一本书取名《灰故事》,这位从小镇叛逆而出的青年,他眼中的小镇是灰色的,就好像一个充斥浓厚烟雾的方盒子,将其中的人们牢牢罩住。灰色象征着这里所发生的是一个个灰暗荒诞的故事,也造就了其作品的叙事基调与情感色彩。按照色彩分析理论,人们对颜色的不同偏好直接与情感相连,如果多使用“消色差的色彩(灰色、黑色),说明表达者在某一时刻压抑的感觉,或是想遮蔽住带有侵略性的感觉”②。在作者毫无光亮的注视之下,自然中的各种事物都隐身在这无差别的灰色中,消失了自身本有的色彩,仿佛只有一个作为物的模糊轮廓。灰色同时也是油画中所有颜料混合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各色人物在这里得以生存,并在这灰色中偶尔闪现他们的光彩。
一、 色彩词汇的情感表达
一个个“灰故事”是由具体的词语构建,而颜色构成的词语在阿乙的作品中出现得较为频繁且考究,他娴熟地运用它们传递着自己注视下事物的样貌。除了基本的颜色字符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粉等,还包含许多绘画中的专有色彩词汇(包括表示程度的同色系词与两种颜色混合搭配的词),如:白色、乳白色、灰白、银色、黄色、明黄色、金色、橙色、橘色、黄褐色、棕色、红色、鲜红、粉红色、法鲁红色、深红色、暗红色、紫红、绛紫色、紫黑色、蓝色、海蓝色、暗蓝色、藏青色、黄绿色、青色、淡青色、暗青色、青灰色、湖绿色、绿色、翠绿、墨绿色、黛色、褐色、暗褐色、黑色等。
其中,法鲁红色、绛紫色等是颇为专业的色卡名称,它们的使用多见于以北京等大都市为背景的故事,如《情史失踪者》。而以农村小镇为背景的故事中多用青色、黄绿色、黛色、绿色、藏青色等自然属性极强的颜色,如《对人世的怀念》。值得一提的是红色、鲜红、深红色、紫红色、翠绿等色彩饱和度高的颜色常用于对尸体的描绘,尸身的浓烈色彩与生者身上的灰暗无光经常在阿乙的作品中出现,如《情人节爆炸案》。
叠词:灰茫茫、灰溜溜、灰蒙蒙、红丝丝、黑黢黢等。
带有特殊修辞的颜色:森白、苍白、蜡白、花白、煞白、惨白、梨色、槐黄色、酱黄、暮色、水红色、血红、珊瑚红、硫黄色、麻酱色、茄紫色、浓绿、冬瓜绿、铜绿色、芝麻灰色、铁灰色、岩灰色、漆黑、油黑、琉璃色、胭脂色等。“我们在一切知觉中就经常可以分清哪种颜色是真正外界存在的,哪种颜色只是由眼睛本身产生的貌似的颜色。”③人们对色彩的认知不仅来自感官,色彩也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情感经验的表达。这类颜色被歌德归类于生理颜色,它们含有复杂的色彩元素,难以简单地使用几种基础颜色调合表述,包含很强的作者主观情绪和对对象的感觉。颜色在这里不仅是物体本身具有的属性,同时也是作者关于它形成的一种观念。这种事物在作者眼中呈现出来的观念往往带有作者给事物打上的独特的印记,作者的情感正是通过色彩词汇被细腻地表达出来。这就体现为种种具象的特殊的色彩。阿乙重视不同对象的个体性差异,例如在表现人物了无生气的病态时,他重点区分了这类难以辨别的灰白色。重病男人的脸用“梨色”——因肺病折磨导致的偏黄绿的灰白色;女孩冰凉脚踝的“森白”——在寒冷之中受冻的冷色调的蓝绿灰;祖父脸色的“蜡白”——因衰老缺乏血色的浅黄灰白色。
二、 长句中的色彩对人物和场景的细致展现
相较单一词汇的色彩描写,长句中的色彩就像在调色盘中不断调和的复合色,其特点是越经调和,纯度越低。往往这类难以明确界定的颜色来源于阿乙对人肤色的关注。《情史失踪者》中“她的皮肤说不上黑也说不上黄,总之不显白”④,或是在《意外杀人事件》中“苍白的脸扑满浓粉,也许是扑狠了,又补些青,这样青里有白,白中泛青,竟像死了些时日的尸身;她还在宽大的唇线中央细描了豌豆那么大一块红”⑤。阿乙的警察经历使他在注视人物时充满了冷漠细致的审视,这种尸检般的观察与描写放大了人物本身某种荒诞悲凉的特质。
相同的颜色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显示出不同状态,而我们在对比中才能识别色彩。阿乙作品中色彩运用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强化环境中的色彩对比,如在灰色背景中,突然出现激烈的色彩冲突可以加剧画面中的不稳定性。《情史失踪者》中“光明就像大军在紧闭的绛紫色窗帘外浩浩汤汤地经过”⑥。金黄色的阳光与带有红色调的暗紫色形成了鲜明的互补色对比,屋内昏暗局促的氛围更加决绝地与充满希望的屋外隔绝开来,为房间内即将展开的搏斗进行铺垫。这种强化的互补色运用经常出现,它突破了人们对“色彩恒常性”的认知,尤其是在对尸体的具体描写中。如《敌意录》“她的五脏六腑鲜红,仍然垂滴着血,而翠绿肠子滚圆的(如巨蛆)”⑦。在血肉模糊中,“五脏六腑”的“鲜红”与“肠子”的“翠绿”其实是难以识别的,阿乙通过主观的强化,将这血腥刺激、涌动着不安与死亡恐怖的场景一览无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除了色彩对比,阿乙也通过光的照射去强调明度对比,在《极端年月》中,经历了爆炸案现场的惨烈以及濒临分手的绝望,“我”在结束现场调查取证工作后看到“一个个人在忽明忽暗的警灯照耀下,像是尸体一具具站起来,像是收割完庄稼,相约回家,像是遥不可及的幸福。像是要抛下我”⑧。作者抹去了单个人物的具体面目,个人在这里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这个符号象征着在遭遇命运毁灭之后破碎化的人像机器般麻木地“收尸”,而“光”刻意营造出的温暖和明媚都只是一种虚假的光亮,这些泛着虚弱生机的光亮遭遇必然的真实碾压之后往往不堪一击。
句子中关于色彩变化的描写往往也传达了作者对人物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女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他刚刚接触或是不够喜欢的女人,描绘中带有冷峻的戏谑。“牙齿紧密,上头确有一层用什么牙膏也洗不脱的黄渍,如果笑得开放点,还会露出大块的法鲁红色牙龈。”⑨女人淡青色的打底裤让人联想起尸斑,瘦小的手被比作“松鼠湿润的红色小肉掌”。被审视的女人仿佛处于阿乙的放大镜之下,她们的美或多或少都被打了折扣,无法细究,并带有敏感、病态的特质。值得一提的是,阿乙给象征着热烈、美艳与危险的红色系赋予了狼狈而笨拙的意味。
相比之下,当爱人出现之时,阿乙眼中的光被点亮,他虚化了对人物外貌的细致勾勒,用抽象通感的方式,去表现爱人带给他情绪触动。“爱人”的形象以金黄色调的“光”为主,是一种积极的、充满能量的色彩意象,“我便像走进篝火,身体生起一层层暖来”。爱人离去,他便陷入无尽的昏暗中。《早上九点叫醒我》中的许佑生“感到光明里起了霉斑,他将在逐渐加重的暮色里走向世界的尽头”⑩,光本质上就是色彩。《极端年月》中 “她说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她不说,天下就黑暗了,我在夜雨中孤苦伶仃地走”。当他与媛媛分手,终于不再出现关于媛媛的幻觉后,他再次看到这位前女友时,不再是通感的情景描写,而是直观的、不留情面的白描,人物也重新回归红色系。“她穿着粗笨的红呢子裙,涂抹着鲜艳口红,打着浓重的白霜。”越是隆重越是尴尬,像是已经失去了生命气息的爱情,却要极力掩饰,反而传达出一种对爱情即将逝去的不甘和抗拒。这是一次对爱情非常残忍的去魅,这种爱情“离席”或是“缺席”的焦虑、荒诞的状态经常出现在阿乙的作品中。或者用阿乙自己的话说更加准确,他想要展现“爱的反面是冷漠”。
同样作为女人,阿乙笔下的母亲角色往往伴有盲目迷信、重男轻女的特质,作者对她们的描绘充满决绝的讽刺。《情史失踪者》中那位面对女儿丁洁妮病情态度冷漠的母亲“搭着一块让人丧气的类似洗碗布那样的白色头巾”,《肥鸭》中的张婆是被称作“火金娘”的乡下悍妇,她的孙女因受到她长期的虐待而成为“肤色呈岩灰色的活死人”。《阁楼》中的母亲对儿女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在母亲的包办婚姻下,三十多岁的女儿“头发已像薄雪盖煤堆,灰白一团”。一个个在封建家长的权威下酿成了个体悲剧。但阿乙也在描述这群人愚昧的同时赋予他们悲苦坚韧的色彩。《儿子》中的母亲阿珍“又黄又瘦,在众人前总是驼背、红脸、将两手撇于腿后”。当儿子丢失后,这样一位软弱的母亲面对众人的指鹿为马,麻木而隐忍地抱回了一条被称作“儿子”的小狗。《极端年月》中为儿子走十里路叫魂的迷信母亲,突然让儿子意识到“白发一路长进了母亲的头发”中。“母亲”这一形象总是施加或被施加各种压抑的灰白色,仿佛她们既是环境的牺牲品,又以温情或严峻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承受和传导着习俗带给人性的压制。
三、文字的图形化——作者与读者之间默契的建立
种种具体的色彩和形状都被作者精心排布到一个空间化的场景之中。颜色和物象以此方式,在剧场式的布景之中重新出场。具体而言,作者把文字作为单一元素排列成图像给读者呈现出一种可视化的场景,也是阿乙作品的一大特点。例如,在《意外杀人事件》中作者专门在注释中特别描述了“红乌镇”的街道位置:
建设中路是红乌镇主街,长1500米,两边各有三条巷道,与主街构成一个“非”字:
求 青 朱
知 龙 雀
巷 巷 巷
(西) 建设中路 (东)
明 白 玄
理 虎 武
巷 巷 巷
通过直观的文字排列,在文本世界中确立了清晰的空间定位,更容易使读者明晰各个街巷的方位并厘清故事中的人物位置关系。这条关于街道的“隐线”在文章最后连环杀人犯的行凶路径中也起到了铺垫作用,平时看似平行独立的街巷与生活在各个“规整小盒子”中经历迥异的小人物们在都这场精神病人的暴走中丧生。而“红乌镇”“青龙巷”“朱雀巷”“白虎巷”“玄武巷”这些带颜色词的地名加以道教传统神话更增添了小镇迷信阴郁的氛围。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早上九点叫醒我》中:
他一共摘下六片并捧凉水浇湿,然后将它们摆成如下形状:
● ●
● ●
● ●
读者与故事中的人物一起像猜谜般注视着这些圆形元素,康定斯基认为“形状也拥有特定的色彩关联。圆形——蓝色,方块——红色,三角形——黄色”。而蓝色又被认为与男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这个以男性掌控引导的充满情欲气息的场景中,圆形元素拥有比任何文字更强大的吸引力。而紧接着作者就公布答案:
“算你懂事。”金艳按照如下的姿势爬上去。
左肘 右肘
左膝 右膝
左足 右足
在排列的几何图案中,一个生涩的男人与一个风情的女人暧昧调情的细节被展现出来,文字图形化带来的这种画面感超越了文字描述,突破了单从文字出发带给读者的视觉想象,通过一种更为形象却又简洁的方式,隐晦地表达出作者想要描绘的画面,在这种隐晦的表达中增加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
按照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观点,“图像是现实的模型”,“图像、事实与对象事物的逻辑图像是一致的”,根据几个圆点的排列组合,以及背后相同的逻辑图像,我们可以想象出阿乙试图呈现的画面。构造的文字图形作为一种辅助性表达,可以帮助读者直观和具体地想象作者所要传达的真实画面。
结 语
“一个人看到颜色和形状、声音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越多,就越能够在更高的层次看到自己的灵魂。”正如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的“颜色是第二性的质”,物体颜色的不同在于人接触这个物体时的感觉,人与物打交道的方式、主体的情绪以及生存处境都会决定人看到这个物的颜色时呈现出一种主观性。这体现在他种种对色彩的特殊化使用中,他使同一类颜色在刻画不同事物时,呈现出独特而微妙的差异。这些色彩的差异使得阿乙眼中的事物尤其能给读者传达出一种情绪上的共鸣。阿乙对色彩的娴熟运用,尤其体现在他将最严峻的事态、冷酷的对象以一种充满历史性的灰色,不动声色地排列于一个巨大的荒诞剧场之中。被陈列者、描述者和观察者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和传输这种荒诞感本身就是阿乙作品的现实性意义。在此意义上,灰色又是最能传达出生存荒诞感的颜色。另外,阿乙在作品中做到了将自然的经验形态和本能的自然活动相结合,他在运用色彩时非常重视事物本身呈现出来的自然的色泽,这保证了剧场中的事物具有真实性。
呈几何图形排列的字符,更是阿乙刻意安排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秩序,仿佛逻辑碎裂的一角,直截了当地传达出空间上一种充满戏谑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来自阿乙将他对人类荒诞生存处境的诊断和对注定会发生之事的必然性的洞察注入文字的空间排布之中。这种方式总能直观地把被生活缠杂掩盖的人直接摆在平面之中,让人直面他的命运。阿乙时常怀着“对‘上帝不要的人’的深刻同情、对‘得不到’的宿命般的求证,以及对人世的悲凉体验”来书写。在这种真实面前,人才会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遭遇自己虚无的命运,而人们的生活就是这一遭遇的战场。这种病态式的痛苦和绝望不仅教会了我们正视生存处境的荒谬性,还让我们在反抗绝望之中学会了与荒谬和解,甚至是在荒谬之中生活。在阿乙揭示的种种荒谬的情境之中,那不可溶解的深深被生活、世俗规范所遮蔽的人性才将其真实的一面展露出来。这些真实的人性本身就是我们荒诞命运的制造者,带给人们苦难的命运就是人类根本的难以磨灭的特质。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遭遇的不是外在的打击和毁灭,我们遭遇的就是我们本身,这就是人类生存荒诞感的来源,也是阿乙必须逼迫我们直面的现实。更加荒诞的是,遭遇自身并没有给我们以熟悉感和安全感,相反,人总是在对所生存的世界的难以填补的陌生感之中遭遇自身的。陌生的世界之中,是一个个陌生的自我。这些自我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作为彼此命运的制造者、遭遇者、承载者甚至牺牲者隐去了自己独特的面孔。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爱情还是暴力都没有挣脱命运荒诞性的安排,反而陷到更深的无力与悲哀之中。究其原因,人总是无法与自我和解,既无法认识我自己,也无法真正成为我自己。挣脱与无力循环不已,就是阿乙揭示出的荒诞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成了阿乙作品的一种画布式的底色,在这种精巧布局之中,荒诞的现实性无疑是阿乙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馈赠。
注释:
①爱克曼著, 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②玛依耶芙娜著,闫泓多译:《色彩心理学》, 河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③爱克曼著, 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④阿乙:《情人节爆炸案》,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⑤阿乙:《五百万汉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页。
⑥阿乙:《情人节爆炸案》,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⑦阿乙:《情人节爆炸案》,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⑧阿乙:《五百万汉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⑨阿乙:《情人节爆炸案》,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⑩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 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