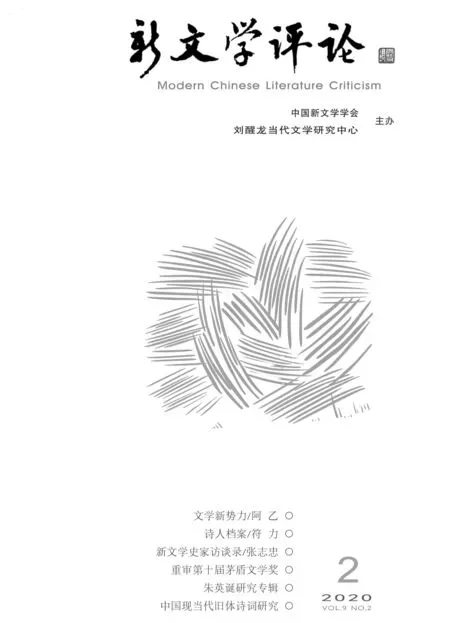“向心怀无限热情却又沉默寡言的事物看齐”
——论符力的诗
□ 赵目珍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数年前拜读陈世骧、王德威等先生论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专著,后来又受阅学者张松建论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的专著,一时很受启发,甚至萌生过“百年新诗有一个抒情传统”的论说。此后心怀大梦欲从事这一论题研究,无奈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唯有辍怀。尽管如此,长期以来阅读和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使我常常得到对此一论说的证验,内心总是充满了喜悦。抒情是中国诗歌的老传统,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由来已久。但是对于中国新诗,这一传统是否贯穿了百年,总还是得对新诗的百年历程做一番研究,否则草率地下判断便是一种武断。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当代诗,每每读到诗人的诗作,我总是习惯于先将其定性为抒情还是非抒情这两种类型中的某一种,甚至在对某些诗人做个案研究时还曾做出过“新诗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抒情的路数上来”这样的断言。可能这是一种偏爱。不过,古今理论家的持说总还是存在诸多明证。比如“诗缘情”(陆机),这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家的话语;“情感是诗的生命,也就是诗人的生命”(李长之),这是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家的话语;“无论什么东西都难以导致中国先锋诗人对激情的放弃,因为激情本身就是诗人放弃一切东西的结果”(陈超),这是中国当代诗学理论家的话语。因此,无论是百年还是千年,理论话语一直有其一脉相承之处。故从某种意义说,百年新诗必然有一个抒情的传统。今天我们要面临的是一个70后诗人的个案。
一、 情:诗的本质
著名诗人李少君曾这样评价符力的诗歌:“符力是一个典型的纯正的抒情诗人,他的特别在于他将海南岛的清新湿润气息带进了诗歌,当然也有一些忧伤。一个经常被遗忘的岛屿上的诗歌,呈现出的特殊优雅面貌,无疑会让人眼睛一亮耳目一新。”①全面考察符力的创作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评价是精当无疑的。首先,肯定符力诗歌的抒情特质;其次,指出其诗歌写作带有地域性特点,从而凸显出了个人化的诗歌面貌。的确,符力的诗歌是以抒情为本质特征的。但其抒情性既有一定的普遍性,又有其个人特色,在许多地方与当下诗人的创作保持着一定距离。
此前看很多学人关于抒情之“情”的理解多解释为普遍的“情感”,其实这种解释有泛滥的嫌疑。在更多的情景之下,情感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它面对的常常是那些激情澎湃的诗人。而有些诗人是不同的,他们常常沉浸于一种淡淡的情绪中,而情绪只像是渗流的源泉,舒缓着跃动,并无激烈奋发的特征。因而,有时候很多诗人的抒情,抒的乃是一种情绪,而非情感。早在新诗发轫之初,理论家于赓虞就曾指出:“诗歌的灵魂是情绪——是人生和宇宙中间所融化成的一种浑然之情绪表现。……诗歌最紧要的质素是这样情绪的表现,而非思想的叙述。”②从某种意义上看,符力的诗歌也常常表现为一种情绪。除了少量略显激越的诗篇如《我为何》之外,他往往从生命的简洁跃动中发掘出那些在内心中隐隐流动的水澜,将它们悄然注入诗中,从而让诗歌有了流动的活力。如早期作品《每棵树都有自己的难言之痛》,前三节借助叙述来表达人与树木之间的互相关系,最后则从主观的视角感受“被一种事物钉着的树木,有苦说不出”,并进而迸发出内心惶然的情绪:“此刻,神祇让一些人歌舞升平/让一些人醉生梦死/只让他亲眼看见:/黑暗之中,冰雨萧疏/无法入睡的树木,默默落泪。”当然,诗人的这种情绪不是显豁的,它被诗人隐藏在了描述的语言中。宋人魏泰说“情贵隐”,有时候这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是诗人内心的隐秘情绪决定了诗歌写作必须如此。
明清之际的学者黄宗羲曾说:“今古之情无尽,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其所谓“情有至有不至”,“情至”是说内心因被激发而情感来临了,“情不至”则指内心的情感没有被激发出来从而也就无从流露。此所谓“情不至”有点类似于理论家常说的“无病呻吟”。而一个人之所以会如此,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因素是诗人没有这方面的情感体验,而是硬着头皮进行创作。前文李少君的评论指出符力的特别在于“他将海南岛的清新湿润气息带进了诗歌”,实际上是已经指出了其诗歌抒情性的一个重要特色,那就是他的许多诗歌摹写的都是海南这一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行为事理。这一点当然与符力本人是海南本土人有关。故而其抒写带有故乡性的内心体验,从情感上而言,大致不会有多少偏差。因此,在符力的诗歌中我们所见到的透露海南气息的作品,往往都是因感至而情深。如其《白沙之夜——致江非》,写在某个五月,他与诗人江非相遇于海南中部小城白沙,二人在街头的夜色里边喝茶边聊一些问题,这其间除了地理背景带有海南风情,诗歌的抒情也融进了海南的山水与人情,如:“在今夜的逗留之地/喝下白沙之水,清心,明目/我们喝淡了茶色/却喝不淡楼房倾覆在身上的暗影”,“家,在千山之外/上个世纪建造的这座老式旅馆/如何安顿过客肉体上的/灵魂里的猛兽/我们,还是仰望星空吧”,“明月,诞生在夜树的枝条上/清辉洒向人间/洒向白沙/天堂,为仰望的人/逐渐明朗/而五月的这个星夜/是谁的咳嗽声,明明灭灭/那一节又一节烟头”。此外,像《致在古榕下纳凉的老人》《大海帮我们记住》《雾中人》《海南——仿辛波斯卡〈越南〉》《暮归》《南海阅读者》《把手伸进海水里》《老城江畔致苏轼》《临高角看海》等都是此类非常成功的诗篇。
二、 物:诗歌内部的秘密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说,“情以物兴”(《文心雕龙·诠赋》),又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可见,在抒情的文学中,外物有着迎意引心的重要作用。研究者如果只是看到了符力对于海南风味的宏观描写,实际上还是不够的。细读符力诗歌的人还会发现,符力对于“物学”有着一种独特的偏好。他的诗歌中总是充斥着大量对物的书写。符力一方面通过物在诗中的“生长”与“伸展”,抵达情的所在,另一方面也通过对“事物”的倾心表达建立起了个人写作的一种指向。从某种意义上说,“物学”乃是其诗歌成功的一个内在秘密。
植物书写是符力诗歌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历代诗人中从来都不缺乏对于植物的关注者,古代诗人中,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都是咏植物的高手,新诗中对于植物比较青睐的诗人有徐志摩、舒婷、王小妮、郑小琼等人。不过,诗人们虽然都垂怜植物,但每个诗人对于植物的关注角度和以之切入诗歌的视角却都有所不同。符力对于植物的迷醉在于他并非通过植物的“穿行”来“体物”,而主要是通过它们来营造一种抒情的氛围或以之作为抒情的载体。所以在符力的诗歌中,我们很少看到他有对植物进行的纯客观描写,即使有,也往往是将对物的赋咏融入抒情之中。如在《平原上的黄昏》一诗的第三节中,他一口气罗列了十四种植物:“园子外的天空下,柳树、栎树、桦树、杨树/如此贫穷:叶子掉光/上无片瓦,哪里都去不了/榉树、朴树、椴树、栾树、槐树、枫树/如此无助:人人自危,不可自拔/哪里都去不了/七叶树、白果树、合欢树、悬铃木/勉强度日,都在那里/等着”。很显然,符力的主要目的还是以之来渲染人的情绪,但这些植物又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与平原和黄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与诗人的情感形成了一种内在关联。符力的确偏爱将植物付诸诗歌,这说明他是热爱生活的,热爱大自然及其所容纳的各种生命的,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总是将这一点在诗歌中体现出来。当然,作为一个在海南本土生长的诗人,符力对于海南植物的找寻与入诗也许还有更深刻的意义。他一直在海岛上虔诚拜写的那些植物,它们本身或许也是作为灵魂的一种所在。一如诗人江非所指出的那样:“读符力的诗歌,总会被他作品中遍布的那些植物的气息所迷醉,在他的诗中滑行,就犹如在一个叶片和根茎所构成的植物王国里穿行。自古以来的中原诗歌、贬臣诗歌以及移民诗歌所造成的输入文化的多重影响之下,海南原生诗人需要根据自己的生活、心灵环境说出对于自身的当下理解,对于符力来说,最有效的,就是要在海南的岛屿上寻找并确立自己的‘神’。符力看到了时间在这些植物性的世界中那种近乎静止的美,他几乎到了时间的源头,这是植物之神为符力带来的它们的神像之美,也是符力为我们交代的一个背向的世界之美。”③
其实,从某个角度看,我更青睐他对于那些普遍性“事物”的着迷叙述。他总是将这些体味深深地嵌入诗歌中,对这些“事物”进行着或狂欢或哀歌式或低沉或高昂的纠察与细读,让它们在素朴的出场中有了召回某些“通向未知”的可能性。如其在《秋天的草场上》深情地呼喊:“哦,是谁让我遇见这些容易被人忽略的事物/是谁让这些声音飘了回来——”;在《江岸上》他则静静地叙述:“傍晚的江岸上,你仍然让我看见/江水奔走,树木静立/这静立的事物如此安逸”,“傍晚的江岸上,你仍然/让我看见树木静立,江水奔走/那奔走的事物,从一开始就脱去了骨头/就学会了婉转与缓慢”;在《雾中人》中,他轻轻地叹息:“我热爱的事物啊,纵使近在眼前/有时候,也难以捉摸”;在《把手伸进海水里》中,诗人体味到:“世上消逝的事物也曾经/亲近每一颗心灵”;在《过鲁甸》中,诗人焦灼地呼叫:“我感到什么事物揪住我的心/死死揪住我的心,像树根,草须/揪住悬崖上的岩石”;在《歌》中,诗人立愿:“星辰璨璨,草木深深/我向心怀无限热情却又沉默寡言的事物/看齐,一意写诗”;在《书坊小记》中,他惘然而又喜悦地叙述:“已是大寒之日,沿着那些纷繁又细小的路子/一些事物早已逃离,一些事物/正秘密归来”。而值得指出的是,诗人这些在诗歌中“特立独秀”的句子大都处于诗歌的开头、结尾部分,即使少数不在这两个位置的句子,也都处于诗歌中间非常显要的位置。这说明诗人是有意安置这些诗句的写作的。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专门在其《文心雕龙》中撰《隐秀》一篇,其所谓“隐”即含蓄、有余味之意;而“秀”则是突显、独立之意,目的在于突出篇中独拔、卓绝的部分。正所谓“情在辞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不过理论家指出,篇中“独秀”的部分虽然有鹤立鸡群之效,但其写作仍然应该出于自然,而不能见出痕迹;但反过来又说,虽然是出于自然,但仍可见出作家长期以来对写作惨淡经营的用心。符力的写作或许是在无意中暗合了这一理论。因为每读其诗,我们总能发现其诗中这些独绝的句子,但又见不出其故意雕琢的影子。然而,一旦你综合起来研究,又发现这似乎是他别具匠心的安排。从写作学的角度讲,这并非一种偶然,他昭示着诗人通过某种技巧(或方式)的运用建立起了个人写作的一种指向。
三、 静:诗的美学风格
符力的诗歌从风貌上来看,主要呈现出一种“静”的美学风格。他总是在素朴的叙述中试图抵达这种氛围,从而让人感受到一种“静”的快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风格的呈现乃是诗人之文本与诗人之情性在内在机理上的一种会通,它昭示出诗人对于“静”这一品格的认知和追求。诗人诗歌的“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对于自然美的呈现。符力非常善于在诗歌中营造自然境界,借助外在的日月、山水、风雨、雷电、花草、林木、鸟兽、虫鱼等意象将场景描述得或氤氲迷离,或清冷幽深,从而将心理实现的外在气息与需要描摹的心境照应得契合如一。如其《雨后》一诗,虽然意在呈现“雨后”所见场景下内心的些许不安,但是诗歌肇始对于白鸟的描写:“拍去雨水,白鸟飞出丛林/栖在昨日栖过的枝丫上,梳理羽毛/重新辨认雨水清洗过的世界/远山依依,烟水迷离/白鸟随时都可以远走高飞”,仍然透露出一股静的意志。如果说这还是诗歌中对于“静”之风格的部分呈现,那么《秋日的高原上》一诗则凸显出了一种整体的静谧。该诗写秋天的高原之上,“大鸟,雄踞众山之巅”,“远走高飞”,“拒绝俗人的仰望”;“一夜之间,湖水蓝透了”;而白云像“神的披风,或者大鸟的羽毛,遗落人间/沉睡于湖底”。该诗描摹了一个无限辽阔的空间,整个景象就像一个没有任何束缚的大自然,清静无为,一无所系,就像诗人用自己的语句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平静,像一个诗人的形容/像一个国度,恒久/不化的感伤。”
二是对于心性安宁的反照。符力的文字虽然时常游走于自然的旷野,不容易显露内心的动荡,但是读者很容易见得出,其实他仍然有表达游弋不定、略有不安的“小心思”的意图。不过,此处需要强调的是,诗人这种对于内心游移的展示都不是大动荡,大写照。人之内心的意志与思维总是处于变动不居之中,这种略有不安的游移本身其实是一种相对安宁的反照。如《青草坐满了那把长椅》,体味的乃是某年某月某日一对年青人在长椅上共坐的场景,然而“谷雨过后/从条形坐板底下,越长越高的青草/坐满了长椅,坐满了/一个人的春天”。很显然诗人意在通过“青草坐满长椅”来表达内心的一种“痛痒”,然而诗人并不直接表露,而是让这种怅惘抑或惘然从青草里冒出。这种手法是高明的。又如《母亲在对岸割芦苇》:“芦苇茂密而修长/母亲,却是/那么矮小而单薄/我东张西望,不见母亲的身影/只见河岸上的/一片波浪,起伏不定/起伏不定”,其手法与前例类似。再如《一个人消磨时光》,写自己“雨夜归来,经过水洼、水洼、水洼/经过路灯光亮树影暗淡/又经过树影暗淡路灯光亮/街巷潮湿,黑夜漫长,但壶中有热水/咖啡分馨香”。从场景的氛围上看,既有暗淡的一面,也有明朗的一隅,这本身即显示出一种矛盾,因此诗人内心不安本就是有所预期:“一个人消磨时光/不欢畅,却也不比太平洋彻夜翻滚还悲伤。”从某种角度上说,诗人的这种“静”体现为了感伤、浪漫与微哀,偏于生命体验中最真实也最客观的一面,但是诗人处理得比较恰切,体现出了一种“平和”的原则。
三是对于意境美的流露。从写作上看,符力也许并无刻意追求意境的企图,但是其长期以来形成的游心自然和吞吐“小心思”的写作倾向,使其诗歌表现出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这种程式理解为一种“形神之间”的过往,而不必将之理解为一种“养成”。但不论如何,符力对于意境美终究是有所奉献的,这也是很多诗人所希望达成和企及的诗之“高处”,值得引起关注。符力对于意境美的呈现,最令人欣赏的是其对整体静谧感的凸显。如其《秋夜》一诗,该诗写某个秋天的夜晚,诗人“离开久居的村庄”,“向山间而去”。一个“白衣行者”“踩着星辉”,像一个孤魂。然后孤魂变成夜鸟,“被月光吵醒/一齐鸣叫。那些声音,让遥远的星空知晓”,“山岭醒来”;最后幻想不远处的山寺里“有一个读书人,在灯下翻阅黄卷”,而诗人“希望他恰好翻到王右丞的《鸟鸣涧》/一抬头,恰好看见/月光照亮北面的窗台”。这种整体的静谧,首先体现为一种宏大背景与皎然个体的合一,其次动用了古人“以动为静”“动静相宜”的表现技巧与写作命理,最后以想象致敬王维诗的禅意,从而让整首诗歌形成了一个既玲珑又浑然一体的风格,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说《秋夜》整体体现的是一种朗阔的静谧境界,那么《过谭昌村》体现的则是一种清冷的静谧境界。该诗写谭昌村里老人们烤火的日常场景:“静默无语。偶尔的音响,是鸡啼/是火堆的叫喊:哔啪,哔啪”,然而当“我踩着落叶离开火山村,已是黄昏时分/烤火老人只剩下其中的五个”。为此诗人设想这谭昌村的“明天,后天,海风越吹越寒凉/一起取暖的将是谁跟谁”,然而诗人并不直接告诉答案,而是悬置思考,以一种场景描写来收束全诗:“列车从南港那边开来,朝琼山那边驶去/我听见的,是呼的一声,不是缓慢的/咔嚓,咔嚓,咔嚓。”这种意境的呈现就像是一种击打心弦的流露,它让读者的内心延伸出了一种悲凉的气息。
从符力十余年的诗歌历程看,他一直持守着“抒情”这一古老的传统,同时保持着对“物”的敬畏和垂注,并且将“静”的风格一直贯穿于诗歌创作当中。可见对于他而言,持守是其诗歌创作的一个法宝。对于某一种类型的诗歌坚守不出,是既有利也有弊的,但对于一个诗人形成自己的独到风格却又异常紧要。符力曾这样表达自己对于诗歌的看法:“适合诗人采用的语言方式,有利于诗人传达作品内容的种种努力,都不会因任何‘争议’而彻底改变。因为,人类的倾向性在主体上不紧也不松地决定了文艺作品所形成的样子。我告诉自己:写吧,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别批评谁,也别听谁的批评。跟着内心走。”④可见他是一个有坚守的诗人,而这或许正昭示着他将在这条道路上打下破与立的根基。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再重复一遍诗人在《歌》中所立下的那个宏愿:“向心怀无限热情却又沉默寡言的事物/看齐,一意写诗”,以此来表达对于诗人的敬意。因为这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精神。
[本文系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2017 年度重点课题项目(zdzz170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符力:《符力的诗》,《中国诗歌》2012年第6期。
②于赓虞:《诗歌与思想》,《京报副刊·文学周刊》1925年7月11日。
③符力:《在翠湖(组诗)》,《诗潮》2012年第5期。
④符力:《符力诗歌及诗观》,《诗选刊》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