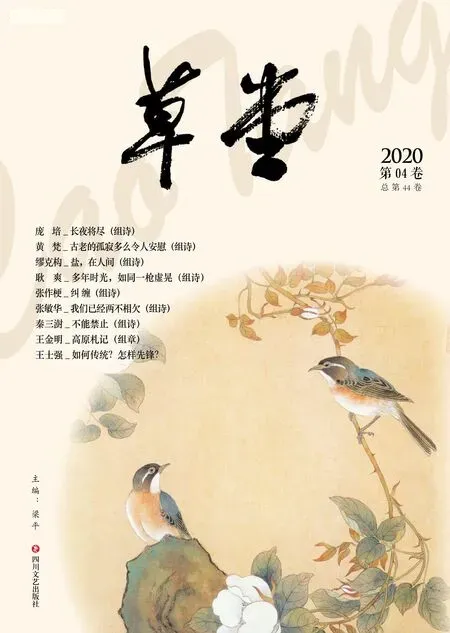我蜷缩在一个浪头里
◎ 庞 培
诗人说不上话,发不出声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形,在诗人的一生中屡有发生,几乎被视为常态,非常蹊跷,也很有意思。他突然沉默下来,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而这沉默,似乎比说话表达更加急切;沉默的一部分声音或言说,仍在他之前抒写的诗作中、在读者那里广为传播。我们不妨说,之前的沉默是有效的。事实上,最好的诗歌有时等同于最好的沉默,因为那是一种人类的智慧和语言莅临人世过后的沉默,所以,诗人一般在三个层面上的沉默(沉思默想)中过活。在第一个沉默中,他保有诗人威权、确切的身份,那个身份几乎囊括了精神世界的一切:神秘、生死、命运、人、自然、音乐、舞蹈、建筑、食物和语言。在第二个沉默中,诗人进入其职业生涯最令人骄傲的阶段:一首诗,一个诗人正静悄悄地跟万事万物做长时间的对话。诗和人世间的昼夜产生交流,不时释放出类似云层中的静电、气候现象一类的信息。 诗人(诗歌)进入了天地间。而在第三阶段的沉默中,诗人不见了,只普通平凡地剩余下一个“人”。他的话语暂时停歇、终止了。或许不能说是终止,但其文字语言背后的生命载体,却普遍地处在非第一人称的人群中间。诗人在休息,在观望,四处走动,甚至酝酿……伟大的诗人即使在这个阶段,也仍旧是看得见的诗人。次一等的诗人进入此阶段,会带给人们显著的焦灼不安,一般三流以下的诗人,在这个沉默、贡献不出新作的阶段,就可有可无了。再往下, 那些处在机械思考阶段的诗歌写作者们,跟本话题(沉默作为诗)就无关了。
那么,诗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
……类似每个人的自己的声音。
诗人是怎样通过其秘密、 秘而不宣的声带,编织进万物众声,进入众生之迷宫的呢?
人的声音——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奥秘!
按照艾略特在《诗的三种声音》一文中剖析的,人的声音大的方面,也起码或至少剩余三种以上,即:高音,低音,假声。
一个时代的文学或精神生态,且由这三大声音区域交织叠加而成。
人类历史上,也屡有声音缺失,诗歌大面积荒凉的时期。
诗人,有时仅仅是个测声仪,有时是被测听的声音本身,有时是所有这些空间生命的碎片的收集者。
在一种文明进入其丰饶期,诗人的在场以及辉煌的缺失,都是较好的例证。就像所有住宅有窗户一样,文明社会也天然地携带其诗人天才的呼吸。
上述三个层面的“沉默”都普遍皲裂、破碎不成形。声音和沉默,在今天,完全不成比例。一般人几乎听不到,也毫不在乎诗的声音,在一个古往今来以“诗教”立国化育的文明传统之后, 出现类似“今天”这样沉默的时代,委实使人难以置信。人们普遍依托无知无识过活。再激愤的言语,也不足以形容这个时代诗性之贫瘠、狼狈程度之一二。事实上,诗人之寡言少语,等同于我们的语言、汉文明之寡言少语。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根本听不到一丝一毫的诗歌;能够听到的、充塞耳畔的,大多是假的。 诗其实跟社会现象无关,是“社会现象”在跟诗有关。诗的声囊紧缩,仿佛一匹被紧攥住四蹄的小马驹,而草原在它痛苦的蹄足之下一望无际。但我说的不是社会现象中的诗,我只想谈谈诗歌,或诗人本身。
缺少了诗,就像暴雨将至的天空,缺少了闪电——一次又一次眨动、燃起沸腾锡水样白的天光,但一次又一次地,天幕深处哑默无声。
就像草原再不盛开细小无名的野花——那种牧民们自古以来亲切称其为“格桑花”的草原雏菊。
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是塔塔尔族人。他能懂得我的比喻。
“我们的剧院简直乱七八糟,没人知道后天或者明天,甚至是今天会发生些什么。”(拉赫玛尼诺夫,1897 年12 月4日书信)
的确,人们在诗歌里倾听天空、沉船、入土的棺木、 婚礼的彩带和新娘脸上羞涩的红晕。人们在诗中倾听婴儿牙牙学语,蹒跚向前。听到绿草地上的晨曦,冰凉露水,短暂而又长久的白杨的身影,听恋人轻轻放下的膝盖,在草地上压出一个握紧了的小拳头。人们在诗歌中倾听食物、泪水、大海和逶迤起伏的山峦。倾听各种大小动物,各种生活细小的动静,各种器皿在室内的涟漪,各种季节缓慢更新的冷暖人生。人们在诗歌里倾听人——自己的同伴,倾听永恒星空的天、地、人。历史、记忆、遗忘、悲伤……人们清澈信赖的目光,像一代又一代人回忆各自不同的青春一般,把眼眸投向那道无形看不见的发育生理线一般的诗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不属于肉眼可见的,在内部的也在外部,在里面的也在表层,而处于灵魂深处的惊喜一定会在最平凡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叫出声音来!
这抑制不住的叫喊,就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