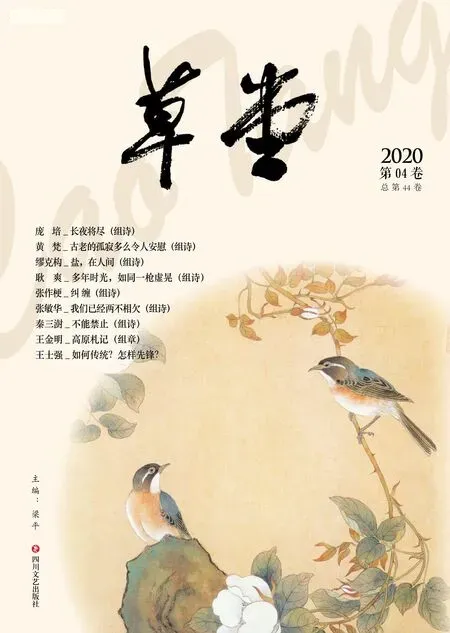作为沉默或沉默时代的诗
——庞培诗歌简评
◎ 覃 才
庞培是60后诗人,按萨义德的“晚期风格”观点,作为写诗、思考诗多年的诗人,庞培也进入了他成熟性、一致性地理解人生、理解诗歌及理解时代的“晚期风格”阶段。庞培的创作谈名为《我蜷缩在一个浪头里》,文中交代的主题却是“沉默作为诗”,乍一看,很难理解二者的一致之处。但看完他在文中相继论及的沉默、声音、诗的有效性及诗的时代意义等内容,再回来思考二者,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与意义,是真的一致的。因为无论是他论及的“沉默作为诗”,还是“我蜷缩在一个浪头里”,谈的都是这个时代中真正的诗是怎么创作的和诗歌在这个“沉默时代”中的意义。
在我看来,庞培名为《长夜将尽》的组诗,作为一个能够进行自我言说的客观文本,是比较“恰当”地回答了他这个创作谈论及的诗人人生、写作状态及诗歌的时代意义等相关问题的。在此,他的创作谈与组诗,是真的构成他本人诗歌创作和当代诗歌创作问题的一个“闭合”隐喻。
结合庞培的组诗和创作谈,“沉默作为诗”至少有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是“沉默成诗”。这个沉默成诗,指向的是诗人一般是在孤独和寂静的状态写出诗歌的。这一点就像海德格尔说的“寂静绝非只是无声”,因为诗歌就是诗人在寂静之时的声音。对一个写诗的人来说,不难理解,我们的诗歌作品,无论好坏,它一定是在我们特定的状态、特定的时间下被创作出来的。这种特定的写诗状态与时间,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写诗的习惯。作为一个严肃和真正的诗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诗状态、写诗习惯,这点不难理解,也不能否认。作为写诗多年的诗人,庞培在他的创作谈中,说了三种沉默。这三种沉默,既是一个诗人写诗的状态、习惯的说明,又是诗歌写作的有效性与好坏等级的判断。沉默与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和好坏关联后面再统一谈,结合庞培的诗歌文本,他所说的“沉默作为诗”至少有几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 沉默是一个人独处的状态。写诗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验,我们的诗歌是在一个人的独处状态下经过或是瞬间思考,再结合相应的回忆、经验后写出来的。这种一个人的独处(即使有人在场,我们也会暂时进入个人独处性的意识与精神空间中),其实就是一种沉默的状态。只有在这种是真正的一个人的沉默状态中,或是有外人在场的居于意识和精神的独处状态当中,我们才能思考眼前与过往之事件、经验、体验的诗性关联,才能写出诗。如庞培在《冬天下午读诗》中写道:“屋子里有阳光、偶尔几声鸟鸣/院子草地完全荒芜了/附近走过的人任其荒芜/一首诗,等候在日子/荒芜的尽头/鸟鸣声,有人的眼睛注视诗句时的/寂寞光亮”。这一个冬天的下午,“屋子里有阳光、偶尔几声鸟鸣”说明了诗人是处于一个独处的沉默状态。在独处的沉默状态中,诗人产生了诗性的思考与回忆,即“寂寞光亮”。这种寂寞的光亮,再经由诗人眼前和过往的想象,生成出“诗人,仿佛人类集体的眼睛/雪、大自然、冬天的郊野/一齐在其中睁开。过去和将来/如同长夜临近”(《冬天下午读诗》)的人生感悟。这一意义上,庞培在独处的状态下写诗的情况解读,足见独处让“沉默作为诗”的写作形态为何。
第二个维度是,沉默是黑夜的空间。对诗人来说,黑色的夜晚非常神奇,它总会不经意间让当下联结过去和未来,让诗人写出诗。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每天晚上都会面对的这个永远沉默、永远巨大、永远平静的黑夜,就是诗歌的生成场域。庞培作为一个理解沉默或是经常处于沉默状态的诗人,他也在黑夜当中感受到了黑夜与人共同具有的这种沉默及其具有的诗歌生成意义。如在这个永远沉默、永远不变的黑夜空间中,庞培产生了自己在变、自己已经“很少是自己了”及时间一去不返的人生感悟:“我现在很少回来了/很少是我自己了/在我的窗外:——长江/人与大地的灵魂契约/滚滚东流”(《暗夜》)。同时通过在这个巨大、平静、无限的黑夜空间中思考,他也向死而生地明白了生命的瞬间与意义永恒的秘密:“我走出我的身躯/终老,安静于这一刻/脱离了称之为白昼的那个黑夜//世上一切的旅行/都是长夜将至/芬芳而馥郁”(《长夜将尽》)。显然,在黑夜这个特殊的空间中,庞培的诗歌表现了“沉默作为诗”、沉默作为意义的可能。
第三个维度是,沉默是一种平静的言说声音。诗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这种不会说话的语言,由于历史的发展、人类的积累,它作为人类词语表达的总秩序和经验总和,本质都是平静的。庞培在创作谈中说:“最好的诗歌有时等同于最好的沉默,因为那是一种人类的智慧和语言莅临人世过后的沉默。”就是在个人的年龄、经历、体验的基础上,以成熟、平静的生命状态共通性地理解个人的生命与整个人类的发展、理解个人的语言与整个人类的语言、理解个人的诗歌创作与整个人类的总诗歌之关系。在庞培的诗歌当中,他所写到的“世界是一个人的/我曾骑马渡海来过/天黑之后我是古镇的月光部分”(《冬天来浏河乡》);“火车,是一代人的遗像/火车穿过旷野/月亮孤零零地进站” (《火车遗像》); “长江东流。汽笛声拉响一个古代瓮城/世上只有一个地方,能让恋人们躲藏经年/历尽艰险”(《看不见的爱人》),就是以中年人的平静心态、平静语言,言说生命、时间及世界。他将这种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具有的人生阅历、生命铅华的平静诗歌创作,提升至人类智慧和语言的共性的概观,是个人诗歌创作与审美成熟的体现。
“沉默作为诗”的第二种解读是庞培所说的在诗人身上屡有发生的诗人说不上话、发不出声。诗人这种说不上话、发不出声的情况,可从个人和时代两个层面去找原因。个人层面上,诗歌作为由人创作的艺术,它的产生与人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尽管界限不是很明显,但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大致上处于好与坏、平静与烦躁、 想表达与不想表达的循环周期之中。在一个诗人身上,这个状态的循环周期,往往影响或对应着写作的周期。也就是说,在状态好的时候、平静的时候、想表达的时候,诗人是能够顺利的写出诗歌的。在状态不好、烦躁及不想表达的时候,诗人就产生了“说不上话、发不出声”的写作疲惫。时代层面上,说“诗人说不上话、发不出声”,即是说诗歌作为时代的发声筒,它在诗性贫瘠的时代有何作为和怎样产生应有的意义问题。 就庞培个人而言,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沉默的时代、是一个诗性贫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诗歌作为时代的声音,是说不上话和发不出声的。诗歌的这种“声囊紧缩”状态,也在表明沉默作为诗人的一部分,是诗歌的一部分,更是时代的一部分,它们是问题,也是意义。
由上解读,庞培所说的“沉默作为诗”,很大程度上说的是他个人诗歌创作状态和他对诗歌创作的时代意义的思考。他的创作谈标题为《我蜷缩在一个浪头里》就是这种思考的一个隐喻性概括。按他的意思,如果我们将时代理解成一片大海,诗歌是推动大海前进的浪头,他个人的诗歌创作无疑也是这个诗歌浪头的一部分。他蜷缩在这个浪头里,一方面表明他诗歌创作的沉默、平静状态,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说话和发出声音,说明他个人和时代的诗歌创作虽然是沉默、式微的,但依然是有意义。哈罗德·布鲁姆说:“诗表面的软弱,有时候也是它的强大,它退却到你的内心,在底线处发出声音,但却能帮助你生活,让你做个不同的人。”就和庞培所说的“我蜷缩在一个浪头”意义相近。因为诗人作为时代的一个个体,在时代的汪洋大海中,诗人个人和诗歌本身都有软弱、无力的时候,这个软弱、无力就是庞培所说的诗人说不出话、发不出声。但作为一个写诗的人,看似无用、软弱的诗歌,却能让你做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个不同的人,并在相应程度上影响时代。这就是诗看似无用却有用、看似无意义的永远的魅力与价值。
显然,在庞培看来,个人和这个时代的诗歌创作是有意义的,但这个意义是以诗歌写作本身的有效性为前提。说得更具体一点,即是以诗歌写作者个人的诗歌才能与写作能力为前提的。庞培将“沉默作为诗”分为三个等级和所提到的艾略特的 《诗的三种声音》 (高音、低音、假声),既相互对应、相互印证,又是他对个人诗歌创作才能和这个时代诗歌创作有效性的判断。 庞培说的三种诗歌沉默中,第一种沉默是诗人经历积累、探索、磨炼后建立了确切的身份并形成了诗歌创作的精神世界的写作阶段。第二种沉默是诗人的写作生涯到了能够感知万物、与万物对话的骄傲阶段。第三种沉默是能够写出具有人类普世性诗歌的阶段。这三个诗歌阶段的诗歌创作,由于诗人个体的诗歌才能不同,就会出现诗歌创作是否有效的问题,即由沉默之音发出的高音、低音、假声。
对个人诗歌创作所处于的层级,庞培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但他说的“惊喜一定会在最平凡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叫出声音来”和“这抑制不住的叫喊,就是诗”,却表明了他诗歌创作的平静状态与意义。加斯东·巴什拉说:“在某些时刻,诗歌散布着平静之波。从被想象出来开始,平静就成为存在的突现,成为一种主导的价值,不论存在的附属状态是什么,无论世界多么动荡不安。”已过中年的庞培,他将对人生和时代的沉默与平静状态的理解,用于诗歌创作的认知与理解,自然也是他对人生、诗歌及时代的理解与价值判断。他深知诗人的沉默即是人的沉默和时代的沉默,诗的意义即是人的意义和时代的意义。在《茶》中他写道的“喜马拉雅山脉东麓充沛的降雨量/茶叶表面的无辜温和/照耀一个寂静的庭院/我在那样的一个黄昏里/正独自享用这人生若梦”,既是在说明个人和时代的沉默即是诗、即是人生,也在表明人能够以此沉默之人生、沉默之诗歌,创造不沉默的时代意义和影响。
庞培《长夜将尽》的这个组诗文本,十首诗呈现出的语言驾驭、哲理化表达及平静意味创造等特征,无疑表明了他是一个成熟和优秀的诗人,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他的创作谈论及的“沉默作为诗”、声音、诗歌的时代意义等,这种相对成熟诗歌观点的思考,更表明他诗歌写作的严肃性。文章开头部分谈到,庞培的这个组诗和创作谈是构成他本人诗歌创作和当代诗歌创作问题的一个“闭合”隐喻,说的是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和创作的诗观,基本是相互体现、相互印证和一致的。他个人在诗歌创作、诗歌观念及实际的诗歌行动上的些许出入,既是他个人的诗歌创作追求、认知与行动的反映,也是这个时代中理想的诗歌存在状态和真实的诗歌状态之间的矛盾映射,所以是一个“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