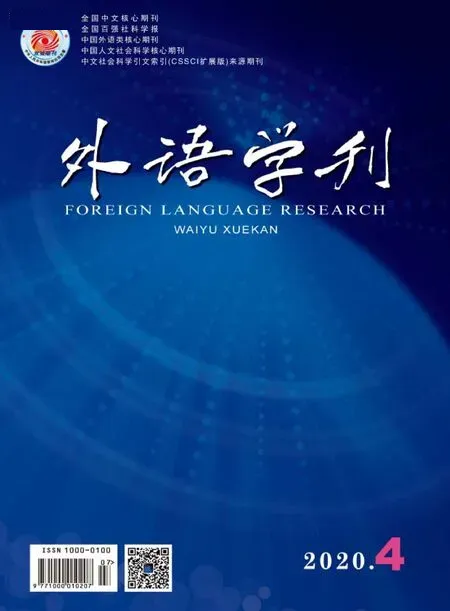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之诠释性理据分析 *
刘性峰
(南京大学,南京 210023;南京工程学院,南京 211167)
提 要:以科学、适恰的方式译介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是优秀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路径之一。鉴于此,本文旨在探究从诠释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的理据。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的诠释学理据主要源自以下几方面:中国古代科技的诠释性、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诠释性以及翻译的诠释性。
1 引言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中国古代科技宛若无数颗璀璨的星星熠熠闪光,尤其是15世纪之前,中国古代科技一直领先世界。这些科技成就几乎涵盖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如数学、天学、地学、军事技术、纺织技术、陶瓷技术、采矿、盐业、植物学、农业、林业、医学,等等。这些科技文明从未停止过同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通。科技文化在不同语言、文化、种族之间交流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翻译。故此,以适恰、科学的方式翻译与诠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成为中国优秀传统科技文化“走出去”的主要渠道之一。
以往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研究多聚焦于翻译策略、语言修辞、术语翻译、文化翻译、读者接受与赞助人等方面。仅有少数学者(王治梅 张斌 2010等)从诠释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翻译,他们均以《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为研究对象,分别借用译者主体性、斯坦纳(G. Steiner)的翻译阐释学、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等理论探究译者目的,知识结构,描述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文本和术语翻译方法等。但是,鲜有研究系统地观照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诠释学理据,未能充分彰显诠释学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解释力。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科技的诠释性和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诠释性和翻译的诠释性3方面展开论述。
2 中国古代科技的诠释性
2.1 科技的诠释性
传统观点多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阻隔开,认为自然科学是纯粹的真理问题,无需人的介入与诠释。而人文科学关涉人类的精神思想,必须依赖阅读者的诠释才能实现正确的理解。威廉·狄尔泰(W. Dilthey)是较早进行这种学科界分的哲学家,其“自然需要说明,精神需要理解”的论断成为许多人为科学划界的依据和标准(转自陈海飞 2005:27)。前者主要是“因果说明”,后者集中于“理解和解释”。这种偏见一直影响许多人,甚至是科研人员,也限制我们对科技翻译的认识和了解。这种对立反映出认识方式的对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方式”(黄小寒 2002:8)。
然而,这种划界并不能够反映科学发展的真实态势。“复杂性范式”的提出者埃德加·莫兰(E. Morin)将经过人为阉割过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殊称为“简单化范式”(莫兰 2008:5),这种简化方式是单面的、肢解性的,遮蔽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干预的内在属性,屏蔽自然科学须要诠释的基本事实,同时也阻隔和遮蔽译者对科技作品多元、动态的思想空间,限制翻译自由,减少科技翻译本来具有的诸多可能性,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及其翻译而言尤其如此。另外,这种分野自相矛盾,因为“理解和解释有无因果性呢?因果说明又有无理解和解释性呢?”(黄小寒2002:56) 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它忽视自然科学实践主体——人——的主观性。一方面,从科学实验、科学理论和科学编史学等角度说明自然科学需要诠释;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之所以需要诠释,是因为其解释受阅读者前见、历史境遇、传统等因素的制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科学诠释学、科学修辞学、技术解释学、科学哲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做出纠正,诠释学的介入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认识提供多层次、多视角、动态的多维阐释空间与可能。首先,科学哲学认为,自然科学同样须要诠释,其解释受阅读者前见、历史境遇、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其次,科学诠释学从科学实验、科学理论和科学编史学等角度说明自然科学须要诠释。同时也表明,自然科学的诠释具有结构性、历史性、语言性和对话性。此外,科学修辞学的当代发展证明,科学发现、科学交流和科学争论等都离不开修辞学的介入,使自然科学在认识论、方法论和哲学层面都具有新的意义。同样,技术解释学的进展打破我们关于技术不需要解释的谬见。因为从存在本体论来看,技术是人类的境遇性存在,而古代科技文本是古人当时科技性存在的表征。
2.2 中国古代科技的诠释性
当下的科学,其概念范畴、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主要源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代科学传统,而中国古代科技在诸多方面同这种“西方的科学”存在较大差异。换言之,除了具备当代科技的一些特点外,中国古代科技有其特殊性和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本体特征、认识方式、语言表征、研究方法等层面以及由这几个方面构成的整体运作系统。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译介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有必要以诠释学理论为工具,立足中国古代科技自身的特质,考察如何从以上诸方面及整体性对其展开诠释,进而探究这种诠释方式和诠释结果对于此类作品英译有何解释作用,为该类文本的翻译批评和实践提供诠释性理据。
以中西认识论比照为例,中国古代科学是生命的学问,强调整体性,天人合一,学问中更多地透视着“人”对于自然的理解与注解,如老子就强调“大制不割”。而西方的学问是分解的学问,研究者将自然作出条分缕析的肢解。西方传统认识论与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方传统认识论的特征表现为理性主义,即通过观察、实验、逻辑论证以证真伪,以寻真理;而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基本特征是亲和生活,具有笼统的整体性,重内向、重情感、重实践、重直觉,以及非对象化、非实体化和非概念化(喻承久 2009:61-79)。同样须要指出的是,根据王前的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同文化有密切联系,“技”与“道”“术”“器”“象”“意”等认知范畴之间有特殊的关系,这就决定中国古代技术与西方技术有很大差别,其解读也不能仅仅依靠当代技术理论(王前 2009:4)。另外,中国科技典籍具有典型的多义性。语言的多义性决定文本先天需要诠释的属性。保罗·利科认为,文本(尤其是书面语)须要诠释的首要原因就是语言的多义性,即“当我们站在词语在特定语境里的使用之外来考察词语时,这些词语具有不止一种含义”(利科 2015:77-78)。因此,对于听者或读者来说,依据其使用语境从多义中选择意义是一种必须的鉴别活动,这种活动就是诠释。依循其自身的特征和运行规律认识该体系,并与西方科技体系做适度与科学的对比,有利于对中国古代科技做出多元的、开放的、动态的诠释,这种诠释异于简化的、静态的、以追求等值为主要目的的翻译价值评价传统,可以为此类作品的翻译提供更加符合其自身实际的解释空间。
2.21 中国古代科技的哲学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很密切的关系。准确地说,哲学人文思想和方法对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影响,许多科学方法都是直接应用哲学的方法。例如,道家的天道自然被医学、农业和畜牧业广泛应用,阴阳五行直接成为中医的基本理论。(林振武 2009: ⅲ)中国古代的科技思想亦是如此,其原因正如张岱年所言,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表现出宇宙生成论与宇宙本体论的统一(张岱年 1985:58)。例如,中国古代医学就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由于中国医学与中国哲学关系太密切,受哲学的影响太大,甚至不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蒙培元 1993:196)一方面,中国古代医学追求“辨证施治”;另一方面,它秉承“整体观念”。
2.22 中国古代科技的人文性
中国古代科技如同中国古代哲学,始终秉持“天人合一”的观点,科技人员的思想和实践大都体现出这一理念,“天、地、人”是一个整体,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相处。“中国古代科学的独立性并不明显,它依附于人文学科或者深受人文学科的影响,许多科学方法是人文思想方法的直接应用,其所产生的独特的科学方法没有独立出来。”(林振武 2009:49)
就中医而言,它是一种自然科学,在本质上,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①, “但在这一过程中, 医学又包含大量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因素”(林巍 2009:64)。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医学认为,要身体健康,须做到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维系一种平衡。另外,中国农学也深受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把天地人3者看成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提出农业耕种要顺天时,量地利,致人和,做到这些就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马佰莲 2004:44)。这种人文精神、社会因素以及天地人的有机整体观都会影响读者对此类文献的理解与诠释,更会制约翻译过程与结果。
3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诠释性
自然科学的语言本来就存在一些特质,如“不严密、多歧义、具有隐喻性;自然语言的种类太多,翻译、沟通困难,语义保真性差”(黄小寒 2002:234)。只不过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在以上诸方面的特点更为明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其多义性与修辞性。
3.1 多义性
造成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多义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中国古代文字的特质所致,体现在字词、句法、语篇等层面。古代汉语一字多义和通假字现象较多,给读者的多样理解留下较大的诠释空间。余光中对古代汉语的特征有过描述,并将其与西方语言对比,“中国文法的弹性和韧性是独特的。主词往往可以省略,……甚至动词也可以不要,……在西洋文法上不可或缺的冠词、前置词、代名词、连系词等等,往往都可以付诸阙如”(余光中 2014:5-6)。因此,在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翻译成英语时,在很多情况下,原文中的主语、谓语动词、宾语等在形式上是缺位的,需要译者将其补全,这更增加翻译过程中译者诠释的弹性。同时,古代汉语没有句读,不同的读者依据自己的理解会有不同的解释。其次,同现代汉语,尤其是欧美语言相比,古代汉语大都十分简洁含蓄,“意在言外”“得意忘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都是中国古代写作的特点。再次,“由于受时空的限制,古典文学多古音、古义、古字,而古语、借字也屡见不鲜。解读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流传的过程,不知经过多少次传抄、刻版与排印,每经过一人之手,就可能产生一些错误,长期累积下来,往往鲁鱼亥豕,俯拾皆是。这对读者的阅读,真是造成莫大的障碍”(庄雅洲 2008:93)。最后,中国古代科技多受《周易》、道教、佛教、儒家思想、墨家思想等的影响,如《黄帝内经》之“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中有阳”“阴中有阴”来自《周易》之“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江国樑1990: 32)。由于这些古代科技思想本身具有很强的多义性,故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多义性的又一因素。这种文本多义性为读者和译者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不同诠释埋下伏笔。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大都呈现出意义的多样性。《黄帝内经》的评注大家王冰在评价其语言风格时说,该书“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王冰 2016:序)。以简洁的文字表达宏博的意义,道理深奥,旨趣深邃。因此,这种文字必然给读者留有较多的想象空间和诠释余地。例如,在《黄帝内经·素问》的 “八正神明论篇”里,“黄帝问曰:用针之服,必有法焉,今何法何则?”此句大意为,黄帝向歧伯询问关于用针的技术,有何方法。其中关于“法”的解释,王冰和张介宾各有不同。前者解为“法,象也”,后者释为“法,方法”。
《黄帝内经》的译者Ilza Veith认为,在翻译该典籍作品时,最大的挑战在于作品中的每个汉字和句子都具有多义性,同时中国的典籍作品大都看似无语法规律可循,又缺乏句读(Veith 2002: xviii)。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在文本(这里主要涉及语言特征)方面极具特质,这也是此类文本翻译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文本诠释学的角度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此类文本在翻译与诠释时的问题、制约因素等,以便制定出适恰的翻译方法和诠释策略。
3.2 修辞性
修辞是语言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英文是rhetoric,源于希腊语rhētōr,意为“说话者、言说者”。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定义为“在任何情况下,能够找到可以用来说服方法的能力”(Aristotle 2007:37),这种能力不同于辨证逻辑能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修辞的核心在于说服读者/听众。由此可知,修辞是用来说服、劝说听众的能力,此种能力有别于逻辑论证。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关于“修辞”的解释是,“说话或写作的艺术,以说服或影响他人为目的”(Mayor 2010:1500)。由以上考察可知,修辞是语言的重要特征,是考察文本的主要参数之一。
传统观点认为,科技文本的语言修辞性不强,因此,有关该类文本修辞性的研究较少。但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科学哲学的修辞学转向、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科学哲学的诠释学转向,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科学、技术文本的修辞特征。“20世纪后期,不少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开始科学修辞学的研究,有的从自然科学案例入手,分析科学史上一些重大理论发现背后存在的修辞学思想;有的基于科学哲学的传统问题,寻求修辞学与科学推理、理论选择和逻辑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李小博 朱丽君 2006:76) 这种研究主要源于以下事实,即科学研究的过程、方法和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是修辞性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实践中语言符号的选择只有通过修辞学才能解释,科学研究活动是一个修辞性交往的过程。(同上)
其实,修辞表达并非是文学作品的专利,科技文本也使用多种不同的修辞手段,以实现作者表达和论证的目的。艾·阿·瑞恰慈(I. A. Ri-chards)指出,“我们不用读完三句普通的流利的语句就会碰上一个隐喻。……即使在已经公认的严谨的科学语言之中,如果不花大力气也不能把它排除掉或防止使用它”(1936:92)。以隐喻为例,“隐喻存在于所有类型的语言中,绝非文学语言所独有,在科学、技术、商业、金融、法律等诸多领域都是隐喻丛生。……因为,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思维现象”(叶子南2013:21-22)。从认知隐喻的角度看,隐喻的基础不仅是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且还有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体悟所形成的相似性。最重要的是,修辞是语言的天性,“从远古到现代,从诗学、文学到哲学、文化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运用隐喻的方法,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科学理论陈述中一些重要的核心概念往往都是隐喻性的,而且这些隐喻概念被科学家作为新的科学事实和概念前瞻性发现的重要工具使用”(郭贵春 2007:4-8)。因此,20世纪产生一门学科——科学修辞学,其目的在于通过对科学研究对象及过程的哲学性修辞分析,揭示科学理论实体和知识形态的修辞学特征,阐明科学论述和文本的实质性内涵,从而表明科学解释的价值和科学修辞的意义。(同上: 105)如果将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修辞性特征剥离出去,则会造成诠释的片面性。
同现代科技文本语言相比,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的语言修辞性更强。例如,《黄帝内经》经常采用多种修辞方式阐述医学思想和治疗方法,该书“除现今较为流行的比喻、比拟、借代、对偶等方法外,还广泛使用诸如联珠、辟复、互文、讳饰等卓异修辞之法”(孙凤兰 2016:110)。《淮南子》语义深奥,并因为深受楚汉赋章法的影响,其文多用修辞之法。《墨子》一书虽然语言素朴,但是依然采用多种修辞方法进行说理。
首先,修辞与诠释具有同源性,它们都涉及语言的理解问题。瑞恰慈认为,“修辞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对误解及其纠正法的研究”(Richards 1936:3)。诠释学,尤其是一般诠释学,不只研究如何理解的问题,更关注如何实现正确的理解,尤其是避免错误的理解。其次,修辞性语言较之于一般语言更具有特殊性,原文作者借助不同的修辞手法使表达能够实现修辞的目的。鉴于这种语言的特殊性,该类文本需要读者和译者做出更多的诠释努力。“原作者创作时产生的一系列主观情感:审美心态、情感活动、灵感互动、感物起兴、心理意象,以及这一切产生的现实语境,除了有限的部分被书写固定下来,创作时的完整心境、当下心理现实及相当大部分的文化背景均已消失,只留下一个有待重新阐释的符号世界。作者与文本分离,译者解读时必须体认与弥合这种心理距离。”(龚光明 2012:62)最后,从广义修辞学的观点看,修辞几乎蕴含文本纹理的方方面面,因此,“对文本的解读其实就是诠释者在源文本施加的种种限制条件下产生出一个新文本的过程,亦即一个修辞过程”(刘亚猛 2006:27)。
4 翻译的诠释性
诠释学本身就具有理解、解释与翻译之意,而翻译须要先理解源作,再用译入语表达这种理解。所以,翻译本身就具有诠释性,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从诠释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现象可以极大地促进后者的发展。
首先,重新定义翻译——翻译即解释,朱健平因此将翻译定义为“翻译就是在跨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历史性的译者使自己的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互相发生融合形成新视域,并用浸润着目的语文化的语言符号将新视域重新固定下来形成新文本的过程”(朱健平 2006:70-71)。其次,就翻译策略而言,诠释学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提出的归化和异化策略对翻译研究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再次,就翻译过程而言,斯坦纳以诠释学为基础,提出翻译的4个诠释步骤,即信赖、侵略、吸收、补偿(Steiner 2001:312-316),这种极具原创性的观点凸显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理解与诠释的作用。诠释学对译作的批评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外,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也呈现出译者创造性的诠释。“翻译,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如果说,理解是对原文的接受,那么,解释就是对原文的一种阐发。在这个意义上,译者既是原文的接受者即读者,又是原文的阐释者即再创造者。”(谢天振 2011:209)翻译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作品是一种创造行为,体现译者的主观性。在论及古代数学的翻译时,弗洛里斯·科恩指出,“翻译并不只是传送。对于讲授自然知识的文本来说,翻译必须是一种非常主动的过程。……译者需要有很高的创造力”(2012:44)。
5 结束语
中国古代科技、相关典籍作品以及翻译的诠释属性等因素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诠释学理据。从诠释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可以为此类文本翻译的研究提供更为多元和科学的研究路径:既可以更为系统地描述和解释该类文本翻译的诠释方式,又能够为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研究提供更加科学的哲学理据;有益于推动相关出版发行机构及政府职能部门探究适合此类文本的传播方式;通过对比中外译者不同的诠释方式,探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在海外市场有效的传播途径。
注释
①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版《辞海》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