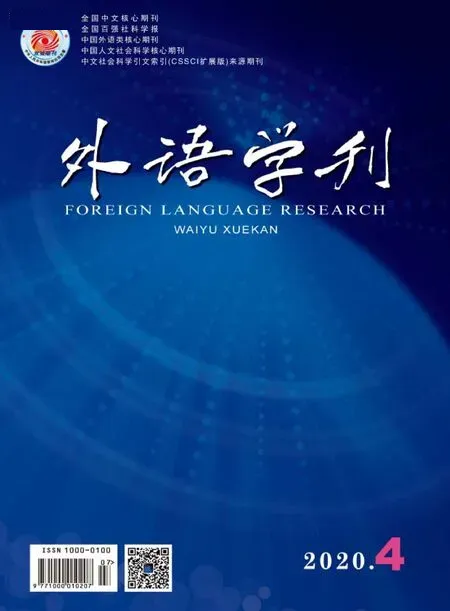《论语》英汉译“天”与“德”的缺席:中庸解“子以四教”*
蔡新乐
(深圳大学,深圳 518060)
提 要:“子以四教”一向被释为三教或二教,依文解经,造成此章解释的乱局;英文译文复因不解“文”字而形成语义重复,几不可读。只有遵循中庸之道,回归天人合一的宇宙论,才可明白,此章说的是:人依凭先贤之文献,吸纳天道之力,而打造内在之德,进而付诸于行动,一内一外,形成第一个阶段;复又回归内中,尽一己之心,形成更为强大的“忠”,进而走向诚实待人,再依礼义不断对自己加以社会化。此为第二个阶段,亦仍是一内一外。正合中庸的原理。圣人“则天”,对经文的释解即是要走向这样的“超越”:翻译的目的在于,使人向宇宙最为崇高的力量转化。
1 问题的提出
本文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为例,试图说明,若不以既定的系统思想来理解经文,译解会如何不通;若依之而行,便可趋向正解。以儒家思想方法论来释解儒家经典,不仅不与传统解经相合,也和依文解经的现代做法不相为谋,因而,其本身就是对以往的解经活动的挑战,更何况又要为跨文化的翻译寻找新的途径和思想工具,难度自然可知。但若不迎难而上,何以葆有最可珍贵的精神力量,并且使之传之久远!
2 今译及其解说的不通:不及儒家思想的再现
“四教”的传统疏解并不清楚,现代理解更是混乱。邢昺疏:“文谓先王之遗文;行谓德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中心无隐,谓之忠;人言不欺,谓之信”(何晏 邢昺 1999:93),“文行”包含“忠信”,并未将之区分开来。朱熹曰:“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朱熹 1983:99),其解仍是含混。故而,有论者认为:“这是孔子的教育的四个重点,是不能够分开的。如果说他是分科了,那就是笑话”(南怀瑾 2014:290)。
经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何晏 邢昺 1999:93)
译文1. 先生以四项教人。一是典籍遗文,二是道德行事,三和四是我心之忠与信。钱穆译(钱穆 2002:187)
译文2. 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生活的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杨伯峻译(杨伯峻 2002:83)
译文3. 孔子用四种内容来教育学生:文化技艺,礼义实践,待人忠诚,办事信实。孙钦善译(孙钦善 2009:87)
译文4. 孔子在四个方面教育学生:文献,行为,忠实,信任。李泽厚译(李泽厚 1998:187)
译文5. 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社会实践,对人忠诚,讲求诚信。杨逢彬译(杨逢彬 2016:140)
译文6. 孔子教学的四项重点:做事的能力、行为规范、忠于自己、言而有信。刘君祖译(刘君祖 2016:222)
译文7. 孔子采用四种教学内容:文献,践行,忠心,诚信。张其成译(张其成 2017:164)
译文8.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导弟子:学问、德行、忠心、诚信。杨朝明译(杨朝明 2013:127)
译文9.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导学生:学术,德行,忠诚,信义。何新译(何新 2007:88)
译文1分明将“四教”改为“三教”,其余译文看似保留了“四”,但因“文行”与“忠信”关系并未厘清,或已将之改为“二教”。
从以上译文来看,因依文解义,不关注义理,因而,一,今译中见不到“忠信”到底有什么区别。比如,译文7和8的“忠心”和“诚信”,似乎完全是同义词。译文5的“忠诚”和“诚信”,译文9的“忠诚”和“信义”几乎也都是同义反复。二,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译文并未表现出它们在“流转”中的区别。亦即,诸多译文根本没有关注这二者所昭示的是一种过程:忠是指尽一己之心,信则突出待人信实。一内一外,内外结合。“含章内映”(何晏 邢昺 1999:3),才可内在充盈,“忠心”已立,才能待人以“信”,二者里表如一,同时又自有分别,故可相互推移而彼此构成。这正是中庸的“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礼记·中庸》)(郑玄 孔颖达 1999:1450)原理的体现。译者显然少有体会,更遑论用于译解。三,既然“忠信”讲的是动态过程,那么,前二者亦必如此。这样,“文”主要也就不是指“文献”“文化典籍”“学问”或“学术”等,而是经由“文”的锤炼而使人得到升华的那种力量,美之名曰“德”。
若依之释义,则“文行”二者便可解为,“文”突出的是“文德”的培养,是人内在力量的集中、优化和强化,因而,作为起始步骤,它强调的是内在化的力量;“行”试图将如此培养出的“德”置于日常的具体行为之中,不断加以见习、检验和验证,进而使之具备指导实践的力量,人生亦变得更具规范性的意义。这也是一内一外的“阴阳推移”的体现。作为第一个阶段的“文行”,亦即夫子之教的起始,“德性”因之不断养成;进而将之导向具体的行为,发扬光大、不断增强力量。在第二个阶段,人则需重新回归,在“内省”或自我反顾中,体贴日常所习是否符合“文德”的基本要求,是否与“德行”的礼义要求相互呼应,此之谓“忠”;同时,在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与人交往、往还时,时刻以“信”为据,而不可须臾有违。
也就是说,“四教”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德”内化以及外显,第二阶段首先是内德的复归、自反自顾,进而又是外显,突出的是不忘初心的那种“信实”。一内一外,复又一内一外。如此循环往复,夫子或其高弟要突出的是,人的“内外合一”之道,就是这样,阴阳翻转,而得时化之宜。这意味着,“四教”不仅仅是“四教”,因为它不论在内涵还是形式表达上,都在突出一个思想导向:中庸可以调适上遂,将人引向一个最为美好的所在。在那里,人心与天道同化,而可真正赢得“天德”。
3 英译的不堪:天之缺席与德的不在
由于跨文化、跨语言的缘故,更因对经文不解,英译对经文的传布或只有字面意义,而最重要的元素却缺席:天并未蕴含其内,德亦不翼而飞。
译文10. There are four things which the Master taught, — letters, ethics, devotion of soul, and truthfulness. Legge译(Legge 2010:62)
此译意为,夫子教诲四种东西:文化、伦理学、心灵的奉献以及信实。在这4项中,letters可指“文化(学习)”,因而,必可容纳置于其后的“伦理学”;而且,这样的“伦理学”亦必与“心灵的奉献”以及“信实”密切相关。译文无视人需对自己加以自省和自顾,不明中庸之法导向人的自然化与其社会化的并行不悖,不通不可避免。
译文11. Confucius through his life and tea-ching taught only four things: a knowledge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conduct, conscientiousness and truthfulness.辜鸿铭译(辜鸿铭 1996:395)
此译特地强调,夫子毕其一生及其教育生涯,只传授4种东西:文学艺术知识、行为、良知及忠实。依此直译,其结果也一样不通:“行为”需要讲授或传授吗?抑或是,行为的规范需要传授,亦即,人视听言动所要遵守的礼义一定要传授,如此,才可成就君子?“文学艺术知识”完全是现代话语,以之取代“文”或只有外在化倾向,因而,也只是“文德内化”的一种手段(且是以现代为名?),而不是“文”的真正目的。舍重就轻,自不能使译文连贯一致,也就有了“行为”和“良知”与“忠实”之分,似乎后二者与“行为”无关,或者说,人的“行为”不要或不能体现这二者。译文如此不讲理,自然无法传译夫子之教的基本意向。
译文12. The Master took four subjects for his teaching: culture, conduct of affairs, loyalty to superiors and the keeping of promises. Waley译(Waley 1998:87)
依此译,“文化”与后3者分设,似互不联系,后3者也一样彼此无关。这也就意味着,“事务性的行为”,并不要求“对长者忠诚”“信守诺言”;不论3者如何联系,行为者自身皆无需自反、自顾和自省。这,还是在传译儒家思想吗?
译文13. The Master instructs under four heads: culture, moral conduct, doing one’s best and being trustworthy in what one says. 刘殿爵译(Lau 2008:117)
依此译,夫子讲授要在4个题目下进行:文化、道德行为、尽一己之力以及讲话要信实。同样的,依之,“文化”与后3者无关,“道德行为”等等,不属于这样的“文化”,亦即,文化不能统摄人的行为;而且,人的行为也和“尽心尽力”及“诺必行”无关。这样处理,的确不无丑化伟大的思想家之嫌。
译文14. The Master taught four disciplines: historical documents, social conduct, loyalty to superiors and faithfulness to friends. 林戊荪译(Lin 2010:127)
夫子讲授四种“学科”,discipline一词太过现代,或为夫子所不能预知。历史文献,不可能如译文所示,成为“文”的全部,而此“文”也不会与“行”(这里译为“社会活动”)无关,进而也不可能与“对长者尊者忠诚”以及“对朋友忠实”无关。和别的译文一样,行事者亦需反身自顾,在德性上不断提升。未见“文”的导向,“忠信”亦未再现。亦即,不明文辞背后的思想系统,译文避重就轻,最后只能使译文整个不通。
译文15. The Master taught under four categories: culture(wen文), proper conduct(xing行), doing one’s utmost(zhong忠), and making good on one’s word(xin信). Ames and Rosemont译(Ames, Rosemont 1998:116)
依此译,夫子要在4个范畴或范围下传授学问,但这里的“范畴”(category)也一样太过现代化。此译书名中有“哲学”一字,译者将其定位为“哲学”,但如此概念化的指向,并非儒家的特色。“文”仍以culture代之,亦是因为对之不解之故。但问题在于,这里一看不到儒家乃至中华文化培养人、造就人才的那种动态过程,是与大自然当中日月星辰的流转以及中国古人所创造的阴阳大化流行的那种宇宙论相互一致的;二读不出深深浸蕴于“文”的世界的古代中国学者是要不断打造文德的。而此德、此能之源头,既有先贤的文献的遗传,同时亦即为上天的赐予。二者合力,营造出的是一个秩序井然而又日月相推的世界,人之“德”得之于天,而内化于人。如此的内在性寄托着空前的力量,是人之为人最可珍视的灵性之源。这样的源,其外化之上及于天,内化之深蕴含于心的倾向,在译文15中,确亦不在场。
4 “文”的意义与“四教”之正义
中国古人确定不易的宇宙论即为“天人合一”。而偏偏这样“人人熟知”的思想,在解经史上几乎缺席,尽管这一思想,如钱穆所强调的,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未来可能的最大贡献。他认为,此观念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处”,“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在此”。其特色是:“把‘天’与‘人’配合着讲”;“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何处来证明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而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钱穆 1992:93)。孔子无疑是对此体会最深者:对他而言,“人生就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同上:94)。
很明显,因对“文”的要义未能理解,众多译文直接代之以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大多数的英译为culture. 则此一culture必定包含着后文所说的任何一项内容,包括行为、忠诚等,那么,大小不分、轻重无别,是否已成英译带给夫子的特别印记,而且,一定也会让读者感到,这位中国思想家头脑不甚清楚,连大小“概念”也分不清。更何况,如此重复,到底为的是什么?难道说,夫子之“教”其“名”已如此不堪,其“实”更加不可思议?如此对待经文,英译能通吗?而这意味着,反过来说,只有回到儒家思想系统,才可能真正把握夫子之教的真意,而不至于再如此荒诞下去。
我们认为,就《论语》本身而论,“文”作为“内德”或“德”的内在化打造,例子是很多的。比如,夫子本人对孔文子这一谥号的解释: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
“好学”的目的何在?当然是做人,后者的根本就在于内德的打造。如此,尽管卫国大夫孔圉为人并不好,但他的“好学”本身却值得称道。因而,“文”之“德”的意向极其明显。再进一步推敲,夫子对尧的赞美,所用的“文”字亦是“德”的意思: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成功”说的是政治、文化方面的贡献,亦即事功,可见于外,故而“巍巍”;“文章”突出当是“德”,自内“焕发”出来。二者或有不同,后者才是夫子要特地强调的。
在先秦文献中,“文”之“德”意十分清楚。如《尚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孔传:“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国语·周语下》:“夫敬,文之恭也。”韦昭注:“文者,德之总名也”(《汉语大字典》编委会 1993:909)。又如,郑玄也在《周礼注疏》中注曰:“文,犹美也,善也”(郑玄 贾公彦 1990:209)。《荀子·不苟篇》中“夫是之谓至文”的“至文”意即“最高的道德”。另如,《诗经·周颂·清庙》有云:“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毛诗正义》:“执文德之人也。执行文王之德,谓被文王之化,执而行之,不使失坠也。王既是有德,多士令犹行之,是与之相配也”(毛亨等 1999:1282)。
《论语·卫灵公》中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有能力将“道”内含于中,使之形成一种空前的力量,进而再向外投射出去,用之于人际交往、立身行事乃至对万事万物的认识,以及别的事务之中。这样的能力一言以蔽之即为“德”。
实际上,“文”之“德”意早已深入人心,因此,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以回文手段写道:“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相济,而后王业成”。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像第十四》中“文德”也是互用:“故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汉代易家荀爽发挥《象传》“君子以同为异”指出:“大归虽同,小事当异,百官殊职,四民异业,文武并用,威德相反,共归于治,故曰‘君子以同为异’也”(李鼎祚 1984:4)。其中“文德”的用法亦复如是。反之,若不修文德,则会像贾宝玉那样:“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红楼梦》第三回《西江月》之一)。
国人对“文德”的重视,起自一种信念。故而,杜维明论儒家的影响指出:儒家的传统则靠百姓日用间的一种关联,这是它在开始的时候就有的信仰,对人的自我转化、自我超升、自我实现的信仰。(杜维明 2013a:20)
显而易见,这样的信念是要向内伸展,进而成就其自身的。易言之,人就是要靠这样的信念,成就立身行事的根本。正是因为“文德”的至关紧要,杜维明强调,“新儒家”才会不计一切为之不懈努力:新儒家们忧虑的是心灵的生命,这种心灵生命的缺失和价值取向的误导,表面上治疗心灵的创伤和调整价值观念的迷惑并非当务之急,即使全力以赴也未必有效,何况有此自觉的少数哲人也因为深受穷困、分裂和解构的痛苦而大有屈辱和悲愤的情绪,维持内心的平静已是非常困难,甚至要有超凡的定夺;在自家分内的日常生活都无法安顿的乱世竟然奋身而起,为民族千百年的心灵再造之大计而思考,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非常大的智慧的。(同上 2013b:33-34)
作为精神世界的基本支撑,“文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刘述先也强调:毫无疑问,中国的传统有丰富的伦理资源。特别在伦理方面,尤其是儒家的传统,是有十分丰富资源的。……儒家伦理绝不可以化约成为封建时代某种阶级的伦理,孔子最大的开创在于体证到“仁”在自己生命里内在的根源,故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论语·颜渊》),这是他对于所继承的传统的深化。孟子又进一步继承孔子的思想,与告子力辩“仁义内在”的问题。如今连西方学者如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也十分明白儒家精神传统的精粹在于“为己之学”,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内部找到价值的泉源。(刘述先 2010:382)
以“内外合一”的中庸来作解,便可认为,一,“文”指人“文—化”自身,亦即,人以灿烂的文化典籍来进行修身的活动;二,“行”则指依道德要求而行于世的行动;三,“忠”总结上两项,强调不论是“文”的内在完善,还是“行”的外在倾向,都应“忠实于自身”——邢昺疏:“忠,谓尽中心也”(何晏 邢昺 1999:53);四,“信”和“忠”一样,也是对“文”之“文化自身”和“行”之“行己有耻”(《论语·子路》)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的归纳:对待他人,理应不轻然诺、言之有信、信守承诺。依此,可出新译:
译文16. 夫子在四个方面教育学生:文以修身,行己有耻,忠己之心,及信实于人之心意。
译文17. The Master taught his students in the following four orientations: cultivating their heart and guiding their behavior in light of the moral principles, and(in turn,)being-true-to-heart and kee-ping-to-the-word.
如此译解或可与中庸之道保持一致:以“文以修身(心)”来说“文”,可显现“文”的内化作用或精神力量;用“行己有耻”来论“行”,能突出人生在世,每一个人都应怀抱特别使命,不忘自身的追求或责任,勤勉而又知耻,必以道德原则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这两方面,一主内,一向外;彼此对应,显现的都是“教化”的力量。后两个方面则凸显的是,不论内蕴还是外化,都应表现在对己对人两个方面:一对己忠,二对人信。二者不可或缺,形成另一个“对子”:内外俱在,相互配合。
因此,夫子提倡“教化”的要求:张扬“文”对于后来者的“内化”力量,即使之成为“后觉者”的精神蕴含;进而,充盈内中的精神,其外化便可形成一代代人灿烂的“文”明成果。因而,这样的“文”作为教育的起始的一面,即“德”,要突出的就是如何在后来者那里发挥出先天的力量,以便接纳、体味、消化并且发扬有关传统,最终形成强大的精神动能,并且在“行”的过程中显现出来。如此,“文”与“行”一重“内德”之养成,一偏“外显”之功用。不过,“行”也需坚守一定的规则和规矩,最重要的当是“孝悌”等道德原理。人生在世,当以天下为己任,志存高远;行己有耻,也就成为士子的不二法则。
再进一步,“忠”说的是人自身:对己要“忠”;不论成败毁誉,都不可忘掉“诚心实意”而坚守自己的追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是待人以“信”。依上文之解,“信”不仅是指信实于人,且还应信守语言本身——那是家园之所在,亦即“文”的精神传统之所寄。而这意味着,从“文”到“行”到“忠”到“信”,“文”或“德教”的力量贯穿始终,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整体性的过程,最终突出的是“文”对“语言”的坚守的强大力量。
之所以说译解遵循的是中庸之道,是因为,这一译解将“文行忠信”分为两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在突出内外一致、表里如一。第一阶段“文行”如此,第二阶段“忠信”更是这样。夫子强调,“内外”的交合和互动,形成不断展开的动态,引出“文教”(德教)的“修身”作用在不停延展和强化:“文”有以致之,可将内转化为外,外再引入内;在内外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人走向社会所应坚守的“信”,并依之造就一个“和谐”的世界。一个过程的结束,最后的落实,是“信守语言”的力量的显现,已将“文”的阶段成果体现出来:从内在(“文”)走向外在(“行”),然后再一次回到内在(“忠”),最终回到外显的力量(“信”)。内外不断交合,内蕴的力量之“德”不停加大、增强。“教化”对人的思想的促进,或者说,它所形塑的人,其力量的体现,其本身不就是这样的“生生不息”?从“文”到“行”,再到“忠”与“信”,然后过程再次开始,形成新的动态:夫子要突出的,不就是这样的生意盎然的“文”的力量吗?
5 结束语
只有回到中庸之道,才可触及“四教”之要义,回归“夫子之教”的伟岸和平易。还应指出,英译所突出的“坚守语言”的“信”字,或可印证“文”的不断内涵和内化的空前力量。但有关讨论以及译文,只是初步的、探索性的。王阳明强调: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物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王阳明 2012:252)
羲皇即伏羲氏,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因其在中华文明史的巨大贡献,被尊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受到中华儿女的共同敬仰。阳明先生要我们做个“羲皇已上人”,意为何为?
这里的论述描述了两种时间——宇宙或自然时间及历史时间。依之,我们主要生存在宇宙时间,亦即,万古如斯的循环之中,但需要做的是以切实的态度和精神面貌,保持“坦然平怀”的心境,进而趋近“羲皇已上人”之境。易言之,阳明先生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走向“成人”最高境:“圣人”。诗人毛泽东有云“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送瘟神》),此之谓也。与这里的讨论的议题相结合,就会明白:
一,阳明先生所主张的,亦即儒家理想的做人境界。如孟子所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孟子·腾文公上》)。故而,“孟子道尧舜,言必称尧舜”(同上)。亦即,一切的事务都是要走向一种人生理想。其中应包括翻译活动。那也是一种修身的活动,也就是“修己”以与古人相往还的体现:如何将古人之心意透过一己之努力,形成“新”的精神力量,那才是“译解”所要做到的。翻译亦即为纯化意识、打造自我的过程。此亦可解为“学”,“明善而复其初也”(朱熹语)。二,这样的铸造实质上就是走向他人、他者、异于我的伟大生命力量,总是高于我的生命力量。因而,“我”不是在翻译别的什么,而是首先在翻译“我自己”:将之译入他者的思想之中,使之在他者的教导之下,尽可能趋向人格上的完美。翻译最为重要的当是自我翻译,是精神翻译或曰思想翻译。三,切不可忘记“简易之道”(《易·系辞上》:“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阳明先生强调,那是人类生存的“背景”“基础”或曰“实质”。一切都是在它的“衬托”“承载”和“支撑”之下展开,没有它就不可能有这个宇宙,也就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归入其中,才会有“羲皇世界”。回归其中,也才可能有翻译。因此,四,有必要诵读阳明先生的另一段话,并以此作结: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木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王阳明 2012:251)
如此,翻译的最高要求,就是要向着宇宙最为崇高的力量转化。故而,古人所推崇的“天”,又如何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