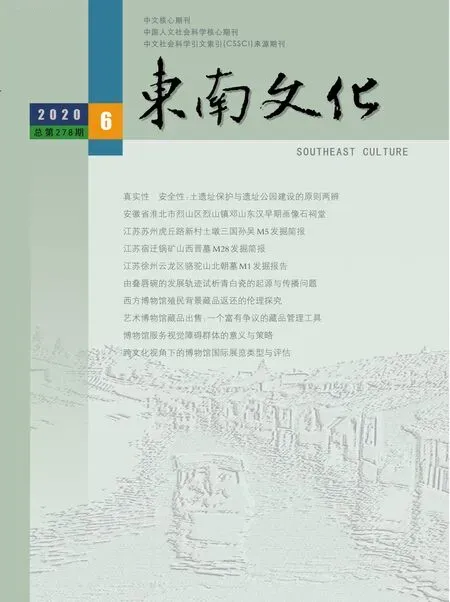建构异域与重构个体:人类学视域中的博物馆与观众
潘 宝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 云南大理 671003)
内容提要:博物馆通过器物表征型塑了自身在现代性社会空间中的异域性,进而影响了观众对器物和博物馆的认知。作为异域而存在的博物馆,既彰显了博物馆对器物的占有与控制,又满足了观众对差异文化的感官体验与文化需求。在器物的展览过程中,博物馆试图通过建构异域来影响现代性社会中“物”与“人”,进而影响个体在现代性社会中的身份与地位。博物馆建构异域的过程也是重构个体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回归至“人”的层面上,而非处于“物”与“人”的二元对立中。
一、作为异域而存在的博物馆
(一)博物馆的现代性与异域性
博物馆之所以能够作为异域而存在,既源于博物馆通过器物所表征的文化形态,又源于博物馆这一空间为观众提供了通过感官体验文化表征的场域,也源于博物馆所处的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社会既是在资本经济的逻辑中表达普遍性的社会,又是在人性价值的伦理中表达差异性的社会。资本经济的逻辑促使人们对“物”绝对占有,人性价值的伦理则促使人们反思“人”的本质。博物馆空间之所以能够存在于现代性社会中,就在于人们试图通过对“物”的占有来影响“人”的行为与意识。
特别是随着公共博物馆的出现,博物馆中的“物”与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近,博物馆在表征器物的同时也在表征观众,更在表征博物馆自身。但距离的拉近并不意味着博物馆空间的异域性在逐渐消逝,恰恰相反,在现代性社会的影响之下,使博物馆作为异域而存在的力量正在增强。“物”的生命史因为博物馆的存在而发生着改变。那些被视为珍宝与精品的物品,在博物馆的作用下,成为公共博物馆空间中的展品,从而满足了观众的非物质性需求,并通过展品表征彰显了观众的文化权力;那些过去属于某一个体或群体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考古学、美学、人类学等视野的影响下,成为博物馆空间中的展品,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和现代审美标准之下的艺术品,更成为型塑文化的表征。
在博物馆的相关研究中,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认为人类学和现代艺术必须将收藏看作西方主体性的重要历史形式;人类学和现代艺术都是通过占有而被发明的——占有意味着“使其成为自己的”,源于拉丁语proprius,表示“正当的”“所有物”。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语义中,博物馆搜集异域的物品(exotic objects)使它们成为博物馆的物品,并将众多他者的、破碎的物品编织进正当的、无缝链接的人类整体当中。正如历史主义把过去不一致的事件收集并排列而称为历史一样,博物馆从其他地方占有了碎片化的物品并重新组合,使它们看起来更像是人(man)的叙事一样”[1]。这也就说明,博物馆不仅收藏“物”而且占有“物”,并赋予“物”新的意义。而那些已经失去生命的“物”,对于大众来说,是陌生的“物”、差异的“物”,是拥有强烈的、吸引感官体验的“物”,是表征历史与追溯群体记忆的“物”,是寄托个体与群体怀旧情结的“物”,是迥异于资本经济逻辑中的“物”。这样的“物”对于生活于现代性社会的个体来说充满着想象的张力,与个体所生活的现实环境中的“物”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与其说博物馆通过展品建构展览空间,不如说现代性社会赋予博物馆一种作用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博物馆通过对“物”的各种不同层面的作用,而将博物馆自身塑造为一种“异域”。这种作用机制就在于通过博物馆为现代性社会的大众建构了一种可以通过感官体验的“异域”。
这种异域的建构既通过博物馆建筑格局营造迥异的建筑风格,从而将自身区别于其他建筑;又通过博物馆策展表征不同的文化形态,从而将部分大众型塑为博物馆观众。因此,博物馆所建构的异域不仅仅是通过策划展览或者观众参观就能实现的,这种异域既有来自于现代性社会对博物馆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又有博物馆对现代性社会的反作用所带来的影响。史蒂芬·拉文(Steven D.Lavine)和伊万·卡普(Ivan Karp)曾指出,“我们需要在展览的设计上试着展现多种视角,或者允许提供一个高度或然性的解释(interpretations)。这将是一个挑战:人们被博物馆的权威吸引,如果权威受到质疑,观众可能失去兴趣”[2]。这就表明,现代性社会将博物馆置于改变“物”的生命史的过程中,而博物馆则将现代性社会置于“物”的批判与反思过程中。现代性社会的逻辑在于通过“物”控制“人”,而博物馆的逻辑在于通过“人”作用于“物”。或者说,博物馆的作用机制在于试图通过“物”的力量改变现代性社会中“人”对“物”的绝对占有,并通过“物”反思“人”对“物”的影响,从而试图将“人”回归于人性的层面,而非仅仅只停留在物性的层面。
(二)博物馆建构异域的方式
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博物馆所展览的“物”已经脱离了观众日常生活的视野,而观众进入博物馆参观在时间上亦是有限的,即观众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是无法与博物馆中“物”的生命历程相比较的,由此,也使得博物馆通过空间与时间的作用来建构异域成为可能。在空间的层面上,博物馆的建筑风格和展览布局使得博物馆区别于现代性社会中的其他建筑与空间,而博物馆空间意义的彰显需要由观众的参观行为来完成,即博物馆为生活于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提供了可以想象的“异域”,这样的异域是由博物馆的建筑风格和展品共同建构的。观众进入博物馆意味着个体身份的转变,这种转变恰恰就是博物馆空间作用的结果。在时间层面上,博物馆延长了“物”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生命长度,且这种延长又是个体生命历程所无法比拟的。个体转变为观众时,其参观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与其日常生活的时间又是无法比拟的,“物”的时间差与“人”的时间差亦共同建构了博物馆这一异域。因此,博物馆所建构的异域既不是远距离与异文化的异域,也不是东方学与人类学建构“他者”视野中的异域,而是空间与时间双重的异域,是与大众如此近距离的“异域”,这样的异域恰恰就存在于个体所生活的城市或乡村之中。
在空间与时间的共同作用下,博物馆的建筑风格与策展方式越来越具有现代性,展品越来越具有异域性,观众越来越具有旅游者与消费者等多重身份,甚至当博物馆与城市和乡村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博物馆空间作用的范围在扩大,博物馆与大众之间的界限似乎亦在消失。例如,户外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的相继出现也在表明,作为异域的博物馆不仅仅是博物馆自身发展的结果,亦是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物”与“人”互动与沟通的结果,也是博物馆发展的一种后现代性。通过建构异域,博物馆正在试图改变人类社会现有的生活方式中对“物”的过度追求与控制,正在试图转变人类社会现有生活方式中那些脱离人性的因素。
二、博物馆异域建构过程中的器物与观众
(一)表征文化的器物
对于生活于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来说,博物馆具有异域性,而博物馆异域的建构不仅使得物品转变为展品,亦使得个体转变为观众。博物馆的器物可能已经成为表征历史与记忆、文化与传统、观众文化权力与休闲权力以及博物馆空间异域性的器物。虽然西方曾经通过建构人类学博物馆或民族学博物馆来表征作为异域的非西方文化,但这种建构方式也曾经或正在被非西方用来建构自己的人类学博物馆或民族学博物馆。博物馆异域建构的过程赋予了器物被现代性社会利用的新方式与新手段。
围绕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器物,在博物馆这样的空间中,现代性社会中的人们可以对其进行收藏、研究、保护、展示,博物馆展览成为器物与观众之间沟通与交流的媒介。而正是由于此过程越来越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如策展人(cu⁃rator)的出现,或者说现代性社会在劳动分工层面上的影响,使得人们对器物的收藏、研究、保护与展示越来越专业化,观众无法在短暂的参观过程中完全理解器物转变为展品的过程。这也进一步使得博物馆在建构异域的过程中越来越走向专业化的策展道路,展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并不一定比器物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更近。对于观众来说,博物馆更多的是感官体验的对象。因此,博物馆异域的建构并非只针对器物,不能说博物馆仅仅是为了器物而存在,恰恰相反,博物馆异域建构的主要对象是大众——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有可能转变为博物馆的观众。
如果说博物馆异域建构过程中的器物是观众的器物,那么,这种器物就是博物馆建构的产物,器物的存在与观众的存在发生关联。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博物馆的展览就没有副作用,玛丽·布凯(Mary Bouquet)在用人类学理论研究博物馆展览时指出,“通过人类学的分析,灵活使用现时的资料以便获得概化展览(conceptualise an exhi⁃bition)的动力。展览不仅仅是约定俗成地使观众看到这里或者那里的人们及其文化的民族志知识(ethnographic knowledge);展览也有可能被描述成表征‘那里’或者‘异域’的文化,这是民族志视野局限性的一种结果。夸大的能力甚至把陈列中熟悉的器物用一种陌生化(defamiliarise)的方式去设计,这有可能打通一条通往理解所有不同器物的道路:在这些展品中通过‘美学’的分类方法,达到所谓‘科学’的目的”[3]。因此,是博物馆赋予了器物在展览中的意义,而非相反。博物馆作为观众与器物沟通和交流的媒介,同时,博物馆亦在观众与器物之间创造了新的空间距离。这种距离既有观众参观过程中身体控制的物理距离,亦有为观众创造一种可以想象的心理距离。不可否认的是,观众在进入博物馆之前,博物馆的器物在空间与时间上与大众都存在距离,这种距离产生了陌生感,器物对于大众来说充满着想象的张力。
器物在策展手段的作用下,成为观众感官体验的对象,而观众的这种感官体验又使得博物馆建构异域的手段被赋予现代性属性。博物馆异域的建构要通过器物与观众共同作用才能完成,博物馆并非只为器物建构了新的文化生境,也为观众建构了新的生活方式。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andler)在论述博物馆人类学与文化理论的关系时认为,“从作为特立独行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中的神秘问题,到现在成为文化理论至关重要的部分,博物馆中的人类学已经从众多学科的边缘回到了中心,并及时质疑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的有关理论。人类学者倾向于将文化重新理论化,以此来将博物馆作为日常知识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中心场所,也将博物馆作为民族主义的文化理论(nationalistic culture theory)制度化的中心场所。博物馆当然是文化财产的所有者,它同时也是利用(using)文化财产表征(re⁃present)文化认同的机构”[4]。这也就意味着,博物馆能够在文化理论的研究中成为建构者,亦在试图赋予个体新的社会身份。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民族—国家(nation-state),特别是公共博物馆的出现,博物馆在塑造新的国家形象与新的公民身份上亦能够发挥作用。因此,博物馆的现代性就体现在器物对观众的影响层面上,只有当博物馆能够以迥异于学校等其他机构的形式来生产知识、为观众建构感官体验对象、改变公众现有生活方式时,博物馆才能够持续不断地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入博物馆参观,而这种吸引的前提条件就在于博物馆需要通过建构异域来满足观众未进入博物馆之前的各种想象。
(二)观众身份的转化
在建构异域的过程中,博物馆既通过器物生产知识型塑博物馆的话语权力,又通过观众的参观行为型塑博物馆的社会身份。在器物知识的生产过程中,观众通过参观行为认知器物,器物是博物馆空间中的器物,观众是博物馆空间中的观众。当且仅当观众进入博物馆参观时,器物才能够与观众共存于博物馆同一时空中,产生直接的“物”与“人”层面上的沟通与交流,“物”的生命史也才能因为“人”而发生改变。弗朗西斯·李欧妮(Françoise Lionnet)曾指出,“博物馆可以帮助我们讲述那些不能够讲述的故事,但是博物馆有可能在诗学想象(poetic images)的作用下,使我们进入与那些展品的主体进行生产性对话的空间中,这样的空间具有强烈的他异性(alterity)”[5]。也就是说,博物馆在观众与展品之间建构了一种可以沟通与交流的机制,但这种沟通与交流并不意味着观众一定能够理解展品,而是在观众与博物馆之间创造了一种诗学的想象。
博物馆异域建构过程中的器物,已经不再只是被赋予神圣性的器物,或者只是被保护与被研究的器物。尤其是当观众在场时,器物是激发观众想象、增强观众感官体验和重塑个体生活方式的器物。而博物馆异域建构过程中的观众,已经不再仅仅是被动接受博物馆教育的观众,也不再只是一味认同博物馆的话语权威,尤其是当器物被观众凝视(gaze)时,观众是接受与理解器物表征的观众。在面对观众时,博物馆应反思自身的服务意识是否真正从“物”的层面转移至“人”的层面,是否仍旧只将博物馆这一“我者”对器物的收藏、保护与研究的认识,强加于观众这一“他者”对器物的参观过程中。在个体转变为观众时,其现代性的个体社会身份已经被重构了。
三、博物馆观众的参观行为与个体社会身份的重构
(一)以“人”为中心的博物馆
博物馆异域的建构并不只是“物”的意涵表征,也不只是器物与展品的共同作用,同样也需要观众的参观行为来实现,亦需要在“人”的层面上重构个体的社会身份。若仅停留于观众应该如何参观博物馆的层面上,一旦出现失序的参观行为时,博物馆有可能视其为不文明行为等;而当观众未按照博物馆所期望的方式理解与解释展品时,观众及其参观行为往往成为博物馆所批判的对象。诸如观众不尊重器物、观众审美水平有待提高等话语的产生有可能是博物馆以“物”为中心的结果。因此,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并非局限于博物馆内部空间,也应当延伸至博物馆外部空间。观众需要的是作为观众的个体与作为展品的器物两者相遇时在感官与心理层面上的平等沟通与自由交流,而非博物馆以类似说教的方式告知观众应该如何参观、如何理解展品,也非博物馆以秩序构建者自居去批判观众参观的不文明等行为。因为在面对观众时,博物馆及其展览并非完全处于客观立场,苏珊·克兰(Susan A.Crane)认为,博物馆通过展览再现历史与激起记忆时,可能会出现“扭曲”,“博物馆里的扭曲必然涉及不恰当的事实,或者是意识形态化的解释(ideologized interpretations)”[6]。这也就意味着,博物馆展览与观众的参观过程之间并非对称的关系,而有可能出现偏差,偏差的原因就在于博物馆可能无法满足观众更多的需求。
但观众这一身份并不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被动选择,而是对其社会身份重构的一种主动适应。也就是说,博物馆与器物、观众以及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博物馆伦理(museum ethics),正如兰迪·马赛勒斯(Randi Marselis)所指出的,“为了和众多的观众卓有成效地讨论博物馆伦理,博物馆必须意识到,在特定的国家语境中,全球性的话语、博物馆学的话语都可能被观众接触到,因此,博物馆亦面临着挑战”[7]。即观众不都以博物馆所期望的姿态参观博物馆,观众以个体的方式通过感官体验展览、凝视器物,以自我的认知理解展品,博物馆试图主导观众的参观行为似乎在个体转变为观众的过程中并不明显。当博物馆更加注重观众的参与过程时,说明博物馆亦在重构观众个体的社会身份。
观众以其主动的参观行为彰显自我在博物馆空间中的能动性。观众以自我的方式在不同展厅之间游走,自主决定在每一件展品前停留的时间,当观众通过展品说明牌或讲解员的讲解进一步了解器物时,观众似乎不认可自身在接受博物馆的教育,而是试图在博物馆异域中寻找差异化的知识生产方式。博物馆为观众建构了异域,而观众亦通过参观博物馆重构了个体的社会身份。这种重构,一方面是基于个体社会身份的转变,即由个体转变为观众的过程中,个体将自身与非观众身份相区别、将非工作状态与工作状态相区别,体验博物馆的展览即是在彰显自我的人性价值;另一方面,重构则通过博物馆的自反性(re⁃flexivity),以“物”的形式影响了观众对自我生活方式的认知,诸如产生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等意识、试图理解与解释展品所表达的艺术气息、接收并认可博物馆所生产与传播的知识信息,从而在参观过程中反思“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重新认识博物馆在现代性社会中的作用与意义。
(二)重构个体过程中的观众
不可否认的是,观众的年龄阶段、受教育水平和对器物知识的了解程度,博物馆的类型及其对待观众的态度等,均会影响观众的参观行为,但却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生活于现代性社会中的每一个体。博物馆观众的参观行为与个体社会身份的重构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博物馆不能只将视野局限于观众的参观过程中,更应该扩展于博物馆外部空间,关注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如何转变为博物馆观众;而个体社会身份的重构相对于观众的身份来说,并非只是特例。卡罗尔·邓肯(Carol Duncan)认为,“博物馆可以成为强大的定义身份(identity-defining)的工具,控制了博物馆恰恰也意味着控制了共同体(community)的表征以及最具权威的真理;也意味着拥有了确认并区隔群体的权力,通过这样的权力,博物馆在共同体的共同遗产上能够宣称一些群体比另一些群体拥有的更多”[8]。同样的,无论是观众还是器物,博物馆都能够通过自身对两者产生作用,博物馆可以通过器物建构异域,亦能够通过观众重构个体。这种重构并不是彻底改变资本经济的逻辑对个体所造成的副作用,而是在关注个体人性价值伦理的过程中反思个体多种社会身份重构的可能性。个体参观博物馆的过程是博物馆发挥“物”的作用的过程,是博物馆试图将“物”的分类方法与知识潜移默化于观众感知结构的过程,进而博物馆试图影响观众对现代性社会空间秩序的认知。
博物馆通过建构异域使观众的参观行为成为个体社会身份重构的方式之一,而个体社会身份的重构亦为博物馆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的方式。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在博物馆中参观时,并不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名受教育者。那些大多处于非工作状态的观众可能更期望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体验不同的“异域”文化和由器物所生产的文化产品、购买博物馆商店纪念品、参与博物馆所设计的互动项目,将博物馆空间建构为其个体甚至家庭的休闲空间。从这样的角度理解观众,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就不再只是以参观“物”为主体的观众,而是以“人”的活动为主体的观众,且这样的观众影响和改变了博物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了博物馆的分类方法与策展手段,亦使得博物馆不再只从“物”的角度思考器物和观众,而更多从“人”的角度思考器物与展览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观众、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