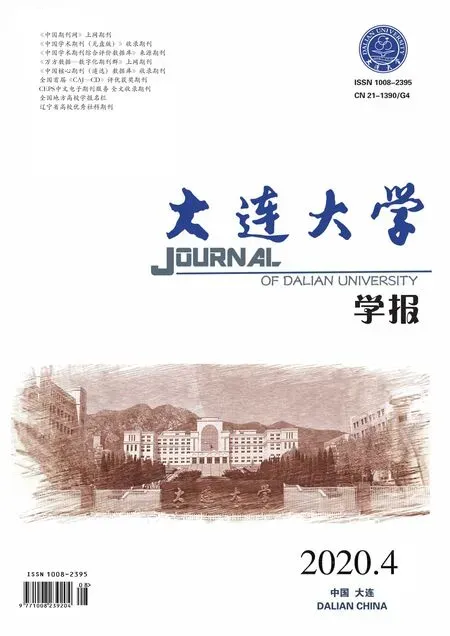董国英的里籍和《楚辞贯》的特点
陈 欣,刘佳富
(1.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550018;2.贵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550018)
董国英《楚辞贯》是一部值得注意的清代楚辞注本,《清史稿艺文志》《清续文献通考》《八千卷楼书目》等著录。然而,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董国英的里籍,各种楚辞书目和提要类著作始终莫衷一是。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董国英的里籍和生卒年、《楚辞贯》的体例和成书过程,以及董国英的楚辞观和方法论作进一步的探究,以期能够推进楚辞学的纵深研究。
一、董国英里籍生卒年考
关于董国英的里籍,《楚辞书录》《楚辞书目五种》《楚辞著作提要》《五百种楚辞著作提要》《楚辞文献丛考》等莫衷一是,有的说他是山东人,有的说他是浙江人,还有说他是朝鲜人的。饶宗颐《楚辞书录》:“《楚辞贯》一卷,博川董国英撰。”[1]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国英,字逸伦,博川人,诸生。”[2]潘啸龙、毛庆《楚辞著作提要》:“董国英,字逸伦,昌化(今浙江省临安县)博川人。”[3]206周建忠《五百种楚辞著作提要》:“董国英,字逸伦,博川(今属山东)人。”[4]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楚辞贯》者,朝鲜董国英所作也。国英字逸伦,自称籍于‘唐昌’‘博川’,皆朝鲜之古地名也,在今朝鲜平安北道之西南部。”[5]1945造成其里籍莫衷一是的原因,主要是《楚辞贯》中董国英自称籍于“唐昌”和“博川”这两个地名引起了后人许多误解。“唐昌”实际上是浙江省昌化县的古称之一,即现在的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乾隆《昌化县志》卷首《序》云:“唐昌为杭郡属邑,地虽僻左,而襟溪带岭,实为江浙之门户。”[6]古代的文人墨客还将昌化最秀丽的山水美景归纳为“唐昌十景”。其实,《楚辞贯》卷首两篇《序》都已经说得很明确了,罗以智《序》中说:“先生名国英,昌化博川人”;余莲《序》云“吾昌逸伦先生《楚辞贯》”[7]。此“昌”即昌化县。
笔者进一步查考道光《昌化县志》和民国《昌化县志》,证实董国英确实是浙江省杭州府昌化县人。对于董国英和《楚辞贯》,这两种地方志均记载甚少。道光《昌化县志》卷十七艺文志书目著录:“《离骚贯》一卷,诸生董国英注。”[8]民国《昌化县志》中的记载与道光《昌化县志》完全一致,载于卷十八“书目集部”中。可惜的是,这两种地方志仅能确定董国英的里籍,从中未能找到更多有关董国英的生平资料。或许因为董国英以诸生终老,未曾出仕,其生平著作湮没不传。
据《楚辞贯》之《离骚》卷首可知,董国英之甥孙程章和程锦,以及曾孙董希仲皆参与校刊此书,其中可略考者仅程章和董希仲。据民国《昌化县志》卷九选举贡生中“五贡一览表”记载,程章为咸丰辛亥科恩贡[9]542。咸丰辛亥为咸丰元年(1851)。民国《昌化县志》卷十四人物忠义“新增殉难忠义”中“绅士表上”列有程章一条:“程章,字云如,号汉槎,清恩贡。咸丰庚申闰三月初二日,粤匪至,督团御敌于八都之董岭,不支,他人有遁去者。章率子会九、会盛、会勋、会松及姪,抵死不退,同时阵亡。邑令袁申详请,奉旨入忠义祠,赐袭云骑尉,见《忠义录》。”[9]980据此可知,程章于咸丰十年(1860)率众子姪英勇抵抗太平军,不幸罹难。另,在民国《昌化县志》卷十四人物忠义“新增殉难忠义”中“绅士表下”,董国英之曾孙董希仲,出现在“第七次案浙江巡抚奏卹”的名单中,云“生员董希仲”,据此可知,董希仲亦于此时罹难。
据《楚辞贯》卷首董国英《凡例》识语和罗以智《序》,可大致推算出董国英的生卒年。董国英《凡例》“识语”云:“嘉庆五年,岁在庚申腊月之吉,博川董国英识,时年七十有二。”[7]罗以智《序》云:“先生名国英,昌化博川人,善诗文,惜以诸生终老,今殁且三十余载。著是书时,嘉庆庚申之岁。余甫生,先生年已七十有二矣。”[7]嘉庆庚申,即嘉庆五年(1800),此年董国英七十二岁,推其生年当为雍正七年(1729)。此《序》写于道光癸卯,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据“今殁且三十余载”,其卒年在嘉庆十五年(1810)左右。
据知见,董国英的著作存世者仅《楚辞贯》一卷。《楚辞贯》卷首余莲《序》云:“闻先生尚有诗稿,托其友某代为付梓,今已散去而不可复求。”[7]又,《楚辞贯》卷末董希仲《跋》曰:“先曾祖读书一生,无所表见。平时诗文,随手散佚,仅留此一卷。”[7]可见,董国英曾撰有待付梓的诗稿若干,惜乎在当时即已散失。
二、《楚辞贯》的版本、体例和成书过程
据目前所知见,董国英《楚辞贯》只有一种版本,即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博川正谊斋刊本。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眉端小字行六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2008年出版的《楚辞要籍选刊》和2014年出版的《楚辞文献丛刊》均是据此刊本影印。此书流传未广,目前仅见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
此书卷首有罗以智《序》、余莲《序》、《史记·屈原列传》、《凡例》六则。正文一卷,首标“楚辞贯”,次行“博川董国英逸伦氏论释”,下小字三行“后学余莲少白参订;甥孙程锦心如、程章云如;曾孙希仲谊斋校刊”。卷末有曾孙董希仲之跋。书中卷首之《屈原列传》和正文均有眉批,“眉批与正文中之阐释略有分工,眉批多涉及《离骚》之中心、脉络、结构等,阐释多为就句解释、分析及义理阐发。然分工似又不甚严格,大约作者全书注好后再加的眉批。”[3]208是书仅注《离骚》一篇,《凡例》曰:“《列传》详言《离骚》,最后带言《怀沙》,其《天问》《招魂》《哀郢》亦只于赞中带言,余皆置之。盖《离骚》一篇,包举全部全义全神,看透此篇,以后各篇自可迎刃而解。故循《楚辞达》之例,直以《楚辞贯》标之,全部论释如天假之年既当呈政。”[7]可知,此书实是未竟之作。“正文的阐释体例为,一般先引他人之注(基本为朱熹、林云铭、鲁笔之注,且以鲁注为多),然后再阐述己之意见,作文义串释。”[3]208笔者统计,董国英引用林云铭、鲁笔二家最多,引林云铭注约二十次,引鲁笔注五十余次。需要注意的是《楚辞贯》中有两处是余莲付梓时加的按语,一处在“曰黄昏以为期兮”二句后,“余莲按,此二句与下章首二句一意,王逸本无之,何氏谓系后人所增,似当从之。”[7]另一处在“屈心而抑志兮”四句鲁注之后,“余莲按,此章承上言君子小人自古难合我,若屈心抑志与之同事,徒然忍受其尤,而不啻自攘夫诟,不如保我之清白以死于直,固为前圣之所厚也。直字正与屈抑字对。”[7]余莲,字少白,号亦青,浙江省杭州府昌化县人。据《序》可知,余莲曾读过“晦庵朱子、月峰孙氏、犀月俞氏、朴山方氏诸评注”,即朱熹、孙鑛、俞玚、方楘如四家注,可见其对《楚辞》亦有一定程度的研究。
据《楚辞贯》卷首董国英识语可知,此书于嘉庆五年(1800)即已完成。然而,直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才刊行,历时四十五年。据《楚辞贯》卷末董希仲《跋》和卷首余莲《序》可略知其缘由。卷末董希仲《跋》曰:“先曾祖一生好学,于书无所不窥。暮年病治骚者多不得其旨,取而论释之,名曰《楚辞贯》。家贫且老,无力版行,藏箧笥中四十余年矣。”[7]又,卷首余莲《序》云:“先生著是书垂三十年。观其例言,盖欲传之世,以嘉惠来兹。乃因无力刊布,至今埋没不闻。以莲幸同梓里,且不获早见天下后世,谁复有知之者!先生以此识学列郡庠中,既无几,渐见色老,而著是书,又不克表见于世。甚矣,文人之穷也。”[7]可见,此书迟迟未能传之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董氏家贫,无力刊布。又,《楚辞贯》卷末董希仲《跋》曰:“岁丙戌,余少白夫子见而序之,谆谆以寿诸梨枣为属。时仲方应童子试未暇也。越壬寅武陵罗镜泉学博,侨寓昌南,因毕君颕侯得见是书,亦为序之,劝即付梓。而仲又授徒里闬,因循未能中心藏之,负疚滋甚。今年春,学博复自武陵邮书催刻,而少白夫子又屡屡言之。”[7]其中“少白夫子”即余莲,“罗镜泉”即罗以智,字镜泉,杭州府钱塘县人,拔贡生。道光二十五年(1845)授镇海县教谕,有政声。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杭州,罗以智罹难。《楚辞贯》于成书四十五年后能刊刻问世,为此书作《序》的余莲和罗以智二人助力甚大。
三、董国英的楚辞观和方法论
(一)贯《离骚》与《屈原列传》为一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是现存最早的有关屈原生平的史料,是研究屈原生平事迹的最重要的依据。自东汉王逸开始,历代楚辞学者大多参考并征引《屈原列传》以“知人论世”。明代一些楚辞注本已经开始把《屈原列传》置于卷首,或附于卷末,如张京元《删注楚辞》、赵南星《离骚经订注》和陆时雍《楚辞疏》等。到了清代,王邦采《离骚汇订》、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胡文英《屈骚指掌》、江中时《楚骚心解》、夏大霖《屈骚心印》、屈复《楚辞新注》、丁元正《楚辞辑解》、陈远新《屈子说志》、陈本礼《屈辞精义》、郑知同《楚辞考辨》、颜锡名《屈骚求志》等著作均置《屈原列传》于卷首,有的甚至详考、作注、眉批,或进一步撰写年谱纪略,如林云铭在《列传》后又作了《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郑知同为《屈原列传》作了注,刘梦鹏撰写了《屈子纪略》,丁元正编写了《拟屈原大夫年谱》,由此可见明清楚辞学者对《屈原列传》的重视。
今存《楚辞贯》虽仅注《离骚》一篇,董国英亦置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于卷首,且作了详细眉批。董国英《楚辞贯·凡例》首条即云:“读《列传》者未必兼读《离骚》,读《离骚》者无不兼读《列传》。顾当其读《列传》也,以为是叙屈子之为人,谁计及《离骚》;及其读《离骚》,则以为是屈子之文也,又谁忆及《列传》?”[7]董国英强调《屈原列传》对理解《离骚》的重要作用,他认识到了《离骚》和《列传》的内在一致性。《楚辞贯》卷首之余莲《序》云:“李安溪曰幼时读《离骚》曾万过,《离骚》精意,尽于史公《屈原传》中,亦宜读万过。此度人金针也。吾昌逸伦先生《楚辞贯》正得此法,其书冠《列传》于首。”[7]李安溪,即李光地。余莲征引李光地之语以肯定董国英《楚辞贯》对《屈原列传》的重视。
由此,董国英《楚辞贯》于卷首不仅录《屈原列传》全文,并且还做了详细的眉批,与《离骚》相发明。例如《屈原列传》开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董氏眉批云:“首句即为《离骚》首句注明语意。”[7]这说明《屈原列传》开首即与《离骚》开首相应相合。又如董氏眉批曰:“‘入则与王’数句,极写政教修明,四邻亲睦,国家治平气象,此用贤之效,与后‘屈原既绌’两长段相对,为《离骚》‘用贤’一柱注脚也。次段叙屈子见疏之由,即是叙屈子作骚之由。”[7]又如“人君无智愚贤不肖”几句,董氏眉批云:“此段又突起议论,以怀王之不能用贤,归咎于不明,不明须合前‘贪’字看。林西仲曰:‘怀王为人贪而愚。’愚则但知有利益,滋其贪,贪则令利智昏,益甚其愚。其以贤为不贤,不贤为贤也固宜。盖取人以身之不修,如何能用人。此为《离骚》‘修己’一柱注脚也。”[7]诚如黄灵庚先生所评:“董氏以《传》释《骚》,以《骚》证《传》,且紧扣‘修己’‘用人’两端,丝丝入理,细致缜密,盖古今一人耳,其启人之思致亦多,于屈平、史迁皆有功也。”[5]1948再如,董氏眉批云:“篇中既以‘修己’‘用人’分两柱,而于‘用人’一柱中又分两项,其前后言怀王受欺于上官大夫,及靳尚、子兰处,盖为取贤士而言;此言宠姬郑袖,及后内惑于郑袖,则为后半篇求淑女而言也。两项同属‘用人’一柱。”[7]此段分析颇为细致,指出了《屈原列传》与《离骚》两相印证的结构关系,文史互证,颇有启迪。
需要说明的是,董国英《楚辞贯·凡例》首条云:“盖判《列传》与《离骚》而二之也,久矣。不知马迁倾心于屈子,全在《离骚》一篇奇文。《列传》为屈子而作,实为《离骚》而作。二子世相近而皆不得志,于时心术才情复一一相当。马迁自是屈子知己,《列传》大率为《离骚》注脚。后千百载欲舍此而读《离骚》,何啻济川者之先自弃其舟楫也。”[7]董国英所云“《列传》为屈子而作,实为《离骚》而作”,以及“《列传》大率为《离骚》注脚”,有失偏颇,明显有为了抬高《离骚》而贬低《屈原列传》之嫌。
(二)以鲁笔《楚辞达》为蓝本
董国英《楚辞贯》卷首《凡例》明确指出:“是编以鲁雁门《楚辞达》为蓝本。”[7]鲁笔,字雁门,号蘸青,一号榆谷,安徽省安庆府望江县人,著有《楚辞达》一卷、《见南斋读离骚指略》一卷。董国英《楚辞贯·凡例》云:“盖治骚者向称七十二家,西仲林氏已言之。自是而后又不知增添许多家数,大抵重复繁杂。惟林氏《楚辞灯》颇有端绪可寻,顾于词意相似处輙举一篇三致意一语混过,荧荧一灯,光所未及照者多矣。迨至《楚辞达》,而大畅厥词,逐字分晰,一洗蒙翳,疏通证明,时见脉络卓然,为治骚家别开生面。”[7]董国英对于前代之注多有微词,评其“大抵重复繁杂”,而仅服膺于林云铭和鲁笔二家,其评林云铭之注云“颇有端绪可寻”,评鲁笔之注云“脉络卓然”。然而,董国英也指出了林云铭、鲁笔二人的不足,其评林注曰:“顾于词意相似处辄举一篇三致意一语混过,荧荧一灯,光所未及照者多矣”;其评鲁注曰:“惜乎刻意搜寻,不免附会,按之当日事情,殊多迂阔,而于三致意处,亦未能按其部位,历历分其层次,欲其全体透彻,豁然贯通,尚嫌一间未达”[7]。董国英认为林云铭、鲁笔二人之注对《离骚》中的“三致意”之处均未能分析透彻。而且,董国英在《楚辞贯》卷首《史记·屈原列传》眉批中强调:“‘三致意’言一篇中念念在存君兴国,盖指篇中以‘修己’‘用人’立柱,段段相承到底而言。”[7]董氏在行批中又具体解释道:“三字当与《论语》‘三复白圭’三字同看,一篇之中直无一字无一句不注意于修身用贤,以存君兴国也。”[7]《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董国英认为对《屈原列传》中“三致意”的理解不要拘泥于“三”之数,即如《论语》“三复白圭”之三,是反反复复之意。董国英认为林云铭和鲁笔对于《离骚》中的“三致意”之处未能“按其部位”“分其层次”。从《楚辞贯》全书来看,董国英对《离骚》中的关联呼应确实分析得细致有层次。
董国英《楚辞贯》以《楚辞达》为蓝本,首先体现在《离骚》结构划分方面。鲁笔《楚辞达》分《离骚》为前半篇和后半篇,共十二段。鲁笔着眼于虚实之写法将《离骚》分为两个部分,上半篇五段,下半篇七段。段与段之间均有过文,即过渡句。董国英《楚辞贯》分《离骚》为前后两篇,共十一段。《楚辞贯·凡例》曰:“通篇分十一段。开端至‘心之可惩’分五段,为前半篇。自‘依前圣’至终篇,分六段,为后半篇。前半按实言情,后半凭空结撰,意境顿别,前后绝不相连属,故以女嬃三章承上起下为过文,作一大纽,自不在前五段、后六段之列。”[7]董国英承袭鲁笔之说,指出《离骚》“前半按实言情,后半凭空结撰”,而其十一段的具体分法,与鲁笔《楚辞达》大体一致(除“女嬃詈原”三章)。而且,董国英和鲁笔二人均指出“女嬃詈原”三章为过文,只不过鲁笔把此过文作为前五段的过渡语,而董国英认为此过文“不在前五段、后六段之列”。其实,董国英是自相矛盾,因后之“依前圣以节中兮”至“霑余襟之狼浪”仍标为“第七段”,分明还是将“女嬃詈原”一段作为第六段。因此,董国英十一段之分法,实际上仍是十二段。
其次,董国英承袭鲁笔之论,承认并肯定屈原之怨情。关于《楚辞》的忠怨之争,历来是身处封建社会的楚辞学者们的敏感话题。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先引用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之语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之后又云:“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先秦以来的“诗言志”说,已不足以完整概括屈原的创作心理,司马迁敏锐地感受到屈原作品“自怨生”的情感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愤著书”说。鲁笔《楚辞达》曰:“忽然想到君心终不察人心,则邪正永无分明之日,家国民生再无望救之时,不觉放声一号,怨字如呼天抢地而出,传神奇笔,其音至今未寂!与前伤灵修数化紧照应,一伤一怨,各有至情至理。”[10]鲁笔高度肯定屈原之怨情,并以“传神奇笔”、“至情至理”赞扬屈原的怨君之词,显示出了与主“忠”派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与儒家诗教观不同的评价旨趣。
董国英沿袭司马迁的诠释理路,指出“怨”作为《离骚》之情感基调的意义之所在。董国英《楚辞贯》在“怨灵修之浩荡兮”四句眉批云:“怨字是作骚之根,陡从上文‘未悔’转出,如呼天抢地,放声一号,其音至今未寂。”[7]董国英与鲁笔所云如出一辙。 主“怨”派的观点陈述主要在于对《离骚》中“怨灵修之浩荡”的阐释,而此句又重在对“灵修”所指的看法上。鲁笔《楚辞达》注“怨灵修之浩荡兮”四句云:“其所以然之根源,总由于君心昏暗,不识人心之善恶,故群小得以蒙蔽行谗,以正为邪也。始而不揆犹之可也,至此日终不察,虽欲不怨而不可得,此亦人穷返本,疾痛呼亲意。遥领前‘不揆余中情’来深一层,故云“终不察”,玩‘察’字,益知‘灵修’二字从君心。”[10]可见,鲁笔认为“灵修”暗指君心。董国英《楚辞贯》在“怨灵修之浩荡兮”四句后注曰:“承上言我虽无悔,能无怨乎?夫见疏见替固由谗言,总由君心放而不收,故于人心之邪正惛而不察。彼党人遂得乘间献谗,敢诬正人以邪行也。既以不察而致谗,终以不察而信谗。忠臣获罪,国是日非,能无怨乎?”[7]可见,董国英《楚辞贯》直承鲁笔之论,认为“灵修”指君心。又,董国英注云:“始而怨王,继而归罪于党人,终仍归怨于王,究之罪党人,而党人之势方张,怨王而王之心不寤,肠转车轮,无一是处,末乃下气安心,拼一死直,期与前圣同归。”[7]清代很多楚辞学者基于其儒家文化的思想根源和政治环境等,对于屈原之怨不能正面肯定。明清时代,从人伦教化角度提出的屈原“忠孝”之说,可谓甚嚣尘上。鲁笔和董国英站在司马迁等“主怨说”的立场,认为屈原当怨,并且高度肯定屈原之怨情,强调《离骚》怨愤之情感基调,这在当时来讲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董国英承袭鲁笔“幻境”之说,但未能生发开来。鲁笔在《见南斋读骚指略》“篇章”部分云:“上半篇前三段自叙抱道不得于君,而不能自已,后二段论断前文以自解,是实叙法。下半篇纯是无中生有,一派幻境突出。女嬃见责因而就重华,因就重华不闻而叩帝阍,因叩阍不答而求女,因求女不遇而问卜求神,因问卜不合而去国,因去国怀乡不堪而尽命,一路赶出,都作空中楼阁,是虚写法。一实一虚,相为经纬,如风云顷刻万变而不穷,而两界河山自分明有立而不乱。看此汪洋大格局,总不离虚实二字。”[10]鲁笔着眼于艺术写法之虚实,用“幻境突出”来概括《离骚》下半篇的艺术表现特点,他认为“女嬃见责”“就重华”“叩帝阍”“求女”“去国怀乡”等一系列情节,“都作空中楼阁”,是幻境的呈现。遗憾的是,董国英虽然继承了鲁笔的“幻境突出”说。但是,董国英并没有对此生发开来。董国英在“民生各有所乐兮”四句后注曰:“后半分六段,叠澜层波,无中生有,一派幻境,要只为篇末一句作势耳。”[7]董国英对“幻境”的阐释仅此一句,而且“无中生有”、“一派幻境”之用语均直承鲁笔之论,并未做出引申。与鲁笔几乎同时的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也畅言“幻境”说,提出了“幻语”“幻景”“谩语”和“漫兴语”等,主要是从楚辞的语言艺术特征及所创造的艺术境界来阐释“幻境”说。鲁笔(约1675-1747后不久)与蒋骥(1678-1745)几乎是同时之人,生卒年均极为相近,早董国英约五十年。由此可见,董国英对于《楚辞》作品文学艺术方面的理解与阐释尚不及前贤。
(三)由疏通文脉进而阐释大义
董国英《楚辞贯》以鲁笔《楚辞达》为蓝本,还体现在董国英的治骚理念和方法上。清代很多楚辞学者已经把《楚辞》作品的结构和脉络,作为其艺术成就予以关注。如王箴《离骚详解》在《自序》中强调其读《离骚》日久后的感觉是“开阖顿挫,始终条理之妙尽出,二千五百言如贯珠焉。”[11]又,朱冀《离骚辩·管窥总论》云:“愚谓读《离骚》,如满案散钱,必须用索贯串。”[12]再如屈复《楚辞新注》云《离骚》是“长篇大作,原有条贯,和氏之璧,御玺材也,槌碎作零星小玉,连城失色矣。”[13]所谓“条贯”正是指文脉大义,而“零星小玉”则是指繁琐的训诂考证。王箴《离骚详解》、朱冀《离骚辩》和屈复《楚辞新注》都突出强调《离骚》之“贯”,体现了重视文脉和结构的阐释倾向。而且,从汤伟《离骚经贯》、张诗《屈子贯》和董国英《楚辞贯》等著作的命名,即可看出清代楚辞学者们对文脉蝉联而贯通的目的和要求。
董国英十分重视《离骚》文脉的梳理,以此透视屈骚精严的结构。《楚辞贯》卷首余莲《序》云:“其书冠《列传》于首,标出‘修己’‘取人’两注脚,于《传》引其端,于《骚》畅其旨,步步相承,丝丝入扣,如牟尼珠一线穿成,更无从前复沓难通之苦,洵不负以‘贯’名篇也。”[7]余莲此评切中肯絮,全书最重要的结构特征即“修己”“用人”二柱,不管是在《离骚》注解、眉批中,还是《屈原列传》眉批中,此二柱贯穿全篇。董国英于《离骚》每章之上大多都有眉批,主要功能就是分析字法、句法、章法和结构等,进而疏通《离骚》之脉络。如董国英在《离骚》起首“帝高阳之苗裔兮”四句眉批云:“以‘正’而生,便注篇末之以正而毙着笔。‘贞’字可贯通篇,为屈子一生守正不阿之本。”[7]董国英拈出一“正”字和一“贞”字,把它们与阐释脉络结构相贯通,辨析其在《离骚》字句经营中“可贯通篇”的重要作用。董国英于《离骚》乱词末句“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后注曰:“于是以‘正’而毙,回顾篇首之以‘正’而生,为全篇结穴。循首讫尾,无数层折,无数烟波,要无一字不照定此句落笔。读至此句,觉言终而气有余,意足而神尤旺。首尾回环,精神团结,曾有一字外散否?曾有一字不贯否?”[7]正如董国英所云,屈原“以正而生”、“以正而毙”,《离骚》“循首讫尾”、“首尾回环”,由此通篇文脉一贯。
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指出:“是书所以名‘贯’者盖有二:一则所以贯穿屈子《离骚》、司马迁《屈原列传》,使二者相互印证,合符若一也;二则董氏以‘修己’‘用人’为《离骚》全篇之二柱,且统摄始终,一贯到底。”[5]1945-1946此二“贯”分析得很有道理,笔者于此再加一“贯”,即董国英与屈子精神相贯注。罗以智《楚辞贯·序》云:“得先生之论释,千载下如揭其心。盖直与屈子之神明相贯注者,凡仅仅比于风雅,玩其辞而遗其旨,抑末矣。”[7]此评价虽有过誉之嫌,但实际上指出了董国英研骚的动机和方法,即“与屈子之神明相贯注”,这亦是董国英《楚辞贯》与鲁笔《楚辞达》一脉相承的一个方面。鲁笔《楚辞达》之师范《序》云:“其释骚也,婉而多风,曲而有直,体二千余年之大文,至是而昭若发蒙,洞若观火。先生之自序其时艺曰:‘间尝独往深山空谷中,四顾无人,划然一啸,忽心关震动,如乐出虚。’然则此书之成,要亦当其划然一啸时欤?”[14]师范,字荔扉,自号金华山樵,赵州直隶州人。他提到鲁笔说自己曾经来到深山空谷无人处,“哗然一啸”,忽然感到“心关震动,如乐出虚”,这应该是鲁笔描述他灵感来临时的感觉。师范感叹《楚辞达》之成书,很可能也是鲁笔“划然一啸”,心有所感而作。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毛庆先生总结的明清楚辞学者所用的“直觉感悟法”[15]。罗以智说的董国英“与屈子之神明相贯注”,实即调动直觉想象,通过自己的方式悟屈子之情,设身处地去体悟和感知屈子之心理。例如《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董国英眉批曰:“一腔如火热肠,讨得一副如冰冷面。”[7]又如于“悔相道之不察兮”四句眉批云:“前从不悔转出,此又从怨转到悔,文心委折,如穿九曲珠。毕竟怨是真,悔是假。惟其真,故至死靡他;惟其假,故一笔便了。”[7]再如“民好恶其不同兮”四句,眉批云:“开口说当世,接口便说本国,总念念撇楚不下,只无奈其终朝不可与处何。”[7]凡此种种,皆是董国英设身处地,想屈子之所想,怨屈子之所怨,悔屈子之所悔。这种研究从动因上来说,早已不是停留在作品文本的层面,而是上升到了精神理念的高度。这种研究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比“知人论世”无疑更加具有情感的感召力。
综上所述,董国英生于雍正七年(1729),卒于嘉庆十五年(1810)左右,是浙江省杭州府昌化县人。《楚辞贯》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直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才刊行,历时四十五年,一直未能刊行的主要原因在于董氏家贫,无力刊布。《楚辞贯》以鲁笔《楚辞达》为蓝本,主要体现在《离骚》十二段结构的划分、承认并肯定屈原之怨情、承袭鲁笔“幻境”之说等方面。董国英身处朴学风潮正盛的乾嘉时期,却没有刻意追求字句训诂和名物考证,而是重视《离骚》文脉的梳理,以此透视精严结构,在分析文脉进而阐释大义方面走出了新路。
——《日知录》陈澧批语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