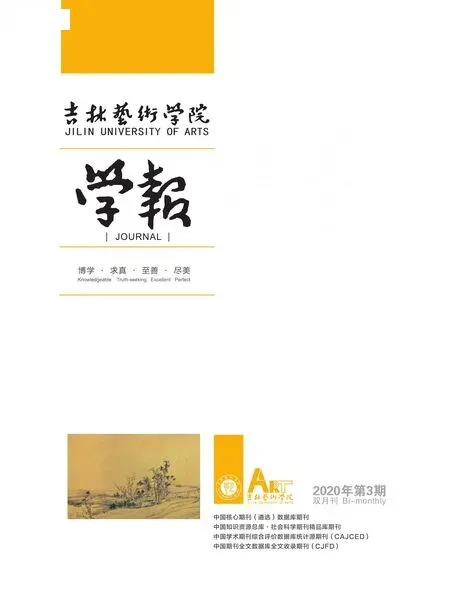论“陌生化”戏剧理论在影视艺术中的流变
李念章 靳娟娟
(云南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周口师范学院,河南 周口,466001)
“陌生化”理论由德国戏剧理论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提出,作为布莱希特的美学思想核心和现代戏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陌生化”理论在深刻影响了布莱希特之后的戏剧美学大观的同时,接踵而至地触及并引发了“陌生化”理论在电影艺术中的一场巨大变动。众所周知,电影作为一种银幕叙事艺术,在叙事手法上与戏剧同根同源,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电影和戏剧在叙事体上,始终是“对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整体来讲,是一种模仿和再现情节的叙事艺术。面对古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既定的戏剧真理,欧洲这片诞生了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的戏剧沃土,虽然看似绚烂多姿,但在戏剧理论的根基上仿佛从未摆脱一种类似于先祖遗传的桎梏。在因循守旧的思想镣铐里,戏剧界一次次看似大刀阔斧的改革,对于叙事体根基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1895年之后,一脉相承的叙述手法被承袭在新兴的电影艺术之中,以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电影被作为一种猎奇观赏而非艺术来叫卖。这种难登大雅的现状,直到蒙太奇手法出现以后,才逐渐发生了实质性的改观,而布莱希特所代表的“陌生化”戏剧理论,无疑在这个筚路蓝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从布莱希特到爱森斯坦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兴盛,在当时的德国戏剧舞台上,面对着以营造“生活幻觉”使观众移情和共情的戏剧创作,布莱希特试图建立一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型戏剧和美学主张。他在《谈实验戏剧》中写道:“感情融合是当今占统治地位美学里的一个支柱。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诗学》中早已对此有所论述了,那就是‘净化’——通过举止表情去陶冶观众的灵魂。演员在舞台上模仿英雄是以暗示和具有转化力的手法去模仿的,犹如身临其境。”布莱希特在此阐释了亚里士多德论述的戏剧问题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戏剧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戏剧模式的可能,他将这种“非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模式称作“叙述体戏剧”。布莱希特所提倡的这种戏剧原则相较于“亚氏”戏剧模式有着两大特点:一是在剧作上有意淡化了亚里士多德所看重的情节,运用非线性、片段化的叙事来解构和拼接剧情;二是强调主体意志评价的在场性,站在更客观的角度来审视角色和情节,力求使观众走出虚拟的“生活幻觉”,保持一定程度的分析和评判能力。布莱希特将这种隔开“生活幻觉”的戏剧效果称作“陌生化效果”,在新的戏剧体系下,演员的表演得以逐渐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摆脱出来,他们不再是角色的傀儡和复制品,而是高于角色,操控角色,有了更多对角色解构和变动权利。剧场亦不再拘泥于营造群体幻觉,而是以理性的思索打破“第四堵墙”,改变观众一贯的旁观者视角,用主动引导的方式替代刻板的情节再现。依据“陌生化”理论,布莱希特先后创作了《三毛钱歌剧》《例外与常规》《母亲》等教育剧,以及《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等映照社会问题的代表作品。当这些剧目以“先进”的手法,独到的见解力和引导性轰动德国剧坛的时候,布莱希特不会想到,在迢递千里的东欧平原上,另一个睿智的头脑正萌发着一场冰雪中的生机。
谢尔盖·爱森斯坦出生于俄罗斯里加,早在莫斯科剧院任职时,这个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便凭借一部《聪明人》崭露头角。《聪明人》改编自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智人千虑必有一失》,爱森斯坦在创作中并没有像其他改编剧作家一样因循守旧,而是充分地对原剧的情节进行打乱和重组,只保留最初的对白和人物,甚至将原剧中没有的人物造型因素和活动大胆地搬上舞台,马戏、杂技、电影装置齐聚一堂,给观众带来了新奇、震撼的情绪感受。他据此实验性演出的成功进行总结,发表了著名的《吸引力蒙太奇》一文。爱森斯坦在文中指出,传统的戏剧形式已经难以反映十月革命之后的现实要求,戏剧当从单纯的审美层次递接到实用的程度,藉此引导人民的革命思想觉悟。“吸引力蒙太奇”运用了与舞台演出看似不相关联的情节和道具,且有着明确的指向性,而其产生的间离效果对主题的彰显亦具备着推动作用。相对于布莱希特对舞台中情感因素的排斥,爱森斯坦则强调引导观众最大限度地融入舞台情感之中,但与传统沉浸式情感不同的是,这种情感的融入要经过事先理性化的构思预设和氛围营造。由于爱森斯坦所提倡的对“陌生化”情感的热处理难以在受时空局限的舞台上尽善尽美地呈现,后期的爱森斯坦决心转入电影生涯。
果不其然,电影灵活多变的空间结构特性成为爱森斯坦徜徉“陌生化”效果的汪洋。1924年到1929年,在转入电影界的短短五年间,爱森斯坦先后拍摄了《罢工》《战舰波将金号》《十月》《总路线》等脍炙人口的影片。这些电影充分应用了“陌生化”原则,对电影的理性实验自此一度成为爱森斯坦享誉世界的个人导演风格。与戏剧的剧场性不同,在电影活动的流程中,观众一直作为一种潜在的对象存在,是故电影的“陌生化”难以依托布莱希特所提倡的观演关系来建立。但其作为一种摆脱时空限制的银幕艺术,在故事建构、镜头设计、蒙太奇剪接上却是广阔天空、大可作为。爱森斯坦的电影“陌生化”,即建立在故事建构和蒙太奇手法之上。
首先,故事情节建构的片段性和群像性。爱森斯坦在电影初期的题材选择上,偏向于选取重大历史事件,显然这与爱森斯坦本人的艺术追求和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诉求密不可分,但不得不说的是,爱森斯坦所选取的题材和表现的方式十分有利于革命激情的营造,原本以歌颂人物和表现历史情节为主的史诗在爱森斯坦手中赋予了更多的人民意志。与以往的线性叙事不同,爱森斯坦在情节构造上倾向于打破传统的叙事结构,用社会片段式的情节去表现宏大的社会现状和人民的英雄气概。在人物的设置上,爱森斯坦消去了贯穿整个故事的主人公,取而代之的是群像式的人民群众。这种分散式的片段,点状的人物线索,成为爱森斯坦电影的构建基础和风格。而将人物打散,情节打散,亦是与布莱希特所提倡的“陌生化”效果不谋而合。正如布莱希特所说的,非“戏剧性”的叙事体相较于“戏剧性”的叙述体有两大显著的优点,一是避免观众将感情完全与剧中人物相混同,使得观众对剧情的评判不是倾向于任何一个角色的个人特质,而是整个剧作所能引发的思想和意义;二是避免个性化的角色和观众的个人情感混同,使得全剧不拘泥于表现个人意志和个人情感,更有利于去展示非个人情感所能左右的宏大历史事件和哲学真理。爱森斯坦对电影故事的建构正是在这种非“戏剧性”的叙述体中,完成了对历史宏大事件的刻画和表达。
其次,“陌生化”蒙太奇手法的引导性应用。自蒙太奇作为电影手法诞生以来,其对剧情引导的建构作用一直是举重若轻的。苏联电影导演库里肖夫实验曾深刻证明了这种镜头的衔接对于剧情引导的效果,他为演员莫兹尤拍摄了一个特写镜头,在这个镜头下,莫兹尤是面无表情的,不具备任何感情色彩。紧接着,库里肖夫分别将三个镜头与莫兹尤的特写组接在一起,并拿给不知情的观众去看。竟然惊奇地发现,观众在看到分别组接的三个镜头(一盆汤、一口棺材、小女孩)构成的画面时,竟然分别体会到了莫兹尤面无表情中的饥饿、悲伤和愉悦的情感。爱森斯坦认为,蒙太奇所营造的主题效果应该在未来的电影中更具备目的性和引导性,它所带来的效果是感性的,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引导的方式,蒙太奇应该具备辩证的理性思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吸引力蒙太奇”,又称“杂耍蒙太奇”。与单纯的镜头组接不同,爱森斯坦强调的是将原本在文学中才可以用到的隐喻手法放置在电影中。值得一提的是,爱森斯坦在此强调的蒙太奇手法运用与格里菲斯所代表的导演不甚相同。传统的隐喻手法所利用的能指和所指是建立在事物在深度观念的联系基础之上,例如在深度的观念中,红玫瑰是爱情符号的代表,红色象征着热烈和奔放。但在爱森斯坦的“吸引力蒙太奇”中,他利用的却是没有建立深度观念联系的事物,而是将两个互不关联的陌生事物并列在一起,试图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感官冲击,表达和延伸镜头之外的主题思想。在他的影片《罢工》中,沙皇镇压工人的镜头与屠宰场宰牛的镜头相并列。屠宰场宰牛与工人起义原本是互不相干的情节,宰牛镜头的插入甚至可能会打破先前观众观看工人激烈抗争情节的兴致,破坏了情节的连续性,并不符合传统电影叙事的习惯。但是爱森斯坦的这种类似“播放事故”的刻意安排,却在此达到了一种情节的“陌生化”效果,观众会对这两个镜头发出自己的见解和思考:沙皇对工人的压榨,不就跟屠宰场里对牛屠杀一个本质吗?爱森斯坦正是通过这种“陌生化”的镜头衔接处理,将故事的解释权和理性的思维辩证交给台下的观众。除了隐喻手法之外,爱森斯坦对蒙太奇的“陌生化”使用还存在于对电影时空的剪接上面,包括电影《十月》中幕后政府与前线战场的因果对立,“吊桥分离”片段中的多视角拼接,以及电影《战舰波将金号》著名的“敖德萨阶梯”段落,都是爱森斯坦的蒙太奇手法对“陌生化”效果的巧妙运用。早期的爱森斯坦不但将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戏剧理论与电影手法结合,并运用到电影作品中,而且对电影理论做出了理性的认识和创新,这种成效是显著的。但在创作后期,爱森斯坦开始过度迷恋单纯形式上的“陌生化”效果,割裂了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体中必然性和可然性的联系,试图将绝对的理性完美地呈现在依靠相对感性支撑起的荧幕艺术之上,甚至将《资本论》这一部充满思辨性的哲学和社会学宏著拍摄成电影,以至过犹不及,险些误入到形式主义中去。
爱森斯坦对于《资本论》的拍摄尝试虽然没有进一步实现,但他开启了“陌生化”理论在电影艺术中大胆尝试的先河,其精湛的电影艺术水准,亦耳濡目染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们。在爱森斯坦之后,“陌生化”戏剧理论依然在当代影视艺术中激流变换,不断丰富和扩宽着它的艺术手法和美学理念。
二、当代影视对陌生化手法的继承和运用
1. 戈达尔的开拓
如果说爱森斯坦所用到的电影“陌生化”的切入点在于片段结构和引导性的蒙太奇手法,那么随着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崛起的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则是将这种片段结构和引导性蒙太奇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以跳切和定格为主的新的“陌生化”方式。
20世纪60年代后,全世界沉浸在一种激进的热情之中,欧洲的电影导演因为看重布莱希特早期的革命性,纷纷开始对他的作品和理论进行研究。戈达尔早期拍摄的电影《一切安好》明显受到了布莱希特的《关于歌剧<马哈戈城的兴衰>的意见》影响,戈达尔在《一切安好》中放肆地打破了电影的“第四堵墙”,我们可以听到共产党工会代表、“新左翼”领导人、工厂经理、普通劳工分别对政治时局的自我见解,看到芸芸众生在历史的车轮下踽踽独行的各自生活。影片没有明确的故事主线和贯穿全局的主人公,戈达尔用跳切的方式打破了影片中各个角色生活的幻觉,使得电影观众得以跳出普通人单一的生活情感,站在宏观的视角审视激进的60年代结束后时代和人民的整体生活状况。戈达尔在他的诸多影片中运用了大量的跳切手法和定格镜头,形成了他独特的导演艺术风格。正如科勒律治所说的“自愿暂停怀疑”的方法,这种视觉画面的中断和定格,将原本连续的事物中断,消除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思想和情感倾向,使之达到一定程度的透明化和陌生化,为观众思考事物提供新的方式和角度,消弥“可见的意识形态”,并赋予其理性因子。
戈达尔在电影艺术中对“陌生化”理论做了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开拓,后来的电影人如汤姆·提克斯、斯派克·琼斯等也都在各自的作品中对这种“陌生化”的隔断做出大胆的尝试,并获得了极大成功。例如《罗拉快跑》不断闪回和定格的画面将人物命运的交叉点一次次地展示在观众面前;《改编剧本》和《纽约提喻法》那被隔断的激励事件和人物行动将叙事置于失控的边缘,既定的发展规律一次次被冲击和打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曾阐述过情节变动的规律:“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发展的可然律应在必然律圈定的发展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变得失真,不再具备艺术的美感和传达。千百年来,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个框架如影随形地烙刻在剧作人心中,以至于循规蹈矩的编剧过度依赖必然律下可然律的单一归属和发展,逐渐将叙事框定在片面的可然之中,视意识形态为可然,视戏剧律法规定的情节为可然,甚至照本宣科一度为叙事戴上了“三一律”的镣铐。而布莱希特所提倡的“陌生化”即在于重新重视事物发展必然律中的可然律,辩证地看待这种游离在必然周围的可然性。在这种对可然性的发掘下,当代电影艺术的方方面面亦开始摆脱既有规律的束缚,“陌生化”理论亦深远广阔地流变于姊妹艺术之中。
2. “陌生化”对影视的可然性发掘
叙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对客观事物的投射和反映。无论诗歌、小说、戏剧、还是电影,都在事物既有的框定下叙写和运转,但由于惯性思维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我们往往在指定铁律的同时忽视了事物诸多的可能情况。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我们站在“陌生化”的立场上重新进行审视,这种闭锁在既定思维中的可然性便有可能被重新发掘,带给我们陌生而又熟悉的惊异。“陌生化”的脱局旁观,在电影中则分别表现在角色的陌生化、情节的陌生化和叙事的开放化中。
对于角色的塑造,东方和西方有着不谋而合的理论根基。印度的《舞论》中强调“味”旗帜下的“随情表演”;来自日本世阿弥的戏剧秘传书《风姿花传》中,“能否使一个曲目取得成功,要在演者的用心如何”,强调演员对角色模仿外观和内情的储备;中国京剧强调程式化的表演和细节的假定性再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亦是主张演员用融入的方式体验角色的生活。不难看出,这些戏剧理论家的主张都建立在演员对角色的还原之上,不论是假定性表演还是移情式表现,都未离开角色既定的人设。而布莱希特认为演员应刻意地脱离角色,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论实验戏剧》中提到:“把一个事件或人物陌生化,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电影作为一种银幕艺术,其表演成型的一次性,要求角色的陌生化具有可预见的充分准备。演员在一次性的表演前必须事先对角色进行理解和考量,给角色形象注入新鲜的血液,而过往的角色形象往往根深蒂固,这就意味着在塑造时必须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剥离和重新解构。以孙悟空这一经典形象为例,在早期的小说、戏曲和影视剧中,孙悟空的形象一直限定在斩妖除魔、惩恶扬善的光辉形象。但深入研究吴承恩的原著文本就不难发现,孙悟空惩恶扬善的形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发展有一个从天真本色,招安天庭到护送取经的过程。孙悟空的阶段性性格的分化,为其“陌生化”提供了必然律的支撑。导演和演员在解构孙悟空这一形象时,便以此有了全新的切入点。1986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基本遵循了小说中的性格形象;2002年上映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则根据张卫健的演员特质发掘了孙悟空更多天真调皮的性格;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系列电影更是颠覆了传统的孙悟空形象,由原著中一个小小的紫霞仙子片段衍生出的痴情悟空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解读空间,一度在大陆兴起了后现代解构主义的热潮。电影“陌生化”的角色塑造在于站在不同的观望角度,使用不同的解读方法,搭配多样的社会诉求为观众带来理性的发现和再思考的解构价值。
情节的“陌生化”也为观众带来了理性思考的价值。布莱希特认为,“惊异是一种为自己也为别人揭示新事物的能力……把对象和事件描绘成异乎寻常、陌生化的形态,让观众产生困惑而促使他们深入认识所发生的内在实质。”电影情节的“陌生化”处理在此即体现在情节设定和起伏的惊异化呈现之中。科恩兄弟导演的惊悚电影《巴顿·芬克》斩获了包括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等多项电影界奖项,其讲述了小有名气的编剧巴顿·芬克在好莱坞自我挣扎与抗争的故事。全片亮点在于将不受事物发展规律的失控情节递接发展出来,造成了惊异化的情节体验。舞台剧编剧巴顿·芬克受邀来到好莱坞写作一部摔跤题材的电影剧本,面对题材和领域的陌生,正当他在破旧的旅店内搜肠刮肚,却下笔无神时,隔壁的房间却发生了种种异象,将他置入到了“人间炼狱”之中。类似于《巴顿·芬克》故事题材的电影还有斯坦利·库布里克的《闪灵》,两者都提及了作为编剧绞尽脑汁,不疯魔不成活的写作过程。但与《闪灵》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下编剧的本我激变不同的是,《巴顿·芬克》中的激变更多的是“陌生化”的激变,观众在这种“惊异化”过程中,逐步出离对剧情发展的设想,从而脱离情节,体味整个故事的氛围和哲学道理。利用惊异的情节扩大观众自由想象的空间,在布莱希特看来更有利于发现事物表象之外的哲学本质想象,而站在电影艺术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媚流俗的惊异化情节设计,无论在艺术哲理上还是票房市场上都是动人心魄的。
惊异的情节带来新的审美观照,而开放式的叙事则异曲同工地将这种不拘陈规的审美观照放开。在布莱希特的早期戏剧中,他通过借鉴史诗的“叙述形式”,获得了情节的跳跃性和开放性。舞台演员跳出剧情评判情节的形式,同样出现在电影银幕之上。在当代电影导演中,伍迪·艾伦是一名“人物自白”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代表作品《安妮·霍尔》中,主人公艾维·辛格在镜头前的讲述成为串联片段式剧情的线索。非但如此,在伍迪·艾伦的诸多作品中,主人公如灵魂出窍式地跳出剧情,指着鼻子评判方才的“自己”“朋友”“恋人”等诸多行为,加强了理性意识的评判和干预,提高了观众的理性审视。除情节的自我审视之外,非封闭式的叙事结构也是“陌生化”理论催生下蓬勃兴起的新生事物。自电影诞生之日以来,线性的封闭式结构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视听语言的不断进步,这一格局才逐渐被打破。
不同于戈达尔对片段情节的跳接和隔断,开放式的叙事结构之隔断不在于单个的片段和镜头,而在于拆分、聚合、重组整部影片,试图用隔断后重组的1+1>2的效果来融入影片更多的思辨真理,类似戏剧中将各个规定好顺序的“幕”打乱重来。在非线性的开放叙事结构应用上,昆汀·塔伦蒂诺是近代影坛升起的一颗新星,“幕”的形式,非线性的开放叙事,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低俗小说》《无耻混蛋》等影片的结构,均以单个人物一幕的群像式展开,不同人物、不同角度的分场叙事,将看似客观的情节理性地拆分成了人物主观视角下不同的色彩和命数。原本客观的情节,在不同视角下一次次呈现之后,非但没有熟悉,反而变得陌生,因为随着人物视角的切换,我们所看到的同一情节所侧重的场面和细节是不同的。各个人物隔断视角的处理,为我们发掘了故事中更广阔的情境空间,观众管窥于各种视角,同时又不会移情于单个的人物角色,类似一种上帝视角的思辨,却又充实辩证的体验,在模糊角色个人情感,深化影片整体主题的同时,亦刺激了观众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理性的发掘正是布莱希特所赞赏的。
“陌生化”理论不但对影视内部可然性的发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叙事结构和叙事情节的开放化,在银幕之外的观演关系基础上,亦塑造了无限的可能。而这其间将选择和交流权从导演交还给观众的趋势,不得不说是对电影在观演关系上对戏剧的一种反哺和回归。
三、观演关系的回归与未来展望
“第四堵墙”特指三面环绕的镜框舞台中面向观众的第四面墙,“第四堵墙”的出现是用于营造观演关系中的戏剧幻觉。墙中的演员视观众于无物,以此便于体验角色,“活”在舞台之上,营造惟妙惟肖的现实幻觉,同时,将观演关系间隔的“第四堵墙”也赋予了舞台的神圣性和仪式感。电影的出现首先在白色的幕布之上,以平面的呈现方式作为天然的第四堵墙将演员和故事情节发展与观众脱离。杨德昌在他的作品《一一》中曾借用角色之口说过:“电影的出现,将人类的寿命至少延长了三倍。”但是对于这种延长的生命,在早期甚至现代的电影中都是不完整的、不具备参与感的生命。田汉在提及电影时,曾感叹道:“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在白昼造梦也。”以此可见,电影作为一种被比作白日梦的艺术,“梦境”的参与感可见一斑。随着“陌生化”理论对第四堵墙的打破,戏剧率先破除了“我演你看”的固定观演关系,然而电影在此方面虽然也做出了百般尝试,仍破解不了角色活在平面中的技术难题。这种僵局,在新世纪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中有了一定的改观。
片段、开放式的结构给了制作者将必然律的可然无限“陌生化”重组的可能,而技术的进步,使得这种可然性的选择权,有了逐渐移交给观众的趋势。这种将故事发展的选择权交给观众的电影形式,有一个新的名字——互动电影。但是,在实际放映中,这种互动的交流感好像并不乐观,因为观看互动电影的人仿佛手中拿着一个电视的遥控,其所选择的情节和片段是预先设计好的,以至于这层关系中,并没有活的交流存在。与其说是打破了“第四堵墙”,不如说是隔着第四堵墙选择下一幕的换场,观众使自己主动而又被动地卷入到了舞台情节之中。是故,早在20世纪就初露端倪的互动电影并没有真正地推翻第四堵墙的隔阂,相反,在这种“死亡”的观演关系中,观众更能体会到诸多预先设计好的情节和人物的麻木。那么,真正的活的观演关系该如何建立?
布莱希特认为,相较于传统戏剧的形式,新的戏剧形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唤起观众的能动性,迫使观众做出理解和判断。这就说明,活的观演关系并不在于演员下台宣读圣旨般地与观众“交流”,而是演员在下台交流后,观众会有什么样的理解和判断。将观众的理解和判断放在第一位,才是打破“第四堵墙”,搭建“活”的观演关系的重心所在。目前,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在线的弹幕交流和评论暂时成为这一活的观演关系的搭建平台,观众之间的思考得以在这一平台上进行互动和交流,逐渐形成了一种边看电影边看弹幕,边欣赏边思索交流的观看方式,观众的能动性和理性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发挥。观众们“吃瓜群众”、“围观路人”的自嘲,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弹幕空间”这一“无形剧场”的诞生和存在。但是,这种交流毕竟隔着迢迢千万里的电波,毕竟是没有血肉的冰冷文字,真的符合戏剧观演关系中“活”的原则限度么?我们姑且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去展望那个即将到来的“现实”。
四、结语
纵观“陌生化”戏剧理论在影视艺术中的流变,不难看出,戏剧和电影在诸多方面艺术美学上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和共通性。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戏剧理论正是遵循着多形式表演艺术相通的必然律途径。“陌生化”对象在电影艺术中进行着可然的流变与发展。戏剧与电影之间相互交融,彼此成就,亦可称为这两门综合艺术之间相互跳脱的“陌生化”思考。戏剧与电影,是综合艺术与综合艺术之间的交流,“陌生化”理论虽是诸多交集领域中的沧海一粟,但其所能相互衍生出的意义和作用,却是可以预见的万顷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