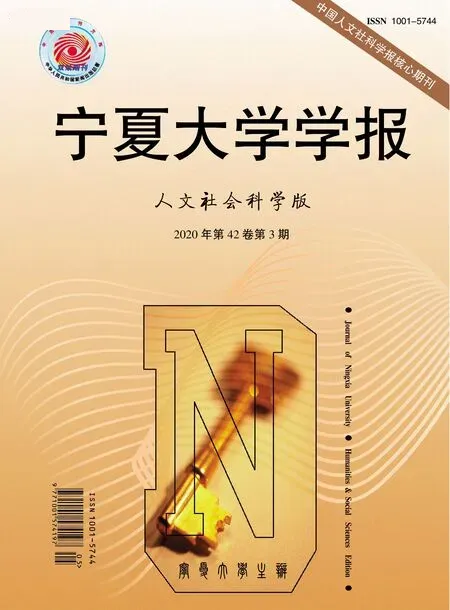苏颂诗歌自注的特质、地位及其文学史意义
林阳华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北宋泉州同安人。他集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于一身,曾任北宋宰相,创下了多项世界级的科技成就,存有《苏魏公文集》72 卷,其中诗歌13 卷,不乏数量客观的自注。学界对其科技思想与成就、仕宦经历、家族教育、文学创作与思想等进行了颇有建树的研究,成果斐然。但有关苏颂诗歌自注的研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学界或对其视而不见,或将其当作文献资料看待,而忽视了其诗歌自注的特质与地位,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基于此,本文尝试对苏颂诗歌自注的特质与地位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具备的文学史意义。以下论述之。
一 叙事的表达:长篇自传体家训诗自注
中国古代诗歌的自传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离骚》《九章》等篇章中皆有一定的叙事因素,关涉作者的个人经历。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唐代的诗歌叙事成分越来越浓厚,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元稹等诗人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自传诗,分属唐代各个时期的代表。到了北宋,自传诗走向了成熟。“自我叙事意味着诗人要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对象加以表现,要求写作的诗人与曾经的自己拉开距离,并对曾经的自己加以审视和叙述。当诗人主动做到这一点,也就具备了比较成型的自传意识”[1]。这意味着诗人需要自觉地对曾经的“自我图像”进行描绘,通过自我视域对过去的“自我图像”作出评判。对“自我图像”的描绘和评判,除了通过诗歌正文本完成外,有时需要借助诗歌副文本——自注——来辅助完成。
苏颂的《累年告老恩旨未俞诏领祠宫遂还乡闬燕闲无事追省平生因成感事述怀诗五言一百韵示儿孙辈使知遭遇终始之意以代家训故言多不文》(以下简称《感事述怀诗》),是宋代一首比较成熟的自传诗。此首诗歌正文重在讲述自己的平生经历,叙事性较强,用于训导子孙后代。如果以充当副文本的“自注”作为考察对象的话,总结其特征,不难发现亦具备较强的叙事性。其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从自注所叙述的人生经历的长度来看,《感事述怀诗》颇长。此诗作于苏颂退居润州时期。苏颂生于天禧四年(1020),致仕于绍圣二年(1095),并于此年退居润州,距离其亡故的靖国元年(1101)只有数年时间。此期的他可以对自己70余年的过往经历进行回顾,时间从读书以来一直到退休之后。这种回顾由于自注的存在,为更好地了解其经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其二,从自注叙事的内容来看,《感事述怀诗》丰富多样。苏颂之孙苏象先《魏公谈训》卷二说道:“祖父以宫使归润,居化龙之新第,著《百韵诗》以代家训。具述祖先基业、平生艰勤、遭遇终始之大纲,训饬子孙……”[2]此处的《百韵诗》便是《感事述怀诗》,以上几句交代了此诗作于苏颂致仕之后,其创作地点在润州的信息。“具述”说明其叙述的范围较广,涉及“祖先基业、平生艰勤、遭遇终始之大纲”等内容,这些在自注中皆得到了体现。
其三,从自注叙事的次数比例来看,《感事述怀诗》较高。据统计,《感事述怀诗》自注数量共31处,这些自注大致分为读音声调自注、典故出处自注、自我经历自注、其他自注四种。其中,自我经历自注有21处,占比67.74%。如果从分布来看,自我经历自注贯穿于《感事述怀诗》始终,与苏颂诗题所说的“使知遭遇终始之意”吻合。
其四,从自注叙事的详略程度来看,《感事述怀诗》较为详细。以应举、为官为例,不难看出这个特点。应举方面,如“赏延辄辞官,雅志将自奋”自注:“康定元年乾元节,推恩近著,先公任中书舍人,欲奏荐。予乞且应举。先公初不怿,既而大称许,复勉以勤笃,又延建安黄晞先生数公置门下,及与长乐王深甫子直,清江刘原父、贡父兄弟同砚席,凡五六年。后予已忝科第,往来京师,犹相从讲论。”[3]讲述了当初自己欲应举,父亲苏绅由反对到为其寻找学伴的事迹,事情的始末清晰。而“予守颍将二年,忽被召迁府界提点,逾年徙三司度支判官,又二年出为淮南转运使。神宗初登极,因送辽使还,陛对,特蒙访问北辽事,颇合旨,仍宣谕二府。故到淮南才五月,召还修起居注。迁西掖掌诰。二年,因论差除御史事,蒙中札召对,询问本朝故事。上初甚以为然,及有褒语。无何执政以为违忤,见黜归班趋常朝者一年半。遇恩出领东阳,移谯郡。还朝两领三班银台,又出南都知余杭,入为史官,尹京府。以孙纯、陈世儒事贬濠、梁,凡五换推,及入对狱,卒无一事絓吏议,乃罢濠领孟,辞以先公薨逝之地,改知沧州”[4],这段注文讲述了从任颍州知州,一直到任沧州知州之间,苏颂为官的复杂曲折经历。其他自注同样如此,不一一列举。
综合以上四个特征,可以看出《感事述怀诗》的诗歌正文与自注,实现了对作者长时段丰富多样的人生经历的详细“双重叙事”,可将其作为北宋诗歌“双重叙事”的代表之一。“单重叙事”是指诗歌正文的叙事,由于缺乏自注的辅助,读者常常难以对诗歌正文有更深入、准确的理解。虽然有时过多的自注会有喧宾夺主之嫌,但《感事述怀诗》做得比较成功。此诗属于五言古诗,风格古朴,语言简练,欲将诗人近乎一生的经历,通过五言百韵诗,在1000 字的篇幅中进行翔实的叙事,需要做到极高的浓缩。对于在诗歌正文中难以表达清楚说明白的,借用散文体式的自注来完成,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尝试将这些自注单独挑出,并加以整理,它们完全可以成为一篇自传散文,从中可以看到苏颂较为清晰的人生脉络。由于较为详细的叙事,且有效地对诗句进行了补充说明,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将其用于补正史、方志之缺,甚至成为编写《苏颂年谱》的重要文献资料。
由于《感事述怀诗》是以自传代替家训的方式呈现的,所以可以把它称为长篇自传体家训诗。在北宋并不乏长篇自传体家训诗,有些声名也不亚于《感事述怀诗》。如在苏颂之前的范质,作有《诫儿侄八百字》,此诗为五言八十韵,全篇训诫色彩浓厚,涉及科考、立身、为人之训等。前半部分有关自己读书、为官的经历,有一定的叙事成分,如“二十中甲科,赪尾化为虬”自注:“二十三进士及第,今举全数”,又如“三十入翰苑”自注:“时三十三”,再如“四十登宰辅”自注:“年四十一”[5],说明了中甲科、入翰苑、登宰辅的具体时间。后半部分的说理味道浓厚,与之对应的自注亦然多为出处自注,涉及曾参、《毛诗》《史记》《左传》等,目的在于训导子侄当慎言、宜尊人、有节义等。而被周剑之先生称为宋代自传体家训诗代表的另外两位诗人,即胡铨的《家训》、郑侠的《示女子》亦为长篇家训诗,其中胡铨的《家训》为五言六十韵,郑侠的《示女子》为五言五十四韵,尽管这两首诗均具备一定的叙事性,同《感事述怀诗》一起推进了长篇自传体家训诗的成熟,然而它们没有自注,属于“单重叙事”。由于自注在解释诗歌时,具有一定的优势,缺少了自注,读者对于诗歌的理解可能会存在较大隔阂或偏差,因此存有自注的“双重叙事”自传体家训诗,实现了对作者人生经历更为全面深入的叙事。以此为据,《感事述怀诗》可称为宋代长篇自传体家训诗自注的代表。
实际上,宋代泉州同安苏氏家族一直较为重视家族教育,其文献资料在《魏公谭训》、苏颂的诗文中有较为集中而全面的体现。苏颂受这种家风的影响,也非常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他采取的方式是多样的。苏颂之孙苏象先将苏颂平时教育后代的言语事迹汇编成《魏公谭训》,共计十卷,囊括的门类广泛,举凡国论、国政、家世、家学、文学、政事、师友、荐举、杂事等,皆有所涉猎,相当丰富多样。当然苏颂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在诗文中亦不忘训导子孙后代。如《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十四首》,此乃苏颂自述因为元丰戊午政争而遭受牢狱之灾的组诗,其中也使用了不少自注,诗序说道:“但以示子侄辈,使知仕宦之艰耳。”[6]目的在于训诫子侄能够知晓仕宦的艰难,叙述自我的仕宦态度和原委,是一个特定时间段的家族教育的展示。相较于《魏公谭训》《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十四首》,《感事述怀诗》似乎能给子孙后代一个更为简约集中地展示自我人生发展脉络的图像,子孙后代像是在听家长讲述一个将近一生经历的故事,苏颂娓娓道来,而其中的大量自注较好地发挥了叙事的功能。
长篇自传体家训诗重视叙事的表达特征,是苏颂诗歌自注特质的一个构成部分,而音训自注、辽国地域文化自注特质,亦不可缺少。
二 数量的呈现:音训自注
音训自注是中国古代诗歌自注的一种重要类型,常见的音训自注包括反切法注音、直音法注音与声调注音三种形式。最早的音训自注产生于初唐,到了中唐取得了迅速发展。据统计,初唐至大历时期的诗人中,杜甫有音训自注1处、韦应物有5 处,而后的白居易达到了47 处,元稹有35 处,杜牧有14 处[7]。白居易将音训自注数量推向了唐代的顶峰,其贡献不可忽视。
音训自注也是北宋诗人诗歌自注常见的类型之一,不少诗人加入音训自注的队伍。借助诗人别集进行统计,王禹偁至少有音训自注7 处,欧阳修至少有音训自注14 处,梅尧臣至少有音训自注6处,韩琦至少有音训自注11处,苏辙至少有音训自注4 处,黄庭坚至少有音训自注15 处,如此等等。以上几位是北宋诗歌数量存留较多,且音训自注数量相对较多的诗人。这些诗人的音训自注数量都未超过元稹的35 处、白居易的47 处。苏颂有十三卷诗歌,诗歌总量并不比以上这些宋代诗人多,但其音训自注达到了35 处,与元稹持平,在北宋处于首位,体现了苏颂对音训自注的重视。其原因值得探讨。
清代陈寿祺《重刊苏魏公文集序》认为苏颂“生平嗜学,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8]。宋代邹浩《故观文殿大学士苏公行状》曰:“自书契以来,坟史所载,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训故文字,无所不通。”[9]以上两处对苏颂的博学多识都作了充分肯定,苏颂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文章具备的浩博雄瞻风格,与其好学当有一定的关系。但综观文献资料记载,除了苏颂本人,其他人未提苏颂对音训之学的重视。以上所举《感事述怀诗》“内负未蹉跎,不能忘起偾”自注:“既知以声病黜落,遂刻意音训之学,自尔颇知字书。”[10]苏颂在十八岁参加科考时,由于未遵循声律而落选,吸取教训之后,他努力学习音训之学,且从此以后通晓该学问,当有较深的造诣。他的诗歌的音训自注特征,与其对音训之学的通晓当有较大的关联。
虽然苏颂的诗歌音训自注达到了35 处,没有超越白居易的47 处,但他在诗歌音训自注史上的开拓性仍然值得肯定。因为相较于其他唐宋诗人的音训自注,苏颂的单篇诗歌音训自注的数量多且集中。尽管白居易、元稹等人的音训自注数量较多,然而较为分散,一般一首诗歌不超过3 处音训自注,而苏颂《感事述怀诗》的音训自注数量就达到了7 处,其中包含直音法注音2 处、反切法注音2 处、声调注音3 处。尽管黄庭坚《送彦孚主簿》的音训自注达到了8 处,然而苏颂《暇日游逍遥台睹南华塑像独置一榻旁无侍卫前无香火对之歆然起怀古之思因抒长句一千四百字题于台上》(以下简称《怀古之思》)的音训自注达到了 19 处,其中包含直音法注音 15 处、反切法注音2 处、声调注音2处。
可能有研究者会指出,苏颂这两首诗歌的音训自注之所以数量多且集中,是因为它们都属于长篇诗歌,其中《感事述怀诗》为五言百韵诗,而《怀古之思》为七言百韵诗。事实上,如果将宋代其他长篇诗歌与《感事述怀诗》《怀古之思》进行比照后,会发现是否为长篇诗歌并非构成音训自注数量多且集中的必要条件。如薛田《成都书事百韵并序》虽然达到百韵,但没有一处自注,而王禹偁《谪居感事》达到160 韵,却只有音训自注3 处。这样的长篇诗歌还有相当多的数量,它们存在着这样的特点:或者没有音训自注,或者音训自注数量不多。而苏颂在单篇诗歌中,音训自注能达到19 处,说明了他自觉地开展此方面工作,是出于表达的实际需要,而不是随意为之。《怀古之思》涉及的19 处音训自注,可以简要罗列于此:“犿”自注:“芳元反”,“吊”自注:“音的”,“反”自注:“平声”,“怨”自注“平”,“睯”自注“音昏”,“”自注“音昏”,“肩”自注:“胡恩反”,“螴蜳”自注:“上音陈,下音惇”,“暖”自注:“音喧”,“踆”自注:“音存”,“汶”自注:“音门”,“芚”自注:“音屯”,“倪”自注:“音诣”,“潘”自注:“音藩”,“偾”自注:“音奔”,“暖”自注:“音喧”,“啍”自注:“音惇”,“忧”自注:“《汉书音义》,郢作忧,音温”[11]。而《次韵签判梁寺丞阻水见寄》“胶”自注:“去声”[12],《送郑无忌南归》“羽”自注:“去”[13],《次行奚山》“禁”自注:“平声”[14],如此等等。这些音训自注侧重注释生僻字、多音字等的读音与声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苏颂创新求变的倾向。如果时人能够轻易辨识,苏颂没必要大量地注释。其他诗歌的音训自注莫不如此。这些音训自注的出现,扩充了信息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诗歌正文的缺陷。
如果再把目光转向南宋诗人的话,会发现苏颂诗歌音训自注数量之多也处于领先地位。陆游的诗歌数量为宋代现存最多,但其音训自注,目之所及似未超过10 处,单篇诗歌自注数量未超过3 处。其他绝大部分的南宋诗人皆是此种情况。但杨万里是例外。杨万里极为重视音训自注,数量达到80余处,为宋代之最。但同样较为分散,单篇诗歌自注未超过3 处,且出现了多处重复自注的现象。
据上所论,或许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苏颂诗歌的音训自注数量多且集中,在北宋处于领先地位。虽然数量少于杨万里,但其单篇诗歌音训自注数量多且集中,为宋代无可比拟者,为读者理解读音与声调带来了切实的需要和帮助。苏颂推动了宋代诗歌音训自注的发展,在唐宋诗歌音训自注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三 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的书写:辽国地域文化自注
苏颂诗歌自注除了以上两方面的特征外,还具备较为全面地书写辽国地域文化的特征。
宋辽关系是北宋社会关系史上一个不可绕过的话题。在北宋长达一百二十多年的外交来往中,派遣各类使者相互进行庆贺、吊祭、攀谈等活动,成为两国的义务。北宋派遣的使臣在车马劳顿、思乡念家、关注边民、享受款待之余,还有要事在身,他们需要记录沿途的路线、应酬等情况,故而以各种名称命名的“行程录”“奉使录”“使辽录”“使辽语录”等应运而生,与之相伴的还有使辽诗。使辽诗作为北宋特有的一种诗歌题材,“皆为使者途经各地抒发感情而作,实为用诗歌体裁记述旅途所见所闻”[15],“旅途所见所闻”涉及的内容丰富,其中不乏辽国的地域文化。除了诗歌正文之外,自注亦是书写辽国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需要加以关注。“(苏颂)《使辽诗》的最大特点是通过详细的注文……为我们保存了宋辽交往的珍贵史料。这是我们所见的宋人诗歌中独一无二的贡献”[16]。这是对苏颂使辽诗自注的充分认可。虽然“宋人诗歌中独一无二的贡献”的说法言过其实,但苏颂使辽诗自注在书写辽国地域文化上的贡献应当引起重视。
尽管北宋使辽诗人不少,然而目前存留的使辽诗相较其他题材的诗歌数量不多,数量最多的苏颂,存有近60 首。在苏颂之前,余靖、王珪、欧阳修、沈遘、刘敞、刁约、王安石、刘跂等诗人都创作了使辽诗,如果就这些使辽诗自注所书写的辽国地域文化而言,可以大体归纳为以下三种。
其一,辽国的方言。余靖于庆历三年(1043)任契丹国母正旦使,四年(1044)任回谢契丹使,五年(1045)任回谢契丹使。刘颁《中山诗话》对余靖使辽的事迹作了记载,其中谈到了一首使辽诗,其云:“夜宴设逻臣拜洗,两朝厥荷情感勤。微臣雅鲁祝若统,圣寿铁摆俱可忒。”[17]其中有多处自注,“设逻”自注:“厚盛也”,“臣拜洗”自注:“受赐”,“厥荷”自注:“通好”,“感勤”自注:“厚重”,“雅鲁”自注:“拜舞”,“若统”自注:“福祐”,“铁摆”自注:“嵩高”,而“俱可忒”自注:“无极”。这些自注形同于我们现在所讲的翻译,因为里面涉及的词汇为契丹语,对于不懂契丹语的宋人来说,会有语言的障碍。此诗在《全宋诗》中名为《胡语诗》,余靖本人通胡语,以胡语创作了此首使辽诗。
其二,辽国的地理环境。1.地理位置自注。王珪于皇祐三年(1051)担任贺辽兴宗正旦使,其《市骏坊》题注:“幽州”,《杏坛坊》题注:“檀州”[18],是对市骏坊位于幽州、杏坛坊位于檀州的分别自注。刘敞于至和二年(1055),担任贺契丹国母生辰使,其《杨无敌庙》题注:“在古北口”[19],又如《古北口守岁二首》“山尽寒随尽”自注:“燕北诸山尽于此”[20],分别是对杨无敌庙、燕北诸山地理位置的注解。2.地名来源自注。如刘敞《寿山》题注:“在中京南,云多老人,往往百余岁”[21],寿山为何名为寿山,是因为此地出现了很多年过百余岁的老人。3.气候自注。刘敞《檀州》“海盖午时消”自注:“每旦海气如雾,至午消尽,土人谓之海盖”[22],当地每天早晨都会出现如雾一般的海气,到了中午便消尽,这是气候现象。4.路况自注。辽国地理环境时常恶劣,在路况上多有体现。如刘敞《铁浆馆》“别道入松亭”自注:“此馆以南属奚山,溪深险。此北属契丹,稍平衍,渐近碛矣。另一道自松亭关入幽州,甚径易,敌常秘,不欲使汉知”[23],铁浆馆周边的地理环境复杂,以南、以北呈现出不同的路况,或者“山溪深险”,或者“稍平衍”,而入幽州后,则甚径易。
其三,辽国的民俗文化。辽国的游牧文化与宋朝的农耕文化有所差别,成为使辽途中所见所闻的一个新奇内容。刘敞《铁浆馆》“奚车夕戴星”自注:“奚人以车帐为生,昼夜移徙”[24],契丹人的居住场所具有很强的移动性。
苏颂先后两次以使臣身份使辽,熙宁元年(1068)以贺生辰副使出使,熙宁十年(1077)则以生辰国信使出使。虽然他出使的时间较晚,但创作的使辽诗数量并不亚于之前的使辽诗人,并且他更加重视借用自注书写辽国地域文化,此为塑造苏颂诗歌自注特征诸种面相的其中一种面相,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其书写的辽国地域文化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其一,辽国的地理环境。1.地理位置自注。如《和就日馆》“月从双石岭间生”自注:“馆之东南有双峰山,行李将至,见月初上。”[25]注明了双峰山位于就日馆东南边的信息。又如《过土河》题注:“中京北一山最高,土人谓之长叫山。”[26]长斗山为中京山的最高山,属于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的例子还包括《发牛山》一处。2.地名来源自注。如《发牛山》“晨装方指南高外”自注:“馆南一峰最高,彼人谓之南高山。”[27]南高山,因其为馆南最高峰而得名。此外,尚有“滟水”“暗冰”等处。3.气候自注。如《北帐书事》“行天畜物密云遥”自注:“北中久旱,经冬无雨雪。”[28]又如《离广平》题注:“十二月十日离广平,一向晴霁,天气温暖。北人皆云未尝有之,岂非南使和煦所致耶!”[29]从侧面说明,广平一带在十二月份,一般是天气寒冷的。关于天气的自注,还包括《中京纪事》《北帐书事》等两处。4.路况自注。如《发柳河》题注:“十二月二十七日早发柳河,蹉程山路,险滑可惧,因见旧游,宛然如昨。”[30]由此可见,柳河的山路艰险。这样的例子尚有多处,如《奚山道中》自注:“险滑百状,每为车马之患。”[31]《和富谷馆书事》自注:“行马危险百状。”[32]《沙陁路》自注:“行马颇艰。”[33]《摘星岭》自注:“过此则路渐平坦,更无登涉之劳矣。”[34]皆是对辽地路况的书写。虽然刘敞、王珪等诗人的使辽诗也对辽国的地理环境作了自注,但总体而言,苏颂的数量更多,而且没有出现与前贤重复自注的现象。
其二,辽国的民俗文化。以上谈到刘敞对辽国的居住民俗的自注,苏颂也有所涉及,其《契丹帐》题注:“鹿儿馆中见契丹车帐,全家宿泊坡坂。”[35]契丹居住地不同于汉族,这是以车为家的反映。契丹人不仅居住有别于汉族,而且其游牧文化与汉族的农耕文化也有所不同。如《辽人牧》题注:“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36]不受束缚的羊群却繁殖旺盛。羊群如此,马群亦然。《契丹马》题注:“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马。有役则旋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番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髙下。视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翦剔,云马遂性则滋生益繁,此养马法也。”[37]契丹马平时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到了战时,却能尽显才华,驰骋疆场,这是契丹人养马的有效方法。贺威、胡延福《苏颂的科学创新思想》认为:“苏颂诗中对契丹马的饲养技术、辽人的牧羊经验……亦有科学记载和经验描述”[38],自注显然为了解饲养技术、牧羊经验提供了比诗歌正文更易理解的证据。苏颂使辽诗自注还展示了辽人的服饰文化,如《和晨发柳河馆憩长源邮舍》“免教辛有叹伊川”自注:“虏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唯巾衫稍异,以别番汉耳。”[39]汉人被辽人捕获后,不得不从辽人俗,他们削顶垂发,只是巾衫有所不同。此外,还展示了辽人的宴请礼仪,如《广平宴会》题注:“礼意极厚,虽名用汉仪,其实多参辽俗。”[40]辽人款待汉臣,虽然采用了汉族礼仪,但掺杂了契丹族的礼仪,体现了两国之间的融合。如此等等。苏颂《契丹纪事》题注:“契丹饮食风物皆异中华”[41],由上不难领略苏颂对于辽国民俗文化的书写异于宋朝的诸多方面。苏颂自注对辽国民俗文化的书写与之前的使辽诗人没有重复,即使个别得到他们的关注,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而且多为前贤未涉及者,体现了一定的扩容性。
苏颂之后的使辽诗自注亦没有达到他的高度。苏辙于元祐四年(1089)担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彭汝砺于元祐六年(1091)担任贺辽主生辰使,两人使辽诗的辽国地域文化自注也只有数处。如彭汝砺《再和子育韵》其一“昨夜先朝木叶山”自注:“木叶山,契丹九庙所在”[42],便是对于木叶山地理位置的自注。而彭汝砺《大小沙陁》题注:“北界自古北口始险阻,过小沙陁、大沙陁,即受礼处”[43],属于路况自注。如此等等。这些自注几乎是对辽国地理环境的自注,但数量和涉及面较为有限。
陈子彬《苏颂〈使辽诗〉中经过的驿馆初探》认为:“苏颂以其政治家的高度责任感,科学家敏锐的观察力和诗人的热情,通过深入生活、虚心学习,仅仅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对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外交礼仪以及人心背向等问题,有了深刻的了解。”[44]这是对苏颂使辽业绩的高度评价。苏颂在自注中对契丹马的饲养技术、辽人的牧羊经验等有着科学记载和经验描述,对地理环境的描写与勘测,体现了他作为使臣的责任担当。可能有研究者会提出疑问:苏颂之所以能够如此,与他使辽次数达到两处有关,只有一次的自然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自注。事实上,余靖使辽次数达到了三次,现存的使辽诗只有一首,而辽国地域文化的自注只有数处,欧阳修、王安石等诗坛大家的使辽诗却没有存留辽国地域文化的自注,而其他的使辽诗人除了刘敞之外,也甚少。这正体现了苏颂有意借用自注以书写辽国地域文化的自觉性。苏颂不仅对辽国地域文化有多方面的了解,而且将其记载了下来,使辽诗自注便是很好的证明材料。苏颂这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所取得的使辽诗自注上的成绩,连同在音训自注、长篇自传体家训诗自注上所取得的成绩,为说明苏颂诗歌自注的特质与地位提供了证据。
四 诗歌自注史:文学史书写的一种路径启示
以上对苏颂诗歌自注的特质及地位进行了探讨,为凸显苏颂诗歌自注在宋诗自注史上的地位提供了阐释路径,为接近诗歌自注历史原生态有所裨益。或许还可以把苏颂诗歌自注研究,再向外延展,描绘更为广袤的风景,这便是对非经典作家文学研究的思考。
目前的宋诗自注个案研究,包含莫砺锋《论陆游诗自注的价值》(《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4期)、高婉青《苏轼诗歌自注研究》(浙江工业大学2015 年学位论文)、刘青《黄庭坚诗歌自注研究》(暨南大学2016 年学位论文)、苏碧铨《论王禹偁诗歌自注的文学功能与文献价值》(《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 年第5 期)等,分别对陆游、苏轼、黄庭坚、王禹偁等诗人的诗歌自注特征进行了探讨。虽然苏轼、黄庭坚、陆游、王禹偁等宋代诗坛大家的诗歌自注研究自有存在的样本价值与典型意义,但这些耀眼的“光环”聚焦了学人过多的目光,造成了宋诗自注史上的许多诗人的缺席。如果在考察某位诗人诗歌自注特质的基础上对其作出地位评价,或许会使那些被遮蔽的诗人焕发光彩,为诗歌自注史的书写提供新的视角。事实上,如果从文学成就与文学影响来看,苏颂并不算一流的作家,这是以整体性、综合性、历史性因素所作的评估。但非一流作家的文学创造力也并非毫无痕迹。苏颂的文学创造力表现,其中之一便是诗歌自注上的成绩。这展现了其文学的闪光点,也树立了其在具有多元性的宋诗自注史上的一席之地。“在新的文学史观的影响下,对作家作品的同情式理解要重于对先验模式的机械套用,对文学史具体场景的现场还原要重于对知识素材的抽象整理归类”[45]。苏颂诗歌自注的特质与地位研究,只是众多宋代诗人诗歌自注研究中的一1,继续挖掘更多的非经典作家的诗歌自注,它们的出现将为共同“现场还原”诗歌自注史的“具体场景”,一起克服诗歌自注史书写时对“先验模式的机械套用”,应当不乏积极意义。
另外,通常的文学史研究对包括诗题、诗序、诗注等副文本关注不够,虽然近年来有所改观,但有待提升。一般的文学史书写,或以经典作家作品为对象,或以诗体为对象,或以区域为对象,或以朝代为对象,如此等等,角度多样,不一而足。但这些文学史的书写皆指向文学正文本,忽视副文本的在场。自注有其萌芽、产生、发展、繁盛、衰落等一系列演变进程,演绎此过程的并非只有经典作家,而是由海量的非经典作家的积极参与,共同推进此过程的顺利运行。梳理这些非经典作家的诗歌自注特质,是评断他们自注地位的重要前提,是书写诗歌自注史的应有之义。这些非经典作家的诗歌自注补充了在承袭因革中的细节信息,使诗歌自注史变得更为丰满鲜活。回到苏颂本身,不难发现,苏颂诗歌自注的特质,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宋代诗坛大家身上体现得并不明显,甚至缺席。以此为观照点,或许可以提供以自注为对象,书写文学史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