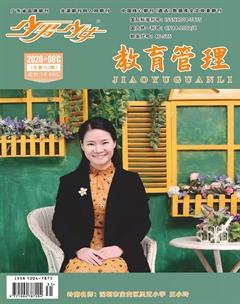从刘兰芝再嫁简析魏晋前封建社会妇女的再婚
唐远廷
摘 要:文章在分析《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再嫁”及魏晋时期其他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主要探寻魏晋前封建社会妇女再婚的影响因素:一是魏晋前仍保存母系社会的余韵,而且受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人口资源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二是在人们的婚姻观念方面,我国最早建立统一大帝国的秦朝的婚姻观念有别于中原,而汉、魏较少束缚,有较强的自由观念,以及汉武帝时期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的影响还未深入。因此魏晋前封建妇女的婚嫁观念并不是完全被禁锢,不管是现实中还是文学作品中,妇女再婚十分平常。
关键词:封建社会;再婚;再婚因素;婚姻观念
一、魏晋前封建社会妇女的再婚
读《孔雀东南飞》,很多人都不太明白一个问题——刘兰芝是被赶回娘家的“弃妇”,可回家后,却接二连三地有人来求婚,最为奇怪的是,这些求婚者还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有才有貌”的官家之子——“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刘兰芝拒绝不数日,“……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言语,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不是说封建时代礼教残酷、门阀森严,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没有自由可言,特别是婚姻,她们既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勺之言,更只能从一而终吗?那怎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儒家认为妇女“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又说“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礼记·内则》)。从这些要求看,妇女们确实行动步步束缚,毫无自由。
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并非就如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那般,也不是时时都按《礼记》要求行事,特别是魏晋之前,妇女的婚姻状况还是比较宽松——夫死妇嫁、被休之妇再嫁也稀松平常,百姓如是,官宦之家,甚至皇家也时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先看一看魏晋以前文学作品的描述现实情况。
魏晋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再嫁不但不被贬斥,很多还受到歌颂。汉乐府《上山采蘼芜》这首诗本写男人喜新厌旧,但“下山逢故夫”中“故夫”一词,说明这女人再嫁了,“故”对应的词是“现”。另一首《羽林郎》,秦汉时期著名诗人辛延年的作品,也有“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这样概括性的语言,说明二婚二嫁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怨歌行》高度概括这种现象——“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在汉代“闻君有两意”是很正常的,而“愿得一心人”就非常难得;而《孔雀东南飞》是写焦刘二人忠贞爱情悲剧的,但文中反映出来的妇女再嫁的情节也为我们提供了魏晋以前妇女可以再嫁的例证。
文学作品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在魏晋以前的现实中,各个阶层妇女再嫁或多嫁的例子也有很多。《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与酒肉之资以内妇”,一贫如洗的平头百姓陈平(还未成为丞相),妻子在嫁给他之前居然嫁了五次。另一个主角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蔡文姬,其父蔡邕也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还曾是曹操的挚友和老师。蔡文姬16岁时嫁给卫仲道,不到一年,卫仲道因病去世,后因社会动荡,被匈奴左贤王掳为王妃并育有二子,曹操统一北方,用重金赎回了蔡文姬,并把她嫁给校尉董祀。不但贫穷人家,富人官宦人家亦如是,比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人们对此津津乐道至今。《魏略》中还记录有这么一件事,曹操致使丁夫人(曹操正妻)所爱之子曹昂战死,“丁……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欲其意折。后太祖……遂与绝,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从“欲其家嫁之”几个字可知,这可是一方诸侯的曹操想岳父把自己的正夫人另嫁他人。事实上,这类事秦汉时还有更为出奇的,《史记》中记载了以下两件事,其一:“吕不韦乃……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乃遂献其姬(于子楚),姬自匿有身,至大期,生子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其二:汉有两个二嫁皇后——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汉景帝的王皇后(汉武帝为了让母亲开心,竟然亲自接来他同母异父的姐姐,并赐爵封邑),大臣和百姓均无人非议。
二、魏晋前封建社会妇女再婚的影响因素
(一)客观因素
考诸魏晋以前的社会历史,笔者认为当时对妇女再嫁如此宽容有以下因素。
第一,魏晋以前,世俗社会中还保存了母系社会的余韵。虽说世界各地母系氏族公社的典型形态,在成文史出现前已大部消逝,但其残余在阶级社会中尚存。中国社会到魏晋时期,虽说已经发展为较成熟的封建社会形态,已经远离母系社会形态,但人们的思想还未进化到跟上时代步伐的程度,母系氏族制的余韵还残留在世俗之中,特别是在当时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思想深处的东西并非可以如社会一样速度进化。
第二,受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影响。虽说从东周开始,中国逐步进入封建社会,但是在这五六百年的时间里,真正和平的时期却很短,生产力比奴隶社会得到了较大的解放,但总体上看水平还是较为低下。正因为如此,男人在家庭中的比重还不是很大,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就相对较高,加之战乱,家庭的重担更多落在了妇女们的身上,虽加重了妇女的负担,但也就相对地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因此,“汉代妇女不仅有一定的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而且还有对家庭重要事务的决策权”(贾丽英在《论汉代妇女的家庭地位》)。
第三,人口资源因素的影响。战乱时,一方面人口急剧减少,另一方面各诸侯国统治阶级急需增加人口来壮大国力,适应战争的需要;和平时,国家大片荒芜闲置的土地需要开发,以便增加粮食储存,进而增强国力。要增加人口,婚姻的开放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男性自不待言,当然也就不能过多地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了。更为重要的是,战乱时男丁战死,寡妇自然很多,如果妻子都从一而终,那人口如何增加?
(二)婚姻观念
以上是客觀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婚姻观念。
首先,最早建立起统一大帝国的秦属于“夷人”,婚姻观念有别于中原“华人”。“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但其后人殷商时代“在西戎,保西垂”(《史记·秦本纪》),他们都在远离中原的西戎一带壮大自己、藩屏周室,直到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因此,秦的婚姻观一直是开放自由的形态,而较少受儒家思想束缚。秦统一后,认为妇女再嫁是正常生活形态,统治者的观念自然而然会影响百姓。
其次,汉、魏起于低微,较少束缚,较强的自由观念也会反映到婚姻观念上。汉高祖起于底层而一统天下,身上流淌着老百姓的自由基因。曹操也出生于寒族,且与阉宦有关,他“要在汉末取刘氏皇位而代之,最为重要的是要摧破儒家豪族的精神堡垒,即汉代传统的儒家思想,然后才可以获得成功”(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反儒家那一套礼仪主张。汉代两个再嫁的皇后,曹操娶多个寡妇,并希望再嫁自己的离异之妻,这些婚姻观念对老百姓的影响可想而知。
最后一点,虽然汉武帝时代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影响还未深入人心。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目的是抑制其他思想,而不是宋明理学的那种束缚个人思维;而且“独尊儒术”思想的深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逐步改变的过程,当时汉统治者还没有来得及使之深入人心,汉代就发生内乱,儒家思想也就起起伏伏,没有能够一以贯之。
只要明白这些因素,人们就不会对《孔雀东南飞》中“弃妇”刘兰芝被县令太守之子抢着说亲的场面感到莫名惊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