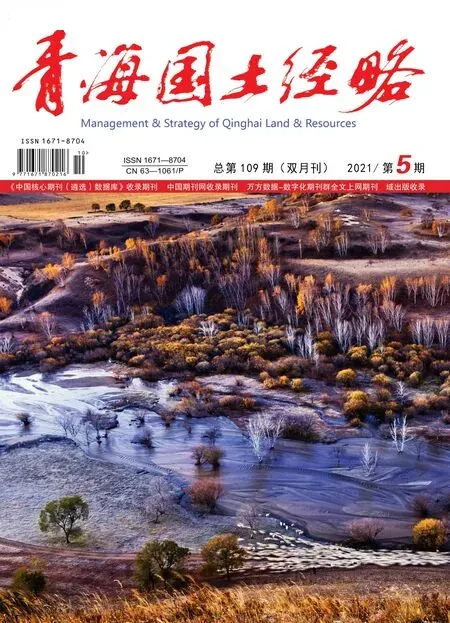雪访贝壳梁
◆ 唐 明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神奇的贝壳梁。
天气预报说天阴有雪,最低气温-7℃。
清晨七点出发,两车,五人。刚出格尔木市区东出口,雪就真的下了起来。车外,雪花慢悠悠地飘着;车内,我们心情轻盈畅美,如窗外自由的雪。贝壳梁,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诺木洪乡东南方向的一片荒漠地带,离格尔木市区130公里。据说是迄今为止我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古生物地层。
驾车的是昆仑拍客俱乐部的谢哥,后备箱里放着他的“800定焦”。摄影家李老师和他的“长枪短炮”一起坐在后排,单枪匹马的我便坐到了副驾,除了手机以外,我没有带任何可以拍摄的设备。哈哈,我大概是摄影家圈子里最资深的酱油王,常常跟着他们蹭吃蹭喝蹭风景,心里又得意又感激。
李老师是南方人,这是他第一次来格尔木,与我们同行,他看上去很兴奋,可爱地保持着一个摄影艺术家可贵的好奇心。他从车窗里看到路边成片的戈壁和沙滩,以及那一丛丛在荒原上凸起的红柳包,会不断地发问,而我们也会很乐意地卖弄似的把我们在此地生活多年的经验和地理知识告诉他。看他那开心的样子,作为地主,我们更开心,河源人都愿意感恩和善待每一位来到这片被高山和河流共同选择了的吉祥之地并喜欢这里的客人。
走过尕垭口,雪越发下得大起来。隔窗远望,远山在并不明朗的光线下,像一幅幅水墨山水图。我虽无数次看过这样的远山,但还是忍不住兴致勃勃观望,像在欣赏一位丹青高手现场作画。笔尖饱蘸水墨,手腕灵动,一笔轻,一笔重,一笔浓,一笔淡,一笔远,一笔近。清晰而又朦胧的山的轮廓跃然眼前。雾岚在山腰上缠绵缱绻,云朵在峰峦上不易觉察地轻盈游动,画面分秒之间发生着令人惊喜的变化,就像画家在不断地用水和墨调整着画面的细节,“雄山陡峭登攀岩,雾开下笔写生浓”的意境马上荡漾开来。我正盼望着,画家能够用点花青和赭石,期待欣赏到浅绛那古朴而雅致的韵味。可惜,车很快就离开了这段可以望见远山的公路。
李老师一定是走过千山万水的人,但我猜他见过的山多半是秀美温柔的,这样的山大概也并不常见吧。我们高原的山,多是没有一点遮掩的,每一个褶皱和棱角都坦露在人的视线中,真诚又坦荡。不过偶尔,就像今天,云雾缭绕,山把锋芒稍稍藏起,变得温柔可亲。李老师兴致勃勃地看着,端起相机隔窗拍下这些水墨画。
一路荒芜,让人感觉有种远离尘世的意思。直到进入诺木洪农场,看到路边的老树和路两边大片大片还没有绿意的枸杞园,方觉还在人间。这些老树的年龄大概与格尔木这座城市的年龄相仿,因为诺木洪农场大概是新居民最早生活的区域,它几乎可以见证格尔木的前世今生,有很多传说和故事。
虽然立春已有月余,但这些老树不仅没有一点春色,反而被冰雪覆盖,缀满冰雪的枝丫在半空越路交织,我们的车子行驶在树下,有种走向童话世界的感觉。仿佛路的尽头有一座神秘的小房子,幸运和惊喜在等待我们到达。
但我知道,我们的目的地不是那童话中的小屋,而是贝壳梁。那亿万年前的古海,到底在用什么样的神秘姿态在等待着我们呢?
雪,比我们先到,她已经把整个贝壳梁轻轻地拥在了她温柔而纯洁的怀里。
眼前,这道长约两公里、宽约七八十米,在薄雪的覆盖下静静平卧着的小长堤就是贝壳梁。它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一段荒芜的长堤,只是筑堤的泥土里加了无数贝壳,它的面前有一条小河,河的另一边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田格力湿地,矮草和芦苇很茂盛。这些还没有从冬的萧瑟中苏醒的草和芦苇并没有影响河的美丽,清澈的河水静静地流淌,有和贝壳梁相依相伴到地老天荒的意味,显得动人。
离得更近一些,踩上坡梁,脚下和满眼,全都是贝壳!它们失去了水,现在,只能和泥砂紧紧拥抱。它们还保持着本真的原白色,并不像电视机里放出来的水底世界里的贝壳那样缤纷,作为贝壳而言,它们实在太普通了,但它们亿万众地聚集在一起并且出现在这片荒原上,就显得那样不平凡了。
我轻轻地弯下腰,在雪地里探访贝壳,寻找亿万年前的风景。大约铜板,小约蚕豆或者更小,数以亿万计的贝壳以及贝壳的碎屑,同含有大量盐碱的泥沙凝结在一起,全都是。青藏高原本来是一片海,这仿佛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里原本真的是一片碧水浩淼的古海,如今,海水退去,这贝壳梁就是古海的遗踪,也是沧海桑田的最好见证。我们在坡梁子上走着,寻找着,惊喜着,赞叹着。
是什么原因让它们离开了水,或者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使得水抛弃了这些美丽的精灵?
李老师端着相机,各种角度取景,要拍下这令人赞叹的奇观。以摄影书上的理论,今天的光线实在不宜拍摄,但,摄影除了追求光与影的美以外,应该还有记录和珍藏这一巨大的使命。
对于贝壳梁的成因,人们有着许多猜测。很多人认为远古的柴达木盆地是一片汪洋,在造山运动中,海水消失,而海洋中的贝壳在死亡之后堆积在了这里,成为青藏高原沧海变桑田的见证。但是有记者在采访地质学专家时,他们否定了这一观点。百度上这样描述:从事过多年地质研究工作的青海省自然资源厅高级咨询委员会委员王秉贤曾经去过贝壳梁。他说,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贝壳梁做过正规的考察,但是从他们所做的初步研究来看,贝壳梁不可能是由于海洋的消失而产生的。根据古地磁性年龄来看,贝壳梁的形成是在距今约15万年前,而造山运动是在1亿年以前。同时,如果是1亿年前的贝壳,已经成为化石了,但这些贝壳与现代的贝壳没有很大区别,还没有石化,因此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准确的。他为我们这样描绘了贝壳梁的形成过程:柴达木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中由海变成了湖,在无数次旱风与干燥的交替演变中,湖水水面逐年缩小,泱泱大湖渐渐干涸露底,旱风挟着飞沙威胁水族。贝类为求得生存转向中心水洼。诺木洪北面一带是盆地最低洼处,贝类们成群结队地涌来,在古河道上越积越多。不知何时,河水改道,旱象加剧。风沙狂戾之下,贝壳们全部灭绝,只留下贝壳的堤墙,挡不住水退,挡不住死亡,只有从贝壳缝隙间涌出的泉水,汇成一弯细流诉说着远去的历史。
我们本土的文化学者程起骏先生在《瀚海天堂柴达木》一书里也有一篇关于贝壳梁的精彩论述,对于贝壳梁的形成,他有自己的观点,他说贝壳梁可能是由一股神秘的外部力量造就的,并分析了原因。
学者和专家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去发现和解读大自然的秘密,可敬可爱,但我们这些普通人,走到看到感受到,似乎就已然满足,并不做过多的深究,显得浅薄,但谁能说这样的浅薄不能收获别样的美好呢!
慢慢地走,突然,听到自己轻笑的声音。想像着这些贝壳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它们还活着,那么我脚边就有成千上万的贝壳的眼睛和灵魂,它们大概正好奇地研究这双脚以及生着这双脚的这个女人——她是做什么的?她为什么来这里?说不定有一只最爱睡觉的懒贝壳,它也许还有一个可爱的名字,沉睡了很多年,却被我的到来扰醒,它很不情愿地睁开半只眼睛,想看看这个烦人的家伙是谁,却意外地惊慌失措起来,哎呀,我在哪儿?水呢?我怎么不在海底?
想到有一只懒贝壳被我扰了清梦,想到它那满脸的惊慌、睁着圆眼睛不明就里的模样,我就笑出了声。我走得更慢、更轻,生怕惊醒更多的贝壳、更多的鱼、更多的珊瑚,或者更多的正游动着的精灵。
雪渐渐停了,天色灰暗,我看到低空有成群的鸟儿飞过,从飞鸟的体形和叫声判断,应该是潜鸭、赤麻鸭之类的水鸟,我猜想可能还有天鹅,因为近年来到格尔木市周边水域越冬的天鹅多处都有,这里离诺木洪湖很近,鸟儿们应该是在那里栖息的。向远处望去,我想象着“绿波迢递雪纷纷”的模样兴奋不已。谢哥和李老师要去找最好的拍摄位置和风景,而我只想顺着鸟叫的声音去看天鹅在芦苇荡里“澹然游清池”的芳姿。下了贝壳梁,我寻着鸟鸣的方向去,希望能够找到鸟儿们栖息的湖。
除了几片在雪地里遗落的羽毛,我没有看到水鸟或者野鸭,更没有见到天鹅。因为我要穿过这片荒原才能到达远处的水边,但,草边上拉起了望不到边的铁丝网。
听谢哥说,相关部门已将贝壳梁列入旅游总体规划,将在这里兴建旅游区,以便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柴达木盆地的地质演变,也更好地保护这一古生物遗迹以及这里的野生动物和水鸟。贝壳梁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人来探究一下的奇观,还有很多人说曾在这里看到海市蜃景,极为神奇。程起骏先生也说过“贝壳梁是诺木洪文化的发祥地,这一带曾经出土过我国最早的元代纸币,而且有许多动人的神话传说。所以,贝壳梁地区的旅游价值极高。”我自然也希望世人都能来领略我们高原的美和神奇,又担忧旅游者打扰了这些藏着深海灵魂的贝壳们的安宁,心里竟然充满了对贝壳梁的担忧还有淡淡的伤感。
离开贝壳梁,我们准备继续向东,穿过田格力湿地再到克鲁克湖和托素湖去探望这两位深情而美丽的有情人,却发现原来走过的路不通了,也围了铁丝网。大家都有些扫兴,但转念又觉得,这世间的事,无非是这个样子,十之八九不能圆满,留下点小遗憾仿佛才更对。听到了鸟鸣,却见不到鸟的身影;想象到了情人湖的悽美,却到达不了他们身边;人生,莫不如是。
当车调头转身之时,再次深情回望贝壳梁——一块寂寞的大石上刻着“贝壳梁”三个红色的大字。平淡而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