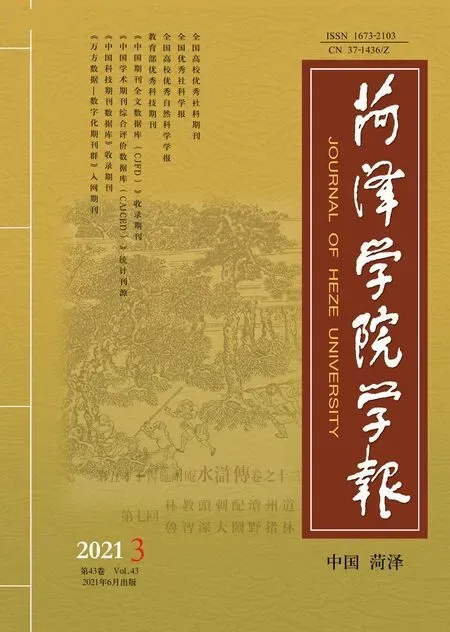明清文人与曹州牡丹传播*
潘守皎
(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菏泽 274015)
曹州栽培牡丹的历史十分悠久,然自明清以来,曹州牡丹才日渐赢得世名,并奠定了曹州此后几百年牡丹培育和销售中心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孜孜于牡丹培植而不辞劳苦的花农当然是主角,他们栉风沐雨,团屋而居,为培植牡丹名品竭尽心力。然而,促成天下士庶为曹州牡丹魂绕梦萦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就是明清两代喜爱牡丹的文人。正如唐代长安牡丹招致六陌街衢车马涌动,宋代洛阳牡丹吸引天下文人驻足一样,明清曹州牡丹名扬天下,也离不开两代文人的宣传推广。
继唐代长安、北宋洛阳之后,明代以来牡丹培育和种植的中心开始转向黄淮地区,此时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就是曹州和亳州。这两个地方在牡丹栽培和种植方面曾经各领风骚,两地在牡丹培植方面的交流也非常活跃。不过,从文献记载来看,在明代中期至清中期以前,牡丹培育和输出的真正中心还是曹州。
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明代谈牡丹者,往往曹州、曹县不加区分,这其中是有缘由的。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明清曹州行政区划的演变。曹州在明清两代的行政区划差别很大,州治也不断变化,两者不能等同。明初曹州所辖不过济阴、定陶和楚丘三县,洪武四年(1371),甚至降曹州为曹县,曹州原来管辖的济阴、楚丘也并入曹县,曹州州治也经历了“乘氏—安陵镇—盘石镇—乘氏”一番轮回。明正统十年(1445),曹州复置,辖曹县、定陶二县[1]。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在谈到明朝曹州牡丹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指曹县牡丹。清朝初年,曹州仍袭明制,辖曹县、定陶二县。至雍正二年(1724),升曹州为曹州府,附郭菏泽(原乘氏县,今牡丹区),辖定陶、单县、曹县、钜野,莘县,鄄城、范县、城武、郓城、朝城10县及濮州(州治山东鄄城县旧城镇)1个散州,行政管辖区域大大增加。此时人们再谈论曹州牡丹的时候,更多的是指菏泽(原乘氏县,今牡丹区)了。
明朝初年由于战乱、河患和人口的变化,曹州牡丹栽培并没有多大规模。明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增长,曹州牡丹种植得到长足发展。嘉靖、万历时期,曹州牡丹已经广为知名,天下欲得牡丹名品者,多亲自或托人往曹州求购。而在曹州牡丹日渐繁盛并赢得世名的过程中,除了辛苦的花农,明清两代文人的宣传褒扬,功莫大焉。
明清两代文人在曹州牡丹传播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筑园建圃 培育新品
一个地方的牡丹赢得世名,离不开牡丹园林的建设以及新品的培育。因为园林是牡丹赏玩的主要去处,又是新品培育的基地。依照文献记载,牡丹进入私第,当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算起。段成式《酉阳杂谈》记载,开元末年,郞官裴士淹奉使幽冀,在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园中,成为天宝年间长安城里的一大景观。唐玄宗时期,杨国忠得到皇家御赐牡丹,并精心加以养护,文献称其奢华艳丽超过皇家。此后,屡见中唐以后诗人写到私家园林中的牡丹,如刘禹锡的《浑侍中宅牡丹》《唐郎中宅与诸公饮酒看牡丹》,白居易的《微之宅残牡丹》等,都写到在私家园林中品赏牡丹的情形。
曹州牡丹从明朝开始兴盛,当时的曹州人是把牡丹当作一种经济作物来栽培的。明朝谢肇淛就在他的《五杂俎》中描写曹州家家户户都种植牡丹,接畦连陌,像种菜一样。不过,若论新品的培育和驻足赏玩,牡丹园林又必不可少,于是,一些致仕的官员以及地方爱花的花农,便开始筑园建圃、种植和培育牡丹。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园子培育出各色名花,使得曹州牡丹闻名天下。
曹州的牡丹园林究竟肇始于何人何时,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依据记载,至少从明朝广泛种植牡丹以后,这里便先后涌现出众多著名牡丹园林,当地人称之为“花园子”。在这些花园中,由于有文献佐证,赵氏花园、方花园、何家花园(凝香园)、王花园等更为有名。
赵氏花园位于今菏泽城东北曹州牡丹园内,其渊源始于明宣德(1426—1435)、景泰(1450—1457)年间。即使按薛凤翔《亳州牡丹史》所载,赵氏牡丹盛于明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年间,这也比亳州牡丹早了很多年。《亳州牡丹史》中说:“德、靖间,余先大父西原、东郊二公最嗜此花(按:指牡丹),遍求他郡善本,移植亳中。亳有牡丹,自此始。”[2]按照薛凤翔的这个说法,亳州牡丹种植始于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这个时间也是晚于天顺、成化的。即使考虑到薛凤翔这种说法可能有抬高自己先人的用意,那么,在此之前,亳州也可能没有牡丹种植的标志性人物和园林,否则,薛凤翔不可能视而不见。
属于赵氏花园体系的还有桑篱园和铁藜寨花园。曹州赵氏花园不只起步较早,其园主及园艺的传承也一脉而下。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先后有赵邦瑞、赵邦宁、赵瑞波、赵克勤、赵玉田和赵世学等。他们培育出闻名天下的“乔家西瓜穰”“倚新妆”等品种,移栽亳州。其“新红奇观”“叠雪峰”“千叶白花”等八种牡丹均为曹州神品,皆出自赵园,亳州薛氏欲购而不得。至清乾隆末、嘉庆及道光年间,园主赵玉田培植牡丹近八十年,育出多种牡丹神品,如“天香独步”“种生红”“种生花”“赵红”“赵绿”“邦宁紫”和“骊珠”等。《新增桑篱园牡丹谱序》云:“赵氏园牡丹二百余色,牡丹一种,驰名四海;赏花诣君子,北至燕冀,中至苏杭,言牡丹者,莫不谆谆乎于我者焉。”[3]
方花园一般认为是曹州官府花园,时曰公署园。万历九年至十三年,南直隶徽州人方复乾任曹州知州,时人称公署内花园为方园。在今天菏泽城区八一路菏泽一中旧院内东北角。方园牡丹曾多次出售移栽亳州,《亳州牡丹史》称亳州牡丹之“飞燕妆”“方家银红”等花“得自曹县方家”,可证曹州方家牡丹名品之多。据统计,《亳州牡丹史》中提到的牡丹名品有二十种来自曹州,当然不只是方家花园。薛凤翔在提到这些花的时候,有时说来自曹州,有时说来自曹县。
王氏花园位于曹州东北王梨庄,据谱牒文献等记载,嘉靖年间王氏十代祖王猛由平度县李子园迁此建村,并种植牡丹,现古今园址即是。清乾隆间(1736—1795),王氏十二世王孜诵是曹州著名花师,对牡丹园经营有方,其创制的松编牌坊至今仍在。后来同辈人王孜唯在青松牌坊两边各做松编狮子一尊、松阁二层,正面编六只狮子、二只仙鹤;又在背面编二只狮子,成为该园特色,至今犹存。同治间,王氏第十七代王惫昌善养牡丹,使牡丹传遍大江南北,又从广东引回两棵线柏,生长至今,成为江北珍贵名木。
何家花园原系袁氏园,约百余亩,位于今岳程办事处岳楼村南。天启年间,曾为御史中丞的定陶西台集人何尔建,从袁氏手中购得此园,成为何家花园的第一位主人,名其园曰“正春园”。何尔健之子何应瑞,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崇祯间宦游归里,何园已经变得繁花如锦,香溢四野,因又名该园为“凝香园”,时人俗称何尚书花园,简称何园。该园所育之“何园白”“何园红”,早在明末已誉满曹、亳、洛阳等地。
毛氏花园在城东北今曹州牡丹园南部的毛胡同,于明代万历年间建园,约五亩。民国时,“五世名医”毛景瑞为园主,园内牡丹花大而艳,其中黑牡丹“黑花魁”“种生黑”等为明代以来珍品,更有姚黄牡丹树一株,高与人等,花近百朵。清初“四大布衣”之一的黄子云(1691—1754)曾造访过毛氏园,留下了《毛氏园观牡丹》:“十亩芳菲园,名花最后看。乍疑春欲醉,可爱露难干。倚日自矜宠,回风不受寒。药阑频徙倚,吟望夕阳残。”[4]
其他牡丹名园还有城南绮园,城东张园、王氏园、陈氏园等,其园主多为进士或官宦,花园或大或小,多各具特色。如城南绮园,占地五亩,中间有南北小径,两旁尽植牡丹,株距五尺。道光年间,花开之日,游客终日不断,园主晁国干著有《绮园牡丹谱》。
这些花园大都坐落于曹州城北、城东,每至阳春,繁花似锦,连绵百余里,犹如花的海洋,为鲁西、豫东之大观。这使得明清以后,曹州成为牡丹种植和观赏的新基地。清光绪年间《菏泽县志·物产》云:菏泽“花卉之繁,凡他邑所有,其数略备,牡丹、芍药等各百余种,土人植之动辄十百亩,利厚于五谷,每当仲春花发,出城迤东,连阡接陌,艳若蒸霞。土人捆载之,南浮闽、粤,北走京师,至得厚值以归故,每岁辄往。”[5]
二、吟诗作赋 记牡丹风雅
一个地方的牡丹赢得世名,还离不开文人的诗赋歌咏。明清以后曹州牡丹渐渐声名远播,文人的赋咏歌唱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些文人中,有曾任高官又作为当地牡丹园主的苏祐、何应瑞,也有清初的宰执大臣冯溥、陈廷敬,还有曾经担任过山东学政的钱宰、李中简,另有任职曹州的地方官员和一些向往曹州牡丹的朝野雅士,如王曰高、吴景旭等。
苏祐(约1493—1573),字允吉,一字舜泽,濮州人。嘉靖丙午年(1526)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晚年归隐乡里之后,种花自娱,以含饴弄孙为趣。他曾经留下一首《南宅内牡丹》的小诗:“载启花朝宴,中楼锦瑟张。高才非李白,异品有姚黄。日映疏疏景,风传冉冉香。言承环膝喜,春在含孙堂。”[6]苏祐还有一首《从弟宅内牡丹》诗,借咏花道出了宦海奔波的劳苦以及归乡与家人团聚的兴奋:“去年花下姑苏客,今日尊前季弟拚。芳草池塘非昨日,故园月色好同看。东篱谩想陶潜菊,南国虚传屈子兰。但使常依春作主,终将持献玉为盘。”[7]何应瑞(?—1646),字至符,为曹州牡丹名园“凝香园”第二代园主,崇祯间宦游归里,看到园中新品迭出、繁花如锦,遂与乡贤相约赋诗:“廿年梦想故园花,今到开时始在家。几许新名添旧谱,因多旧种变新芽。摇风百态娇无定,坠露丛芳影乱斜。为语东皇留醉客,好教晴日护丹霞。”[8]
由于明清时曹州牡丹天下知名,一些文人雅士也越来越关注曹州牡丹。于是,有的曹州人以牡丹作为风雅礼物馈赠亲友,而一些朝里官宦和外地文士也以得到曹州牡丹为荣,并设法罗致。向曹州人索要牡丹这样的事情,明朝中期就已发生,到清初此类事则更加普遍。试举几例如下:
冯溥(1609—1691)为康熙年间刑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冯氏73岁致仕后,加太子太傅,后返归青州故里。闻听曹州牡丹天下有名,曾向曹州刘兴甫索要。刘兴甫不辞劳苦,封裹后亲自奔波千里送至其府上,冯溥作《喜曹州刘兴甫送花》记载了这件事情:“君家近洛阳,名花实繁夥。我乞数株栽,君云无不可。不惮人力劳,千里亲封裹。策蹇君自来,惠我数百棵。”[9]
陈廷敬(1638—1712)为清代著名宰相、学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担任《康熙字典》总撰修官。陈廷敬与冯溥相比,虽是晚辈,但曾与冯溥同朝为官。当作为曹州佐吏的老部下向云泽亲自送来曹州牡丹的时候,他喜不自胜,作成小诗《向云泽自曹州以牡丹见遗赋答》,以示感谢。康熙年间的另一位大臣汤右曾也曾求得曹州牡丹,很高兴地作诗记其事:“种自曹州寄,名仍洛下来。东风相欺得,芍药出丰台。”[10]
可见,由于文人对曹州牡丹的推崇,它已经成为师友相馈的重要礼物。甚至有人以不能得到为憾。康熙年间浙江吴兴人吴景旭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令他遗憾的事情。好友臧受澄住在曹州,为他寻得十种牡丹名品,但由于归期无望,不能及时带来,让他望眼欲穿:“偶阅前贤谱籍中,最称曹县状元红。杏坛近得春为主,梓里遥将富此翁。迢递莺花虽阻绝,依稀鹿韭尚成丛。如今白舫无多路,早晚迟君颂酒功。(自注:岁庚中,臧受澄客曹南,觅十本将见遗,惜归期逗留不及携来)”[11]
对于曹州牡丹赞誉有加并赋诗吟咏的,还有那些曾经饱览曹州牡丹的朝野名士和在山东以及曹州任职的地方官员,如王曰高、陈燮、李中简和钱载等。
王曰高(1628—1678)曾为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后官至礼部掌印给事中。王曰高曾作过很多首曹州牡丹诗,他在《曹南牡丹四首》其三中写道:“洛阳自昔擅芳丛,姚魏天香冠六宫。一见曹南三百种,从今不数洛花红。”[12]诗中说洛阳的牡丹自古以来就曾经独擅芳名,尤其是姚黄、魏紫。可是,如今看到曹州新培育出的无数名花,洛阳的牡丹就再也不值一提了。乾隆间闽籍名士陈燮两度行经曹州,最让他难以忘怀的就是曹州牡丹,在《题余雪村曹州牡丹谱后》其三中,他把花开遍地的曹州称为“胭脂国”,并表示如果再来曹州,一定要徘徊花前,“一日花前一百回”[13]。
当然,也有人因为经行曹州而没有赶上花期感到遗憾。浙江嘉兴人钱载(1708—1793),乾隆朝担任礼部侍郎,是秀水派代表诗人。在担任山东学政时曾造访曹州,但钱宰来时已是绿树城深、子规啼叫的夏日,牡丹花期已过。他只好赋诗感叹:“屡与花期屡后期,花天况复妒风姨。苍苔小院飞蝴蝶,绿树深城叫子规。酒散独依斜月坐,春秾犹属老年思。村村姚魏家家诧,郑重何人折几枝。”(《至曹州牡丹花期已过》)[16]
三、为记作谱 述牡丹源流
一个城市与牡丹关系的确立,还离不开一些文人写作的牡丹谱录。这些谱录能够让人了解一个城市以及一个地区的牡丹之盛,以及牡丹栽培的历史和渊源,并能够展示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风俗和文化。正如洛阳牡丹天下闻名,得益于欧阳修写作《洛阳牡丹记》加以褒扬,天彭牡丹后世知名,离不了陆游的作谱功劳。明清以来,曹州牡丹之所以为人熟知,苏毓眉、余鹏年等人写谱作记功莫大焉。
关于曹州牡丹的谱录出现较晚,但它们对于当时曹州牡丹盛况的记录,足以让天下人记住曹州牡丹。这些流传的牡丹谱录主要有康熙年间曹州儒学学正苏毓眉的《曹南牡丹谱》、乾隆年间曹州重华书院教习余鹏年的《曹州牡丹谱》、道光年间赵孟俭原著以及宣统年间赵世学增补的《新增桑篱园牡丹谱》。除以上谱录之外,在此前后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计楠的《牡丹谱》都涉及到曹州牡丹。薛凤翔《亳州牡丹史》中提到的牡丹名品,出自曹州的有20种左右,计楠《牡丹谱》中所列他们家103个牡丹品种,其中曹州名品19种。
撰著《曹南牡丹谱》的苏毓眉为山东沾化人,顺治十一年举人,康熙七年担任曹州儒学学正。苏毓眉善画山水,能为歌赋,曹州大地很多处都留下了他的作品,如《曹州八景》《雪霁园十景》等。《曹南牡丹谱》篇幅不长,但根据其亲身所见,描绘清初曹州苑囿遍布的盛况:“新花异种,竞秀争芳,不止于姚黄、魏紫而已也。”而且,各园牡丹“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数百株”,“即古之长安、洛阳,恐未过也。”[17]
撰著《曹州牡丹谱》的余鹏年,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人,乾隆年间举人。他于乾隆五十六年来到曹州重华书院任教,当时担任山东学政的清初大诗人翁方纲次年来曹州督学试士,嘱咐他一定要撰著一部曹州牡丹的谱录,他遵嘱两个月便完成了书稿,翁方纲阅后专门作了三首七绝以嘉其事。余鹏年所著《曹州牡丹谱》历数牡丹花谱源流以及曹州著名花品,并在最后讲述牡丹栽培技术的时候,特别注意结合实践,不盲从古人书本经验,道出了牡丹栽培要因地因时制宜的道理。
撰著《新增桑篱园牡丹谱》的赵孟俭和赵世学,原本是曹州著名牡丹园桑篱园园主,精通园艺,培育出很多著名品种。该书把牡丹分为黑色、黄色、绿色、白色、紫色、红色、粉桃红色、杂色8类,已基本等同于今天牡丹9色的分类。桑篱园共有牡丹200多种,尤其有黑色9种,超过其他任何牡丹谱录中关于黑牡丹的记载。可见,赵氏桑篱园非常善于培育黑色牡丹。赵世学一生专注于牡丹新品的培育,受到地方官员的高度称赞。
其实,为曹州牡丹撰著谱录的不只以上诸人,另有一些诗人以特殊形式撰写曹州牡丹花谱。这些谱录以及具有谱录意义的诗歌,则是曹州牡丹谱的另一种特殊的补充形式。如王曰高用诗写就的牡丹花谱,咏赞了红色、浅红、绛红、白色、粉色、浅粉、淡粉等诸色牡丹10品;晚清曹州知府赵新的《杂咏牡丹》也是一种特殊的曹州牡丹谱录,这组诗描述了姚黄、魏紫、豆绿、墨魁、冰清、梨花雪、一品朱衣、葛巾紫、红巾、掌花案、瑶池春、花牡丹12种名品的形貌特征。诗人在这组诗的序文中说:“菏泽牡丹不下百余种,此仅取其一二耳”,显然有以诗为谱的寓意。特别令人注意的是,这组诗每首之后都有一段注释,除了描写该种牡丹的独特之处以外,还道出该花得名因由,正是牡丹谱录的应有内容。如《姚黄》:“花王应被赭黄袍,色似初春柳散绦。曹国竟同燕国侈,熔金新筑一台高。旧云:牡丹黄者皆单瓣。予在曹所见如姚黄、御衣、黄金轮之类,无不起楼有高五六寸者,非独佳种,亦培植得宜也。第此花不甚受水,插瓶即萎。或者其品甚高,不肯供人耳目之玩,与花之有品而自重者尚如此。”[18]
赵新还特别关心牡丹种植,并经常光顾牡丹园看望花农。赵孟俭是道光以后桑篱园主人,一生守贫莳花。赵新来到桑篱园,看到赵孟俭不问世事,身居团焦陋榻,专心培育牡丹,犹如庄周再生,于是感慨莫名,连作四首诗赠送给他。其一云:“此老无惭市隐名,莳花真可当春耕。前身合是庄周蝶,安稳香中过一生。”[19]
在整体调研中,43.04%的研究生认为要想提高新生入学教育或活动质量需要深入新生进行调研,了解新生的真实需要;39.37%的研究生觉得要开展形式多样、吸引力强的新生活动;10.5%的研究生认为要注重思想的引导,7.09%的研究生认为要增加时代气息的教育内容。调研访谈中研究生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同样具有花谱和花史意义的还有顾嗣立的诗《曹县》和刘大绅的《牡丹行》。顾嗣立诗中说明了随着时代的变迁,牡丹种植的中心已经由洛阳转到曹州:“牡丹数洛阳,花谱佳名富。迩来地气迁,曹南为独秀。”[20]刘大绅则指出,陆游之所以大肆夸赞天彭牡丹,是因为他没有到过曹南(即曹州)的缘故:“洛阳花事既消歇,天彭亦号小西京。当时中原已沦没,南人未到曹南城”。他的《牡丹行》的诗注中,还提到乾隆年间的河患对曹州牡丹的摧残:“志言曹州牡丹甲于天下,乾隆年间,黄河漫溢,少不如前。”诗中还描写了滔天洪水的巨大破坏力,以及洪水过后,牡丹花事不如以前的情况:“灵犀奋勇毒龙怒,洪涛一鼓翻长鲸。青畴绿壤卷入水,草木非敌难为勍。嗟我不才从事晚,春风到日花间行。眼中犹见十余种,醉倚酒甕听流莺。”[21]
四、作文修志 记牡丹之盛
曹州牡丹之所以不知渊源于何时何人,在于缺乏文献记载。但嘉靖、万历之后,牡丹培育、种植、销售信息渐繁,实有赖于文人慕牡丹雅赏,并作文修志以记之。明中期德州临邑人邢侗,在一封信中谈到他对曹州牡丹的渴慕。邢侗明万历二年进士,官至湖广参议、太仆寺少卿,他雅好花赏,曾于自家园中种植芍药数亩,唯独因为园中缺乏千叶楼台牡丹为憾,便写信托人搜求曹州牡丹。他在《与王士龙书》中称,“曹有王五云先生,家多异蓄,于牡丹尤富。”[22]
信中提到的王士龙,名为王五云,与邢侗同为万历年间人。王氏有牡丹园五十亩,种牡丹六七百种,是当时曹州培育、种植大户。邢侗信中说王五云家里的牡丹极为富有,以至于在灶间与烧柴并用,家畜与家禽胡乱啃食牡丹也无人管束。他想象自己若能将王五云家里的牡丹移栽过来,“曲阑小树,杯酒淋漓”,自是人生一大快意之事。邢侗同时的另一位明朝官员谢肇淛则在他的《五杂俎》中记载了万历年间曹州牡丹的普及,并描述了当地花农像种菜一样种植牡丹的情形。
这些人虽然没有记载曹州人为什么会想到种植牡丹以为生计,也没有记载曹州牡丹从何而来,但字里行间对曹州牡丹种植的普及以及培育的用心还是有全面的反映。曹州人种植牡丹的事情,也使得地方官员引以为傲,并经常夸示别人。明万历曹州兖西道佥事胡廷宴就在他的《兖西道公署园亭记》中说:“曹故饶于牡丹。诸亲友觅曹南土物,吾即夸牡丹之繁,园亭之盛。”这篇记文写出五百年前曹州牡丹之盛,也说明在当时,牡丹就已经成为曹州的象征了。
当然,以上文人没有关注曹州牡丹的源流,这样的遗憾在后代文人所撰修的方志之中虽然略有弥补,但在考析曹州牡丹来龙去脉方面仍然有很多没有辨析清楚的问题。
明万历《兖州府志》云:“曹州唯士人好种花树牡丹,红药之属,以数十百种。”[23]这里只记载了曹州人种植牡丹、芍药的品种规模。清康熙《兖州府曹县志》中记载得较为详尽,并且通过该志的记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至迟到了清朝初年,天下牡丹盛事悉归曹州的事实:
尝考洛阳《牡丹谱》及欧阳文正公《牡丹谱》,不逮《亳州谱》远矣。彼时已有六七百种,分五色,排次序。至于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县距州仅百里,当昔盛时,而姻亲往还,童仆连络,故佳艳时,获怡赏,亦重价多相购置。李悦心诗云:“生憎南亩课桑麻,深坐花亭细较花。闻道牡丹新种出,万钱索买小红芽。”盖实录云。[24]
以上朱琦所撰《兖州府曹县志》中说,他曾经认真考证过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谱》以及其他洛阳《牡丹谱》,它们都没有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记录详尽。亳州牡丹盛时,已经有六七百种牡丹(按:薛凤翔《亳州牡丹史》之《表》部分记牡丹6品271种,未有六七百种),康熙年间,亳州牡丹花事渐渐消歇,而曹州牡丹日益天下闻名。
《兖州府曹县志》的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明中期以来的亳州、曹州等地牡丹并盛的时期,已经由曹州牡丹独盛所代替。正如明《兖州府志》云:“曹州唯土人好种花树牡丹,红药之属,以数十百种。”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刊刻的《曹州府志》卷七《风土》云:“曹郡……花卉之数,他方所有,大抵略备。牡丹、芍药为名品,江南不及也。”[25]
二是曹州人不只大量种植牡丹,而且还大量输出牡丹,成为名副其实的牡丹传播中心,这也是时人所谓“曹州牡丹甲于海内”的事实依据。康熙朝文坛领袖王士祯云:“今(清初)牡丹河南惟许州,山东惟曹州最盛,洛阳、青州绝不闻矣。”又云:“曹好走牡丹,品种甚多,先祭酒府君(王士祯父)尝往购得黄、白、绿数种。长山李氏独得墨牡丹一丛,云:曹州止诸生某氏有之,亦不多得也。”[26]这些情形,在清初一些文人关于牡丹赠答的诗作中同样得到印证。
总之,通过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明清两代文人对于曹州牡丹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些人中,无论是那些风雅的花农或致仕归里的官宦,还是来此地为官或者行经此地的文人,抑或是那些高居庙堂不曾来过曹州的人,他们对于曹州牡丹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喜爱和向往。他们或筑园建圃,或吟诗作赋,或为记作谱,或作文修志,为曹州牡丹的传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廿年梦想故园花,今到开时始在家”,曾经宦海漂泊的何应瑞看到故园牡丹的时候,感觉到的应是一种心灵的回归;“可能重访胭脂国,一日花前一百回”,乾隆间闽籍名士陈燮发誓再来的时候,一天要在花前徘徊一百次,表达的是对曹州牡丹的缱绻不舍;“寄语旧游崇敬侣,三生缘证一丛花”,曾经担任山东学政的李中简更是把看到牡丹视为三生的奇缘;久居庙堂之高的陈廷敬也免不了在看到牡丹之后而露出青眼:“春风料峭几枝斜,秾艳依然带露华。”[27]
今天,牡丹成为菏泽一张亮丽的名片,牡丹文化传播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大力发展牡丹文化旅游的同时,在科技手段的支撑下,发展牡丹产业也成为振兴当地经济的一条新的路径。2013年4月18日,国家林业局在菏泽召开了全国油用牡丹产业座谈会,对牡丹的产业研发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自2019年4月12日始,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中国花卉协会主办,菏泽市人民政府、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会承办的世界牡丹大会,每年在菏泽召开。大会以“美丽、健康、创新、发展”为主题,把新时代的牡丹文化传播带入更高、更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