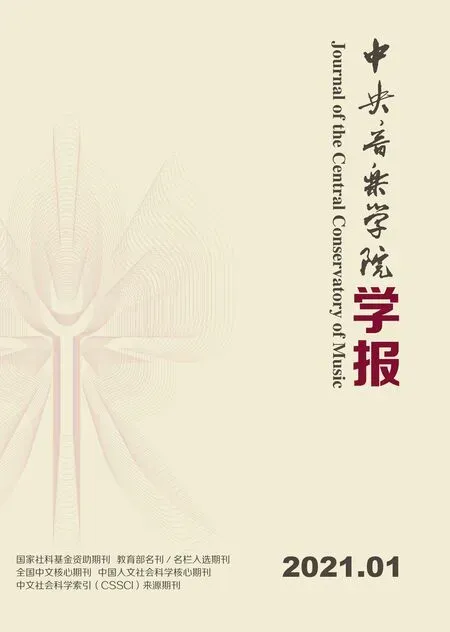新中国70年音乐创作中的中西多声思维碰撞与融汇
刘康华
“中国的音乐如同中国文化一样正处在两条河流的交流点,它将不再是从前的河流,而是一条新的河流。在这条新河流中融合有老河流的水和另一条河流的水。我们的‘国粹’不会失去,反而令我们获得更可宝贵的‘国粹’”。这是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先生早在70多年前(20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在《中国新音乐的方向》一文中高瞻远瞩的话语,其洞若观火的学术视野以及深刻的学术内涵至今仍使我们感到震撼与鼓舞。
纵观百年中国音乐创作中和声的运用,正生动地体现了马思聪先生的上述判断。这是一条由和声运用中的中西多声思维碰撞与融汇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河流”。这“洋为中用”的百年探索与实践,在逐渐趋于成熟的历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犹如无数条小溪聚成江河,至今仍奔流不息。
自从20世纪初我国最早出版的钢琴曲开始运用和声以来,西方的和声理论与技法传入我国并在国人的音乐创作中被实际运用,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源自于西方的和声理论与技法,以其自然音响原理的客观可依,以及人文艺术表现的丰富多彩,被许多东方民族所借鉴吸收,我们中华民族也不例外。然而消化过程中的‘水土不服’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需要中国作曲家展示其艺术智慧并通过创造性的艺术实践来探索解决”。(1)刘康华:《和声运用中和弦结构的风格化处理(下)——论纯五声和声材料的构成、运用思维与处理技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46页。我们在借鉴西方和声理论与技法的同时,吸取了我国民间音乐的多声思维与实践特点,从而形成了中西多声思维的碰撞与融汇。下文重点阐述百年中国音乐创作中后70年(新中国70年)的有关内容(前30年笔者已另有撰文(2)刘康华:《探究我国早期音乐创作中和声运用的民族风格问题》,《音乐研究》,2020年,第2期。)。
一、碰撞的起因及实质
1.碰撞的起因——新音乐创作对发展多声思维的需求
中国新音乐是指,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与中国传统音乐相比较而言的新的音乐形式,“学堂乐歌”是当时新音乐最初的典型。1919年的五四青年爱国主义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先河,同时也将新音乐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重要标志是专业音乐创作的兴起。一批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音乐家,开始摆脱旧曲填词的学堂乐歌形式,用本国前所未有的新的音乐形式来表达国人的思想情感。这种新的音乐形式是学习西方作曲技术“洋为中用”的结果,其中又以借鉴西方的和声理论与技法,发展我国音乐创作中的多声思维,力图以更为丰富的音响与艺术表现力来展示作曲家的乐思为主要特征。
专业音乐创作的最初实践者赵元任在1927年的《新诗歌集(文字部分)》中就直言:“中国人要么不做音乐,要做音乐,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就是得用和声。”(3)赵元任:《赵元任歌曲选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46页。40年代王震亚先生仍是重庆国立音乐院作曲学生时,与同学们一起以《山歌社》的名义学习研究民歌,为民歌配伴奏,立志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他在创作实践中深有体会地说:“要发展中国音乐,就必须运用和声。新的时代里,音乐将会飞跃的发展,解决中国音乐的和声问题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4)王震亚:《五声音阶及其和声》,上海:文光书店出版,1949年,“序言”。可见,从新音乐创作来讲,迫切需要和声;从发展新音乐理论与音乐教育来讲,更需要和声。
从史料上看,20世纪10年代我国音乐界的有识之士曾出版过介绍和声学基础知识的书(如1914年高寿田译述、曾志忞校订的《和声学》),但真正将和声学引入专业音乐教育、推动新音乐创作发展的,当属20年代起萧友梅先生与黄自先生的音乐教学活动。
20世纪20年代初,萧友梅先生就在北大音乐传习所主讲了和声学课程。不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设了音乐体育专修科(任主任),后来又在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职,均教授过和声学,期间编著了《和声学纲要》,并在实践中逐步将其充实完善,后更名为《和声学》。1927年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萧友梅创立了上海国立音乐院,其《和声学》即成为当时的重要教材。
黄自先生1929年从美国学成归国,翌年即被聘为上海国立音专教授兼教务主任。他协助萧友梅先生正式成立理论作曲系,培养的首届作曲学生,正是被后人称为“黄自四大弟子”的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日后均对中国音乐与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定仙曾撰文回忆道:“我的理论作曲完全受益于黄自老师。我跟他学过和声学、高级和声、和声分析、键盘和声、单对位法、复对位法、赋格、曲体学、曲体分析、乐器法、配器法等课程。——同学们都很尊重他。”(5)江定仙:《悠悠往事堪自慰——我的自传》,载《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二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
可以说,学习借鉴西方的和声思维与技法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音乐发展的必由之路,它是伴随着专业音乐创作与教育同时起步的。
2.碰撞的实质——中西多声思维的不同
和声的基础理论与自然科学的音响学有关,因此会产生一些能适应不同文化风格音乐的共同规律。但和声实用理论与技法又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技术,属艺术学的范畴,其纵横多声思维与西方的历史文化、哲学美学,人文艺术与音乐传统密切相关,显然不同于我们中华民族,因而当作曲家借鉴来“为我所用”时,两种音乐文化的碰撞便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更大范围内“西学东渐”在音乐领域内的一个反映。这种多声思维的“不同”包含有两个方面:
(1)构成多声的基本材料不同
首先体现在音高关系的基础——调式材料。西方音乐是基于大小调体系调式(自然大调与和声小调)以及七声自然调式(中古调式与民间调式)。而我国传统音乐则是基于五声性调式,这类调式是以五度音列相邻五个音为调式骨干,首音为“宫”,其后各音依次为“徵、商、羽、角”;若向上、下五度继续延伸的音则为五声外音,如向上五度延伸的变宫、变徵,向下五度延伸的清角、清羽等。
其次体现在纵向音响的基础——和弦材料。西方音乐是以三度叠置的三和弦为基础,三和弦可继续按三度关系叠加和弦音为七和弦、九和弦等,还可以用变化半音来改变和弦的结构音。而我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则是以单一调式内的自然音在旋法风格统一的多声部叠合中自由构成和音为基础。
(2)形成多声的基本思维方式不同
西方的主调音乐是:以和弦及其连续序进而构成多声部音乐的思维方式。而在我国则是:“各声部以同一旋律的变体在横向进行时作纵向的叠合,体现了分合相间的线性多声思维特征。”(6)樊祖荫:《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研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44页。这是樊祖荫先生近年主持完成的研究项目——“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观点。他着重强调:“有两个方面是组成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最重要的构件和最重要的表现方式:一是高度重视旋律的表现作用,体现出以横向线性进行为主的思维方式;二是在音乐的构成与发展上充分运用变奏方法,不仅将它在横向上作为旋律发展的主要手段、在曲体构成上作为最重要的结构原则,而且在纵向上也呈现为各声部多由同一旋律的变体叠合构成的形态。”(7)同注⑥。
由此可见,中西音乐在构成多声的基本材料以及形成多声的思维方式方面均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从而使得中国作曲家在创作中运用西方和声与我们本民族的音乐相结合时,产生了风格上的矛盾,这种创作活动在客观上会有一个很长的“磨合期”。马思聪先生70多年前的真知灼见:“中国的音乐家们,除了向西洋学习技巧,要向我们的老百姓学习,他们代表我们的土地、山、平原与河流”(8)马思聪:《中国新音乐的方向》,《新音乐》,1946年第6卷第1期,载《马思聪全集》第7卷,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34页。,道出了他对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看法,同时这话语也是马思聪先生本人身体力行的生动写照。马思聪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许多中国风格浓郁、脍炙人口的小提琴作品,比如《思乡曲》《塞外舞曲》《回旋曲》《牧歌》《西藏音诗》等,以及20世纪40年代所作的大量民歌改编曲都表明了这一点。
3.早期探索的奠基作用
20世纪20—40年代我国早期和声的实践与探索为后70年奠定了基础。20世纪早期,当西方和声理论与技法开始在国人的音乐创作中被实际运用之时,也是我国作曲家探索和声在中国音乐中如何应用、如何与民族音调相协调的启始,从最初的较生硬到逐渐相适应,有一个不断实践与积累的过程。“虽然当时我国民间丰富的多声部音乐尚未被发掘,甚至由于时代的局限而使有些作曲家对民间多声音乐的存在与否,尚有着某种程度的误解;但作曲家们对民间器乐的演奏特点,尤其是能演奏多音的乐器如琵琶、笙、古琴、古筝等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对民间器乐合奏、戏曲与曲艺说唱等伴奏的声部关系,也有一定的切身感受,民间音乐的调式基础、旋法特征、变奏手法等,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曲家们创作中的多声音乐构思。因而作曲家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意识地、或在潜意识中从民间音乐的思维特征中汲取养料,而体现出中国作曲家早期和声运用中的某些风格处理特点”。(9)刘康华:《探究我国早期音乐创作中和声运用的民族风格问题》,《音乐研究》,2020年,第2期。
比如,民间支声型声部的变奏分合关系,在相互间风格的协调与调式音列的一致等方面,会影响到作曲家早期应用和声时,去探索除旋律之外的其他声部的五声音调化的问题,尤其是和声的显著声部——低声部,以及体现风格的关键结构部位——终止式。另外,为避免大小调体系功能性低音的写法,作曲家会采用既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即将五声性旋律置于低声部,上方以八度旋律重复并夹置和声音程以丰富之,或以色彩性和弦烘托之。还有运用在同一调式音列范围内主题与加花变奏的多声结合,句尾各声部趋向同度音的集中进行等等。以上提到的这些特点,在赵元任、萧友梅、黄自、冼星海、马思聪、谭小麟、江文也、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丁善德等人的音乐创作中都有许多生动的反映。(10)同注⑨。
本文并非是全方位研究新中国70年来作曲家在和声运用中风格探索的各个方面与经验,而是侧重于探究在中西多声思维碰撞中,中国作曲家如何汲取民间多声思维与实践特点,从力图克服和声运用中的“违和感”,到逐渐融汇中西多声思维,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多声形态。
二、在碰撞中追求风格与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20世纪50—70年代),是中国作曲家在创作中探索和声运用的民族风格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50年代起政府有关“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举措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发展,如开展大规模的涉及传统音乐各个乐种的普查、整理工作,尤其是在调查、收集、记录、整理民歌的活动中大大推进了对民间多声部歌曲(戏曲、说唱等)的发掘与研究,这些工作与成果非常有利于启发作曲家创作中的多声思维与技术运用。
另外,在和声学界,尤其在高等音乐院校的作曲技术理论教学中,一批和声学者与教师积极展开了关于和声运用的民族风格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如1951年上海音乐学院的丁善德先生在教学中深感用西方大小调体系和声来配置中国民歌的风格不协调之处,遂根据自己的教学体会与创作经验作了《关于中国风味曲调与民谣的和声配置问题》的讲演,并整理成文发表于1951年《上海音乐》第1—4期。更重要的是,1955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和声教研室举行了和声民族风格问题的专题学术讨论会,由时任副院长、作曲系主任江定仙教授主持,并亲自作了一个重要的书面发言,之后经整理题为《和声运用的民族风格问题》一文在中央音乐学院校刊上发表。再者,黎英海、赵宋光、吴式锴等学者也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学术专著与论文(11)黎英海:《汉族调式及其和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赵宋光:《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吴式锴:《中国民族调式和声问题初步探讨》,《音乐研究》,1960年,第1期。。这些学术成果既是对前人在创作中探索和声民族风格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后人继续追求和声民族风格写作的实践指南。这些宝贵的学术文献至今仍对和声的理论研究以及教学产生重要影响。
20世纪50—70年代是中国作曲家在传统调性范围内探索和声运用的民族风格问题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成果丰硕。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作曲家依然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排除干扰,在特定体裁的创作,如民歌、民间乐曲、古曲的改编中为和声运用的民族风格探索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这一时期作曲家在和声运用中最典型的特征是:吸取民间多声思维与处理特点,结合西方和声理论与技法同我国五声性调式风格相适应的部分,而形成较成熟的多声技巧与音乐风格。

谱例1.陈培勋《粤曲“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1953年)(12)李名强、杨韵琳主编:《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第二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第58、65页。
谱例1(a)(b)是陈培勋广东音乐钢琴改编曲《双飞蝴蝶》的主题,分别摘自该作品的开头与尾声。从织体写法上可看出作曲家试图表现民间合奏的一些声部特点,(a)例主题的前半句(1—2小节)以双八度“合”开始,后半句(3—5小节)以“分—合”结束。然而在“分—合”低音的结合上我们还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中隐含的功能性低音进行,这在尾声的(b)例中得到了印证,右手八度旋律夹置和弦的处理,既丰富了这种具有民间合奏特点的声部关系,又保持了鲜明的和声调性。

谱例2.陈培勋:广东小曲《思春》(1952年)(13)李名强、杨韵琳主编:《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第二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陈培勋的广东小曲《思春》的一开始,承担旋律的钢琴右手声部有一个颇具特色的、由五声三音组构成的旋律动机d-e-b-d-e(见谱例2高声部第3及6—7小节),作曲家从主题中抽取该“动机”用于左手声部,作为固定音型与主题做二声部的结合,相互间既有民间支声型多声的分合特征,又有主调音乐将五声调式旋律纵向合成和弦做固定音型伴奏的特点。

谱例3.杜鸣心:鱼美人选曲《水草舞》(1959年)(14)童道锦、王秦雁编:《杜鸣心钢琴作品选》,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杜鸣心《水草舞》的中段,采用以半拍错开节奏的八度旋律夹置和声音程的写法。谱例3的前两小节是引子,第3—6小节是第一乐句,旋律是运用了有变徵音的b羽调式,和声为b小调的Ⅰ—Ⅲ—Ⅴ级三度关系的和弦进行。由于第一乐句结束于属和弦——#f小三和弦,因而第二乐句旋律从#f羽调式开始(见第7小节)便极为自然。接下去第8小节中最后半拍清角音D的出现替换了角音#C,又将旋律的宫调系统移回到D宫,从而将旋律引回b羽调式。值得注意的是第9小节最后半拍旋律中清羽音C的出现,而使其后再现的b羽调式主题在对比中更为突出。该例体现了作曲家既继承前辈八度旋律夹置和声音程从而突出主题旋律的写法,又在和声、节奏与调性处理上更为丰富,色彩变化亦更为鲜明。

谱例4.(a)桑桐: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NO.6《哀思》(1953年)

谱例4.(b)黄虎威:巴蜀之画NO.4《弦子舞》(1958年)
谱例4(15)李名强、杨韵琳主编:《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第二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第32页和第18页。这两个片段出自于两位不同的作曲家,但却采用了大致相同的手法,即将主题置于低声部,上方声部以节奏音型化的和弦予以伴奏。我们除了感受到低声部民歌风的主题外,还可在节奏音型的和弦高声部听到一条简化的旋律变体。换句话说,作曲家在节奏音型化的和声上融进了一条分支声部,以简化的旋律音调丰富了音型化的和弦,这种带分支声部的和弦与低声部的主题相结合时起到了既对比又统一的效果。

谱例5.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刘庄:钢琴协奏曲《黄河》第三乐章(1973年)(16)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法、刘庄:《黄河钢琴协奏曲》(两架钢琴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第三乐章是根据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第二段“黄水谣”与第五段“黄河怨”改编而成,谱例5是该乐章引子后钢琴独奏的片段,旋律为bE宫调式,采用了“黄水谣”的曲调。从织体写法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钢琴左、右手是一对充分发挥钢琴演奏特点的民间支声型八度旋律。在钢琴左、右手声部本身以及相互之间,或表现“黄水谣”的基本旋律,或加花、简化变奏,或附加平行音程等不同声部形态进行多种变化,既体现了民间多声的结合特点,又模仿了古筝等民间弹拨乐器的演奏效果。然而,融合在其中的和声主调思维也是显而易见的。和声是bE大调,例中第1小节是作为属和弦的引子,其后2—7小节为第一乐句,开始于主和弦(2—4小节),结束于属和弦(第7小节);8—15小节为第二乐句,也开始于主和弦(8—9小节),但结束于Ⅱ级和弦(第15小节);两句中出现的其他和弦也均在这三个和弦范围内。所有的和弦都呈现出省略三音或添加附加音的五声风格化形态。谱例5的音乐片段既体现了同一旋律通过“加花”“简化”而形成不同变体的民间支声的结合关系,又在主要结构点上继续保持了与主调和声背景的联系。

谱例6.王建中:《百鸟朝凤》(1973年)(17)李名强、杨韵琳主编:《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第四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第61页。


《百鸟朝凤》是一首在民间流传很广的由唢呐主奏的鼓吹乐合奏曲,谱例6是王建中根据该乐曲改编的同名钢琴曲,摘引的是开始的12小节。作曲家在乐曲的一开始就用钢琴模仿了民间器乐合奏的热烈气氛,表现了百鸟争鸣的生机勃勃景象。从乐谱上看,这种效果是作曲家融合了民间支声型与主调和弦型多声写法的结果。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百鸟朝凤》的旋律在钢琴右手最高声部,常用八度重复加强音响。另外在旋律下方附加了纯四度音程以模仿唢呐吹奏特点,由于旋律中时常出现装饰性的变宫音,因而其下方对应的纯四度就是变徵音(见谱例6高声部)。
2.整条低音(见谱例6中带箭头线条所指示的声部)声部是一条上方旋律的简化声部(1—4、7—8、11—12小节)与附加五度的变奏声部(5—6、9—10小节)。低声部中不时出现较大的音区起伏,乃是作曲家为了使其在主要结构点上承担和声低音而作的音区调整。
3.旋律是E徵调式(A宫调系统),与其结合的和声是E大调。前8小节主题充分展现了我国传统音乐“起—承—转—合”乐思发展的四个逻辑阶段,即1—2小节“起”,3—4小节“承”,5—6小节“转”,7—8小节“合”。和声亦以相同的思维与手段与之相结合:在“起、承”的阶段,和声是E大调的Ⅲ—Ⅰ、Ⅴ—Ⅰ和弦进行;“转”的阶段和声在对比的下属功能(Ⅳ级与Ⅱ级和弦)中发展,“合”则是再现了Ⅲ—Ⅰ的和弦进行。如此和声布局既有支声式低音追随旋律的因素,也有在旋法基础上合理设计和声的结果。由此可见,民间多声与和声主调写法的融合造就了这段音响丰富而生动的表现力。
下面我们再来看两段根据古琴曲改编的乐曲和声处理上的一些特点。

谱例7.黎英海:《阳关三叠》(1978年)(18)童道锦、王秦雁编:《黎英海钢琴作品选》,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第86页。

谱例7黎英海先生的《阳关三叠》,用纯四度的简化主题(见钢琴右手声部的上层),点缀强调了古曲旋律的基本骨架,模仿了古琴的弹拨发声特点。与此同时,作曲家又将支声思维与主调思维相结合,在恪守同一调式音列范围内,运用纯五声和声材料作背景来烘托。旋律调式在bA宫调系统内时常有交替,f羽调式是其中较主要的一个,所摘片段的和声正是从f羽调式的主和弦开始。从作曲家所运用的纯五声和声材料来看,尽管都是在调式五个音范围内构成的非三度叠置的四音和弦,但当作曲家把特定的音置于低声部,并且在其上方又加入纯五度音的支持时,该低音就取得了和弦“准根音”的意义,而使该和弦具有特定的结构功能。比如,前3小节为一乐句,其中第1小节为第一乐节,2—3小节为第二乐节;具有功能意义的和声进行是:Ⅰ—Ⅳ、Ⅳ—Ⅲ—Ⅰ—Ⅳ,由于这个乐句中两个乐节的结尾均是f羽调式的Ⅰ—Ⅳ,因而同时也就具备了同音列bb商调式Ⅴ—Ⅰ的交替功能。总之,这些含“准根音”的非三度结构和弦及其进行色彩性较强而功能性较弱,作为古曲旋律的和声背景颇为协调。

谱例8.王建中:《梅花三弄》(1973年)(19)李名强、杨韵琳主编:《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第四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第77页。


谱例8也是一首古琴改编曲,摘自王建中《梅花三弄》的中段。古曲旋律在钢琴左手的上方声部,并且在每一小节旋律的下方都伴随有和弦(见例中方框所示),大多在强拍。右手声部以十六分音符的均等节奏为旋律作加花变奏,例中用圆形圈出的音即是琴曲的主要音,可见民间音乐的多声特点依然是这段音乐的主要特点。然而作曲家结合的主调型和弦不同于谱例7《阳关三叠》中所采用的非三度结构和弦。琴曲旋律为F宫调式,所摘片段1—5小节为第一乐句,6—11小节为第二乐句。作曲家采用了F大调三度结构的和弦来与其结合,第一乐句前3小节为Ⅰ—Ⅲ—Ⅰ,值得注意的是作曲家将Ⅲ级和弦省略了三音而附加了音阶的增四度音,赋予了其特殊的色彩。第5小节乐句结束于Ⅲ—Ⅵ,形成了d小调Ⅴ—Ⅰ的交替功能。第二乐句进一步发展三度关系进行“Ⅳ—Ⅱ—Ⅶ—Ⅵ—Ⅰ”最终至主和弦,和声是自然调式风格,大多采用弱功能进行以取得与旋律风格相协调的效果。
三、在碰撞中趋向融汇与个性
从20世纪80年代起的后40年,中国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作曲家们放眼世界时发现,我们学习借鉴了半个多世纪的源自西方的调性和声体系,竟然被西方人自己打破了。在探索新音高组织技术的过程中,一部分西方作曲家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从东方音乐中吸取养料与灵感。因而,在面对突如其来涌入的各种音高组织的新思维与新技法时,中国作曲家除了新奇、学习、研究、借鉴之外,更多是冷静的思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锤炼”,中国作曲家群体已从中西多声思维的碰撞中探索应用与协调、追求风格与特点,变得更为成熟了。突破西方传统的调性体系,恰好给中国作曲家立足本土、扎根传统、探索适合本民族表达方式的多声部手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更深入地学习、研究并获取传统文化与传统音乐的精髓,以传统多声思维为根基,同时也广泛借鉴与汲取西方音高组织的新思维与新技法,在融汇中西多声思维中出新,创建中国作曲家的乐风,从而逐渐彰显出“以我为主”的多声思维个性。

谱例9.周龙:弦乐四重奏《琴曲》(1982年)(20)Zhou Long,Poems from Ta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Printed in U.S.A.2004,pp.9-10.

周龙的弦乐四重奏《琴曲》取材于古琴曲《渔歌》,谱例9是作品开始的段落。最初的主题由中提琴、第一小提琴、大提琴相互转接而成,即谱例中由线条连接的各音所构成的渔歌音调。该旋律同时被点描式的简化声部所点缀(见圆圈所示的音),伴随着时分时合的其他变体在不同声部中的忽隐忽现,再加上弦乐器各种特殊的演奏法而产生的模仿古琴发声的音响,一首清雅超然的琴曲被生动地呈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不时出现的由弦乐器震音所构成的非三度结构四音和弦(由第2、6、8小节第一、第二小提琴声部中的方框所示),在弱奏中营造了一种特定的氛围,其音高选择分别是A-B-D-E、C-D-F-G与D-E-G-A;它们与各自前后的旋律音结合为G宫、F宫、C宫三个宫调系统,在同一“均”的范围内分别以“三宫”的纵合化音响伴随着G商调式的渔歌音调,既烘托了琴曲的意境,又有相互间色彩对比的变化发展。

罗忠镕为独唱与三件民乐器而作的《送别(王维诗三首)》基本上采用民间支声、接应、固定音型等手法,通过作曲家的艺术化处理而使作品更富于诗意。人声旋律是含变徵音#F的C宫调系统“E角调式”,箫是与人声旋律同一的不同变体,二胡是人声旋律的接应型加花变奏声部,而筝则承担着全曲的和声背景。
虽然筝演奏的和声音型化背景仅用了C宫调系统的五个骨干音,但在作曲家的有意设计中,依然显示出了从呈示、发展到最终统一的逻辑关系。谱例10未摘录的全曲开始的3个小节,伴奏音型是从E、G、A 3个音开始;至本例摘引的前3小节,音型增至D、E、G、A4个音;其后的4—6小节音型改变为G、A、C、D;从本例第7小节至最后,音型增至完整的五声音阶的5个音C、D、E、G、A。音响体现出逐渐变化、对比、丰富,最终归为整体的发展过程。
杨勇为二胡与大提琴而作的二重奏《河神》,以大提琴空弦纯五度叠置的四音和弦作为和声背景,两件中外乐器采用同一主题不同变形的支声型写法。主题是D商调式,但最终交替到G徵调式。乐曲一开始两件乐器就围绕着主音D作舒展而悠长的吟唱,仿佛在缓缓叙述与相互对话,声部的分合关系主要突出了民间音乐中较有特点的大二度音程,如第1—3、5、7小节等;时而声部间有较大音程的“分”,也以分后的斜向进行而汇合为同度,如第4、6、8—11

谱例11.杨勇:《河曲——为二胡与乐队而作》第一首《河神》(2003年)(22)杨勇:《河曲——为二胡与乐队而作》,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61页。
小节等,尤其是其中的8—9小节声部数量增至三个,之间的分合关系以及和声关系亦更为丰富。另外,两种不同音色的对比,旋律中清角、变徵等五声外音的运用也使这段音乐的风格更为鲜明。

谱例12.陈其钢:《京剧瞬间》(2000年作,2004年修订)(23)李名强、杨韵琳主编:《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第七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第53—54页。
陈其钢在《京剧瞬间》的创作自述中说道:“在写作之前,我所知道的只是一种情绪,一种远远的、如烟的感觉。在这个感觉中包含了自己熟悉的京剧音乐的音调。”(24)李名强、杨韵琳主编:《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第七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第279页。该作品是以京剧二簧行板的过门为基本素材创作而成。京剧过门是一个两小节的主题,为了充分展示这个主题,作曲家在将其单独呈示后,以不断变化的分支声部与它结合来发展这个主题。
具体手法为,作曲家将主题重复了七次,上方声部在七次中均保持了主题的原始音高,但却逐步由简入繁地作加花变奏;而下方的分支声部在七次呈示中主题虽不变形,但每次均以不同的音高移位与上方主题作严格的平行进行,这种音高移位是按逐次缩小半音音程而展开的,即从小六度→纯五度→减五度→纯四度→大三度→小三度→小九度(小二度)来体现,因而,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七次不同色彩的双调性的结合。
谱例12(a)是支声型的第一次陈述,上方主题为bA商调式,下方的分支声部为小六度平行的C商调式。第二、三次陈述,下方分支声部与主题的音程关系按半音依次递减。(b)是支声型的第四次陈述,上方主题开始作加花变奏,下方分支声部与主题的音程关系已移位至纯四度,为bE商调式。经过第五、六次变化,最终达到(c)的第七次陈述,上方主题加花变奏的节奏密度已达到均匀的十六分音符,下方分支声部与主题的音程关系亦已移位至小九度,形成G商调式与上方bA商调式的结合。作曲家以这样的手法将音乐推向了下一个发展阶段。
郭文景的竹笛三重奏《竹枝词》以“冻竹、雨竹、风竹”三个乐章借竹这一自然物表现了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谱例13是第一乐章“冻竹”开始的14小节。从多声思维上看,这是一段主调型与支声型相结合的写法,从音高结构上看,体现的是传统五声与现代音高相融合的关系。主调思维主要体现在第1、3小节的d小三和弦,支声思维则体现在第5—13小节中二声部互为主次的变体旋律的叠合。

谱例13.郭文景:《竹枝词》(第一乐章“冻竹”1—13小节)(25)作曲家提供的电子乐谱。


谱例14.
这是两条大致相同的五声调式旋律在横向进行时作相差半拍的组合。竹笛Ⅱ演奏的旋律是bE宫调式,始于角音G;竹笛Ⅰ演奏的旋律是A宫调式,始于宫音A。两条支声型旋律的宫调系统相距三全音(见谱例14第1行),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一条结构循环的三全音调式:G-A-bB-B-C-#C-bE-E-F-#F-G,这是将一个八度等分成两组三全音,每组内的结构按半音数“2-1-1-1-1”构成,这也是梅西安有限移位调式的第7种(见谱例14第2行),但作曲家是将其拆分为相距三全音的两个宫调系统的旋律来表现的。我们再综合观察竹笛Ⅱ、Ⅰ的发音顺序,就会发现其完全符合这条三全音调式音列的上、下行顺序,从而体现出传统五声与现代音高的融合关系。当然,作曲家是先设计了结构循环的半音化音列,还是先设定了特定关系的宫调系统并不重要,关键是作曲家内心对音高的控制符合了某种特定的规律。
另外,再从十二音范围来看,相距三全音的两个宫调系统可综合为没有重复音的十声音列,相对十二个半音尚缺“D、#G”这对三全音,作曲家正是将D作为该乐章的中心音,将d小三和弦作为“准主和弦”,而将#G或等音bA作为中心音的对比,这在乐章的开始与结尾部分表现最为明显(见谱例13的第1、3小节,以及谱例14分析图示第2行第2小节)。
叶小纲为钢琴三重奏而作的《五色经幡》描写了他对西藏高原的感受。与前例《竹枝词》相比较,在多声思维与音高结构上,显示出了大致相同的主调型与支声型相结合的写法,以及传统五声与现代音高相融合的关系,但具体处理的技术特征不同。
谱例15的2—3小节,是这部作品五声性动机的不同变体,在三个声部中以同一节奏型作叠合进行。钢琴右手声部从第2小节的B宫调系统转换到第3小节第一拍的#F宫调系统,大提琴声部与其同步,从F宫调系统转换到C宫调系统,可见钢琴与大提琴声部在同时叠合时是三全音关系,两个宫调系统的十个音级中不含共同音。另外,再加上小提琴声部从A宫调系统到D宫调系统的转换,由此形成了整体上横向多宫调系统五声性旋律与纵向半音化关系叠合的、具有多调性色彩的特殊音响。5—6小节的五声性动机变为单一宫调系统的八度齐奏,其半音化关系由纵向移至横向,即从第5小节的#F宫调系统到第6小节的F宫调系统,与2—3小节形成明显对比。该片段中穿插的和弦均为作曲家特设的色彩性半音化结构和弦。

谱例15.叶小纲:《五色经幡》(2006年)(26)Xiaogang Ye,Colorful Sutra Banner:for Piano Trio,Schott,printed in Germany,2006,p.9.
秦文琛曾以《中国传统音乐对我创作的影响》为题在多个音乐院校讲学,《远去的歌》是体现他这种创作观念的典型作品之一。他曾表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使用了一种我称为‘宽线条’的技法。‘宽线条’是众多声部在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只是演奏同一条旋律时出现刻意设计的‘不精确’造成大片错位的音响。‘宽线条’观念来自中国民间音乐形态。比如西南山区的多声部民歌。”(27)周勤如、郭赞记录整理:《与作曲家秦文琛谈音乐创作》,《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3页。
《远去的歌》是秦文琛为短笛、双簧管、单簧管和一位打击乐手而作的《太阳的影子Ⅷ》的第三乐章。作曲家用三件木管乐器吹奏着同一支气息悠长的曲调,而打击乐电颤音琴不时地给予点缀装饰。谱例16是乐曲1—9小节的一个长乐句,歌调从小字三组的高音区“C→D”开始逐渐缓缓地迂回下行,最后8—9小节单簧管、双簧管、短笛先后依次斜向进入小字一组A音。这其中精巧的音高设计、缜密的节奏安排、特色的演奏要求、微分音的运用等多方面细微的差别,显示出三件木管乐器的“和而不同”,但又统一在一条作曲家内心音响控制的“宽线条”之中。

谱例16.秦文琛:《远去的歌》(2009年)(28)Wenchen Qin,The Sun Shadow VIII,Hamburg:Musikverlag Hans Sikorski GmbH & Co.KG,pp.16-17.

结 语
如今,中国作曲家多种风格的音乐创作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认同,这与他们在中西多声思维的碰撞与融合中既向西方学习,又向民间学习,不断探索、进取、彰显个性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70年中国音乐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20世纪20—40年代为此打下的基础不容置疑。中国作曲家一个世纪以来,“在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有学习、有探索、有反思、有升华,除了‘洋为中用’,更会‘寻根问祖’、立足本土去发展,这个过程已从开始的‘生涩’逐渐趋向于‘成熟’。这是一个学习、交流、吸收、融汇、创新的过程,并且至今仍在延续”。(9)刘康华:《中国当代作曲家和声语言构成的思维与技法研究》,《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22页。
马思聪先生七十多年前的“河流融合”之说,数十年后得到了大洋彼岸著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先生的隔空回应:“让我们不要谈论影响,而谈谈汇流。让不同的传统交融,带来一个全新的主流,整合所有的音乐概念和技法,将它们融合到一条宽阔的音乐河流之中。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确保所有的文化都保留其自己的独特性和诗意。”(10)哥大全球中心/北京:《他是瓦雷兹的弟子、谭盾的老师,在中西文化汇流中创造音乐》,2019年5月,参见网址:https://www.sohu.com/a/317540237_622275
——为混声四声部合唱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