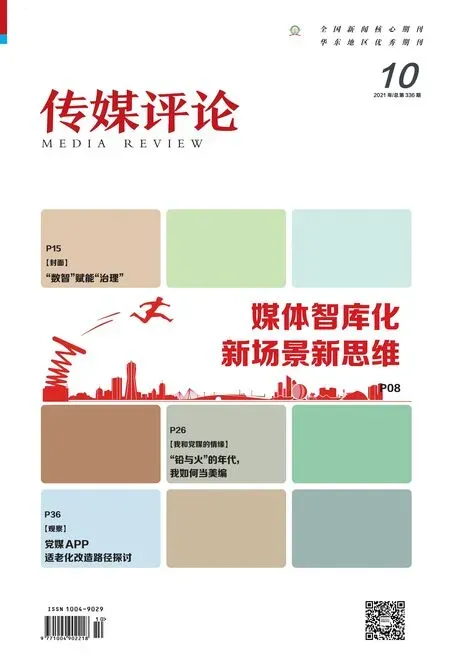“铅与火”的年代,我如何当美编
——访《浙江日报》原美术编辑傅伯星
文_郑 文

傅伯星,1939年生,1955年考入原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中,1960年毕业,分配至浙江日报社工作,长期担任美术编辑,后参与创办《大众美术报》,任副主编。1990年提前退休。
采访组成员:浙江传媒研究院 蒋卫阳
浙江日报全媒体文化新闻部 郑文
浙江法制报 胡晓峰 陈骞
采访组:傅老好,您曾在《浙江日报》长期担任美术编辑,请介绍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和在浙江日报的工作经历。
傅伯星:1960年,我从美院附中毕业,分配到浙江日报社工作。毕业之前大概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等待工作分配,期间《浙江工人报》每天派人来学校找我画插图,前一天画完,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刊登一块豆腐干大小的插图。这让我对美编工作有了初步印象。
我们那时候分配工作还可以填报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出版社、报社。我记得很清楚,公布结果那天,人事处前来宣布名单:“傅伯星,《浙江日报》。”
上班以后,我被分在3楼的美术组,组长叫邓泳涛,美术组最多时一组5人。
有一段时间,印报的纸张质量非常差,无法印照片。为此,领导提出,干脆用画来代替照片,能画的尽量画。
我到岗以后,组长让我先熟悉业务,最开始每天画小报头,那时候年纪轻、眼力好,邮票大小的报花都能画。或者画通栏花纹、写美术字。我也画插图,画得比较快,基本上当天要当天给。一般最早是上午10点多接到任务,画到下午4点。有时候晚上8点钟,临时接到通知说要换一个稿子,我就得赶紧画个插图出来。
后来工作时间调整了,下午开始上班,下班时间最晚的时候要到凌晨2点钟,我要等制版打样完成,看过效果没问题,才能回去。
我最多的时候一天4个版,画了28件作品,有插图,有报头,有题花,有装饰件等。画画的时候,经常有排字房的工人在旁边催,有时候他们嫌我慢,领导就在旁边批评他们:“不要催,让小傅好好画。”
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替我的班,我长期上夜班,把身体搞坏了。但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可以整天画画,而且报社的资料也比较多,需要找资料的时候,我就花大把时间在报社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在“铅与火”的年代,美术编辑是如何工作的?
傅伯星:我记得,报社在上世纪60年代开了一个叫“必要的一课”的专栏,需要许多插图。有时候我一个人来不及画,就把两个同学叫到办公室帮着画,一个是吴山明,一个是刘国辉,现在都是不得了的大画家了。我们3个人在办公室里,其他同志腾出地方,让我们坐在那里安心画画。
吴山明说这份工作很适合我这个“快手”,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是以快出名的。报社就需要手速很快的人,如果速度很慢的话,报纸就要“开天窗”了。我基本上能够适应报社的需要。
比如,新戏剧上演,报纸上需要一张舞台速写,我就得立刻去看戏,看完回来马上画出来,这是我的工作常态。报纸临时要用,我得有拿出“急就章”的本事,事先根本来不及准备,这就要靠平时积累。
平时怎么积累呢?我大概每两个月要下乡采风一次,这也是当时领导非常提倡的,到附近的农村画速写,同时收集一些资料。那时候的报纸一共4个版,第1版是重要消息,第2版是农业、工业、财贸,第3版是文化,第4版是国际时事。其中农业农村占了很大一块,需要提前准备一些绘画素材,比如农村里各式各样的用具,箩筐、篮子、马灯、灶头等。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老同志起初很不理解我为什么每次下乡都要画这些具体的物件,直到当我画插图用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这些东西是画画的素材。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美编的生活。
当时的总编辑于冠西同志有很多设想,希望我们去实现。那时我们的摄影技术还不是很过硬,图片也无法在报纸上做得很大,所以主要用画来表现新闻,相当于画新闻。于冠西大概是从清末民初的《点石斋画报》上了解到这种形式,觉得非常好,问我们可不可以借鉴这个形式,自己开创一下试试。我们说好的,然后我自己去乡下采访,编成一篇短文,再配上一张图。我记得曾经画了丽水乡下的一所小学,那个年代孩子很多,小学生如果有弟妹的话,会把弟妹也带到学校里去,让老师代管。这个举措在当时作为新生事物来推广,我画了插图,写了文字,在报纸上发表后,不少人说我的文笔不错。这对我是个非常大的鼓励,后来我有不少插图的文字都是自己写的。
于冠西同志还有一项创新,他说以前漫画基本上都是讽刺批评不良现象,现在看来也可以表扬好人好事。上世纪60年代,上海《新民晚报》美术编辑乐小英、《人民日报》漫画家苗地都是画这种类型漫画的,画风轻松活泼。我们就按着于冠西的这个思路去画这类东西。
总的来说,整个美术组的工作以画插图和表扬性漫画为主,还有报纸版面设计、外出组稿、写简评等。我感觉那一段时间的报社生活很充实,我很喜欢,所做的工作也能让领导和同事满意。
采访组:您在报社工作期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傅伯星:改革开放以后,我调到《浙江共产党员》杂志当美编。这本杂志一共48页,美编的工作量不大,领导对我说,你文笔不错,时间也很充裕,这本杂志里的两页副刊也给你编吧。这样,我就又编副刊,又当美编。
编副刊以后,我的采访任务也多了,因为我要自己想点子去采访。我写得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是采访《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当时,我在美院采访一位老教授,听说王莘原来是在宁波的,后来去了天津音乐学院当院长。我根据这个线索到天津去采访王莘,采访的主要内容就是《歌唱祖国》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后来《参考消息》等报纸转载了我写的这篇文章。
慢慢地,我感觉自己的工作量还不够饱和,我的想法就是利用空余时间尽量多做点事情,我就想要么另外办一个美术报吧!
我写了一个详细的规划,当时的总编辑郑梦熊很有兴趣,觉得这个点子好,就叫我写一个申请报给省委宣传部。他告诉我开始应该怎么写,结尾应该怎么写,最后是“如无不妥,请予批准”8个字。后来新闻出版局同意了,《大众美术报》就这样诞生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报社的条件虽然是艰苦的,但相对于其他单位来说已经很好了。那时,我老爸冬天到报社给我送棉衣,看到我办公室里还有电炉,晚上食堂还提供夜宵,他非常惊讶,觉得条件很不错。
报社领导对我非常照顾,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晚上吃白馒头总说吃不掉,叫我去给他们“代劳”。在那样的环境里我真正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采访组: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希望与寄托?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分享?
傅伯星:我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总体印象,不管是报社的新一代同行,还是整个美术界的年轻人,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动手能力不足。
我们那个年代,速写本是随身带的,有空就会画几笔。而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拥有一流的电脑和画画工具,但手绘能力还不够。
第二个问题是知识面太狭隘。我感觉现在学校里专业分得太细了,导致学生的人文素养、知识面也随着它的细化而细化,有些学生甚至连基础知识都不懂。比如说美院雕塑系的同学要做一个文天祥的雕塑,问我,文天祥的胡子是怎么样的?帽子上是不是有块方的玉?我说,你们要把《文天祥传》拿来看一下,搞清楚你要塑造的形象大概是在他什么年纪的时候,这样你就知道该不该有胡子或者胡子有多长了。至于帽子上方的玉,真实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方的玉是戏剧的产物。
总之,我觉得美术编辑第一要有比较强的动手能力,第二要有比较广的知识面。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这个时代是不是还需要这些,也可能是我倚老卖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