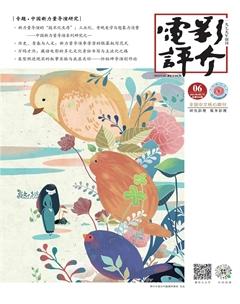游走在边缘的生存体验
王仙子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转型,中国影坛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一批风格独特的年轻导演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学术界称其为“新生代”或曰“第六代”。新生代导演在影片中不断用自叙的方式表达长大成人的渴望、焦虑和想象,同时也怀着一种对真实还原的冲动,开始尝试将摄影机的镜头直接对准当前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个体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在这一群体个性鲜明、风格各异的电影实践中,贾樟柯电影以其特立独行的美学风格脱颖而出。反映在其电影创作的艺术旨趣上,则是以青春的自恋和冲动替代群体的焦虑和躁动,以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置换宏大、崇高的集体仪式,以动荡不安、迷离驳杂的当下都市生活取代静穆雄浑、广袤无垠的乡村图景。在这一叙事策略转型过程中,贾樟柯用镜头记录下青少年长大成人的青春苦涩,用客观纪实的镜头冷峻地描摹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电影《世界》(2004)即是其代表。
一、贾樟柯与《世界》
贾樟柯1970年出生在山西汾阳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青少年时期,他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曾经做过当兵、顶替父母职业、学画画考大学的打算。在中学阶段,他爱好写作和文学,多次发表过小说、诗歌。一个偶然的机会,贾樟柯萌动了当导演的冲动。他说:“有一天我实在是没事干了,赶上放电影,放《黄土地》……电影看完之后,我就改变了,我要当导演,我要拍电影。”[1]由此,贾樟柯的电影之路随即展开。经过两次挫折,贾樟柯终于在1993年如愿以偿地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为了实现他少年时代的导演梦想,他组织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并于次年拍摄他的第一部作品《有一天,在北京》(1994),由此开始了他的电影实践。
贾樟柯将目光投向边缘群体的真实生活,普通人、边缘人等被主流影像遮蔽的各类群体进入他的视线。在他的影像话语里,民间的记忆成为最真实的原始资料,它们不是官方书写的特权,而是边缘群体游走在边缘的一种生存体验。这些社会的边缘人,是游离于社会体制外的个体生存者,他们往往猥琐而渺小,也似乎缺少民族救亡和理性启蒙的远大理想,更多的为自身的衣食住行而焦虑,或為情感精神的无所寄托而内心困顿。
《世界》于2004年正式上映,这是贾樟柯被解禁之后的首部获得国家电影局认可的电影。电影讲述的是以北京世界公园的舞蹈演员赵小桃与公园保安成太生(小桃的男友)为中心的一群打工者的生活。电影开头,画面一片黑暗,话筒却已传来喧闹的背景音和一个女声反复问:“谁有创口贴?”画面清晰后,女主角赵小桃穿着翠绿色的印度服装穿越走廊,经过穿着表演服装的匆忙准备上台的演员,一边仍在“寻找”她的创可贴。
相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社会语境的冲突、分化、无序,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则是通向共享、整合、有序的努力。在第六代导演的影片被称为“地下影片”“独立电影”“先锋电影”“体制外电影”之后,他们很大一部分人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体制内轨道进行电影艺术的创作,贾樟柯后期影片《世界》正是他进入体制内的第一部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终于让这些‘第六代电影人明白: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回归体制,重新寻求合法身份,以及进行某些电影观念的转变和调整,更是硬道理。”[2]在这一趋势裹挟下的贾樟柯电影,如《世界》则呈现出进入体制内主旋律的唱响:包括为社会寻求弥合的努力、为人与人之间沟通所形成的关爱,边缘群体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皈依。
二、沟通与回归:《世界》的主题
漂泊,或离散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当亚当和夏娃被上帝赶出伊甸园,流落到人世间,便注定了人类要在精神放逐和身体漂泊的双重创伤里终其一生。而由现代化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世界又使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处身于这一情势之下的芸芸众生,其命运更是无从把握。由这种无从把握而生的恐惧必然致使单个的个体寻求解救之道,而弥合这种双重创伤的途径,最好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关爱……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历经了世纪末的社会转型后,社会渐次强调主流意识形态,通向共享、整合、有序的努力。那么对应这一趋归,贾樟柯电影里折射出的图景则是:边缘群体以沟通的方式实现自我救赎,进而完成对传统道德、正统主流价值观念的皈依。
“谁有创可贴?谁有创可贴?”影片开始后的长达6分钟里,舞蹈演员赵小桃就这样一直喊着,四处寻找创可贴。对于这个开题,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隐喻,或詹明信所言第三世界文学的“寓言性”。这是赵小桃一代流落现代化大都市后,极具代表性的悲惨际遇:身体和心灵在漂泊的都市里饱受煎熬和痛苦,当她∕他们发出痛苦的申诉和权利的表达之时,却长久没有得到社会的安慰、保护以及同情和关注。但不同于此前,如“汾阳三部曲”里冷峻和不做交代的电影叙事手法,贾樟柯在片中却交代了赵小桃找到了创可贴(一个无名同事突然之间提供给她的)。在笔者看来,最终还是会有社会关注的眼光和同情的心态来聚焦这群边缘人物(具体说是城市里的“漂一族”)的悲欢离合,虽然他们“伤口”会让他们疼痛不已。
除去这个片段,影片中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场景,即对“二姑娘”遭遇的书写。不善言语、腼腆的“二姑娘”为了多赚几块钱夜间加班费,从脚手架上跌了下来,被送进了医院的急救室。在奄奄一息的时候,“二姑娘”要了纸与笔写下她的遗言,她歪歪扭扭地写在一张香烟纸上的,是她欠别人钱的一张清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一个个人名和所欠金额,总数一共是168元,其中最大一笔是50元,最少的只有几元钱。在生命的尽头这位农民工想到的是“欠人家的钱一定要还”,即使人死了,都要严守着自己做人的根本和信念,把钱还上。从贾樟柯拍摄这部影片的意图可以感知,事实上贾樟柯是要在不同的阶层、不同人群结构里寻求一种沟通和关爱。他认为《世界》是他想说的“新的社会,新的关系”。在这种新的社会和关系中,“一个时代的产生,可怕的并不是形成新的阶层,而是阶层与阶层之间缺乏一种沟通,一种关爱。”他认为:“电影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是可以帮助沟通的。它好像是焊接点一样,可以弥合人们的陌生,弥合人们之间的冷漠。”[3]
可以说,贾樟柯对这个情节的设置和处理,彰显他在融入体制内后所趋于的“回归”之势,伴随这一回归的是影片中人间温情的逻辑的展现,是不无感人的情感人生的排演,因而少了青年的先锋和反叛性,流入平常琐屑生活的描写和记录。这或许可以看成是市场、艺术和国家意识形态三方权衡的必然,因其必然,包括贾樟柯在内的第六代导演共拥一条相同的宿命。路学长曾经说:“毕竟我们的电影是为中国观众拍的,为的是给国内观众看。”[4]现在张元也意识到:“以前一心拍片,力求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很少考虑观众。那时拍电影就是目的,现在不同了,希望自己的感受有人看、有人听、有人共鸣,激励我继续拍片,继续表达自己。”[5]
跨入21世纪,融进体制内拍片,从“地下”走向“地上”状态以后,贾樟柯电影的电影美学风格如上文所述,渐次趋于回归传统和主流。在这一“回归”的主题中,除去前文所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关爱”,影片所及之处,表现出另一个较为显著的是对坚守的肯定和褒扬,即在爱的笃定和尊严的护持下延展影片的所指。
在《世界》里,借边缘群体为主流和传统立言则成为影片的实质性内容和所指。在社会习俗的束缚中、在国家意识形态体制的规训里,回归一个家、寻求一份安稳的精神寄托,成为他们一致的追求。摒弃那个曾经喃喃自语的遗世独立,选择融入话语共享的大众空间,这是能在传统与现代、集体与个人、市场与艺术等诸多二元对立的事项中自由择取、融合整一。
三、价值归旨:对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
贾樟柯对边缘群体和现代性的关注,应该说是一个自觉自为的艺术行为。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他在带给现代中国整体进步的同时,也残酷地剥夺了边缘群体的话语权,甚至式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益,所以,“我(贾樟柯)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放得开,更直接去寻找一种挑战的主题去面对。”[6]而这个“挑战的主题”,便是对社会内部机制的一种影像解剖。
贾樟柯电影一大特色便是其现实性。尤其是在展现当下社会发展进程中那些被社会忽略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方面,透彻而又真实地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他的影片主要呈现的是大的社会背景下不被人重视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小偷、三陪小姐、無业青年、民工、下岗工人等,贾樟柯以电影这种大众媒介为载体,关注、关怀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真切的展示了他们的生存体验与精神状态。
当贾樟柯的镜头从山西来到北京,他再一次(第一次是学生时代作品《小山回家》)将镜头对准了城市里的边缘人群——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世界》里,他把故事的背景搬到了北京,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了中国的大都市,以至于很多报刊都以“贾樟柯进城”这样的揶揄标题报道。但我们看到他选取的北京,并不是北京最有社会底蕴、文化内涵的胡同、四合院等,而是世界公园。贾樟柯选择这样一个具有虚拟性质的生活背景,蕴含着他的批判精神:世界公园里有各国的著名景观,那是虚拟的辉煌世界,人却不能在其中真实地生活。北京对于赵小桃和成太生而言,也只是一个景观而已。对于都市体制外的人(包括农村和中小城市),都市只是仅供观赏的舞台或景观,是永远也进不去的卡夫卡式的城堡,他们只是工地上的机器、舞台上的道具,在富丽堂皇的虚幻舞台后面才是他们的人生。他们是站在“世界”之外的中国人。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历史,是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在追求现代化步伐中的前行和徘徊。那么,当整个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后,以现代化“立国”的渴望则显得愈加强烈和急迫。而以这种欲望为动力的中国社会,因生产关系的调整刺激了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发展,促使思想观念的转型和嬗变,文化也在生产力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中,不断汲取传统文化资源,与西方文化交流和融汇,在不断地自我更新后滋生繁衍。这种状况必然会对正处于现代化时期的中国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政治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现代化也意味着它不只是一套正面价值的胜利实现,而且还同时伴随着一定的负面影响。商品化社会由于瓦解了传统社会必然造成“神圣感的消失”,从而几乎必然导致人(尤其是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无根性和放逐感,尤其是商品社会几乎造成了商品拜物教,社会合理化趋势,以及公共媒介对私人空间的侵吞和挤占。而当现代化在中国进入21世纪时,随着大众文化的泛滥,“更使整个现代社会强烈地感到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基础的崩溃。”[7]
同时,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方位改革,在为欲望正名的同时也把整个社会问题凸显出来。“先富”与“后富”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催生剂,与沿海开放城市高歌猛进的经济神话相伴生的是一批批民工潮和民工热现象,他们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的“自我牺牲”。纵观20年来的改革开放,这个类似启蒙主义的立场,究竟给了这些底层民工什么?他们热情的投入和产出是否一致?以他们近乎无法拥有社会资源,无法掌控话语权的劣势,能不能与这个以话语权力、社会关系网络为特征的现代化社会相安无事?贾樟柯电影为边缘群体立言,以影像的方式将这一大众群体从利益的牢笼中抽离出来,涂抹人文主义的底色,在我们看来是必要且及时的。
四、大都市中的边缘群体:对现代性的反思
按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现代性理论,就艺术和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而言,现代性可区分两种剧烈冲突的现代性:一方面是社会领域的现代性,源于工业与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本质上属论战式的美学现代性,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波德莱尔。[8]前一种现代性,我们称之为社会现代性,又称世俗现代性或资产阶级现代性,它表现为和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如启蒙主义、工具理性与科技万能等观念,它是理性、民主、自由、科学……是一种进步神话;后一种现代性,美其名曰审美现代性或美学现代性,它以主体性和个体性为内核,对工业主义和资产阶级市侩主义及其观念进行批判。一般而言,“审美现代性”以其对现代化和“社会现代性”的疏离构成与后者的巨大分裂,从而本质上具有反现代性的一面。这是现代性自身发展中意义深刻的二律背反。作为艺术门类的诗歌、小说、电影、音乐、绘画等文化样态,则成为审美现代性存在并发生批判功能的有效载体。
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现代化决不意味着一个单纯的命题,而是多种元素的混杂。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在对象上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它既是商业、工业系统,又是大众文化,同时是不断地被精英文化所渗透、所感召的一个文化领域。在学者戴锦华看来,“就回答中国现代性话语构造和扩张过程这样一个命题来说,没有比电影更好的对象了”。[9]
《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大都市影像展现了一个多维的空间结构体。如全球性的想象空间、舞台的仿像空间、遮蔽现实的景观空间以及人物内心共拥同一价值观的心理空间等。对这空间的处理,贾樟柯用几个段落板块来讲述,将几对相对独立的人物关系与经历并列组织在一起,来说明和印证外来务工者的漂浮和不饱和的生活状态。“不出北京,走遍世界/See The World Without Leaving Beijing”;“大兴的巴黎/Paris In Beijing Suburb”;“乌兰巴托的夜/Ulan Bator Night”;“一天一个世界/Ever-changing World”;“美丽城/Belleville(巴黎的中国城)”;“汾阳来的人/Boys From Fenyang”。形成了非常清晰的段落区分。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在走出中国内陆小城镇后,贾樟柯已自觉地将边缘群体串联在现代化的大都市空間里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在这里,我们将主要择取“全球性的想象空间”和“遮蔽现实的景观空间”两个反映时代特征和趋势的维度,探讨贾樟柯电影对大都市空间的表达。
首先,在全球性的想象空间方面,电影是通过北京“世界公园”、外籍来华劳务工者以及中国输出的劳务人员流动来建构的。
通过影片可以看到,故事发生的环境和背景已不再是山西汾阳那个“比哪儿都慢一拍两拍”的小城镇,而是已经加入WTO,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大都市北京以及更为宏阔的世界。在北京“世界公园”里,足不出国可见美国、巴黎和伦敦等超级大都市,尽管只是仿像,但正是通过这些仿像,我们能够接触和了解异国文化,拓展视野。正如“北京世界公园”的保安成太生对刚从汾阳进京的二姑娘介绍的:“这是美国的曼哈顿,这是双子星大厦,美国的真货“9·11”时没了,我们的还在。”再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全球一体化是休戚相关的,这在影片中主要是通过两个相关的故事来建构的。其一是俄罗斯妇女安娜以及“北京世界公园”民俗村工作的那群外籍工作者,他们由异国而来,加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其二是赵小桃的前男朋友梁子去乌兰巴托打工。影片这两个故事,从经济学而言,这是一种典型的劳力资源重新分配和利用,很明显它是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必然,使得中国在开放的时代氛围中融于全球经济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中,而这势必影响中国对世界的想象图景。
因而我们看到,影片不断在中国本土与世界的图景之间切换:影片中的人物在现实中的北京(这里有两类形象:一类是现代化的摩天高楼、飞机等便利的现代交通工具;另一类是肮脏居民区、憋窄的地下旅馆)与异域的美国、巴黎、伦敦等城市随意穿行。如影片开始和中间反复出现一个镜头一样,太生问坐在缆车上的小桃:“在哪里?”小桃颇以为傲地对太生说:“我要去印度!”仿佛她真的是在穿梭世界。再比如赵小桃和安娜在小旅馆吃饭聊天,当安娜似懂非懂地听到播音员说出“乌兰巴托”时,他兴奋地谈起了身困乌兰巴托的妹妹,观众也随之想象出一个有关乌兰巴托图景的境地。
其次,遮蔽现实的景观社会空间。法国思想家、实验主义电影艺术大师居伊·恩斯特·德波(Guy Ernest Dobord)认为“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10]是“关于现实的片断的景色,只能展现为一个纯粹静观的(Contemplation)、孤立的(Seule)伪世界”,[11]“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12]
结语
从电影提供的画面来看,《世界》故事可以说是发生在一个由景观组成的虚拟、封闭的空间之内。在世界公园里,可以充分感受到机械复制时代的诸多产物,从英国的大本钟到法国的凯旋门再到美国的双子塔,虽然在物理空间上只有几公尺的距离,但它是虚幻的,没有人可以进入那些只在旅游风光片中才有意义的建筑;在此,“世界公园”成为一种后现代景观,作为消费文化现象出现,被作为一种空间消费了。人们通过消费来这里感受到异国风情,感受到令人赞叹的各种景观,尽管这里的景观只是一种“仿像”,但在穿上了指定的幻想盛装后,“无”就假装成“有”了,人们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然而,吊诡的是,景观形象的消费根本无法消除分离和异化的状态,相反它只会加深分离和异化。在赵小桃、成太生白日里盛装演出,辉煌一时后,晚上他们又不得不回到那个憋促黑暗的廉租房。在那个浓缩“世界”的地方,到处都是建筑,但是主人公们不可能进入到这些建筑中去,这里不是供他们栖居的地方,反而他们是被抛弃了的。在廉价旅馆的房间、宾馆包房、暂时无人参观的退役飞机,这些临时的私密空间内,赵小桃和成太生难堪地谈情说爱,这是莫大的反讽。“一个人假如不能拥有一所房屋,他就不可能参与世界事务,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13]于是,我们看到在世界公园里的一切都是表征,虽然它如此“具体可感的真实”,但逼真、生动的形象也只被用来掩盖现实的缺失。“世界公园”在影片中也沦为一个空洞的符号,一个装饰性的、体积巨大的模型。
参考文献:
[1]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351-352.
[2]吴小丽.已知和未知的“第六代”[ J ].上海大学学报,2006(13),6:15.
[3]张会军,马玉峰整理.贾樟柯谈电影《世界》的创作与发行[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6):87.
[4]陈犀禾,石川.多元语境中的新生代电影[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29.
[5]丁玉兰.解密张元——张元访谈录[ J ].母语,2000(5):88-97.
[6]张会军,马玉峰整理.拥挤的世界、变化的中国、思考的贾樟柯——贾樟柯谈电影《世界》的创作与发行[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6):87.
[7]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初版前言[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
[8][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43.
[9]戴锦华.犹在镜中[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105.
[10][11][12][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3,11.
[13][德]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C]//刘锋,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