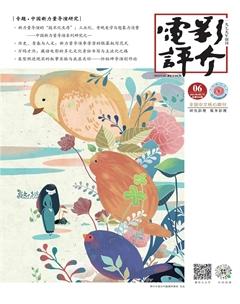类型化非虚构影片的表征系统与实存“论断”
魏婧婧
一、非虚构影片的标准及分类
当代美国学者诺埃尔提出“假定性论断”和“意图—响应”这两个概念,他认为其更符合非虚构影片的特征。“我们可以认为,与虚构类作品相反,这一类型作品的暗示性信号传达者抱有一个既定的明确意图,希望观众能够意识到传达者的意图,从而形成一个对于文本命题内容的既定明确立场。”[1]创作者的意图根据生活中的经验衍生,继而通过影片传达给观众,而观众从一开始便清楚地确认这一故事并不只是虚构情节,更多来源于真实生活,于是对创作者做出回应。“意图—响应”交际模型的运用使非虚构影片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范畴,创作者与观看者同时沉浸在电影的艺术世界中,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浸入式体验的构思策略不仅拉近了观众与创作者的距离,使二者更易产生情感共鸣,并且使非虚构影片脱离了过于僵化的客观形式的桎梏,能够与时代的市场化发展趋势相适应。
实际上,早在20世纪末这一类非虚构影片就在西方国家大为盛行,且很多都成为了不朽的经典作品。例如记录纳粹德军非人道罪行和战争期间难得的人间温情的《辛德勒的名单》,便是根据二战期间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同类型影片《美丽人生》尽管不像《辛德勒的名单》具有原型,但也是根据导演的儿时记忆编制;《肖申克的救赎》的很多情节借鉴了《逃出亞卡拉》,而《逃出亚卡拉》便是根据1961年旧金山的“恶魔岛越狱”事件改编而成;《拯救大兵瑞恩》中瑞恩的原型是美军士兵弗里茨·尼蓝,这一在诺曼底登陆事件中的营救细节被制作为影视作品,以宣扬美国珍视个人生命权的官方意识形态思想。
中国对非虚构影片的关注是自新世纪以来开始的,尤其是近几年更是注重客观真实与主观创作的完美融合,这一改变使新世纪以来中国影片的真实性更为立体化的同时,也让剧情更加具有可观感、吸引力。不同于西方国家在非虚构影片制作方面较为散乱的关注点,中国制作方显然积累了更多经验与方法,因此,很多影片不仅符合“假定性论断”的标准,而且类别逻辑更为清晰。新世纪以来,大致有三类非虚构影片相继产生。
第一类是历史类型的非虚构影片。例如吴宇森的《赤壁》以三国混战为背景展现那个年代的雄心与激情;胡玫的传记历史片《孔子》再现了为理想而被奔走于列国之间的圣人形象;李仁港的《鸿门宴》取材于楚汉争霸事件;王竞的《大明劫》以两位真实人物为原型凸显了在面对天灾人祸时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一九四二》呈现了饥荒年代的人生百态。
第二类是社会类型的非虚构影片。谈到这一类型,必然要提到导演王竞,他擅长于纪录片拍摄制作,出身于摄影专业,因此对于镜头的掌控极其苛刻,他的一系列作品大多源自生活中的真实体验,加以恰当的人工制作,呈现出一幕幕克制但依旧情感饱满的画面。例如,《圣殿》是有感于当代青年沉迷网络世界而作的一部超次元影片;《无形杀》改编自“铜须门”事件,从旁观者角度刻画了人肉搜索的恐怖力量;《我是植物人》则是导演对于制药行业乱象的深刻思考。另外,《烈火英雄》《我不是药神》《烈日灼心》《滚蛋吧,肿瘤君》等影片同样源于真实社会热点事件,并且更注重对事件主人公的细微刻画。
第三类非虚构影片聚焦于宣传积极正面的国家意识形态思想。例如《湄公河行动》《战狼》系列、《中国机长》《红海行动》《攀登者》等影片都是近年来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佳作,这些电影为中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发挥了一定宣传作用。此外,近年来中国所拍的很多献礼片如“建国三部曲”、《我和我的祖国》《古田军号》等,既属于历史类,亦属于国家类非虚构电影,在近代史故事框架中融入了国家先进意识形态。
以上所述的影片尽管类型不同,但却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都是属于假定性论断的电影,创作者通过宣传活动、媒体发声等方式事先“告知”观众故事有其真实原型,于是从理论上而言,观众在观影之前便能够预知大致主题,并且带着一定的期待心理观看影片。从这个角度来讲,故事不是创作者虚设的,也不需要观看者来想象,而是需要一种确认行为——使观众确认艺术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吻合程度,因此被称之为“论断”。那么“假定性”又是何意呢?不同于传统定义中的“非虚构”概念,新世纪以来中国理论界对于“非虚构”的界定更为宽容,因此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类影片中有其施展余地,只要把控好尺寸,便能使影片达到“艺术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境界。
二、“假定性”:浸入式的表征系统
对于非虚构影片和故事性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一直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之一,到现在看来,非虚构影片并不排斥故事性也成为业界共识之一。[2]故事性是一种具有“假定”特性的情节,因此在传统观念中往往被纳入虚构影片的范畴,但实际上非虚构影片同样需要表征系统的运作,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表征是经由语言对意义的生产。[3]这句短小精悍的话对表征做出了一种定义——语言是人发出的媒介,意义是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结果,生产则是一种主观能动性十足的操作过程。因此,从这一句话便能提炼出表征的核心特征,即主观性。在影片制作过程中,主观性体现为创作者对非虚构事实的加工和沉浸式的投入;在影片的传播接受过程中,主观性则体现为观众对艺术加工后的既有事实的浸入式感知。
在影片《大明劫》中,导演以乱世中的两个人物为表征符号,即名将孙传庭与名医吴又可。这两个人都在寻找“药方”,不同的是,孙传庭想要找到的是救国良方,而吴又可孜孜以求的则是救人命的药方。整个故事以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为背景,其中的瘟疫场面、战场血腥、武器枪炮大多根据史实呈现,但导演却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表征符号作为串联起整个故事的核心点,这显然是一种出自本心的人为抉择。创作者的镜头缓慢地跟随着这两个大背景中的“小人物”游走于那个不可能完全再现于人世的年代,正是这种反差性极大的安排,令观众触摸到了与历史纪录片截然不同的新鲜感。观众不再被放置于旁观者视角,冷漠地看着片中人经历一场场生死离别,而是跟随创作者进入两个表征符号,即两位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借由他们的眼睛,看到那个年代的生活细节与人情冷暖。名医与名将的交集在历史记录中是未知的,但未知不代表不存在。创作者的这一联结显然为影片注入了莫名的神秘色彩,但这种神秘又并非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是一种“假定性”的存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非虚构影片也正是通过这种“假定性”联结方式使观众获得更为细腻的观影感受。其他的历史类非虚构影片亦不外如是,《孔子》一片如只是将《论语》中的名言名句当做台词搬上大银幕,虽则称得上真实客观,但如今具有一定艺术品位的观众必定难以接受此种拍摄模式。因此,导演选择从孔子54岁之后周游列国的人生经历开始讲起,其中穿插治理中都、夹谷盟会、堕三都失败、问道老子、被迫出走、流亡卫国等情节,孔子与南子若有似无的感情线更是引起观众兴趣,这种在史实基础上适当加工的技巧正是当代非虚构影片的主要特征。
社会类非虚构影片对“浸入式体验”的构思技巧运用得更为娴熟且直接,因为不同于历史事件的绝对客观性,人们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看法本就可以是多样化。《烈火英雄》不仅描写了消防员正面对抗火灾的壮烈场景,而且对其背后的故事亦不惜笔墨——认真负责的江立伟因为一个小差错导致队友牺牲,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创伤应激后遗症,黄晓明将这个角色前期的英勇前行与后期心理上的矛盾演绎得惟妙惟肖;马卫国则对标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人,在父母亲人的教诲与压力中不断鞭策自我,郑志这个角色戏份不多,但却格外出彩,他前期的懒散怠慢与后期为队友牺牲的无私形成鲜明对比,令观众产生敬仰之情……此外,这部影片采用了双线叙述手法,正面对抗火灾的主线之下又有辅线,即对江立伟妻儿的描写,她们在逃亡路上遇到的种种意外是没有也无法被记录下来的,但我们却不能说这些情况不存在,因此这是一种“假定性”的情节。在这些细微情节中,英雄的付出变得更有意义、更加真实,因此这种形式上的虚构反而促生了真实感。《滚蛋吧,肿瘤君》中女主角的臆想、《我是植物人》中各种巧合的集聚、《我不是药神》中见人便给橘子的羸弱中年男人吕受益……这些人物和情节大多是一种“假定性”存在,但影片却在这些微末细节中升华为富有深意的哲思。
国家类非虚构影片同样会有“假定性”的镜头,这些具有感染力的表达在观众的内心形成惊涛骇浪,从而加深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战狼》系列中冷锋面对强大势力时依旧如有神助、《湄公河行动》中彭于晏的飞檐走壁潇洒机智、《红海行动》中海清散发出人道主义关怀。这些情节多少有些偏离正常思维逻辑,但又并非完全虚构,观众与创作者在这些具有“假定性”特征的非虚构剧情中共同表达了对祖国的爱与敬仰。
三、“论断”:不可想象的实存
“当我们讨论故事片的真实性时,其实讨论的是可信度的问题;当我们讨论纪录片的真实性时,其实讨论的是创作者是否对片子进行了加工,即是否客观。而它们往往被“真实性”这一个词代替了,表达存在混淆”。[4]
这段表述来自于中国当代导演王竞,他厘清了电影界对于不同种类的影片真实性看法的差别,纪录片的真实性在于不可加工,故事剧情片的真实则体现为可信度,这两个标准看似模糊,实则对应的发出者是完全不同的。“不可加工”要求的是创作者在制作过程中完全客观,不能添加个人情感;而“可信度”则是对接受者的期待,也就是说希望观众对影片中的情节产生信任感。这两个标准实际上可以融合于新世纪中国的非虚构影片中,于是便产生了非虚构影片的第二个核心特征,即“论断”。创作者根据客观事实为框架构建故事,之后的一切“假定性”都必然建立在这个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是创作者传递的意图。不同于虚构影片将意图模糊化,非虚构影片是通过客观事实将意图表现出来,而作为响应,观众则会根据客观事实对其进行合理猜测,于是一种具有现实性的“论断”便由此产生。
非虚构影片与纯粹故事片最大的差异便是其剧情框架并非由编剧想象而成,而是根据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加工而成。
历史类非虚构影片将距今时代久远的故事搬上大银幕,理论上说当代观众会对此类作品产生一定疏离感、陌生感,21世纪以来中国的电影制作人并不完全照搬史实,而是根据当代观众的价值观、审美观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之后再进行呈现。这种操作方法使影片既不偏离史实,又能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例如《一九四二》根据1942年7月到1943年春发生在中国河南的大饥荒事件改编,这场导致150万人死于饥饿和300万人逃离河南的灾难被冯小刚以一种纪实性的镜头拍摄出来。基调偏暗的调色、符合中国抗战时期的服饰、食物与风俗、极具特色的地方方言……这些特征源于“真实”二字,这种真实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无法抵达的高度,也正因为这一份真实,才能引起身处和平富足年代的人们的警惕与关注,使人不禁想起千年前孟子的那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再如《大明劫》《鸿门宴》《孔子》《赤壁》等历史类影片,也均采用中國恢弘历史中的一段真实故事,以其为基底,追溯一段段令人动容的远古回忆。
不同于历史类非虚构影片选取的题材时间久远,社会类非虚构影片往往以当下热点为突破口,但它们同样是观众在观看之前便能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影片的“真实”,因此将其看作一种实存,并在欣赏过程中作出“论断”。例如根据“大连7·16大火事件”改编的《烈火英雄》,灾难的突发使许多人陷入错愕,事后不论是劫后余生的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无法获悉现场细致情况,但影片却以镜头方式展现了火灾的肆虐场景与消防员的抵抗精神,以一种相对客观的形式再现了灾难发生时的种种状况。《滚蛋吧,肿瘤君》则完全是漫画家项瑶对自己抗癌生活的点滴记录,个体面对疾病时的无能为力和主人公面对生死无常的乐观心态在真实事件框架中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对这个原型人物的敬畏感油然而生。另外,《我不是药神》中那个为人们寻求“便宜药”并具有复杂人性的原型人物陆勇、《无形杀》讨论的“铜须门”事件、《红海行动》展现的“也门撤侨事件”,亦都是以不可想象的实存,使观众在进入艺术世界之前已经触及到了真实世界,这种提前触及可以令观影体验更为深入。
国家类非虚构影片是以真实事件为底色进行拍摄的方式,有助于提升作品对观众的吸引力,使观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找到依托点。如《建党伟业》将镜头放置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的涌动暗潮之中,对民国初年动乱、五四运动、张勋复辟等大事件进行细致还原,真实感扑面而来的同时,也让观众对我党的光辉历史产生敬仰之情。再比如《中国机长》直接取材于发生在2018年5月14日6时27分的飞机紧急返航事件。从重庆飞往拉萨的川航3U8633航班在重庆江北机场正常起飞,机内载有包括机长刘传健在内的9名机组人员和119名乘客。飞行途中,飞机挡风玻璃突然破碎,机长迅速做出反应,决定就近迫降。这一刹那间发生的灾难在影片中的再现,令观众感受到了中国机长的从容不迫与高超专业能力。
结语
21世纪以来,中国的非虚构影片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即历史类非虚构影片、社会类非虚构影片与国家类非虚构影片。此三类影片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艺术原型,这使观众确认自己所看到的故事是曾经发生过的既有事实,因此非虚构影片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论断”,因为观众是在“确认”一种存在,而非“想象”一个存在;但所有的表征系统背后都不可能缺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操控。因此,非虚构影片在形式上依旧具备主观特质,但这种特质并不影响其非虚构之本质,反而能够促使影片更为生动活泼、为大众喜闻乐见。
参考文献:
[1][美]诺埃尔·卡罗尔,刘弢,彭程.虚构类影片、非虚构类影片与假定性论断的电影:对概念的分析[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02):35-55.
[2]任远,戚天雷,赵宏林,雷霖.几种非虚构影片的故事性解析[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11):43-46.
[3][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8.
[4]王竞.纪录片创作六讲[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4: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