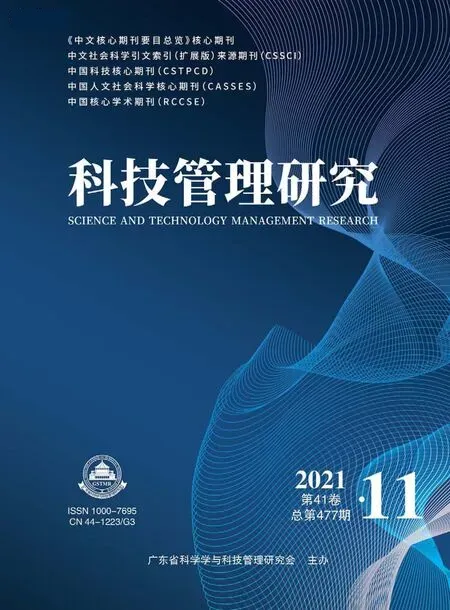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研究
——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的双中介作用
何智敏,陈怀超,侯佳雯
(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西太原 030024)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驱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资源。由于知识的默会性、复杂性、难以模仿性等特征,企业需要进行有效的知识治理以赢得竞争优势。战略联盟为联盟企业获取、吸收和整合知识提供了便捷条件[1],是企业完善自身知识治理的有效载体。然而,由于联盟伙伴目标不一致、在信息和认知上存在差异以及缺乏有效沟通等原因,联盟各方往往会产生冲突[2],导致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造成联盟企业之间知识合作的困境,使得企业通过联盟获取并有效利用知识的愿望难以实现。因此,联盟企业如何通过关系维护,塑造有利于知识治理的情境,有效规划和管理知识,实现高效的知识治理,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
知识治理现已得到了学者们的较多关注[3-6]。对于知识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集中于企业个体层面,从知识特性以及知识活动主体等方面展开探讨[7-8],但鲜有文献以联盟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联盟企业之间的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社会网络理论认为,联盟网络关系是一种网络资源。从这一角度来看,联盟关系的构建是联盟成功的关键因素[9],这种关系的强弱会影响联盟企业获取资源的难易程度[10]以及联盟企业之间的沟通、信任和合作效率,进而影响企业能否在联盟合作过程中实现高效的知识治理。因此,需要关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
此外,在企业借助联盟合作获取所需的知识、实现企业知识治理的过程中,成员能力往往会影响其预期绩效的实现。从联盟整体视角来看,联盟成员之间存在复杂的竞合关系,合作中可能存在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现象使得企业不愿意充分共享知识,有效的联盟管理则是避免这种“联盟陷阱”的关键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能力,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过程中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从企业个体视角来看,由于知识的默会性和复杂性,企业即便通过联盟获取了所需的外部知识,但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利用往往并不容易,作为一种重要的内部能力,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关系强度—成员能力—知识治理”的研究模型,考察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直接影响,同时,从外部与内部两种视角出发,将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纳入研究框架,验证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影响过程中的双中介效应,从而揭示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内在机制,为联盟企业有效利用联盟关系、提高企业知识治理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直接影响
Grandori[11]最早提出知识治理这一概念,并指出知识治理是对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共享、交换等知识活动过程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对知识治理的概念进行了拓展和延伸[12-13]。本文参考任志安[13]的分类方法,将知识治理分为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认为知识治理是指组织通过选择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机制和激励方式,以实现知识的获取、转移、共享、整合、应用等知识管理活动的最优化。其中,正式知识治理是指通过企业组织结构、赏罚机制、领导权等方式治理知识;非正式则主要借助企业文化氛围、管理方式、员工公平感等方式治理知识[14]。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任何企业或个人都嵌入在一定的“联结”中,这些“联结”相互交织,构成了交叉和重叠的网络[15]。在这一交互作用的网络中,行为主体之间往往会形成密切的关系。潘文安[16]认为,关系强度是指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联盟网络关系强度描述了联盟成员联系的频繁程度和组织资源对联系承诺的程度[10],反映了特定关系的双方或多方通过联盟关系传递资源量的多少[17]。
随着联盟成员之间关系强度的提高,企业之间的联盟活动更频繁,合作中投入的资源数量更多[18],有利于企业间形成良好的关系资本,约束联盟成员的行为,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提升共同行动和联合规划的意愿,从而促使联盟企业建立更为开放、包容的规章制度及契约安排,放松对合作项目的制度限制,使联盟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各项规章制度向有利于知识治理的方向更新改进。比如,通过建立适合知识治理的分权式组织结构,赋予从事相关知识工作的基层人员更大的权利,缩减一些复杂的制度限制,从而减少对联盟企业间知识合作的阻碍。同时,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双方企业员工提供更多交流和合作的机会,联盟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员工积极传递和共享知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联盟企业的正式知识治理。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1a: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的正式知识治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联盟企业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往往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承诺的基础上[19]。联盟关系的增强能够提高联盟双方的互惠意识,促进企业建立良好的知识分享氛围,形成宽松的管理风格,鼓励员工积极共享知识、交流经验、分享心得,并使之成为一种组织习惯与心理契约,促进联盟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此外,联盟企业之间紧密的关系能够克服合作伙伴间的文化差距[20],有利于双方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不断向对方学习,使联盟成员在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更好地契合联盟企业的知识管理活动,促进联盟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b: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联盟能力的中介作用
联盟能力是企业通过学习、共享和应用联盟管理的技巧和经验所形成的联盟管理能力[21]。联盟企业之间的关系强度越高,企业之间的交流互动就越频繁。通过不断的互动,企业会积累大量合作知识和经验[22],这些知识和经验会逐渐在企业内部扩散开,融入到企业日常活动和管理中,提高企业对联盟合作项目的协调管理效率以及对各种资源的整合效率,进而提高自身的联盟能力。同时,紧密的联盟关系能够为联盟双方提供更多一起解决问题的机会,并且随着关系的增强,双方情感上的认同度也逐渐提高[23],当联盟合作中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时,联盟成员更愿意通过交流磋商共同解决问题,企业间情感的认同会使企业间的分歧逐渐减少,企业的联盟能力也会随之增强。
一般而言,在联盟企业中,竞争与合作总是同时存在、相伴而生的,这导致很多企业存在顾虑而不愿意充分共享知识。作为企业的一种外部能力,联盟能力主要体现在企业对联盟合作的促成、驾驭以及企业自身的管理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在达成联盟契约的同时,还能够帮助企业采用合理有效的程序和机制,促进联盟知识活动顺利开展,有利于联盟企业内部知识治理。从正式知识治理的角度来看,拥有较强联盟能力的企业能够借鉴联盟活动中的知识管理经验,运用有效的管理控制手段加强对企业内部员工的引导和控制[24],并根据联盟知识合作的需要对企业自身知识治理的相关制度、契约等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使联盟企业逐渐形成合理高效的契约规定及制度框架,发展有利于联盟合作的组织架构及激励计划,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知识治理。从非正式知识治理的角度来看,具备较强联盟能力的企业能够通过一些跨文化管理培训使企业更好地认识联盟企业间的文化冲突,加深彼此的文化理解和认同[24],形成更加开放多元的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在知识治理过程中形成更加和谐的组织氛围与行为规范;同时,联盟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够在知识管理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帮助企业在知识管理活动中勇于革新,灵活应对,有助于企业形成创新、高效的管理风格,促进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可见,联盟企业间的关系强度能通过促进企业联盟能力的提高进而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a: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2b: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3 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消化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25]。在紧密的合作关系中,联盟双方彼此具有高度的信任,能够促进企业建立正面、积极的行为预期,使其更愿意承担风险,积极地进行信息分享[26],从而帮助企业更容易通过联盟方获取有价值的知识,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知识吸收能力。此外,企业之间较强的关系意味着双方的交流互动频繁,沟通渠道顺畅,双方能够有更多机会就知识互动中存在的难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将知识以易于理解的形式来传递表达,有利于联盟企业对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获取、吸收和转化,由此提高联盟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
在联盟企业的合作过程中,知识的传递和交换充满了不确定性。知识本身的复杂属性造成了企业对知识理解和吸收的困难,使得联盟企业间的知识获取和转移很难顺利进行[27]。作为企业的一种内部能力,知识吸收能力的积累能够促使联盟企业快速准确地识别和获取所需知识,并充分理解外部知识,将外部的复杂知识简单化,隐性知识显性化[28]。联盟企业运用知识吸收能力能够将获取的新知识与既有知识进行整合,使外部知识内化为企业自身的知识,促进知识转移、共享和使用最优化,从而有效实现企业知识治理。同时,从正式知识治理的角度来看,联盟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越强,越容易吸收外部的一些显性知识和经验,帮助企业更好地构建并完善知识治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管理架构等,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知识治理。而在非正式知识治理方面,较强的知识吸收能力还能帮助联盟企业识别外界的隐性知识和潜在信息,使联盟企业从外部环境学习中吸收有效的知识管理经验,帮助联盟企业形成适合知识治理的组织氛围和管理风格,促进联盟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因此,联盟企业之间紧密的关系有助于联盟企业提高自身的知识吸收能力,进而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b: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确定了各变量测量量表的初始题项。为确保相关题项能准确表达其初始内涵,对于一些英文文献的测量量表,本文采用“翻译—回译”法,翻译成中文并回译成英文,通过比较、分析,形成最终的中文题项。其次,邀请了4 名相关领域专家对各变量测量量表的指标选择、可信度、完整度和内在逻辑等进行分析,并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最后,选取了拟调研企业中的5 位中层管理者进行访谈,就量表的语言表达和措辞等展开进一步探讨,并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进行了完善,以方便受访者更准确地理解问卷内容。
关系强度量表主要参考了Capaldo[29]、彭伟等[30]的研究成果,从与联盟方的互动、资源投入量、合作范围、合作关系4 个方面测量。知识治理量表参考Lawson 等[31]、曹勇等[32]的研究,分为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2 个维度,其中,正式知识治理量表描述了与知识治理相关的奖励机制、晋升机制、组织结构、部门合作、规章制度5 个方面;非正式知识治理量表包括知识治理的氛围、风格、管理的公平性、员工交流4 个方面。联盟能力量表主要参考Schreiner 等[33]、刘景东等[34]的研究成果,从联盟的协调机制、工作调整、问题解决以及对联盟方的支持4 个方面测量。知识吸收能力量表则主要参考李刚等[35]、Zahra 等[36]研究成果,从对外部知识的判断、理解、融合和应用4 个方面测量。本文涉及的变量均采用李克特5 级量表进行测量。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企业性质、所属领域以及调研企业与联盟企业是否属于同一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采用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值进行衡量;企业性质包括国有/国有控股、集体/集体控股、民营/民营控股以及其他,分别赋值1、2、3、4;产业类型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分别赋值1、2、3;调研企业与联盟企业属于同一行业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2 调研与样本回收
本文主要采用判断抽样,并辅之以滚雪球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将问卷通过某高校MBA、MPAcc 学员以及关系网络发送至调研企业受访者,并借助邮箱和问卷星等网络形式将电子版问卷发送至相关企业受访者。在问卷发放过程中,调研团队对问卷中存在的不易理解的语句和术语进行及时解释,尽可能提高数据可靠性和有效性。问卷收集历时2 个月左右,共计回收192 份,剔除27 份不合格问卷后,最终得到165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5.937%。
本文采用Harman 单因素分析方法进行了同源偏差检验,把所测量变量的所有题项放在一起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0.955%,表明本文数据的同源偏差不严重。
2.3 样本特征
本文针对样本企业的规模、性质、产业类型以及与联盟企业是否属于同一行业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1 所示。可见,员工人数为1~50 人、51~200 人、201~500 人、501~1 000 人、1 000人以上的企业分别有42、36、36、26、25 家;属于4 种性质的企业分别有114、21、16、14 家;属于第一、二、三产业的企业分别有5、48、112 家;此外,有128 家企业与联盟企业属于同一行业,另外37 家企业与联盟企业属于不同行业。

表1 样本特征
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3.1 信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Cronbach'α值和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CITC)进行信度检验。由于题项AC1 的CITC 值为0.256,且删除AC1 后联盟能力的Cronbach'sα值增大,因此删除AC1。删除AC1 后的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Cronbach'sα值均大于0.7,且所有题项的CITC 值均大于0.5,表明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本文所采用的量表均是在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与该领域专家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形成的,因此,该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由表2 可知,各变量的KMO 值均大于0.7,且都通过了Bartlett 球体检验,表明该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各变量的题项均能聚合为一个因子,且因子载荷均大于0.5,累计方差解释率最小为61.284%,这表明该测量量表的聚合效度较好。

表2 信效度检验结果
3.2 回归分析
3.2.1 关系强度直接作用的检验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直接作用,第一步放入控制变量,第二步放入自变量,构建了模型1 至模型4。其中,模型1 和模型2 检验关系强度对正式知识治理的直接影响;模型3 和模型4 检验关系强度对非正式知识治理的直接影响。
由表3 可知,所有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均满足标准(Tolerance>0.1,VIF<10),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模型1、2 可知,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1.042,P<0.01),假设H1a得到支持,表明联盟企业间关系强度的提高能够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知识治理。同理,由模型3、4 可知,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1.262,P<0.01),假设H1b也得到支持,表明联盟企业间关系强度的提高能促进联盟企业的非正式知识治理。可见,联盟成员之间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实现。

表3 关系强度直接作用的回归结果

表3(续)
3.2.2 联盟能力中介作用的检验
验证联盟能力的中介作用时,首先检验关系强度对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其次检验关系强度对联盟能力的影响,最后检验关系强度和联盟能力对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依次构成模型1 至模型7。其中,模型1、2、5、6 检验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中的中介作用;模型3、4、5、7 检验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中的中介作用。
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在模型5 中,关系强度对联盟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906,P<0.01),而模型6 中,联盟能力对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显著(β=1.148,P<0.01),同时,自变量关系强度的系数也显著(β=0.182,P<0.01),这表明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a成立。模型7中,联盟能力对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仍然显著(β=1.086,P<0.01),同时,自变量关系强度的系数也显著(β=0.278,P<0.1),这表明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b得到验证。

表4 联盟能力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
此外,本文采用Bootstrap 方法进一步验证联盟能力的中介作用,设定样本量为5 000,置信度为95%,所得Bootstrap 置信区间分别为[0.837,1.256]和[0.727,1.266],均不包含0,表明联盟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2a和H2b。可见,联盟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过程中均发挥了“中介物”作用。
3.2.3 知识吸收能力中介作用的检验
根据中介作用检验步骤,本文构建了模型1、2、8、9 检验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构建了模型3、4、8、10 检验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与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由表5 中的检验结果可知,模型8 中,关系强度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显著(β=0.890,P<0.01),同时,模型9 中,关系强度和知识吸收能力的系数都显著(β=0.480,P<0.01;β=1.036,P<0.01),可见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3a成立。在模型10 中,关系强度和知识吸收能力对非正式知识治理的系数也同时显著(β=0.383,P<0.05;β=0.988,P<0.01),说明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非正式知识治理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3b得到验证。

表5 知识吸收能力中介作用的回归结果
同样,本文采用Bootstrap 方法进一步验证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设定样本量为5 000,置信度为95%,所得结果的bootstrap 置信区间分别为[0.713,1.135]和[0.621,1.156],均不包含0,表明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3a和H3b。可见,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过程中也起到“中介物”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构建了“关系强度—成员能力—知识治理”的研究模型,并就所获取的165 个样本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究了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影响,并分析了企业外部的联盟能力和内部的知识吸收能力在此过程中的双中介作用,揭开了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作用“黑箱”,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关系强度能够显著促进联盟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研究结果表明,联盟关系的提升能够提高企业之间沟通合作的效率,推动联盟知识合作顺利进行,从而对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往研究已经证实了关系强度能够促进联盟合作绩效的提升,本文将视角转向联盟企业自身的知识治理,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证实了关系强度促进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观点,拓展了知识治理在联盟企业中的研究,表明紧密的联盟关系为联盟企业知识治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回答了“联盟能给企业带来什么”的问题。
第二,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双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强度有助于联盟成员能力的培养,提高了企业的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了联盟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研究结果遵循“关系强度—成员能力—知识治理”的作用路径,表明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在关系强度对联盟企业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过程中均起到“中介物”的作用。已有研究分别证实了联盟关系对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的促进作用[37-38],本文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关系强度能够通过联盟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促进企业的知识治理,是对现有研究的进一步延伸,揭示了关系强度影响联盟企业知识治理的内在机制,回答了“成员能力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
4.2 启示
第一,积极构建并维护联盟关系,增强联盟成员之间的“向心力”,促进企业知识治理。联盟企业应提升对关系资源的重视程度,积极培育并加强联盟关系。主动与联盟伙伴进行充分交流,在合作过程中保持及时有效的沟通。通过组织企业间的联谊和交流会等活动,促进彼此间的情感认同,减少联盟冲突。自觉履行联盟契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增进联盟信任。积极扩大合作范围,建立良好的关系资本,尽可能与联盟方达成共赢,实现资源共享。通过联盟关系的不断增强,促进联盟企业自身知识治理水平的提升。
第二,注重联盟能力的积累,发挥联盟能力的桥梁作用,提高知识治理水平。联盟企业应该建立跨企业的沟通与协调机制,确保与联盟伙伴沟通渠道顺畅,并根据联盟目标在其内部建立起针对性的协调处理程序,设置跨部门合作机制,提高协调效率,有效推动联盟活动的开展。同时,悉心听取联盟伙伴的建议,在面临困境时主动承担责任,增进联盟企业之间的信任。通过在合作过程中不断的归纳、总结,积累丰富的联盟经验和能力,从而促进联盟企业更加高效的知识治理。
第三,积极培育知识吸收能力,提升知识治理效果。联盟企业应该在内部建立有效的知识管理系统,并通过强化技术知识培训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从而促进企业在联盟合作中快速准确地识别并获取所需外部知识。同时,通过积极组织内部知识分享活动,鼓励员工进行跨部门信息分享,使员工之间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吸收外部知识,加快新知识的转化应用。通过加强企业对新知识的识别、获取、转化和应用,促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积累,从而提高联盟企业的知识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