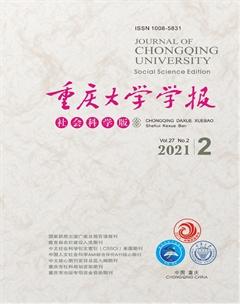江南区域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检讨和省思
孙竞昊 卢俊俊
摘要:方兴未艾的环境史视野和方法可为江南区域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东南沿海源于地理区位的原始自然生态条件,规范了以水利开发为枢纽的区域农业经济和文明形态的指向。进入帝国时代以来的分分合合、起起伏伏历程中,长江中下游自然资源的优势日渐发挥出来,其经济在六朝时期稳步增长,终于超过了成熟开发早的黄河流域,尽管政治中心大多依然在北方。元明清阶段的长江三角洲形成了以平原稻田为核心、商品化的多种经营为特色的区域环境—经济—文化模式,不但在生产力、物质财富上,在全国独占鳌头,而且也展现出一定时空单位内自然与人为良性相互作用的美景。然而,竭尽自然资源的“江南模式”从长期环境后果看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其“先进性”的进一步突破也湮没在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和王朝循复的轨辙里,没有出现如“英格兰模式”那样现代性的滥觞。
关键词:江南;环境史;开发;文明类型;省思
中图分类号:K206;X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1)02-0248-16
一、引言:环境史作为区域史研究的新门径
中国大陆的区域史研究真正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彼时的学术关切多与若干宏大叙事问题和主题相连。90年代初以来,注重实证性成为区域史研究的主流。迄今取得最为显赫的成果当属江南史,尤其在社会经济史领域。江南史探讨的一个传统是贯穿其中的大问题情结;即便是细化、“碎片”的個案研究,也无法完全回避何以中国没有自行“走出中世纪”的拷问。如近20年来“加州学派”的王国斌、李中清、李伯重、彭慕兰等就江南的经济、资源、人口、社会组织与国家权力都进行了颇有新意的研究或再研究,诸如“早期近代”“早期工业化”等比较语境中的话语范式颇有反响。同时,门槛高的江南史研究如何突破既有的瓶颈,成为近年来的一个普遍困扰,而环境史研究的突起是包括江南在内的区域历史研究中一个主要风向。
尽管以往的历史书写对环境多有关注,但环境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于今蔓延为国际上最为前沿的显学之一。与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相比,“环境史”不仅仅是研究“环境的历史”——即环境不仅仅作为研究的对象和领域,而且更为重要地在于视野、方法、思维、辨识的路径:在整体、有机的史观下,生态环境不再充当背景或布景的被动角色;而人作为自然界中最具能动性的“超自然”物种,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中,塑造和重塑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社会与文化形态正如休斯对环境史定义:“环境史是一门历史,但并非只是环境的历史,而是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 ,[1]1。
伊懋可和马立博是把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先驱。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选择了三个区域“特例”,其中之一为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从物阜到民丰”的嘉兴;而马立博的专著《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则聚焦于珠江三角洲。在方兴未艾的江南环境史研究成果中,以王建革的通史性专著《江南环境史研究》最具分量。至于把江南环境史作为博硕论文选题的新生代,其学术路数争奇斗艳,如对GIS、数字人文等新知识、新方法的运用。这些环境史取向的新尝试正在深化我们对江南史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史的认识王利华则是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即:“环境史研究需要具备跨学科知识和素养;研究者除了需要知识储备、宽阔眼界、复杂头脑,更重要的是具备更加开放的态度与学习精神,准备接受超越本学科以外的知识和观念。”,[2] 。
“多元一体”格局常指称庞大包容、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及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费孝通阐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认为在中华文明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且独具个性的区域差异;但在不同区域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过程中,渐次形成具有认同性的“多元一体”格局。 ,[3]3,36,[4]。土肥、物阜、景美、水秀、民安、文盛是江南千年来的形象,无论在开埠前的传统时代,还是在欧风美雨沁润下的近现代。高度繁荣的江南区域文明的独特模式是在其环境开发的历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本文旨在对自然与人的互动中对江南开发和发展所蕴含的线索进行考辨,并提炼出与既有环境史讨论相关的重要命题进行反思,期以裨益于江南环境史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环境史探讨。
二、关于江南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区域形态
中国传统时代培育了十分成熟的农耕文明,尤以江南最为发达、先进,于明清时期臻至巅峰,也是世界上传统农业效益最高的区域之一。江南独有的地利、天时,是该地区人类赖以生存、文明赖以发展的首要自然前提和制衡;而且自然因素也是变化着的,尤其是与人持续地相互作用。所以,应该从地理区位及其相关的自然条件发凡,并总结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诸种因素。
(一)地理区位与天然景观及其变迁的特性
如年鉴学派所言,自然界的变化通常是渐进的,所以具有内在同质性的空间界域在一定的时间单位内相对固定。尽管如此,区域亦会因为自然本身和人为的因素而变动不居,而且也时有突变的情况,特别是随着人力干预自然的力度的增大和偶然事件的发生。
历史上“江南”指称的地理范围不尽一致,有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界定的学术标准也不尽一致,主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但诸说异中有同,总的说来是指长江中下游流域;到了明清阶段,更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太湖带状冲积平原流域。笔者赞成李伯重从生态地理出发的说法:明清时期的江南涵盖东部的江南平原、西北的宁镇丘陵、西南的浙西山地 [5]34,67。而平原基本坐落在苏、松、常、杭、嘉、湖六府,也就是学界所集中讨论的江南鱼米之乡之所在。
关于地理区位衍生的自然条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学术界已有充分的论述。笔者阐明的是,虽然自然因素总体上变化相对缓慢,但来自人类开发、改造自然的行为在江南生态环境沉浮中发挥的作用尤为显著。在对江南地区大规模开发带来日益增长的物质回馈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原始生态的无情破坏。江南的自然植被逐渐由农业植被和栽培树种所替代。尤其到了后来,原始森林被滥伐殆尽;而自然土壤亦因各种农业活动而人为熟化为耕作土壤,其中以水稻田为主。人为因素导致的结果,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第二自然或人为自然(humanized nature)。其环境与社会后果十分复杂,可以说有利有弊且相互转化。
(二)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之述评
缘于所在区位的气候与地文,江南最充沛的天然资源就是水。司马迁曾以“三江、五湖之利”来概括“无冻饿之人”的“江淮以南”[6]3267,3270。“三江”“五湖”的指谓,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地貌及时人的观察不尽一致,但我们还是大约地认定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北向南的长江、吴淞江(吴江)、钱塘江(浙江)流域;中心是太湖盆地
关于“三江”的区域界定,笔者趋向于狭义的江南指称,即“长江以南,岭南以北”。,[7],[8]31-42。
一般认为,太湖由潟湖演变而来
如张修桂所论:“太湖及其附近地区自晚更新世末期以来,由于内外营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经历着一个由沟谷切割的滨海平原景观,演变为蝶形洼地的泻湖地貌形态,其后由于出入口通道的变化,泻湖演变为太湖。”,[9]。这种湖沼平原的疏涝是一项异常艰巨、繁重的工程,然而一旦开发利用,即为农业提供极其优质的土壤、水文条件。而且,河流、湖泊、沼泽、池塘,以及后来的人工河道(水渠、运河)、水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构成了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水网系统,除了便于农业灌溉,又服务于前现代通常比陆路更为节省和高效的交通运输
张海英以生态条件为起点分析了明清江南以水路为主的交通网络。 ,[10-11]。隋唐以来,作为京杭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的江南运河,则成为江南区域内和跨区域的重要干线。
这些优势是基于传统农业社會而言。经过人类长期垦殖经营,到了适值小冰期的明清阶段,除了沿海滩涂外,江南基本上已被整改成水网平原和水网圩田平原,以及湖荡平原和湖荡圩田平原,盛产稻、麦、棉、油料和桑蚕。但从如何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瓶颈的角度看,彭慕兰等人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煤、铁等矿产,燃料等资源贫乏,对于可能的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能源与动力而言是个明显的缺陷[12]。这也是为什么江南商品化、城市化如此发达,但江南人民的主要生产活动依然拘囿于农业经营以及建立在种植业基础之上的加工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李宏图等人认为:“16世纪的英国农业革命,是一场持久的农村资本主义改造运动,使得英国的农业经济具有更为深刻的商品化、市场化性质,亦使英国农村封闭落后的社会面貌、僵化腐朽的封建关系遭到破坏、瓦解,是为工业革命坚实的物质基础。” ,[13-14]。
三、关于明之前江南开发与区域文明发展的轨辙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各地区自然条件相差甚巨,从而造成自然与人互动中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极大的区域差异,而区域间不平衡、不同步性,以及文明中心的移动,都是通常现象。江南的经济及文化后来居上,在明清时期雄踞执牛耳之地位,这可从史前开发以来的脉络中寻得缘由。
(一)东南沿海史前的原始性开发与东周时期的一度崛起
被称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流域开发早,长期作为华夏文明圈的中心,并在壮大中融合各地文明。相对而言,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地广人稀,虽早有原始性的开发,但由于排涝防洪和沼泽地的处理所需要的大量的人力和较为先进的工具、技能等条件尚不具备,所以生产活动长期滞留在火耕水耨的原始经营阶段,难以建立起稳固有力的政权进而发展出高级的文明。
然而,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表明,南方地区也存在过多个璀璨的史前文明。南方农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河姆渡文化遗迹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与相对干旱、寒冷的北方的农作物品种粟和稷形成对比。而良渚文化遗迹显示出水利设施在稻田开发中的突出作用,体现在具有防洪、防潮、航运、灌溉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的拦洪水坝系统上
洪焕椿用“金三角”来比喻长江三角洲,认为其优越的生态条件孕育了河姆渡、良渚等远古文化以及之后不断壮大的区域文明;邹逸麟、赵志军等学者在强调河姆渡、良渚等文化遗址的社会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同时,亦突出水利设施的重要作用。,[15]1-6,[16]344-346,[17]。然而,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没有像黄河流域那样连续性演进。
东周时代,各诸侯国、各地方政权竞相“富国强兵”。春秋后期,吴国雄起称霸,逐鹿中原;战国之初越国灭吴,势力纵贯南北。“兵强”的根柢是“国富”,这就是东南地区吴越地的早期开发路径:大举兴修水利事业,用于农业灌溉和交通运输
春秋吴越地区虽处于草莱初辟时期,但时至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时代,大力开发荒田,修作陂塘,推动农业、水利的渐次发展。,[16]494-495,[18]。先秦时代吴越地区的开发总体说来还是粗放型,其尚未开化的野蛮民风,一如《越绝书》中的一段话:“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19]吴、越先后一度称霸的盛景不过为昙花一现。
(二)秦汉时期东南吴越故地的边缘化及汉末以来的重新崛起
秦、汉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制形态的奠基时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构架成型。秦、汉先后持续地向南开拓,逐步把以前视为“化外之地”及与北方正统政权若即若离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纳入帝国的正式政区内,于是东南成了秦汉帝国不容分割的一部分。而失去了区域独立性的东南,其经济与政治的地位在帝国格局里也被边缘化了
秦统一中国以后,对东南地区采取同化和强迫迁移的政策,其目的多在于削弱其政治地位及影响力。 ,[20]。但是,相较于早期的粗放型开发,此时的开发已渐次趋向于成熟型农业经济陈桥驿认为,以于越为代表的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在春秋战国以降经历了从迁徙农业到比较高级的定居农业阶段,精耕细作程度呈现显著的提高,农田水利工程得以修建,东汉绍兴鉴湖的修筑是为典型的案例。 ,[20-21]。
汉末及三国鼎立时期,北方战乱剧烈,人口大量流失,黄河流域不仅经济急速凋敝,生态结构也因战争蹂躏和长期开发益发衰退。北人蜂拥南迁,其先进的经济组织和生产技术推动着南方农业经济的实质性开发。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潜在的优越自然条件得以充分开掘和发挥,生产力水平未久便高于其他地区。南朝士族沈约(441—513)的一段评论可见一斑:“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22]
(三)中古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环境开发与经济发展区域模式的确立
农业社会的基本劳动是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其他生产活动均为附属、补充,这种典型的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相对单一型自然经济的特征在北方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而长江中下游的自然条件与北方殊异,开发又晚,由此在六朝分裂时期形成了经济生活的特殊性,学术界多有论述,兹简述如下。
一是水利技术在稻田建设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排涝与灌溉上。南方各地根据农作的不同需求,对江、河、湖、泽等自然水系加以利用,得以建立良好运行的水利排灌系统,从而起到防害、增产的效果。总体说来,平原上的“治水”事业较为细碎、精致,且地方性陂塘等水利工程较为发达,与北方由政府主导的大工程不同,适宜当地稻田的栽植与灌溉[23-24]。
二是沼泽改造中常见疾病的克服。如疟疾、痢疾等“瘟疫”(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是稻田开发进程中的重要安全保证。瘟疫易滋生于低洼多水的沼泽区,所以田间排水能力的提高有效地阻断了疾疫的传播途径。此外,医学、药学的进步在疫病防治上不断取得进展,对疟疾等疫病的种类、症状和诊治案例在文献上皆有详细记载
六朝时期关于以疟疾为代表的疫病应对,可以从国家、社会及个人层面探讨。而且医学防疫技术的进步,不仅体现了时人对于瘟疫认识的进展,同时包括了医学体系、医事制度的日趋完善。,[25-26]。
三是人口压力对农业等生产的集约化和商业化的促进。基于南方相对安定的局面,北人不断南下,人口在较短时期内的大量迁入形成了地狭人稠的尖锐矛盾。迫于人地关系的加剧紧张,江南人民除了从事精耕细作的集约型种植业外,纷纷从事工、商等“货殖”副业,经济活动多样化,市场化程度高
漆侠认为宋代江南地区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矛盾,解决矛盾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途径就是精耕细作,改善耕作技术,力争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李根蟠进一步指出,人口南迁在造成南方人口压力的同时,促使了南方日渐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也加速了南北方经济重心的转移,[27-28]。
六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稳步成为中国新的经济重心,而且相比于波动起落过大过多的北方,大规模的动乱较少,经济活动大致保持着持续嬗进、稳定上升的态势,并在之后的隋唐宋时期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板块[29]。
長江中下游地区历经隋、唐、宋约700年的时间进程,相对稳定、统一的政治状况推动水利建设进入稳固、发展的新阶段。隋代出现了全国性的人工河道网络——大运河。其中,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贯通南北。自此,历唐、五代十国、北宋,长江、钱塘江流域的漕粮、百货可以抵达中原北方地区,化解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矛盾。唐代广修海塘使得东南沿海平原减少了海潮侵蚀的危害,有利于内河、湖泊水利、水运体系的稳定,既维护了交通安全,也保障了农业用水。唐王朝还致力于修整湖泊、疏治河网等多项水利建设。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立国近100年,重视民生,大兴水利,东南沿海进一步开发。北宋承继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区域急遽发展的步伐,东南沿海成为国家财政与经济的保证,以至于在人文、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都急剧上升;到南宋时,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彻底南移
正如周魁一阐析,“相对稳定的隋唐宋时期,为经济发展开创了前提条件,长江流域的经济得到长足的进步,完成了经济重心由黄河中游地区向长江下游地区的转移,而此时期水利建设的重要特征就是太湖地区农田水利系统的治理、以大运河开凿为标志的内河航运网建设以及航运和农田水利等工程技术的普遍创新等。”,[30-31]。
四、关于元明清时期江南环境、资源与农业经济的模式
蒙元重修南北大运河转运漕粮,后来主要靠海运。而之后的明清两代,帝国的财源主要来自江南,承载主要漕运任务的京杭大运河成为生命运输线。“苏湖熟,天下足”“苏松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等谚语,都生动地反映了宋元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地位。而明清时期江南“重赋”“赋税甲天下”的说法,固然说明来自中央政权的压榨,也反映出国家对江南的倚重。明清时期的江南还涌现出一些经济、文化领域的新气象,广为中外学界注意。对此,先有“资本主义萌芽”之说,后有“早期近代”“早期近世”“早期工业化”等范式的讨论。明清时期(或曰“中华帝国晚期”)江南的环境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中关于农耕生产技术,学术界已有成熟的经验主义研究,这里的归纳主要依据李伯重在《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书中“第三章:技术”和“第四章:农业资源利用的合理化”里的相关论述。但本文旨在构建一个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类型,如同黄宗智在其江南史专著中表达的初衷:“重在探讨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抉择作用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中的每一局部都是与整个系统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的。”,[32]。
(一)水利工程与地表景观
水环境是江南农村生态环境的中心,丰富的水资源为江南农业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潜力[8]558。而江南农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水资源的利用效能。水利的发生与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结构的规范,出发点是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与生产需求,所以受到生存需求、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等多种因素的制导。与北方一般由国家主导大型水利项目不同,江南水乡的水利建设经常由地方精英主导
王毓铨等人认为,明代兴修水利的三大成就为:“以保护灌溉农田为主要目标的全国各地常年性的水利工程建设与维修;以确保国家财赋重地为根本的江南苏、松诸府水患的治理;以保障漕运为中心的国家治黄工程。”这是宏观治理方面,但具体到长江三角洲地方层次的具体治水项目,政府多依赖地方社会的力量,并取得一定成效。
,[33]226。江南人民因势利导地发掘和发挥了既有的环境与资源便利优势,工程量细小、繁多,基础设施零散;而若干人工运道的开凿和使用基本上属于对天然水系的疏导性治理。
这种开发带来的地表特征表现,一是兴盛的水利景观:海塘、运河、水渠、水闸、堤坝、池塘星罗棋布,道路与桥梁环绕其中,保障了农业生产与生活的稳定。二是发达的圩田设施及功能:这是肥腴江南水乡最有代表性的景观。圩田的水环境与土壤环境对江南农业的生产活动有一种动态稳定的效用[8]558。加之大力开河筑圩,排水御洪,江南呈现出独具一格的水网圩田工程,故而用于农地灌溉和保持土壤(淤泥)肥力的蓄水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34]。但同时,大规模围垦江湖滩地,破坏了原有的水文生态环境,加剧了洪涝灾害[35-36]。
(二)耕作模式
伴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人口压力、人均耕地有限诸问题愈来愈尖锐。江南民众出于农业发展与资源利用合理化的目的,致力于传统农业技术的改进与推广。
(1)季节性整地:整地,是指作物耕种或移栽前进行的一系列土壤耕作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翻耕、耙田、犁田等,目的在于提高肥力,创造良好的土壤结构和表面状态,为作物生长、田间管理提供持久的良好条件。除了季节性整地外,农民亦使用各种方式以节约人力劳动,最为典型的是牛耕的使用。明正德《松江府志》载:“(水车)有不用人而以牛运者,其制为木盘如车轮,而大周施牙以运轴而转之,力省而功倍。”[37]7土地的精耕细作,使得人畜资源、土壤资源得以有效利用,推动了劳动生产率、农业产量的提高。
(2)大量施肥:江南一年二熟制的种植制度,对于土壤肥力有较高的要求。除广施各种农家肥外,饼肥的引入对江南的农业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李伯重所说,“清代前中期江南,肥力使用有重大进步,堪称‘肥力革命。其中包含饼肥的引进”[5]53。得益于便利的水运交通,江南地区得以从华北、东北等地获得大量的肥料
过慈明在肯定外地输入江南饼肥数量的增加,有利于缓解江南农业缺肥矛盾的情况之外,也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即受制于自然经济和农民有限的购买力,江南农家肥的商品化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是有限。,[38]。对于土壤培肥的迫切需求,甚者三耘三挡,即“三通”。以松江府为例,“肥田者,俗谓膏雍。上农用三通。头通红花草也。二通膏雍多用猪践。三通用豆饼”[39]。
粪肥、绿肥、饼肥等有机肥亦广泛使用,提高土壤结构的优化程度。在农业史学者看来,利用各种废弃物质酿肥、施肥,施行作物轮种和农林牧渔多种经营,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利用,不断改良土壤,是中国传统农业得以数千年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废弃物的循环利用,颇为符合园艺型生态农业的特征。
(三)种植制度与技术
(1)选种与种植制度:对于江南水乡而言,水稻是主要栽培品种。基于生态环境、品种特性的不同,水稻的类型主要分为早、中、晚三种,以适应不同季节中光照、温度、水分等条件的变化。同时,选种亦有多种标尺,如作物长势、耐肥性、耐水性、产量、品质等。故而选种过程颇为精细:农户挑选肥实光润、颗粒饱满的良种,种植于肥沃土地上进行精心施肥与灌溉,收成之后,从中再选更加优质的种子进行养种,如此“三年三番后,则谷大如黍”[40-41]。
选择适宜本地自然条件的稻种,不仅有利于提高产量、减少土壤肥力消耗,同时亦助于推广一年二作制的种植制度。江南的种地模式有二年一作、一年一作,稻、麦一年二作制,重视轮作制、间作制、翻田制的应用。但以水稻与春花(即冬季作物)轮作的二熟制比较普遍。当时主要的春花作物是麦、油菜和豆[42]324。由于耕地复种指数的提高,使得亩产量亦随之增加。同时,春花作物的种植,更是大幅度地增加了耕地亩净产值[43]。清嘉庆《嘉兴府志》载:“春花熟,半年足。麦及菜、豆子多收,谓之春花好。”[44]
(2)选地:平原因地制宜开发成稻、棉、桑田。不同农作物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各有差异。基于作物的生长习性,合理利用水土资源颇为重要。水稻性喜温湿。棉花耐旱,适宜疏松、通气性强的土壤性质。而桑树是喜光树种,但不耐涝。经过长期的农业发展,江南平原逐步形成三个相对集中的作物分布区:低田地带种植水稻,高田地带适宜种棉,杭嘉湖平原及太湖周边宜于栽桑
范金民对于棉花、桑树等商品性作物的种植区域、面积的论述,见氏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6页);李伯重对棉、桑、稻等作物的分布区、种植比重的分析,见氏著《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王湘云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6-71页);谢湜则是以清代常熟地区为例,进一步分析高乡、低乡的搭配问题,认为对高乡近海植棉、低地圩田建设的考察,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地域社会运作和区划格局变迁的丰富视野。见谢湜《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历史地理》2007年第1期)。
,[5]66-71,[45-46]。
相较于平原地带,山地、丘陵的水土条件有所不同。供水不便、地势较高、土燥多石的生态环境,虽不宜于种植粮棉,但是却有利于桑、茶、竹、木和各种经济林木的生长[5]75。清乾隆《安吉州志》载:“山乡鲜蚕麦之利,茶虽工繁利薄,然业此者,每藉为恒产云”[47]。此外,山地资源的合理使用,固然有利于农户的生存发展。然而在坡度较大、不宜种植的山地环境中,经济作物排挤自然植被,则会对外在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48]97-98。
(3)经济作物种植的比重日渐提升。仰赖于适宜的水土资源以及发达的市场体系等优势,江南地区种植经济作物的比例越来越高。农户积极地改变生产结构,调整作物种类,农业生产得以多样化发展。以正德年间松江府丝、棉业为例:“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37]10正如王家范所言,丝与棉闯入农村经济生活,改变了农村家庭的收益结构,经济作物和副业的比重日增,有的甚至发生倒置,蚕、丝或棉布的收益成为主业[49]。以至于,长江下游的粮食需要从中游的湖广等地輸入。
然而,江南农户弃农亩而就蚕桑,并非仅是利润的驱动,而是谋生的必要手段[50]。正如明末徐光启所言:以杭嘉湖诸府为代表的江南丝、棉等手工业所得,“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51]。在明清江南赋税压力之下,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种植结构,渐次趋向多样性、商业性,是为民众努力以副补农、以工补农的积极调适[52]。
(四)劳动组织
(1)密集的劳动与资本投入和合理的劳动分工:传统农业生产中,提高作物产量的途径之一,是提高生产过程的集约化。明清江南农业集约经营的主要形式,就是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数量,提高精耕细作的技术。以明前期太湖地区的水田为例,垦耕土地中之牛耕尚未普及,无力畜牛的普通农户只能使用铁搭等农具实现深耕效果。效率虽不及牛耕,但是加之人力投入和肥料使用,亦可以达到增强土壤的蓄水、保肥和抗旱能力的效果[53]。
此外,男耕女织或依据性别差异而從事不同的劳动,在纺织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日渐盛行。甚者在农历四五月即农忙与蚕忙季节,农家往往宁可雇佣劳力下田帮忙,也不愿他事影响妇女养蚕 [5]157。明末嘉兴府海盐县的蚕桑业可见一斑,从初始“素不习蚕”,到“蚕利始兴”,最后于天启年间形成“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的景象[54]。而时至乾隆年间的湖州府,更是“蚕事……渐盛于江南,而湖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55]。况且,较之大田农作,蚕桑或棉纺对体力、时间、年龄的限制颇为宽松,老幼均可有所协助。更重要的是,如王国斌等学者所揭示的,与工业革命前欧洲同时期的城市制造业相比,享有长期和平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农村手工业具有更大的竞争力——这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不必“投入大量资本购买机器和工具”,没有仰赖“信用资本”的大的“借贷需求”[56]120-122,175-178。
(2)多种、综合经营的“副业”:致力于提高农业技术与生产效率的农户,在种稻植棉外,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农林牧副渔综合生产的生态农业。以明嘉靖常熟人谈参为例,“谈氏以低价收购了大批田地,之后雇佣乡民,‘凿其最洼者池焉,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复三倍”[57]。这种合理利用生态食物链原理构建的生产模式,在产生更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亦有助于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到明末清初,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多种形式的生态农业模式纷出,如嘉湖地区的“以农养畜,以畜促农”,即“以粮食喂猪,以猪粪肥田,以桑叶饲羊,以羊粪壅桑”[48]74-75,[58]。正如李根蟠所言:“这些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把土地利用率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9]
(3)家庭丝、棉纺织手工业的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高。受益于江南发达的市场体系与畅通的贸易网络,家庭手工业产品得以在更广阔的区域进行交换。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价格运动,亦会推动家庭手工业的专业化、市场化趋向[60]4。较于稻粮,丝、棉手工业在江南市场中的需求、收益更具优势,以致出现棉农售棉买粮的现象。李伯重指出,清末江南农村妇女一年从事棉纺织的天数,至多为200日左右 [61]32。这种以丝棉纺织业为代表的家庭手工业,日渐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一家收入的主要来源。
然而江南地区高度发达的家庭手工业亦有其特殊性。一是受限于市场的需求,小生产者易处于被动的境地;二是原料、染料等材料的相对匮乏,大多仰赖外地。但总而言之,这种“为远处市场”而进行商品生产的农村家庭原始工业化过程,是手工业发展、进步的重要阶段[60]37。
(五)环境开发的张力与国计民生
环境的开发与国计民生的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表现为以下几点。
(1)人口压力下粮田的无止境开垦:缘于地少人多的处境,江南农户在拓垦耕地、开发山林方面颇具成效。但时至乾隆时期,江南的荒地开垦殆尽,而无节制地毁林开荒、围垦湖地,对于自然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48]97。以太湖为鉴,明清时期的太湖流域自身发挥着巨大水库的效用,但伴随着以圩田为代表的农业的过度开发,不断侵夺太湖周边的湖泊、沼泽及河道,一则极大地削弱了整个水利系统的蓄水功能,二则降低了排泄能力,河湖的淤浅渐次加重[62]。此外,外来的棚民把开垦山地、丘陵作为生计来源,粗放型的使用方式,导致可使用的土地在量或质上濒临枯竭。时至明清时期,南方大部分低山丘陵地区已开发殆尽[63]。换言之,山外移民在开发山区、谋求生存的过程中,自觉地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而生态环境的破坏亦由此加重。
(2)明中期以来基于商业化、货币化的赋税变革:南宋以降,江南地区已然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市场体系趋于完善,经济地位臻于高峰。然而在促使经济活动的市场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伴随着的是最大限度地从土地榨取财富
赵全鹏指出,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结构在利润、重赋等因素的驱动下,向多种经济作物种植转变,而这种转变背后不仅导致明中叶江南渐次成为缺粮区,而且对于土地的开发亦竭尽全力。 ,[64]。此外,田种稻,地栽桑,山种茶,水荡养鱼虾,国家征赋无处不及 [65]39。江南重赋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基于江南农业经济的进展而不断加重,与江南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66]。而为了弥补江南重赋后收入锐减的状况,农户须农副并进,多样种植,竭力开发外在的自然生态[67]。故而中央政府的赋税变革虽充盈了国库,但是作为国家经济基地的江南却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
(3)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脆弱化:农业生产片面地强调高效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在实现增长的同时,减弱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以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步步加剧。山林滥伐,减少森林的覆盖面积,山区水土流失现象频发,导致泥沙淤塞、土地不断荒弃,而水利事业的发展亦多不尽人意,严重影响农业的正常生产与水利排灌,旱、涝灾害愈演愈烈;部分山地的植树造林也多为直接经济效益所驱动,并非致力于遏制或治愈水土流失。时至清中期,森林政策更是以尽地力、地无遗利为重点, 农民于闲隙处植林,即“遇见闲隙之地,不可种谷者,随处栽植加意培养”,虽从中有所获利,但对于维护区域环境、恢复生态平衡并无显著助益[68-69]。
五、江南环境与人互动模式的历史价值与定位
对特定时空下历史现象的评估,除了剖析其本身,还要瞻前顾后地考察——这是历史主义原则;也要左顾右盼地思辨——这是区域比较视野,从而在历时性纵坐标与空间比较的横坐标中确立其运动中的位置和走势。
(一)“理性”的小农经营模式
李伯重高度评价江南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即合理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耕地、水面以及人力、畜力;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水平,也就是增加对耕地单位面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以获得更高的產量。他认为集约化导致了生产力(包括耕地和劳动力)的提高,而不是内卷化——内卷化虽能导致耕地生产力的提高,却只能是以降低劳动生产率为代价。江南平原上的各种劳动、资本、技术、资源因素可以合理、优化地结合,使得劳动生产率达到最优 [5]90-91,169-171。吴承明认可李伯重对生产各要素可以达到优化配置的乐观观察,但也指出,小农经营模式下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确没有催生出技术革命
吴承明赞成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有“优于领主经济”的积极作用,但“它妨碍新生产方式的建立”。进一步理解,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结构”,还是一种“社会组织”,其“形成、发展以至解体,与传统的义利观、本末观、家庭观念、多子继承,以及国家巩固自耕农的政策,榷关制度等,都是分不开的”;王国斌和他的合作者认为,“早期近代”的中国的家庭结构与同时期的西北欧相比,就生产各要素与市场的联系及其效益的视角来分析,经济效率并不一定存在差异。 ,[5]1-5,[56]50-68,[70]。
明清江南很少有大规模组织生产的“经营地主”现象
罗仑、郑志章的早期研究试图说明明末以来江南地主直接雇工经营土地可以取得高于租佃收益的优势,但他们所举零散个案无法挑战关于租佃制普遍化的“陈说”。,[15]23-49、50-67,说明中国古代租佃地主制下以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单位为基本经济细胞的结构不仅能最大化地发挥生产效益,而且能最大程度地适应市场化机制。而且,地主制下小农经济不断变化、重建的顽韧生命力,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从总体上具有“弹性”的特点[71]。
(二)增长,还是衰退迟滞?怎样一种前现代经济“增长”?
黄宗智以自己对江南和华北的研究为例,用内卷化或过密性(involution)增长来表述“没有发展的增长”,指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退、迟滞本质。而李伯重和加州学派的其他学者则强调了对“斯密式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的扩大理解,即:集约化、市场化高度发展,超越了“总产量增加,生产率下降”的过密或内卷增长范式参阅龙登高对黄宗智与加州学派相关论点的述评;王国斌辨析了对“斯密型动力”的两种不同看法,并认为在1800年之前其在中国与西欧发挥的作用并无大的差别;李伯重着眼于“早期工业化”的动力和前景,认为中华帝国晚期江南的“斯密型”工业发展,具有强劲的竞争力以及潜在的转型优势。 ,[60]11-29,[61]409-418,[72]。
但是,按照加州学派的观点,开埠前的江南及中国其他发达地区还是未能突破以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张为内容的斯密型增长瓶颈,不似发生在欧洲,准确地说在“英格兰模式”下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推动的总量与人均产出同时增长的所谓“库兹涅茨型增长”(the Kuznetzian Growth)或“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范赞登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在欧洲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相对富有效率的制度的结果,这些制度最晚从15世纪开始就已是该地区的典型特征。参阅(荷)扬·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隋福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所以,加州学派虽然高度评估“江南道路”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和发达市场,但对开埠前江南经济的定性还是与黄宗智没有根本立场上的区分[73]。
(三)“前现代技术锁定”与“高水平均衡陷阱”
伊懋可用“前现代技术锁定”与“高水平均衡陷阱”来解释开埠前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态势。他认为,虽然中国在农耕技术上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但收益被增长的人口吞噬;人口增长又驱使技术改进。然而,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在产生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取得适应一定环境条件的既有霸权并阻碍潜在的实质性革新,最终陷于所谓“前现代技术锁定”[74-75]。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受到遏制,使得传统的经济与生活停滞在较高水平上,难以冲出既有的技术、经济、环境相互掣肘的魔咒。
伊懋可的问题关怀与所谓“李约瑟难题”的旨归并无二致。李约瑟尽管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还是将其置于前科学阶段(proto-scientific approach),认为没有出现以节省劳力(cheap labor)为动机的革命性发明,尽管有机械化技术进步的潜在可能性
加州学派高度评价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的同时,也认为欧洲战争带来的竞争是一种走上“资本集约化”的可能,所以更有可能催生出工业革命。 ,[56]135-137,[76]。
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商业化与城市化途径与形态的张力及局限。以获得自然与人力资源的最大回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明清江南呈现出了高度的生产专业化、分工劳动的地域分化、市场化、城市化。这时的江南地区已不囿于自然环境因素的界域,成为一个存在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粗具“现代”意义的经济区[77]。我们甚至可以推论,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最有可能发生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地区。可是,历史的进程却并非如此弗里斯在赞同清代中国的经济实现商业化的同时,又认为清政府即使在其最辉煌的时期,亦没有尝试推动中国经济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革或者促进创新,只是努力实现静态的效率。参阅(荷)皮尔·弗里斯《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郭金兴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402页)。
。鸦片战争后的开埠,才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运动的固有规则
金观涛、刘青峰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延续称之为“超稳定系统”,认为其长期的社会迟滞,并不是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因素,而是由于中国社会宗法一体化和强控制等特性,使其只能孤立地成长,而无法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78]。
(四)19世纪的江南:危机与转机
近年来学者们常用“19世纪危机”形容中国在这期间从环境到经济到政治的全面危机 [79-80]。但对一些区域来说,危机、转机、发展并存;而且每个区域的机遇不尽一致。明代以降,江南虽不乏自生的零星民变,但皆非大规模战乱的渊薮
冯贤亮认为,时至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之际,江南地区亦无大规模战争的困扰,需着重处理的是诸如盗匪的变乱。而且盗匪之患虽会加剧江南社会的不安定,但是于全国而言,并不是最严重的。 ,[81]。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来说是飞来横祸,江南的财富、文化、人口的损失惨烈空前。但江南随后的复原和发展同样惊人。“同治中兴”,不单是王朝秩序的恢复,更重要的是兴办“洋务”以“自强”。与大多数内地城乡传统经济与社会的瓦解不同,江南等东南沿海地区奇迹般地进行了现代转型,充当了现代化的先锋。
可以说,开埠前江南经济与市场的充分发展也为现代经济起飞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以通商口岸上海为中心,向现代城市或城镇转化的市镇成为新经济网络与秩序的桥头堡,江南腹地的资源和农副产品为新型工场和工厂提供了原料,精明强干、技术熟练的江南手工业劳动者成为最早的现代工人阶级[82]。开埠以来外来资本、现代技术与国际市场在东南沿海的成功,说明了江南优越的积淀与活力。今天作为上海的广阔腹地的长江三角洲,依然生机勃勃。
六、鉴示:江南开发和发展历史经验中的自然与人
通过考察江南区域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人力、技术、组织等因素不断地改变既有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结构。这个复杂曲折之过程以及成败得失,有益于推进对区域与国家、自然与人多种和多重关系的深入思考。
(一)环境史视野下的“江南模式”
从环境与人互动的角度看开埠前的所谓江南区域文明模式,就是高密集地集中人力、物力、技术,“合理”地把这些因素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地从自然获取财富的典范。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利弊,是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遗产。
其“利”,如前面所讲,首先体现在区域经济收益、社会安定上
邹逸麟在为冯贤亮的专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写的“序”中提到:“江南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持续发展繁荣?明清以来不少明智之士指出,江南地区赋税最重,为什么未能成为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正是本书所要解决的课题。”,[65]1-3,即持续性的“富”——造就了江南城乡相对持续性的和平发展和理性平和的精神、文化氛围,这既有利于“民生”,又有益于“国计”。其次还体现在人为环境的美上,无数关于江南农耕社会里田园美丽风光的诗文,映射人与自然——尽管是人化的自然——之良性互动,即借助于合理的水利技术与精细化的生态循环技术,人为地营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江南风貌[83]。这种特色鲜明的江南区域生态文明模式彰显出,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单位里,通过农业与水利作用于自然可以起到积极的效应。
其“弊”,长期来看,主要是环境因长期人为开发而持续恶化所带来的自然与社会难题。首先,在田园版风光的表象下,优越的原生自然条件丧失,导致生态结构的一次次失衡。生物多样性被单一化取代,自然界自身新陈代谢的韧力趋弱,抗拒天灾人祸的能力下降,需要不断增加人为投入以补阙挂漏——甚或越修越脆弱[84]。其次,环境的脆性也加剧了社会——生产、生活及组织——的脆性,不断地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困难
伊懋可夸张地用了“三千年不可持续发展”这个看似“悖论”的措辞,旨在强调中国历史上从日益损耗的环境获取生活与生产资料的难度越来越高,直至逼近前工业阶段技术所能及的临界点。 ,[85]。
王建革认为,宋代农业发展的生态还算平衡,但元明清时期衰退了。“传统时期的战争破坏并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避免的崩溃,真正的损害更多源于和平时期的愚昧,鉴湖消失,吴江成陆,黄埔改道,都是过度开发引起的变化”[86-87]。这种历史教训凸显了人为因素干涉自然的适度性的問题。
(二)如何超越“经济发展—环境衰退”的因果研究公式?
“经济发展—环境衰退”几乎是环境史学家评析人类开发自然界的一个经典公式,不免有简单之嫌。前面所讲的江南开发的利与弊,不能孤立地被评估,而应超越江南区域,置入历史进程中,在中华帝国的版图里展开整体性的检视。
1.从全国范围的环境变化与后果观察
从历史上看,中国东部的开发沿循了由北向南的序列,即在华北(中国北方,包括中原)、江南、华南次第展开。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先后被垦殖为鱼米之乡,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土地等自然资源,并带动了区域商品化和城市化。总之,东部得到高度开发,经济发展,人口繁茂,甚至可以说东南少数发达区域的财富勉力支撑着整个国计民生。
国家严重地仰赖江南,迫使其过度开发,结果随着经济高度发展,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愈发高昂。伊懋可用“大象的退却”,马立博用“虎的消失”为象征符号,展现了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巨大牺牲。与此对应的是,被忽视的内地、西部则长期处于迟滞状态,游离于国家核心经济区的边缘地带,呈现出明显落后的发展阶段差异性。如此的发展起点,严重制约了其缓解内外压力与调和区域矛盾的应变能力[88]。故而当难以解决人口增长、生态恶化、民众生计等诸多问题时,往往成为区域性或全国性变乱的源头
如吴金成以明中期的江西社会为分析对象,认为在人口过密、经济落后、自然灾害等因素的作用下,该地民众难以为生,叛乱、寇贼现象蜂起,社会动荡不安。
,[89]。南与北、东与西两极分化的畸重畸轻格局延续至今,可以说利、弊俱存。环境史学的宏阔视野和方法有助于我们把江南、华南的历史置于超区域性语境进行理解和评估。
2.采用全帝国体系的相关政治经济分析
江南与华南在帝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区位和地位不同。与华南学派所归纳的华南“王化”路线不一样,始自六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其与北方政治权力中心休戚相关。无论是隋唐时期的大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是明清时期狭义上的江南——长江三角洲地区,虽然不是大一统政权的政治核心,却是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基本经济区”;即便在分裂时期,也是各个政治势力争夺的中心地区
冀朝鼎指出,长江流域自东晋南朝以降,明显承担着基本经济区的作用,其重要性与日俱增;自隋唐始,虽然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是长江流域已渐次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区,占据着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29]。
所以对江南的把握特别要超越江南本土的环境开发,需放入帝国的政治经济格局里,在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编程中,并在政治治乱、权力消长、王朝更替的轨迹里考稽。如,在政治一体化的大一统帝国里,“举国体制”可以动员和组织大的水利等公共工程和投资“公共产品”设施,有利于各地经济与社会的稳定运转 [56]204,212-216;但这种“仁政均衡”是以“平均主义”的方式解决区域之间的物质财富差异。再如,怎样看待江南及全国的人口问题,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劳动力短缺”,而不是过剩——因为集约需要的劳动付出高,吸引了外地劳力的迁入翰香所代表的“传统”观点更具说服力: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阶段,江南人口不仅密度冠于全国,而且受到(土地)资源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而产生大量剩余人口。
,[5]27,[90]。但是,如何宏观地、长时间跨度地、实质地看这个议题呢?在胡焕庸线以东,开埠前开发殆尽,人口压力日益增加,特别是康乾以来的“人口爆炸”,是不是陷于像伊懋可所说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乱是不是一种“马尔萨斯”式灾难
何炳棣认为中国在19世纪落入“马尔萨斯式”陷阱,并强调“当自然灾害、战争、叛乱、瘟疫的积累影响已具体化时,马尔萨斯式的限制就成为事实,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而李中清等人却把“中国人口过剩”的论调称为“马尔萨斯的神话”,他和王丰的专著旨在“挑战”和“否定”这种“神话”。该书的主题在“引言”里阐明。
,[91-92]?即看一个区域,不能漠视传统中国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帝国历史运动中特有的“周期”性循复,即增长—衰退—继续推进—失衡—重建的王朝兴亡更替,以及近现代的动乱、革命,对江南境遇和命运的左右——江南无法置身于外
关于明清之际江南遭受的毁灭性经济与社会劫难,参阅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0-478页)。
,[65]470-478,[93-94]。
另外,江南作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发达、最先进的地区,不仅在全国经济网络以及对外经济联系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而且在经济与文化领域里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被归结为 “江南道路”或“江南模式”,或可与“英格兰道路”对比,以探析中、西之间的“合流”与“分流”
王国斌认为: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斯密式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是一种“农业帝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1500年以来的“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别;他后来的这种论述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更加明晰化。他和其合作者指出:“尽管当时(19世纪)的中国已经因为人口过多而笼罩着马尔萨斯的阴影,但‘低速发展和‘停滞仍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在17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地区也都经历了以商品化为主要特征的‘斯密型增长。所以欧洲率先跻身于近代经济之列,其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经济本身,而是在于政治。欧洲于中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意外地造就了其经济上的优势。”,[56]9,225-229,[95]。而江南等东南沿海的发达没有带动传统社会的异变和突破,即便其在开埠以来的现代化成功并没有带动整个国家的成功转型,然而却推动了我们对区域与国家关系的深入思考。
(三)环境变迁中人的能动性及其限制
在人与自然互动的环境史视野下对江南区域文明形成过程和特性的分析,可以丰富我们对自身及所处的世界的经验和知识,有助于鑒往知来。
1.自然本身的极限和逻辑
在对待自然上,人类有生存和发展的逻辑诉求。千年来,江南做到了“富”且“美”;国家大体上实现了既定目标,特别在明清阶段,重赋的江南成为帝国的“基本经济区”
王家范提到这样的历史“悖论”:“江南既是‘黄宗羲定律受害最深重的地区,又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他认为江南人民是利用农、副各种手段从自然界和市场取得物质回馈;王国斌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的饥荒与人口折损应更多地归罪于社会危机,而不是真正的资源危机。”但他们忽视了两种危机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
,[56]41-42,[96]。但是,自然界并非用之不尽、取之不竭,而且特定的知识、技术、社会组织形式、政治管理体制限定了资源、能源的开掘和使用。明清江南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前现代人力所能及的自然极限:尤其是鉴于康乾以来人口的急剧增加,平原水田单位面积的产出能力近乎极致。虽然勤劳聪明的江南人民竭力从事多种经济活动,但获益也多直接或间接来自包括丘陵山地在内的土地。
另外,人力作用下的环境后果兼具可操纵和不可操纵性、可预期和不可预期性。被改变了的自然界往往潜伏着更大更多的危险,其反作用力往往表现为更为频仍、更为剧烈的灾害、疾病的“报复”,以及大自然的自我修复
许多水利事业的情形往往是越为了经济目的而“治理”,环境后果越恶劣。如王毓铨等人的研究显示:“直至终明之世,江南苏、松诸府仍是旱涝交加,灾害频繁。”,[33]231-241。
2.环境与人互动的社会制约
一个区域或地方的兴衰,固然受制于生态环境与技术手段之间的关系,但来自人类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权力的强大影响不可轻视。从江南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与人力的交织中,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国家权力、战略部署常常决定着地方经济与社会的波动,并进而制动,甚至主宰了一定时空单位内的环境嬗变。比如,王朝——国家财政对江南的过分依赖,以用于全国范围的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迫使江南竭尽一切手段和途径,不断地向自然界无节制地索取资源,所以,在大一统体制下江南繁荣维系和发展的环境和劳动代价高昂。结果,江南虽然相对于其他地区富足,但主要财富为国家与外地商帮攫掠,难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不具备量与质上扩大再生产的自主再生力[97]。
3.追求人与自然动态的和谐
即便到了今天,我们对自然与人类相互作用的关系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知,但在生存和发展的实践中如何做到“天”“地”“人”动态的 “合一”或和谐,依旧是永无休止的探索之路。江南开发与环境的旧事告诫今人:人可以有所作为,但不能为所欲为。这是富有现实关怀的环境史学给予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M].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利华.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展望[J].全球史评论,2011(1):309-325.
[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4]孙竞昊,王悦.高校历史教学中的民族与区域问题刍议[J].历史教学问题,2020(3):166-171.
[5]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M].王湘云,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六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吴宏岐.释《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谓的“江南”[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4):172,188.
[8]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9]张修桂.太湖演变的历史过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1):5-12.
[10]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23.
[11]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和研究的方法[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增刊).
[12]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4-64.
[13]王斯德,李宏图,沐涛,等.世界通史·第二编: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9-91.
[14]埃里克·琼斯.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M].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189.
[15]洪焕椿,罗仑.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6]邹逸麟.论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过程及今后发展,我国早期经济区的形成: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M]//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17]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续)[J].中国农史,2020(4):3-9.
[18]孙竞昊.浙东运河考辨:兼论宁绍平原区域水环境结构及水利形势[J].社会科学战线,2019(12):111-133,281-282.
[19]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卷8·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M].北京:中华书局,2013:222-229.
[20]陈桥驿.古代于越研究[J].民族研究,1982(1):1-7.
[21]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J].地理学报,1962(3):187-202.
[22]沈约.宋书·卷54·孔季恭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40.
[23]牟发松.从“火耕水耨”到“以沟为天”:汉唐间江南的稻作农业与水利工程考论[J].中华文史论丛,2014(1):31-68.
[24]陈金凤,赵凌飞.略论东晋南朝江南地区的陂塘建设[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9-22.
[25]余新忠.中国传统疫病应对成效探略[J].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5):42-47.
[26]邓铁涛.中国防疫史[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40-82.
[27]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73-74.
[28]李根蟠.中国农业史[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114-183.
[29]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M].朱诗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92.
[30]周魁一.农田水利史略[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60-66.
[31]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M].方健,何忠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94-195.
[32]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2:21.
[33]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4]张芳.中国传统灌溉工程及技术的传承和发展[J].中国农史,2004(1):10-17.
[35]汪家伦.明清长江中下游圩田及其防汛工程技术[J].中国农史,1991(2):92-99.
[36]庄华峰.古代江南地区圩田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3):87-94.
[37]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4[M].刻本,正德七年(1512年).
[38]过慈明.明清江南地区农家肥的商品化研究[J].巢湖学院学报,2016(5):88-93.
[39]姚光发.光绪《松江府续志》卷5[M].刻本,光绪十年(1884年):2-3.
[40]耿荫楼.国脉民天[M].区种五种本,清光绪:2.
[41]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99.
[42]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24.
[43]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中国经济通史·清[M]. 2版.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368-369.
[44]馮应榴.嘉庆·嘉兴府志·卷32[M].刻本,嘉庆六年(1801年):15.
[45]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9-16.
[46]谢湜.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J].历史地理,2007(1):111-139.
[47]刘蓟植.乾隆·安吉州志·卷8[M].刻本,乾隆十五年(1750年):35.
[48]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M].合肥:黄山书社,2006.
[49]王家范.明清江南史丛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7.
[50]洪焕椿.评刘石吉先生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J].学术月刊,1984(12):49-50.
[51]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蚕桑广类·木棉[M].陈焕良,罗文华,校.长沙:岳麓书社.2002:565.
[52]陈忠平.论明清江南农村生产的多样化发展[J].中国农史,1989(3):1-10.
[53]游修龄.中国稻作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48.
[54]胡震亨,姚士粦.天启·海盐县图经·卷4[M].刻本,天启四年(1624年):13.
[55]胡承谋.乾隆·湖州府志·卷37[M].刻本,乾隆四年(1739年):15.
[56]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M].周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57]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3-154.
[58]闵宗殿.明清时期浙江嘉湖地区的农业生态平衡[J].中国农业科学,1982(2):90-95.
[59]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21-122.
[60]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61]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2]魏丕信.中华帝国晚期国家对水利的管理[C]//陈锋.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797-798.
[63]鲁西奇,董勤.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4):31-46.
[64]赵全鹏.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活动[J].史林,1996(1):24-26.
[65]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6]范金民.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755-757.
[67]王家范.明清江南社会史散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89-190.
[68]清高宗实录·卷83·乾隆三年十二月庚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
[69]相原佳之.清朝中期的森林政策:以乾隆二十年代的植树讨论为中心[C]//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04-514.
[70]吴承明.关于传统经济的若干论述:与方行先生的通信[M]//经济史理论与实证:吴承明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99.
[71]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67-176.
[72]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09-219.
[73]孙杰,孙竞昊.江南史研究与问题意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的检讨[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39-52.
[74]ELVIN M.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298-316.
[75]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M].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76-178.
[7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M].袁翰青,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2.
[77]孙竞昊.试析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形态、特质及性质[C]//牟发松,陈江.历史时期江南的经济、文化与信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40-141.
[78]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历史时期江南的经济、文化与信仰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75-226.
[79]RICHARDS J F. The unending fronti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M].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12.
[80]李明珠.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前言[M].石涛,李军,马国英,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3.
[81]冯贤亮.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J].云南社会科学,2001(3):49-60.
[82]孙竞昊,卢俊俊.明清时期江南文化的精神旨趣及其市场动力[C]//唐力行.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七期(将刊).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83]王建革.水文、稻作、景观与江南生态文明的历史经验[J].思想战线,2017(1):156-164.
[84]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M].关永强,高丽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0,445-446.
[85]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53-355.
[86]王建革.江南环境史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586.
[87]ELVIN M.Three thousand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 [J].East Asian History,1993(6):7-46.
[88]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农耕社会环境论析[J].江海学刊,2004(4):125-130.
[89]吴金成.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M].崔荣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19-32.
[90]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M]//从翰香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4-119.
[91]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M].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01,320-321.
[92]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M].陈卫,姚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2-14.
[93]王家范.农业经济结构的历史内涵[M]//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62-204.
[94]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及相关宏观问题研究四论[C]//孙竞昊,鲍永军.江南區域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165-167.
[95]王国斌.农业帝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在当代的遗迹[C]//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57-279.
[96]王家范.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从“黄宗羲定律”说开去[M]//明清江南史三十年(1978-20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04-215.
[97]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分配结构关系探析[J].史林,1996(4):29-36.
Examination and reflection on a few significan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Jiang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UN Jinghao, LU Junjun
(Jiangnan regional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P.R. China)
Abstract:
The perspective and approach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n provide new incentives to the studies of Jiangnan regional history. The original natural settings of southeast China due to its location preliminarily conditioned the pattern and orientation of the hydraulic-initiated regional agri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n imperial Chinese history full with unification and division as well as fluctuation, the rich resource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zi Valley had manifested its increasing supremacy, leading to rising economic prominence which steadily surpassed the earlier thoroughly developed Yellow River Valley during the Age of Division, thus in contrast with the continuing political importance in the north. The late imperial era saw mature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mplex, demonstrating highest productivity in the national context, and certain pretty humanized landscape resulted from reciprocal nature-human dynamics in certain temporal & spatial continuum. Notwithstanding, the “Jiangnan way” of development noted for exploiting the earth had caused more and more negative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and furthermore its incipient “progressiveness” meant least significance in the grand unified empires politico-economic framework as well as dynastic cycles, nothing approaching the so-called “English model”.
Key words: Jiang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development; types of civilization; reflection
(责任编辑 胡志平)